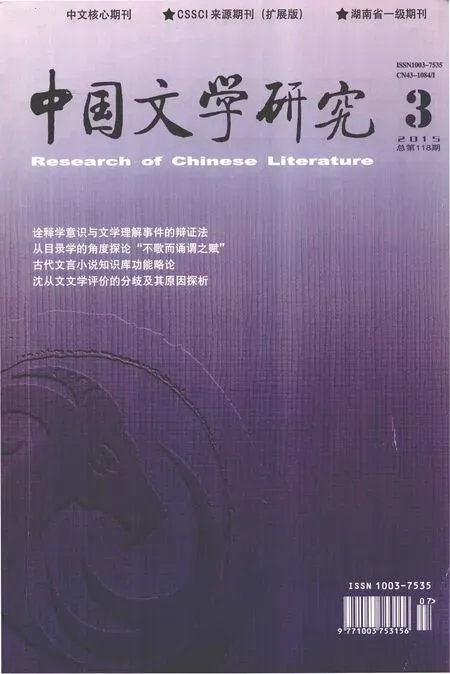《庄子》中的孔子形象与道儒之争
黄浩然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在先秦典籍之中,除《论语》以外,记述孔子言行最多的便是《庄子》。在内、外、杂共三十三篇中,或多或少涉及孔子的就有二十一篇,接近三分之二。而且,孔子在其中的形象相当丰富,不完全是被批驳的对象。这一现象足以引发一系列的思考:《庄子》中的孔子为何会有多重形象;庄子如何看待儒家学说不行于世;庄子如何评述“圣人之过”。这些,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在三种形象背后
孔子在《庄子》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其中与“原型”反差最大的便是孔子化身为道家的代言人。在不少场合中,孔子摇身一变,成为道家的一代宗师,以内篇为例:在《人间世》第一、二节中,孔子跟颜回谈“心斋”,跟叶公子高谈“游心”、“养中”;在《德充符》第一、四节中,孔子与常季交谈时言王骀“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与鲁哀公谈“才全而德不形”;在《大宗师》第七节中,孔子在谈论孟孙才时提到“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上述命题的论述自然不是出自孔子本人,他只是在代替庄子发表言论。
这种角色的孔子之所以存在,与庄子的立说方式有关——所谓“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尽管学界对寓言、重言、卮言的解释存在分歧,但一般认为“寓言、重言、卮言都是庄子虚构的故事,通过这些小故事让读者去悟出其中的哲理”。在这些虚构的故事中,庄子并没有像《齐物论》那样,以杜撰的啮缺、王倪、瞿鹊子、长梧子为主角,而是选择原本存在的孔子。其实,如果将故事中的孔子换成撰造的名字,其所要表达的哲理也不至于受到影响。但孔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通过他来表述道家的重要命题,效果就非同一般了。
孔子在《庄子》中还有一种角色与“原型”反差很大,那就是变身为道家的尊崇者。这类故事有着相对固定的叙述模式:孔子原本宣扬儒家学说,因为某位道家人物的点拨开始反思,在认识到自己的浅陋之后转而尊崇道家。致使孔子改换门庭的关键人物有好几位,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老聃,这大概与传言有关——孔子曾问礼于老聃。庄子也不管是否确有其事,将传言中的师徒名分一再坐实。
从某种程度上说,孔子的代言人角色或许还可以被杜撰的人物代替,但孔子的尊崇者角色就很难被取代了。这一角色需要经历一个转变的过程,即从儒家学说的信徒蜕变为道家学说的拥趸。因此,这一角色的承担者在儒家学派中的知名度越高,蜕变的效果就越明显,而道家学说的魅力也就越突出。庄子委孔子以重任,看中的正是孔子在儒家学派中的绝对地位。
除上述两种角色以外,孔子在《庄子》中还扮演着第三种角色——儒家的卫道士。孔子的这一形象与其“原型”最为接近,以《盗跖》为例:当孔子得知柳下季之弟盗跖为祸天下时,他以“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批评友人未能尽为兄之责;当孔子不顾个人安危面见盗跖时,他以“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的“圣人才士之行”奉劝盗跖。面对这样的孔子,盗跖以道家学说加以全面驳斥,最后使其“目茫然无见,色若死灰”。
孔子的卫道士形象自然也与《庄子》的立说方式有关,毕竟孔子与盗跖之间的对话是杜撰出来的,而这又反映了道儒之间的直接交锋。相对于前一角色中略显符号化的儒者形象——“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孔子在这一角色中的儒者形象变得丰满起来——他在面对柳下季和盗跖时就充分阐述了儒家学说。不过这是庄子有意为之的,其目的在于为批判儒家学说提供对立面。而等待这位儒者的,将是道家毫无顾忌的攻驳。
因此,无论孔子在《庄子》中扮演何种角色,其赖以存在的背景都是儒家的,只不过这种背景会因为角色的不同或隐或显,而这也正是孔子备受“倚重”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在三种形象背后的,是争执不下的道儒两家学说。
借用《天道》中尧的话来说,道家追求的是“天之合”,儒家追求的是“人之合”。《论语》中子贡的话可作为印证:“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此,钱穆先生以为:“孔子之教,本于人心以达人道,然学者常教由心以及性,由人以及天,而孔子终不深言及此。”孔子这种孜孜以求人道、终不深言天道的学说,被庄子视作“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而在庄子批评旁道、光大正道的努力中,孔子的三种形象应运而生。
二、儒家学说不行于世的道家视角
在借用孔子虚构故事时,庄子多次提及孔子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之事:《山木》第五节提到孔子“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第七节又提到“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盗跖》第一节提及孔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不过,庄子并没有仅仅把眼光放在孔子的狼狈遭遇上,他还从道家的视角对儒家学说为何不行于世进行过一番剖析。
首先,庄子认为孔子不明“古今之异”。在《论语·阳货》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的政治理想:“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尽管学界对于“吾其为东周乎”的解释尚无定论,但钱穆先生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兴周道于东方”。而庄子对此并不认同:“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暂不论将周鲁之别等同于舟车之别是否有夸大之嫌,但庄子所指出的“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确有其不可废之处。与之相近的观点在诸子(尤其是法家)中并不鲜见:韩非子认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吕氏春秋》认为“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故择(一作‘释’,弃也)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法家“出于理官”,讲求实用,而这恐怕是孔子学说确实欠缺的。
其次,庄子认为孔子不知“仁义多责”。按照庄子的理念,在“无义战”的时代,孔子所应做的只是保全自己,“仅免刑焉”。然而,孔子却在乱世危局之中四处宣扬儒家学说,“临人以徳”。这在庄子看来是非常危险的:在《人间世》第一节中,庄子借孔子提醒颜回“强以仁义绳墨之言炫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而“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为人菑夫”;在《山木》第四节中,“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吊之”,并帮助孔子分析其中的原因,“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换言之,当有道之人身处无道之际,遭受责难也就不可避免了。
再次,庄子认为孔子不明“自正”之理。对于孔子的“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并不以为然:“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离位而乱莫大焉。官治其职,人处其事,乃无所陵。”成玄英疏云:“夫人伦之事,抑乃多端,切要而言,无过此四者。若四者守位,乃政教盛美,若上下相冒,则乱莫大焉。是以百官各司其职,庶人自忧其务,不相陵乱,斯不易之道者也。”反观孔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势,而下无大臣职事之官,而擅饰礼乐,选人伦,以化齐民,不泰多事乎”。不过,“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孔氏之所为,或许正是其分内之事。
庄子不时提及孔子宣扬儒家学说失败后的狼狈遭遇,并对其为何不行于世从道家视角加以分析,目的在于指明儒家学说的必不可行之处,其中所包含的对道儒两家的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其实,旁观者或许清,当局者也未必迷。对于庄子所指出的种种,孔子不可能丝毫不知,但他却“知其不可而为之”,非凡的人格魅力令人感佩。
三、圣人之过
庄子对儒家学说不行于世进行分析,最多只能算作他者的冷眼旁观,庄子本人以及庄子所代表的道家学派从根本上是不认同儒家学说的,这一点在讨论有关“圣人之过”的问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道儒两家的学说中都存在“圣人”,但所指迥异。庄子在解释何为“圣人”时,以“尧让天下”而许由拒绝为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尧却是儒家话语中的圣人,所谓“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庄子对尧舜这些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很是不屑:“是其(姑射山之神人)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之所以如此“诋訾”圣人,是因为庄子深悉“圣人之过”:“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悬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所以说,令孔子念兹在兹的仁义,在《庄子》中反倒成了圣人的罪证。
其实,庄子学说中也有关于“仁义”的论述:“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成玄英疏云:“端直其心,不为邪恶,岂识裁非之义!率乎天理,更相亲附,宁知偏爱之仁者也!”庄子还提出过“大仁不仁”,以为“五者(大道、大辩、大仁、大廉、大勇)无弃而几向方矣”。陈鼓应先生解释为“大仁是没有偏爱的”,并认为它“和《老子》第五章的‘天地不仁’及《庚桑楚》‘至仁无亲’同义”。简言之,庄子所认同的,是上古时代那种自然而然的、发自内心的“仁义”。而儒家的仁义并非如此,“仁可为也,义可亏也”。庄子深知两种仁义的根本区别,因而对儒家仁义所带来的后果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对于个体而言,儒家的仁义是有害无益的。《在宥》第二节指出“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大宗师》第八节批判尧黥人以仁义、劓人以是非,让人难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途”。在前一个故事中,尧舜是仁义的信奉者,他们践行仁义的过程也是损害自己身体的过程;在后一个故事中,尧仍是仁义的信奉者,他劝人施行仁义而明辨是非,使人受仁义的束缚而丧失精神自由的可能。庄子似乎在通过这两个故事告诫世人:在儒家仁义的大纛下,无论是主动践行者,还是被动施行者,其身体和精神都会被仁义捆绑,不复自由自在。
推而广之,这种仁义不单于个体不利,更于天下不利:“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丽不以胶漆,约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与庄子倡导的仁义不同,儒家宣扬的仁义如同“胶漆纆索”一般施加在道德之间,“此失其常然也”,“使天下惑”。庄子不禁反问:“有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
其实,儒家奉行尧舜式的仁义,最多导致“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并不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可如果仁义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那情况就非常糟糕了:“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庄子也分析过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另一方面,“爱利出乎仁义,捐仁义者寡,利仁义者众”,而“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夫禽贪者器”。
庄子据此断言,如果大盗、诸侯窃取仁义、利用仁义的情况得不到改变,那么“仁义之慝”就会遍布天下,而“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若究“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
尽管“人与人相食”的论调稍显耸人听闻,但不幸的是,庄子所担心的情景在历史中不断上演。能够从当下的学说预见千世之后的局面,也展现出庄子令人叹服的预见力。不过,庄子将责任归咎于圣人,却值得商榷。儒家宣扬的仁义在后世为奸慝盗用,甚至于导致“人与人相食”的悲剧,都绝非儒家的初衷,而其间的复杂联系,亦远非“圣人之过”四字所能概括。
四、结 论
先秦诸子著作中时常出现其他诸子,他们见诸笔端时的面貌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仍能体现其原本的形象和思想,《荀子·非十二子》和《韩非子·显学》在提及其他诸子时即是如此。与之相比,《庄子》中出现孔子的情形就显得很不一般了:从儒家的卫道士到道家的尊崇者,再到道家的代言人,孔子的形象与其本来的面貌渐行渐远,甚至彻底背离。在探究这个问题时,既要考虑到庄子独有的立说方式——寓言、重言、卮言,更要考虑到庄子潜在的论争动机——以道家学说全面压倒儒家学说。同样的,庄子对儒家学说为何不行于世以及圣人之过所作的讨论,也应视作道儒论争的组成部分。
在这场论争中,庄子对于儒家学说所发表的洞见让人印象深刻,但“辩也者,有不见也”,其中的论述肯定也有不到之处,毕竟庄子通晓的是道家精义,毕竟其中还夹杂着门户之见。而无论是洞见还是不见,都可以成为后人探究道儒两家学说的重要基石。
〔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张采民.忘筌·梦蝶——庄学综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
〔3〕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
〔4〕《韩非子》校注组编写,周勋初修订.韩非子校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5〕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