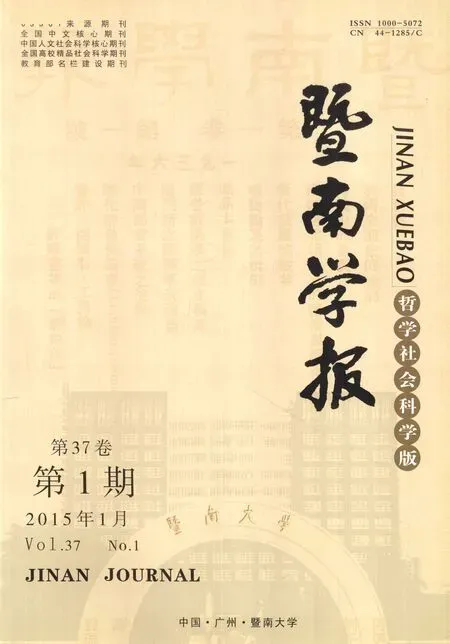论罗马法中信托担保的结构和保护模式
史志磊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引 言
信托担保(fiducial cum creditors)在罗马法学发达的古典时期是非常盛行的债权担保制度。该制度至少得到了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彭波尼、马尔切勒、尤里安等古典法学家的关注和研究,并且该制度在当时银行业务中的适用已经相当广泛且成熟。但是在优士丁尼进行大规模法典编纂时它已经消亡,因此表面上在《学说汇纂》中并没有以信托担保为论述对象的片段,在没有被收入《学说汇纂》的法学著作和其他类型的史料中也没有关于该制度的专门论述,有关该制度的历史文献具有碎片性和模糊性,但是学者对《学说汇纂》研究的深入和考古工作的开展为法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资源。依据这些资料,西方学者对信托担保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在时间上形成了两次研究高潮,分别出现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和20 世纪末21 世纪初。可以说本文是世界范围内的第二次研究高潮在中国的延续。本文的着力点在于依据原始史料对信托担保制度的结构和保护模式展开讨论,达到在讨论信托担保制度的现代运用之前形成对罗马法中信托担保的清晰认识之目的。
一、信托担保的结构
完整的信托担保制度由三部分构成,转让信托财产的行为、彰显当事人转让财产目的的信托简约和信托财产的拍卖,其中前两个要素在信托担保制度中是必然要发生的要素,最后一个要素只有在信托债务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不履行债务的条件成就时才可能发生。
(一)信托担保的设立方式
在我国学术界,对在信托担保制度中通过要式买卖或者拟诉弃权的方式转让信托财产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对结论的证成缺乏对相关史料的征引和讨论。
Gai.2,59 ……如果某人以信托的名义采用要式买卖或拟诉弃权的方式将物转让给另一人……
圣依西多禄,《词源》,5,25,23
信托是为获得现金消费借贷而以要式买卖或者拟诉弃权的方式转让物。
上述两个片段明确指出了信托担保可以通过要式买卖或者拟诉弃权的方式移转担保财产,但并不是所有的相关史料都是如此。
波埃修斯,《西塞罗〈地方论〉评注》,4,10,41
接受信托的人,即以要式买卖的方式获得某物的人,需要以同样的方式返还信托物。……
同时,只提到要式买卖一种方式的原始文献资料还有《贝提卡铜板》和《庞培要式买卖》,原始文献资料的冲突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我认为,波埃修斯在《西塞罗〈地方论〉评注》中只提及设立要式买卖一种方式与著作的论题有关,波埃修斯的目的在于对西塞罗《地方论》进行评注,解释清楚《地方论》的内容即可。因此对于西塞罗《地方论》中涉及的信托,波埃修斯的目的在于说明何谓信托,这种说明甚至可以是例示性的,而不在于对信托进行全面的描述。至于西塞罗在《地方论》中是否只涉及要式买卖一种方式,已不可考。生活在公元5 世纪末6 世纪初的波埃修斯离信托担保盛行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两个世纪,因此在准确性的程度上无法与记述作者生活于其中的盖尤斯相媲美。因为盖尤斯生活在帝国东部的亚细亚行省,这是否意味着在罗马市民法中设立信托担保的方式只有要式买卖,拟诉弃权只是在行省中适用的设立方式?因为盖尤斯生活在行省,所以将行省的法律写进了他的著作之中。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拟诉弃权不仅可以在行省实施,也可以在罗马实施,只是在行省,在总督面前实施,在罗马,在国家的执法官比如裁判官面前实施。正是因为拟诉弃权可以作为设立信托担保的一种方式,才使得信托担保也可以适用于略式物。
贝提卡铜板和庞培要式买卖记载的信托担保行为是具体的个案还是如同程式一般具有通用性?学界对于后者的个案性没有争议,前者并不被认为是具体的个案。原因在于,首先文本中使用的人名明显是虚构的,卢丘斯·提丘斯(Lucius Titius)、卡丘斯·塞尤斯(Caus Seius)以及奴隶的名字达玛(Dama)和米达斯(Midas)都是非常普遍的名字,犹如汉语中经常出现的“张三”、“李四”一般。其次,虽然文本是在位于今天西班牙的古罗马的贝提卡行省发现的,但是文本中涉及的地名巴亚(Baianus)位于意大利半岛的坎帕尼亚地区。蒙森认为该文本可能出自一位被邀请来分号开展业务的钱庄的管理者之手。如果该文本在贝提卡行省偶然被发现的事实不那么重要,那么就可以合理地推断因为赋予书面记载以较强的证明力,相似的情形也在罗马的其他地区盛行,一旦有适用信托担保制度的需求,就可以很方便地诉诸它,这与电信公司提供的消费者只需签字就可以缔结的格式合同具有相同的道理。因此,虽然贝提卡铜板记载的不是一次具体的个案行为,但也仅仅能够证明要式买卖对于当时的钱庄来说是比较喜欢采用的一种担保方式,这不仅与要式买卖不用诉诸官员而较为简捷之外,还与要式物的价值较大且不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价值损耗有关。
需要注意的是,在罗马法中,除地役权外,通过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所移转的所有权是不受限制的所有权,不能附加条件或者期限。
交付是否为设立信托担保的方式?传统的论证逻辑是价值导向的,即因为在信托担保中缺乏某些要素,使交付不能有效地运转。
D.41,1,31pr. 保罗《告示评注》第31 卷
单纯交付永远不会使所有权转移;若先有出卖或其他正当原因而后据此交付,则会使所有权转移。
从保罗的论述可以看出交付需要正当原因,否则交付不能使所有权发生转移。因为在信托担保制度中,信托简约不能构成一个有效的正当原因,因此交付不能成为信托担保的设立方式。因为要式买卖是一个抽象的不需要正当原因的转移所有权的行为,因此信托担保可以通过要式买卖设立。然而要式买卖并非一开始就是抽象的买卖行为,原初的要式买卖也是具体的需要正当原因的行为,因此上述观点的合理推论就是在要式买卖演变为抽象的买卖行为之前不存在信托担保,也就是信托担保是一个相对晚近的制度。这与信托担保是一个原始的制度,并且可能产生于市民社会之前的事实相矛盾。因此合理的解释是交付之所以不是设立信托担保的方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历史问题,也就是交付从来没有被用来设立过信托担保制度。
(二)时效收回与出卖权
Gai.2,59 目前,在另一些情况下,知情者仍可以取得他人的物品。实际上,如果某人以信托的名义采用要式买卖或者拟诉弃权的方式将物转让给另一人,当他占有此物时,可以实行一年期的时效取得,这显然包括与土地有关的物。这种时效取得被称为时效收回,因为我们通过时效取得了我们曾经拥有的物品。
Gai.2,60 然而,信托关系或者是与质押债权人建立的,或者是与能够安全地保管我们物品的朋友建立的。如果信托关系是与朋友建立的,显然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实行时效收回,如果是与债权人建立的,在债务清偿后均可实行时效收回;如果债务尚未清偿,只有当债务人不是从债权人那里租用该物,也不是要求债权人允许他暂时占有该物时,才能实行时效收回。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实行获利性时效取得。
透过盖尤斯的报道,时效收回的积极构成要件包括占有和一定时间的经过,消极构成要件是在信托担保中信托债务人不是通过租赁或者容假占有的途径获得占有。但对时效取得来说,根据中世纪法学家的概括包括5 大要件:标的的适格、名义或原因、主观诚信、占有和一定时间的经过,主观诚信成为罗马法中时效取得的要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十二表法》中并无主观诚信的要件。与时效取得相比,时效收回的要求甚为宽松。第一,时效收回不以诚信为要件,申言之,除了在信托担保中,排除租赁占有和容假占有的时效收回效力外,法律对时效收回权利人如何获得占有并没有要求。第二,不管是土地还是其他物件的占有期限都是1 年,与《十二表法》第6 表第3条“土地的时效取得和追夺担保为期2 年,所有其他的物件时效取得为期1 年”的规定不同,对土地及与土地有关的物在期限的要求上打了一半的折扣。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法律在时效收回的制度设计上偏袒了信托债务人的利益,不过与信托担保制度为获得担保债权的目的而将超过目的的利益授予信托债权人相比,法律以这种方式平衡了双方的利益。但是法律的这种平衡手段使信托债权人的所有权时刻都处于危险之中,除非他向信托债务人设立租赁和容假占有,一旦信托债务人以各种方式获得信托财产的占有,且在债务履行期间届满时不向信托债权人偿债,信托债权人除了诉诸诉讼程序要求偿债之外,没有别的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虽然在形式上信托担保制度偏袒了信托债权人,但在现实生活中,信托债务人往往能够获得较大的利益。
当事人对这种实际的利益失衡诉诸信托简约来平衡。众所周知,在信托担保制度的初始阶段,若信托债务人到期不偿还担保债务,信托债权人有权没收信托财产(lex commissoria),但这通常不利于信托债务人,人们逐渐在信托简约中约定信托债权人只能出卖信托财产,然后以价金满足其债权。这在贝提卡铜板中得到了证实,然而信托债权人的出卖权还承担着其他的功能。贝提卡铜板中记载的信托简约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双方约定信托担保持续到信托债务人完全偿还债务为止;第二,如果信托债务人或其继承人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履行债务,信托债权人可以在他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出卖被信托的土地和奴隶或者信托财产的一部分,并以出卖的价金满足债权;第三,如果信托债权人出卖了信托财产,他不必违背其意志地通过微价要式买卖(mancipatio nummo uno)的方式返还信托财产,也不必为购买人承担追夺担保责任。毫无疑问,第一点和第三点都是有利于信托债权人的,第二点也具有同样的功能,因为信托债权人可以在他选定的时间和地点出卖信托财产,以消灭信托债务人实施时效收回的可能性,否则,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后信托债务人在未履行债务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实施时效收回,如此就将信托债权人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有可能遭到侵害的时间得到了限缩,若他以租赁和容假占有的方式让信托债务人继续占有信托财产,则信托债权人的所有权遭到损害的可能性被压缩为零。彭波尼在《萨宾评注》第35 卷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如果信托简约约定债权人可以自由地出卖信托物,即使债务人已经无偿债能力,债权人仍不得被强迫出卖信托物,因为这涉及你的利益。……”(D.13,7,6pr.)虽然在优士丁尼《学说汇纂》中该片段论述的内容为质押中的出卖权,根据勒内尔的观点,本片段的原始内容应该是涉及信托担保制度的。
(三)信托担保与罗马法中非转移所有权的担保
在罗马法原始文献中,pignus 指除了信托担保之外的各种物的担保形式,既指移转担保物占有的担保,也指不移转担保物占有的物保形式。与信托担保相比,其不涉及担保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因此本文将pignus 翻译为非转移所有权的担保。转移标的物占有但不转移所有权的担保被称为狭义的非转移所有权的担保,即pignus datum,也即后世质押制度的前身;早期罗马人既不转移标的物占有,也不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物保形式称为pignus conventum(协议质押),它出现的时间在质押之后,大约公元前2 世纪初,在土地租赁关系中,佃农将其带进土地的农具质押给出租人以担保土地的租金,但是若转移农具的占有,佃农将无法正常劳作,土地出租人也将因收不到租金而受损害,因此他们达成协议,由佃户继续占有农具,当佃户到期不缴纳土地的租金时,出租人将获得农具的占有。后来这种担保关系也适用于房客。但是在赛尔维令状之前,出租人在承租人不缴纳租金的情况下取得占有并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可以这样描述二者的关系,在协议质押产生之前,非转移所有权的担保与质押是同一概念,在协议质押产生之后,非转移所有权的担保成为质押和协议质押的上位概念,也就是说,尽管两种担保方式在占有模式上存在区别,但罗马人并不认为它们存在本质的区别。塞维鲁时期,在与希腊人的贸易中,基于功能和法律结构上的相似性,罗马人开始使用希腊地方法中的hypotheca(抵押)来指称协议质押,并且有时将其与不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但转移占有的质押对立起来(D.13,7,9,2)。这种使用希腊式表达的风气在后古典时期更盛。在《学说汇纂》中收录的古典时期罗马法学家的著作在词语使用上并没有严格区分不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但转移占有的担保和既不转移标的物所有权又不转移占有的担保,hypotheca 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指称不转移占有的担保,但在个别情况下是转移占有的质押和不转移占有协议质押的统称,与原初的pignus 同义(D.20,1,5,1。pignus 与hypotheca 只有名称上的区别),但是也存在使用pignus 来指称不转移占有的担保形式的情况(D.13,7,35,1。pignus 只需要向债权人转移担保财产的占有,所有权依然属于债务人,然而,后者可以通过容假占有或者租赁的方式继续使用他自己的财产)。这可能是《学说汇纂》的编纂者添加的结果,但这造成了后世学者在研究罗马法中的实物担保制度时在术语理解上的困惑。若想彻底弄清楚各个法律术语的所指和意义,以及每个片段的原指是什么,需要对每一个片段都进行认真的评注研究,这是一项浩瀚的过程,这不是本文的论述重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罗马法中的质押和抵押与动产和不动产的区分不存在对应关系,这与大陆法系的近代民法理论不同。
然而,在后古典时期信托担保是否与非转移所有权的担保趋同,也就是说信托担保也不需要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这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领域。19 世纪末,美国比较法大家威格摩尔写了一篇题为“担保的理念:法律理念的比较研究”的雄文,文中对犹太法、伊斯兰法、埃及法、迦勒底法(Chaldean)、斯拉夫法、印度法、日本法、希腊法和罗马法中的担保现象进行了比较研究,概括出了人类担保理念的一般发展规律,从时间顺序来看,其中最早出现的担保模式用罗马法的术语表示就为非移转所有权的担保(pignus),该模式还可以细分为债权人占有担保物和债务人占有担保物两种模式,第二种模式为出卖—买回(the Sale for Purchase),作者把罗马法中的信托担保归入这种模式,当然威格摩尔还把活质(vifgage)作为第三种模式。尽管把罗马法中的信托担保归入出卖—买回的模式之中是值得讨论,并且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威氏三模式论并不适用于罗马法中实物担保的发展史。
威氏在其文章的第三部分谈到罗马法中信托担保的命运时写到,信托担保在优士丁尼的时代,甚至在此之后依然存在,在优士丁尼《学说汇纂》和《法典》中没有出现信托担保的原因是特里波尼安及其助手在他们所收集的涉及信托担保的片段中,将fiducia 篡改为他们比较熟悉的hypotheca。他的理由是:第一,法律上和实务上信托担保和抵押都是相通的,因此名称的改变不影响制度的运行。在古典时期随着罗马帝国经济的繁荣,设立方式烦琐的信托担保不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被抛弃,此后罗马法学家讨论的信托担保已经与以前的信托担保不同,信托担保发生了异化,此时非转移所有权的担保的规则适用于信托担保。在优士丁尼时期,作为非转移所有权的担保方式之一的抵押主要适用于土地等不动产,在适用对象上与信托担保相同。威氏甚至断言信托担保的设立方式此时已不需要要式买卖或者拟诉弃权,简单的交付(traditio)就已足够。第二,当时发现的一些非通过《民法大全》流传下来的法学著作中只出现了pignus 和fiducia 两种担保方式,例如盖尤斯《法学阶梯》、保罗《判决集》以及《梵蒂冈残篇》中都是如此,但是在《学说汇纂》中收录的盖尤斯和保罗的著作中只出现了pignus 和hypotheca 两种担保方式,最关键的是同一个作者的同一个片段在不同的著作中有不同的版本,例如《保罗判决集》PS.2,17,15 中以“pignora vel fiducias”概括所有的实物担保制度,但是同一个片段在《学说汇纂》中被改为“pignus vel hypotheca”(D.20,6,11),如此就得出了fiducia 被篡改为hypotheca 的结论。可惜的是威氏并没有注意到勒内尔在8 年前发表的《市民法还原》一书,否则他至少应该修正他的结论,得出保存在《学说汇纂》中的古典法学家讨论信托担保的片段被篡改为讨论质押或者抵押的片段,也就是说是用pignus 或者hypotheca 篡改了fiducia,而不只是hypotheca。
勒内尔的研究成果发表后,罗马法研究者对于特里波尼安及其助手在编纂《学说汇纂》时将某些原初讨论信托担保的片段篡改为讨论质押的片段已没有争议,威氏的研究成果丰富了对于信托担保被篡改的研究。这种篡改是否意味着当时的编纂者认为信托担保和非转移所有权的担保在法律上是相似的或者在法律实践中它们已经趋于雷同?若信托担保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异,变异是何时发生的?是否如威氏所言变异在古典时期就已经发生?通说认为信托担保在古典时期仍然保持着其本来的法律结构,因为这一时期作为信托担保法律制度基础的要式买卖、拟诉弃权和时效收回依然是现行有效的法律制度。信托担保是随着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的消亡而消亡的。信托担保不能通过交付而设立,至少现在没有发现通过交付设立信托担保的原始文献,关于这一点前文已做了详细的讨论。但是在后古典时期信托担保是否发生了威氏所言的变异?争议甚大,克罗地亚学者卡洛维奇博士(Tomislav Karlovi∫)认为信托担保直到公元4 世纪末和5 世纪初从法律实践中消失,一直保持着其本来的法律结构,没有发生变异。但是布尔兑赛意识到《西哥特罗马法》的编纂者有意识地将信托担保融合进非转移所有权的担保之中。但他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最近这项工作由塞尔维亚学者西奇(Magdolna Si ˙)完成了。她的研究对象是保留下来的后古典时期及中世纪早期的法律文献和铭文资料,重点探讨了在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早期信托担保是否还意味着移转担保财产的所有权、要式买卖对信托担保的意义和信义(fides)与信托担保的关系。西奇认为尽管在西罗马的通俗法学中信托担保和非转移所有权的担保之间存在共通的规则,但是在法律文献中信托担保和非转移所有权的担保并不是同义词。信托担保制度是债务人基于债权人信义——信赖后者会很好地保管担保财产且会将财产返还给他——将财产移转给他,或者债权人基于对债务人的信义——信赖债务人会很好地保管财产且会在自己的要求下满足自己的要求——仅仅在担保财产之上设定担保负担,财产继续在债务人手中。信托担保与要式买卖的关系也变得松散,信托担保也可以通过要式买卖的变异形式——具有一定庄严性的行为(iuris solemnitas)——而设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信托担保需要移转担保财产的所有权,信托协议使信托财产的地位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即信托担保对信托财产来说只是一定期限内的负担。虽然卡洛维奇博士和西奇在观点上存在冲突,但是他们的观点都否认信托担保与非转移所有权的担保之间的一致性和趋同性。
二、信托担保的法律保护
根据现代法律观念,当事人的合意只要不违背法律、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就可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在罗马法并不是这样,即使在法律最发达的法学昌明时期,除少数诺成、要物契约和一些无名契约外,当事人如果没有履行一定的方式,仅有单纯的合意,若不另订罚金口约,债务人并不受制裁。这种缺乏形式(至少是对它不要求特定形式)而且不是根据某一债因而达成的协议被称为简约,简约不产生法律上完备的债,也不存在任何以它为根据的诉讼,信托简约也不例外。再者,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在罗马法中是移转所有权的方式,实施它们的目的在于所有权的移转,而非其他,但在信托担保中,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虽然也移转了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但所有权的移转并不是当事人追求的目的,从而构成一种脱法行为。因此通说认为古罗马法律对信托担保并不提供保护,受信托人在其债权获得满足之后是否返还信托财产取决于受信托人的信义。但随着信托担保制度适用范围的扩大和罗马社会陌生人化,法律不得不对之做出一定的反应。但法律如何做出的回应罗马法并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因此这也成为一个理论建构的领域和法学家角力的竞技场。
在罗马法中,若受信托人不按照信托简约的约定实施某种行为而损害信托人的利益,法律对信托人的保护是授予其信托之诉(actio fiduciae),放在整个信托的历史中,这当然是相当晚近的事情;若信托人不遵守信托简约的约定而损害受信托人的利益,法律授予受信托人信托反诉(actio fiduciae contraria),它的产生时间比信托之诉的产生时间更晚,已经是古典时期的事情了。然而两者在诉讼程式上无本质的区别。事实之诉(actio in factum)这一术语在罗马法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不以某一获承认并符合标准的权利或关系为基础,而是以一种既无自己的类型和名称又未获承认或以任何方式被归入市民法中的新关系为基础而提起的诉讼;同时,事实之诉这一术语也被在一种较狭窄的意义上使用,指裁判官不时地根据特殊情形所准可的诉讼,同永久告示中受保障的市民法诉讼和裁判官诉讼相对立。不管事实之诉这一术语在何种意义上使用,都是裁判官对自己享有的治权(imperium)的使用,因此事实之诉一定是裁判官法上的诉讼,在本文中事实之诉是在第一种意义上被使用的。事实上,随着事实之诉的发展和成熟,一部分上升为权利之诉(actio in ius)。信托之诉是事实之诉还是权利之诉还是经历了从事实之诉到权利之诉的演变过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从争议产生的源头即勒内尔对生活在哈德良皇帝时代的法学家尤里安编纂的《永久告示》(Edictum Perpetuum)的还原工作,及其工作成果以同样的名称为书名的著作谈起,需要说明的是,勒内尔的还原成果即其著作《永久告示》分别在1883 年、1907 年和1927 年出版了3 个版本,最后一个版本与前两个版本相比,关于信托之诉的性质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1.勒内尔的还原成果
(1)作为事实之诉的信托之诉的程式。
奥卢·阿杰里为担保债务而将讼争土地以信托要式买卖的方式转让给努梅里·内基迪,债务已经清偿或者债权以其他的方式获得满足或者债务因努梅里·内基迪的原因而得不到清偿,努梅里·内基迪没有返还讼争土地也没有实施类似的行为。他应该如同诚信的人们之间做事那样诚信而无诈欺。审判员判处努梅里·内基迪向奥卢·阿杰里支付与讼争土地价值相等的金钱,如果不是事实,则开释。
在程式诉讼中,完整的程式包括“请求原因”(demostratio)、“原告请求”(intentio)和“判决程式”(condemnatio)三个部分,而信托之诉的上述程式中,开篇说明事实,没有严格的“原告请求”,“他应该如同诚信的人们之间做事那样诚信而无诈欺”一句类似“原告请求”,但这是该程式的核心部分。接下来是授权审判员判罚或者开释的词句。因此依据该程式提出的诉讼被勒内尔成为事实之诉。
(2)作为权利之诉的信托之诉的程式。
被诉的事实是奥卢·阿杰里以信托要式买卖的方式向其债权人努梅里·内基迪转让他的奴隶斯提古(或者一块土地),努梅里·内基迪应当根据诚信向奥卢·阿杰里给予或做必要之事,审判员为奥卢·阿杰里判罚努梅里·内基迪,如果不是事实,则开释。
勒内尔做如此还原的理由为,第一,根据Gai.4,62 的报道,信托属于诚信诉讼的一种;第二,公元前2 世纪的法学家技术性地将诚信诉讼程式中“原告请求”部分形塑为“诚信所要求的”(oporter ex fide bona)标准程式,法学家们采用的归纳的逻辑,这里同样面临着归纳者是否穷尽被归纳对象的问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上述结论就面临着概念不能涵摄所有对象的危险。答案确实是否定的,妻物之诉(actio rei uxoriae)就是一个例外,妻物之诉的程式为:努梅里·内基迪应当向奥拉·阿婕莉亚返还部分妻物,他应该更加公平地返还。审判员为奥拉·阿婕莉亚判处努梅里·内基迪,如果不是事实,则开释。因此,若没有其他的论据,勒内尔还原的作为权利之诉的信托之诉的程式是危险的。事实上,勒内尔并没有坚持他的观点,20 年后在《永久告示》第三版中就放弃了第二种还原,由于语言的障碍,笔者无法确切得知勒内尔放弃的理由,但是作为勒内尔放弃第二种还原的拥护者埃尔伯在其著作中认为,勒内尔还原的权利程式之所以错误是因为程式的技术性原因,即在信托之诉的程式中没有出现诚信诉讼中出现的“依照诚信给付或做必要之事”(dare facere oportet ex fide bona)。
2.勒内尔之后的学术争论
勒内尔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在罗马法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对此意大利学者阿尔纳多·比斯卡尔迪对参与争论的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综述,他将学者们的观点分为两个派别,一派认为信托之诉先后存在事实之诉和权利之诉两种诉讼程式类型,一派认为信托之诉只存在一种诉讼程式。其中后一派学者又可以分为持信托之诉是事实之诉和持信托之诉是权利之诉两组。
属于第一派的学者虽然在观点上存在些许差别,但都认为信托之诉的历史与使用借贷和寄托诉讼的历史相似,根据Gai.4,47 的报道,后两者存在事实之诉和权利之诉两种诉讼程式类型,并且事实之诉在信托关系的保护史上具有原始性。随着法学家的努力和信托关系的完善,信托关系经历了从裁判官法上的关系到市民法上的关系之性质变迁,裁判官因势创设了权利之诉的程式,并且随着权利之诉程式的出现,事实之诉的程式逐渐消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但不限于1927 年之前的德国学者勒内尔、保罗·约尔特曼、汉斯·克雷勒(Hans Kreller)和意大利学者卡罗·隆戈、彭梵得。
如上文所述,属于第二派别中持信托之诉是事实之诉言论的学者首先是1927 年以后的勒内尔,以及他的支持者埃尔伯。然而持论者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盖尤斯将信托之诉归类于诚信诉讼的范畴,而诚信诉讼都是权利之诉,事实上,持论者之所以有此论断的原因在于对诚信诉讼的标准程式“诚信所要求的”过分信赖。阿兰乔·鲁伊兹认为这种过分信赖是错误的,在罗马法中保护信托关系的唯一程式是权利之诉,而在程式中究竟是“诚信所要求的”还是“他应该如同诚信的人们之间做事那样诚信而无诈欺”并不改变信托之诉的本质。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意大利学者乔万尼·罗冬蒂(Giovanni Rotondi)和德·法兰齐西(De Francisci)。
根据Cic.〈De off.〉3,17 和Gai.4,62 的报道,信托之诉属于诚信裁断(arbitria bonae fidei)或者诚信诉讼(iudicia bonae fidei)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对诚信诉讼的发生史进行一番考察对揭开信托之诉性质的谜团是有益的。
3.诚信诉讼的发生史与信托之诉的性质
如同考察其他制度的起源一样,诚信诉讼的起源是模糊的。虽然一些原始文献可以将诚信诉讼追溯至一定的历史时期,但若进一步研究它的起源,则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推测的因素。
毫无疑问,与市民法诉讼相比,诚信诉讼是缺乏法律基础的,Cic.〈De off.〉,3,15,61“对于没有明确法规惩罚的罪行已判决惩处,在这些判决中特别补充说明‘按诚信’(sine lege iudiciis,in quibus additur ex fide bona)”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诚信诉讼的法律基础需要诉诸裁判官的治权是有疑问的。
罗马早期的社会规范体系呈现出“两层楼式”的结构,上面一层表现为法(ius),违反法受到拥有特殊程序的法律诉讼的追究;下面一层表现为信义(fides)或者公平(aequom bonum),它们处于法律之外,对它们的违反在实践中通过私人裁断(arbitrati privati)来纠正,Cic.〈De off.〉3,17,70 佐证了该论断,其辞曰“大祭司昆图斯·谢沃拉曾说过,那些补充有‘诚信’的裁断具有最高的效力,并且认为‘诚信’这一词语使用得非常广。它用于监护、合伙、信托、委托、购买、出卖、承包、租赁以及社会生活涉及的其他各个方面”。市民法对信义的接纳通过将私人裁断纳入市民法诉讼而完成。事实上,这是市民法对信义的第二次接纳,第一次发生在《十二表法》时期,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市民法诉讼对诚信诉讼的接纳之关键在裁判官的治权。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诚信诉讼具有了荣誉法诉讼的性质,因为裁判官的权力只限于根据法学家的意见接纳和承认已经在市民之间存在的具有市民法性质的诉讼形式。这个观点也得到了路易吉·伦巴尔迪(Luigi Lombardi)的支持,他认为诚信诉讼来源于罗马人之间的建立在信义之上的关系,比如监护关系、信托关系、合伙关系和委托关系,这些关系在当事人之间建立可诉诸道德的义务。那么如果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就需要诉诸一个客观的超越双方当事人的标准。同时,他认为诚信诉讼的程式来源于私人裁断的实践,随着这些程式在实践中被固化且具有了普遍性,裁判官就接纳它们为市民法上的诉讼。虽然诚信诉讼具有市民法诉讼的性格,但它并不建立在法律之上,它立足于根据信义可以要求当时做某种行为的社会观念和罗马法律传统。
Gai.4,10 此外,有些诉讼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形成的,有些诉讼是根据其自身的效力和权力而成立的。……
盖尤斯在此把市民法上的诉讼分为根据法律规定形成的(quae ad legis actionem exprimuntur)和根据自身的效力和权力而成立的(quae sua vi ac potestate constant)两个类型。接下来Gai.4,11 -31讨论了根据法律形成的诉讼,其中Gai.4,30 讨论了根据法律形成的诉讼的衰落,这些诉讼都是拟制的诉讼,因为诉讼的程式要符合相关法定言辞。Gai.4,33 讨论了不需要拟制的诉讼,即根据自身的效力和权力成立的诉讼,首先是请求返还之诉(leges action per condictionem),接着盖尤斯指出使用借贷之诉、信托之诉、无因管理之诉和“其他无数诉讼”都具有同样的性质。哈威尔·阿帕里西奥(Javier Aparicio)认为使用借贷之诉、信托之诉和无因管理之诉都为诚信的市民法诉讼,且盖尤斯以“其它无数诉讼”指称的诉讼也是诚信的市民法诉讼,并且他将Gai.4,10 中的“效力和权力”(vi ac potestate)与Cic.〈De off.〉3,17,70 中的“最高的效力”(summa vis)对应起来。如此就解决了诚信诉讼在市民法诉讼中的归属问题,诚信诉讼属于“根据自身的效力和权力而成立的”诉讼范畴。因此,诚信诉讼并不具有荣誉法诉讼的性格,裁判官的治权在诚信诉讼的产生史上起的作用只限于“引介”的工具功能,不起决定性作用。在诉讼程式的“原告请求”部分是否出现“诚信所要求”的术语与诚信诉讼的性质毫无关系。
因此,作为诚信诉讼之一种的信托之诉只能是权利之诉,如前文所述,这并不意味着信托之诉起源于法律诉讼。该诉讼起源于依照诚信的私人裁断,它的根在罗马共同体内的习俗,基础在于信义,其程式是通过私人裁断逐渐完善的,成熟固定之后,被裁判官接纳为市民法上的诉讼。信托之诉和妻物之诉是最早的两种诚信诉讼类型,因此它们的程式也保留了原始的特点,因此“诚信所要求”的术语没有出现在它们的程式中。不能因为寄托之诉和使用借贷之诉有事实之诉和权利之诉两种诉讼程式,(Gai.4,47)而推测在信托之诉中也存在两种程式,因为寄托之诉和使用借贷之诉在成立时间上远远晚于信托之诉。
三、结 论
综上所述,笔者基本还原了罗马法中信托担保制度的面貌。在罗马法的实物担保体系中,信托担保是一种古老且独立的担保制度,随着法律的演进,它与法律的精神和其他法律制度之间逐渐出现了裂痕,并最终导致它的消亡。在古典时期,信托担保与其他制度相互配合,较好地平衡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信托债权人虽然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但是信托债务人可以使用条件极为宽松的时效收回制度对抗之,使信托债权人的所有权处于危险之中,为消除这种危险,信托债权人又可以设置容假占有和租赁抗衡,信托简约中约定的出卖权也起到了一定的抗衡作用。保护信托简约的信托之诉和信托反诉获得市民法的承认延续了罗马法中的衡平精神,信托之诉和信托反诉虽然是私法上的诉讼,但是产生的效果具有公法性。若这些制度都无法在当事人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关系,当事人可以诉诸刑事法律。但是这种衡平机制随着法律的发展逐渐被打破,重要的一点是不需要诚信的时效收回不再为人们所接受,衡平精神的流失使信托担保走进了故纸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