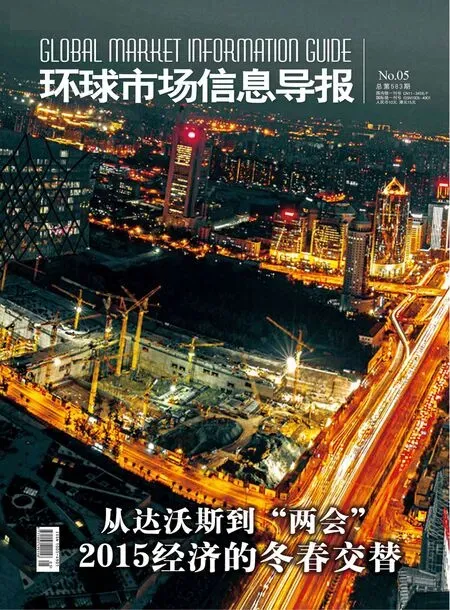最是寻常能动人
(文/马阳杨,来源:经济观察网)
Point
这些信件,不能保证读者得以进入张爱玲的心灵世界,她这样澄澈深情的灵魂,又岂是纸页上的言语所能涵括的?但我们多少能体悟她曾身临的寒意与领受的温情。
“近来我特别感到时间消逝之快,寒咝咝的。”“近来时刻觉得时间过去之快,成为经常的精神上的压迫。”“无论如何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了。”
我只摘出这三句,大概便可模拟出笼罩在张爱玲后半生命途之上的阴霾。她对时间是不信任的,因之也有了一点点犹疑、一点点悲凉、一点点焦虑。正是这“一点点”,使张爱玲的目力异于常人,继而渗入笔端,生发出那易于蹈袭却难得其真味的韵致。
张爱玲迁居美国后,生活不易,此中详情,虔诚的张学家们多有考证。可陷常人于困顿的不如意,频频光临她孤立无援的异乡生活,丧夫、多病、虫灾,难以抛就的世俗物性生活与亟待静心潜入的艺术世界,在两端撕扯着她;艺术家或可偶逢的幸运,张爱玲却往往无福尽享,费劲周折申请下一笔研究经费、又为琐事分神以致计划搁浅,在伯克利加大谋一份研究员的职位、受累于天性中的避世而难以博得主事者陈世襄的赏识,一俟首任聘期结束,她也再难立足。
以上种种,都可见诸夏志清先生细心评点辑就的书信选中,张氏的自述、杂忆以及旁人的散记、追念亦可作参差的互证。这位现代中国的天才女作家,毕竟不容于远为激进的红色中国,属于她的时代倏忽而来,又倏忽而逝。去国离乡之后,张爱玲籍籍无名,仿佛不满于她昔时的风光,生活报复性地施予其种种难堪,她自然疲于应付,生活可以用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毁掉菲茨杰拉德,可以用酒精依赖症击垮海明威,也可以用无休止的琐碎与庸常折磨张爱玲。1960年代以后,随着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问世,张爱玲的创作重获重视,声望日隆,及至晚年,读者、评论家对她的敬慕恐怕更胜当年,可惜她的房间早已容不下一张静谧无忧的书桌。张爱玲也许从未有过才华枯竭的恐惧,但漫无边际的虚空不啻于将她敏感的心掷入荒原。
蒙夏志清先生誊写并详附按语,这一百三十四封书简得以献诸普通读者,书名不作惊人语,极是朴素端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作家的一大幸事,便是有一位忠实于她的批评家,他需识见过人且能激赏其才华,又可取信于读者而作有效的绍介,有如埃兹拉·庞德之于乔伊斯,或是埃德蒙·威尔逊之于纳博科夫。受限于政治情势,1950年代末期的张爱玲早已不复往日荣光,不过十年间,她便如冰山没入海平面,成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与当代写作实践的缺席者。夏志清独具慧眼,在《小说史》中为她专辟一章,同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张天翼、钱锺书分庭抗礼,更将《金锁记》誉为中国从古以来最杰出的中篇小说,叹赏之情,可见一斑。两人的鱼雁往来自夏志清奉寄《小说史》始,终于张爱玲逝世前一年,除却张爱玲为顽疾所缠的两三年,通信鲜有中断。夏志清与张爱玲谋面不过寥寥数次,日常事宜的交流全凭这纸上言,可说是最为士子珍视的君子之交。但这不妨碍张爱玲将夏志清引为知己,下笔也自然无需遮掩,少了许多虚饰客套的陈词。她常将目下的难处和盘托出,在美生活期间的种种不顺遂,以及生计之困顿、写作之停滞,在信中都有毫无保留地直陈,细腻可感,是张学研究的第一手,也是第一流资料。
夏志清凭借《小说史》一著,揽下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成为炙手可热的汉学明星,此后笔耕不辍,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出版,已是执欧美汉学界之牛耳的大学者,稿约不断,台港报刊对他也极为重视,颇负盛名的“《联合报》文学奖”便邀其作为评委。初出茅庐或尚未扬名的作者,若获其青睐,便可进入学界的研究视域,在一般读者中也可赢得出手不凡的上佳印象。借着批评家的声誉与出版传媒界的资源,面对张的嘱托与求援,夏志清总是不吝援手、倾力相助,无论是代为接洽出版事宜,还是求索不易寻获的参考书籍,抑或是举荐作保,他都亲力亲为,张爱玲很受感动,这是一种不受利益沾染的友情。我们常在信函中读到类似的表述——“你我既是知己,我便不必言谢,但如此情谊,我仍要记一笔以慰你心”或者“在你我便不道谢了,想你不会见怪”,那份赤诚,那份纯粹,溢于言表。
国内治现代文学的学者,熟读文献资料的不少,文坛掌故、逸闻趣事皆可信手拈来,但精擅外语的不在多数,其中具有国际视野的更是寥寥。偶有兼备者,从事的都是古板的比较文学研究,所谓主题学,所谓媒介学,所谓源流、版本、流散,几无生趣,如此窘境,累叠出一幅怪诞的画面——治现代文学的,便不读外国小说,精于西洋文艺的,因为不熟悉语境,便也插手不了相关的研究。这与民国文坛的活泼生态大相径庭,彼时的名作家中,兼擅外语者不可胜数,而1920、30年代也正是欧美现代主义勃兴之时,北平、上海都是远东重镇,通衢便利,与外界通邮已非难事,若从作家个人交游的视角考量中外文学互动,想是极有趣的着力点。以张爱玲为例,她的英语极为纯熟地道,读书之余,可曾与心仪的当代西洋名家通信?前此的研究资料中,尚未得见相关考辨。倒是在这一册《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中,可揣摩出一些端倪。根据夏志清的说法,张爱玲与普利策奖得主、当时的名作家马昆德相熟,在给宋琪的一封信中,张坦言《半生缘》其实是根据马昆德的《普汉先生》所改写的,莫寄台、苏友贞分别就此写过长文加以评析,我好奇的是,张是因书得以结缘马氏,还是先有人情上的牵连、嗣后镜鉴其书以成己作呢?相关的资料尚付阙如,期待有心人循此线索,加以补白。另一位与张爱玲有交情的美国作家想必出乎读者的意料,他正是近来颇受出版社及读者追捧的不羁才子杜鲁门·卡波蒂。《怨女》的英文版印行后,恰逢英镑贬值危机,销路不佳,张便想延请几位名家过目后予以评荐,当即选的就是卡波蒂。在另一封信函中,她告诉夏志清卡波蒂并未回信作答,因为“早忘了看过《秧歌》”,我们知道《秧歌》是在香港美国新闻处的襄助下,方获发行,卡波蒂过目此书,多半是美新处请他事先审读,提出评鉴报告,既如此,张爱玲得以与卡波蒂通信,定是卡波蒂对《秧歌》大为欣赏,进而发展了私人友谊。两人都是天才型的作家,写作伊始,便是通途,卡波蒂十七岁便文名大盛,张爱玲更是早慧的典型,在此一面,他们或许多少惺惺相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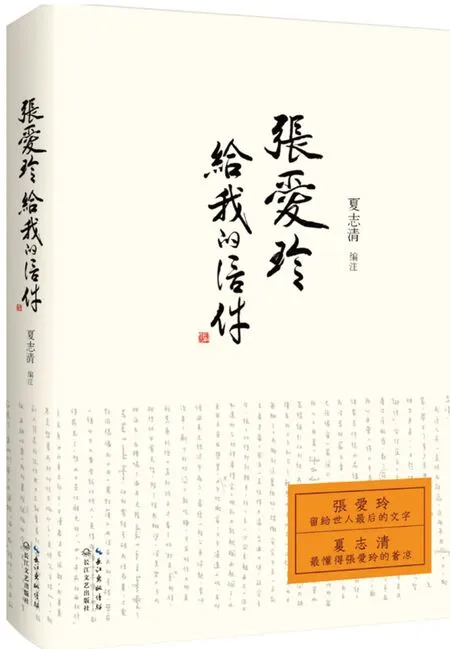
既是私人信函,两人兴味所至,免不了要臧否人物、笔涉世情,熟谙台港知识界与文艺圈的读者能从中读出不少秘辛与轶事。提及张恨水,张爱玲毫不掩饰喜爱之情,附了一句“除了济安没听见人说好,此外只有毛泽东赞他的细节观察认真”,初想,这场面极为怪异,几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再一思,却添出几分世态的吊诡来,确是饶有趣味。虽幽居不问世事,但张爱玲的眼光依旧尖利如初,未尝得减半分,从夏志清与钱锺书的合影上,她看出“他去年在意大利才知道你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跟你合摄的照片上他眼睛里有狂喜的光”,一代狂生,虽曾表示悔其少作,但遇有名家称许,自然大感得意,这种隐现的心绪,是逃不出张爱玲的眼睛的。对于后辈作家,张爱玲提得不多,唯一的例外是蒋晓云,对这位夏志清钦点的“张派”传人,张爱玲有称许、有保留,其中数篇她谦称“没看懂”,有几篇她又觉得过于显白,当然也有佳构令她动容,她丝毫没有因为夏志清的力荐而丢失自己的判断,这是迂,这是直,这更是诚与真。
晚近几年,每有张爱玲的遗著问世,便是出版界、读书人间的大事,其著作不仅畅销,而且常销,譬如《小团圆》,单是大陆,销量已在百万册之上。而她在世时,作品行销所及,不过是台港两地,虽则据信件披露,皇冠出版社予其的版税为15%,相当公道,符合大作家的身价,但销量毕竟有限,年入不过2000美金左右,而这已是张爱玲唯一的固定收入。如若大陆的版税收入能提前惠及张氏,则她的晚景绝不至于如此凄凉,以至于殁后三四日方为人发现,以她的天才,兴许又能为我们读者留下数册精美耐读的文字。
这些信件,不能保证读者得以进入张爱玲的心灵世界,她这样澄澈深情的灵魂,又岂是纸页上的言语所能涵括的?但我们多少能体悟她曾身临的寒意与领受的温情。夏志清的批评不是阿谀奉承、虚与委蛇的捧场文章,他以才情赢得张爱玲的信任,以真情赢得张爱玲的真诚,他们在纸上的相遇,演绎了一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传奇。他们因文学而邂逅,又书写了各自的诗样人生,冲淡、从容、平和,从寻常中来,往寻常中去,却道是,最是寻常能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