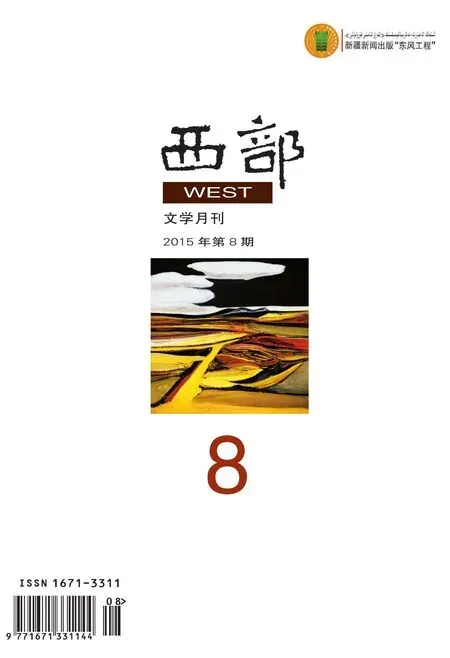一卷星辰
汗漫
打开书,就是漫漫长夜。
——杜拉斯《写作》
1
《中华经典藏书:庄子》。散文集。庄子。中华书局。
这套关于中华经典的丛书跨越时代,涉及孔、孟、老、庄、《诗经》、《离骚》……最喜欢庄子。读《庄子》,就是读先秦语言之大美。
庄子飞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如蝴蝶、鲲鹏。与山岳般静穆的孔子构成对比。早庄子一百余年的孔子,在大地上传扬修、齐、治、平的儒家真理,坐牛车,思想、语调就比云朵里的庄子低沉、缓慢许多。
庄子尤其热爱蝴蝶,就通过一个梦,混淆了自己双臂与蝶翅之间的区别。蝴蝶,就是自由,穿越种种藩篱,栩栩然,打破现象与幻象、草木山川与枕头之间的边境。“多么可爱的来世/绘在你的遗骸之上。/多么尊贵的标志/在大气的秘密中”——瑞典当代女诗人奈莉·沙克斯的这首《蝴蝶》,像是在献给庄子。
庄子尤其不喜欢讲理,就有了著名的“濠梁之辩”,与惠子辩论“庄子是否知道水中的鱼快乐”这一命题,双方逻辑推理一番之后,惠子似占上风,但庄子却跳出逻辑以一言决定胜局:“我是站在濠梁的桥上知道鱼很快乐哦!”不讲理,霸道,但抒情,对一尾鱼也怀着流水般的温存和体贴。
在《庄子》这本被争论存在伪作的书中,庄子或者说模仿庄子的某人,以寓言方式对孔子的入世思想表达不屑。孔子至死都要处于人群之中,哪怕那是一群讥讽、嘲弄、攻讦、利用着他的人。庄子却转身而去,在山水自然、梦幻寓言中建立人生路径——道。但当孔子难得流露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游于海”一类“消极意绪”,庄子就似乎在孔子身上终于捕捉到了暗通于自身的隧道尽头的大海波光——
庄子在思考“道”时,大约想到了岛、大海。在生命的汪洋中,需要一个岛,自成一体。周围有鲲,磅礴游动,突然跃出水面转化为覆海载天、垂翼乘风的大鹏。岛上,有一个做白日梦的人转化而成的蝴蝶,翩翩然——庄子善于转化。他对万物怀着感同身受的慈悲、爱。万物齐一,齐物——他感觉自己就是世界,无论鲲、鹏,还是蝴蝶、鱼,所以他逍遥,他游。读庄子,就是在长天秋水般的古典汉语中作逍遥游。
历代文章大师或许并非一概认同道家,难舍功名庙堂之心,但似乎都明明暗暗地学习庄子那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作文方式——向庄子学习写散文。向孔子学习写社论、领导讲话。庄子叙事、引征、比喻、议论、抒情“,云气空,往返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林云铭)。金圣叹曾经把《庄子》与《史记》、《离骚》、《水浒传》、《杜诗》、《西厢记》并列为六才子书,这显然是才子眼光而非志士情怀。才子书不是圣贤书,可亲近,可习摹。
但庄子说:“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这样“夜半有力者”一般的笔力才情,只能与生俱来吧?而我这样一个“昧者不知也”,在梦中大约也只在眺望若干稀薄奖金和异性,显然没有庄子的大格局,我言浅、纸矮。
关于“小大之辩”,庄子在《秋水》篇中借北海若之口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但我想,井蛙虽局限于井中,但若能说出对井口一棵青草、一朵白云的深沉情感,也动人吧?夏虫虽转瞬即逝,但它若能参悟出一场热风、一次芒种的意义,也是美妙的吧?庄子似乎热爱大、持久,但在北海若的上述言论之后,口风一转,笔锋一转:“小而不寡,大而不多”,否定数量意义上的大小差别,最终导出“万物齐一,孰短孰长”的“齐物”思想。他就是这样多变、不拘泥,所以洒脱、自在。
庄子在启发我: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自我争辩、不断转折、妥协的过程,使言辞逶迤开阔如长河、旷野。他倾心于伟大,但也迷醉于一只蝴蝶的小、短暂,这只蝴蝶于是拥有了与鲲鹏同样的力量和世界——
越过梦境和大海,到先秦以后的时代、人心里来。
2
《杜甫传》。冯至。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手中的版本是1952年的繁体版,竖排,如同纸质的杜甫纪念碑,仿佛《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即从巴峡穿巫峡”的那只小船,顺流直下,从唐朝来到我面前。
冯至在这部传记写作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是,“以杜解杜”(杜甫地位确立于死后数代,比生前已经成名的李白还要缺乏历史资料,只能通过杜甫诗作来还原杜甫),“以诗人写诗人”(从一个当代诗人内心出发来体贴一个唐代诗人的心路里程,但避免使杜甫现代化)。全书分十二章:“家世与出身”,“童年”,“吴越与齐赵的漫游”,“与李白的会合”,“长安十年”,“流亡”,“侍奉皇帝与走向人民”,“陇右的边警与险峻的山川”,“成都草堂”,“幕府生活”,“夔府孤城”,“悲剧的结局”。冯至神追杜甫,对无法抵达的时区就留下空白,而不妄自猜测。
当我写到这里,突然有两位异国异代的诗人并置于脑海:杜甫,里尔克。
我猜测,冯至在写这部传记过程中,一定想到过他所翻译、热爱的伟大的诗人里尔克。因为,杜甫与里尔克酷似:飘泊,置身于家国动乱的时代,孤独,沉思,居于幽暗,死在异乡,诗篇中的霜风秋气开阔浩荡——汉语的《秋兴八首》与德语的《秋日》,交相辉映。我爱这两位诗人,尤其杜甫,因没有语言隔阂而可以直接用河南土话对谈。青年时代喜欢李白,中年以后,人生立秋以后,觉杜甫更亲。用冷、硬语调内暗藏温情的中原土话,朗诵他的白露明月、秋边雁声,更亲。
唐代,河南籍诗人众多:盛唐杜甫,中唐白居易、李贺,晚唐李商隐……这些诗人风格不同,但都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一千年来的心境和形态。家国悲欢,成为历代中国诗人的命运和写作主题:用身体、命运、文字来一同与时代发生关系。杜甫、苏东坡、陆游等等诗人,本质上类似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就公共事务发言,对修、齐、治、平有大抱负。他们本意上并非要做一个诗人,仕途不畅才去纸上谈兵,像杜甫所言,“名岂文章著”。
杜甫往往被冠以“现实主义诗人”。何谓“现实主义”?我认为,那该是一种对现实不回避的态度,而非一种艺术风格——“无边的现实主义”,我赞同罗杰·加洛蒂的这一概念。现实主义始终未完成,并表现于各种艺术流派之中。一切诚实的写作,都是广义上的现实主义,不瞒不骗,“真与自然”。而某些香水、脂粉、广告一类品质的文字,常常被冠以“现实主义”之名,其实与现实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喜欢河南诗人罗羽的现实主义之作《祖国诗》:“鹌鹑是你的祖国,夜莺的咳嗽不是你的祖国/……/动车不是你的祖国,鲁山牛腿山羊是你的祖国/刮过去的风不是你的祖国/沙河里的柳叶藻是你的祖国……”尽管他被称为一个先锋主义诗人。
先锋,同样不是某类写作风格的专利,而应是所有诗人、作家都应具备的精神。尤奈斯库说:“先锋就是自由。”我理解,就是思想自由、表达自由。任何一个诗人对于现实生活的发现和表达,都应独一无二,尽管困难,只有一少部分杰出诗人才能做到,也不应放弃对于这“困难、独一无二”的认知和追求。杜甫就是唐代的先锋诗人,“乃真与古人为敌,变化不可测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与古人为敌”,其实,就是与时风流弊为敌。现实的,必须是先锋的——都需要“为敌”的勇气和才力。读杜甫,强烈感到:伟大诗歌的本质就是悲歌,痛彻肺腑。伟大诗人的命运或许只能是悲剧,慷慨有余哀。
青年时期,杜甫写出《望岳》,像李白;中年、晚年,因时代巨变而诗风巨变——《登岳阳楼》(“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高》(“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与登泰山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已迥然不同,充满“悲”、“病”字眼。生活愈挫败,其诗愈雄奇(落实于语言的平实之中)、苍凉(落实于感情的温存之中)、辽阔(落实于意象和叙述之中)。杜甫不再像李白,而成为杜甫自己。
杜甫启示:写什么(山水自然还是世道人心)不是问题,怎样写(口语、意象还是叙述,现代还是后现代)也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一个诗人能否诚实面对自我和世界,这是最基本的写作准则和诗学伦理。
杜甫感时——感应一个时代无微不至的冲击;忧国——忧虑一个具体而非抽象的国度,一草一木、一人一事都是这国度的肌肉、血脉、神经和呼吸。像杜甫一样承受了、担当了、克服了自己的命运,一个诗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并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度、一个时代的徽记——城春国破,草木山河。
杜甫之后,热衷于应制诗、酬唱诗的诗人多矣,撒娇、献媚、谋利,诗歌气象趋于软弱、阴柔、陈俗。像杜甫一样痛哭的诗人,稀少。
今天,市场经济时代,诗人们所面对的种种个人或公共的疑难,为写作带来复杂性和难度,但也可能使写作者丧失表达的勇气、辨别力、底线。趋利、避义、王顾左右而言他、“多买胭脂画牡丹”式的写作,大行其道。
当我揣着信封里的小规模润笔为高档楼盘写广告诗的时候,杜甫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我伪造一点泪水写所谓“底层诗歌”的时候,杜甫写《三吏》、《三别》……差异巨大,如同泥巴与云朵。像杜甫那样写作,我们就不敢在汶川大地震面前、温州动车追尾事件面前,轻浮、草率地抒情,就耻于化装舞会式、市场营销式的游戏和表达。
2012年,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周年,我与众多诗人赴河南祭拜。杜甫出生地:郑州郊区巩县依山而凿的一间窑洞,木门紧闭,门前有杜甫童年打枣的雕塑。杜甫墓:庞大土丘混同于山坡,衰草绵延,如白发瑟瑟——“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融入故乡山坡的一个诗人的巨大白头,依旧忧思难眠?
以杜甫、里尔克为镜,一个人、尤其是中年人,其写作应能够与内心及周遭广大、苍凉的秋意,保持呼应,发生关系。是时候了。与无边落木一同萧萧而下。尽管夏日曾经盛大。
五十四岁那年,杜甫在长江上写下《旅夜书怀》,有名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前一句是空间,后一句是时间。时间、空间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和奔流,并定格于六年后长沙到岳阳的一艘破船上。
现在,我也正渐渐接近他的光景和心境,且像他一样处于远离中原的异乡。不同的是,他漂泊在船上,把越江而去的一只沙鸥看成未来的自己;我漂泊在床上,把床单上的皱纹看成梦乡的地图。差异巨大——
他在痛苦,我在痛快——所以我将很快就在人间、纸上消失,而他负责继续承受人间和纸上的疼痛、苦难。
3
《苏东坡传》。林语堂。张振玉翻译。
林语堂在美国以英文写下的这部传记,读者对象显然在异邦,所以角度也以西方视角来审视北宋一个伟大文人,修辞手段有异域气息——像多明戈唱《贵妃醉酒》、梅兰芳唱《蝴蝶夫人》。
借助于张振玉的翻译,林语堂来到我面前说:“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一位瑜珈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正如耶酥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厚敦柔’。”
显然,苏东坡只可能出现于中国,就像诗歌中的月亮、梅花只能属于中国。显然,林语堂爱东坡。苏轼是先生,东坡是兄长,我和林语堂都呼他“东坡”。与流放地黄州的向阳东坡有关的这个名字,揭示出一个异代兄长野草般的人性、韧性。
在黄州,东坡交游、种地、研究并推广猪肉烹饪新方法。即便在逼仄困顿的处境下,东坡文字仍充满对周围人群的温存而毫无阴暗湿冷——《前赤壁赋》:“……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后赤壁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行歌相答。”《记承天寺夜游》:“……寻张怀民……何夜无月,何夜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等等文字之中,“客”、“二客”、“张怀民”、“家童”屡屡闪现——以出世的情怀做入世的事情,在与凡夫俗子的关系中确立一个人的存在,这就是东坡、朝东的山坡。
除上述名篇外,东坡在黄州期间还产生《念奴娇·赤壁怀古》、《寒食帖》等等神品。因苏东坡,黄州成为中国文学地图上的一个亮点,让我眯起眼睛去看。
黄州下游,九江,东坡舍舟上岸,登庐山,写出三首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观潮》:“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宿东林寺》:“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示人。”三首与东坡的命运交响、映照的诗,如同在向后人传授作文技巧:要跃出自身皮囊去辨识出广大生活的“真面目”,要对烟雨江潮怀抱反复不息的、眷眷的温存感,要有溪声山色一样的禅意难言……
清末民初诗人况周颐词话集《蕙风词话》曰:“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让我一下子想到“不合时宜,独谈古调”的苏东坡。“词心”,推而广之,可为诗心、文心、良心。“风雨江山外”的“万不得已者”,是一种万不得已、欲罢不能、忍无可忍的情感,遥遥自风雨江山之外呼啸,而来到诗人的血肉、笔端——一个诗人的心,反复游荡于风雨江山之外的广大世界里,像马,哒哒哒哒,反复奔向一个诗人空山般的胸腔、纸笺……
“吾心安处是吾乡。”东坡如是说。一个只能把故乡安放在心上、诗心上的人,出蜀,而难以归蜀,越汴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杭州、颍州、扬州、惠州、定州、密州、儋州、常州——“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东坡,把乡愁放大到整个北宋中国的苏东坡,让我热爱伟大的汉语,并像他一样试图安顿灵魂于其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青天大约在以风声回答:“明月自李白、张若虚而始有,至东坡为盛矣——千载共婵娟!”
一条长江,贯穿南方中国。上游是杜甫,中游是苏东坡,下游入海口处的上海,是谁?我?不。我显然没有巨大的勇气和才华,来与前贤并列于汉语和地理这双重的长江。我适合在苏州河边捏着酒瓶晃荡、唱歌、看妖冶模特在外白渡桥边扭捏着腰肢拍摄广告片。
我曾经用一周时间在黄州、赤壁、庐山一带漫游,再对照东坡文字,失望而归。两岸景象已雷同于其他地域。某些江段、支流,亦不复有东坡笔下的汹涌有声,举网而无鱼。沿长江,曾产生东坡写过的众多词牌:临江仙、西江月、江城子、满江红……如今,长江已成为一系列水库的联合体,与经济学发生的关系比与文学发生的关系更加紧密,一道道大坝像数学中的等号:江水=电=金钱=旱季=消失了的鱼群和壮丽……
当下,我只能写“后现代赋”,在上海长街两侧摩天高楼模仿出的“断岸千尺”的阴影里,想念明月印在地上的人影树姿。只能读东坡,疲顿逼仄之时,从苏海中取盐壮胆。
我开始热爱、寻找、积累、临摹他的字迹。古人云“见字如面”,我见东坡墨迹,亦应如见东坡面容吧?把这些墨迹与相关诗文对比,可看出某一字眼上的圈画、涂改、浓淡,从而发现一个北宋文人内心的犹豫、愉快、决绝。因时光推移,《春中帖》有若干字空无或消逝,像晚春树木若干花朵凋谢了许多瓣,空茫处,暗香一缕仍在。东坡大部分信札墨迹,写在客栈异乡,《寒食帖》、《渡海帖》、《北游帖》……“轼顿首”三字屡屡现。其所顿之首,已云散烟消数百年,幸而那支纷披的狼毫或羊毫顿挫于纸上的痕迹犹在——毛笔,就是一个书生黑发纷披的头颅,狼毫羊毫组成的头颅,顿,叩,在一张大地般的宣纸上……
其中,一部分名帖被怀疑是伪作,是他人在摹拟东坡的处境、心情、语调、手感、墨迹。但摹拟东坡墨迹,是多么困难的事呵——要全身心地趋近东坡,使自己像朝东的山坡,阳光一地,野草纷披,满腔温情如山涧春水负载落花和小鱼倾斜到低处去、到人心里去。
被模拟,应该是苏东坡能够原谅甚至感动的事: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后,还有人想去替他活、爱、怜惜、感慨、书写,去替他寒、渡、游。
被追随,应该是东坡高兴的事——我,就想成为远远跟随他的一个弟弟,像苏辙……
4
《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散文集。张岱。中华书局。
这一版本繁体、竖排。阅读的速度就慢下来,我的头渐渐低下来,抬起,再渐渐低下来——这姿态像鞠躬、悼念,适合读张岱充满了伤逝气息的文字。
全书包含《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两部著作。前者写江南风情、人物,后者分七十二章细细描绘西湖景色,怀恋明末清初以前的故国山河、锦绣岁月。贯穿一“梦”字,像梦游人呓语。张岱晚年文字,纯熟,简劲,诗意充盈——诗意就是失意,失去了的事物在回忆中更加绚丽、痛切、动人。
山阴人张岱,出身书香门第,坦言自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浮华习气、名士作风兼备于一身。明亡后不仕,隐居杭州,自谋生计,暮年仍以羸弱之身舂米担粪、种菜养鸡,与少年时代纵情声色的生活反差巨大。写作,或者说做梦,成为安慰余生的重要方式。
尤其喜欢书中两篇文字,与西湖有关:
(一)《西湖七月半》。写初秋西湖的种种人物行状,“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人分五类:“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的达官贵人,“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的名娃闺秀,“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的名妓闲僧,“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的市井之徒,“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的文人雅士——这最后一类人中有张岱,待其他人散入城门之内的万户千家,西湖寂静,明月高悬,“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我亦多次自上海去杭州,看西湖上的那五类人似乎仍在,当然,“名妓”们可能已无名隐形,“闲僧”们正忙着用手机炒股、发微博。我大约属于“市井之徒”一类吧。走,看,想,与西湖有关的前尘旧梦就散漫涌上心怀,却无一字能写,似乎所有的感喟都被张岱以及更早的白居易、苏东坡、杨万里等等文人写尽。他们都属于张岱笔下的第五类人,越朝叠代,欢聚同醉,散乱共眠于西湖荷花之中的轻舟内。目前,西湖荷花十里依然,明月依然,但纵舟酣睡于荷香清风之中的古典场景已不复存在。
(二)《湖心亭看雪》。湖心亭如今需购买门票才能乘舟上岛,且夜晚禁入。只能回想这蕞尔暗影中曾经发生的诗意一夜:“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余奴手一小船,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这雪夜,使我所有的夜晚都黯然失色;这文字,让我所有的文字都乏善可陈。只能幻想在深夜里拥一皮肤雪白的女子,让她西湖般卧着,“上下一白”,惟长腿“一痕”、嘴唇“一点”,我手“一芥”,手上老年斑“两三粒而已”……趣味显然低俗了。我知道自己的缺点。
张岱喜欢有缺点的人,“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我喜欢这个“缺点”鲜明的前人——
他不广大,履痕、笔墨徘徊于山东、江苏、浙江这一当时华夏的繁华地域,尤其是西湖,他似乎无视长城以外窥中原的异族马队正滚滚而来,而以记梦的方式,传达苍凉与感伤。
他不灵活,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自为墓志铭》),失败失意之气一身,我却觉得可以亲而近之,而周围善于变脸、勤奋进取之士则令我惧而远之。
他不端庄,没有明代二袁小品中秩序严谨的士绅气,行文迅疾时长句连绵,如匪徒手持长枪,攻城略地,欺男霸女,缓慢时短句断续,如醉语,如梦呓。《西湖七月半》写得快、热闹,像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写得慢、静,像湖心亭内外的雪……
我多次自上海去西湖,快、热闹屡屡可见,即使时令并非七月半,但没有遇到过下雪,“断桥残雪”的景点标志,与西湖上树立的另外一个标志“苏堤春晓”,基本上都处于梦忆、梦寻的非现实姿态。张岱就是一座断桥,魂断,靠文字来粘连往事与现实这两岸之间的关系,指出春日拂晓的方向、苏东坡的方向。他也应该喜欢这位修筑苏堤的前贤大家。《湖心亭看雪》与苏东坡的《记承天寺夜游》,语调、情怀、趣味都那么像。
古往今来,凡喜爱在深夜看雪、赏月、游走的人,应该都很像吧。像痴人、梦中人,痴人说梦。
没有雪、月,就在夜深人静时持一支笔,穿过一张白纸,也好。
5
《笑林广记》。清代“游戏主人”编撰。人民文学出版社。
早年,听父亲讲过两个故事,大笑——
其一:某天清晨,一人看见落了露水的桌子,就开玩笑伸出手指写了谋反的字样,恰好被其仇人看到。仇人狂喜,夺过桌子扛起来就往县城衙门里狂跑,去告状、复仇。等到官员坐在大堂上,太阳升起,桌上露水与字迹已经晒干了。官员问告状人有何事登堂,他沮丧、郁闷,无状可告,只好说:“小人有一个桌子,不知老爷买不买?”
其二:一乡下人穿着新浆的衣服硬硬地入城,一路被晨露打湿,待入城,衣服已经变得绵软,乡下人甚惊异。午后,出城,太阳高照,衣服被晒干了,硬硬如初,乡下人甚惊异。到家后即对妻子说:“不要说乡下人进城硬不起来,连乡下的衣服见了城里的衣服也硬不起来。”
现在,我知道这两个故事出自《笑林广记》。一个清代人搜集编撰的通俗笑话集,含一千多个可乐、可笑、可气、可爱、可沉思、可回味的小故事,每个故事约一二百字,类似于今天的微博、微信——这个化名“游戏主人”的人,活在今天,一定是微博控、微信控,天天发段子,粉丝云集。
读这本书,我明白,今人、古人的差别其实并不大,从生存状态到心理、趣味,我自己就完全可能是那个进城告状的人(祖先扛着桌子,我扛着电脑),就是那个进了城连衣服都自卑的人(祖先的衣服是自家裁剪并浆过的,我的衣服是批发而后零售的),古今一也,大同小异。
闲翻这本书,最喜欢的还是一个题为《恍惚》的故事,抄录如下:“三人同卧,一人觉腿甚痒,竟将手在第二人腿上竭力抓爬,痒终不减,抓之愈甚,遂至出血。第二人手摸湿处,以为第三人遗溺也,促之起。第三人起溺,而隔壁乃一酒家,榨酒声滴沥不止,以为己溺而未完,竟站至天明。”
这一篇属于卷五“殊禀部”。全书分“古艳部”、“腐流部”、“术业部”、“形体部”、“闺风部”、“僧道部”、“贪吝部”、“讥刺部”、“谬误部”等等共十二卷。《恍惚》,我最喜欢的这个故事,似乎应该属于第一卷“古艳部”——那恍惚,多么古雅惊艳,完全就是一首诗!当然,放在“殊禀部”也有道理——古且艳,需要一种特殊的禀赋、能力。
比如,庄子,就是一个恍惚的人、古艳的人,能够看见鲲在大海游动而后一飞冲天转化为鹏,与水中的鱼交换双方的快乐,梦见一只蝴蝶梦见了他……
比如,博尔赫斯也恍惚,文字跨越散文、小说、诗的文体边界,像镜子中、夜色中变幻不定的事物。他写过一首《梦》:“……/白昼给予的一切都无法与之比拟。/我是人人,我是无人。我是别人,/我是他而不自觉,他曾见过/另一个梦——我的醒。他评判着/他置身局外而且微笑。”他读过庄子?
比如,特朗斯特罗姆,这个瑞典诗人在恍惚中低语:“在黑暗中醒着/能听到橡树上空的星宿/在马厩中跺脚”了。“所谓醒悟,就是从梦中向外跳伞。”
好诗人,大约都是这样恍惚、古雅、有殊禀,像《笑林广记》中同卧一室的三个人,但需要夜晚和梦的帮助。在夜晚、梦中,一个人才有可能混淆着眠与醒、意与象、自我与他者、是与非等等事物之间的界限,得大自由、大自在——
当然,进入恍惚之境,还需要一个条件:隔壁有一个彻夜榨酒、滴沥不止的小作坊。
我把《笑林广记》当成一部诗集来读了。
6
《闲情偶寄》。李渔。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选择笔名“汗漫”,灵感就来自明末清初文人李渔《凉州》一诗:“似此才称汗漫游,今人忽到古凉州。笛中几句关山曲,四季吹来总是秋。”1666年,李渔五十六岁了,从南京的芥子园出发,开始缓慢的远游。经燕、秦,于1667年初抵达皋兰,也就是今天的兰州。之后,继续西行,至凉州,写下了这首诗,让三百年以后的我怦然心动。后来,又相继在其他古代诗人笔下读到“汗漫”二字,隐隐感觉这是前人在为一个1960年代出现的后生命名——要开阔、自由、宽远……
李渔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对征逐仕途不感兴趣,潦草地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未能晋级,就怡然踏上一条无人选择的人生道路,从而造成其与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们命运景观的不同。他渐渐成为了著名的闲人、雅士、情色小说家、戏班子班主、生活用品设计制造家、环境美学专家、画家、美食家、选美顾问、时尚人士……渐渐成为了独特的“这一个”。荷尔德林所说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指的就是李渔这类人吧。一个清代的享乐主义者,一个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抒情诗人,在生活的细节处发呆并发现、生发出美感的人,“充满劳绩”。
《闲情偶寄》就是这样一部享乐主义之书、生活美学之书。全书分词曲(写作中的结构、词采、音律等)、演习(戏曲表演中剧本选择、改编、作曲、念白等)、声容(女子姿态、装扮、风情等)、器玩(几案、床帐等)、种植(木本、藤本、草本等)、饮馔(蔬、谷物、肉类等)、颐养(行乐、止忧、节欲等)各个部分,涵盖了清代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显然,这也是一部才子之书。一个通才,有体贴万物、美化生活的慧心妙手。比如,他游历西域时随身携带的无臭、描花的便桶,和隐藏炭火以升温的椅子,就是他自己手操斧子、锯子、画笔,反复琢磨而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一个奇才、怪才,“似此才称汗漫游”。
正是在这次西行过程中,李渔对女子手足之美加深了认识,在《闲情偶寄》中写到:“予遍游四方,见足之最小而无累,与最小而得用者,莫过于秦之兰州、晋之大同。兰州女子之足,大者三寸,小者犹不及焉,又能步履如飞,男子有时追之不及了,然去其凌波小袜而抚摩之,尤觉刚柔相半。”又云:“媚态二字,必不可少。媚态之在人身,犹火之有焰,灯之有光,珠贝金银之有宝色,是无形之物,非有形之物也。”再云:“匀面必须匀项,否则前白后黑如戏场之鬼脸。点唇则与匀面相反,一点即成,始类樱桃之体;若陆续增添,即有长短宽窄之痕,成一串樱桃而非一粒也。”书中,此类对女子美妙之处的独特认识比比皆是,可见,李渔应是一个“女性爱好者”。故,就性保健问题,李渔又向男性传递经验:“御新人,则旧之,仍以寻常女子视之,而不致大动其心,过此一夕二夕之后,反以新人视之,则可谓驾驭有方、张弛合道者矣。”
李渔五十六岁时的西行,像他以往在江南游走一样,带领由十余名美女组成的戏班子,一路演出他编写的戏剧,一路与名门望族交往并帮助他们选择美妾以得到酬报,一路手提自己发明的便桶和椅子。他就是利用演出、募捐、刊印《芥子园画谱》、《肉蒲团》各类畅销书等收入,养活了一个家族及佣仆约八十余人。尤其是他创制的一种谋财之道,依然被今人沿袭:向县令以上官员发函,征集他们的审判案例及判词,以署其姓名、编入《资治新书》系列丛书(由翰林院官员题词并参与编撰),但入选者须缴纳审读费、购书款等等若干两银子。这让我想起当下各类暧昧机构所征集、编撰的《中国名人录》、《当代杰出企业家经营案例丛书》、《世界华人英才榜》,向乡长镇长总经理一类人撒网、钓鱼。李渔,如果活在今天,应该也能进入年度富豪榜,在各种讲坛、论坛、沙龙里游走无碍,把银子之俗与汉语之雅流畅地结合在一起。
闲情偶寄。人生如寄。一个人,文人,偶然寄托于天地和笔墨,转瞬即逝。好在还有种种的闲情,使这“转瞬即逝”稍稍有了暖意。
他的同乡前辈李清照,在故乡金华兰溪写过《武陵春·春晚》:“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春愁,不是闲情,但需要以闲情对抗春愁——春日草木一般繁盛的忧愁。李渔,懂。我,也懂。
1680年,李渔在杭州去世,七十岁,值了。
7
《随园食单》。袁枚。中信出版社。
李渔百年之后,清乾隆时代的诗坛盟主、江南才子袁枚出现,作美文,品美食,爱美人,酷似李渔。
《随园食单》,美食随笔集,历来版本众多。我收藏的这本2008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漫画版《随园食单》,有趣。它以原文为脚本,构思了袁枚、厨师、管家等人物形象,描绘了袁家在南京随园里的生活场景,工笔的袁枚与小妾,水墨的菜肴与山川,彼此辉映。
这本清代食谱表明,除了衣着风格剧变,我们今天的生活与袁枚时代没什么区别。当代餐厅大厨把袁枚奉为祖师爷,向徒弟们讲解清代的菜园、牧场、江湖、刀工、火焰、苦涩、甘美之间的辩证关系。而我把《随园食单》当作一部比《随园诗话》更有意味的风俗志来看。
袁枚与长他百年的李渔,个性都可归结为三个字“不耐烦”——对做官、学满语、写宫廷气味十足的温柔敦厚的格调文字,通通不耐烦。于是,中年辞官,隐居南京小仓山,把一个废旧园子进行改造,成为随园,袁枚自身也随之成为了随园——满园随意的植物清风。在随园,即使担粪的仆人也会在走过一棵梅树下时抒发感伤:“它落了我一身的花呀……”正在菜园里挽着裤腿摘野菜的袁枚闻之大喜,起身奔进书房,铺开宣纸,一挥而就:“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
随园,就是诗国。一个脱离政坛的文人,成为诗国领袖。《随园诗话》就是一部乾隆时代的诗歌选集,携诗而求入选的诗人若过江之鲫游入随园。二十六卷《随园诗话》选诗六千九百零九首,入选诗人一千九百九十一位,其中江苏诗人占百分之三十五,浙江占百分之二十九,其余为两湖、两广等等省份,由此可见江南诗风之盛、才子之多。这样一个浩大工程,巩固了袁枚的诗界地位,也为其赚取了可观版税,使得随园里的妻妾子女、一干随从仆人凡二十余人,保持了较高的生活水准。
“枚平生爱诗如爱色,每读人一佳句,有如绝代佳人过目,明知是他人妻女,于我无分,而不觉心中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随园诗话》之所由作也。”袁枚自述。今天看来,这部选集中相当一部分诗属平庸之作,并非“绝代佳人”,或许袁枚也有不得已之时,碍于情面或银子?
在编纂《随园诗话》的晚年,袁枚大部分光阴在漫游,“所到黄山、罗浮、匡庐、天台、雁荡、南岳、桂林、武夷、丹霞,觉山水各自争奇,无重复者”。从《随园诗话》可看出,他去苏州最频繁、滞留时间最长——为了艳遇。袁枚的两个宠妾,就是在苏州遇到的鲜艳女子。而他在《随园诗话》之外专门为女弟子编辑的诗选集《随园女弟子诗选》,达六卷,收录二十六位女弟子的诗作——与鲜艳的语言相遇,要比与宫廷案牍相遇愉快吧?
与美食相遇也是一种艳遇。《随园食单》就是《随园诗话》的伴生品、袁枚鲜艳生活的伴生品。这本书初版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分为“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江鲜单”、“特牲单”、“杂牲单”、“羽族单”、“水族有鳞单”、“水族无鳞单”、“杂素菜单”、“小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菜酒单”共十四个方面,涉及三百二十六种南北菜肴饭点,是袁枚经四十余年逐步体验、记录、总括而成,行文走笔如同烹炒煎煮,色香味俱全,品读之,回味悠长。
如,“厨者之作料,如妇人之衣服首饰也。虽有大姿,虽善涂抹,而敝衣蓝缕,西子亦难以为容”。对待美食,须如同侍奉那些有大姿的美人。
如“,菜有荤素,犹衣有表里也。富贵之人嗜素甚于嗜荤。”于是,我对宴会上声明吃素的人充满敬重,对自己依然热衷于蹄、羊肉汤充满羞惭和不安。
又如,“厨者偷安,吃都随便,皆饮食之大弊”,必须“戒落套,戒混沌,戒苟且,戒穿凿”。像文学院教授在讲写作原则。除饮食之大弊,如除语言之弊、灵魂之弊。当下,偷安于文坛者,比比皆是。
又如“,上菜之法,盐者宜先,淡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无汤者宜先,有汤者宜后”。似乎在谈一个人由青春到晚年的生命秩序,自重而轻,由繁入简,化实为虚——最后成为汤汤江海上的淡云轻风。
再如“,味太浓者,只宜独用,不可搭配,如李赞皇、张江陵一流,须专用之,方尽其才。食物中,鳗也,鳖也,蟹也,鲥鱼也,牛羊也,皆宜独食,不可加搭配”。让我想起当下政坛、文界、市场等等领域李赞皇、张江陵一类的才俊,独来独往,醒目,皆宜独自被时光之舌所餐食。而我这样一个平庸的人,只能呆在白菜、萝卜、米一类人群中,混沌老熟,消失。但袁枚又说“:粥饭本也,余菜末也。本立而道生。”粗粥淡饭间暗藏大道——一个凡夫俗子虽列于“菜单”上的诸般才俊之末,但这“末”恰恰属于人生的根本、基本。
醉翁之意不在酒,袁枚在借题发挥——借一份食单发挥性灵、消解块垒。他的诗学主张就是“性灵派”。一个至性至情的诗人,诚实,可爱。
翻读《随园食单》,发现其中的南方视角——袁枚,这个杭州人,南京客居者,尽管对北方食物也有涉及,但情怀、味蕾毕竟在长江以南。比如,他笔下的“饭”与我故乡中原的“饭”概念不同,前者仅仅指米饭,后者则通往面条、饺子、馒头、油条、胡辣汤等等内涵广阔的北方事物——这些,袁枚笔下没有出现。
袁枚不太爱酒,只喜欢江南一带绵软的黄酒、米酒。他认为山西汾酒这种烧酒、燃烧着的酒,如同“人中之光棍,县衙中之酷吏也。打擂台非光棍不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此处擂台、盗贼,指餐桌上那些气势汹汹的猪头、牛腿一类佐酒菜。与汾酒相比,黄酒、米酒大概就是人中之少妇,与其相宜的菜肴,大概是熏鱼、扬州干丝吧。熏鱼如梅雨天,扬州干丝如扬州园林,非少妇游走其间不可尽显其美妙——
在《随园食单》“点心单”部分,袁枚写到“萧美人点心”这一则时,有些走神——“小巧可爱,洁白如雪”,好像写的不是点心而是萧美人。而且把“萧美人点心”的地址记得很清晰:“仪真南门外”。不知道袁枚在仪真南门外徘徊流连了多少次呢。也不知道今天的南京,“仪真南门外”又是什么景色。
我把《随园诗单》看成比《随园诗话》更绝妙的诗集——叙事诗,抒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