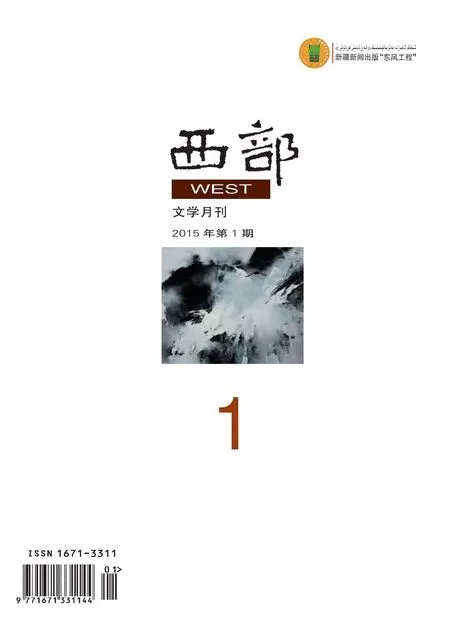访谈录
《西部》:叶舟老师和龚静染老师都是“双栖作家”——诗歌、小说双管齐下。每天从睡眠中醒来,你们首先意识到自己是诗人还是小说家?如何在小说和诗歌这两种文体间进行思维转换?小说和诗歌有什么内在的隐秘联系?
叶 舟:坦白讲,“×栖作家”或许是评论家为了言说的方便所使用的概念吧,我个人在具体的写作中并没有这样的分心,比如暗示自己“下面是诗歌时间”,或者说“下面是小说时间”,小子,你要井水不犯河水!同样的道理,没有哪个人从天光中醒来,先确定自己的性别身份,是男?还是女?更不可能去揣摩自己小说家或诗人的角色,他(她)只是作为一个人醒来了,感谢上天,又来到了新的一日。这是生命的赐予,恩重如山。
我尝试过很多的文体,诗歌、小说、散文、随笔、影视剧本、音乐剧、诗剧,还包括报纸的社论和发刊词什么的。我喜欢那种拆除了一切樊篱的写作,在其中“交叉跑动”,把小说写得太像小说,把诗歌写得太像诗歌,恐怕也是一种局限,一种作茧自缚。
要说小说和诗歌之间有什么内在的隐秘联系,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最高的诗意”,即对待生命的敬意,对万物生长的膜拜,对一切恩养的报答之心。
现在把“话筒”交给龚静染,听他的高见!
龚静染:我想,作为写作者,诗人和小说家最根本的区别可能是语言状态的不同,而不是身份,或者文体的差别。当我面对心中涌动的东西的时候,写作是自然流出的,是自觉的。至于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字,一切听从内心的指引和神的旨意。
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写诗什么时候写小说,好像也没有两种文体转换间的纠结。人的大脑是个巨大的储存器,记忆和经验被激活的一瞬间,语言迅速合成,就会作出“诗的”或者“小说的”判断,这也许就是写作最神秘的地方。要说诗和小说在文体上的差别,我觉得诗人有点像银匠,小说家更像是铁匠,他们面对的材料和工艺可能有点区别,但我相信,他们对写作的等待是一样的。
关于人的真实存在,这是在诗或小说之外的。每天清晨起来,我想到的是自己还活着,其实连这点我都很少想过,所以我更不会想到自己是诗人或者小说家了。身份的确认往往是在写作完成之后,身份是文本意义的;而写作的开始是被唤醒的,唤醒你的可能是一列火车、一头牛或者一只小鸟。我更多想的是,它们将如何来到我的文字中。
《西部》:“诗人小说”与“小说家小说”有本质的区别吗?诗人对语言十分讲究,总是精益求精,甚至有“语言洁癖”,“诗人小说”的特点和魅力何在?
叶 舟:一部《旧约》,你既可以将它看成是伟大的散文,也可以看成是一首史诗,同样能读出小说的脉络与筋骨。博尔赫斯的诗歌与小说,在我看来也是界限模糊,互为表里,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诗歌是一种绽放的花朵,刹那间的产物,貌似没有道理的呈现,劈头盖脸的和盘托出。而小说必须述说它在绽放之际的层次、逻辑、内部的韵律,甚至包括它的痉挛、哽咽和溃烂,找出它的源头、经脉与前世今生。——在这个过程中,对结构的讲究和挑剔,对语言的洁癖,应该是一种肃然和敬畏使然。
龚静染:我不认为“诗人小说”与“小说家小说”有本质的区别。诗人也好,小说家也好,在小说写作时都需要有对语言的思考。但诗人视语言如钻石,唯美、精湛、凌空蹈虚,小说也因此获得了一些独特的韵味和视角。世界上就有不少作家都曾经尝试过诗与小说的融合,如以色列作家奥兹的《一样的海》。
但小说的核心还是人物和故事,小说的风格可以呈现一种语言态度,比如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等就可视作诗性小说,他们虽然不是诗人,但他们小说中的语言有诗的趣味,有抒情气质,在叙事中永远蒸腾着清远、飘逸、优美的气息。我想这也是人们对“诗人小说”的一种期待吧。
《西部》:中篇小说《民国少年》讲述了在抗日战争背景下的一段“民国往事”,写出了一群裹挟于、碾压于历史车轮之下的和盐有关的小人物们的命运,或许他们才是历史中最坚硬的部分。《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则凭空设色,回到更遥远的北宋,讲述了苏东坡被贬黄州的一段“种诗”的传说故事。两篇小说都是历史题材,两位老师如何看待历史重述和历史想象?
叶 舟:这个短篇小说完全是一种想象,一次劈空结撰。去年六月在湖北黄冈采风时,我第一次知道“东坡居士”这一伟大的称谓,是苏轼流放当地时被命名的,由此入列青史,为后人仰望。而恰恰是在那一时期,东坡先生创作出了“赤壁二赋”等著名篇什,抵达了他文学生涯的另一个尖峰时刻。那一刻,我就有了企图心,想用一篇文字来探究东坡居士的这一心理。需要说明的是,《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这个名字借自诗人李亚伟早期的一首诗作标题,我想呈现诗人们身上那种共有的好奇心和恶作剧。
文中,那个木讷的小叶就是我本人,修文则有小说家李修文的影子。我和他结伴去了北宋年间,到了黄州城东门外那一片荒凉的坡地,向东坡居士取经。——历史重述或历史想象,就在于你提灯夜行,穿州走府,忽然踅进了一条歧路,找见了那一座尘封的庙——
于是吃茶。
于是晒经。
龚静染:时空的距离感对我有很深的诱惑。在写作《民国少年》的时候,我常常有一种要走进那些消失的人物中间的冲动,我常常觉得他们不是故人,不是冰冷的名字,他们就在我的身边,音容笑貌仍然温热如新。
过去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深深震撼于一个历史学家用了文学性的叙事来完成对历史细节的还原。黄仁宇是迷恋文学的,不然他就不会去写长篇历史小说《汴京残梦》和《长沙白茉莉》了。我在想,长期专注于历史研究的人大多有学院派的刻板,但是他花了长时间去写小说,说明文学在捕捉逝去时空的人物与命运时有其独特的呈现,是严谨的历史考据不能替代的。后来我又看过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等系列作品,同样看到了历史学家在文学中寻找到了叙事技巧。可以说文学是他们修复、解读历史图像的绝好工具。反过来,历史是文学的无尽的宝库,史学家的视野也是文学的方向,作家要有对历史的真正洞察,才会获得文学的自由飞翔。
《西部》:龚静染老师2014年刚刚出版了长篇小说《浮华如盐》,讲述了抗战初期四川盐商的故事。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也写了大量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小说,运用回忆和想象把现实和虚构结合起来,讲述普通人的生活。几年前,叶舟老师写汶川地震的诗作《祖国在上》流传甚广。如何理解战争、地震等天灾人祸中的人类存在?
叶 舟:我宁愿没有这一首诗,也不愿看见灾难发生,哪怕是最微小的伤害。
但灾难的确来了,排山倒海,地动山摇。我在兰州,甘肃也是灾区,除了救助、个人捐款、做新闻报道之外,我还和其他的诗人们一起用赈灾晚会的形式,给灾区募集了十几万的善款。《祖国在上》这首诗就是给晚会写的,后来央视拿走了,所有的频道都在播出由康辉和欧阳夏丹朗诵的视频,放大了它。
我想说,它只是一份祈祷词,一首度亡经。
龚静染:2008年5月12日那天,我正在成都的一幢高楼上,地震来的时候,大楼像狂风中的树一样左右摇晃,我听见钢筋快要折断的声音。那一刻,我感到了彻底的绝望。很多人说,如果再摇半分钟,成都可能就完蛋了,但我们侥幸活了下来,虽然对于那些亡者,这侥幸显得非常不公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想写一个有力量的东西,在大灾难面前可以站立得起来的东西,但可惜这永远是徒劳的。因为生命极其脆弱,恐惧和不安永远会伴随着人类,我们的文字无法摆脱苦难的纠缠。
现在我仍然住在一幢高楼上,那些来自断裂带上的大小地震经常都会骚扰着我们的神经。有时候是在白天,有时是在深夜,有时感觉得到,有时完全不知晓。地震和一个城市,地震和个人好像已经浑然一体。但这并不代表我在灾难面前不再惊慌失措,相反我会想起生命中一个个侥幸,正是那些侥幸拯救了我们,是它让我们绕过了灾难的降临。所以,我要更多地写那些不幸的人们,在恐惧与挣扎面前,幸存也是卑微的,但也许只有卑微的文字才能与灾难坦诚相见。
《西部》:在西部写作,如何理解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对地域性的过度沉迷是否意味就是“地域寄生”?文学又如何超越地域性?
叶 舟:我喜欢“沉迷”这个词,如果它代表着独执己念、一意孤行的话。
问题在于,这多少年来,我只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过客,青藏高地上的一个叩问者,天山南北的一个抒情者,黄土高坡上的一个守望者,黄河上游的一个漂泊者……我的沉迷不仅不过度,其实才刚刚发生。我盼望有一枚上帝的钉子,能将我的祈祷和文字挂起来,让我笼盖四野,长风浩荡。
希腊谚语说,不要在岸上相信一名水手。——但愿在西北这一片辽阔的旱海里,放下我的名字,让我引舟如叶,一帆远去!
龚静染: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熟悉的生活,是生活给了写作的理由。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产盐巴的地方,天天看到的都是井架、枧管,闻到的是浓郁的盐卤的气息,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巨大的。但这些东西变成文字的时候,它会带来更深的思考,我会去追寻那些已经远去的背影,也会去思索盐作为一种物质同生命的关联。
川南家乡和童年的生活是我最早认识的世界,也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当然更是我的故事需要的土壤,所以我很难走出这样的“地域性”。正如种子是不能超越土地的一样,我也不能超越自己熟悉的那点生活,写作毕竟是件需要老老实实去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