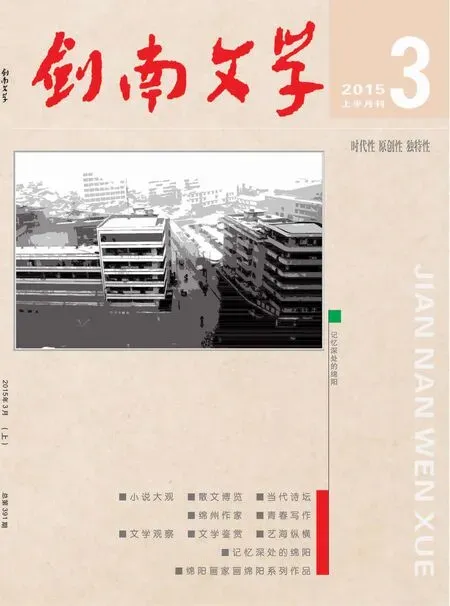刘禹锡贬谪后期思想的变化
■邓张萍
宝历二年秋,刘禹锡终于结束了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 奉诏回洛阳时遇到白居易,刘禹锡在宴席上写下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首诗是刘禹锡思想成熟的关键,诗中刘禹锡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中,昔日好友多已不在,而自己也如“病树”、 “沉舟”历经坎坷,进入垂暮之年,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时间就是一副良药, 即使当年有怨、 有恨,如今也已随江风而去,若问前程 “暂凭杯酒长精神”。可以说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朗州是刘禹锡伤悲、愁绝的积累期,也是其怨愤的勃发期。然正是这样无情的打击,二十二年的贬谪经历才让刘禹锡由最初的犹抱希望到绝望、愤懑不平到思考人生、洞察世事到理性皈依顺势自保的明智之路。
一、朗州之怨愤
永贞元年八月顺宗内禅,宪宗即位,意味着只维持了一百六十四天的永贞革新失败。作为失败者的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并且“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内。” (《旧唐书》卷十四 《宪宗纪》上)这等于是将刘禹锡的政治生涯判了死刑。遭受贬谪后的刘禹锡随着其“立足点的变化和心理的再度位移,亦即其关注对象从社会政治向个体生命,追求目标从建功立业向雪冤复仇……内向的悲恨聚敛代替了外向的激情发越,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让位于对自我生命、人生、命运的深刻表现。”“少年气粗” (《上杜司徒书》)的刘禹锡一方面不免有逐臣之愁、怨、愤。 “如今暂寄尊前笑,明日辞君步步愁” (《赴连州途径洛阳诸公置酒相送张员外贾以诗见赠率尔酬之》),未至贬所而逐臣之愁已是一步深似一步。“仙公一奏 《思归引》,逐臣初闻自泫然。莫怪殷勤悲此曲,越离长苦已三年。” (《闻道士弹思归引》) “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谪居悼往二首》) “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 (《采菱行》) “应怜一罢金闺籍,枉渚逢春十度行。” (《朗州窦员外见示与澧州元朗州郡斋赠答长句二篇因而继和》)刘禹锡在朗州一贬就是十年, 逐臣思归不得,远望长安徒自伤,心中的怨愤一年深似一年。元和四年九月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叛乱,朝廷诏讨,王承宗上表自首,朝廷不责反复其官爵,待之如初。朝廷对待叛逆者尚如此宽宥,对逐臣却又是一番面目,怎能不令刘禹锡发出 “逐客憔悴久, 故乡云雨乖。禽鱼各有化,余欲问齐谐”的不平之语。如果说王承宗是上表自首而获得宽宥,刘禹锡又何尝没有激切的表白自己的志节。 “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 (《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 “水朝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然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成为 “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 (《资治通鉴》卷二三九 《唐纪》五十五)将其再度贬谪的借口。十年的期待换来的只是短暂的希望和更深的打击。 从永贞元年九月到宝历二年秋,历时二十二年刘禹锡基本上是以贬谪官的身份在地方为官。这样的现实与其心中所追求的理想的巨大差距,怎能不令其产生希望渺茫、人生无望之感,由最初的怨愤到最后的心如死灰。如此深刻的失意与绝望的种子经过二十二年的滋生已在刘禹锡内心深处长成一颗参天大树,它时刻提醒着刘禹锡,警醒着刘禹锡,它的根渐渐伸向当年那个意气勃发的刘禹锡,二者在刘禹锡的思想深处较量着。
二、理性成熟期
苏轼说刘禹锡 “虽已败犹不悛也”③说其不知悔改,在贬谪之初确实是这样,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时间谪居贬所,朝中群臣对永贞革新成员的不能释怀,使刘禹锡认识到要重新被朝廷接受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刘禹锡的思想行为是有所改变的,对于前尘往事,当前局势多了一份理性的思考。其 “报国松筠心”的理想没变,但对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变了,刘禹锡不再单纯的向统治者表白自己的志节,而是开始思索自己的过往,由之思及自己的人生、未来以及未来的道路当如何走。
宝历二年刘禹锡在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写道: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首诗可以看作是刘禹锡思想成熟的标志, 在此诗之前刘禹锡未脱谪籍,其心态尚偏激,多有怨愤。然此诗之后,刘禹锡则豁然开朗,对之前所执淡然处之,对人生、时局更多采取顺应之势。这是刘禹锡在长期理性思考中得出的结论。刘禹锡由最初的坚贞守志, 到理性成熟的释然绝非偶然。由内而说,刘禹锡的坚贞守志归结到底是要实现其个人价值。刘禹锡被贬之后,永贞革新的一些措施如削藩镇、罢宫事、整顿财政在宪宗朝并未被废除,甚至还取得不错成就,如宪宗先后平定了李琦、吴元济、李师道的叛乱,抑制了藩镇自安史之乱以来的猖狂气焰,使大唐暂时获得表面上的安定统一,人称“元和中兴”。从客观上说刘禹锡的政治理想部分实现,刘禹锡对此应感到十分欣慰。确实刘禹锡在元和十二年所写的 《平蔡州》中满怀欣喜的写道: “老人收泪前致辞,官军入城人不知。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 然这样的诗在元和期间是多么难得。在刘禹锡的诗集里充斥的全是其对贬谪所导致的生命沉沦的不满与怨愤,希翼重新被朝廷起用的激切,乃至产生心如死灰之感。应该说刘禹锡所追求的政治理想的本质是实现其个人价值。客观上政治观点的被采用并不能让刘禹锡满足,因为当他的政治观点被采用时他还被贬谪在外,他的个人价值还没有在实现政治举措的过程中得到发挥,则纵然政策很成功,刘禹锡也不能由心安慰。在刘禹锡的眼中,忠君思想更重于爱民,实现个人价值的必要条件就是回到朝廷参与国家机要。刘禹锡在贬谪期曾任朗州司马,历任连、夔、和三州刺史,为地方的高级长官。在此期间刘禹锡写了不少贴近民间生活的诗歌,如 《采菱行》全诗前五分之四记录了采菱姑娘们在辛勤劳动中活泼、可爱的情态, 洋溢着一种清新欢快的风神情韵。然末尾四句诗人笔锋一转, “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 当年屈原流放于沅湘间却心系怀王,眷恋楚国,刘禹锡以屈原自比托思对朝廷、君主的思念,在浓厚的乡土风情中插入诗人逐臣思归之情,于全诗有狗尾续貂之累。 其对百姓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其心中时刻不忘朝廷又怎能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中去体会百姓的苦乐。再如,刘禹锡任连州、和州刺史时,当地都曾发生过灾旱,刘禹锡积极部署 “慰彼黎庶” (《和州谢上表》),然作为一个“家本儒素” (《夔州谢上表》)、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封建士大夫来说,刘禹锡更多的是将之作为自己的责任在积极奔波。亲身经历过灾旱的刘禹锡在他的诗中却极少描述到当时百姓的生活情景,只是在奏章上略加描述。对百姓,刘禹锡是一种负责,对君王朝廷,刘禹锡是诚心归依。刘禹锡之所以重君而轻民自有其阶级性原因,然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刘禹锡认为他的个人价值只能在仕途中实现,而且是一条青云直上的仕途,而能给予他这样机会的只能是君王权贵。
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刘禹锡一直坚信 “天与所长” “使施兮” (《子刘子自传》) “于是蹈道之心一, 而俟时之志坚。”(《何卜赋》)而现实是他的这份坚持并不被统治者和当权者所认可。刘禹锡也不甘心在地方做困于浅水之蛟。更为重要的是在唐代贬谪官是没有自由的,一个依附于专制皇权的官员连最起码的行动自由都没有,何况皇帝权臣的猜忌、百官的“交口相攻”,更又何谈实现个人价值。元和十年刘禹锡再度出贬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 “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 刘禹锡的思想取向圆柔不能不说是贬谪经历与变幻莫测时局给予他的必然产物。 对于 “一坐飞语, 如冲骇机”(《谢中书张相公启》)的经历,刘禹锡更是发出 “长恨人心不如水, 等闲平地起波澜”(《竹枝词九首》其七)的嗟叹。这一切无不使刘禹锡转变心性,二十二年的贬谪经历磨去了刘禹锡少年的“孤直”,学会更多的思考问题,其心性也由外向的激切勃发向内在的理性收敛发展,其对待人生遭际也在反思中走向成熟。
三、时代的必然
刘禹锡的这种心态转变在中唐并不是特殊状况。中唐是一个精神崩溃与精神重塑的时代。 “战争和动乱扭曲了世人,一种深刻的变化在社会内部潜移默化地进行着,传统的生活观受到蔑视,时代精神和人们的心理遭到改变……迫使人们以一种新的观念,新的方式生活着。” 中唐以后短暂的元和中兴随着宪宗的死一去不复返, 大唐反旗四树,元和表面的安定统一毁于一旦, 君臣无序,上下颠倒,传统道德观念处于崩溃边缘,必然导致人们价值观的改变,享乐主义、悲观主义、颓废主义随即产生。个人是处于特定时代中的个人,时代的整体精神面貌左右着个人的价值取向,尤其与时代潮流融合为一的个人。中唐混乱的形势处处表现出这是一个不能用理性来判断的非理性时代。如果说一个富盛的时代能够产生像李白那样浪漫的诗人,那么一个非理性的时代只能产生理性的文人。富盛时代宽松的社会环境允许李白式浪漫诗人天马行空式的放纵,然在非理性时代,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迫使人们不再单纯依靠想象、理想而存在,而是 “努力寻求着一条既能够为现实社会所容,又能使自己的心灵安适的生存之路”, 表现在精神层面上即由外向向内向深化, 向生命的本体复归。以中唐五大诗人: 韩愈、 柳宗元、 刘禹锡、白居易、元稹为例,他们都是抱着济世之心曾显赫于仕途, 也都曾在仕途中遭受困厄。纵观这些诗人,白居易是其中见机最早的一个,早在永贞元年白居易目睹永贞革新失败者的遭遇便感叹“由来君臣间,宠辱在朝暮”的残酷现实,发出 “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 (《寄宦者》) 的感慨, 在贬居江州时,白居易“胸襟曾贮匡时策,怀袖犹残谏猎书。从此万缘都摆落,欲携妻子买山居。” (《端居咏怀》)到最后“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 (《咏怀》)走出一条亦隐亦宦之路。韩愈早年亦“少年气真狂,有志与春竟”(《东都遇春》), 然遭贬潮州之后, 韩愈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汲汲于自我得失,甚至建议宪宗 “东巡泰山,奏功天下”招后人物议之为 “催挫献佞” (洪迈 《容斋笔记》),远无当年的慷慨磊落之气。 再如柳宗元的“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冉溪》);元稹的 “剑头已折藏须盖, 丁字虽刚屈莫难。休学州前罗刹石,一生身敌海波澜。” (《寄乐天》)这五位诗人在经历了人生起伏之后,不同程度的颇乖前志,不约而同的走向人生的另一条道路,即由当年的积极用世到后来的逐渐顺势内敛的自保之路。这种趋势在中唐已是普遍现象,是士人在险恶环境中探寻到的一条保身之秘,是士人在经历了自我人生追求与时代环境冲突失败后对人生历程的理性抉择,更是时代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