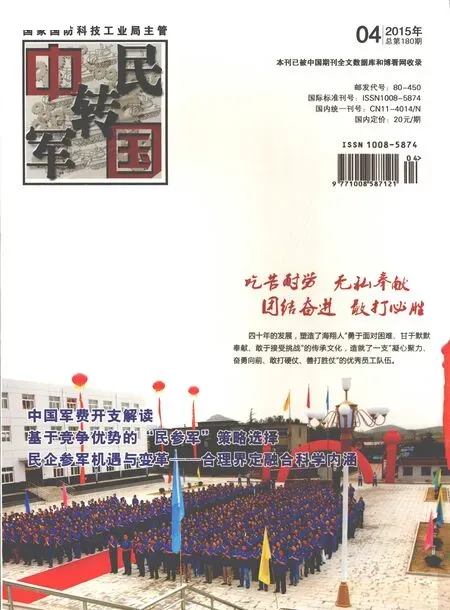于敏:隐姓埋名地站在核前沿
■ 吴志菲
于敏:隐姓埋名地站在核前沿
■ 吴志菲

于敏档案盘点:
于敏,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26年8月出生于河北宁河(今属天津),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副主任、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2015年1月9日上午,一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摘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桂冠的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院士双手紧握……
微驼的背,稀疏的华发,慈祥谦和的长者。于敏曾被隐姓埋名近30年,直到1988年身份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就连于敏的妻子都曾感慨:“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今天,很多人称呼于敏为“中国氢弹之父”。对于这称呼,于敏极力反对,他常常对身边工作的人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实在追问之下,于敏只是说:“在氢弹的理论设计中,我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隐姓埋名的岁月
1961年1月的一天,于敏应邀冒雪来到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一见到于敏,钱三强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经(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所里研究,请报上面批准,决定让你参加热核武器原理的预先研究,你看怎样?”
从钱三强极其严肃的神情里,于敏立即明白,祖国正在全力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理论也要尽快进行。
在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为什么提前研究氢弹?原来,原子弹和氢弹有很大差别,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氢弹的威力要大得多。
接着,钱三强拍拍于敏肩膀郑重地对他说:“咱们一定要赶在法国之前把氢弹研制出来,我这样调兵遣将,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相信你一定能干好!”片刻思考之后,于敏紧紧握着钱三强的手,点点头:“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98年解密。连妻子孙玉芹后来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晚年,于敏说,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氢弹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核大国对技术绝对保密。我国科研人员重担千斤。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的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
一次核试验前的讨论会上,压力、紧张充斥整个屋子。这时,只听到——“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敏和陈能宽两位科学家忽然你一句我一句地将诸葛亮《出师表》背诵到底。那一刻,在座所有人无不以泪洗面,所有人真切体会到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
当时,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几年里,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严谨治学、一丝不苟是于敏最大的特点。作为一个科学家,有许多事他不亲自去做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于敏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无论是作为理论部的副主任,还是作为副院长,他从来不满足于听汇报,凡事自己要亲自画图纸。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之后的12月28日,又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进行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速度之快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1965年1月,于敏率领“轻核理论组”携带所有资料和科研成果,奉命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9月,他带领小分队赶往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做密集的报告,寻找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
一天,于敏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第二天,邓稼先就赶到了上海。一到嘉定,就钻进计算机房,听取了于敏等人的汇报,并与他们讨论分析,兴奋的像个大孩子头儿。
经过著名的“百日会战”,于敏率领的团队实现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并定型为中国第一代核武器。曾有核武器专家指出,世界上仅有两种氢弹构型,一种是美国的T-U构型,另一种就是于敏构型。而于敏构型比美国T-U构型设计更加巧妙,首爆氢弹体积比美国要小。
1967年6月17日8时,罗布泊沙漠腹地。徐克江机组驾驶“轰6”进入空投区。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弹体降到距地面2900多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

2015年1月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颁给于敏院士
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强烈的光辐射,将距爆心投影点400米处的钢板铸件烧化,水泥构件的表面被烙;布放在8公里以内的狗、10公里以内的兔子,当场死亡一半;700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破坏,车内动物全部炭化;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3公里、重约54吨的火车吹出18米,近4公里处的半地下仓库被揭去半截,14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科技人员把爆炸当量的数据送上来了——330万吨。
但听一声惊天“雷鸣”,万里碧空升腾起炽烈耀眼的火光,一朵蘑菇云顶天立地……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参试人员个个激动万分。此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守候在电话旁,他早已成竹在胸。“我这人不大流泪,也没有彻夜不眠,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多年之后,于敏回忆说。
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庄严宣告:“我国在两年八个月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东方巨响,震惊世界。西方科学家评论道: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后来,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杜祥琬曾与于敏共事多年,全程参与了氢弹的研制,他透露:“实际上,早在1966年12月28日,我们和于敏在罗布泊进行的‘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就标志着我们已经掌握了氢弹的所有特征。”杜祥琬回忆道,于敏的脑子极快。1966年在上海做氢弹理论实验,计算机不断吐出纸带,上面记录着氢弹每个时间、空间点的变化。于敏一眼就发现从某个点开始,纸带上的数据出了问题。“这需要很高的物理理论基础才能做到。说明于老的理论功底极好,脑子极为敏捷。”
突破氢弹后,于敏带领团队乘胜又干成几件事——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为我国核武器发展战略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今天看来,件件意义深远。
三次死里逃生后站在核前沿
由于工作的需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常年转战的是新疆、青海的荒野戈壁和四川的深山老林。工作条件之艰苦难以想像,有的地方甚至连基本的查资料看书的条件都不具备。在这样的环境下又承担的是那样的工作压力,许多科学家的身体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于敏作为“两弹”的核心人物更不例外。
1969年,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大型空爆热试验并行准备,连着做。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的身体很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岗上看火球时,就见他头冒冷汗,脸色发白,气喘吁吁。大家见状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正当于敏他们在为祖国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的时候,林彪发布“一号命令”,直接插手核武器的研制工作,理论部被迫搬迁“三线”,不少专家被打到河南喂猪放牛种地。于敏、周光召等幸免,但必须举家随大队人马迁往大西南。
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回到北京后,于敏的病情日益加重。1971年9月13日,林彪阴谋败露,研究院的斗争也降了温。军管组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特许于敏的妻子孙玉芹10月回京探亲。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心急,赶紧扶他起来给他喂水,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连军管组都同意,作为特例,将于敏的妻子迁回北京。
这次出院后,于敏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为了完成任务,他顾不上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再次奔赴西北。1973年由于在青藏高原连续工作多时,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他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了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于敏虽然身体不好,但是从来没有因为身体情况耽误过丝毫工作。作为研究人员,于敏的工作对象是武器理论设计,但他对实验相当重视。著名实验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曾说接触的我国理论物理学家中,最重视物理实验的人是于敏。他八上高原,七到戈壁,为我国的核武器事业,隐姓埋名,殚精竭虑,确实到了鞠躬尽瘁的地步。1980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20世纪80年代初,于敏就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理论研究的开展。
1986年初,邓稼先和他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对我国所处发展阶段作了准确估计,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伏案工作的于敏
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衍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他们的建议被采纳后,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1993年后,于敏给新任院领导写信,提出核禁试后一定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用经过实验校验的精密的计算机模拟来保障库存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性。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于敏第一个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了言。
于敏虽然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但他仍然关注着这一领域的最新动向。他认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武器对它没有威慑性。防御了对方的威慑,就成为新的垄断。于敏说:“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以保持我们的威慑力。”
——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