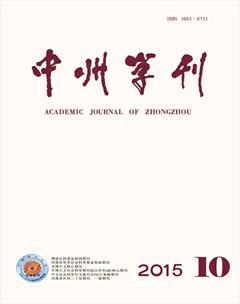《红楼梦》女性悲剧的制度文化原因探究
徐继忠
摘要:尽管以林黛玉为代表的《红楼梦》中众多女性悲剧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导致她们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却是一样的,这就是中国古代男权主义制度和专制主义制度以及二者派生出的世袭制度、婚姻制度、嫡庶制度、教育制度、司法制度、官僚制度等等。正是这些腐朽落后的制度剥夺了她们的自由、压抑了她们的情感、摧毁了她们的理想、泯灭了她们的才干,最终戕害了她们年轻的生命。隐藏在这些制度背后的是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君贵奴贱的政治文化和亲亲尊尊的伦理文化。
关键词:红楼梦;女性悲剧;男权;制度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149-04
《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这是众多文学大家的共识。王国维先生认为,《红楼梦》打破了中国历代小说与戏剧中始离终合、始悲终欢、始困终亨喜剧结局的传统观念和写法。他指出:“《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①王国维先生从西方美学的角度阐释《红楼梦》的悲剧价值,这一阐释开辟了现代小说学的审美性研究领域,在红学研究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从社会和人生的角度探究《红楼梦》悲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②海外新儒学的重要代表和集大成者牟宗三先生认为:“《红楼梦》乃悲剧中之悲剧”,“黛玉之死是第一幕悲剧,宝玉出家是第二幕悲剧”。③这是牟宗三对这部伟大现实主义杰作的悲剧演成轨迹进行的历史性定位。
与《窦娥冤》和《孔雀东南飞》等以单个女主人公为中心的女性悲剧相比较,曹雪芹通过《红楼梦》塑造出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性女性悲剧世界,并且在这一悲剧世界中表达了他对那个社会的深刻批判。对此,红学家佩之先生认为:“一部《红楼梦》,他的主义,只有批判社会四个字。书里面的社会情形,正是我国社会极好的一幅写照。”④从中可以看出,佩之先生是在揭示《红楼梦》的悲剧思想主旨,并进一步指出这一“批判社会”之思想主旨是通过曹雪芹用隐形的批判手法演绎出来的。
以往学者们研究《红楼梦》大多从美学、文学、哲学等角度欣赏这部“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人物生动”的伟大杰作,而本文则从制度的角度来审视曹雪芹对当时社会诸多弊端的深刻思考,同时还试图从文化的层面揭露封建制度在残害妇女方面所犯下的深重罪孽。
一
从中西方悲剧理论对比角度来看,《红楼梦》确立了独树一帜的制度悲剧理论。同“悲剧源于个人欲望”的西方悲剧理论不同的是,曹雪芹认为《红楼梦》中年轻女性的悲剧,是中国古代一系列封建制度的悲剧。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就会发现男权主义制度和专制主义制度是封建制度的核心制度。而当男权主义制度和专制主义制度融合生长在一起来掌控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时,年轻女性的生存空间就会被挤压到社会的边缘,导致她们的发展权利、受教育权利和政治权利等诸多权利被男权与强权全部剥夺,由此她们成为“裸权族”。
具体来讲,封建文化控制下的封建意识和封建伦理剥夺了女性的发展权利,这等于扼杀了占总人口约50%的女性的聪明才智和劳动权;“女子无才便是德”扼杀的是女性的受教育权,使女性在蒙昧无知中艰难生存;“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剥夺了女性的政治权利,框定的是女性的狭隘活动空间;“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更是剥夺女性自由和幸福的帮凶。《红楼梦》中进入“薄命司”行列的“金陵十二钗”便是被上述传统文化垃圾繁衍出的中国古代封建制度摧残的典型女性悲剧代表。
中国古代女性的悲剧与女性权利丧失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她们的悲剧正是因为权利被剥夺了才使得男权与强权可以任意蹂躏她们。整个中国古代女性的悲剧都是源于男权主义制度和专制主义制度高压态势下形成的婚姻制度、教育制度、司法制度、世袭制度的联合迫害。而这些腐朽落后制度的产生与形成又是源于中国古代农耕时期经济基础和家庭发展状况。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⑤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楼梦》这部旷世之作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描述中国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吃人本质的百科全书。中国传统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却是残缺的,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呈现出其腐朽性和落后性。“《红楼梦》之所以是伟大的悲剧,正因为它是诗意生命的挽歌,把最有价值的诗意生命毁灭给人们看,便构成最深刻的感伤主义悲剧。”⑥曹雪芹用美好的诗词歌赋等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赞美的就是这些优秀的青年女性,而戕害这些女性“诗意生命”的正是残缺落后的封建制度。
贾元春是无数皇帝宫中女子悲惨命运的代表。元妃省亲看似场面宏大,实际暗藏悲音。读者听到的是元妃的哽咽哭泣,看到的是她满眼的泪花,这是元妃对自己以及像自己一样的众多女性在皇宫中生活的“写真”。元妃的哭泣正是对皇家男权的血泪控诉,是对一切没有人情味的皇权的诅咒。贾元春虽然才选风藻宫,但是强大的皇权和男权让她在省亲时因哽咽而说不出话来。皇帝是男权的代表,在“一夫多妻”制度下,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仍然满足不了皇帝的淫欲,致使元春在“那见不得人的地方”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这无疑是在诉说千千万万个像元春一样的女性都在皇权制度压抑下这样悲惨地死去。可见,封建皇权制度既是中国古代男权主义制度的最高形式,也是所有制度中最腐朽、最落后、最残忍的制度元凶。
可以说,男权与王权结合产生的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意义上的男权。男权与家庭权利结合形成了族权、父权和夫权,女性依据“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规定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而“三纲五常”和“七弃”(也称“七去”或“七出”,是我国古代的离婚制度)则赋予家庭中男性的绝对权力,于是性别压迫、性别歧视、性别奴役在家庭中普遍出现。贾迎春是依据“在家从父”规则嫁给孙绍祖的,又是依据“出嫁从夫”而遭受“中山狼”的百般凌辱的,最后孙绍祖还是依据在家中的男性绝对权力将迎春迫害致死。即使是王熙凤这位脂粉堆里的英雄,仍然逃脱不了贾琏这个渣子男根据“七弃”这一离婚制度而最终将其休弃的厄运。曹雪芹通过《红楼梦》对女性悲剧命运的研究,揭开了封建制度支撑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的运行机制。正因为批判这样的社会运行机制,曹雪芹才创立了“悲剧源于社会制度”的中国古代悲剧理论。
男权在与女权较量中经过确立、稳固、扩张之后,还发生了适合那个时代的变种,世袭制就是男权主义制度与官僚制度结合演绎出的变种形式。需要指出的是,世袭制与其他封建腐朽制度一样,也是迫害女性的工具。男权在社会中确立统治地位后,还面临着男权统治地位的延续问题,即男权的可持续传递问题,而男性借助男权通过迂腐的世袭制巧妙解决了男权统治地位的延续问题。这样一来,皇权的延续依据的是世袭制,官僚的延续依据的也是世袭制。于是,无才无德的皇帝之子依据世袭制名正言顺地成为国君,继续蹂躏像元妃一样的女性。而像贾赦、贾珍等一群道德败坏的世家子弟依据世袭制袭了官,他们借助官僚权力将男权连续化和具体化,从而可以继续迫害像秦可卿、鸳鸯、尤三姐等年轻的女性。《红楼梦》中除去贾宝玉懂得怜香惜玉之外,有谁尊重女性、爱惜女性、懂得女性呢?有谁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用真正的感情去爱过女人呢?又有谁在女性遭受欺凌、迫害、蹂躏之时,而对可怜的女孩们施以援手呢?可见,在男权主义制度下,上至皇帝,中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官吏,男权主义制度都是迫害女性的罪魁祸首。
二
从中西方悲剧意识载体对比角度来看,《红楼梦》创立了文化悲剧论。与西方悲剧意识载体不同的是,《红楼梦》的悲剧意识载体是传统文化。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至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易卜生的社会悲剧,再到奥尼尔的当代悲剧,基本上表现了西方悲剧意识载体的核心内容及演进路径。而曹雪芹却相异于横向意义上西方的悲剧意识载体定势,着力从纵向传统文化中提炼出不同于中国古代历史上以“和”为文艺思想的喜剧结局规律及表现方式,在沉沉的哭泣中控诉男尊女卑文化的种种罪恶。
众所周知,对什么是自由以及如何获得自由的解答方式不同,成为区别不同文化的精神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意识和男权至上原则禁锢的恰恰是女性的自由,而用来禁锢女性自由的正是在落后传统文化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封建制度。从表面上看,是皇宫、家族、寺庙禁锢了女性的自由,实际上是传统的腐朽制度剥夺了她们的自由。在这些“吃人的制度”中,男权主义制度是“吃人的制度”的主体。这样一来,男权主义制度和专制主义制度就是导致女性悲剧命运的最强幕后黑手。当男尊女卑的文化基因和男权至上的制度形式契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古代中国独有的制度文化。
在《红楼梦》中,无论是性格孤傲的林黛玉,还是八面玲珑的薛宝钗,都属于“薄命司”之列,都没有逃脱悲剧的命运,这就从根本上相异于西方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论”。不仅贵族小姐不是因为性格而“香消玉殒”,就连女奴丫鬟们也不是因为性格才导致“红颜薄命”。活泼、开朗、率真的晴雯被逐出贾府最后悲惨地死去,“心地纯良、克尽职任”的袭人虽然随和、温顺、贤良却也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无论是最尊贵的贾元春,还是想有一番作为的贾探春,同样也都没有逃离悲剧命运的折磨,这从另一个侧面相异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说”。这是因为,贾元春和贾探春都属于生于“末世”中的“有命无运”之女子,等待她们的只能是悲剧的结局。这些鲜活女性都是男权制度文化这一无形大网中的不幸小鱼,最终都会被男权文化无情地吞噬掉。
可见,由男权衍生出的皇权、族权、父权、夫权是男尊女卑社会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实施性别压迫、性别迫害和性别歧视的利器和工具。当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被普遍接受时,男性据此蹂躏女性,男性据此为所欲为。女性若反抗,结果就是鱼死网存;女性若不反抗,最终命运也是水枯鱼亡。晴雯是有反抗意识的,而袭人是顺从封建男尊女卑文化的,她们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她们的命运可谓殊途同归。在中国古代女性命运的出口处,迎接她们的都是同样的不幸和悲哀,而这恰恰证明了女性悲剧的必然性。这样一来,西方的性格悲剧意识载体和命运悲剧意识载体都相异于中国古代悲剧现实,中国古代悲剧意识载体就只能定格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层面。
三
从中西方悲剧本质对比角度来看,《红楼梦》形成了“女性悲剧就是国家悲剧”的东方悲剧本质论。有关悲剧本质的问题历来是哲学家和文学家们探讨的理论问题之一。对此,亚里士多德、黑格尔、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都有过精辟的论述。但在众多的理论家中,尼采对悲剧本质的揭示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认为:“希腊艺术的繁荣不是源于希腊人内心的和谐,反倒是源于他们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因为过于看清人生的悲剧性质,所以产生日神和酒神两种艺术冲动,要用艺术来挽救人生。”⑦鲁迅先生也提出过既简捷又明了的观点:“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些论述都说明,再现人生的不幸和毁灭是悲剧的本质。这种“不幸”和“毁灭”出现在中国古代时,主要降临到了那些可爱的女人身上;但在西方古代社会,这种“不幸”和“毁灭”则主要由那些强有力的男子来承担。当女性成为悲剧主角时,国家和社会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女性悲剧与国家悲剧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呢?
在《红楼梦》的众多女性悲剧中,贾元春悲在宫中,贾迎春悲在家中,贾探春悲在和亲中,贾惜春悲在庙中,妙玉悲在庵中,这是众多女性悲剧的空间载体。林黛玉是有爱而无婚姻的悲剧,薛宝钗是有婚姻而无爱的悲剧;王熙凤是有才干弄权腐败者的悲剧,李纨是“三纲五常”约束下无青春气息者的悲剧;还有晴雯、金钏、十二戏子是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底层人的悲剧。这是《红楼梦》中女性悲剧的不同内容和不同表现方式。虽然她们悲剧命运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她们“悲”的根本原因是无差异的。王蒙指出:“《红楼梦》的悲剧是感情悲剧也是政治悲剧,是文化悲剧也是社会悲剧,是家庭悲剧也是个人悲剧,是形而下的悲剧也是形而上的悲剧。”⑧由此将感情悲剧、家庭悲剧、政治悲剧、文化悲剧和社会悲剧联系在一起,形成最强烈意义上的国家悲剧。既然上至贵妃娘娘,中至贵族小姐,下至奴仆丫头的命运都是不幸的,那么,等待这个民族与国家的最终结果也必将是灭亡的悲剧。
《红楼梦》同其他爱情悲剧和家族悲剧不同的是,曹雪芹通过描述年轻女性的悲剧,让读者深深地感受到“女性的悲剧就是民族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和国家的悲剧”。初看《红楼梦》,感觉她是一部描写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爱情的悲剧小说;再看《红楼梦》,发现她是一部述说贾王薛史四大家族兴衰的家族悲剧;细读《红楼梦》,方解其中民族意义和国家意义上的“辛酸泪”一二。当我们静静地深入品味《红楼梦》时,才窥出伟大的曹雪芹想要告诉后人的是:在当时清朝政府标榜的所谓“盛世”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或者说,“末世”就要到来。更进一步讲,在这个真正的“末世”中众多鲜活女性生命的悲剧就是这个民族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和国家的悲剧。而更为可悲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预测不到“末世”即将到来,也不知道“末世”中天天上演的这些悲剧必然发生的根本原因,更不懂得“伟大女性孕育高尚民族和伟大国家”的深刻道理!
四
从东西方悲剧写作方法对比来看,《红楼梦》的写作手法是独树一帜的。与西方悲剧的比较法、透视法、历史的方法等不同的是,曹雪芹采用了光影对照法来阐释《红楼梦》的深刻思想内涵。在贾府出现的水、代、文、玉、草这五代男人中,虚写的是水、代两辈,实写的是文、玉、草三辈。从第三代开始,贾府便一代不如一代了:要么一心炼丹,只求长寿,贾敬就是第三代中这样的好道之辈;要么放荡无为,好色成性,贾赦就是第三代中这样的龌龊之辈;要么性本愚暗,庸懦无能,贾政就是第三代中这样的平庸之辈;要么荒淫无度,穷奢极欲,贾珍就是第四代中这样的享乐之辈;要么偷鸡摸狗,朝三暮四,贾琏就是第四代中这样的下流之辈。如此的后几代是贾府男人中的真实面貌。曹雪芹就是以贾府男人作为阴暗的“影”,而以年轻女性作为明亮的“光”,在“光”与“影”的对比中,歌颂女性的真善美,鞭挞男性的假恶丑,突出表现了女性的率真、美貌、善良和才干,深刻揭露了男性的不学无术、好逸恶劳、奢侈腐化、凶恶狠毒和冷酷无情。
通过艺术性的光影对照法,曹雪芹让读者体会出中国封建社会男性与霸权对女性的摧残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过,这使得女性的形象在对比中变得伟大而且清晰。然而,如此光鲜、异样、优秀的年轻女性,却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结局。这表明《红楼梦》说的不是一个女性的悲剧,也不只是某个婚姻问题的悲剧,而是那个社会里青年女性的普遍悲剧。“光”与“影”的对比越强烈,这些优秀女性被毁灭的价值就越高,悲剧的价值也就越高,从而悲剧的思想价值取向也就越明确。如此的写作方法,是西方悲剧写作手法无法比拟的;这样的独特写作手法表现出来的思想价值取向也是所有中国古代小说中独一无二的。
注释
①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②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8页。③牟宗三:《红楼梦悲剧之演成》,《文哲月刊》(第1卷),1935年,第19页。④佩之:《红楼梦新评》,《小说月报》(第11卷),1920年,第8页。⑤[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页。⑥刘再复:《红楼梦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99页。⑦[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⑧王蒙:《红楼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285页。
责任编辑:行健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