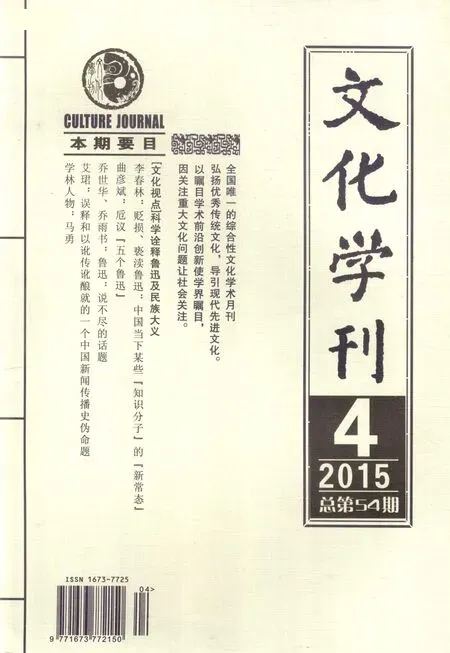生态批评视角下的生态价值观研究
杨海燕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辽宁 大连 116035)
生态批评视角下的生态价值观研究
杨海燕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辽宁 大连 116035)
生态困境直接催生了生态批评思想的问世,迫使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反思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生态批评认为,生态问题不仅出现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同时也发生在精神领域里,人的生态与人的心态密切相关,生态问题的解决首先有赖于人类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取向,生态价值观作为一种精神因素,将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推动力和活力。
生态批评;生态价值观;大地伦理;诗意的栖居
现代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在比较中印欧三大文明特征时说,人这一生总要解决三大关系,而且顺序是不能错的。首先要解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其次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一定要解决人与内心之间的关系(梁漱溟)。这一命题恰好也是生态批评思想的宗旨和任务。生态批评认为,只有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物)的关系,其余的两个关系,即人与人、人与自我(内心)之间的关系才会有解决方案。
纵观人类社会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视线就不曾中断过。由于人类不合理的行为活动,人类物质与精神价值取向的颠倒,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生态危机,人的生存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生态困境直接催生了生态批评思想的问世,迫使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反思人们行为的价值取向。由此,生态批评者指出,人的生态与人的心态密切相关,生态问题的解决首先有赖于人类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取向,生态价值观作为一种精神因素,将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新的推动力和活力。
一、“寂静的春天”:生态价值观的里程碑
《寂静的春天》(1962)一书通常被视为是生态批评浪潮中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生态价值观创立的一个里程碑。这部划时代的著作“改变了历史进程”,“扭转了人类思想的方向”,[1]开创了生态时代的新文明,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生态保护运动应声而起。
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是一名海洋生物学家、生态作家,以其代表作《寂静的春天》拉开了生态革命的序幕。《寂静的春天》主要描述了使用化学药剂对生物的危害以及对天空、海洋、河流、土壤、动物、植物的影响与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春天本应是一片万物复苏、郁郁葱葱、生意盎然的生动景象,但在《寂静的春天》里,由于人们滥用杀虫剂的结果,到来的春天却是死寂沉沉,没有百花争艳、没有鸟语花香,一切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通过这个寓言,卡森警示人们,倘若继续滥用这些“死神灵药”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一个无鸟鸣唱的“寂静的春天”会不期而至。
《寂静的春天》以大量的事实和科学依据揭示了滥用杀虫剂对生物界、自然界的破坏和对人类健康的损害,抨击了这种依靠工业技术来征服、统治自然的生活方式、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处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2]
在西方的文化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它充满着整个精神文化空间,即认为科学是知识和真理的至高权威。1687年,牛顿完成了宏大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用英国哲学家 A.N.怀特海的话,就是整个世界进入了“崭新的时代”,即工业时代。然而,牛顿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是机械的、工具的,他认为自然世界是一种客观存在,大自然是为了人类利益而存在的,人完全可以凭借着科学来征服和统治这个世界。始于 17世纪启蒙运动倡导的理性主义,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图景完全被打破了,一个有机统一的世界被分裂开来。在启蒙运动之光的照射下,人类凭借着理性知识,凭借着科学技术的无穷力量,向大自然展开了全面的进军。18世纪的西方产业革命带来了物质的富庶、繁荣,也带来了环境灾难、资源贫乏和人口膨胀等生态问题。从17世纪以来笛卡尔和牛顿开始的机械的自然观,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可以对自然肆意掠夺,最终把人类自己置于空前的生态困境之中。
《寂静的春天》之所以成为一部伟大的生态批评文本,不但是因为卡森揭示了杀虫剂对生物和人类的危害,更大的原因是她对人类控制自然提出了质问,质疑了科学技术社会对自然的基本态度,指出“隐藏在干预和控制自然的行为之下的危险观念”,她说,“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哲学观点,放弃我们认为人类优越的态度”,[3]因为人们的生存受到威胁不是来自于自然世界,而是人类对大自然所抱有的那种傲慢、无礼和狂妄的态度和行为所导致。卡森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原有的自然观、哲学观,建立起全新的生态思想和生态哲学观。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大自然的淡出和缺席已成了此后社会文明中一切缺憾的根源,卡森和她的《寂静的春天》对改变人类傲慢的自然观和世界观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正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谈及到《寂静的春天》时所说的那样,“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4]自 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日益紧迫,生态批评家、生态思想家和生态伦理学者把人类对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的观念的历史性反思和哲学批判一直触及到《圣经》,美国生态学家、史学家林恩·怀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5]人们当今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是自启蒙运动和工业文明以来,支配自然、违背自然规律、干预自然进程、破坏生态平衡的必然结果,人类自己应当做出深刻的反思,人类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应当改变。
二、“大地伦理”:生态价值观的哲学思考
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具有深刻的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思想文化根源。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不仅作为一种理论选择具有现实的和策略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哲学伦理学或价值论上的合理性。早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里就这样写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须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昆虫并海里的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手中。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为你们的食物,如同我赐给你们的蔬菜。”在这里,“人类中心”,“人类至上”,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对抗全都被这位“上帝”敲定了。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中,自然界是非人类的,只具有工具价值,它本身没有独立于人类的价值,是一个没有内在价值的客观存在,它被人类利用,受人类驱使,任人类宰割是理所当然的。
在以理性和技术至上的启蒙精神的指引下,人们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大自然攻掠式的无度开发,毁坏一个物种就像撕掉一张纸那样随意,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和谐统一的、相互依存的,而是紧张、对立的关系。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针对启蒙运动导致的人与自然相对立的理性文明,提出了批判和质疑。他们运用辩证的方法,指出了启蒙运动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他们认为,“人对自然工具性的操纵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把“自然界贬成了统治的对象,贬成了统治的原料”,[6]人类实际上就把自己贬成了统治的对象和原料。
在工业文明的进程中,恩格斯就向人们提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取消了。”[7]自然界与人的全面价值关系,如生命价值、审美价值、伦理价值等,都被碾压在工业文明的滚滚的车轮中。可见,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的问题,更是一个信仰问题、审美问题、哲学问题和伦理问题。最根本的还在于改变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即改变人们的机械的还原主义的世界观,建立整体的、多样性的、生态的世界观,以及相互联系的价值观。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美国生态思想家,是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创始人。他的遗著《沙乡年鉴》(1949)被誉为是“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一本圣书”。该书的最后一章“大地伦理”,通过探讨人类与大地的关系,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生态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学,颠覆了以往只有人类之间才存在伦理的观点。
大地伦理的宗旨是人们要从道德上关怀大地,利奥波德指出:“我不能想象,在没有对大地的热爱、尊重和敬佩,以及高度赞赏它的价值的情况下,能够有一种对大地的伦理关系。”[8]他从生态整体利益的高度,去检验每一个问题,去衡量每一种影响生态系统的思想、行为和发展策略。他的大地伦理的检验标准是“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9]利奥波德把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视为最高的善,最高的道德观,他从伦理维度上为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观奠定了哲学基础。
大地伦理认为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自然万物都拥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都拥有自身存在的权利,它们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相对相关的联系。如果说在这个生命共同体当中,人类是最高生物,那也只意味着人类对于维护自然在整体上的完善、完美承担更大的责任,对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性、多样性担当更多的伦理和道德责任。而这正是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所缺乏的东西,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造成了人和自然的深刻的分离和对立。大地伦理则要改变这种理所当然的价值哲学思想,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观。人类是大地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凌驾于大地之上的统治者。
大地伦理把伦理的边界从个人推及到共同体,要求人们“热爱、尊重和赞美大地,高度评价它的内在价值”。利奥波德的这个主张得到了生态哲学家和环境伦理学家的拥护。阿尔贝特·施韦策发出泛爱万物的感想,“有道德的人不打碎阳光下的冰晶,不摘树上的树叶、不折断花枝,走路时小心谨慎以免踩死昆虫。”[10]汉斯·萨克斯在他的《生态哲学》一书中写到,“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这种学说虽然容易让人理解,但这毕竟是一种粗糙的推断。对自然的考察使我们详细地看到人是整体中的一个成员。整体怎能只为其中众多成员中的一个而存在,即使这个成员是最杰出者?把人类视为宇宙中心之说完全忘记了自然。”[11]R.F.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一书中指出,大地伦理“把一种至少是与人相等的伦理地位赋予了大自然。它的对立面是‘人类中心主义’,后者认为人类是所有价值的尺度”。[12]大地伦理给人们的启示就是,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应当受到尊重,甚至大自然的一切,包括山脉、河流、天空、大地在内都体现了宇宙间一种神圣的和谐,它们的存在都应当受到尊重,它们的完整性、稳定性都应当受到维护。
三、“诗意的生存”:生态价值观的实践
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把人从外在的自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使人的内在自然受到工具理性、科技设置和组织管理的奴役,人的思想、精神、个性、感性深受压抑和扼制。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面临的最大的困惑或焦虑,莫过于自我认同的危机。不断变化和日益模糊的参照系,使人们很难找到自己的定位,很难把握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自我”,人与自然天然统一的纽带被切断了,人成了无根基的存在,普遍带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感觉”。科技的发展、人的异化扰乱了人们的价值活动,伦理价值被剥夺了普遍的有效性。
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了社会偏重于理性和理智、偏重于技术和工具、偏重于概念和规则,人们变得越来越趋于物质、技术、使用、功利,越来越重视眼前的和现实的利益。人们不再追求价值理性——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目标。人们更多的是表现出工具理性的行为,即只顾眼前的和现实的利益和需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指出,当代技术的发展同时意味着统治人的力量的发展,物质生活条件已成为外在的强制性力量。
价值理性的萎缩使得人们不再扼守道德、审美、宗教的原则,眼前的、现实的利益高于一切。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消解则意味着人文精神受到冷落、遭到排挤,在衰落。人类要高扬价值理性的大旗,只有人类彻底改变对自然的态度,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才能去矫正被扭曲了的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看来,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人与自然相处的最高境界是人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
“诗意的栖居”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生态价值取向的生活,是践行价值理性,因为信仰的力量、精神的充实可以削减对外在物欲的追求,精神能量的升华可以替代物质能量的流通,是人类有可能选择的最友好、最可行,也是最“低碳”的生存方式。人与万物拥有一个自然世界,人类只是这个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人类是其中进化的最好的生物,那就更应该懂得人类要与自然保持一种平等、友好、亲切的关系,而不是蔑视、敌对、紧张的关系。人类要想长久的生存和发展下去,就要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对于大自然的任何索取都要谨慎为之,学会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保证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符合自然规律。
提及到“诗意的栖居”,人们自然要想到美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梭罗和他的名篇《瓦尔登湖》。梭罗对自然的虔诚态度,他对自然万物的细微观察,他对自然给予人的精神营养和审美价值的赞叹,以及他对他那个时代所流行的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都为人们诗意的筑居、诗意的栖居和诗意的生存提供了独特的灵感和支持。
梭罗的《瓦尔登湖》(1854)则是生态价值观的一个具体的实践。1845-1847年间,梭罗独自来到了瓦尔登湖畔,在他的小木屋里度过了两年多的隐居般的生活。每天他徜徉在瓦尔登湖畔,沐浴在阳光下,观察、思考、阅读、记录大自然的点点滴滴的变化。湖里银光闪闪跳跃的鱼儿,大地上奔跑的各种动物,如松鸡、野鸭兔子、土拨鼠等都是他的伙伴。在物质生活上,梭罗过着最简单、最简朴的原始般的生活,自己种菜,有时靠打点零工支付每个月最基本的生活费,但在精神生活上,梭罗是富有的、满足的、恬静的。作为一位自然阐释者,梭罗通过自己亲身的实验,以诗意般的语言把大自然的美丽、动人和他对自然的深厚感情都写进了他的《瓦尔登湖》。
就像许多西方生态批评学者从东方哲学汲取营养一样,梭罗本人也深受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观的影响,他的《瓦尔登湖》就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所描述的人和自然相伴相生的现代写照。“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作者用白描的手法,描绘出万物生机勃勃、铮铮向荣的景象。春末夏初,飞奔的野雉,饱满的蚕茧,荷锄而归的农夫勾勒出天、地、人那么和谐、优美、令人神往。也许有人会说,这种古代农业文明已是踪迹难寻的往事,但现代人恰恰缺乏的是对自然体贴入微的亲近,在自然之母面前,变得冷漠、麻木不仁,对大自然的赠予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梭罗的《瓦尔登湖》告诉现代人,自然不仅给予人类丰富的物质,还可以净化人们的灵魂,抚慰人们的精神。同样,这样的哲思也见诸于中国古典诗词中:“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山林中这位隐逸者,如同梭罗一样,置身于大自然中,完全可以抛弃个人的名利、虚荣和欲望,闻到大地的芬芳便满怀喜悦了,完全是一种诗意的栖居。人们的这种生态价值取向的生存方式,正是体现了马克思的断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3]
“诗意的生存”可以帮助人类这个最后可能打乱生态系统的物种进行自我节制、自我约束,顺应自然、敬畏自然,回归自然、亲近自然;而“诗意的栖居”就展现在美国生态学家艾伦·杜宁为人类提出的五个“回归”的设想当中:“接受和过着充裕的生活而不是过度地消费,文雅地说,将使我们重返人类家园,回归于古老的家庭、社会、良好的工作和悠闲的生活秩序;回归于对技艺、创造力和创造的尊崇;回归于一种悠闲的足以让我们观看日出日落和在水边慢不得日常节奏;回归于值得在其中度过一生的社会;还有,回归于孕育着几代人记忆的场所。也许亨利·戴维·梭罗在瓦尔登湖边告诉了人们一个真谛:‘一个人的富有与其能做的顺其自然的事情多少是成正比’。”[14]
四、结束语
启蒙主义曾让人类骄傲地认为他可以战胜自然,取代自然,高踞于自然万物之上,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却破坏了生态系统,造成了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技术与情感、智慧与良心的割裂与对抗。以卡森《寂静的春天》为标志的现代生态运动的兴起,使现代社会中一路飙升了三百多年的科学技术的地位受到质疑,生态文明正是对启蒙理性主义至上、科学技术主义至上、工具理性至上的反思,审视与批判。信仰的执着、哲学的反思、诗意的生存再度唤起人们对于生命的敬畏,对于自然的亲近,对于伦理价值的思考。大地伦理强调大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与自然万物是一种平等关系,是来自一个大家庭的亲情关系,它体现了人和自然地和谐、协调与一致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而这正是生态价值观所具有的超时代的价值观。

泥模艺术——喂猪
[1][3]Paul Brooks.The House of Life;Rachel Carson at Work.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2.227.293-294.
[2][4]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87.
[5]Lynn White.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Cheryll Glotfelty&Harold Fromm.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6- 14.
[6]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35.
[7]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78.
[8][9]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13.216
[10][12]R.F.Nash.大自然的权利[M].青岛:青岛文艺出版社,1999.73.9.
[11]汉斯·萨克斯.生态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9.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9.
[14]艾伦·杜宁.多少算够[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13.
【责任编辑:王 崇】
I0-05
A
1673-7725(2015)04-0226-06
2015-03-06
杨海燕(1956-),女,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西方文论及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