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的风车
陈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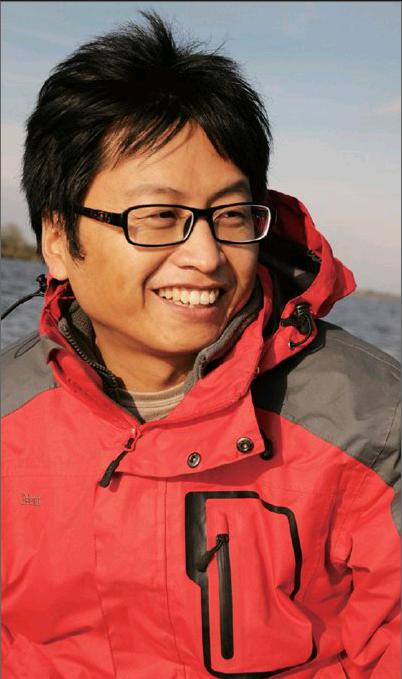
究竟该如何将世俗的语言铺垫成一首诗?是陷入先验的载道泥淖,为了什么而作或者追求诗歌形而下的诗外意义,还是跟随诗意的牵引随意赋形?如果将诗歌视为语言的孕育者,一直以创造的姿态引领着语言前行的步伐,那么后者显然是良途。将神秘至于天赋的诗意体验赋予滞后的语词,而非执拗于从现有词汇中发掘诗意,是优秀的诗篇萌生的惯例。冯晏的诗就是在不停地“布”这样的诗歌语言的格局,扩展已有词汇的阈限。她总是试图用超越性的感受将诗歌置入更为广阔的跨界精神经验之中,以先锋的意义综合各种诗性元素,以新鲜的感触覆盖词汇的过去,这是她的诗歌世界的惯性,一往无前并不可中止。《航行百慕大》是她最近完成的一部相对较长的诗篇,是依据去年春天专程旅行百慕大的经历写作的,可以看作是又一次在语词经验的意义上超越过去的标志性诗篇,甚至有诗学风范的阶段性质变的征象。
诗人以大开大合的想象建构海上的几个夜晚,在百慕大三角的历史与现实中穿梭,在人、星空、宇宙、海浪、黑夜等居于同一时空的意象中思考“恐惧”与“消失”的意义,于意识流的碎片式思绪涌动中,勾连起诗意与思想的系结。现实和传说中的百慕大三角是神秘的,飞机、舰船等无征兆的失踪让这片浩瀚的海域充满不安和恐惧。但对诗人的汹涌思想来说,这种时间终结的地方却恰恰是获得永生的“窄门”,“百慕大三角,让我的虚弱通过这道窄门”,透过它,“消失本身就是进入真相,或者永生”,于是诗人以想落天外的思绪营构出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消弭了物象间的差异,衰老了时间带来的沉重,“远离是一种接近”,“坚强是软弱的”,一切轻如飞鸿,无论欲念与暴躁,甚至是“现实和非现实”,在一个风月无边的意念场域里,“流星溅起几只西伯利亚雪雁,/划破冥想;犹如在非洲,羽毛眷恋宁静,/成片白鸥瞬间藏起整条河流”,如此大量的罗列色彩纯白淡雅,而又空间跨度极大的意象,来表征刹那间的浪花涌流充盈出的溢彩诗意,跳脱而阔达,月涌大江流,诗意斐然。或者说,整首诗都是诗思流韵、意象惊艳的,“船尾奔跑,一只白狐吸光了空气”,将航船的轨迹描画得如此灵动、鲜活的,只能是黑格尔说的“这一个”。“一只白鲸弓起脊背,鳞片映出玄月。海浪,/芙蓉花飞溅,每一滴水都被海藻和未知的气息/放大了”这样的以多姿斑斓的意象来映现其时的游月与浮云、海浪飞溅如芙蓉的诗句,一定会让人想起冯晏在几年前写的那首《词语》,“多年储存的汉字,完全可以比作我/每年存下的面中麦子和米中的灵性/为自己的疼痛或快感,为喜欢的植被/生物或者爱,我算不清共采摘过/多少词语编成花束献出来。可闷在深处/挑选不出一个词相送的人,始终在/别处的风车上令我的词语眺望不停/他几乎废掉了我所有洪亮的声音”。那时的诗人以诗的方式抚摸恰切的词语赋予的诉说之美,如花似梦,体味诗思与词语相遇的刹那间的豁然与惊奇,但那份样对诗意“客观对应物”的痛苦追寻已经被《航行百慕大》的喷薄而出而得以缓解。
曾有诗人将诗歌与哲学的关系比喻为“近邻”,但将哲学入诗,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风险,哲学是要说的,以逻辑推理取胜,诗却是在说与非说之间徘徊,以语言的张力充盈诗意的花园,其中的度量着实难以把握。和海德格尔同为德国人的黑格尔就曾“警告”说,“诗尤其要避免可以破坏形象鲜明性的凭知解力的生硬的割裂和联系以及下判断作结论之类哲学形式,因为这类形式会立即把我们从想象的领域里搬到另一个领域里去”(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但在失却掉形式上的音韵铿锵后,智性的僻路和深度写作必然是汉语新诗着力探寻的方向,百年的经验让汉语新诗并没有更好的选择。杨炼、张曙光、王家新、陈东东,等等,都是在这个路途上奋进的躬行者。冯晏是认同于这个方向的,并以此超越了性别的阈限,将写诗升华为人类的共性写作。“一个当代诗人,生命中那些最深刻的价值你是否还没有能力发现,有关潜意识的书籍已经读了几十年,然而,潜意识与宇宙科学和自然科学到底有多大的联系可以被你的写作所接受到呢?”进而思考诗与“先知”、“未知”以及对语言的承诺。近作《诗的格局》中的诗学阐释几乎可以看作其诗歌写作承前启后的宣言。
如此,读冯晏新世纪以来的诗是颇费脑筋的,相对于汉语新诗主流的日常叙述,她的深度写作和智性表达是显在的,也是独具风韵的。这或许是和她喜欢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这两位哲学家有关,前者的存在论和心理哲学,后者的数理逻辑和语言哲学,都为她的思想性写作铺垫出了漫长的诗歌红毯,在思想推理的森林里探幽寻踪。在“像一把消沉的锁,锈在/荒漠的古道上,不说话、不熟悉/把沉默养在笼子里”的“过去”花园中体味缄默的优雅(《过去》);在阿赫玛托娃的厨房里思索死亡与等候的意义, “曾经排队300小时探望的人/已被处决。你继续着排队/风霜雪雨中,你还想探望谁?”(《阿赫玛托娃的厨房》);在历史和现实的光影交互中,赋予新圣女公墓以超越性的存在征象,“逝者如石林,在空间站立,低语/无形无声,犹如宇宙一一守护一种踪影”,时光易逝,纵使曾经繁华喧嚣、叱咤风云,但在浩瀚的宇宙中,在死亡的恒久中,终究是转瞬的“踪影”(《新圣女公墓》),恍若云乌,飞而无痕;在思辨和推理中演绎“虚无”的跃动,“你迎向百合、咖啡,当你觉得沉重/虚无折断了你钢丝的外表”,欢喜如百合,大苦若咖啡,也无法荡漾起虚无的底色,“无意义,比事物本身更加虚无”,由之,现实世界的陌生人也无法因为陌生而新鲜,而一旦进入语言的“荒原”,则在荡涤掉现世的虚像后,“面对沧海倾诉真心,并开放着”(《感受虚无》),有了一切;即便是长时期以来被女诗人青睐有加的“私人空间”,也不复有压抑的痛苦和宣泄的快感,所浸染的也是“文明的呐喊”与“人类的忧伤”的悖论,电话、衣柜、窗帘等众多室内意象在时钟、秒针等时间意象的催逼下,不再有隐私的意义,“是的,热闹和寂静你都厌倦了”,也只有流连于“堆积的焦虑”,“听时钟在房间里发出巨响”(《私人空间》),恍惚之间,穆旦、卞之琳苦心孤诣勾勒的孤独影子渐渐浮现出来。将诗歌的翅膀飞翔在人类的死亡、时空、存在等终极哲学命题,并能够用具象而可触的意象表征之的,冯晏的诗是让人惊讶并饱含期待的。至此,黑格尔的警告也逐渐有了历史的意味。
进而,我愿意将这种期待的结果赋予《航行百慕大》,这里的感觉是锐敏而多姿的,“深夜,我听见泡沫熄灭,啤酒在嘴唇沿岸流淌”,思想的光影凝聚在繁星的伞下,意念之蛇逶迤着将消失的惊恐点映到轻握的“一只狼毫毛笔”、即将坠落的“一枚胸前的扣子”。这里的思考是远方的,落光叶子的老树下,参悟通透的梦境和孤独的光芒。这里的关怀是深刻的,在死亡的尽头矗立着永生的灯塔,在被关掉的城市颜色里、海的蓝色里、语言之光里,诗人似乎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悖论融汇到一片静物的平静中,水深处的章鱼、伸向地球之外的虚线,都在诠释着生命潜在的价值。同样的,这里的拷问亦是无尽的,摆脱了世俗羁绊之后的世界如此的徜徉,可以追问“在空寂中/冷风停在第几感?”亦可以思索“对于无人,偶然在哪里?”并不顾及到是否有答案的可能。在略带神秘色彩的笔触中,投射出难以穷尽的生命观念,由即将消失带来的恐惧归结到消解生死之界的空灵与超脱。
去年的五月,冯晏曾写有名为《在海上》的诗篇,书写着和《航行百慕大》相类似的命题,那里的恐惧“让黑暗遮蔽迷雾”,而“我要在雄性升起的空地/等天堂被云打开,听灵魂之歌轻轻传来”,那时的诗人还向往着“做一枚笔画,去一首诗歌中等待”词与世界的通灵,期待着“让风暴袭来几个彻底的句子”,明了而单纯,显在而容易把握。但一年后的《航行百慕大》已是以越轨的笔致,进入到语词背后浩瀚的精神星空了。这里一定有猜不透的只有诗人才知的机缘,也许是百慕大的海启发了诗人的灵智,也许是与日俱增的阅读积淀为诗人的感悟洞开了一扇窗,在不长的时间里,两首诗氤氢出的质的变迁着实让读者惊讶。这应该是一个启示,一个新的诗歌和诗人的启示,用超验的个性视角推动新的诗学世界,诞生出更为优卓的诗歌文本。
但如此走下去,冯晏的诗也许注定如见到风车的堂吉诃德,看似荒诞,但却以非一般的勇敢丰富着前行的意义,“是否诗人只有甘于精英读者群;甘于接近更大的孤独,才可以在探索中静默地伸向精神上最能带来激情的现象体验,甚至永不期待交流呢?”(《诗的格局》)是的,只能是这样!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优秀的诗篇都是贵族而小众的,虽然早已是共识,但总为诗歌所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