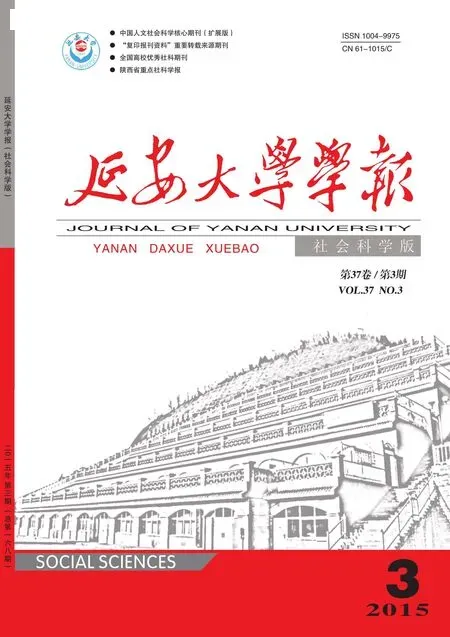试论白马藏族民间故事中的“殉情母题”——以《新娘鸟》和《阿拜波与娥曼妹》为例
杨 军,蒲向明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史学院,甘肃成县742500)
试论白马藏族民间故事中的“殉情母题”
——以《新娘鸟》和《阿拜波与娥曼妹》为例
杨 军,蒲向明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史学院,甘肃成县742500)
关于中国民间文学“殉情母题”的研究,目前所见成果较为有限。新疆、甘陕川一线的结合区域,是民间文学殉情母题多发的地区,白马藏族民间文学就存在这个特定区域内。通过对目前公开出版的白马藏族民间故事集的题材研究,可发现其中存在着特征显著的殉情母题。以《新娘鸟》和《阿拜波与娥曼妹》为例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白马藏族民间故事不仅具备“相爱——干涉——殉情”的母题叙事模式,而且还存在着“传情——殉情——团圆”的母题情节模式。在艺术审美方面,这种“美的毁灭”殉情母题具有悲剧美和崇高美,对唤醒白马藏族的激情正义,激发他们追求真理和信念、延续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
白马藏族;殉情;母题;《新娘鸟》;《阿拜波与娥曼妹》
爱情婚姻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文学中的婚恋题材因此而显得数不胜数,对于中国文学当然概莫能外。著名的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因其文化意义厚重,历史影响深远,堪称婚恋题材的民间文学之典型。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民间爱情故事都无一例外地显示出了难以调和的悲情主题:源于西周的牛女故事中,痴情男女相隔天汉而“泣涕零如雨”;传出秦代的孟姜女为夫哭长城,负遗骨而亡于潼关道;出自两晋的梁祝故事,二人殉情而亡、化蝶双飞;成于宋或更早的白蛇传,白娘子为情所困,竟被镇于雷峰塔之下。如再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这四大民间爱情故事均包含“殉情”因素,除梁祝故事外,孟姜女为夫殉情,牛女为河汉所隔“如”殉情,白娘子压在塔下为许仙“活”殉情。因而,有论者称:“殉情”是古今中外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叙事母题,它触及人类共同遭到的悲惨命运与人类的集体心理深层;在世界各民族文学中,无论作家文学还是民间文学,都存在殉情故事。[1]
但是,目前我国学界对这一殉情母题的研究并不丰富。克热木提出的一些论断,也仅限于他对维吾尔族尼扎里爱情叙事诗研究所得的结果,虽然他的研究视野是开阔的,引证涉及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爱情与阴谋》、《梁祝》、《娇红记》、《霍玉传》、《莱丽与麦吉侬》等诸多古今中外殉情母题的杰作,但见著知微的研究并未得到重视。比如说殉情母题的地域特征问题,就值得学界重视,维柯在《新科学》中指出:“一切民族无论是野蛮还是文明的,尽管是各自分别创建起来的,彼此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隔得很远,却都保持住下列三种习俗:1.它们都是有某种宗教;2.都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3.都埋葬死者。”[2]可见,殉情所包含的爱情婚姻和死亡丧葬两大主题,在时空上是存在隔区的。从维吾尔爱情诗到牛女故事、孟姜女故事,再到《牡丹亭》卷首所言题材来源之晋武都郡(治所在今甘肃省成县西)太守李仲文女“还魂故事”(见《搜神后记》卷四)看,新疆、甘陕川一线的结合区域,是一个民间文学殉情母题多发的地区。赵逵夫先生近十年来对牛女传说起源于西汉水流域的研究,以及织女原型为秦人先祖女修的论证、刑天神话和氐族渊源、三目神崇拜和白马藏族文化的探讨*限于篇幅,赵逵夫先生的具体观点在此不一一引述,可参见他自2005年以来发表的30余篇相关论文。,都为我们考察这一殉情母题多发地区的民间故事提供了理论支持。对白马藏族民间故事殉情母题的探索,可以丰富我们对这一地区民族文学的了解,为研究中国文学开拓一个新颖的认知空间。
一、“相爱——干涉——殉情”的母题叙事模式
白马藏族民间故事极其丰富,仅从今所见正式出版的四川平武白马藏族民间故事集《新娘鸟》和《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两个集子*周贤中搜集整理的《新娘鸟》一书由重庆出版社1984年出版,邱雷生、蒲向明主编的《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由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即可知一二。此前,笔者曾探讨过白马藏族难题故事母题的情况,认为该“母题类型故事反映出来的种种思想观念,充满着明显的平民意识和较为深邃的民间智慧”[3]。相应地,对白马藏族民间故事的“殉情母题”加以研究,能使我们在另一层面加深对白马藏族民间文学的深刻了解。
对白马藏族民间故事的分析和研究,渐成热点之势,也不乏取得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但是专家学者涉及白马藏族民间故事母题研究的并不多。笔者试图运用母题叙事的有关理论,以白马藏族民间故事《新娘鸟》和《阿拜波与娥曼妹》*《新娘鸟》见故事集《新娘鸟》第35-48页,《阿拜波与娥曼妹》见《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故事卷》第271-282页。为对比研究对象,探查这两个殉情故事的母题叙事模式及其特征。
《新娘鸟》主要流传于四川平武县托博河流域白马藏族村寨。故事讲述的是:一对相恋的白马藏族青年生前被土司迫害不能成婚,死后变成了一对美丽幸福的鸟儿比翼双飞。女青年鹅满早、男青年姚得波互相仰慕、自由相爱,在媒人的说合下,经其父同意,双方订了婚事。后来,土司的儿子暗珠看上了鹅满早,便委托杀巴带着丰厚的聘礼(钱、铜铃、牛羊)去鹅满早家提亲。鹅满早的父亲不敢违背“山神要暗珠和鹅满早结婚”的旨意,收下了暗珠的聘礼,悔掉了女儿和姚得波的婚事。姚得波和鹅满早伤心欲绝,相约逃跑。暗珠听到姚得波、鹅满早准备逃跑的消息后,设计射死了姚得波。杀巴叫人焚烧姚得波的尸体,尸体经火焚烧,终不得燃。鹅满早走到尸体旁,一边唱歌,一边焚烧平日里给姚得波做的绣花靴子、花腿带、腰带和狐皮帽子,尸体终于化为灰烬。随后,鹅满早纵身跃进了火堆,自焚而亡。两人死后,变成了一对小雀子,这就是“新娘鸟”。
《阿拜波与娥曼妹》主要流传于甘肃省文县白马河流域白马藏族聚居区。故事同样描述了一对男女青年“生死相许”的爱情悲剧:娥曼妹的父母把女儿许配给了有钱人的儿子阿古来,但娥曼妹对这桩包办婚姻誓死不从,约定和阿拜波私奔。阿古来在阿拜波、娥曼妹私奔的必经之路上放置了毒箭,毒死了阿拜波。阿拜波死后,依当地风俗举行火葬,其尸体却无法点燃。娥曼妹来到火堆旁,一边哭着唱着,一边往火堆里扔衣物,阿拜波的尸身终于被烧完了。娥曼妹唱罢后,跳进了熊熊大火之中,实现了和阿拜波生死不分离的诺言。后来,在埋两人骨灰的白马河的两岸(南岸、北岸),各长出了一棵灯笼木树。两棵灯笼木树枝叶相连,成了鸟儿的家。一对美丽的鸟儿在树上唱着欢快的歌儿跳来跳去,一刻都不分离。据说,那对鸟儿就是阿拜波与娥曼妹的化身。
比较而言,《新娘鸟》和《阿拜波与娥曼妹》的故事情节大抵相似,从故事的叙述格局来看,文本都是由四个情节单元构成的,即:(1)男女青年相爱;(2)爱情遭到家长干涉反对;(3)一方被害身亡;(4)另一方殉情自杀。汤普森曾指出:“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4]这两个故事的不同寻常和动人之处在于男女主人公不仅具有敢于大胆追求自由爱情的奋斗精神,而且还有着封建社会妇女对美满婚姻的渴求,故事主题表现了对理想的幸福家庭给予肯定并尽情赞颂。换言之,故事令人震撼之处就在于:有了这样的爱情至上者,为了真爱什么都可以放弃,甚至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其爱情故事“相爱——干涉——殉情”的情节结构在文本中反复出现,进而固化为一种叙事模式,并在不断的描述和反映中凸显了相恋的青年男女“不能爱,毋宁死”的悲壮和崇高,使得作品获得了“死亡即永恒”的艺术生命力。由此,故事的情节单元已形成“相爱——干涉——殉情”的母题叙事模式,呈现出其作品叙事方式高度的类型化特征。
这两篇故事,客观上也存在着互为“异文”的可能。陈建宪指出:“母题既可以是一个物体,也可以是一种观念,既可以是一种行为,也可以是一个角色,它或是一种奇异的动、植物,或是一种人物类型,或是一种结构特点,或是一个情节单元。这些元素有着某种非同寻常的力量,使它们能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不断地延续。它们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它们通过各种不同的组合,却可以变化出无数的民间文学作品。”[5]不同地域的白马藏族都存在着的“殉情”母题,作为该族民间叙事文学作品内容的最小元素,在一定意义上唤醒了当地青年男女的爱情观念和行为,从而产生一种不同寻常的力量,为不断延续的白马藏族传统文化产生传承推动。
二、“传情——殉情——团圆”的母题情节模式
白马藏族的婚姻奉行一夫一妻制,多主张近亲结婚,推崇“亲上加亲”,婚姻形式上主要是由父母包办。大多数男女青年在婚前有一段交往自由。选择对象不能超越规范。只要经父母、族长同意,婚姻关系就算成立。[6]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些家长在儿女婚姻问题上更多看重男方家庭的经济状况,致使“恋爱自由、婚姻不自由”的现象时有出现,并最终发展为“殉情”。《新娘鸟》、《阿拜波与娥曼妹》等故事就体现出这样的价值判断。
《新娘鸟》中,姚得波和鹅满早俩人的婚事被土司的儿子暗珠所扼杀,其原因就在暗珠丰厚的聘礼(五头犏牛、十只山羊等)以及“山神”的旨意(说媒人杀巴梦见山神扎里瓦为鹅满早和暗珠主持婚礼)。此时,鹅满早被气得死去活来,悲愤地唱道:
成对的金鸡哟,被鹰赶散了/结伴的青鹿哟,被箭打散了/流向大河的山泉水哟,被石头塞断了/姚得波阿哥哟,你的阿妹给卖掉了。
姚得波气得咬碎了牙,他拿出弓箭,马上就要去找暗珠算账。
《阿拜波与娥曼妹》中,阿拜波和娥曼妹的相恋因为阿拜波家境贫寒遭到了娥曼妹父母的反对,他们硬是把女儿许给了模样丑陋好吃懒做、有钱人的儿子阿古来。娥曼妹誓死不从,阿古来仗着有钱有势,欲强娶娥曼妹为妻,设计毒死了阿拜波。
经济条件的富裕程度是传统婚姻考量的重要指标,是决定相爱的双方能否实现婚姻理想的现实基础。鹅满早、娥曼妹的家长从经济条件、家庭背景的角度出发衡量婚姻本身是否幸福,也许有一定的现实合理因素,但这毕竟不是当事双方真实的情感感受。家长的极力反对,导致相恋的男女青年双双殉情,将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和结合的相爱,演变为死亡之后的精神之爱和灵魂之爱,从而形成了一种极具心理震撼力的的悲剧情感。黑格尔曾经说过,“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引起同情,他就必须本身具有丰富内容意蕴和美好品质,正如他的遭遇的伦理理想的力量使我们感到恐惧一样,只有真实的内容意蕴才能打动崇高心灵的深处。”[7]姚得波、鹅满早、阿拜波和娥曼妹等四人勤劳勇敢、忠贞不渝,是白马藏族群众理想人物的化身,他们的殉情死亡是婚姻理想的破灭,他们的悲剧深深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新娘鸟》中的男女主人姚得波、鹅满早相互倾心,以歌传情,表达了他们对自由爱情的渴求以及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
姚得波鼓起勇气,向木楼唱起一支歌子:
你那明亮的眼睛/如海子水的清澄/我的心在海子里溶化了/姑娘啊,救救淹没的猎人/你绣的靴子是轻盈的小船/你织的腰带是船上的风帆/送我这些珍贵的赠品吧/姑娘啊,你的剪子别把悬望剪断。
鹅满早听出了姚得波的声音,止不住一阵激烈的心跳,在窗后轻轻地唱起来:
绣花鞋是给爱人穿的/爱人才能用姑娘的腰带/阿哥啊,你若真心来相爱/快把咂酒*咂酒,系“咂杆酒”或“咂杆子酒”的简称,因喝酒时要使用芦苇或竹子做的长咂干(类似吸管),故名。该酒又称五色粮食酒,是白马藏族人用青稞、高粱、玉米、小麦、豌豆等五种粮食,经过蒸煮晾干后装缸,放酒曲发酵而成的纯粮酒,为其标志性特产之一。送过来。
《阿拜波与娥曼妹》中,阿拜波和娥曼妹借助多首情歌来抒发彼此的爱慕思念之情,表现了爱情的坚贞以及对包办婚姻的抗争:
阿拜波唱道:美丽漂亮的姑娘啊娥曼妹/你的脸庞像金贡山里的花儿一样/你的身材像白马河畔的杨柳一样/你的歌声像美妙动听的银铃一样/你那动听的歌声驾着彩云飞翔/飘呀飘,飘进了阿拜波的心房。
娥曼妹隔山唱道:
世上的男子有千千万万/只有你才是我唯一的爱恋/你头上的白毡帽插着白羽毛/像一朵白云飘进了我的心田/羊群是我白日里的伙伴/你是我枕头上梦乡的田园。
在爱情遭到破坏之际,阿拜波和娥曼妹相互鼓励,依然用对歌的方式来表达爱情的忠贞不渝,并以此和恶势力(阿古来)做着坚决的斗争。
娥曼妹唱道:
只要和哥哥天天来相逢/青石板做床也安稳/泉里冷水洗脸也温暖/顿顿粗茶淡饭也心甜。
阿拜波唱道:
世上的姑娘数不清/只有娥曼妹最称我的心/拦路的荆棘要除尽/一定要把阿妹迎进门。
男女主人公用民族地域特色极浓的语言(情歌)将所渴慕的情人的容貌(眼睛、脸庞、身材等)和女工(织的靴子、腰带)加以赞颂和描绘,充分反映出在炽热爱情支配下的青年将自己心上人高度美化的心理状态以及独特的民族审美方式。
忠厚老实的男青年姚得波、阿拜波分别和漂亮聪明的女青年鹅满早、娥曼妹相互爱慕,自由恋爱,但美好的爱情婚姻理想却被传统的包办婚姻无情扼杀,并最终导致相爱的男女双双殉情。
这种“传情——殉情——团圆”的母题情节模式,表明两个故事中男女主人公虽然没有实现肉体的结合,但它们死后化而为鸟,用另一种形式得到了“团圆”。也就是,如果这些情侣们生时没有走到一起,那死后也会如愿以偿。[8]
三、“美的毁灭”:殉情母题的悲剧艺术魅力
《新娘鸟》、《阿拜波与娥曼妹》作为白马藏族殉情母题的代表性作品,集中反映了存在于白马藏族社会的爱情悲剧。悲剧常常表现生活中最富有激情、最庄严壮丽的事情,常常以死来加强它的庄严和壮丽。白马藏族这种殉情母题的悲剧魅力,实际类似于纳西族民间文学的悲剧因素*纳西族故事的男女之爱是生活中富于激情和幻想的部分,这一富有诗情的生活内容遭到不幸或者毁灭时,必然会在人们的心灵引起震动。参见杨福泉《东巴经叙事长诗〈鲁般鲁饶〉刍议》一文,载《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2期,第14页。,作品以男女主人公毁灭生命来实现理想婚姻的悲剧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同时又增加了故事本身的悲剧艺术魅力。
作品通过悲剧人物(男女主人公)的成功塑造将白马藏族青年“恋爱自由、婚姻不自由”的痛苦进行了高度的艺术凝练,并借助作品结尾的殉情幻化(新娘鸟、灯笼木树),深刻反映了白马藏族男女青年执着于爱情理想的从容和坚毅,以及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决心和勇气。鹅满早聪明美丽,“她的嗓子像深山里的福马鸡一样动听,她会唱的歌子像达布河里的白石头一样多,她织的花带像五月的杜鹃花一样美”,她勤劳、痴情、纯真,给人一种怜爱之美;娥曼妹不仅模样俊俏,而且还有一双巧手,“织出的彩带比天上的五彩云霞还美丽,缝制的五彩花衣就像山花一样漂亮”,她善良、果敢、执着,不畏阿古来等人的迫害,纵身跳进火海,以求和她心爱的人同死;姚得波、阿拜波忠厚老实、勤劳勇敢、诚实善良,都是白马山寨里的好青年,但是却最终被恶势力(暗珠、阿古来)残忍毒杀。男女主人公可以说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们真挚而自由,向往一切美好的东西。彼此深沉地爱恋着对方,却又遭受着以一己之力无法抗拒的外力干涉,强弱明显的对比下,也特别类似与哈萨克族青年男女无所畏惧地进行抗争,甚至甘愿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哈萨克族民间殉情故事体现了一种豪放而悲壮的叙事模式,无畏抗争直至献出生命。见潘帅、范学新、努力哈丽帕《论哈萨克族民间爱情叙事诗中的殉情母题及其文化内涵》一文,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57页。他们的殉情,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美的毁灭”,是对人的生命力之美、抗争精神的肯定和赞美。“只有经历了死亡的冰原般的考验,人类的爱才得到理想光辉的沐浴,才走向神话般的浪漫和永生”。[9]
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又大量运用了对歌、烘托和渲染等多种表现形式,提升了作品的悲剧艺术张力,并由此产生了“生之毁灭”的悲壮美和崇高美。娥曼妹得知阿古来欲毒死阿拜波的消息后,就用唱歌的方式为阿拜波通风报信;“树上臭不过屁巴虫,世上狠毒不过虎狼心,阿拜波呀阿拜波啊,请你一定要当心。上面的路上安有毒箭,下面的路上挖有深坑。上面的路上你走不得啊,下面的路要你绕着行”(《阿拜波与娥曼妹》)。阿拜波被毒伤以后,两人对歌互致问候、互相安慰。娥曼妹惦念着阿拜波的病情,用歌声安慰阿拜波:“我的心上人啊,我的可怜的人,毒箭伤在你的身,好似万箭穿我心。天大的悲痛要忍住,你要安心养伤病”。阿拜波听到歌声后,感到莫大的安慰,轻声唱道:“你的问候好亲切,字字句句暖我心。只要你心中还有我,天大的伤痛我能忍”(《阿拜波与娥曼妹》)。起伏跌宕的描写,烘托出女主人公殉情前浓郁的悲剧氛围。阿拜波死后,娥曼妹哭声感天动地,高声唱道:“雷公啊,你快快地扯起火闪(闪电),风神啊,你快快地刮起狂风。我的心上人啊,你不要把我牵挂。”“随着娥曼妹的歌声,狂风大作,雷鸣电闪,风助火势,柴火烧得更旺了。”娥曼妹唱完后,跳进了火海,实现了和阿拜波“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爱情诺言。顿时,“风停了,雨住了,天边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阿拜波与娥曼妹》)。
中国的民间爱情故事有着二元对立的“结构语法”,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美学特征。作为一种二元对立的故事结构,对立性对故事的矛盾激化和戏剧冲突有着重要意义,从而形成讲述故事时的一种对立性的悲剧美学。在《新娘鸟》、《阿拜波与娥曼妹》中,男女青年坚如磐石的自由爱情和封建家长包办婚姻以及暗珠、阿古来等恶势力的对立激化了故事矛盾。在矛盾的进一步扩大中,对立性一直是故事冲突的推动者,最终以双方殉情结尾,并以化身新娘鸟、灯笼木树实现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爱情追求,从而形成一种悲剧美。从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人应该具有的“为理想而不惜付出生命”的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抗争精神。作品的悲剧美和崇高美具体体现在能够唤醒人们的激情正义、激发人们追求真理、追求理想信念的真性情中,正如郎加纳斯所言:“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那样能够导致崇高”。[10]
四、结语
白马藏族故事希冀的理想爱情是以超越金钱、门第的认同感为基础的。这种爱情、婚姻的认同感和现实世界里的道德、伦理、情感以及价值追求相悖时,相恋的男女双方必然会为自由婚恋而奋起抗争,甚至选择死亡殉情,并最终实现殉情母题的“大团圆”结局。在传统的婚姻观念以及强大的恶势力(暗珠、阿古来)面前,姚得波、鹅满早、阿拜波、娥曼妹等普通民众的反抗,其力量终究是薄弱和有限的,他们唯有以殉情来做最后的抗争,以生命的最后呐喊来控诉这种制度、价值观念的不合理。我们觉得,恰恰是殉情母题所做酝酿的这最后抉择,才最终升华到信仰的高度,情感精灵们的生命本身才获得了存在的价值。[11]
白马藏族故事中的男女青年视自由婚恋为生命意义的全部,他们甘愿为情而生、为情而死。事实上,极度的爱的本身,就意味着死的冲动。[12]“爱和死:永恒一致。求爱的意志,这也就是甘愿赴死。”[13]他们认为,不能如愿以偿的婚恋,其生活注定是不幸福的,与其在痛苦的深渊中沉沦,还不如以毁灭生命来逃避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讲,殉情母题故事对死亡的追求,亦即对幸福的追求。较之纳西族,白马藏族的殉情母题故事只是个别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意义。随着白马藏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进一步密切以及婚恋观念的不断解放,白马藏族故事殉情母题的“土壤”已不复存在,殉情母题已经成为民族故事残存的文化记忆。但是,研究曾经出现过的殉情母题叙事,对于深入了解白马藏族的民族性格、民俗文化心理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阿布都外力·克热木.浅谈维吾尔爱情叙事诗中“殉情母题”及其文化内涵——以尼扎里爱情叙事诗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05(4):189.
[2][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35.
[3]杨军,蒲向明.母题类型视野下的白马藏族民间难题故事——以陇南白马藏族故事为例[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04-109.
[4][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M].郑海,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499.
[5]陈建宪.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探索[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22.
[6]邱正保,张金生,毛树林.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调查资料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150.
[7][德]恩格斯.美学:第3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88.
[8]阿布都外力·克热木.尼扎里的“达斯坦”创作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34.
[9]颜翔林.死亡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41.
[10]郎加纳斯.论崇高[M]//西方文论选(上).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5.
[11]吴春兰.“生生死死的恋爱”——从中外文学看殉情主题作品[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专刊:124.
[12]陈艳萍.纳西族殉情作品及殉情风尚生死观探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60.
[13][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尹溟,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134.
[责任编辑 王俊虎]
2015-03-1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白马藏族文学的整理与研究”(11XZW023);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陇南白马藏族民间文学整理和研究”(1128A-01);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科研项目“母题类型视野下的陇南白马藏族民间故事研究”(2014LSSK02008)
杨 军(1978—),男,甘肃徽县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史学院副教授;蒲向明(1963—),男,甘肃天水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史学院教授。
I206
A
1004-9975(2015)03-00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