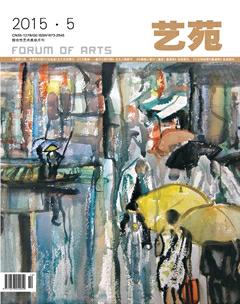从现实抽空到虚无——贾樟柯电影符号的嬗变
文‖徐 桃 李丽娟
从现实抽空到虚无——贾樟柯电影符号的嬗变
文‖徐 桃 李丽娟
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的贾樟柯,在现实与虚幻中,力图真实地展现中国底层人物在社会变迁中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他在电影叙述形式上,从开始的人景交融呈现日渐沉入到对对象人物的本体刻画中,在追求人性探究的过程中,却表现出符号化倾向,对电影真实的展示反而有无力之感。
贾樟柯;电影;真实;无力

电影《世界》 海报
从《小武》、《任逍遥》到《世界》的故乡三部曲再到《三峡好人》、《二十四城》、《天注定》,贾樟柯的电影一直以“伪纪录”的方式用摄影机展现变化中的中国。在贾氏电影语言的叙事中,从早期展示真实的似乎就在身边的人物、场景、画面,到日渐沉入到对对象本体的叙述中。虽然表现形式和结构在变化,但递进呈现出来的却是现实感不断被抽空、人物被抽离的虚无感,即使发展到《天注定》中红色暴力向生存的宣泄也显得空白无力。
一、“旧的是拆了,新的在哪呢?”
贾樟柯的电影一直展现现代性发展对中国的冲击,他电影表现的方式就像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把摄像机扛到大街上去”的追求一样,都在强调电影用于记录生活的真实感受与变迁。在他的电影作品里,“当下”的人物和“当下”的生活境遇,是一脉相承的,投射进入的视角虽然显得冷静却关切。如贾樟柯所言:“在传统的影像里面,看不到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也看不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状态,几乎所有的人都回避这个问题,对当下社会的状况、人的处境视而不见。影像在20世纪90年代的缺失令人焦灼。90年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都处于一个强烈的转型期,时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混乱、焦灼、浮躁的氛围里,每个人都在这个氛围里承受了很多东西,就像你看到的,每个人都要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一切都在重构之中,再解构再重构,有的在坚持,有的在突变。这个时代的变数,是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1]77
在这种巨大的时代激变中,对国家的主导者和社会精英分子而言,把握其运动的动脉并适应其变化,是件相对容易的事情。而对于生存在社会底层甚至边缘的普通人而言,面对这些变化,所能做的多是默默承受,传统观念的扭曲、物质生活的分层,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并由此产生生存的动荡感,贾樟柯的电影主人公都是此类人物。在《小武》中,通过一个小偷的生存空间,展示出一个中国基层的社会结构管理层面——小镇,它所遭受到的时代冲击,及引发的小镇居民人际关系的社会重组。小武生于农村,在这农村城市化进程初级阶段的小镇里谋生,虽谋生手段不合法,但奇特的是在变化中作为不见融于正常道德体系中的他,却是最固守原有伦理思维的人。影片中,小武与小勇是两个从小长大的好友,一起做过小偷。小勇理解并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成为企业家,他的婚姻成为小镇的大事。成功后的他急于摆脱过去被主流社会所不容的经历,急于与小武摆脱关系,将小武送的礼金退还,恼怒的小武谴责他的钱来的也不干净。小勇让手下托人给小武的话很是识时务“走私香烟不叫走私,那叫贸易;开歌厅不叫挣歌女的钱,那叫娱乐业”。谁占据了社会资源,也就有了合法性命名的权力。
这部电影原有一个很长的名字,《靳小勇的哥们,胡梅梅的靠山,梁长有的儿子:小武》,这原本是小武之所以为小武的身份认证,代表着他生活中固守的爱情、友情、亲情。在影片中,这种关系却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展示的:小武执意要给小勇结婚送两斤钱的红包,他把偷来的钱放在秤看是否足秤斤两,这个细节似乎也暗示了钱也成了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尺码。他喜欢的小梅跟有钱老板走了,从小的玩伴发财挤入主流阶层急于与其断绝关系,母亲将小武准备送给梅梅的戒指给了城里人二嫂,小武在表示不满的情况下被父亲赶出家门。影片中小武视为生存基础的情感不断被金钱抽空,而耐人寻味的是,小武的职业是小偷,钱是他偷来的。他在偷取别人财物的同时,自己的依托也被不知哪里的力量给偷去了。小武的身份被剥夺了,没有了情感的链接,也没有未来生活的希望。小武戴着大黑边眼镜,穿着不合身的西服,在路上晃荡,本身就与这个小镇的背景格格不入,不停叫嚣“严打”的大喇叭也正在把他排斥其外。在经历过这一痛苦经历后,他被软弱地暴露在闹市街头,承受边缘人被唾弃的打击。
贾樟柯电影的主人公主要是年轻人,处于改革初期时期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传统国家意识教育体制下成长,出生在农村或小城镇,又在传统道德标准和伦理体系中浸染。他的另一部作品《站台》,讲述一群汾阳县文工团里的两对男女青年之间发生的事情。贾樟柯利用大标语、歌曲、电影等时代文化符号,把他们包裹在一个旧的国家意识营造的文化中,又极力表达这些文艺青年挣扎着要摆脱旧的思想,穿喇叭裤、听广播播放的邓丽君歌曲、向往改革前沿广州的时尚…… 这是个破旧迎新的时期。《小武》中有句台词是: “旧的拆了,新的在哪?”电影中的小武就像个观望者一样游离在背景之上,他似乎不是生存其间的一份子,茫然地寻找自己的生存之基。《站台》中的这群青年,在影片中也没有结局,他们只是在努力地适应中却又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鲁迅的伟大是把中国当时的底层人民的各色精神心态剖析得淋漓尽致,从而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广大农民的命运,他们遭受的不仅是物质贫穷和生存危机,还承受着精神的耻辱烙印。贾樟柯之所以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电影的希望,也正是因为他通过他的镜头做了同样一件事情,关注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个古老国度里生存的底层人民所经历的苦楚,并用电影的方式记录这个时代。《小武》中新闻报道香港回归,流行歌曲《九九女儿红》、《真心英雄》……这些影像在电影中的保留,就是贾樟柯尽力保存当下社会状况的努力。
二、虚假的世界与渺小的存在
“我愿意直面现实,尽管真实中包含着外面人性深处的弱点甚至龌龊。我愿意静静的凝视,中断外面的只有下一个镜头的下一次凝视。我们有力量看下去,因为——我不回避。”[2]18到《任逍遥》和《世界》中,贾樟柯已经在凝视中开始思考形而上的“人何处安生”的生存之道。
《任逍遥》讲述了两名失业工人子弟19岁的少年斌斌和小济抢劫银行未遂的故事,故事很简单,风格已经不再像前两部影片那样忠实纪实,已有些迷离。贾樟柯自己在其中扮演一个穿着背心不停唱歌剧的疯子,疯子代表着脱离社会正常秩序的存在,反喻的是影片中看似真实社会的不正常。小济追求比自己年长的矿区野模特巧巧,巧巧问,为什么要泡她,小济说不出理由,就一个劲地说泡。就像他自己的生活一样,只有刺激没有内容。影片中,不断出现电视画面,讲的都是21世纪初中国国家大事,镇压法轮功、中美撞击事件、申奥……斌斌和小济这群人的生活,虽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中,但媒体所报道的事件似乎跟构成这个国家基础的老百姓生活没有任何联系,一种空间交错感营造出来的影像中的虚幻世界。当厂区传来爆炸声时,斌斌戏言“美国打来了”,这是老百姓的调侃,也是对电视营造的遥远世界的嘲弄。斌斌的女朋友考上北京的大学,而自己却因为肺炎而无缘参军。冲破现状的努力破灭了,“哪他妈有以后啊”,自知爱情将远离的斌斌喊出的是对真实世界的绝望。
到电影《世界》中,贾樟柯开始在几层世界中游移来表现人在现实中的错位,更进一步打破了以往的纪实风格,采用近乎实验性的叙事手法。在《世界》的开头,赵小桃长达六分钟的镜头不停叫唤“谁有创口贴”,这样的开篇,就像新写实小说家刘震云《一地鸡毛》的开篇一样“小林家的豆腐馊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极小行为,引入的场景是进城打工者的一个需要愈合创伤的心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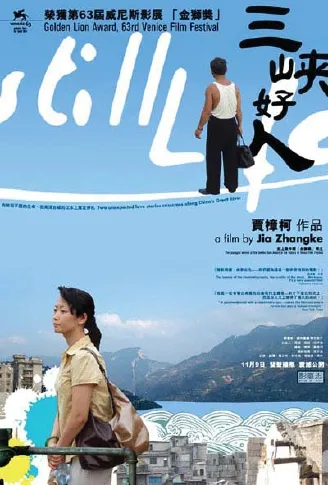
电影《三峡好人》 海报
世界公园,这里有世界最著名的景点,最能代表一个国家典型自然和历史的象征物。熙熙攘攘的游客,花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能“不出北京,走遍世界”,从艾菲尔铁塔到金字塔只需几分钟的时间。压缩的历史,变成了图景世界,各个经典景点的表象化、缩小化压缩,没有了历史、没有了文化、更没有了情感,有的只是个内容干瘪的、没有色彩的图像。表面看来什么都有,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这个世界,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世界,荒谬而无奈,似乎已经没有时间和过多的精力去体味表象下那厚重和深沉的东西。在这片图景的映衬下,有的只是平凡生活的烦琐,日复一日地缠绕着人的生活,并构成了每个人具体的世界,没法摆脱,也无从逃避。为何还有那么多中国人来此欣赏这样的世界?这被抽空了时间、空间和历史的世界?它的成功正是与极速发展下的中国人普遍的躁动感不谋而合,急于进入发展,急于进入所谓全球化的发展轨道,急于摆脱自己对外在世界的无知。《世界》用这个故事背景充分展示一个处于高速运动中却不知去向的社会所产生的焦躁情绪,从山西农村来的外来打工者,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感受着伤心、乡愁、失败、爱情和渴望。影片中还有关于短信交流方式的flash,营造出虚拟空间。似乎中国人就在这象征机械复制时代的世界公园中,和现代科技创造的虚拟空间中无谓地生活着。贾樟柯大量地应用隐喻、象征、荒诞、非理性的手法强化表现效果,进而达到对这个时代内在价值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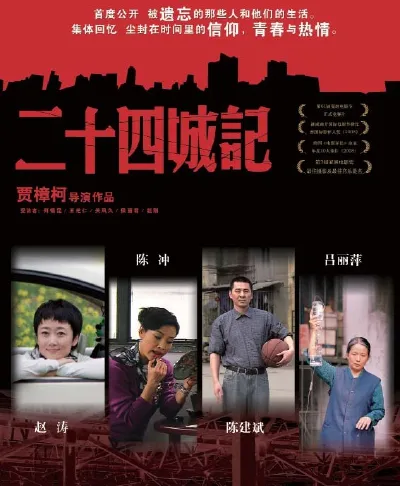
电影《二十四城记》 海报
《世界》让贾樟柯在法国、西班牙等地获奖,在国外扬名。但他意图忠实记录这个时代的想法,忠实地讲叙一个故事来展现中国转变时期一面的做法,已让他略觉不够。其自《小武》以后的作品,画面构造越来越雕琢,塞得东西也越来越多,就如候孝贤与贾樟柯的一次对话中所言:“《小武》受到重视后,你想一股脑把想过的东西全呈现出来,就把人放到一边,专注到空间、形式上去,反而太用力、太着急了。”[3]贾樟柯的影片从《小武》到《世界》是个终结,到《三峡好人》的出现又是个跳跃。贾樟柯这样评价自己的转变:“《小武》到《三峡好人》之间拍了三部片,我是有种负担感。《小武》里面,我特别关心人的生理性带来的感动,之后,基本上考虑人在历史、在人际关系里的位置,人的魅力少了一些。到三峡之后,阳光暴晒着我们,这对天气的直接反应都能帮我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特别是去了折迁的废墟,看到那里的人用手一块砖、一块砖拆,把那城市给拆得消失掉。镜头里的人感染了我,我在大都市里耗掉的野性、血性,回去一碰,又点着了。好像在创作上点了一个穴,原来死的穴道又奔腾起来。”[3]
《三峡好人》点中的穴道,与其说是贾樟柯又找回到原来创造的灵感和动力,不如说是他又发现一个更好地讲叙自己思想的电影语言。在《世界》中,这种方法已经初见成效,让他名扬海外,就是在背景意味极其丰富的画面里,让人物进行穿插、进入、出来,就像是萨特的情景剧。
三峡工程,作为国家工程,让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小城镇,两年间就被人一点点地拆毁,并沉入水底不见天日。人在这要被遗弃的城市里,忙忙碌碌,各有各的心思。骑摩托车带客的年轻人指着江面说自己的家就淹没在水底;年迈旅店老板被迫住进了桥洞;年老色衰的妓女为了生存只能离家去广州;因工伤断了手臂的工人被弃之不理迁往广东寻找活路;神气的小马哥转眼被埋在拆迁废墟中……这些虽是简单的扫描,而这些人生存在这块土地,有更复杂的情感面对这样的局面。贾樟柯选择的却是两个过客,主人公的身份就注定了,他们的眼光只是漠然地观望这个地方的变化。

电影《天注定》 海报
在影片中,有不少拉长镜头,一个用山、云、雨和人联系着古代与现代的巴蜀之地。在这里,宏伟的山峡间、残破的旧城废墟上到处是光着膀子、抡着大锤、挥汗如雨劳作的民工。自然、小镇废墟、人三者间隔不相融,忙碌的人们在废墟上就像蚂蚁一样,让人不明白为什么拆了又建,就像在玩一个无谓的游戏。长江峡谷用万年来计算,小镇则是千年,人的生命不过百年。沈红到兵兵的宿舍时,墙边就挂了一串时间停止的钟表,有各色不同的手表、闹钟、怀表,在时间面前人尤其显得渺小,就是这悬殊的时间对比下,人如蝼蚁般地不停地忙碌着。谈起对三峡的直观感受,贾樟柯说:“看那个地方的变化我觉得很残忍。”也许这些蝼蚁一样生存的卑微生命,让观众感受到的只是灰暗的生命色彩。韦伯言:“官僚体制使社会成为一架大机器,个体则成了这个系统中的一个元素。为了服从体制或系统的功能,个人必定要压抑自己的个性与自由。”而在这种大型的集权政治的展示外,电影似乎更想表达的是,巫山云雨映衬下,人行为的荒谬和无助。
韩三明最后望着走钢丝的人,就像看到自己的命运,更像是看到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命运。看似到对面有很多条路可供选择,实质能到的只有一条路,还是险路,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人生抉择的无奈和悲凉。类似鲁迅在《药》的坟顶围上一圈象征希望的小白花,在营造出这样绝望气氛下,贾樟柯用荒诞的飞碟和三峡纪念碑的腾飞这样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意图打破这现实,表达了作者想表达的一点希望。但这些希望建立在荒诞的外星人神迹上,这多少更显绝望了。
三、重建遗弃下的血色幻景
在这种历史时期的大拆建中,每个人的生活都在与此深刻地交接在一起。到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中,一个大型工厂被改建成商业楼盘,曾生活其中的多位亲历者以被访谈的方式讲述整整涵盖五十年的内容:大丽丢失了孩子、小花讲述上海女人、宋卫东讲述“文革”时期的童年、苏娜讲述新新人类。在这种类似真实的访谈方式中,贾樟柯却又邀请了中国观众熟悉的吕丽萍、陈冲、陈建斌、赵涛夹杂其中,导演自己作为采访者,声音时而在影片中响起,又将观众拉回了现实中。这种亦幻亦真的叙述过程,造成了空间固定下的时间交叉、错乱。这个工厂已经不属于这群人,重建的二十四城更与他们无关,他们只是在这个土地上生存过,而在这块土地上的建筑消长,是被远离这块土地上的人所决定。每个被采访人之后的生活没有说明,“二十四城”楼盘建设或以后的事情也无结局。电影中不时地展示着一首诗歌,这句诗“整个玻璃工厂是一颗巨大的眼珠,劳动是最黑暗的部分”,像是一个诗眼。
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曾说:“一个导演最大的危机在于电影有非比寻常的说谎的能耐。它组合的力量大得无以复加,因此伪造世界的能力几乎是不受限制的。”[5]15贾樟柯在电影中,所展示的“真实”社会,真实的让人产生不真实感。近期的《天注定》,贾樟柯在电影里讲了几个普通人在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走向犯罪或自杀的故事。剧本以真实发生的故事为原型:周克华案、邓玉娇案,还有富士康工人跳楼。从里面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里的各种光怪陆离的现实,周克华的反社会犯罪、村官的贪腐而逼民反、东莞色情服务下的婚配情感制度的危机、流水线工厂员工生存无望的自杀、逼良为娼的绝地反击。
《天注定》里充斥各种意象——途经主席打车像时,三轮车上的圣母玛利亚、两岸繁华与破败的划江而治、漫天焰火下的一声枪响、一厚摞人民币刷在脸上的耳光、会所里制服包裹着的肉欲横流、响彻军乐伴奏下列队走过……这些隐喻就是构成这四个主人公的生存世界。相较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杨德昌是冷静到近乎沉闷的四个小时,镜头如一把精准的手术刀一般,将日常生活潜流里暗伏的暴力因子一一解剖出来;贾樟柯则是用暴力在电影中残忍而直接地进行展示。
这发生在天南地北的四个故事在电影中的组合,贾樟柯的手法类似电影《巴别塔》:三儿(王宝强)在山西的高速公路上杀了三个地痞后和大海(姜武)擦肩而过,三儿在重庆一家银行门口作案后逃亡和一个广东小老板(张嘉译)一辆车;老板和他的小三小玉(赵涛)不欢而散,小玉做小三不成,在洗浴城做烈妇不成,逼到绝路只能奋力一击杀死侵害自己的地方官员;广东老板工厂里的一个打工仔因为造成工友的工伤,担心扣工钱而跳槽去了东莞一个大酒店,和一个做小姐的老乡产生情愫后又默默离开换到了富士康,最终麻木和无助让他从宿舍毫不犹豫的跳下。这四个普通人,在看似安逸和平的时代,悲剧性地活不下去,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暴力这一最古老的武器去反抗,或杀死了别人,或杀死了自己。
除开社会意象的隐喻外,作为生存动物本身的隐喻也是随处可见:被鞭打的老马、被宰杀的鸭、被玩弄的蛇、被放生的鱼。这四种动物类比的就是电影的四位主人公:大海是不堪欺凌的马、三儿是不想任人宰割的鸭、小玉是孤独冰冷的蛇、小辉是渴望自由的鱼。这些动物的结局是,马累死,鸭果腹,蛇归笼,鱼窒息,无一生还。四种动物都生不由己,逃不过宿命,哪怕曾经挣扎过。在中国的生存法则中,国家暴力以各种形态自然出现,官逼民反自古有之。电影中,一反贾樟柯作品的静态,大量血色的运用,充满了杀戮和血腥,但即便如此剧烈的暴力反叛,在电影中仍是个无结局的虚幻,小玉侠女般的脸庞,也被淹没在木然的人群中消失不见。太多的人死了,更多的人活着。
电影的最后,戏台上演着经久不衰的晋剧《玉堂春》,县官拍下惊堂木,不顾堂下苏三的哀怨,说:“苏三,你可知罪?”
[1]练碧辉.“怨恨”的反叛眼神——电影《小武》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J].温州师范学报(哲社版),2006(6).
[2]贾樟柯.贾想 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姚志峰.电影:生命的印记——贾樟柯对话“偶像”侯孝贤[N].中华新闻报,2007-1-10(02).
[4]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一个导演的故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J90
A
徐桃,海南科技职业学院讲师;李丽娟,海南科技职业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