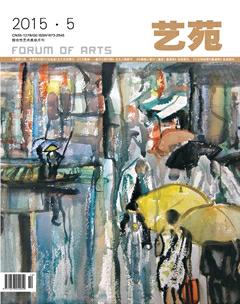朝向中国式“现实”的映射:《十二公民》“性格化”戏剧表演解析
文‖尹 兴
朝向中国式“现实”的映射:《十二公民》“性格化”戏剧表演解析
文‖尹 兴
电影《十二公民》是一部缺少场景转换、情节单一的舞台剧式现实主义电影。影片很好地在将戏剧性与电影性联姻的同时,如万花筒般映射出当下中国转型期现实的横断面,凸显中国现实生活中各种观念的冲突以及沟通的困境。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成功地运用“言语视像”和“舞台语”技巧,而其中“潜台词”的使用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也承担着重要功能。
《 十二公民》;性格化;戏剧表演
可以这么说,所有的电影符号“文本”都是“文本”自身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结合使电影不再单纯是镜头之间的组合剪辑,更是一个浸透了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构造。“原文本”与其他或隐或现的“副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关系,甚至比电影文本自身更加醒目。[1]141-1422015年4月,人艺青年导演徐昂的处女作《十二公民》公映,其“副文本”显然指向好莱坞1957版经典法庭片《十二怒汉》。事实上,远早于徐昂,1991年日本版《十二个温柔善良的日本人》、2007年俄罗斯版《十二怒汉:大审判》早已嫁接各自的本土文化,成功演绎不同民族版本的《十二怒汉》。“西德尼·吕美特无需为影片中的戏剧化风格而作出解释,这种风格演绎为一种优点,即在幽闭的空间中产生更令人紧张的气氛。另一方面,摄影导演鲍里斯·考夫曼从罗斯的结构紧凑的剧本中发掘紧张的背景气氛,堪称擅长在有限空间内拍摄的黑白电影专家。”[2]331《十二怒汉》唯一的场景是一间不足40平方米的陪审团的休息室,12位陪审员挤在其中,讨论一个被指控的贫民窟问题少年是否弑杀父亲。令人反思的问题是,西德尼·吕美特这部法庭影片何以能长盛不衰,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绽放出风采卓异的花朵?此外,在这样一部缺少场景转换、情节单一的舞台剧式电影中,戏剧性是如何与电影性联姻的?
在高度忠实原版基本编剧结构的基础上,《十二公民》以近乎话剧的形式对电影人物进行符号化的本土改编,同时抛出“富二代杀人”、“地域歧视”、“干爹现象”等社会热点议题。十二位演技高明的戏剧演员集体亮相,以“性格化”的戏剧表演诠释了其所代表的不同阶层。“他们每一位都带着自己的故事而来,在对案件的抉择上参照个体前史经验。徐昂似乎也并不在意‘电影化手段’,一切几乎都通过演员大段大段的对白来完成。”[3]98《十二公民》的导演徐昂来自北京人艺,电影演员也全部来自国家话剧院或北京人艺。影片成功完成一次在封闭空间的良心拷问,几乎是把一整幕话剧搬上了大银幕。令人惊叹的是,相比于《煎饼侠》的火爆场面和《捉妖记》的粉丝捧场,《十二公民》这样一部不合“主流”的“反动”电影居然获得了业界的一致好评。研究这部扎于中国现实最敏感神经之上的罕见“戏剧电影”,剖析影片中十二位演员精彩的“性格化”戏剧表演,自然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一、言语视像与“舞台语”技巧
最能影响戏剧演员舞台言语表现力的是“内心视像”,换而言之,即把“插画式的规定情景”嫁接于演员的舞台语言(台词处理上)。“我们的天性是这样安排的:当我们和别人进行言语交流的时候,我们开头是以内心视觉见到所谈的东西,然后才谈出我们所见到的。如果我们在听别人说话,那么我们就是先以耳朵来领会我们所说的,然后再以眼睛见到我们所听到的。听,在我们语言中,是意味着见到我们所说的;而说,就等于在描绘视像。话语对于演员不单纯是音响,而是形象的刺激物。因为当你们在舞台上进行言谈交流的时候,与其说是对耳朵说话,不如说是对眼睛说话。”[4]96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只有极少数天才演员能够“本能地先在脑子里‘见’所要说的东西,然后再把它说出来。很少有演员能够天才地自发地运用脑子里形象思维的机能来给自己说的台词创造言语视像……戏剧表演技巧的规律,不仅体现于演员‘说’台词的技巧,而且还是演员‘听’台词的技巧”[5]206。在一定意义上,《十二公民》更像是8号陪审员(何冰(1)饰演的理智与情感兼具的检察官陆刚)对其他十一位陪审员及其所代表的各色阶层上的一堂法学基础课。作为北京市检察院的资深公诉人和主诉检察官,长期的职业生涯让陆刚养成了“排除合理怀疑”(2)的态度。他依赖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维路径,步步为营、抽丝剥茧,最终在说服其余十一位陪审员的同时,向后者成功诠释现代司法的精神理念与尊严价值。陆刚这一角色的演绎既需要爆发力极强的激情表演,又需要沉稳内敛的美学表演风格。如果缺少言语视像、感觉记忆和内心视像这样的戏剧表演技巧,很难取得成功。

电影《十二号公民》 海报
回到电影《十二公民》中何冰的表演上来,何冰本人认为真诚的表演才是对戏剧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于表演应该从两个方面谈,一个是表演技术;一个是演员为人。在人面前,技术不重要。谁的技术好一点,谁的经验丰富一点,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决定一个演员表演的好与坏。演员在表演中毫无杂言的创作品质,才是最难得宝贵的。”[6]87陆刚这个角色被徐昂导演定位为“理性”,可问题是“理性”究竟该如何演绎?在排练的过程中,何冰即有效运用了“言语视像”的表演技巧,他告诉徐昂:“我是个演员,我不知道理性该怎么演。我只好就坐在那儿,我说我得出现视像,在我眼里没人了,就是个大脑——这是我的大脑,我看着我的大脑,是一号,我不知道他在帮助我。二号这是我的算计跟胆小,三号是我内心强烈的愤怒,四号是我的傲慢,五号是我的隐忍。我就这么挨个分,脑子里不去看人了,不去看谁谁谁了,就这么训练。我说你看行吗现在出来,徐昂说可以,就这么来。”[3]99在大多数情形下,何冰的表演中规中矩,形体和台词带着些许戏剧演员的痕迹。作为一部变奏版的主旋律故事,这与陆刚的角色设置有关,因为“检察院元素”的植入要求检察官必须是所谓的“一身正气”形象(3)。[7]38尽管如此,陆刚发飙失控的几大段表演还是彰显了何冰的表演功力。笔者不敢断言何冰那时是否自发地或者无意识的运用上了内心视像和感觉记忆,但几个场景相信把观众全都看得屏住呼吸、凝神沉思。当10号陪审员说“我们在这儿判决半天起不了什么真的作用;其次,答案都这么明显了,再说小事儿那就是吹毛求疵了”时,一直温文尔雅,给人沉稳理智印象的陆刚终于拍案而起。相信正是“言语视像”舞台语技巧的应用,让演员何冰恍惚间看到了蒙冤入狱的“富二代”的无奈与惊恐,让他仿佛看到“呼格案”中呼格父母的一头白发。也正是其他陪审员的麻木不仁激起了演员内心狂乱的感觉记忆,何冰因此能够出神入化的精彩演绎下面的台词:“咱们现在是在法律大学的教室里,为了一批将来要成为法官的年轻人在讨论一件谋杀案!当然是为了我的儿子,也是为了您的儿子!是为了我们的儿子在谈论一个人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这个人是不是应该被枪毙,事关一个人的生命,难道不应该吹毛求疵吗?!(声调提高,运用颤音)往大了说,事关一个国家未来法律的公正!不应该吹毛求疵?!(声调绷紧到最高点,再次运用颤音,似乎要爆发一般。众位陪审员都安静下来,10号陪审员也坐回了自己的座位。此时何冰稍作停顿,放下激动挥舞的双手。)吃饱了撑的,把孩子送到这儿来念书!”[6]169这里的“耍点子”、“言语视像”技巧的运用相信抓住了每一位观众。
反观与何冰演“对手戏”、扮演3号陪审员的韩童生(4)老师,也可以说是运用“言语视像”的舞台语技巧撑起了戏份的半壁江山。“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3号表面上有着老北京的一切特点,油嘴滑舌,市侩,民粹主义,善良,懦弱,而他深藏的部分也被演绎得很好。与儿子的矛盾所造成的严重的心理阴影都通过对所谓的孝道的偏执报复性地传递出来。”[7]39当狂躁的3号陪审员反驳11号陪审员时,有这样一段台词:“合理怀疑?呸,你甭在这跟我臭拽!(从桌上拔出刀,把它举起来)唉唉!看看这儿,这个!有人亲眼看见那个你刚刚说的这个,清白的、可爱的小朋友,把这个东西,插进他爸的胸口上了!合理吗(把刀插进桌子里)!你可真是好样儿的!”[6]196应该说,稍有想象力的演员都会将言语视像沉入到自己想象的事发场景中。但是要观众能从演员的神情中感觉到刀刃的冰冷,体悟到3号比刀刃更加偏执冷酷的心灵,那就见艺术家的表演功底了。韩童生扮演的3号陪审员从感情至上最终回归理性,他决定无罪的举手瞬间相信震撼了每一位观众,而那一番关于“父子心结”的倾诉更是深深扎在了每一位观众最敏感的神经之上:“……打这起,六年没回来,六年一个电话也没有。为这个,他妈跟我离了。我没事,我一个糙老爷们儿我怕什么啊,可他妈怎么办啊?我一个人一天能吃几顿饭能花几个钱啊?我每天起早贪黑每天出车我都不知道是为了谁!我看见那个‘富二代’我就觉得刀子捅进来了,你们怎么都觉不出来,怎么就只有我一个人觉出来了!”[6]238在这里,韩童生扮演的3号表面是愤怒,心里却在流泪。他恨着自己的儿子,但是作为家长,他也恨着自己,恨自己的冷漠,无情的在检讨自己。如此精彩的表演不仅需要天赋的想象力,更需要将规定情景“插画式”的天赋“形象思维”才华。也可以说,这是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经典“言语视像”理论——“听”,意味着见到人们所说的,而“说”,就等于描绘视像——做出了最好的论证。[5]206
二、“潜台词”与戏剧表演
演员在台词创造时,“潜台词”表演是其遇到的最为重要的心理技巧。剧作家运用高超的写作技巧,创作出大量反映剧中角色性格特征的,或指桑骂槐、或指东说西的弦外之音。而演员在表演创作时遇到的问题则是,需要把角色“潜台词”的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准确表述出来。应该说,《十二公民》之所以人物性格鲜明、表演出神入化,和演员准确演绎各段具有丰富内涵的潜台词息息相关。
韩童生扮演的3号是典型的北京出租车司机,身穿黄色制服,手拿一个雀巢咖啡伴侣的旧瓶子,上边套着老婆勾的毛线套儿,瓶子里的茶酽得吓人。他的衣着总保持刻意的整洁,就像刻意要求别人给予他尊重和认同似的。3号嗓门很大,说话尖锐刻薄、咄咄逼人,似乎每句话都是带有弦外之音的“潜台词”。韩童生说:“作为一个生活在胡同里的地道的北京人,他会自然而然地说出许多片汤话,他的语言也会自然地流露出一些懒散和玩世不恭。当他急了的时候,他也犯北京的三青子。”细细品味韩童生的“潜台词”表演,在他指桑骂槐的“潜台词”语言下,其实又深藏着一颗受伤和敏感的心。[6]41作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出租车司机,3号知道如何与各色人物打交道,如何讨取他们的欢心。所以在与何冰扮演的8号陪审员初遇之时,他会带着出租车司机特有的贫,打趣陆刚:“您别看您小鼻子小眼儿的,怎么能生出那么一个浓眉大眼的儿子来呀,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啊,基因那东西我觉得不一定可靠。”而当陆刚挑战其余十一位陪审员,投出“无罪”票之时,他的话里开始充满了挑衅:“我怀疑你刚才是一直睡觉来着。就算你刚才睡觉,你电视总看吧,网你总上吧?广播里天天讨论这个案子,你总听见过一耳朵吧?”韩童生的表演十分精彩,那语调神情把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让观众全听明白了——“别和大家伙儿为难,我这一关你就甭想过!”果然,往后,只见3号像遇到了天敌一样,和陆刚“死磕”上了,开始捍卫起一件件看似无懈可击的“铁证”。而当所有的证据都存在“合理怀疑”,场上其余十一人都认定“富二代”无罪之时,他开始刷的一变脸,眉毛直竖、狠狠地大声嚷道:“从法庭到媒体、从人证到物证,都告诉你们一个浑蛋儿子杀了自己的父亲,都在告诉你们他是有罪的!学校出的题是——让我们根据现在得到的证据得出一结果,你们照着证据来了吗?!你们现在在证明所有的证据都是错的!(对陆刚)你有权利坚持你的观点,我也有权利坚持我的看法儿。不就是耗着么,来吧,我今儿打算住这儿了。”3号陪审员索性躺在了躺椅上,那架势,实际上已经把“潜台词”的言外之意——“我和你们‘死磕’上了”全部表达了出来!辅之以动作表演,戏剧冲突通过“潜台词”不断向强节奏推进,而角色的性格特征也从而被赋予更具感染力、更深切丰富的内涵。
按照胡导先生的说法:“人物在第二计划中进行言语行动时,或者说,人物在进行双重行动,特别是在进行双重的心理行动时,所说出的台词,一定具有潜台词意味或本身就是潜台词。人们在生活中说话时,有没有言外意、画外音,会自然呈现为不同的语调——重音字配置的不同,速度节奏处理的不同,是否运用停顿也不同,相联系地说话人的神情流露等都会不同。”[5]209-210在影片《十二公民》中,有好几段关于天气的漫不经心的对话,其实句句都包涵着潜台词。例如,“这天儿阴的!雨再下不来,真能把人憋死……”(5号陪审员)、“哥们儿,不热呀,这么捂着?”(5号陪审员)、“要下雨了。”(2号陪审员)、“这雨终于下起来了。”(陪审团长)、“这雨下的,让我想起以前的一场雨——就在工体的那场球。”(陪审团长)、“雨真大。”(3号陪审员)。假若演员在表演之时,既不能“听懂”作为潜台词的天气与案件之间复杂微妙的隐喻关系,又无法“看到”各位陪审员内心的烦躁挣扎犹如波诡云谲的天气,那么观众真的只会以为演员在冗长单调地谈天气。概而言之,演员在创造角色的潜台词时,要把人物在当前语境下不直接向对手人物说的话,通过语调处理、节奏控制、神情表露和顿歇运用说出来。惟其如此,观众方能真正感悟到“潜台词”的弦外之音。在《十二怒汉》片尾(1957年版),雨过天晴,一众身心俱疲但经历暴风雨洗礼的陪审员走出法院。与《十二怒汉》呼应,在《十二公民》的结尾,十二位被“烦躁”包围的陪审员走出闷热难熬的讨论室,步入夕阳之中,他们相互搀扶、互相交流。这样“光明”的结尾也许可以视作两位导演运用的电影语言“潜台词”,但表现过于直白,相信只要不过于愚钝的观众都能看明白。
三、结语:性格化戏剧表演与现实主义戏剧传统的回归
现实主义戏剧原则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剧中角色的社会属性、时代特征、典型性格藉由尖锐的社会题材和写实的社会环境凸显出来。从五四时期的戏剧《娜拉》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抗战戏剧”和“左翼戏剧”,中国戏剧界在创作中明确提出过“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这样的口号。进入新时期,剧作者逐渐认识到:“戏剧复归到‘五四’以来易卜生式的现实主义的本质内涵上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现实主义戏剧并不是一个僵死的概念,它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8]90-921957年美国版本的《十二怒汉》本质上所普及的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陪审团制度,它有助于观众懂得如何尊重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和权力;俄罗斯版本的《十二怒汉:大审判》无疑体现了一种抛弃成见与仇恨,重寻善良仁义、展望未来的美好意愿;而日版的《十二个温柔善良的日本人》则抛出了一个纠葛复杂的终极命题——在人情与法理相悖之时,我们应该怎样站队?与美俄日等国情况不同,中国的司法体系中并没有陪审团制度。《十二公民》以模拟陪审团为前提,使原作的根本语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事实上,电影故事与陪审团制度关系并不大,仇富心理、明哲保身、地域歧视、父子代沟、官民矛盾……这些激流涌动的社会问题、这些触及中国焦虑、中国尴尬的各式现实偏见才是与观众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上来说,《十二公民》这幕呈现于大银幕上的话剧之所以具有非凡的“现实主义精神”,正在于它深深扎入了中国现实最敏感的神经之上——我们究竟该如何消弭中国社会各种先验的偏见?
依赖12位演员棱角分明的性格化表演,《十二公民》的现实主义戏剧传统方才得以回归。“圆滑世故的小摊贩、淳朴老实的保安、玩世不恭的刑满释放人员、心思缜密的企业家、游手好闲的包租公、满嘴京片子的土著的哥。由他们所引申出来的偏见,也囊括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父子代沟、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歧视等等早已深入人心的扭曲观念。这些观念与他们各自的职业和地位息息相关,而且时时刻刻都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9]122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十二公民》如万花筒般映射出当下中国转型期现实的横断面,凸显中国现实生活中各种观念的冲突以及沟通的困境。评论电影中演员的精彩演技、评鉴角色所创造的各色台词,恰也是一次对于现实主义戏剧传统的反思。
注释:
(1)何冰,北京人艺演员,1999年曾获第1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04年二度荣获该奖。何冰以演绎一些京味儿十足的小人物让人印象深刻,曾出演《戏剧的忧伤》、《茶馆》、《大将军寇流兰》等话剧。电视剧代表作有《浪漫的事》、《大宋提刑官》、《空镜子》等;电影代表作有《甲方乙方》、《没完没了》。参见李玉娇等著《十二公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页。
(2)“‘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刑事案件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由于刑事诉讼中贯彻‘无罪认定’的公认原则,所以除了特殊情况外,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排除合理怀疑的运作要素主要为证伪方法,对于陪审团来说,首先是一个寻找控方有罪证据的瑕疵或疏漏的过程,其次是运用逻辑思维检验控方的论证是否充分的过程。”参见张雪纯、葛琳《证伪方法、经验法则和心理因素——以影片<十二怒汉>为分析文本诠释“排除合理怀疑”在陪审团制度下的运作要素》,《当代法学》2005年9月第19卷第5期,第105-106页。
(3)2015年6月2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专访《十二公民》导演徐昂,将该片当作普法教育的蓝本。联系当下热议的“呼格案事件”以及本片联合摄制单位的“中国检察官文学艺术联合会”,似乎可以把《十二公民》视作变奏版的主旋律故事。
(4)韩童生,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曾获第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3届中国戏剧金狮奖。代表作有话剧《玩偶之家》、《生死场》等;电视剧《永不瞑目》、《家有儿女》、《范家大院》、《浮沉》、《裸婚时代》、《民兵葛二蛋》等;电影《阳光照进现实》等。参见李玉娇等著《十二公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页。
[1]赵毅衡.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史蒂文·杰伊·施奈德.有生之年非看不可的1001部电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3]康怡.《十二公民》:对经典的平庸改编,还是上半年最好的话语电影[J].大众电影,2015 (10).
[4]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M].郑雪来,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
[5]胡导.戏剧表演学:论斯氏演剧学说在我国的实践与发展[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
[6]李玉娇,徐昂,韩景龙,等.十二公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7]杨时旸.《十二公民》:没有人关心真相,所有人只想发泄自己[J].中国新闻周刊,2015 (21).
[8]刘平.新时期戏剧启示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9]时间之葬.不同土壤中开出不同花朵:美日俄中演绎各自的《十二怒汉》[J].国家人文历史,2015(12).
J90
A
◆本文是西南科技大学博士研究基金项目“‘虚无’世界的‘黑色悲剧’——20世纪‘新黑色电影’研究”(项目编号:11sx7113)阶段性成果之一;西南科技大学“50年代中国的文化、传媒与社会”科研团队(项目编号:13sxt016)阶段性成果之一。
尹兴,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副教授,广播影视文艺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广播影视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