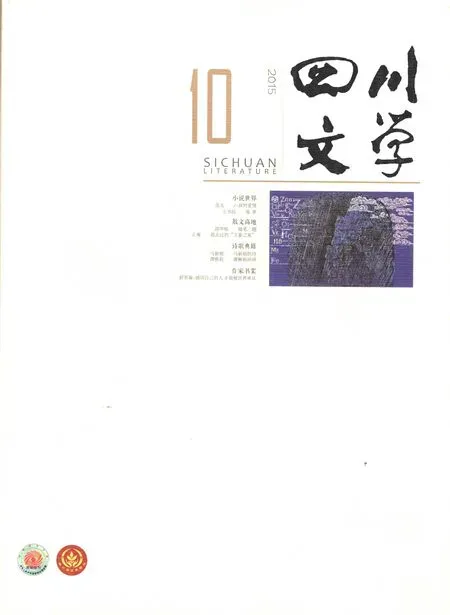感动自己的人,才能被世界承认—非访谈刘震云
舒晋瑜/文
大多数时候,刘震云是不动声色的,包括他的幽默。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目光平和,有时候看着你,有时候了不知道看谁,旁若无人地自顾自地说。在平常的闲聊中,刘震云大概是使用对话最多的作家。他会随口编一段对话,涉及的两个人,也许一个是上海人、北京人或其他人,但另一个肯定是河南人。他甚至会用不同的方言(也许不太准确)去完成这个对话,扯着扯着,眼看不着边际了,陡然间一句话就能把你带回到原来的主题。你才发觉,被他绕了一个大弯子,虽然绕远了,但却饶有兴趣,就是你心甘情愿跟着他的语言走迷宫,到了终点还意犹未尽。
这就是刘震云的魅力。所有他在的场合,能带给大家无穷的乐子。你就听他讲故事,听得懂就会心地笑,听不懂的也能被他的神态迷住。他比较常用的口头语是,“这样的话呢”,说完这个就表示故事又有了递进。他是一个比较会写故事,也比较会讲故事的作家。《甲方乙方》《手机》《我叫刘跃进》等影视作品的成功,使刘震云打响了中影集团打造的“中国作家电影”第一炮。他几乎成了“专业贺岁作家”。
为什么是刘震云?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他是那么普通的一个人,不用上班,过着规律甚至有些闲适的生活。他早晨六点半起床,跑步一个半小时,上午工作两小时,下午工作两个半小时,晚上九点半就睡觉。不写作时看书,或者出门见人,要么就去买菜,和菜市场的人交朋友。他喜欢有生活品质的人,这与职业无关。他和卖水果的胖子成了朋友,胖子可以支使他帮忙挪水果箱,也会邀请他去水果摊后的大帐篷里尝尝刚出锅的饺子;他和钉鞋的湖北师傅成了朋友,湖北师傅习惯带着手套钉鞋,缝完拉链会反复用肥皂打磨,特别认真,这使那份工作看上去有一种尊严感。装修房子,他又和卖石材的老赵成为朋友,老赵只跟他说心里话:“像我一个卖石头的,能有什么呀,就剩下心里话了。”这让刘震云无比感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他又是极其不普通的人。他读了20多遍《论语》,总结孔子有三大特点:“第一,孔子是非常刻薄的人。过去我认为他是忠厚的人,其实不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因为孔子和身边的人没有话说。刻薄的人有见识,刻薄的背后,藏着对所有人的悲悯。可能刻薄的人更忠厚。第二,孔子是大作家、大思想家,他不是把事儿往深刻里说,是把深刻的东西往家常里说,这种境界也了不得。把事往深刻里说的,过去我觉得是大师,但现在我意识到其实那是学徒。第三,孔子说话绕,绕半天就不知绕到哪儿去了。这三个特点,经琢磨。”
《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大书
不知道此言一出,刘震云是否会得罪朋友。但是听他讲完故事,便知道这又是肺腑之言,是这个时代毫无意外的结论。虽然简要地概括一部作品可以有不同角度,比如认识的角度、面对世界的角度,或者情感的角度。但是概括《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是以故事的角度:两个杀人犯,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到他就是想和他说知心话。
好朋友的意思,不是你缺钱的时候他借钱给你,而是面对事情、面对世界、面对生活的态度相同,具体到某一件事上有默契。刘震云说,在生活中找一个朋友不容易。人神社会和人人社会的最大区别,是多出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也许神不存在,也许无处不在。神可以使你痛苦、忧愁、想忏悔的时侯,有个落脚的地方。中国的社会,如果你有忏悔、有忧愁,没有上帝,只好在人与人之间找一个知心朋友。“人找人,话找话不容易。” 神不会背叛人,但是朋友会变得不是朋友,如果他把你的话兜出去,知心朋友会变成一把刀扎向你的胸口。所以有时候,知心的朋友是危险的。
“一句顶一万句”是林彪1966年说过的话,时隔43年,刘震云拿出来做书名,有何用意?他说:“我今天说这句话,跟林先生是话同音不同意。他的话是政治指向,要达到政治目的,我指向的是生活。我这部作品中的人物,皆是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还有提刀上路杀人的……我对他们说的,是一句知心话。”他进一步解释说,“一句顶一万句”,也不是林副主席和他的发明,这意思古来有之,已被人说过几千年。比如说“一智能破千年愚”,“一语定乾坤”,“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说的都是“一智”、“一语”的重要。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和牛爱国戴“绿帽子”,原因并不在杨百顺和牛爱国身上,而是他们的老婆出了问题。杨百顺和牛爱国发现自己身边出了西门庆和潘金莲时,提刀上路就要杀人,当找到时又突然发现错不在他们,而在自己。自己的“绿帽子”,原来是自个儿缝制的。杨百顺和牛爱国发现,“绿帽子”只是个表象,看似是男女间的事,根子却不在这里,而是因为他们跟他们的老婆之间没话,老婆与给他戴“绿帽子”的人,倒能说到一起。偷汉子的女人和奸夫,话语如滔滔江水。说了一夜,还不停歇:“咱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从有话无话的角度讲,给他戴“绿帽子”的两个人,做得倒是对的。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从腰里拔出刀子,又掖了回去。
“从男女关系的角度说,潘金莲该杀,但从有话无话的角度,从知性的层面讲,他们是对了。”刘震云说,自己无意为潘金莲平反,而是不同的角度。他采取的是公众视角,从虚的角度讲这个故事,西门庆和潘金莲冲破了所有的束缚和规矩,冲破了人类所有的道德底线,奋不顾身,越过高山大海也要到一起去,他们是英雄。
写作就是找朋友
写作的圈子,影视的圈子,媒体的圈子……刘震云出进自如,他的人缘很好,几乎没有听到过负面的反映,也没看到过负面的报道。即使是有争议的评论,也是就作品论作品。然而,朋友满天下的刘震云,内心又是孤独的。当他说,他在作品中找朋友时,我感觉到他的悲伤,就像一个热衷于摆积木的小孩子,摆好了,推倒再摆,沉迷于自己搭建的世界,孤独抑或自得其乐,无人得知。
“我的写作让我意识到,写小说是认识朋友的过程。写《一地鸡毛》的时候我认识了小林,他告诉我,家里的一斤豆腐馊了也不扔,比八国首脑还重要,我就说这是一件大事;写《手机》的时候,严守一问我:你觉得谎话好不好?我说不好。严守一说:你错了,是谎话而不是真理支撑着我们的人生,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写《我叫刘跃进》时,刘跃进问我:世上是狼吃羊还是羊吃狼?我说废话,当然是狼吃羊。刘跃进说错了!他在北京长安街上看到羊吃狼。羊是食草动物,但羊多,每只羊吐口唾沫,狼就死了。到《一句顶一万句》时,杨百顺和牛爱国告诉我:朋友的意思是危险,知心的话儿是凶险。我说有道理,我吃这亏吃得特别大。”刘震云说,写作对自己最大的吸引力和魅力,是可以在书中找到知心朋友。书中的知心朋友和现实中的不一样,书中的朋友永远是有耐心的,这本书中的人物可以说是我最真心的朋友。什么时候去找他们,他们都在那儿等着你。这是他写作的动机,也是写作的目的。
“我一直努力坚持我在文学和生活圈子的关系,我喜欢就不能零碎地做这些事。要全面、整体、多方位地找书中的朋友,调整文学生活和自己的关系。”刘震云说,大致有4个系列,一是故乡系列,二是“一”字头系列,比如《一地鸡毛》《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三是官场系列,有《官人》《单位》,后来看到好多人在写,他就不写了;四是“我叫某某某”系列,下一部书肯定会是“我叫XXX”,也许有一天会写一部“我不叫潘金莲”。
我不直腰,所以割麦子比别人快
刘震云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归结为是因为有深入持久思考的能力,直接的影响者,则是外祖母。
“我受外祖母影响非常深。她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但她年轻的时候,在我们那儿是特别大牌的明星,她的名气相当于朱丽娅•罗伯茨,朱丽娅成为明星不奇怪,因为她是演员。外祖母成为明星不容易,她是长工。那时她在地里割麦子,三里路长的麦子割到头不直腰。她的‘转会费’非常高,像罗纳尔多。外祖母说,我为什么比别人割得快?我知道不直腰。直第一次,就想直第二次,直第二次就有第二十次。我知道干什么事都得伏下身子不直腰,所以我‘割得比别人快’。”
“真正的好作家首先得是思想家。”刘震云说,见识是考验作者的最根本的标尺。“作者的写作手段都是差不多的,真正的考验不在写作中,而是在写作前,在于你能不能从相同的生活中有不同的发现。就是作者的见识是否独特,凡是好作者,见识与其他人必然不同。”
考量一个作者,看其是否具有深入持久的思考能力至关重要。刘震云解释说,这里的思考有两个层面:一是整体思考。开始写之前要想好到底写多深多长,思考两天和两个月不同,思考两个月和两年又不同;二是写作时的具体思考,细节、人物、情节、对话都要照顾到。还有一个是持久思考,要对自己的创作体系有整体考虑,不能乱枪打鸟。“写完《一地鸡毛》,再写《一地鸭毛》,读者喜欢,评论家也喜欢。但是我希望改变。”“写出好作品,在写作前和写作时深入思考,写作后迅速遗忘也特别重要。就像重新登上另一个山头,从零开始。不断把自己归零,也是我的习惯,不管是生活还是写作,我习惯不断重新开始。我相信以后能写出好作品。”
结伴去汴梁
常常有人问刘震云:你是怎么想到写《我叫刘跃进》的?他不直接回答。他说:“我常拿结伴去汴梁打比方,俩人在一个路口相遇了,‘大哥,去哪里?’原来都是去汴梁。吸烟,说话,又投脾气,于是结伴而行。走着走着,更熟了,开始说些各自的烦恼和压在心底的话。到了汴梁,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揖手而别。过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那人兴许磕着烟袋想,‘老刘也不知怎么样了?’”
在刘震云那里,这种相遇不是偶然的,《一地鸡毛》《温故1942》《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我叫刘跃进》体现的是他的思考与创作处于不同阶段时的状态。他一路走过来,在那段路上碰到小林,经过一段路又碰到300万灾民,再走再碰到一大批胡思乱想的人,走到现在就碰到刘跃进,这种相遇不是乱竿打枣。这个变化在外人看突然,在他内心是必然。这是作者创作体系的问题。
《温故1942》的创作使刘震云第一次意识到能“结伴去汴梁”的重要性。“我在生活中碰到一个朋友,他要编一部百年灾难史。其中有1942年河南旱灾饿死了300万人,作为河南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调查这场灾难。我去问活下来的当事人,问我外祖母当年的情况,我外祖母就问:‘哪一年?’我说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外祖母还是问:‘饿死人的年头多了,到底是哪一年?’深重的灾难竟然瞬间转变成另一个事:遗忘。你们家死了这么多人都不知道?忘了。我就急了,遗忘使我震撼。这种态度比前面的考察都重要得多。”从此开始,他就不断地“遇”到能够相知相交的“伴儿”。
写完《一地鸡毛》,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写300万灾民。以刘震云的创作轨迹,写完《我叫刘跃进》,绝不会有《我叫李跃进》。“我再有什么作品,也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意想不到,不但对读者重要,对我也重要。”
谁是贼?刘震云才是“贼”
和刘震云接触多了,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特别善于琢磨、善于领悟,更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作家。他真诚地说:“不是我谦虚,是确实不懂,我对世界知道得不多。如果知道得少,假装知道多,容易把自己架在半空中。身边好多朋友说的道理我不明白,后来明白了是因为学习了。‘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两人行就有我师。发现别人一百条缺点,于你无补,发现优点才有好处。谁是贼?刘震云才是贼,从别人身上学东西,是深入思考能力的营养补充。”所以,只要有时间,他不拒绝和任何人一块儿坐一坐。
在《甲方乙方》中,刘震云扮演了一个失意青年;在《我叫刘跃进》中,他扮演了只露了一面的打哈欠的人。虽然镜头不多,刘震云却又学到无数东西。“最大的收获是发现电影对话的趣味,过去小说对话是顺着下来的,‘吃了么’,‘吃了’,‘吃什么’?‘红焖肉’。电影中不这样,这一句说:‘吃的什么?’下一句就是‘老张这家伙不是东西!’再接下来可能说:‘老李这两天可没闲着。’对话的信息量高度密集,极有趣味性,这种形式放在小说里,更有趣味性。学到很多书外的东西,没坏处。”
“还有一个收获,接触到了不同的人。比如导演、演员、摄影师、搬道具的小伙子……他们都是过去我没见过的人。由于行业的不同,他们说话的习惯和做事的方式不同。这对我有两个好处,一是对生活面了解得更宽了,二是,发现每个人都是一个哲学家。搬道具的、群众演员……千万不要小看他们,他们思考世界的角度会对你有启发。”
“我在《农民日报》认识一个校对老姚,我们俩关系特别好,他是哲学家,他爱指出我作品里的错别字,每次都很严肃。我说:‘您不是一字师,是几百字师。’生活中,他教我好多道理。比如说饿着肚子千万不要上街,那样容易乱买东西,吃饱了上街省钱,我试了试,果然是对的。”
刘震云读书,也能读出别个无法体会的味道来。他把书分三类:一类像白开水,作品和生活一样,不读也罢;一类像酒,但喝多了会变形;一类是酒精、酵母,这才是真正的好作品,不是作者写完就完成了,而是读者读完也没完成,只完成一半,好多年过去,又读了两遍,和作者的心相通了,会心一笑,这时作品才完成了。“过去有一句话,叫功夫在诗外,同样,功夫在书外。《论语》并不长,为什么不懂?是因为字之外的东西多,越读越多,这样的书费劲。这个费劲就证明,读者和作者的碰撞是一次完成不了的。真正的好书不是作者一个人完成的,是激发读者思考感受的触发点,这样的书,才真正能够使读者和作者一起完成共同的写作。书读完了,真正的读书才刚刚开始。这是读书的比较好的境界。”
一个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来到河南一个县传教,传教40年一共发展了8个教民。一天,传教士碰到了杀猪匠,就想发展他。传教士问他:你信主吗?杀猪匠说,我不信,我信主有什么好处?传教士说,主能让你知道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杀猪匠说我现在就知道,我是一个杀猪的,从张家庄来,到李家庄去杀猪。传教士想了半天说,你说得也对。接着又说,你总不能说你没有忧愁。杀猪匠说,我有忧愁。牧师说,有忧愁你不找上帝,你找谁呢?杀猪匠说:上帝能告诉我什么?传教士说,信主,主马上会告诉你,你是一个罪人。杀猪匠马上急了,说我跟他一袋烟的交情都没有,怎么还没有见面他就说我错了呢?……传教士死后,杀猪匠打开了传教士设计的教堂图纸,那是一座宏大的教堂,彩绘的玻璃,精致的座椅……杀猪匠发现教堂上面的钟在轰鸣,所有的窗户全都推开了,自己心里的窗户也被推开了。这个时候,他知道这个传教士是世界上最好的牧师……
“传‘教’给我喜欢的人,也是我奉行的准则,把‘教’传给汉学家和批评家,这事我不干。”刘震云认为,感动自己的人,才能被世界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