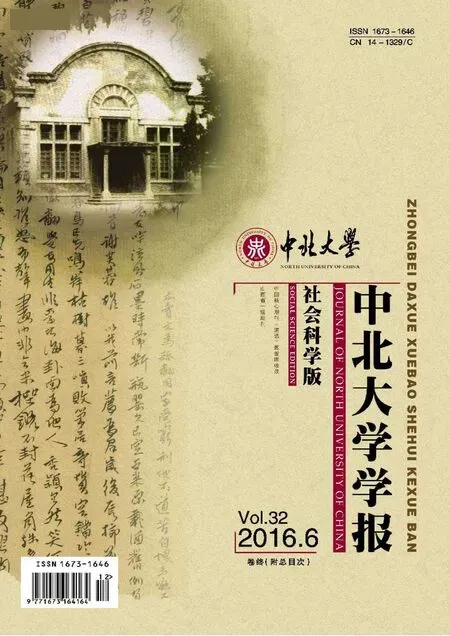谁的创伤在说话——《塔楼》的创伤叙事分析
李若平
(山西医科大学 外语系, 山西 太原 030001)
谁的创伤在说话
——《塔楼》的创伤叙事分析
李若平
(山西医科大学 外语系, 山西 太原 030001)
《塔楼》是美国当代女作家珍妮弗·伊根的畅销之作, 本文以该小说为文本焦点, 以创伤理论和修辞叙事批评方法为理论基础, 分析作者在创伤叙事背后的交流目的以及由此引发的读者叙事判断, 指出《塔楼》的叙事核心是创伤: 童年创伤、社会文化创伤及创伤的复原。
珍妮弗·伊根; 《塔楼》; 创伤; 修辞叙事
心理创伤是个现代性、社会性的话题, 指社会生活中较严重的伤害性事件所引起的人的不正常状态, 既涉及个体也涉及群体。 它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 往往会改变人们对自我、对他人、对世界的看法。 创伤文学则力图通过“再现创伤的形式和症候来表现创伤的冲击力”[1], 反映创伤人物的创伤经验引起的自我重建或社会文化创伤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在众多的创伤文学中, 当代美国女作家、2011年普利策小说奖获得者珍妮弗·伊根(Jennifer Egan, 1962~)的作品《塔楼》可谓独树一帜。 《塔楼》是伊根2006年出版的畅销之作, 然而, 自它问世至今, 人们一直将其视为“恐怖小说、悬疑故事或浪漫传奇”[2], 惊叹于它的荒诞与超现实, 却忽略了作者着力凸显的创伤一面。 本文欲融合创伤理论与修辞叙事批评方法, 通过分析小说所呈现的构成创伤叙事的多种技术路径, 揭示《塔楼》的核心是创伤。 这是一部匠心独运的创伤小说, 同时它也间接地表达了作者对后现代社会敏锐的思考。
《塔楼》共十六章, 分三部分, 前两部分聚焦于男主人公、正在监狱中服刑的罪犯雷和他创作的网络、手机控丹尼为主人公的故事, 第三部分是雷的写作课教师霍莉的叙事。 为了方便论述, 笔者现将《塔楼》分为框架叙事层和嵌入叙事层, 前者是由故事叙述者“我”分别讲述的两个不同的“雷的故事”与“霍莉的故事”, 后者则是由雷讲述的“丹尼的故事”。
1 童年创伤与社会文化创伤
嵌入叙事层“丹尼的故事”是由一个正在监狱中服刑、名叫雷的罪犯讲述的。 在丹尼的故事中, 伊根试图通过童年创伤对个体人生的影响来隐喻社会文化创伤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冲击, 其透视角度是施害者因自我行为对自身造成的创伤。 丹尼幼时曾把表兄霍华德推入到岩洞的水池中, 导致后者几乎淹死, 这个创伤事件使得两人从此踏上不同的生命航程。 成年后的丹尼生活困顿, 承多年未谋面、已腰缠万贯的霍华德之邀, 决定共同将一哥特式的欧洲古堡重修为一座完全杜绝现代化通信工具的旅馆。
童年恶作剧给丹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内疚、自责等罪恶感由于缺乏直接交流的渠道, 没有被发泄出来, 导致他患上了发育创伤综合症(Developmental trauma disorder)[3], 使他从一个 “好孩子”堕落为“失败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创伤通过自我潜意识的防御和适应机制被压抑到脑海深处。 但是, 当他与霍华德在古堡重逢后, 创伤浮出水面, 其“延宕性”体现了出来。[4]在《塔楼》第十一章, 夜幕降临, 丹尼无意间来到古堡水池边, 竟发现水池产生了诡异的变化。
“丹尼站起来。 这不可能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我不相信这会发生。 他看到池水张开, 出现一个坑, 好像一张嘴、一条隧道或者一座坟茔, 相当大的黑洞, 丹尼感到一丝恶心。 这不是真的, 这是幻觉, 都是我脑子里的想法, 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5]158
在上述这段文字中, 下划线处是自由直接引语(不带引号和引述语的直接引语), 它们构成了人物的内心独白, 反映丹尼的自我意识在慢慢减弱, 而潜意识心理活动却在不断加强, 暗示出丹尼那种莫名的、混杂着恐惧的紧张感。 古堡中的水池与童年岩洞事件中的水池相似性成为丹尼创伤记忆的扳机点, 这不受其主观意愿控制, 深埋在潜意识当中的创伤记忆通过幻觉浮出水面。 小说中关于创伤事件受害者霍华德的记忆、梦境和幻觉多次重复入侵丹尼, 并以现在的方式蛰居在他内心深处, 成为他在古堡生活的一部分, 使其惶惶不可终日。 丹尼想要逃离古堡, 逃离创伤记忆, 却又像麦比乌斯圈上的蚂蚁插翅难飞。
若进一步挖掘伊根叙事背后的交流目的,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 嵌入叙事层的个体创伤联系着更大的社会文化创伤。 古堡是一个拒绝任何现代化通信工具的世外桃源, 而丹尼却须臾离不开手机和网络。 “他心里发痒, 只想打电话——这是原始需求, 就像人有大笑、打喷嚏、吃饭的冲动一样。”[5]6在古堡中丢失了手机的丹尼仿佛被整个世界所遗忘, 他焦虑不安, 疯狂地想同外界取得联系, 获得某种情感寄托, 始终无法适应没有手机和网络的生活。 他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被现代科技所控制, 失去了主体性。 小说暗示丹尼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后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 手机和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理解与经验, 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其制约, 心为物役。 这种社会普遍症候给后现代人造成了一定的创伤体验, 而创伤并非由战争、暴力或自然灾害引起, 而是由人类迅猛发展的科技导致的。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认为: 当群体成员感到他们受到可怕事件的压制, 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抹灭的痕迹, 成为永久的记忆, 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未来的认同, 文化创伤就发生了。[6]他还指出, 社会文化创伤并非自然存在, 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这样看来, 造成社会文化创伤的事件不仅应包括战争、大屠杀、社会暴力、宗教迫害等人为导致的重大伤害, 还应包括社会发展中的具有双刃剑性质的科技进步。 科技进步推动社会发展毋庸置疑, 这是其积极的一面; 但它可怕的一面是, 随着科技进步, 技术越来越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 人被技术化, 就像《塔楼》中的丹尼一样, 过于依赖现代科技, 一旦失去机器与技术, 就会产生被抛弃感和与世隔绝般的孤独感, 很难有效地适应当下环境。
由于科技发展导致的文化创伤对社会的侵入缓慢、不易觉察, 所以其潜在威胁性巨大, 它将影响整个群体成员的根本生存经验。 全社会将陷入一种群体性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比如严重的焦虑、科技依赖症等。 群体中每一个成员都难以摆脱, 这是人类自我行为对自身造成创伤, 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创伤。 这种由于技术发展而导致的社会文化创伤, 就像小说中个体童年创伤对幼小施害者自身造成长期的影响一样, 若不给予适当处理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侵蚀人类的健康与生存, 人类难以逃离。
2 童年创伤、犯罪与监禁
童年创伤对施害者会产生某种影响, 对受害者则可能造成终身不可磨灭的伤害, “丹尼的故事”的叙事者雷就是这样一个童年创伤受害者。 框架叙事层“雷的故事”被分别安插在小说前两部分的第四、七、十和十三章, 呈等差排列。 雷对母亲的记忆“一片空白, 就像一张照片上挖去一个窟窿”; 对于父亲, 也只记得“粗壮的腿”。 显然, 雷在童年期并没有得到来自原生家庭无微不至的关怀, 他是在情感忽视(CEN)的环境下长大, 这给他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童年忽视是构成儿童创伤的主要因素之一, 被长期情感忽视看似微不足道, 但其影响却深远而无法自行消除。 心理创伤研究专家朱迪斯·赫尔曼曾强调:“在成人阶段发生持续性创伤, 会侵蚀已经定形的性格结构; 而在儿童期发生的持续性创伤, 则会扭曲尚未成形的性格。”[7]96实证研究也显示:“童年受虐待和被忽视使青少年被捕的可能性增加了50%以上, 成人期被捕的可能性增加了38%, 暴力犯罪被捕的可能性也增加了38%。”[8]小说《灯塔》中, 童年创伤导致雷在人生成长道路上的认知和行为方面出现了各种偏差: 十几岁时进入少管所, 因非法买卖坐牢五年, 四个月前刚被假释出来, 却又因杀人再次锒铛入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雷的犯罪就是对童年创伤的极端反抗。
服刑期间, 在教师霍莉的指导下, 雷陆续创作出被其射杀的对象丹尼在古堡中的惊险哥特故事。 这种小说中的小说叫元小说, 所采用的语言称元叙述语言。 元叙述语言处理大致有六种: 矛盾、排列、中断、随意、过分和短路。[9]《塔楼》的元叙述语言主要通过短路表现出来, 短路指的是文本作者时不时地介入到作品的叙事当中, 例如文本中的“我怎么才能解释丹尼看到对讲机的感觉呢”“我打算告诉你们丹尼是怎么想的”等等。 从修辞叙事角度来看, 元叙述在读者与叙事间产生了间离效果, 所以起初读者会被惹恼, 与此同时, 该元叙述也孕育出一种文本约束功能, 使读者在相似性方面将框架叙事层同嵌入叙事层联系起来, 在差异中识别同质性, 推断出作者叙事背后的交流目的, 最终做出相应的叙事判断。 伊根的元叙述是用哥特叙事的外壳掩盖了创伤叙事的内核, 形成一道特殊的修辞意义风景, 既暗示出创伤的隐蔽性和不易觉察性——丹尼因自我行为对自身造成的创伤就是雷的创伤, 也反映出伊根对社会批判的深刻性——监禁对罪犯造成的创伤难以磨灭, 不是直接明显地对后现代社会进行种种批判和揭露, 而是将内容纳入到形式当中, 这就使得对社会的批判变得更为深刻。
监狱作为国家机器, 以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方式对其施加惩罚。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一书中提出, 监狱的主要功能在于“惩罚人的灵魂”[10], 监禁就其本质来讲是残酷的, 它会给罪犯带来各种严重的心理创伤。 美国著名犯罪学者格雷沙姆·塞克斯曾论述了监禁的五大痛苦: 自由的剥夺、物质及受服务的剥夺、异性关系的剥夺、自主性的剥夺和安全感的丧失。[11]
监禁对罪犯这一特殊群体造成的创伤是持久的、难以磨灭的, 其创伤性表现最为凸显的部分就是焦虑, 焦虑是“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引发的不安, 而这种价值则被人视为其存在的根本”[12]。 监禁剥夺和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 既断绝了罪犯与外界的联结, 也限制罪犯在监狱中的活动, 极易使其产生被抛弃感与孤独感, 继而转化为对自由的焦虑; 大量的监规和一成不变的监禁生活会使罪犯感到厌烦, 产生对时间的焦虑; 监狱中的暴力环境则使他们丧失安全感, 如《塔楼》中写作课上犯人间的相互暴力攻击、餐厅内同监犯对雷的严重人身伤害等, 这些随时随地发生的暴力令罪犯紧张、恐惧, 继而产生对空间的焦虑; 与异性交往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需求, 但在监狱里, 罪犯与异性进行正常交往几乎是不可能的, 被剥夺了与异性的关系更容易让罪犯产生身份焦虑。
监禁带来的对自由、 时间、 空间和身份的创伤性焦虑不仅令人痛苦, 且难以自行消除, 所以对改造罪犯极为不利。 在雷的故事中, 雷为了减轻面对监禁生活的焦虑, 压抑监禁带来的痛苦, 先是自身产生了意识状态疏离这种防御机制, 把监禁看作是一场梦, 对现实环境产生非真实感; 接着他又借用讲述“丹尼的故事”这种元叙述修辞叙事方式, 表面上是为了吸引霍莉, 本质上却是渴望消解这种创伤性焦虑; 最终雷选择了越狱, 以期彻底摆脱创伤枷锁。 意大利犯罪学之父龙勃罗俊在《犯罪人论》中提出, 对于犯罪应当“注意加以预防, 而不是医治”[13]。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治愈创伤者的创伤是对犯罪的最佳预防。
3 创伤与复原
框架叙事层中与“雷的故事”并置的是“霍莉的故事”, 它出现在小说的最后一章, 也是小说的第三部分。 伊根在一次访谈中曾坦言: 小说中最难写的部分就是“霍莉的故事”[14]。
雷在监狱中的写作课教师霍莉也是个受过创伤的人物, 由于自身吸毒导致儿子夭折而精神崩溃。 霍莉的创伤与丹尼的创伤有相同之处: 自我行为导致自身创伤。 但与丹尼不同的是, 霍莉总在努力寻求创伤救赎之路, 她是通过其自身“讲述”的方式治愈创伤。
“心理创伤的核心经历是自身自主权的丧失和与他人感情联系的中断, 因此, 创伤复原的基础就在于重建受创者的自主权和创造新的联系。”[7]133被心理创伤夺走了的自身主导权的恢复可以使受创者重获安全感。 在“霍莉的故事”中, 人物叙事者霍莉的讲述在同步叙述与回顾性叙述中交替进行。 回顾性叙述给读者提供了充分的叙事, 显示事件的确定性, 同时也为同步叙述提供了背景, 同步叙述以此为后台而动态向前运动。 霍莉的回顾性叙述交待了她的创伤源: 儿子夭折, 而这全是拜自己吸毒所赐。 霍莉的叙述丝毫不混乱、思路清晰, 并有一些判断性语言。 “我告诉我母亲: ‘医生说我必须原谅自己, 否则我没法继续生活, 所以, 我正努力尝试那样做。’”[5] 233霍莉意识到自己是唯一需要对创伤事件负责的人, 摆脱毒瘾以及随后攻读硕士均表明她已经恢复自身主导权, 对自己的身体、情感和思想可以进行掌控。
处理创伤之后, 受创者面对的任务是开创未来, 必须了解创伤在其生命中的意义, 努力重建新的联系, 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 霍莉的同步叙述就呈现了她如何与正常生活再度联系, 不再受到过去创伤的牵制, 积极拥抱人生, 转变自我。 在家庭方面, 她摆脱了瘾君子丈夫并努力发展与孩子们的关系, “我的工作, 我唯一的工作就是保护这两个女孩子的安全和健康, 这样她们的生命才有意义”[5] 232; 在感情方面, 则是努力寻找真爱, 她要寻找雷笔下的古堡、寻找雷。 “我用谷歌搜索‘旅馆、古堡、欧洲’……搜索时, 我注意到一个叫‘塔楼’的旅馆, 图片上显示是一个带有塔楼的古堡……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古堡、长长的方塔、 显示迷宫般地下隧道的旧地图、巨大的圆形游泳池……这就是霍华德的古堡——雷的古堡, 相同的地方, 我放声大笑, 虽然笑声虚弱, 但却舒心。”[5] 244
通过述说的方式释放创伤记忆, 将创伤记忆转化为叙事记忆, 是治愈创伤的有效手段。 “治疗创伤是一个发声过程, 一个人治愈了创伤, 他就能分辨过去与现在, 能记起那时候的自己(或其亲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并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生活于此时此地, 享有美好的未来。”[15]
“塔楼”是小说中最为突出的意象, 一个固定的指涉, 是揭示创伤本质的核心隐喻, 它既提供了小说的标题, 也渗透到了故事当中, 使得三个故事之间的对应得以建立。 作为“古堡内最后的防卫、核心地带”[16]的塔楼象征着人潜意识中的创伤记忆。 在“丹尼的故事”中, 丹尼意欲逃离塔楼意味着他想要摆脱创伤记忆; 在“雷的故事”中, 塔楼幻化为监狱, 雷也想寻找逃离途径, 文学创作及其越狱均表征了他渴望从监狱的束缚中解放, 完全摆脱创伤记忆。 但对于这两个人物而言, 创伤记忆是以一种内在化的方式影响着他们, 对他们起着潜在的作用, 在没有充分认识到创伤的实质前, 没有有效地将创伤在意识中整合、认知和重构前, 即便加以反抗也徒劳无益, 创伤记忆的监狱是永远无法越狱的; 在“霍莉的故事”中, 霍莉走进塔楼, 寻找真爱, 创伤记忆的大门向她敞开, 预示着只有认识创伤、释放创伤记忆, 才有可能治愈创伤, 小说开放式的结尾也暗示了创伤的可治愈性。
4 结 语
通过以上梳理与呈现, 作者伊根的种种修辞叙事策略成功地完成了对创伤主题的表述, 刻画出深受创伤影响的创伤群体像, 虽使文本复杂化, 却增加了读者解码的乐趣, 同时也隐晦地表达了作者对后现代社会问题深刻的批判与敏锐的思考, 向读者传达着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 体现出独特的审美旨趣。 诚然, 人类在成长的过程中, 往往会因自我行为而对自身造成创伤, 但是倘若能充分认识到这种创伤, 反思创伤, 那么人类完全可以实现自我救赎, 从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1]Anne Whitehead. Trauma fiction[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2]Vince Passaro[EB/OL]. 2016-03-11[2016-04-24]. http:∥jenniferegan.com/reviews/the-keep.
[3]Sandra L Bloom. Creating sanctuary: toward the evolution of sane societie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4]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Baltimore: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5]Jennifer Egan. The keep[M].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6.
[6]Jeffrey C. Alexander, 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Jeffrey C[C]. Alexander (ed).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4.
[7]Judith Herman. Trauma and recovery[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5.
[8][美]巴特尔. 犯罪心理学[M]. 杨波, 李林, 等译.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3.
[9]胡全生. 英美后现代小说叙述结构研究[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10][法]福柯. 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 [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11]Gresham M. Sykes, The society of captives: a study of a maximum security prison[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12][美]罗洛·梅. 焦虑的意义. [M]. 朱侃茹,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3][意] 切萨特·龙勃罗俊. 犯罪人论. [M]. 黄凤, 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14]Joshua Lukin. Part of Us that Can’t Be Touched. [EB/OL]. 2016-03-11[2016-04-24]. http:∥www.guernicamag.com/interviews/egan_7_1_10/
[15] La Capra Dominick.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Vendelon Vida. Jennifer egan[J]. The Believer, 2006(8): 80-82.
Whose Trauma is Talking——The Traumatic Narrative ofTheKeep
LI Ruopi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1, China)
This paper takes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 Jennifer Egan’s bestselling novel,TheKeep, as an example, drawing on traumatology and rhetorical narratology to analyze the author’s purpose behind her traumatic narrative and the audiences’ judgment on it,and finally proposes that the narrative center ofTheKeepis trauma:children trauma, social cultural trauma and the recovery of trauma.
Jennifer Egan;TheKeep; trauma; rhetorical narrative
1673-1646(2016)06-0088-04
2016-05-27
山西医科大学科技创新基金项目: 伊根的小说修辞叙事视阈下的精神创伤主题研究(01201326)
李若平(1972-), 女, 讲师, 硕士, 从事专业: 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
I712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6.06.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