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友记
周洁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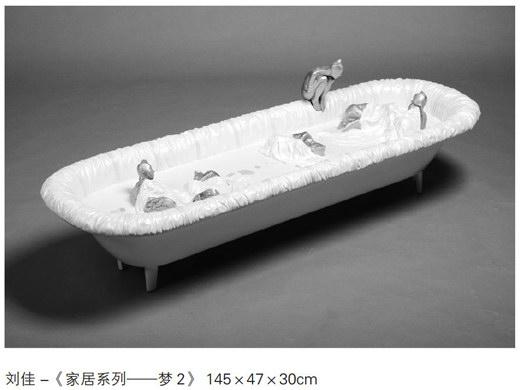
蜜 蜜
月亮是什么味道的?
甜甜的好多眼泪。
搬到香港以后,我还是没有写作。
我有时候找找我十多年前认识的陶然老师,饮个茶,讲讲十多年前的话。
香港,我也只认得他了。
第三年,我终于去了一下香港作联的春节联欢晚会,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开朗爱笑的女士,那个晚上有很多人,很多人跟我说话,可是我一句都不记得了,我也谁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她带我绕过了六张别人的桌子,找到了另一桌的周蜜蜜。我请周蜜蜜为我签了一个名,签在她的名片上。我好像还说了我喜欢你。那个嘈杂混乱其实有点糟糕的夜晚,我说我喜欢你。
不要笑,实际上我从来不问任何人要签名,有很多人来香港,莫言王蒙白先勇,我陪我的女朋友们去看他们,她们买了好多好多书她们围绕着他们,我远远地笑,为她们拍合照,我不问任何谁要签名,即使有一次最帅的余华来了,可是我没有他的书也没有一支笔,我说老师可不可以签在我的手背上,他都要笑得昏过去了。所以,我还是没有任何谁的签名。
我有周蜜蜜的签名,我就是喜欢她。她从她的那一桌站起来,转过身看着我,我都要哭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温柔又和气的表情,好像月亮一样。有人在微博上问月亮是什么味道的?我说甜甜的好多眼泪。
后来我很喜欢拍她,每次见她都拍好多她,她总是说她不漂亮,叫我不要拍,可是我眼里的她,真的好漂亮。
我也不是经常见她,我也不经常见陶然,香港这么小,我们都见不到。
开朗又爱笑的女士是当时《香港作家》的副主编周萱,她辞职前向香港作联推荐了我。于是2012年到2013年,我做了一年《香港作家》的副总编辑,总编辑是周蜜蜜。
那一年,我过了最多次的海,去了最多次的港岛。之前的三年,我最远只去到九龙塘,我住在有全香港最美日落海滩的乌溪沙,我不看夕阳也不爱人,我还是一个字都没有写。
《香港作家》是双月刊,于是我每隔两个月去一下北角看大样,从《香港文学》的编辑潘生那里拿了样稿,坐在潘生的椅子上面校对。陶然也在那儿,如果他在,我会坐到他的对面,说一会儿话,我看不到陶然的脸,因为他桌上的书太多,把他都遮住了。很多时候他不在,潘生也不在,我在前台拿了样,坐到楼下的日本馆子,点一份早餐,开始校样,早餐牌换成了午餐牌,大家还没有开始在餐馆前面排队,我就离开了那间日本馆子。我把样稿带回家,第二天早晨再把看好的大样送回北角。
出刊的那些天,我和周蜜蜜用电子邮件联络,每天早晨,五六点钟,每一期《香港作家》,都会是几百封电子邮件。一个太勤奋的每天早起的主编,和一个不读书也不写作,只是每天不睡觉的副主编,来来往往的电子邮件。
有的文章我很不喜欢,非常不喜欢,我甚至被那些文章气哭了。我跟她说我真的哭了,我说再叫我看那样的字我就只好死了,我讲了好多遍好多遍,她说哎。她只能说哎,她只能做我的甜甜的好多眼泪的月亮。
作联在柴湾,印厂在荃湾,2013年尾《香港作家》出纪念特刊的时候我才去过一次,我只是不高兴,很不高兴。
坐在荔枝角公园的长椅上,我们的面前是跳来跳去的小孩。她说她想请辞《香港作家》,事情太多,总也忙不过来。我说我也辞了。她说不要啊,你要继续下去。你也一直不写字,真是太可惜了,她说。好多小孩跑来跑去,阳光碎成一块一块。我拼命仰着头,眼泪才不会流下来。
后来每一次见她,告别的时候,她总会说,你要写呀。
我知道她一直在写,写作这么艰辛的事情,她一直在写。而且是给孩子们写。?
所有为孩子们写作的作家都太伟大了。
我以前写作的时候,写过一些小时候的故事,我小时候的故事,那些故事也发表在《少年文艺》或者《儿童文学》,我甚至写过一个大人童话《中国娃娃》,是我最后出版的一本书,也是十四年之前了。我自己知道,都不是给孩子们看的故事,我小时候的故事,就是我小时候的故事。
只有心里面装了很多很多爱的人,才写得出来给孩子们看的故事。
我不喜欢小孩,所有的小孩。所以我写不出来。
所以我喜欢为孩子们写作的她。
她也真的一直像个孩子一样,有甜蜜又柔软的心,对谁都很好。
有一次送什么书过去给她,约在她家附近的一家茶楼。已经是第五年,我还是不会一句广东话我还是不会吃广东点心,我仍然搞不清楚香片和水仙有什么差别。她问我爱吃什么,我答不上来。她站起来端来一碟点心,又站起来端来另一碟点心,她说试试这个,也试试那个,都很好吃的。
她也总送我漂亮的东西,发夹,挂坠,闪闪发光的,她说女孩都喜欢亮晶晶的小东西。我已经中年,却是她眼里永远的年轻人。
《香港文学》三十年的会上,看到她和北岛站在一起,拍了一张他们的合影,晚上调了色发给她,她说了很多感谢,很多开心。其实那个晚上,我最开心,我们一起蹭了北岛的车过海回家,他们说的全是神奇又传奇的人和事情。我一直在发抖,北岛是我的男神,坐在男神的旁边,当然会发抖。我不知道她的男神是谁,她一定没有她的男神。她已经是所有人的女神了。
最近一次见面,是她年幼时候的好友回国,搬来我家对面的屋苑,她们一堆童年朋友聚会。她从她们的小派对里溜出来了一小会儿找我,那个屋苑和我家屋苑的中间,是一个天桥。她穿了裙子,总是裙子,有花朵的平底鞋,美得惊人。她走过那条天桥,停住的瞬间,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看她。就是那么美丽。
后来送她回去,她的朋友们走出来接她,优雅的女士们,珍珠项链和流苏的长围巾,看着她很开心地走入她们中间。她没有忘记回头跟我说,你要写,不要再浪费你自己。
她的生活,她的朋友们,就应该是那样,很美好。一切都太好了。
第二天我们美国的朋友陈谦过来香港,她又过来了一下,我们坐在钢琴室里聊天,断断续续的钢琴的声音,我拍了她们的腿,还有鞋子。
已经是第六年,我在香港的第六年,我终于开始写点字。碎的,小小的字。
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打动我,永远都不会忘掉。我长大以后的故事,都不再好玩也不再打动我了。写给孩子们的故事,就是这么重要。
住在山里的老奶奶听到了轻轻的敲门声。哎,门缝里伸进来一双冰冰凉的小手,两片小树叶,一个怯怯的声音,请卖给我合适的手套吧。老奶奶给冰冰凉的小手戴上了小小的毛线手套。哎,是小狐狸的手呀,老奶奶在心里面想,真的好冷呢,山里面的小狐狸都来买手套了呢。
陶 然
刚刚到香港的时候,我只有陶然。
我打电话给他,约他饮茶。北角的茶楼,我还不知道香港人都是要先用滚水洗碗洗杯的。我说一定要洗的吗?他说一定,这些碗碟都不是你看到的那么干净的。
有两位老师的话我总是特别用心地听的,一是《山花》的何锐老师,尽管很多时候我加了倍地用了心听,我也没有听懂,还有就是陶然老师了,陶然老师的普通话绝对不是香港的腔调的,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印尼华侨,但是可以这么说,在我还没有认识周蜜蜜老师和蔡溢怀老师之前,陶然老师的普通话,一定是所有的香港老师中间最好的了。
刚刚到香港的时候,我还会把菜放进碟子里,我还会问服务生要一杯冰水,我会一直等待幸运饼干,我常常有错觉,以为我还在美国。
我在美国的十年,好像也只与香港有点联系。我离开的最后一个小说,《香港文学》发了,我回来的第一个小说,也是《香港文学》发了。我到底还有《香港文学》。
《香港文学》三十年的会,我带了一台相机去拍他,他在那个晚上特别帅。我也喜欢那样的会,全都是很酷的写字的人。尽管我们没有三十年,我与他只有十七年,其中十年又是见不到的,我在美国,一个字都没有写。
可是我想得起来和他的第一面,《厦门文学》的会,在厦门。我去那个会好像是因为我在他们那儿发了小说《朝西边走去》,十七八年前的事情,如果是今天,题目肯定会被改成《西边》吧?我不知道。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好像还有朱文和舒婷,我都忘记了,可是我和陶然就这么认识了,还有还有,鼓浪屿的青菜真的很好吃。
隔了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忘记我在厦门听过的那个故事,相爱却错过的男女,约定一年只见一面,已经十年,直到这一个第十年,女人突然半夜发烧,同屋出去找药,门外碰见男人,话还没有讲完,男人就在走廊里奔跑起来,四十岁的中年男子,竟然慌张到跌了一跤,同屋望着他冲出去买了药,又冲回来,同屋说要出去走一走,出门回头的最后一眼,看见女人的额头上白色的湿毛巾,男人的手心细长的血迹,是跌倒时的擦伤,他顾不得,他的眼睛只望住她。第二天傍晚,同屋要搭长途车去广州,男人送她去车站,等车的时候,男人给二十岁的小年轻同屋买了一支冰淇淋,然后讲了这一个故事,相见就已经错过,一年只见一次,这个会或者那个会的机会,只愿一面,就满心欢喜。同屋听完了故事,吃完了冰淇淋,上了要过夜的长途汽车,同屋是去广州跟男朋友分手的,一年异地恋,到了尽头。
我给陶然讲了那个厦门故事,他说是吗?实际上只要见到他,我就会给他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很多是真的,也有很多是假的,他只是听着,完全都不笑的。实际上我们总也见不到,我们只是通邮件,我用电子邮件祝他生日快乐。
很多人觉得我不看书,新书都不用送给我,陶然总会送给我,签上最工整的名字,我有他十七年前的书,也有他今年的书,在他那里,这就是一件互相敬重的事情,尽管世界都变了,很多人写谄媚的字,很多人混来混去,他都当看不到,他写他自己的字,写作到了他那里,重新变回一件干净的事。
我请辞《香港作家》的时候给每个人发了邮件,《香港文学》的编辑潘生还会回给我一句,哎,你又怎么啦?我没有等到陶然的回复,他一句话都没有。我给他讲好笑的故事,他不说话,我告诉他有的文章太坏了,我看了想死,他也不说话,我说我要和谁打一架,我不一定输的,我现在很凶,他都不说话,他也不笑,他皱着眉,略带生气地看着我。
他也不像蜜蜜老师那样叮嘱我不要丢了写作,很多时候我们坐在一起饮茶,就是一句话都没有。他一定是这么想的,我是怎么样都会回来写的,早一天,或者晚一天,无论他说话还是不说话。
很多事情当然会被忘记,事情太多,记忆也在变化,可是我会一直记得那个城大的会,我赶到了会场,灯都没有空调也没有的会场,他坐在那里,一个人,我走过去,坐在他的旁边,暗淡的房间,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会。
当然后来我们还是找到了对的被临时更换的会场,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个会那个会呢?各种各样奇怪的会。我只是会想起来,我们曾经一起坐过一个一个人都没有的会场,好像全香港只有我在他的旁边,凝固了的时间。但是我就是这么觉得,那真是太棒了。
赳 赳
我忘了是我先去北京还是胡赳赳先来香港了,好多年前的事情,我又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但是香港的那次我是记得太清楚了。冰逸在唐人的个展,胡赳赳说有北岛,我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去上环,北岛还是我的男神。
我穿着牛仔裤和球鞋,找荷里活道找了一个钟头,走进唐人的那个瞬间,我还很茫,所有的人都太懂艺术了,除了我,我站在一个记录片作品前面,看了十分钟完全不动的长江水,直到胡赳赳找到我。
胡赳赳好像给我解释了冰逸的每一个作品,诗人和一半花朵一半精灵的爱人,如今我只记得冯唐的喜怒哀伤,还有摆在船头的摄像机,滔滔江水,从重庆到南京。
冰逸之前,我们在深圳还见过,或者冰逸之后,那是我十年来第一次见人,而且是见一个比我还小的人。我们好像说了很多话,其实那是我状态最差的一年,我从没有那么茫然过,我在生活和写作中间晃荡,找不到平衡的点。那些话我也都忘了,但是我记得那间空空荡荡的寿司店,胡赳赳选择的角落里的背后要有墙的座位。
然后我就去北京了,或者胡赳赳又来了一下深圳。我们肯定一起去了谁的家,去的路上我肯定质问了他有没有去过东莞,那个谁肯定喝大了,可是喝大了他也肯定没有弄丢他的包包,还有还有,日料店的屏风肯定倒了下来,砸到了谁的头。深圳的大房子,胡赳赳去了厨房,找到了最好的那支红酒,每个人都喝到了好酒。回去的路上,月亮太圆了,我反复地反复地问他,我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才好呢?他说没事的没事的,回家吧。
然后我就去了一下北京。2008年,只有胡赳赳和兴安和我说话,兴安说的,控制叙述,你太挥霍了。胡赳赳说的,你需要对美好的坚定的信念。
他带我去了798,可是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在他录一个访问的时候,我溜了出去,外面是水泥地,很多树,摇曳多姿的树叶,我看树叶看到他的访问做完,再带我离开那儿。
第二天我又去了798,我买了一张肯尼亚小孩画的树给张小跳做生日礼物。只有一棵树的儿童画,树干是棕色的,树叶是绿色的,很多树干,很少树叶。木林森计划,所有卖画的钱都用来恢复肯尼亚的森林,徐冰说了很多话,我只记得这一句,画的树变成了真的树,小孩们就会意识到,创作就能为社会做点什么。
一直以来,所有的画展我都是不去的,所有的画我也都是看不懂的。我初中时候的美术代课老师说的,同学,你画的全是平的。我问我的同桌他是什么意思?同桌说老师的意思是你是个完全不会透视的小孩,你看到的一切是平的,你画的一切就是平的。我说我怎么会透视呢?我是X光机吗?
我的同桌后来专业绘画,甚至倾尽所有去中央美院学习,在成为一个很美好的家庭主妇之后,绘画成为了她更为美好的爱好。上个星期因为我决意回来写作,她与我断绝了关系。她说做回一个上窜下跳的你真是太可悲了。
然后我的一个还留在加州的女朋友给我看了她的老师Marc Trujillo的一幅画,Costco的一个转角。这个女朋友是生物化学学士数学硕士,又决意回去学艺术。她说她生出来的那一天就知道自己是要学艺术的。我就哭了。我当然也是生出来的那一天就知道自己是要写作的。可是我哭不是因为这些那些出生时候的理想,我只是为了那一个转角。
我几乎忘记了的美国的瞬间,厌烦,疲惫的周末,巨大的手推车,无边无际的食物和未来,不快乐的过去了的但是永远不会遗忘的时光。
六月,我为了我的随笔书《请把我留在这时光里》去北京。真的是隔了七年,七年才去一次的北京,这一次是云南菜和干锅,还有巫昂,让我想起来七年前的烤鱼和张小跳。我们肯定一起去了一个地方,窗口肯定可以看到最亮的桥,再也没有人喝大,忘掉自己的包包,我肯定拍了好多张阿丁的画,巫昂的画,竖着的,横着的,胡赳赳肯定给潘采夫煮了一包方便面,还有酒,每个人也都喝到了好酒。回去的路上,月亮还是很圆,兆龙饭店老到再也不会让我害怕了。
我睁着眼睛等天亮,天还没有亮我就去了机场,集市一样的机场,没有空气也没有网,我想的全是我再也不去北京了再也不去了。飞机快要到香港,窗外是海面与岛屿,我头一回觉得香港才是我的家,这种感觉太吓人了太没有办法了。
唐 棣
我也忘了我是怎么认识唐棣的。
所以廖老师问我的时候,我眼睛望着天想了一会儿。廖老师说网上认识的吧?后来他俩坐在一块儿的时候,我就突然问廖老师,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廖老师眼睛望着天在想,我就说,网上认识的吧。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太好玩了。
我只记得我认得唐棣的时候,他是一个写小说的。如果不是写小说的,我为什么要认得他呢。我认得所有写小说的。后来才知道他拍短片,不过我一个都没有看过。
我们用短信聊天,我是说那种,按住说话,跟对讲机一样。
他的声音总是少年的,急促的,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喘不过气的那种。
说的话也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无边无际的,跳来跳去的。我一度怀疑过他和我一样,有专注力失衡的问题,也就是注意力缺失障碍,就是多动症。我真的很讨厌这些装模作样的词语,就好像我有一个朋友,明明就是爱缺失,他们管他叫做示爱言语障碍症。
后来我发现他写长篇小说,一个能够写长篇小说的人就不会是多动症,他应该拥有全世界最专注的专注力。
就让我一个人留在我的多动症好了。我一直偏好于写超短篇的小说,我也很擅长极短的叙述方式,我没有回避我在长篇小说上的无能和无力。诚实地说,写长篇会杀了我。
唐棣是一个思维跳跃又写长篇的年轻人。
我就是很喜欢和跳来跳去想事情的人说话,就好像跟我自己说话一样。要找到跟你一个节奏的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写到这儿,我发给唐棣看了一下。我说你要是不高兴我就不写了。
他说他高兴。
好吧。我第一眼看到他,他就是很高兴的样子。他带着他的电影《满洲里来的人》过来香港参加电影节,我真是太吃惊了。一切都太突然了。他的狮子一样的热情和专心足够他把他的事情都做得太快太好了。
我去太空馆看了他的《满洲里来的人》。
实际上我从来不去香港电影节,任何电影展,任何艺术展,任何书展,任何书店,大众书局,商务印书馆,旺角的二楼店,即使我已经站在铜锣湾的苹果店,我都不会往上一层,去到诚品。
已经是我住在香港的第七年,我跟香港以及文学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到太空馆,最靠边的位置,前面是一对学生情侣。
整场电影的节奏,就是我们说话的节奏,奇怪的,停不下来。
除了,血的颜色太蕃茄,我都要吐了。
我只问了旁边的廖老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划成三级。男主角出场了三分钟以后,廖老师说你看,就这三分钟,已经三级了。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廖老师你睡着了没有。因为我前面的姑娘睡着了,她还把头枕到她男朋友的肩膀上。我只好把头拧到另一边的最边上,我都快要落枕了。姑娘醒了以后,她的男朋友给她盖了一件衣服。是的是的,整场戏,我都在观察我前面的姑娘,还有坐我左边的老师,睡着了没有。
我脑子里想的是,温暖的尸体到底是不是尸体呢。
如果导演唐棣能够听得到我这样的观众脑子里想的,他会不会疯掉。他又不能选择他的观众。可是这样的全场爆满,要是我,就顾不得观众们在想什么了,大家都来看我的戏,我很高兴。还有掌声和有趣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提前走掉。一切都太好了。
等待下一个访问的间隙,我们在太空馆的外面站了一会儿,还有男主角。他还挺帅的。
电影节的工作人员安排他在这个间隙再接受另一个访问。唐棣站到了五米外,半岛酒店做背景,别人的摄影机对着他,他的很大的包放在他的脚下。我看了一眼他和他的包,他都没有带过来一个助理替他拎着他的包。可是他的腿那么长,摄影机应该也拍不到他脚旁边的包。这么想着,我就远远地,给他和他的包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我把脸转回来,对男主角说,你快被他折磨死了吧。
男主角穿了一件闪亮亮的皮外套,银的长项链,他小心地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唐棣,说,还好。
然后我们一起走去艺术中心的星巴克喝了一杯咖啡。我给唐棣和廖老师照了一张合影,温和的光,从我的角度看过去,他们的脸都很温和。他们也都是很温和的好人。
可是,他们的作品那么狠。血淋淋的。
我也曾经那么狠过,如果有人侮辱我的语言。我旁边的男主角,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有一个小时候的朋友,就是那个说我拆解生活,用情绪支撑小说以至于人物都没有面目的朋友,那个说我内心荒凉,自己连微信头像都没有的家伙。
那一个晚上他突然发了一条朋友圈。回家的路上有风吹过,“这是满洲里来的风啊。”其实,我没有去过满洲里,也不知道风来自哪里,我只是突然觉得,这时候有满洲里的风真好。
苏
过去的十年,我只写了两篇书评,一篇是李修文的长篇小说《滴泪痣》,一篇是台湾作家谬西的《裸身十诫》。准确地说,我为谬西写的那些字并不能算是书评。2000年,那个年代的书还不需要在封底印推荐人语,腰封上也没有当红名家的名字。
我读了谬西并且写了字是因为鲜网的苏,她是我在加州的第一个朋友。我仍然记得那个中午,少见的阴天的中午,我们约在柏拉阿图的一间日本馆子。苏的国语没有什么台湾腔,她甚至也没有说多少关于鲜的话。我仍然记得我吃的是加州卷,苏要了素菜天妇罗,因为苏吃素。
那一段时间,我与所有的朋友都断了联系,所有的出版社和编辑,我偶尔写电子邮件给《雨花》的姜琍敏,他是发我第一个小说专辑的编辑。我写的零碎的字句,有时候寄给他,后来我完全不写了,与他也不再联系。我只留存了我在鲜网的会客室,我的隔壁是纪大伟。
2000年,鲜网在中国大陆的推广刚刚开始,我们的客厅都很冷清。再后来,我连我自己的网页也不去了。
苏找我写谬西,大概是因为她负责谬西那本书的推广,而我正好住在附近,她可以与我谈一谈。可是我连谬西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我也没有读过他或者她的文章。我坚持地认为,要我写谁的书评,我必须先认识他,而且必须是认识了很久,就像我来写李修文一样。
所以我接下了谬西的书,但是极为勉强。我也想过我已经不再在中国了,我需要一个不一样的开始。
苏离开的时候,我看见她开一台巨大的车,苏很瘦,衬得那台车特别大。
我很快地读完了《裸身十诫》,谬西的语言方式是我陌生的,他其实写得很小心,通篇的绝望。我不知道我要怎么为他写书评,之前我写过一些读书的字,一句两句,因为有时候我也用那些别人的书检查我自己。我不是评论家,我并不需要分析他写作时的状态,找出他结构上的问题。我对他也没有什么感情。所以我像往常那样,写了一句,两句,我在那个瞬间的感受。写得太多,就会有差错。
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男人和各种各样的女人。身体里面扎着一根玫瑰刺的男人,从完美圈套里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存在过的男人,有爱却怀疑爱的女人,爱着热的他又爱着冷的他的女人,没有心的女人,偷盗名份的女人。我看不清楚他们的纠缠,可是他们真实地存在着,就像谬西自己说的,他可以冷眼看这个真实的世界,记录下来。像他那样平静又冷淡,他的故事却碰伤了你的心。
因为字太少,看起来的确像敷衍,我一直觉得对不起苏。苏倒一直安慰我,说挺好。苏后来大概回台湾了,或者转了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那个阴天的中午,我们坐在一张长椅上,我们大概说了一些话,鲜网之外的话,加州的天空,结婚还有爱情,我记不大真切了。我只记得苏说,我来拍一张你的侧面吧。她从她的很大的包里掏出了一个相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修 文
也许所有读过《滴泪痣》的人都会认为,这个男人是很爱这个女人的,如果她死了,他就活不下去了。可是他还活着,而且幸福了。这令我困惑,因为世界实在是没有什么可留连的,我形容过它冷酷,可是这对年轻男女的世界,它对他们,实在是太残忍了。他们生来被诅咒,死亡都不能平息他们与这个世界的互相仇恨,也许还不是恨,什么都与他们无关了,他们被遗弃了,连神都遗弃他们。女人所做的一切,聋了哑了,逃了死了,也许更多,不过是使这个男人和这个世界有了关系。女人的爱使男人和世界有了关系。
书里的女人经常说这三个字,我不配。很多女人说这三个字,有时候我也说一说。可是我只觉得,是他不配。也许他的确为她做了很多,可是实际上他什么都没干,他什么都干不了。他沉醉在爱里,脸上露出白痴的笑容。
其实,有什么配不配的呢,男人和女人,如果他们相爱,他们变成了一个人,没有什么配不配的了。不要再出现这个字了。我们都知道,他爱她,她更爱他,再也不会有一个女人会像她那么爱他了。
写到这里,我想我应该叙述一下《滴泪痣》这个故事,一个男人来到日本,爱上有泪痣的应召女郎,他们相爱又互相折磨,后来她死了。他问,上天还会让我们在来生里再见面吗?
也许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他的希望,虽然这个希望并不可行,实现不了。男人们总用这样那样的念头安慰自己。即使女人死时凄惨,她一定不相信还有来生,还有前世,他却说,也许上天会让我们在来生里再见面。就那么一点希望。
爱情的真相就是这样,我一直都喜欢这样的故事,在困境中挣扎的男女,贫贱的生活。所以这个故事必须发生在日本,故事的主角必须是很年轻的男女,故事里必须出现温泉和樱花,还有死亡。
我想李修文写《滴泪痣》只是要告诉我们希望,微薄的爱的希望。当然还有青春,眼泪和血浸透了的青春。
尽管我更喜欢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杏奈去了印度,爱上会写诗的恐怖分子,深情又英俊的恐怖分子,他被杀了。阿不都西提是一个好看的处男,后来他死了,他只在电话里和女人做过爱,他有一匹马。筱常月用昆曲演唱蝴蝶夫人,她也死了。他们每一个都比主角有意思,他们都死了。
我最喜欢这一段。十二点过了以后,我去客厅里叫她进房睡觉,她在看我看过的那张报纸,听见我叫她。“说错了这位客官,”她一边将烟头扔进烟灰缸用力掐灭,一边说:“你应该这样说,你这个婊子还不滚过来睡觉。”
我知道多数人都会认为这些没什么特别的,就像李修文以前的那些小说,《心都碎了》那种。我不说什么了,都是我喜欢的句子。
我也不在乎别人会为他写什么,或者别人眼里的他会是什么样的。反正他在我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朋友,不过他是那样的,谁都是他的朋友,一样的朋友。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没有负担。
我在二十岁的时候认识李修文,他那时是《作家》的编辑,比我大一岁。
那是一个炎热夏天的下午,热到我什么都不想写。我父母在客厅看电视,我讨厌把时间浪费在电视上,我在自己的房间看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好看极了,我忘记了夏天有多热。就在那个下午,我接到了李修文的第一个电话,关于我在《作家》的第一篇小说《吹灯做伴》。他的声音很好听,而且有礼貌。接完了电话,我就坐到客厅,陪我父母看了一下午的电视。
后来我们又通过一些电话,我主要是告诉他我因为年龄被轻视,我只告诉他是因为他比我大一岁,那时候我身边的人都比我大十岁,我不和大人们说话,他们都很奇怪。
他一般是说哦,然后等待我平静下来。所以我们的通话经常是两个人的沉默,我把话说完了就不说什么了,他抽着烟,一根又一根。直到现在,我都很感激他在我年轻的时候沉默的陪伴。
我后来制造了很多是非,我的名字里有太多口了,他们把我说来说去。没有人能够做点什么,也没有人愿意站在我的旁边。
我和他已经不大说话了,我不再说话,和所有的人都不说话。我离开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给他。
我把桌子都掀翻啦,他说。我就笑了。即使那不是真的,他听不下去了,为我掀了一次桌子,他是唯一那个还站在我旁边的人,即使那不是真的。
我们从没有见过面,我不知道他的长相,有人说他长得很高。那么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高个子。
宝 光
宝光出新书,很为他高兴。上一本他的书,还是二三十年前,他的头发还很长,牙齿都还在,书名里还有玫瑰和歌。
这个人,要我来写,该是一部长篇小说。我写长篇始终不怎么行,所以,一直没有写。
而且要我来写他,等于也是写我自己。我一直不怎么想写我自己,一是岁数还不够,说起想当年总有点虚,二是要我想一想我的过去,还真是蛮痛苦的,这条写作的路实在艰难,人人都是一本苦难史。有人说我好命,撞到好时代,我百口莫辩。所以,冷暖自知吧。
我2000年去了美国以后,再也没有写过什么字,算起来,已有十三年。十三年去国离乡,十三年不读不写,今天我还能够说说话,我对我自己还是满意的。
也许以后我会越说越通顺了,也许我说完宝光的这些话以后我就又不说了,谁知道以后的事情呢。
我决定先来说一说跟他的头一回见面,从短篇开始,落下第一个字,要不然,一个字都没有了。
我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写诗,1991年,我的旁边一个人都没有,我也看不到我的未来,于是高一暑假的时候我找到一份《翠苑》杂志社的暑假工。
坦白地说,我最想找的是常州日报的暑假工,我十六岁的时候是这么想的,报社就是一个理想国,里面的人全是王。暑假的第一天,我踩脚踏车去了大庙弄,门口的门卫连门都没有让我进去。我站在报社对门观望了好久,成年人进进出出,我看了一个上午。
到了下午,我就踩着脚踏车去了西新桥。《翠苑》杂志社在三楼,我在二楼半停了一下,残破的水泥楼梯,我慢慢地上了楼,一个门旁钉了编辑部字样金属板的房间,门关着,一个人都没有。
我下楼梯的时候遇到两个人,一个板寸,一个头发比我还长。板寸冷冷地打量我,长发说,你找谁。或者长发冷冷地打量我,板寸说,你找谁。
我觉得这两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是宝光,另外一个,可能是村人,也可能是沙漠子。都是往事了,记忆难免出错。
我倒是清楚地记得《翠苑》的老师跟我讲,不要同流氓混,毁了你自己。
《翠苑》的老师好多位,我不说这是哪一位了,他或者她确实为我好,年轻小姑娘,混沌,不当心就行错步路。你们也不要乱猜,伤感情。
我倒是偏要同他们混。
其实我自己是不能混的,家教严,吃过晚饭连家门都不能出,我还要上学。
所以我跟宝光,到底只吃过两次饭,一次在公园路的路边摊,还有周啸虎,一次是金锋家,好像还在清潭。我对金锋多少还有点怨气是因为他当面批评我的小说,后来我无数次地在我的小说中写他的老婆戴着圆框眼镜,胖胖地走来走去,作为回报。
我对周啸虎也有怨气是因为他喝了酒,把我当拐杖。我又不认识他。我只好同宝光抱怨,宝光笑着说周啸虎是好人,叫我放心。他的酒杯都没有放下来。
所以你也看得出来,宝光那个样子,在他那里,人人都是好人。
还有董文胜,我是另外认得他的,另外的故事,不长,短篇,我空了再来写。
我后来一直没再见到村人,直到有一年冬天回常州,中吴网拿一个博客热情奖,我同他聊了非常简短的五分钟,那时他已患癌病,气色倒还好。我离开常州以后,很快就听到他去世了的消息。他的风波,他的故事,我是离了很远的人,所以尽管我很早就认识了他,可是我一个字都是写不出来的。
我后来又去了一趟杂志社,他们都在搬家,搬到西新桥的那一边。有一位老师请示了当时的领导石花雨,领导爽快地说好。老师说我们纯文学,钱不多,我说我不要钱,我来社会实践的。暑假结束,领导还是发给我两百元工资,领导说实在不好意思。我当时也有一些稿费,我也终于发表了我在常州日报的第一个作品,是我摄影课的功课,拍的红梅公园的灯展,编辑是刘克林。我时常把他同电视台的另一位编辑搞混,他们的脸简直一模一样。
1992年,两百块,这个数额还是很高的,又是我的劳动所得,我很感激。
这一本《翠苑》杂志,要我来写,是另外一个长篇小说,我不写,因为老师们实际上待我不错,我对老师们也都还有感情。
这些老师,每一个散开来写,都是独立的中篇小说,但是他们肯定是不希望我写,小说基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有的时候,也败坏生活。
一个高中女生能干的事情有限,我被分配做清洁,打水,有时候也要卖杂志。我只卖出去三本《翠苑》杂志,我爸一本,我妈一本,我一本。
第二年暑假我还是回杂志社做暑假工,熟门熟路了。老师说升我职,助理编辑。我被派去采访客车厂,厂长没看出来我高二,还请我吃了工作餐。新闻稿写得我想死,但我觉得是锻炼。我后来在宣传部写报告,也是锻炼。
后来杂志社来了几个阿姨,拼命欺负我,我本来以为广告部的老师老是半夜三更带姑娘来杂志社,大清早我打完热水还得处理沙发上的斑点已经是我最烦恼的事情,可是这些阿姨一来,还有几个骑鲨鱼摩托车的有钱人,他们成为了新的烦恼。
我还是回忆得起来杂志社里夏日的好时光,老师们一高兴起来就喊,吃火锅啦。大家坐到万福桥的重庆小饭店,麻辣火锅好吃死了,阿姨也不欺负我了,因为我不吃猪脑,不同她抢。
那些坏的好的日子,宝光一次也没有来过。沙漠子有时候来,日报的李怀中偶尔也来,这些大人来来去去,说的都是大人的话,我全当看不见。我不知道宝光为什么不来,他不是来过的吗?后来他不来,这个要问他自己。
宝光的朋友们都不写他,半个常州都是他的朋友,这些朋友个个会写,文武双全,可是他们不写,他们同他又都是三十年四十年的。我同宝光算到底二十年,其中十九年是虚的,没一起吃饭也没一起喝酒,面都见不到。
2001年春天,我在美国收到一个陌生人的电子信,他说代宝光写信问我,美国的出版环境是不是会好一点?我问他叫什么名字,怎么有我信箱,宝光有事问我为什么不自己来问。他支支吾吾,言词闪烁。我坚信他是骗子,不再复他信。
后来我知道宝光那时候在劳教。身体不自由,文字也不自由,一点出路都没有,托了人来找我,他以为我自由。其时我离了中国,写作反倒艰难,后来更是一个字都不写了。
隔了一年,我回国探亲,也去看看他。他仍住在西瀛里,有个记录片导演跟着他,拍他。我看他的头发没了,牙齿也快掉光了,我开始怀疑他吸的兴许不是大麻。
记录片导演要求我也站在弄堂口,让他拍几个镜头。我不乐意,又不好拒绝。记录片导演讲好吧,就拍你的背影好了。后来我看到电影,他还拍了我的侧脸,不高兴的侧脸,配了乐,还配了一条火车,当然他是拿这些东西配宝光,把他拍成一个民间精神。
那一个傍晚,宝光慢慢地,慢慢地倒了下去,街沿积了水,宝光就倒进下水道里去了。记录片导演说你倒是过来搭把手啊,我俩一起顶住他,把他板正,他又慢慢地,慢慢地立起来。
宝光的脸倒是一直笑嘻嘻的。
我思来想去他犯了什么罪,他们讲他混江湖。我认得的他,明明心怀慈悲,逼他斩人,他也只用刀背。
如果他的劳教就是为了吸了非法的什么,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他也从来没有跟我讲过。我只知道我一个朋友的丈夫同他关在一起,我的朋友要坐长途汽车坐到底,再走路翻过两个山头给她的丈夫送烟。她讲他在里面有了香烟,他的日子就好过一点了。
宝光讲这个女人有情有义。
宝光出新书,朋友们都来了,管策写了书名,董文胜必定是要配图,金锋洪磊可能写推荐人语,金磊已经写了书评,他讲他混江湖不混文坛。文坛可不就是个江湖?
他的朋友们写他,我不看我也知道他们会写他的刀光剑影的江湖。
写到这里的时候,宝光上线,我把这半篇发给他。我问他写得对不对?他说怎么记怎么写。
他讲的我们头一回见面,倒不是《翠苑》杂志社,是青果巷小饭店。
“夏天,你穿着当时流行的豹纹西裤,背着书包,是一个姓马的朋友介绍的,你们的父亲是朋友,我送了一本诗集给你,你把它放进书包,说,要去学校上课了。那年,你十七岁?多美好。我后来带你去洪磊家玩,再后来,你告诉我在电台上班,你告诉我在《雨花》上发了小辑,你说请我吃韩国料理,我就在劳动路上等你下班,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料理的吃法。还有,我的玫瑰诗稿也是你帮我打字的,在亚细亚影城,你把诗稿给我时还捎带一句,你的诗比你的人漂亮呵。”
这些片断,我全部忘得精光。马生我还有点印象,他父亲确是我父亲的朋友,早早出来做生意,后来成为我一个朋友的姐夫,说是生意越做越大。我见他的时候已经肥头大耳,生意大了,肯定更瘦不下来了。豹纹西裤,我要反驳的,我这一辈子,最怕狗,最恨西裤,还豹纹。宝光当是记窜人了。至于去了洪磊家而不是金锋家,我今天听到也是吃了一惊,那么那个穿圆领短袖,走来走去,有点凶的老婆不是金锋的,是洪磊的?
这个事情要去问洪磊或者金锋才能够确定,可是这个问题对于这篇文章不是很重要,所以还是先放下吧。
亚细亚影城我记得分明,因为就在我家门口,我常在那儿约人见面,杂志社派我采访一位越剧名伶,我也约她在亚细亚影城。她见了我十分吃惊,肯定是因为我穿校服还背书包,但是她素养很好,坐在亚细亚影城的台阶上配合我做完采访。
上了年纪,仍然美成一幅画的女人,我再也没有见过第二个。
我从美国搬到香港的间隙,在常州住了几个月,我想租个房间写作,宝光朋友是二房东,把他们的仓库,其中一间阁楼的二楼转租给我,一楼是一个画画的小孩,跟我讲想跟金锋,将来像董文胜那样。冬天,他穿一双老棉鞋,单薄棉衣,冻得动来动去。
房间有个气窗可以望见楼外面的桑树,一座水塔,我在地板中央放了一张课桌,一把椅子,每天挎着电脑来去。
楼前是个秋千架,后院放着一口棺材,不知道宝光从哪儿弄来的。后门我跟画画的小孩从来不开,到底是口棺材,没事不去开,秋千我也不坐,邻居家有条狗,没事我不出去招狗叫。
我还是一个字都没有写。离开十几年,不是开玩笑的,不能写了,就是不能写了。
倒是经常见到宝光,他同他的朋友们吃喝玩乐,看电影看到半夜。我有时候参加,多数时候不参加,不参加是因为我对他们来说到底是外面的人,他们讲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坐在那里,横竖不自在。很多人也不欢迎我,大概是知道我写小说,怕我写他们。
但是这半年,是我认识宝光二十年以来,同他最熟络的半年。这半年发生很多事情,有人来了,有人走了,彼得潘都结婚了,我和宝光共同的好朋友车祸死了。
我写作一直不专心,又要回香港住,仓库也就不再去了。有一天仓库要被拆掉,宝光叫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到底我也在仓库呆过了一阵子。
我因为不能写作,文章到底没有写。我也挺不容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