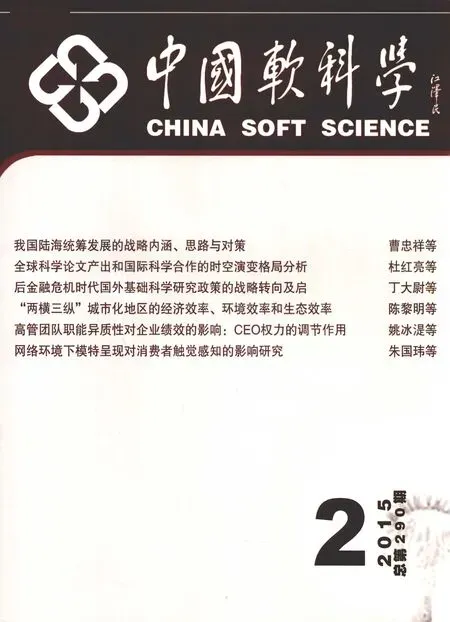美国、德国、日本气候援助比较研究及其对中国南南气候合作的借鉴
美国、德国、日本气候援助比较研究及其对中国南南气候合作的借鉴
秦海波1,2,王毅1,谭显春1,黄宝荣1,GANDENBERGER, C.3,LÜNINCK Freiherr Von, B.3
(1. 中国科学院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 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 系统与创新研究所,卡尔斯鲁厄 76139)

摘要: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推动和深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中国气候外交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维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深入分析比较了美国、德国和日本开展的气候援助,总结归纳了三国的重点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国际气候援助的历史演进以及2012年后的发展趋势。本文最后结合研究发现以及中国的现实国情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今后深化和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对外援助和南南合作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气候变化;气候合作;气候援助;气候融资;南南合作
收稿日期:2014-05-08修回日期:2014-11-20
基金项目:国家发改委“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技术合作战略研究”课题、“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课题和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资助(XDA05140300)。
作者简介:秦海波(1982-),男,新疆沙湾人,中国科学院与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公共政策及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205; 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15)02-0022-13
Abstract:South-South climate-related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climate diplomatic activities and an important tool to protect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shape a responsible image of China. This paper made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Japan, the three typical donors’ climate-related aid work and, tried to summarize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Then it discussed strategic evolution of climate-related aid of OECD-DAC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related aid after 2012.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and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this paper finally proposed several recommenda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China’s South-South climate-related cooperation in fu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limate-related Aid among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and Japan:Implications for China’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Concerning Climate Change
QIN Hai-bo1,2, WANG Yi1, TAN Xian-chun1, HUANG Bao-rong1,
GANDENBERGER, C.3, LÜNINCK Freiherr Von, B.3
(1.InstituteofPolicyandManagement,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190,China;
2.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49,China;
3.FraunhoferInstituteforSystemandInnovationResearchISI,Karlsruhe76139,Germany)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ooperation; climate aid; climate financ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一、 引言
气候援助,是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的资金和技术等援助[1-2]。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背后的各国博弈愈发复杂尖锐,发达国家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角度出发,日益重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的援外及合作,意图拉拢分化发展中国家,同时开发潜在的气候技术市场[3]。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碳排放国,中国目前也正承受着国际社会日益加剧的巨大减排压力。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气候援助,既可以帮助和促进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升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有助于增强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相互理解和支持,维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3-5]。
中国已经在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和合作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专业力量,但中国目前的气候援外局限于能力培训、清洁能源设备捐赠“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等[6]”。援助手段单一、管理较为分散、资金规模有限,尚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气候援外的深入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多从宏观视角论述中国实施气候援外和南南气候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3, 7-8],难以为中国制定气候援外战略方案、构建政策支持体系、提高援助管理绩效等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美国、德国和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提供气候援助最多的三个国家,2010-2012年三国共计提供了约38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9-11,16]。美国、德国和日本气候援助的相关经验,对中国的气候援外和南南气候合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将深入分析、比较和总结美、德、日三国的气候援助工作,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国际气候援助的历史演进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DAC)的CRS数据库*DAC成立于1960年,是OECD属下的委员会之一,主要负责协调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DAC包括了28个发达国家成员国和欧盟,其成员国提供的援助占世界ODA的90%以上。从1998年起,DAC开始通过其援助申报系统(Creditor Reporting System,CRS)监测成员国针对“减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沙漠化”类别的发展援助;2009年12月,又增加了“适应气候变化”类别。详细内容参见www.oecd.org/dac。和历年气候援助统计报告,以及一些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由于统计标准不一致,DAC-CRS数据库并未完全涵盖美国的气候援助数据。除个别说明外,有关美国的数据主要来自其2010-2013财年预算报告和2012财年气候援助报告。
二、美国、德国和日本气候援助分析
(一)美国
1. 美国的气候援助战略
美国长期对国际气候谈判持消极态度,拒绝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2]。但自2008年奥巴马总统上任之后美国的气候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明确表示将在气候变化方面担当领导者的角色[13]。奥巴马政府大刀阔斧制定了一系列气候变化新政策,在国内减少石油消费,鼓励清洁能源和低碳能源发展;在国际上积极参与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多边和双边合作,发挥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12]。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国政府承诺2010-2012年期间提供75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Fast-start Finance,FSF)*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即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在2010-2012年期间提供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这一资金目标后被写入《坎昆协议》(2010年)中,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正式内容和成果。,来帮助最贫穷和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抗击气候变化[14]。次年9月,奥巴马总统签署《全球气候变化倡议》(Global 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GCCI),计划借助双边、多边和民营机制,把气候变化问题纳入有关的对外援助方案,以倡导低碳增长,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增强社会气候适应能力,并减少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造成的排放[15]。根据美国国务院《2012财年气候援助报告》(U.S. Climate Finance in Fiscal Year 2012),2010-2012财年,美国政府累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74.6亿美元的FSF气候援助[16]。国会拨款援助、发展融资和出口信贷是美国气候援助的三个主要形式,其中国会拨款援助(主要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务院和财政部等政府机构)占全部援助总额的六成多(见表1)。

表1 2010-2012财年美国“快速启动”气候援助一览 单位:百万美元,现价
数据来源:U.S. Department of State,2013。
注:ⅰ.美国政府财年是从当年10月1日起至下年9月30日止。
ⅱ.美国的FSF气候援助不仅统计了有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援助,也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其他援助中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部分。
ⅲ.表中的缩写:USAID指美国国际开发署,State指美国国务院,Treasury指美国财政部,MCC指美国千年挑战署,OPIC指美国海外投资公司,Ex-Im指美国进出口银行。
2. 美国气候援助的重点领域
美国在GCCI框架下的气候援助包括清洁能源、可持续景观以及能力建设三大领域,主要通过国务院、财政部和国际开发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三个核心部门以项目的形式实施。2010-2012财年,这三个部门的GCCI预算分别达到4.6、11.3和10.5亿美元[17]。清洁能源是GCCI最主要的援助领域,2010-2012财年美国政府批准用于清洁能源双边援助的资金累计达到13.3亿美元,占GCCI预算的52.5%。清洁能源援助主要通过加速推行清洁能源技术、政策和方法,减少生产和使用能源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可持续景观援助主要包括森林和土地使用项目,美国在2010-2012财年拨款10.0亿美元,帮助有关国家制定高标准的计划,以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REDD+*REDD+是指通过减少毁林、减缓森林退化以及可持续管理,增加森林碳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详细内容可参见www.un-redd.org。)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能力建设重点是帮助气候变化最脆弱的低收入国家建立广泛、透明并且能够满足其成员需要的管理系统,以帮助其减少气候脆弱性,缓和气候变化对环境和经济产生的后果,提高正在进行的发展努力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2010-2012财年,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USAID一共获得6.4亿美元的财政拨款,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3. 美国气候援助的具体措施
USAID是负责美国ODA具体执行的主要部门。USAID将气候援助列为其重要的工作领域[18],已经开展了数十年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援助工作。除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免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之外,目前USAID主要致力于通过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走气候友好型的低碳发展之路,包括:一,帮助发展中国家制定和执行低碳发展战略;二,向其提供早期预警系统以及其他设备;三,帮助其改善水资源管理、农业、卫生以及灾后重建;四,探索将气候变化融入进农业、减灾、政府治理等发展援助之中等。2012年1月,USAID发布《气候变化与发展战略报告2012-2016》(Climat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2012-2016),提出了未来五年气候援助的三大战略:一,加大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以减少森林砍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二,帮助发展中国家和社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三,将气候变化融入到USAID的所有项目与行动。到2016年,USAID计划帮助20个伙伴国家制定和执行低碳发展战略,将气候变化融入粮食安全、全球健康、民主以及其他的发展援助中,并最终找出最有效的方法来支持低排放的气候友好型发展[19]。
(二)德国
1. 德国的气候援助战略
在过去20年中,德国一直积极履行千年宣言及其核心目标“消除贫困”,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双边援助国之一[20]。德国一直将气候变化视为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型的主要挑战,2003-2012年累计提供了180多亿美元的气候援助,是欧盟所有成员国里最多的。特别是自2007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以后,德国开始加大对气候变化和发展等一些关键性全球挑战的话语权争夺[21],气候援助规模也明显增加(见图1)。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德国承诺的FSF气候援助份额约为16.6亿美元(12.6亿欧元)。根据Kowalzig的研究报告,2010-2012年,德国实际提供了约17亿美元(12.9亿欧元)FSF援助,略微超过了原先的承诺[22]。实际上,FSF援助只占同期德国气候援助的七分之一。DAC-CRS的数据显示,2010-2012年德国的气候援助总计达115.7亿美元,占其同期ODA总额的近三成。目前国际社会对于FSF所要求“新的、额外的”标准还没有明确的定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充足的、可预期的资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公约以及随后的《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都未对“新的、额外的”做出明确的定义。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ODA仍低于其国民生产总值0.7%的国际社会公认目标,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气候援助标准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德国是少数几个对FSF有明确定义并应用到实际援助工作中的国家之一[23],但目前还缺乏更充足的数据来评判德国的FSF援助。从最新的数据来看,FSF资金到期后德国并没有缩减气候领域的援助。2013年德国政府气候援助预算资金为19.2亿美元,比2011和2012年还略微有所增加(见图2)。

图1 2003-2012年德国气候援助及其占ODA总额的比重(2011年美元不变价) 数据来源:DAC-CRS数据库,www.stats.oecd.org。 注: ⅰ.援助总额包括双边援助及其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开展的多边援助。 ⅱ.DAC将气候援助根据援助类型分为适应援助和减缓援助,根据援助方式分为直接援助(Principal Objective)和间接援助(Significant Objective),根据DAC气候援助统计报告 [9-11],2010-2012年德国分别有2.9亿、8.1亿和5.8亿美元项目同时申报了减缓和适应援助。图1中援助总额的计算方法为:适应援助(直接援助+间接援助)+减缓援助(直接援助+间接援助)-重复统计部分。
2. 德国气候援助的管理*本段部分德国机构的名称(BMZ、BMU、KfW Bank、GIZ)为德国缩写。
德国气候援助主要由经济合作和发展部(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BMZ)和环境部(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Building and Nuclear Safety,BMU)负责,但两部门常常各自为政,缺乏一致性的援助战略,招致了很多批评声音。不过BMZ和BMU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2013年联合发布合作战略报告,提出未来要加强彼此间合作,发展更加成熟的援助办法[24]。BMZ的气候援助可以分为气候融资和技术援助两类,前者主要通过德国开发银行(German Development Bank,KfW Bank)渠道,后者主要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erm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GIZ)负责。2010年,BMZ气候变化项目资金达到15亿美元,占其总预算的78亿美元的近两成。这一方面反映了气候援助与发展合作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也表明BMZ将气候援助视为帮助受援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型的重要手段,而不是仅仅把它当作环境援助的“升级版”。BMU是德国气候援助另一个重要的提供者,2008年BMU发起成立《国际气候倡议》(International Climate Initiative,ICI),其气候援助主要通过ICI渠道。ICI每年预算1.6亿美元,主要关注气候减缓项目以及碳捕获和封存技术,适应性的项目仅占10%左右,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申请。起初ICI的资金主要来自欧盟碳交易(Europea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U ETS)收入,这种通过ETS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一种政策创新。随着排放许可证价格的下跌,目前ICI的资金主要来自BMU的预算[25]。
3. 德国气候援助的优先领域
德国的气候援助主要包括减缓、适应和REDD+/生物多样性三种类型,其中减缓援助占大约五成,适应援助占两成多,REDD+援助占将近三成,这个比例构成与过去德国的气候援助战略一直比较重视减缓气候变化有关。目前德国的气候援助理念正在发生转变,不再强调减缓气候变化,而是希望通过投资提高受援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以增加援助的成本有效性。德国政府的气候援助预算也反映出这一变化趋势[22]。如图2所示,德国政府2013年适应援助预算支出达到9.5亿美元,比上一年上涨了五成多;减缓援助预算支出为8.7亿美元,比上一年减少了1.2亿美元,减缓、适应和REDD+的三类援助的比例更加平衡。德国通常只向DAC受援国名单里58个国家提供气候援助,不过也有特例,主要是针对一些对气候变化特别脆弱的小岛屿国家。德国先会和受援国开展一系列对话来确定气候援助的优先领域,随后双方共同参与制定优先领域战略报告,受援国可以根据这些战略文件向BMZ及其执行机构提交实施方案建议书[24]。

图2 2008-2013年德国气候相关援助及FSF份额(现价) 数据来源:Jan Kowalzig,2013。 注:2013年数据来自于德国政府2012年的预算报告,并不是最终数据,仅作为参考。
(三)日本
1. 日本的气候援助战略
日本一直不甘心做“经济大国-政治小国”式的跛足国家,自冷战结束以后就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性环境议题作为其外交战略的重点领域,试图扩大国际影响力,为其迈向政治大国铺平道路[26]。日本政府一方面积极通过国际场合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阐述其环境援助政策;另一方面则利用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雄厚优势,积极开展国际环境合作和援助[27]。正是在这种外交战略背景下,日本一直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议题,于1997年成功主办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京都气候大会*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会议。,并为《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做出了贡献。进入新世纪,日本依然将气候变化作为其环境外交的重要内容。2002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提出“小泉构想”,指出日本将积极利用ODA并加强技术转移、人才培育等工作,促进《京都议定书》生效[28]。近年来尽管日本政局持续动荡,首相更迭频繁,但历任首相都对气候变化外交的目标保持了一致,极力通过在气候变化领域内的作为塑造日本的大国形象。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日本政府承诺到2012年提供150亿美元的FSF援助,占到所有发达国家FSF承诺捐款总额的一半[29]。
2. 日本气候援助的发展趋势
日本是DAC成员国中提供气候援助最多的国家。2003-2012年十年间,日本累计提供了400亿美元的气候援助,占同时期DAC气候援助总额的四成。从趋势上看,2003-2007年日本的气候援助一直比较稳定,维持在每年2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只是在2008年以后才开始快速增长(见图3)。从比例上看,日本气候援助占其ODA比重是DAC成员国中最高的,即使是最低的2006年,气候援助也占到日本ODA的12.5%。2009年以后,日本的气候援助一直占其ODA总额的50%,最高的2010年甚至一度达到70.5%,远远高于DAC平均水平。由于受到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截止到2012年12月,日本累计提供了约135亿美元FSF援助,其中来自ODA资金大约在76亿美元左右[30-31]。仅从数据上直观地看,2010-2012年,日本的气候援助达到195.6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前七年的总和,远远超过了其承诺的FSF份额。但是如果结合日本的ODA总额一起分析,不难发现2010-2012年日本ODA总额和前几年相比甚至还略微下降。这也反映出日本看似大规模的气候援助,实际上只是把原有已存在的发展援助贴上了一个“气候变化”的新标签,增加的只是纸面上的比例而已。很多学者批评日本用“新瓶装旧酒”显然是不无道理的[32]。

图3 2003-2012年日本气候援助及占其ODA的比重(2011年美元不变价) 数据来源: DAC-CRS数据库,www.stats.oecd.org。 注: ⅰ.援助总额包括双边援助及其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开展的多边援助。 ⅱ.DAC将气候援助根据援助类型分为适应援助和减缓援助,根据援助方式分为直接援助(Principal Objective)和间接援助(Significant Objective),根据DAC气候援助统计报告 [9-11],2010-2011年日本分别有6.4亿、5.7亿美元和3.4亿美元项目同时申报了减缓和适应援助。图3中援助总额的计算方法为:适应援助(直接援助+间接援助)+减缓援助(直接援助+间接援助)-重复统计部分。
3. 日本气候援助的管理
日本的气候援助有严密的组织和管理体系,涉及的部门和机构主要包括日本外务省(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MOFA)和新成立的日本国际协力组织(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前者主要负责气候援助的统筹协调和决策制定,而后者则是日本ODA的主要执行机构。为了提高援助的质量、效率以及协同性,2008年10月日本政府将原有的负责技术援助的旧JICA,负责开发优惠贷款的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JBIC)和MOFA负责无偿赠款援助的机构(但仍有30%的赠款援助由MOFA管理)进行整合,组建成立了新JICA。这样一来,新JICA就从原来集中执行技术合作的机构转变成为融合赠款援助、技术援助和开发优惠贷款三大援助机制的全新对外援助组织。新JICA目前每年预算在100亿美元以上,已超越USAID成为全球最大的双边发展援助机构[33]。气候援助是新JICA援助工作中最重要的一块,2008年成立伊始新JICA就发布了《JICA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指南》(Direction of JICA Operatio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声明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视为其发展援助的重要议题,计划利用日本先进技术和经验,同时有效整合财政援助手段,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的可持续发展[34]。
三、美国、德国和日本气候援助比较与经验借鉴
(一)美国、德国和日本气候援助比较
2007至2008年前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气候政策都相继发生调整,开始重视气候外交以提高本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影响力。特别是美国一改往届政府的消极态度,积极在气候变化方面担当领导者的角色。与此同时,三国气候援助规模也开始大幅增加。2010-2012年,德国和日本分别提供了115.7亿和190.3亿美元的双边气候援助,占其同期ODA总额的29%和58%,远高于DAC平均16%的水平。德国和日本两国气候援助都有七成的资金投向了减缓领域,适应援助只占三成。由于缺失美国双边气候援助数据,本节主要对美国、德国和日本的FSF援助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见表2)。
截至2012年底,美国、德国和日本都基本完成了其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承诺的FSF援助份额。在资金来源方面,德国全部来自于其ODA资金,美国九成来自ODA资金;日本六成来自ODA资金,其余四成(约50亿美元)主要由其他官方资金(Other Official Flows,OOF)提供。需要指出的是,美、日两国的FSF援助数据都避谈“新的、额外的”标准,只有德国给出了明确定义:在2009年原有气候援助基准上新增的和(或)依靠新融资渠道(如EU ETS)获得的公共资金[23]。此外,尽管《坎昆协议》要求要平衡分配减缓与适应领域的气候援助,但美国、德国还是将七成的FSF援助投向了减缓领域,而日本的比例更是高达82%。
美国、德国和日本的FSF援助还存在其他很多区别之处:第一,美国和日本的FSF援助有八成是通过双边渠道,由本国发展援助机构负责实施;德国的FSF援助分配比较均衡,双边渠道和多边渠道的比例是55%比45%。第二,德国和日本FSF援助中无偿援助占26%,其余资金通过优惠贷款方式提供;美国有六成的FSF援助是无偿提供,其余四成为优惠贷款。第三,美国和德国的FSF援助基本上平均分配给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日本的FSF援助则主要集中在亚洲(63%),非洲和拉丁美洲分别只占10%。
美国、德国和日本FSF援助大都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其中,外交部门负责援助战略制定和统筹协调,但美国和日本的外交部门也安排了少量预算可以直接开展气候援助。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主要是依托本国的双边发展援助机构开展,如美国USAID、德国GIZ。优惠贷款则由本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负责,如美国OPIC、德国KfW Bank。日本相对特殊,2008年日本对外援助机构进行了重组整合,无偿援助、技术援助和优惠贷款援助都统一由一个部门(新JICA)负责执行。
(二)美国、德国和日本气候援助经验借鉴
第一,倚重气候援助手段开展气候外交工作。2007年后美国、德国和日本逐渐开始重视气候外交以提高本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影响力,而气候援助一直是三国气候外交倚重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其ODA中的比重逐年扩大。此外,美、德、日三国还借助援助和合作的名义开展一系列气候外交活动。如美国和德国积极倡导构建全球气候合作与援助新机制,提升本国在国际气候议题中的领导力;日本以提供援助为由先后主办与小岛屿国家、非洲国家、以及东亚国家的气候政策对话,对发展中国家施加潜在的外交影响。

表2 2010-2012年美国、德国和日本气候援助比较 单位:亿美元,现价
数据来源:双边数据来自DAC-CRS数据库,www.stats.oecd.org;美国FSF援助数据来自U.S. Department of State,2013;德国FSF援助数据来自Harmeling Sven, et al,2013;日本FSF援助数据来自Delegation of Japan in UNFCCC,2013;Takeshi Kuramochi, et al,2012。
注:ⅰ.DAC-CRS数据库关于美国的气候援助数据存在缺失,考虑到数据的一致性,表2中双边援助数据以OECD-CRS数据为准。
ⅱ.指占其无偿援助的比重,优惠贷款和其它资金未作减缓和适应区分。
第二,将气候援助融入发展援助之中。美、德、日气候援助目前突出的趋势就是将气候援助融入其发展援助之中,主要表现在:一,制定国家级的气候援助战略,将气候变化理念融入发展援助之中。如USAID提出,要将气候变化融入粮食安全、全球健康、民主以及其他的发展援助中,并最终找出最有效的方法来支持低排放的气候友好型发展[15]。二,整合本国在资金、技术和经验等方面的优势,统一行动形成合力。如日本将JICA、JBIC等负责对外援助的机构重组成立新JICA,有效融合了无偿援助、融资援助和技术援助等多种手段,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第三,协调和监管机制健全完善。美、德、日的气候援助涉及外交、援助和财政等政府部门,如何协调和监管各有关部门就成为完成援助目标的关键所在。在协调方面,美国的经验是首先制定统一的援助原则(GCCI),其次通过国会预算拨款的形式来审批、控制和协调各部门开展不同针对性的具体援助工作。对于项目监管,德国和日本主要是依托DAC-CRS数据库,通过援助者自行标记、申报来识别和监测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发展援助。
第四,注重企业、NGO等民间机构参与气候援助。美、德、日气候援助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吸引和支持企业与NGO等民间机构参与气候援助,主要包括:一,加快通过气候融资、出口信贷等措施吸引私营企业参与气候援助与合作,抢占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和气候技术市场。如日本FSF援助中有约四成的资金(50亿美元)都是通过OOF渠道以鼓励私人企业参与气候投资。二,重视对本国以及受援国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的支持,促进气候援助的多元化操作和使用。德国FSF援助中资助各类NGO的资金达一亿美元,其中近八成分配给了本国的NGO[23]。
四、讨论
(一)DAC气候援助战略演进与发达国家的气候援助
通过对美国、德国和日本气候援助的比较研究,本文发现2003-2012年德国和日本的气候援助资金变化都表现出明显的两阶段特征:2007年之前,德、日两国气候援助资金规模基本稳定,占其ODA比重的变化幅度较小;从2008年开始,德、日两国气候援助无论是数额还是占ODA比重都开始大幅增长,并在FSF阶段(2010-2012)达到顶峰(见图1和图3)。而DAC的数据显示,这一时期发达国家整体的气候援助资金变化也呈现出与德国和日本类似的趋势特征(见图4)。前文中曾指出2007年后美、德、日都开始注重气候援助,而究竟何种因素促使这些发达国家的气候援助战略发生调整?本文将尝试从DAC气候援助战略演进的视角讨论发达国家气候援助战略变化的驱动因素。

图4 2003-2012年DAC针对环境的援助(按里约公约分类)及气候援助占ODA的比重(2011年美元不变价) 数据来源:DAC-CRS数据库,www.stats.oecd.org。 注: ⅰ.援助总额包括双边援助及其通过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开展的多边援助。 ⅱ.DAC将气候援助根据援助类型分为适应援助和减缓援助,根据援助方式分为直接援助(principal objective)和间接援助(significant objective),根据DAC气候援助统计报告 [9-11],2010-2012年分别有38.8亿、36.1亿和41.7亿美元项目同时申报了减缓和适应援助,图4中援助总额的计算方法为:适应援助(直接援助+间接援助)+减缓援助(直接援助+间接援助)-重复统计部分。 ⅲ.美国气候援助申报的要求与DAC“里约标签”并不完全一致,DAC-CRS数据库关于美国的气候援助数据存在缺失。考虑到数据的一致性,图4以DAC-CRS数据为准。有关美国气候援助的详细信息,可参见www.state.gov/faststartfinance。
深入分析DAC近二十年气候援助战略的变迁,可以发现几个重要的事件(时间)节点(见图5):一,1998年1月,开始监测成员国针对减缓气候变化等里约公约*指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地球峰会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总称。目标的援助[35];二,2002年5月,发布政策声明要将里约公约整合到发展合作与援助之中[36];三,2006年4月,将适应气候变化确立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三个优先援助领域之一[37-38];四,2008年1月,强制要求申报里约公约援助[39];五,2009年12月,在里约公约援助中增加适应气候变化援助类别[40]。这些事件(时间)节点表明,DAC的气候援助战略并不是静止不变而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演进过程。依据这些节点,DAC的气候援助战略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2006年之前,减缓气候变化是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荒漠化防治并列的里约公约目标援助类别;2006年之后,适应气候变化被升级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优先援助领域之一。DAC气候援助战略调整对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对外援助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新世纪以来德国(图1)、日本(图3)以及DAC(图4)的气候援助数据都印证了这一点。2003-2007年DAC的气候援助几乎没有变化,维持在每年5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与生物多样性以及荒漠化相关援助的差距较小。随着2006年适应气候变化被DAC确立优先援助领域之一以及2008年强制要求申报里约公约援助,2008-2012年DAC气候援助逐年快速增长,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荒漠化防治援助的差距也越拉越大。
当然,发达国家气候援助战略必然也会受到国际气候谈判形势和世界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影响(见图5)。特别是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集体做出“2010-2012年提供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援助(FSF),到2020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的承诺后,2010-2012年DAC气候援助数据暴涨至每年200亿美元左右规模。但本文认为DAC气候援助战略相对独立于国际气候谈判形势,且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更为直接有效且具有约束性。理由有三:第一,2009年之前,国际气候谈判在气候援助方面未有任何显著进展。但同期DAC的气候援助战略一直在调整演进中,发达国家气候援助规模也随着DAC气候援助地位的上升和要求的变化逐渐增加。第二,虽然国际气候谈判在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和2010年坎昆会议上就气候援助取得重大进展,但截至目前(2014年8月)DAC除了在2009年底增加适应气候变化援助以外,并未进一步提升气候援助的战略地位。第三,FSF承诺虽然大幅提升了发达国家2010-2012年的气候援助规模,但其影响只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未见发达国家对FSF阶段结束以后的气候援助战略有任何实质性部署或行动[32]。
综合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发达国家的气候援助虽受到DAC气候援助战略和国际气候谈判形势的双重驱动,但前者的影响更为直接有效且具有约束性,对发达国家气候援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下节中笔者将基于这一论断讨论国际气候援助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二)国际气候援助中几个焦点问题
目前,国际社会正在为实现2020年每年1000亿美元长期气候援助目标而艰苦谈判。关于国际气候援助谈判的争议主要聚焦在三个议题:一,发达国家是否兑现了2010-2012年300亿FSF承诺;二,2012年FSF到期后国际气候援助的发展趋势;三,到2020年每年1000亿美元长期气候援助的资金来源。本节将基于前文对美、德、日以及DAC气候援助的研究结论,对这三个问题作出回答。
第一,由于很多发达国家公布的FSF援助数据避谈“新的、额外的”标准,目前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是否兑现了FSF承诺还存有很大的争议。本文根据DAC-CRS数据计算发现:一,2010-2012年发达国家气候援助整体规模在2007-2009年的水平上增加了近400亿美元;二,2007年-2012年发达国家的ODA援助总额一直维持在每年13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与此同时,针对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分析也发现,其FSF全部或大部分来自于ODA资金。由此本文认为,发达国家在数额上基本兑现了FSF承诺,但绝大多数FSF资金实际上来源其原有的ODA。
第二,FSF援助已于2012年到期,而气候公约下的新资金机制(绿色气候基金)目前仍在艰难谈判之中[41]。实际上,国际气候援助中双边援助总量远远超过多边援助,是更为重要的资金来源。而本文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双边气候援助主要受OECD-DAC气候援助战略的驱动,其在2006年确定的“将气候变化作为促进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优先援助领域之一”战略中并未发生重大转变。因此本文判断,2013年后一段时期内国际气候援助还将以双边援助为主并至少维持在2008-2009年的水平,即每年100亿美元以上。

图5 发达国家气候援助的外部与内部驱动因素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UNFCCC网站内容及OECD相关报告总结整理。
第三,对于2020年长期气候援助目标的资金来源,发展中国家主张以公共融资为主,发达国家则更倾向于依靠碳市场和私人资金,双方仍处在博弈之中[41]。综合国际气候援助历史与现状,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22],本文认为到2020年后国际气候援助仍将主要依靠双边渠道;而要实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援助目标,来自ODA的资金须达到5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这对于现有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五、对中国南南气候合作工作的建议
综合以上的研究成果,本文对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对外援助和南南合作工作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重视气候援助在气候外交中的重要作用,将南南气候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建议尽快提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政策倡议,制定出台国家级的合作规划,推动建立发展中国家之间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机制;借助南南气候合作方式,积极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气候外交,逐步提升中国的影响力。
第二,增加气候援助的资金投入,将气候援助逐步扩展到发展援助领域。建议适度调高财政资金对南南气候合作的支持力度,加强对援助资金的监管和审计;建立完善气候援助的管理协调机制,将一部分气候援助项目交由科技、农业、卫生等专业部门负责实施。
第三,建立多元化的气候融资机制,扩大气候援助的资金来源。建议成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建立多元化的气候合作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借助现代型、专业型的基金管理模式,提高气候合作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
第四,加强对企业、NGO等民间机构的支持,促进本国与受援国的公众参与。建议加强对中国绿色低碳企业借助南南气候合作渠道“走出去”问题的研究,建立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和管理服务体系;增加对相关NGO、科研机构以及其他民间机构的资助,以“稀释”官方援助的政治性,增进本国、受援国以及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Z]. 纽约: 联合国, 1992.
[2] 联合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Z]. 纽约: 联合国, 1997.
[3] 刘燕华, 冯之浚. 南南合作: 气候援外的新策略[J]. 中国经济周刊, 2011(9): 18-19.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OL]. www.gov.cn, 2011-11-22.
[5] 曹亚斌. 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小岛屿国家联盟[J]. 现代国际关系, 2011(8): 39-43, 51.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4)白皮书[OL].www.gov.cn,2014-07-10.
[7] 周宝根. 国际官方发展援助新动向及其对我国的影响[J]. 国际经济合作, 2008, (2): 18-22.
[8] 周强, 鲁新. 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新趋势[J]. 国际经济合作, 2011(1): 77-81.
[9] OECD-DAC. Trends in aid to environment, a compon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nance (1991-2011) [M]. OEC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port 2012. Paris: OECD, 2012: 55-68.
[10] OECD-DAC. Statistics on climate-related aid 2012 [Z]. Paris: OECD, 2013.
[11] OECD-DAC. Statistics on climate-related aid 2013 [Z]. Paris: OECD, 2014.
[12] 张莉.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演变特征和奥巴马政府气候变化政策走向[J]. 国际展望, 2011, 10(1): 75-94, 129.
[13] OBAMA B. Recorded remarks to global climate summit [OL]. www.change.gov, 2008-11-18.
[1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fast start climate finance [OL]. www.state.gov, 2013-12-22.
[15]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Obama’s development policy and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 [Z].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2010.
[1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climate finance in fiscal year 2012 [Z].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3.
[17] LATTANZIO K R. Th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itiative (GCCI): budget authority and request, FY2010-FY2013 [Z].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2.
[18] USAID. USAID’s work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OL]. www.usaid.gov/climate, 2013-12-22.
[19] USAID. Climat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2012-2016 [Z]. Washington, D.C.: USAID, 2012.
[20] BMU. Facts and figures of Germa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OL]. www.bmz.de, 2014-05-19.
[21] 余南平. 发展援助的中间道路: 德国对外援助研究[J]. 德国研究, 2012, 27(4): 30-52, 125.
[22] Jan Kowalzig. Promising the moon or delivering down-to-earth? An overview of German fast start finance 2010-2012 [Z]. Berlin: Oxfam Germany, 2013.
[23] Harmeling Sven, Anja Esch, Linde Griesshaber, et al. The German fast-start finance contribution [Z]. Bonn: German Watch,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3.
[24] BMU and BMZ. Together for a common cause: Germany’s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ing [Z]. Berlin: BMU, 2013.
[25] Katrin Enting and Sven Harmeling. German climate finance: put to the test [Z]. Bonn: German Watch, Stuttgart: Brot für die Welt, 2011.
[26] 宫笠俐. 后冷战时代日本环境外交战略研究[J]. 东北亚论坛, 2012(3): 98-104.
[27] 林晓光. 日本政府的环境外交[J]. 日本学刊, 1994(1): 19-32.
[28] 吴飒凤. 新保守主义式微下的日本外交新思潮——环境外交路径之建构[D]. 新北: 辅仁大学日本语文学系, 2009.
[29] JICA. JICA’s cooperation for climate change 2010 [Z]. Tokyo: JICA, 2010.
[30] Delegation of Japan in UNFCCC. Japan’s fast-start fina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up to Dec. 2012 [OL]. www.unfccc.int, 2013-12-22.
[31] Takeshi Kuramochi, Noriko Shimizu, Smita Nakhooda, et al. The Japanese fast-start finance contribution [Z]. 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2012.
[32] 张雯, 王谋, 连蕙珊. 气候公约快速启动资金实现进展与发达国家环境履约新动向[J]. 生态经济, 2013(3): 29-32.
[33] JICA. The start of new JICA [Z]. Tokyo: JICA, 2008.
[34] JICA. Direction of JICA’s operatio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Z]. Tokyo: JICA, 2010.
[35] OECD-DAC. Tracking aid in support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Z]. Paris: OECD, 2011.
[36] OECD-DAC. Integrating the Rio conventions into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Z]. Paris: OECD, 2002.
[37] OECD. Declaration on integrat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to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Z]. Paris: OECD, 2006.
[38] OECD. Framework for common action around shared goals [Z]. Paris: OECD, 2006.
[39] OECD-DAC. The DAC’s work to integrat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M]. OEC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port 2012. Paris: OECD, 2012: 45-52.
[40] OECD-DAC. Integrat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to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Z]. Paris: OECD, 2009.
[41] 王遥, 刘倩. 气候融资: 全球形势及中国问题研究[J]. 国际金融研究, 2012(9): 34-42.
(本文责编: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