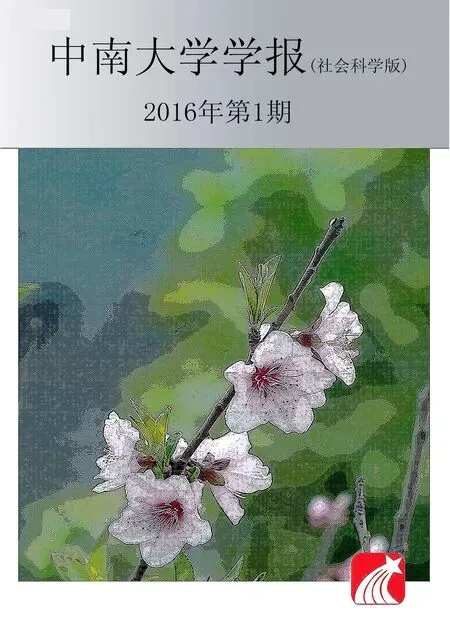集权与制衡:论附条件不起诉中的权力配置
谢登科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集权与制衡:论附条件不起诉中的权力配置
谢登科
(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附条件不起诉有利于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贯彻“教育优先”原则,但却将公诉、处遇决定、社会调查、监督考察等多项职权集于检察院,检察官在附条件不起诉中享有巨大裁量权,背离了现代检察制度权力制衡的理念。附条件不起诉中权力配置有“一体化”和“分立化”两种模式,两者各有利弊。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实行“一体化”模式,扩张了检察官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时的自由裁量权。裁量有利于确定个别化处遇措施,但却存在滥用风险。为防止权力滥用,有必要对附条件不起诉中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予以控制。
附条件不起诉;权力配置;自由裁量权;监督考察
现代检察制度是刑事诉讼中权力制衡的重要途径,它废除了纠问式下法官集侦查、追诉、审判等多项职权于一体的诉讼模式,将追诉、审判职能分别配置给检察官、法官,保障了审判中立性和公正性。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则在某种程度背离了现代检察制度权力制衡的基本理念,将公诉、处遇决定、社会调查、监督考察等多项职权赋予检察院,使其成为一个“集权的制度载体”,检察官在附条件不起诉中享有巨大裁量权。在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实行捕、诉、监、防“一体化”模式,加大了附条件不起诉集权程度。为实现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优先”原则,这种集权有其正当性。但集权也造成多重裁量权叠加,裁量权越大,滥用风险越大。因此,需在附条件不起诉中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予以适当控制。
一、“集权的制度载体”:附条件不起诉中的四种职权
附条件不起诉,也称为暂缓起诉、暂缓不起诉等,它是对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附条件和附期限地暂予不起诉,根据其在监督考察期间的表现再决定是否起诉的制度。作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处遇措施,附条件不起诉可避免对犯罪者贴上罪犯“标签”,减少其回归社会障碍,有利于犯罪特别预防。但它也面临权力过于集中的风险。2010年6月,浙江省宁波市某检察院对涉嫌交通肇事罪的王某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这一普通刑事案件,却因适用附条件不起诉而引起媒体广泛关注,被解读为“行善代刑”“侵犯法院审判权”。[1]不过,鉴于附条件不起诉运行的良好社会效果,我国2012《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这一实践经验,将其作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内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需进行社会调查。因此,检察院在附条件不起诉中承担了公诉、处遇决定、社会调查、监督考察四项职权,成为“集权的制度载体”。
(一) 公诉权:检察院的专属权力
公诉权是公诉机关提请法院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权力。从本质上看,公诉权是司法请求权,本身不具有最终判定性和处罚性,它包含的实体请求只能通过审判实现。[2]公诉权是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专属权力,它实现了诉审分离,有利于裁判中立。检察院行使公诉权的活动包括: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出庭公诉以及由公诉派生的不起诉等。在附条件不起诉中,检察院公诉权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审查起诉。检察院需对案件事实、证据材料等予以审查,以判断其是否符合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条件。第二,起诉或者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是介于起诉和不起诉之间的过渡措施,填补二者间空隙。[3]是否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起诉,取决于其在考验期内表现。若存在刑诉法第273条第1款规定情形之一,则应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决定提起公诉;若在考验期内履行相应义务及负担,则应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
(二) 决定权:实质意义上的裁判权
在普通刑事案件审查起诉阶段,检察院审查后应作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而在附条件不起诉中则需作出两次决定,这两次决定的法律效果截然不同。第一次决定在审查起诉完毕后作出。检察院认为案件符合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条件,在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意见后,可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这里的“决定”与其他案件中审查起诉后作出的“决定”存在本质差异,它以实体性处遇措施为主要组成部分,包括义务负担、保护处分等内容。第二次决定是考察期限届满作出的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此时的“决定”与其他案件中审查起诉后作出的“决定”无本质差异,都是对案件的程序性处理。
附条件不起诉被指责为“侵犯法院审判权”,主要是第一次决定涉嫌对法院审判权侵犯,因为其包括对犯罪嫌疑人实体性权益的处遇决定。从正当程序出发,附条件不起诉存在侵犯法院审判权之虞。但若放弃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只能面临定罪量刑的不利结局,被贴上犯罪者“标签”。背负这一“标签”会阻碍未成年人回归社会而被迫选择再次犯罪,产生“因犯罪而犯罪”的恶性循环。[4]因此,附条件不起诉“侵犯法院审判权”的不正义,可避免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导致“因犯罪而犯罪”恶性循环的更大不正义,这是其存续的正当根基。
(三) 社会调查权:社会危险性评估的权力
刑诉法第268条规定,公检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可根据情况进行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本质是调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格,查明其人身危险性大小,将调查结果作为对其确定个别化处遇措施的依据。[5]社会调查与侦查行为存在本质差异。前者主要关注犯罪人人格,后者则主要关注犯罪行为和事实。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对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展开社会调查,可有针对性地确定个别化处遇措施。该规定将社会调查权赋予公检法三机关,检察院亦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享有社会调查权。通过社会调查,为其决定是否适用附条件不起诉、采取何种监督考察措施提供决策依据。
虽然刑诉法第268条赋予检察院社会调查的裁量权,但适用附条件不起诉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悔罪为必要条件,这就需办案人对未成年人的认识能力、犯罪前后表现、犯罪后悔意、为弥补损失和道歉所体现的诚意等因素予以调查。另外,确定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个别化监管措施,也要求办案人进行社会调查。因此,在适用附条件不起诉中,社会调查不可或缺。
(四) 监督考察权:实质意义上的执行权
附条件不起诉是设置一定条件和期限的临时性处分措施,最终是否提起公诉,取决于被附条件不起诉人能否通过监督考察。监督考察在附条件不起诉中居于核心地位:一方面,它直接反映之前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是否合理。通常而言,如果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以及监管措施合理,那么,监督考察工作也会比较顺利。另一方面,监督考察结果直接决定着是否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提起公诉。
监督考察,是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在考验期内履行义务情况予以的观察和督促。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权或者执行权,即执行现有法律或生效司法文书的权力。在附条件不起诉中,检察院是监督考察权主体,而被附条件不起诉人是监督考察对象。刑诉法第272条第1款将监督考察权配置给检察院,主要考虑检察院在决定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前,已充分了解案情和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由其监督考察,有利于工作衔接,有利于考察期届满及时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6]因此,工作便利性和衔接有效性是将监督考察权配置给检察院的主要理由。
二、附条件不起诉权力配置的实践模式及运行图景
附条件不起诉由检察院适用和运行,其中的四项职权亦由检察院承担和行使,但刑诉法并未明确上述职权在检察院内部由何部门承担。权力配置模式不同,附条件不起诉运行效果也不尽相同。
(一) 权力配置的两种模式:“一体化”与“分立化”
从理论逻辑上分析,上述职权在检察院内部有两种配置模式:“分立化”和“一体化”。在实践中主要采取“一体化”模式。
在“分立化”模式下,将社会调查、审查起诉、监督考察等职能分别交由不同机构或人员负责。在附条件不起诉中,承担社会调查、审查起诉和监督考察的检察官,并非同一人员,而是将社会调查权、审查起诉权、监督考察权予以区分后配置给不同人行使。“分立化”模式实现了社会调查权、决定权、监督考察权的相互分离,可避免权力过度集中,实现权力有效制约。将权力制衡理念注入附条件不起诉是“分立化”模式的最大优点。决定是否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检察官,不必承担监督考察工作,无需将监督考察便利性作为是否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隐性条件”,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附条件不起诉运行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但由于决定权与监督考察权分属不同检察官,这就要求监督考察权人重新熟悉案情及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个人情况,必然造成工作重复,影响司法效率,也不利于未成年人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无法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一体化”模式,是将附条件不起诉中蕴含的公诉、处遇决定、社会调查、监督考察等职权配置给同一人员或者部门行使。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2年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省级、地市级检察院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较多的基层检察院,原则上都应设立独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实践中,全国各级检察院基本都成立了专门的未成年人检察机构。附条件不起诉中的各项职权,通常由检察院中负责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承担。在“一体化”模式下,基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机构除了承担附条件不起诉中的四项职能外,还需承担批捕、法律监督、犯罪预防等职能,权力高度集中和重叠。集权程度越高,滥用风险越大。“一体化”模式本身存在诸多缺陷:第一,将社会调查权、决定权、考察监督权等多项权力集于办案人一身,会造成权力过度集中,若缺乏有效控制,很容易权力滥用。第二,给办案人带来沉重工作负荷。在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中,办案人承担社会调查、公诉审查、考察监督等诸多工作,还需两次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趋简避繁的自然理性,会让检察官减少甚至拒绝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导致该制度在运行中的失灵。第三,办案人往往会将监督考察便利性作为决定是否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重要因素,可能导致悖离未成年人平等保护的立法初衷。
“一体化”模式虽存在上述缺陷,但也具有“分立化”模式无法比拟的优势:第一,有利于附条件不起诉各项工作衔接,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性劳动。附条件不起诉工作繁重,“分立化”模式虽可减少单个检察官的工作负担,但却增加了检察院总体工作量。负责社会调查、处遇决定、监督考察等不同职权的检察官都需阅读卷宗、熟悉案情,增加了检察院内部案件移送环节,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中的重复性劳动。而在“一体化”模式下,社会调查、处遇决定、监督考察等工作均由同一检察官承担,减少了案件移送环节,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性劳动。目前,在我国基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机构普遍人员不足的背景下,“一体化”就成为附条件不起诉权力配置的最优选择。第二,有利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专业性强,它不仅要求检察官谙熟法律,还要求其知晓教育学、心理学等专业知识;不仅要求检察官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还要求其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一体化”模式可让检察官在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中积累实践经验、提升专业水平,有利于未成年人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第三,有利于对被附条件不起诉人采取有针对性的处遇措施。如前所述,附条件不起诉作为一种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处遇措施,可避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贴上罪犯“标签”,有利于犯罪特别预防。但这要求办案人熟知案件事实和未成年人个人情况。由同一检察官承担社会调查、处遇决定、监督考察等职权,有利于其尽早、全面、详细地知悉案件事实和未成年人情况,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有针对性的处遇措施。正是基于上述因素,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附条件不起诉权力配置主要采取“一体化”模式,而没有采取“分立化”模式。
(二) 附条件不起诉的实践图景:适用率低与选择性适用
通过对东北三省检察院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实证调研发现①,其存在适用率普遍极低和选择性适用的问题。这些问题与附条件不起诉中的权力配置不无关系。
1. 适用率极低
以2013年为例,H省各级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535件887人,其中,适用附条件不起诉仅14人,占比1.58%。Q市为该省第二大地级市,下辖7区9县共16家基层检察院,仅有N市(县级市)检察院对3名未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其他检察院均未开展附条件不起诉。J省各级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532件1 209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仅24人,占比1.98%。N省各级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 049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仅55人,占比 2.68%。[7]从调研来看,附条件不起诉存在适用率极低的问题。适用率低不利于发挥附条件不起诉的应有功能,无法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适用率低的重要原因在于,职权高度集中导致附条件不起诉任务繁重,而趋简避繁的自然理性,会让检察官选择少用或者不用附条件不起诉。
2. 选择性适用
J省下辖某县检察院2013年受理审查起诉百余起刑事案件中,仅在一聚众斗殴案中对3名未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3人全部为在校学生。N省S市S区检察院2013年审查起诉50余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仅在一故意伤害(重伤)案中对4名未成年人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其中3人为在校学生,另一人则为本市户籍。H省H市检察院2013年至2014年附条件不起诉6件8人,其中在校学生5人。从调研来看,附条件不起诉存在选择性适用问题。适用对象多为在校学生、在本辖区有固定工作或居所人员。而对外籍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即使符合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条件,也会拒绝适用,这有悖于对未成年人平等保护。附条件不起诉的选择性适用,与其权力配置模式不无关系。检察院既要决定是否适用附条件不起诉,也要承担监督考察工作,这就会让其在决定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时更多地从监督考察便利性来考量,而忽视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平等保护和教育优先。
三、附条件不起诉中的裁量权控制
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决定》明确推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一体化”模式,现在绝大多数检察院都设专门机构或人员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体化”模式扩张了检察官适用附条件不起诉中的裁量权。裁量是实现个别化正义不可或缺的工具。由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个性差异、行为多样,检察官享有广泛裁量权,有利于确定个别化处遇措施。但裁量权越大,滥用风险越大。附条件不起诉在实践运行中的适用率极低和选择性适用,与检察官巨大裁量权不无关系。因此,有必要适当控制检察官在附条件不起诉中的裁量权。
(一) 裁量权限定:强化适用刚性,细化考察措施
限定就是要确定裁量权的界限并防止裁量超越界限。[8]附条件不起诉中的裁量权主要体现在程序启动以及监督考察上,因此,对检察官裁量权的限定主要需从这两方面着手。
首先在程序启动上,应建立“以适用为原则,以不适用为例外”的程序启动制度。所谓“以适用为原则,以不适用为例外”,是指只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符合刑诉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条件,就应当没有裁量余地地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只有在特定例外情形下,才可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而附条件不起诉作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处遇措施,是贯彻该原则的重要制度。若对符合刑诉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条件的未成年人案件,检察院仍可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就意味着未成年人只能面临被定罪量刑,这恰恰是对“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的悖离。因此,附条件不起诉在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已经决定了其应当以适用为原则,而以不适用为例外。
有实务界和理论界人士认为我国附条件不起诉条件苛刻、范围狭窄,主张在立法上扩大其适用范围。[9]该主张直接源于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率低的现实。但若不了解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率低的真正原因,而仅在立法层面扩大其适用范围,则并不必然带来其适用率的上升。刑诉法第271条第1款将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五、六章规定犯罪,可能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体现了立法的谨慎性。由于该刑罚要件是宣告刑,而非法定刑,这就决定了实践中50%以上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都符合该条件。比如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2011年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30件303人,其中判处1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为170人。[10]因此,现有立法能保障附条件不起诉在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适用率。其适用率低主要原因在于检察官裁量权过大,具体表现在检察官对应当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亦可裁量性地决定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检察官在裁量是否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时,考虑了许多法定条件之外的不合理因素,比如工作便利性、未成年人是否为在校生、未成年人有无固定居所等等。这些不合理因素直接阻碍了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因此,为提高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率,使“教育为主”原则真正得以贯彻,有必要建立“以适用为原则,以不适用为例外”的程序启动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可在司法解释中明确,只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符合刑诉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条件,就应当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只有在特定例外情形下,比如未成年人累犯、未成年人系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等,才可不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缩减检察官在程序启动中的消极性裁量权,强化附条件不起诉适用刚性。
其次在监督考察上,应细化对未成年人处遇措施和义务负担。刑诉法第272条第3款规定了四项监督考察措施,要求在所有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中须同时适用,但缺乏针对犯罪类型、原因、个人状况等具体因素的考量,难以实现考察措施个别化原则的要求,导致检察官裁量权过大。以“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为例,“遵守法律法规”是所有公民都须履行的基本义务,即使立法不将其规定为考察措施,未成年人也有义务遵守。个别化原则要求,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性格特点、家庭状况、社会交往等情况,确立有针对性的考察措施。刑诉法中缺乏这种个别化考察措施的规定,会让检察院在适用附条件不起诉中缺乏可遵循的依据;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则无法确立对自己行为的合理预期。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97条规定了包括完成戒瘾治疗、心理辅导、公益劳动、赔偿被害人损失、特定行为禁令等六项有针对性的考察措施,但仍然有待细化。可将附条件不起诉中对未成年人的监督考察措施分为四类:①保护措施。主要包括戒瘾治疗、精神治疗、心理辅导或其他适当之处遇措施。可以根据被附条件不起诉人的情况,提供包括衣服、食品、住宅等暂时救助措施。这些保护措施,旨在向未成年人提供物质、心理、技能等帮助,改善其生存状况,减少其犯罪倾向,帮助其回归社会。②被害人赔偿。赔偿被害人具有恢复性司法因素,可实现对被害人权利救济,也有利于培养未成年人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③作为负担。比如包括向公益团体、社区等提供义务劳动。作为负担,可避免下层群体的未成年人因经济困难而降低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可能性。④不作为负担。比如禁止驾驶、禁止饮酒、禁止出入网吧等特定场合、接触特定人员等等。不作为负担行为类型较多,但并非针对某一特定犯罪适用全部不作为负担,而应根据犯罪类型、原因、个人状况等因素选择适用一项或者数项。
(二) 裁量权建构:适用规则完全公开,具体个案有限公开
建构在于控制裁量权行使方式,其核心是公开,“公开是专断的天敌,是对抗非正义的盟友。”[8](108)公开的前提是掌握足够信息,足够信息也是应对公众质疑的必要前提。检察院在适用附条件不起诉中所作各项决定,与法院所作刑事判决,虽然在实体内容上存在相似之处,但作出决定的程序却存在本质区别。附条件不起诉中的决定程序,缺少裁判中立、两造对抗的基本构造,其本质上是单方行政决定程序。这种决定程序具有书面性、非公开性的特征。非公开性虽有利于减少未成年人回归社会障碍,有利于在实体结果上对未成年人保护,但却在程序上缺少了对检察官裁量权控制,不利于对未成年人进行程序性保护。因此,附条件不起诉运行中,需强化对检察官裁量权的制度建构:首先,需公开已制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实施细则,这样有利于指引附条件不起诉裁量权实施,有利于实施过程中外部监督。其次,赋予检察院在适用附条件不起诉中的权利告知义务,强化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保障。未成年人社会经验不足、法律知识欠缺,多数并不知晓附条件不起诉,这就要求检察院在维护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方面承担更为积极的义务,赋予其权利告知义务。再次,可在附条件不起诉中引入听证程序。听证程序可让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侦查人员等利害关系人享有表达意见的机会,增强附条件不起诉公开性、正当性与权威性。在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中,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适成年人在场权[11],弥补未成年人诉讼能力的不足。虽然,从保障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出发,不宜将附条件不起诉运行程序和决定结果向社会完全公开,但有限度地公开则很有必要。这种公开的底限,就是须让利害关系人、合适成年人参与其中,对他们公开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程序、决定和理由。
(三) 裁量权制约:取消事前行政审批,强化事后监督制约
制约是权力主体之间相互制衡、约束以防专断。常见的制约是做出最初行动之官员的上级,该上级反过来可能还会受官僚结构中的上级制约,还包括同一级的同事、利害关系人、立法机构、新闻媒体制约。[8](160-162)不少国家在附条件不起诉中都确立了法院的司法审查机制,比如德国。我国刑诉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应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意见,就体现了对检察官裁量权的制约。公安机关对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有权要求复议。若公安机关意见未被接受,还可向上一级检察院提请复核。被害人对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可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被害人也可不经申诉,而直接向法院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则检察院不能适用附条件不起诉,应当起诉。上述规定体现了对附条件不起诉的事后监督和制约。
实践中,很多检察院对附条件不起诉案件实行三级评估审查,即办案检察官、部门负责人、主管检察长分别评估审查。这是一种行政化“科层式”权力制约模式。这种制约方式有其优点,但也存在弊端。通过上下级科层制约,强化了对检察官裁量权制约,但它要求在每件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中都需事先取得审批,手续繁琐、工作量大,使得很多办案人不愿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我国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率低的问题突出,在提高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率的进路下,将“科层式”权力制约作为控制检察官裁量权的主要方式,未必是最佳途径。因此,有必要优化附条件不起诉中裁量权制约模式,取消事前“科层式”行政审批,强化事后监督制约。对于侦查机关复议、被害人申诉应认真审查,必要时可通过听证方式给予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侦查人员、被害人阐述观点的机会,对审查后处理结果予以充分说理,并向上述人员送达。事后审查机制,是一种非常态化制约机制,它只有在被害人、侦查人员提出异议时才会启动,因此,既能实现对检察官裁量权的有效制约,也可大大降低附条件不起诉工作量。
注释:
① 调研详情见闵春雷等:《东北三省检察院新刑诉法实施调研报告》,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33-53页。其中,关于附条件不起诉调研详情见谢登科:《困境与出路:附条件不起诉适用实证分析》,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45-149页。
[1] 孔令泉, 张建勇.“行善代刑”引来情与法之争[N]. 民主与法制时报, 2010-07-06(A02).
[2] 徐静村. 刑事诉讼法学[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1:231-232.
[3] 兰耀军. 论附条件不起诉[J]. 法律科学, 2006(5): 121-129.
[4] 谢登科.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3): 104.
[5] 徐昀.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与运用——两种心理学的视角[J]. 当代法学, 2011(4): 102-105.
[6] 郎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M].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2: 473.
[7] 谢登科. 困境与出路:附条件不起诉适用实证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 145-149.
[8] 肯尼斯·卡尔普·戴维斯. 裁量正义[M]. 毕洪海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59.
[9] 韩红, 杨蕾.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完善[J]. 学术交流, 2013(1):83.
[10] 黄洁. 程序复杂附条件不起诉遭“冷遇”[N]. 法制日报,2013-05-09(5).
[11] 谢登科. 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出路——基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110-115.
[编辑: 苏慧]
Centralization and balance: Power allocation in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XIE Dengke
(School of Law,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The system of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has centralized many powers in procuratorate, such as public prosecution, judge, social investigation,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It has deviated from the basic idea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counterbalance in modern prosecution. From the analysis of logic, there are two models of power allocation in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including integration model and separation model. Either model has its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juvenile procuratorate in China has applied the integration model, so prosecutors have great discretion in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Discretion would facilitate to individualize the treatments in juvenile with the risk of abuse though.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prevent abuse, it is necessary to define and restrain the discretion in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conditional non-prosecution; the allocation of powers; discretion; supervision and investigation
D915.3
A
1672-3104(2016)01-0083-06
2015-10-19;
2015-12-15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刑事简易程序实证研究”(15CFX031);吉林大学廉政建设专项研究课题“纪检监察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2014LZY017)
谢登科(1980-),男,湖北随州人,法学博士,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司法数据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