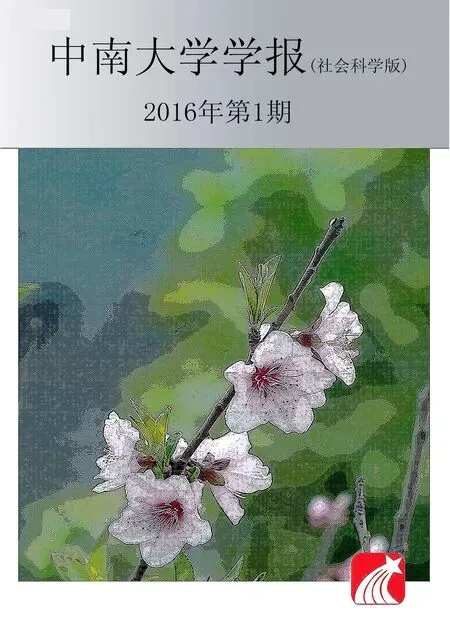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李长银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李长银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幸德秋水的《基督抹杀论》是“一部战斗的无神论著作”。经朱执信的绍介和“狸弔疋”(刘文典)的翻译,该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非基督教运动中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如若将考察的视线从非基督教运动转向当时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不难发现该书中的生殖器崇拜学说还为当时的民国学人如钱玄同、周予同、郭沫若等考察上古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由此来看,《基督抹杀论》可谓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非基督教运动;上古史研究
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马采先生翻译的《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杀论》,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据该书“出版说明”说,“今天重译、出版这部无神论著作,不仅是为研究日本近代思想史提供基本文献,而且相信它对批判宗教有神论,宣传无神论,也会发生应有的战斗作用。”[1](出版说明2)所谓重译,因为该书早在1924年即由北京大学出版部翻译出版过,译者署名“狸弔疋”。不过,商务编辑部方面似乎并不知道这位译者的真实身份,以及该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等相关情况。而这些情况实际上是这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就是这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名”之所在。因此,本文力求在爬梳当时文献的基础上,对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等相关情况进行一番初步的探讨。
一、《基督抹杀论》:“一部战斗的无神论著作”
幸德秋水(1871—1911)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家和先驱人物之一。幸德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广长舌》《社会主义神髓》《基督抹杀论》等撰述中。其中,《基督抹杀论》是幸德“十多年来以著述立身”的“最后文章”“生前的遗稿”。从性质来看,该书又是幸德“最后一部战斗的无神论著作”。[1](出版说明2)
1910年3月,幸德秋水接受友人小泉三申等人的劝告,暂时退出社会活动专心从事著述工作,到相州汤河原养病。在养病期间,幸德秋水开始起草《基督抹杀论》,“以消遣时光”。幸德在致高岛米峰的信中即说:“目前正在研究基督传记,觉得这种东西,也许不至于遭受禁止发售,如有关于印度神话的书,烦请寄来供参考。”[1](113)大概在5月末,该书“只剩下十四、五页就可以脱稿”[1](110)。不幸的是,“到了5月25日,便以信州明科的宫下制造炸弹被发觉为导火线,日本当局以此为借口,蓄意把事件扩大化,把从1908年以来和幸德秋水有过接触的几乎全部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二十六人提出起诉,捏造事实,构成所谓‘大逆事件’。”[1](130)直到11月9日,预审作出决定,宣布提交大审院公判。幸德才稍有闲暇,特请借以笔墨,在监房中续写《基督抹杀论》。当时的写作条件十分恶劣,幸德所在的监房是三席之一室,绝无一点火气,所以此书的剩余部分是幸德“借着从壁顶上的小铁窗透过来的微光,耸动着病骨,呵着冰冻的手笔写下来的”[1](1)。《基督抹杀论》不愧是一部战斗的无神论著作!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据幸德秋水在《基督抹杀论·自序》中所言,该书“殆不及当初计划之一半”,而且“论究考证尚失之于简疏,次序行文亦不免于芜杂”。不过,幸德自信“我国从来学者论客,从事基督及基督教的研究者虽大有其人”,但“还未闻有否定作为历史人物的基督的存在,断定十字架是生殖器标志的变形”,因此决心将该书“托付于二三亲友,将其付印出版”。[1](1-2)
从“以消遣时光”到“凿壁偷光”,再到不顾“叙说简疏”而决心付印,幸德秋水将生命的最后时光大半耗费在了这部《基督抹杀论》上。因此,这里有必要简要交代一下该书的“趣旨目的”。根据幸德秋水在《基督抹杀论·绪论》中的说法,当时的日本“正处在国民旧道德的基础已开始动摇,而新伦理的注意还未确立”,而基督教在日本“传道虽然为日尚浅,信徒尚属少数,但在思想界的感召力,却比从来的神、儒、佛教更为显著和强大”,因此探讨“基督何许人”不仅是“摆在哲学家、历史家、宗教家书桌上的问题”,实在又是“对一般国民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实际上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简要言之,该书的目的之一是摆脱基督教权的束缚。[1](4)
不仅如此,当时的有志之士早已看出《基督抹杀论》的实际指向是日本天皇。本来,受国家主义思想影响的幸德秋水在1905年之前还虔诚地崇拜天皇,是议会道路的忠实信徒,并想通过议会选举,使工人阶级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票,依靠天皇实现“一君万民”的社会主义。但面对天皇政府一系列的残酷镇压,开始认识到所谓“日本是东方最文明的国家”的虚伪性,其“天皇观”发生了动摇,因而在其接受无政府主义作品与无政府主义者之后,迅速转向无政府主义,并提出“日本式”的“直接行动论”。[2]而所谓“基督抹杀论”,实质上就是以否定基督的实在,断定基督教为迷信的内容作为假托的最后的“天皇抹杀论”。
遗憾的是,尽管《基督抹杀论》的出版得到了幸德秋水友人堺利彦、高岛米峰的大力帮助,可说是“费尽了种种劳苦和心思”,但由于幸德秋水在1911年1 月24日即被执行了绞刑,以致未能看到该书的出版。不过,或使这位已逝的哲人略感欣慰的是,《基督抹杀论》得到了时人的好评。田冈岭云在《回忆最后的离别》中表示,只要《基督抹杀论》这本书存在,幸德秋水的名字就可以永久不灭。[1](110)高岛米峰在《幸德秋水与我》中则指出,该书“完全是宗教史上的议论,不但一点都不含有所谓危险思想,而且议论痛快,行文悲怆,尤其是否定作为历史人物的基督的存在,断定十字架为生殖器的变形,刺骨剜肉,把世界的大圣基督剥得几乎体无完肤。当然这里不少是借用西方人研究的成果,但作为邦人的著作,却不妨可说是破天荒的奇书”[1](112-113)。不仅如此,该书出版之后,可谓畅销一时,出版一个月内七次重版,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二、《基督抹杀论》与中国非基督教运动
事实上,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自己的国度,还对域外的近代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论者在考察该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情况时指出:“幸德秋水的这本遗著,一直等到10多年后,国内再掀社会主义高潮,1924年的时候才与国内读者见面。”[3](202-203)今按《基督抹杀论》中译本确实出版于1924年,并或与“国内再掀社会主义高潮”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更加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非基督教运动(1922-1927)的产物。
不过,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在中译本出版之前的一些传播情况。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内最先介绍《基督抹杀论》一些观点的,应该是中国早期革命党人朱执信(1885—1920)。1919年12月25日,朱执信在《民国日报》发表《耶稣是什么东西?》,文章引用《基督抹杀论》所言向来宗教的教主都有十二个大弟子是应天上十二宫之作,以及十字架是男性生殖器变形的说法,大肆渲染,并得出“耶稣是口是心非、偏狭、利己、善怒、好复仇的一个偶像”的结论。[4]此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宗教的产物,因此发表之后尤其在非基督教运动期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反对者在报刊上撰写专文进行批驳,赞成者则将之视为反基督教的经典之作,被印成各种小册子进行散发。《基督抹杀论》亦随之得到了国人的注意。时任金陵神学院教授、《金陵神学志》主编的王治心即在一篇文章中说:“好几年前读过朱执信先生的遗著《耶稣是什么东西?》,中间说起日本幸德秋水氏的话,并且引用他所著《基督抹杀论》里的材料。”[5](1)张仕章则说:“讲到幸氏的《基督抹杀论》,我在三年前曾经看见朱执信在他所做的那篇《耶稣是什么东西》当中引证过的。”[5](2)由此来看,幸德秋水的《基督抹杀论》早在中译本出版之前,就已通过朱执信《耶稣是什么东西?》一文的宣传,开始在近代中国迅速流传。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朱执信《耶稣是什么东西?》一文毕竟只是略引了《基督抹杀论》中的一些观点,不能使国人对该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以致时人表示“究竟不知道所谓《基督抹杀论》者,是一本什么样的书”[5](1)。《基督抹杀论》中译本的出版则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1924年12月,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发行,译者署名“狸弔疋”。这显然不是译者的真实姓名。前已指出,根据《基督抹杀论》重译本的“出版说明”,译者马采先生及商务印书馆编辑部方面似乎并没有“破译”出“狸弔疋”的真实姓名。更为离谱的是,一位幸德秋水研究专家将“狸弔疋”误作为“狸吊正”。[3](203)事实上,早在《基督抹杀论》于1924年出版之际,“狸弔疋”的真实身份就成为了一个谜。《基督抹杀论》一书的批评者张仕章即没弄清楚“狸弔疋”的真实姓名,认为“是假托伪造的”,所以无法向译者问难质疑。[5](3)因此,对于外界来讲,继《基督抹杀论》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之后,该书的中文译者究竟是谁,成为了一桩悬案。
不过,对于与译者交往密切的人来说,这根本算不得上是什么悬案。1925年1月3日,《钱玄同日记》载:“幸德秋水之《基督抹杀论》,已由叔雅译出,今日购得一本。”[6]这里的“叔雅”,即是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刘文典的字。这一“发现”,还可以从周作人的回忆中得到印证。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共四卷,其中第四卷为《北大感旧录》,其中就涉及刘文典。书中有言:“刘叔雅名文典,友人常称之为刘格阑码,叔雅则自称狸豆乌,盖狸刘读或可通,叔与菽通,尗字又为豆之象形古文,雅则即是乌鸦的本字。”[7]周作人、刘文典同受业于章太炎,周作人对刘文典自称“狸豆乌”的解析可谓入目三分,心知其意。根据周作人的提示,“狸刘读或可通”,但至于“狸弔疋”中的“弔疋”是否由“豆乌”而来,周氏没有言明。但按图索骥,“疋”有“疏”义,又同“雅”,比如《尔雅》亦作《尔疋》。如此来看,“狸弔疋”的真实身份即是刘文典。①
接下来有必要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即刘文典为什么要翻译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这一点,时人尤其是基督教徒看得格外清楚。王治心说:“现在‘非基督教同盟’为要借用推翻基督教的武器底缘故,便有北京大学一位捏名叫什么‘狸弔疋’的滑稽家,从已经禁止出版的日本破书堆中找出了十五年前的炮弹壳当武器——想做一笔投机生意,把他翻译过来。”[5](1)张仕章说得更为明确:“我们真想不到在现今中国的知识阶级中竟有人把十五年前幸德秋水所著的《基督抹杀论》从废纸堆里寻了出来,译为汉文,‘以作非基督教运动’的利器!”[5](2)“我以为他的目的,无非要拿幸氏的‘遗著’来做一种宣传‘非基督教运动’的工具,——或不过是一种‘投机事业’罢了!”[5](10)由此来看,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中译本可以说是非基督教运动的产物。
1922年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会议召开的消息先期传出,很快激起一股反对的浪潮。2月26日,上海一些青年学生为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大会在北京清华学校开会,邀集“各校同志”召开组织筹备会议,决定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3月4日,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上议定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章程》。上海方面点燃的反教思想火炬不久便传到了北京。3 月11日,北京大学一批青年学生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3月21日,“非宗教大同盟”发表宣言。这一系列举动立即引起了新文化运动中大部分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关注,并引发了关于“信教自由”的论战。根据现有资料,刘文典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场论战,但却以翻译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这样一种方式推动了非基督教运动。
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中译本出版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仅被列为“青年必读书”②,而且“已经到了全中国每个智识阶级手里”,成为了非基督教者手中的利器。这就引起了基督教徒的恐慌。张仕章说:“不料现在竟有人把这本书(指《基督抹杀论》——引者注)的全文译出,又拿‘非认历史上人物基督之存在,断定十字架为生殖器表号之变形’做广告。这岂不是要使中国的思想界忽然混乱,又使全国的青年人大受迷惑么?”[5](3)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殷雅各则说:“近来北京大学出版部刊行一书题名《基督抹杀论》是由日本译出的,是幸德秋水在明治四十三年著的,幸德秋水后因谋杀天皇之罪被处死刑,听说这书在日本没有声价。但是这中文译本曾经多数中国学生研究,所以基督教会不得不从事辟这书的谬妄。”[8]由此来看,《基督抹杀论》可谓非基督教运动期间一个“最大的劲敌”。[9]
“劲敌”当前,基督教徒不但没有临阵脱逃,反而开始有组织地对《基督抹杀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1925年6月,一部旨在批评《基督抹杀论》的著作出版发行,此即《评基督抹杀论》。该书的性质可以说是一部论文集,汇集了数位基督教人士尤其是“中华基督教文社”成员的相关批评。③第一篇是王治心的《发刊的所以然》,认为《基督抹杀论》的基本观点“是历史上过去的陈迹”,因而该书仅是一个“骇得煞人的炮弹壳”。第二篇是《青年进步》总编辑范皕诲的《序论一》,指出《基督抹杀论》“大半根据西方之旧说”。第三篇是留学美国基督教文字事业促进社总干事沈嗣庄的《序论二》,论证无论《圣经》还是《圣经》以外的书都指向“耶稣是历史的人格”,因而《基督抹杀论》的否定看法是不能成立的。第四篇是沪江大学毕业硕士历任中学教授张仕章的《我对于狸译基督抹杀论的批评》,通过详细的分析得出结论,即《基督抹杀论》“无论从外观上或是内容上看来——早已变成过去时代的残骨遗骸了!”第五篇是时任金陵神学社会学教授彭长琳的《基督抹杀论书后》,指出即使四福音书记事如《基督抹杀论》所言存在若干矛盾之处,但与事实之真伪毫无关系;并认为四福音书并非如《基督抹杀论》所论证是第二世纪以后之人所撰述,而坚持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之亲笔,且著于第一世纪;最值得关注的是,该文指出《基督抹杀论》在论证基督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默证”问题,即“当时文书中,不载其事,不能武断其即无此事也”。进而言之,一方面“基督在世时,罗马史家之记载,除塔西塔斯与西乌陀尼亚斯二人外,多已湮没,无法稽考”;另一方面,“罗马之鄙视犹太乃人所共知,且基督之言行,以及其所交往之朋友等,皆史家所不屑记录”。第六篇是时任金陵神学哲学教授张孝侯的《读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书后》,概要地批评了《基督抹杀论》的方法与结果,比如引用的证据不过是拾几个人的牙慧,关于基督教起源的看法是一种出于诬蔑的心理而下的武断结论等。第七篇是当时尚是金陵神学学生周博夫的《基督可以抹杀吗?》,旨在说明基督确实是历史上的实在人物,即使基督可以抹杀,《基督抹杀论》亦不足作抹杀基督的兵器。第八篇同样是金陵神学学生包少芳的《读基督抹杀论后》,旨在分析《新约》之编纂成立虽然如《基督抹杀论》所言当在第四世纪底后半期,但现代所有新约的最早古卷早在主后三周底初叶已有原抄本,因而不能据此否定历史上的基督。客观而论,上述批评虽存在一些疏阔乃至谬误之处,但足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基督教徒应付《基督抹杀论》的攻击。
继《评基督抹杀论》之后的1925年1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辟基督抹杀论》一书。与前者不同,该书是一本专著,著作者为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殷雅各,译者为聂绍经。该书除《绪言》外,共分为十八章,前三章旨在指明《基督抹杀论》存在三大明显的错谬,分别是“根据无学者价值的理论”“引用荒僻的证据”与“作自相矛盾的论断”;第四章至第十六章则主要建设性地以“历史的证据”证实耶稣基督的存在,并陈述耶稣优美的品格和道理;最后一章则进一步给出了作者信基督的三个理由,分别是基督能满足我们寻求上帝的欲念、基督使善占胜利、基督能赐予我们止于至善的力量。今按该书虽然存在某些宗教信仰的成分,但论证逻辑清晰、材料翔实,有效地消除了一些基督教徒因受《基督抹杀论》影响而产生的疑惑。
上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概述《评基督抹杀论》《辟基督抹杀论》著作者们的基本观点,主要是想从一个侧面说明《基督抹杀论》对基督教徒构成的威胁。此外,这里还应当指出的是,《基督抹杀论》并未因《评基督抹杀论》和《辟基督抹杀论》的出版而停止在近代中国的流传。换言之,《评基督抹杀论》和《辟基督抹杀论》的著作者们并没有说服非基督教者,这些非基督教者仍然将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视为足以给基督教以致命一击的锐利武器。总之,幸德秋水的《基督抹杀论》,由于契合了中国当时的非基督教运动,在近代中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三、《基督抹杀论》与民国上古史研究
事实上,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范围并不限于非基督教运动,还波及了当时的上古史研究。这还得从《基督抹杀论》中的一个基本观点说起。《基督抹杀论》共分为十二章,其中第七至九章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基督教的起源”进行了集中探讨,并提出“十字架是生殖器标志的变形”的观点。幸德秋水曾在该书《自序》中自信地表示,这一观点至少在日本国内是“发前人所未发”。不过,在批评者看来,这一特见“虽未之前闻”,但实出于幸德秋水“诬蔑的心理”而下的“武断的结论”。[5](94)即使是引用过这一观点的朱执信在《耶稣是什么东西?》中也指出,“这个推定,还不能作为十分真确。”[4]然而,如若将观察的视线由非基督教运动转向当时的上古史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学说的重要影响。
国内学术界最先受《基督抹杀论》这一观点启发而进行古史研究的可能是钱玄同。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努力》周报所附月刊《读书杂志》第九期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在该文“按语”部分,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此文一经发表,立即在当时的人文学界产生了巨大震动。同年6月10日,钱玄同于《读书杂志》第十期发表《答顾颉刚先生书》,响应顾颉刚的文章。文章讲到六经的性质问题。关于《易》的性质,钱玄同指出:“我以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时代底东西;‘乾’‘坤’二卦即是两性底生殖器底记号。”[10]有论者指出,钱玄同的这一看法“使这项人类生活史上的习俗进入原始哲学领域”[11]。
根据现有资料,钱玄同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看法,一方面源自清人罗慎斋《诗说》中的一个“创见”④,另一方面即是受了《基督抹杀论》的启发。早在1973年,胡秋原指出,钱玄同“知道日本有一个幸德秋水,写过《基督抹杀论》,说基督无其人,十字架代表生殖器崇拜”[12]。这一看法是有证据支持的。前已指出,朱执信曾于1919年12月25日发表《耶稣是什么东西?》,该文在曾引用过这一观点,而《耶稣是什么东西?》在非基督教运动中被印刷成各种小册子发行。而钱玄同当时积极介入了非基督教运动[13],看过这篇文章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是故,钱玄同在《基督抹杀论》中译本出版的第一时间即购买了该书。
钱玄同虽然在国内学术界破天荒地揭出了《易经》的根本还含有生殖器崇拜的意味,但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论证。继钱玄同之后,畅发此旨的是周予同。1927 年9月5日,周予同在《一般》杂志发表《“孝”与“生殖器崇拜”》,为“生殖器崇拜”在伦理道德中找到了立足之地。文章指出,先秦诸子握有思想界权威的,只有道、儒、墨三家。墨家只承认孝为社会普通伦理之一,而孝在道家的哲学中几乎没有些微的地位。与墨家和道家不同,儒家不仅承认孝在社会伦理上的实际价值,而且给以哲学上的重要地位。推测其中缘由,儒家之所以特别重孝,起初也不过为到达或宣传其大德目——仁——之方法或手段。不过,这绝不是容易实现的,于是儒家利用当时民众的幼稚思想,将初民“生殖器崇拜”的宗教加以修正,使成为“生殖崇拜”的哲学,再由“生殖崇拜”的思想来解释孝和仁。总之,儒家的根本思想出发于“生殖崇拜”。[14]
与钱玄同相近,周予同在文章中同样没有给出其观点的来源。从现有资料来看,周予同的这些观点,一是来自上述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中关于《易经》性质的看法⑤,二是来自《基督抹杀论》。周予同文章后面加的“附注”为我们提供了最初的线索。根据这一“附注”,周予同此文曾“举以语”李石岑,而李石岑“间采以实其所著之《人生哲学》”。[14]李石岑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与周予同是同事,所著《人生哲学》出版于1926年。今按此书有数处直接引用或借用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关于“十字架是生殖器崇拜标志的变形”的看法,尤其一再强调“孔子的学说是从‘生殖崇拜’的思想出发”。[15]如此来看,周予同在文章“附注”中所言不虚。而周予同关于孝与生殖器崇拜的看法与《基督抹杀论》的学源关系亦由此略见一斑。
继周予同之后,将生殖器崇拜与上古史研究这一课题推向新高度的是郭沫若。1928年11月25日,郭沫若以“杜衎”的化名在《东方杂志》发表《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一文,文章指出:“八卦的根柢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像男根,分而为二以像女阴,所以由此而演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16]这一看法实际与前述钱玄同、周予同的观点基本一致。1931年5月,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由上海大东书局影印出版。其中收录《释祖妣》一文,文章考释出“祖妣为牡牝之初字,则祖宗崇祀及一切神道设教之古习亦可洞见其本源”。据甲骨文的字形,祖为男根,妣为女阴。原始社会知母不知父,“然此有物焉可知其为人世之初祖者,则牡牝二器也。故生殖神之崇拜,其事几与人类而俱来。”[17]这一看法不仅开辟了考释文字的新途径,而且以甲骨实物证实了中国古代存在生殖崇拜的问题。有论者指出,郭沫若是生殖器崇拜说的提倡者,与其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期是有关的。而幸德秋水作为一个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在当时的日本有着广泛的影响,郭沫若受其著述尤其是《基督抹杀论》的影响一点都不奇怪。[18]
从钱玄同发表《答顾颉刚先生书》到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的出版,短短数年间,生殖器崇拜说开始成为当时学人研究上古史的一个利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引钱玄同、周予同的文章先后被收入到《古史辨》,郭沫若则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等文章集结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古史辨》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皆是在民国上古史研究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对民国史学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在这些作品的示范下,生殖器崇拜说开始广泛地被应用到中国上古史研究中。毋庸讳言的是,之后这些作品更多借鉴的是上述学人的看法与西方生殖器崇拜说,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的影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不过,溯本追源,《基督抹杀论》不能不说是启发当时国内学人借以生殖器崇拜说研究上古史的一个源头。
四、结论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等情况的初步梳理与考察,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基督抹杀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当时中国的反宗教思潮尤其是非基督教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经朱执信《耶稣是什么东西?》一文的绍介,该书的基本观点开始在近代中国迅速流行。继之凭借“狸弔疋”(刘文典)的翻译,该书成为了非基督教者手中的利器,给基督教徒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因而招致了基督教方面的批评。如若将考察的视线从非基督教运动转向当时的上古史研究,不难发现该书中的生殖器崇拜还为当时的民国学人如钱玄同、周予同、郭沫若等考察上古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由此来看,幸德秋水《基督抹杀论》可谓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注释:
① 《刘文典全集》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和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联合出版,该书共四册,其中第四册收录了刘文典的三种译作,分别是《进化与人生》《生命之不可思议》《进化论讲话》;《刘文典全集》修订本由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第四册在前书的基础上增收《告全日本国民书》译作一种。但由于《刘文典全集》编委会未能考订出“狸弔疋”即是刘文典,因而未能将《基督抹杀论》收入其中。
② 1925年初,《京报副刊》举行了一次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活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参与活动的安世徽和李宜春即将幸德秋水的《基督抹杀论》列入“青年必读书”。
③ “中华基督教文社”,原名为“中华基督教文字事业促进会”,1924年成立于上海。该社“发扬基督教文学,提倡基督教事业,探索真理,研究学术为宗旨”。
④ 1923年2月9日,钱玄同在致顾颉刚的信中说:“清乾隆时,湘潭罗典有说《诗》之作,中多怪话,如《东门之枌》中‘视而如荍’,他把‘荍’字解作男子生殖器。这话见于民国元年《中国学报》之江叔海底笔记中。”详见顾颉刚:《古史辨》第1册,第70页。
⑤ 顾颉刚于1926年6月12日即将《古史辨》第一册邮寄给周予同(详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1,第801页),而周予同不久即在同年7月11日的《文学周报》第233期发表《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周予同在此文中表示从封面一直看到附录。由此可见,周予同是看过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的。
[1] 幸德秋水. 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杀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2] 杨孝臣. 论幸德秋水[J]. 历史研究, 1982(4): 161-173.
[3] 张陟遥. 播火者的使命: 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4] 谷小水.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朱执信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498-505.
[5] 沈嗣庄. 评基督抹杀论[M]. 南京: 南京金陵神学志理事处,1925.
[6] 钱玄同. 钱玄同日记·中[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610.
[7]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下[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343.
[8] 殷雅各. 辟基督抹杀论[M]. 上海: 上海广学会, 1925: 1.
[9] 评基督抹杀论[J]. 时兆月报, 1925(7): 29.
[10] 钱玄同. 答顾颉刚先生书[J]. 读书杂志, 1923(10): 1-3.
[11] 常金仓. 二十世纪古史研究反思录[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111.
[12] 胡秋原. 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M]. 台北: 学术出版社,1973: 83-84.
[13] 刘贵福, 闵融融. 钱玄同与 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J]. 社会科学战线, 2011(10): 245-247.
[14] 周予同. “孝”与“生殖器崇拜”[J]. 一般, 1927(9): 14-33.
[15] 李石岑. 人生哲学[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7: 272.
[16] 杜衎(郭沫若). 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J]. 东方杂志,1928(11): 73-93.
[17] 郭沫若. 甲骨文字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2: 40.
[18] 廖名春. 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J]. 原道, 1998(4):110-129.
[编辑: 颜关明]
The spreading and influence of Kotoku Shusui’s Erasing Christ in the modern China
LI Changyin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99, China)
Kotoku Shusui's Erasing Christ is a book of battle for antheism With Zhu Zhixin's introduction and Liu Wendian's translation, the book exerted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f we turn the research angle from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to that of ancient histor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theory of genitals's worship in the book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many schola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cluding Qian Xuantong, Zhou Yutong and Guo Moruo. From this perspective, Erasing Christ is well worth being considered one “famous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world.”
Kotoku Shusui; Erasing Christ;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history
B97
A
1672-3104(2016)01-0220-06
2015-05-05;
2015-06-11
李长银(1986-),男,辽宁绥中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