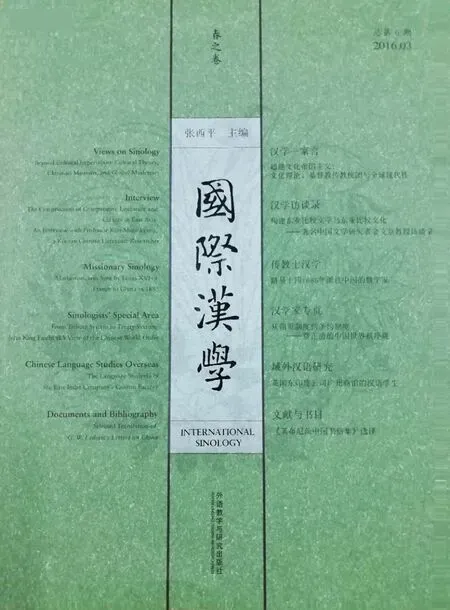从校勘学角度看霍克思《红楼梦》英译本
□ 范圣宇
现有的《红楼梦》英文全译本共出版两种,即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外文出版社,1978—1980)和霍克思(David Hawkes, 1923—2009)、闵福德(John Minford, 1946— )译本(企鹅出版社,1973—1986)。这两个全译本各自所根据的底本,差别是很大的。①外文出版社1999年出版了杨宪益、戴乃迭译本的汉英对照版,收入“大中华文库”, 2003年又出了“汉英经典文库本”,但实际上这两个本子的中英文并不完全对照。此外,彭寿(Bramwell seaton Bonsall,1886—1968)译本在香港大学图书馆网页上有电子版,见http://lib.hku.hk/bonsall/hongloumeng/index1.html,但至今尚未出版印行。据“译者前言”,他所使用的底本是上海广益书局印行的本子,极少数地方根据其他本子也做了修订。彭寿并未提及出版年份,但他是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这一译本的,见彭寿之子杰弗里(Geoffrey Weatherill Bonsall,1924—2010)2004年7月的说明,http://lib.hku.hk/bonsall/hongloumeng/title.pdf。本文尝试借用史学家陈垣在《校勘学释例》卷6第43“校法四例”中所提出的方法论,来考察霍克思如何组织《红楼梦》英译本的底本。霍克思未必读过陈垣的《校勘学释例》,但他所用的校勘方法却与陈垣先生的观点深自契合,这实在是个很有趣的现象。②霍克思、闵福德翻译而笔者负责中文版本校勘的五卷本《红楼梦》汉英对照双语版已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2012年7月出版,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本子,笔者以为不妨称之为“霍闵本”。校勘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似乎也值得与感兴趣的读者一起探讨,另文再谈。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只涉及霍克思译的前八十回。
《校勘学释例》原名《元典章校补释例》,因为陈垣认为“《元典章》写刻极精,校对极差,错漏极多,最合适为校勘学的反面教材,一展而错误诸例悉备矣”。③陈垣:《校勘学释例·重印后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5页。换句话说,他是拿《元典章》作为批评的靶子。我们选择从校勘学的角度来讨论霍克思的《红楼梦》英译本,原因恰恰相反,因为这个杰出的译本所体现的,多半是成功的例子。这不论是对剖析像《红楼梦》这样版本繁复的作品的译本,或是讨论译者的创造性,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中,胡适把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称为“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校勘之学起于文件传写的不易避免错误。文件越古,传写的次数越多,错误的机会也越多。校勘学的任务是要改正这些传写的错误,恢复一个文件本来面目,或使它和原本相差最微。校勘学的工作有三个主要的成分: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④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见《校勘学释例》,第1页。有意思的是,霍克思的《红楼梦》英译本恰恰可以用来解释胡适对校勘学的总结。霍克思的英译本所体现出来的他在翻译之前的校勘工作,确实说明他发现了底本的错误并且加以改正①霍克思在多种场合都说过,他翻译的底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版。如 David Hawkes, Introduction to Vol.1, The Golden Days.London: Penguin Books, 1973, pp.45-46, 再如 David Hawkes, “The Translator, the Mirror and the Dream”, in Classical,Modern and Humane: Essays in Chinese Literature.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59, 还有Interview with David Hawkes, Conducted by Connie Chan, at 6 Addison Crescent, Oxford, Date: 7th December, 1998.。本文要尝试的则是胡适总结的校勘学工作的第三个成分:证明所改不误。
我们知道,《红楼梦》的版本大体可以分成脂本(抄本)、程本(刻本)两个系统:脂本(算上已佚的靖藏本)共12种,现存的脂本止于前八十回,而且其中没有一种本子是完整的,程本又有程甲本、程乙本之分,所以至少有14种。如果要系统地校读整理这些本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霍克思在英译本第1卷《枉入红尘》导言中说:“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品在作者死后将近三十年还未出版,而且以多种版本在世上流传着,其中没有一个本子可以说是绝对正确的,这多少是件让人惊讶的事。”②David Hawkes, Introduction to Vol.1, The Golden Days, p.15.《红楼梦》版本问题的特殊性,使得版本校勘成为研究者与译者以及研究译本的学者回避不了的题目。
从校勘学的意义上说,霍克思译本比杨宪益译本更值得讨论,这是因为霍克思汇校参考的本子,显然要比杨宪益多。③关于杨宪益、戴乃迭使用的底本究竟是哪个本子,杨先生自己的说法就不甚一致。他在英译本“出版说明”里说是有正本;但在《银翘集》中却说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庚辰本,见如水:《记杨宪益先生》,《银翘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第126页);而在他的回忆录《漏船载酒话当年》中,他说的是吴世昌先生帮助他与戴乃迭参照了多种手抄本和印刷本,择善而从,编成翻译的本子,这样看来他的译本又是一个“百衲本”了。综合这几种说法,并仔细校读译本,笔者认为他在翻译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是有正本,并主要参照庚辰本对其中的讹误做了校正。也就是说,“出版说明”的说法是最准确的。当然,译者也声称“我们的翻译根据其他版本对抄写原稿的人犯的某些细微错误或缺漏也做了修正”。他们所做的修正,主要是底本中明显不通顺的错别字或缺漏之处。然而在原文叙事的时间、地点以及细节上的前后矛盾,则极少改动。他们对版本问题,显然没有霍克思那么关注。根据香港岭南大学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2000年出版的霍克思《〈红楼梦〉英译笔记》,以及现任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编撰的《霍克思文库》(未刊稿)④霍克思曾将生平收藏的约4500册中、英、日文图书捐赠给国立威尔士图书馆,其中包括他在翻译《红楼梦》过程中使用过的各种资料及词典、参考书。吴建中先生在威尔士大学攻读图书馆学博士学位时,曾被威尔士图书馆邀请去为这些图书编目,吴先生于是编撰了《霍克思文库》(Hawkes’ Collection)一书,该书尚未出版,由上海图书馆收藏。,霍克思使用过的底本主要有《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俞平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王希廉评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台北:广文书局,1977)、《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北京:文学古籍出版社,1955年影印庚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影印己卯本)、《百廿回红楼梦》(台北:青石山庄出版社,1962年影乾隆壬子年木活字本)、《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影印有正本)、《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这几种。⑤霍克思译本第三卷于1980年出版,因而在此之后影印的版本都不可能是他使用过的,1980年出版的本子他在翻译过程中用到的可能性极小。不少论者引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新校注本(以庚辰本为底本)来讨论杨霍两家译文,严格地说总是不甚恰当,因为这与旧通行本(1964年版)在文字上仍有不少出入。详见吕启祥:《〈红楼梦〉新校本校读记》及《〈红楼梦〉新校本和原通行本正文重要差异四百例》,载《红楼梦开卷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3—307、332—404页。至于用1993年出版的蔡义江校本或者其他本子来讨论霍克思的英译,恐怕差距更大。仔细校读霍克思的英译本和这几种本子,我们会很容易发现,霍克思笔下的《红楼梦》并没有严格依照上述某一种版本,而是综合杂糅了各本之所长(当然偶尔也有选择不当的时候),因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面貌。⑥由于探讨抄本(脂本)如何过渡到刻本(程本)这个过程难度极大,况且甲辰本直到1989年才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不论霍克思还是杨宪益在翻译过程中都不可能参考过这个本子,因此我们可以忽略不计。至于程甲本,也是直到1992年才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因此也可以忽略不计。同理可知其他本子如蒙府、列藏、舒序本等等,也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
中文《红楼梦》的脂本和程本虽说并非完全对立,但界限是分明的,文字出入较大。俞平伯在汇校《红楼梦》的过程中就曾说过:
由于抄本既零乱残缺,刻本又是被后人改过的,所以最初就把目的放在两个地方:(一)尽可能接近曹著的本来面目。(二)使它的文字情节能够比较的完整可读。乍一看,这两个目的可以统一的。……然而仔细推求,在整理工作的过程中,时常发生困难。……汇合这些过录传抄的本子,与原稿的真面目是有距离的。照现在的情形说,只可以说总比刻本接近一些罢。所以就上述第一个目的说,整理这些抄本还是有意义的。但如兼顾第二个目的,则矛盾更多。这些抄本,姑且算它原本,假如文词不顺,情节不合,我们要把不顺的使它顺,不合的使它合,那就必须改。在这抄本群里改来改去,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假如不成,就不得不借重转后或更后的刻本,以至于用校者自己的意见。无论改得成绩如何,反正已非曹著的真面目了。主要的困难就是这样。①俞平伯:《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序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2页。
由于霍克思翻译之前需要汇校出一个相对优秀的本子,所以他遭遇的困难是同样的。不过,由于现有资料的匮乏以及《红楼梦》成书过程中的舛误,要呈现“曹著的真面目”, 不论对任何人来说,恐怕都殊非易事。而如果要呈现“霍译的真面目”,倒确实是有蛛丝马迹可循,汉英对照双语版的汇校,正是朝这个方向的努力。如果我们套用俞平伯的话,校勘霍克思所用的中文底本,目的在于使汉英对照本“尽可能接近霍译的本来面目”。
霍克思的译本,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现有英文版里的第一个“百衲本”。霍克思曾在《译者、镜子及梦》这篇文章中谈道:“我想,今天没有人能反对这种观点,那就是《红楼梦》是由许多不同版本经过了许多人的编辑,在某种程度上综合而成的。”②David Hawkes, “The Translator, the Mirror and the Dream,” in Classical, Modern and Humane: Essays in Chinese Literature, p.175.他的言下之意是说《红楼梦》本来就是综合体,所以他在翻译的时候考虑如何将众多底本的优点集中在一起也是无可厚非的。当然,众多底本孰优孰劣本来就有争议,霍克思的选择也只是一家之言,并非定论,他曾经坦承:“就这部特定的小说而言,在不同的版本之间所做的几乎任何选择,都要求译者对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做出决定—关于小说作者的身份、小说的演变、评论者的身份、最初编辑的可信程度、他们编辑的性质,等等。”③Ibid., p.159.探讨他对这些底本是如何进行选择的,无疑是个有趣的题目。本文借用陈垣的方法论,来考察霍克思在翻译过程中究竟做了哪些校勘工作,对我们有些什么启发。
胡适说:“校勘的需要起于发现错误,而错误的发现必须倚靠不同本子的比较,古人称此学为‘校雠’。”④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第3页。《红楼梦》版本的问题也不是霍克思一开始翻译就注意到的,他曾说:“但后来我才开始对本子之间的差异等问题感兴趣,原因是你开始认真工作的时候,所有的问题,比如故事的不一致,情节的混乱,本子之间的差异等等,都冒出来了,当然,那些书和资料也都是逐渐出版的,我很迟才得到那个乾隆钞本。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没怎么考虑版本问题,开始的时候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本子和俞平伯的八十回校本,后来书才慢慢多了。”⑤Interview with David Hawkes, Conducted by Connie Chan, at 6 Addison Crescent, Oxford, Date: 7th December, 1998.霍克思言下之意说他意识到版本问题也有一个过程,而且他主要参考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版的本子与俞平伯八十回校本,这也是他在翻译的时候(约1970—1980)所能见到的最流行的两种本子。
陈垣在“校法四例”中提出了校勘学的四种基本方法,霍克思在汇校翻译的过程中都使用到了。下面我们逐一来考察:
一、对校法:“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⑥陈垣:《校勘学释例》,第129页。
不论是霍克思在翻译的过程中组织底本,还是我们现在来校读英译本与中文各版本之间的异同,首先使用的当然是对校法。这其实是排列组合的关系,不论是译本与A本,译本与B本,译本与C本……,或者A本与B本,A本与C本……之间的差异,都要通过对校法来校勘。霍克思的译本底本之所以讨论起来麻烦,是因为他在脂本与程本之间寻求一条“中间路线”,而程本与脂本之间的主要差异,可以参看吕启祥详细对照人民文学出版社20世纪50年代旧通行本和20世纪80年代新校注本之间的差别,写成的《〈红楼梦〉新校本校读记》一文。①吕启祥:《红楼梦开卷录》,第273-307页,另可参看此书附录《〈红楼梦〉新校本和原通行本正文重要差异四百例》,第332—404页。她对新旧版本所分别依据的脂本、程本之间的优劣大体上作了比较客观的判断,并说:“无论是阅读、欣赏、评论、研究,都离不开一个好的本子,校订和整理《红楼梦》新校本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假如我们要讨论《红楼梦》的译本,当然也离不开一个好的底本,所以探讨霍克思如何校勘众多版本,才能更清楚地说明其译本的价值所在。霍克思曾说:“我得纠正一件事。我没有编辑手稿。许多很好的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果你把这功劳归给我,那我就太可笑了。”他一再声明自己“没有做任何编辑。如果你把它叫做编辑的话,那不过是从不同的本子里挑选而已。我开始的时候没怎么在意。如果你认真研究的话—恐怕不值得你那么做—但如果你仔细对照我的译文和各种版本的话,你也许会发现我的译文与一种流行的本子更接近,而随着我越来越了解它,也越来越意识到其中的问题,越往后我就越折中了。”②Interview with David Hawkes, Conducted by Connie Chan, at 6 Addison Crescent, Oxford, Date: 7th December, 1998.
这里所谓“流行的本子”,指的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版。霍克思显然十分谦逊,然而,从不同的本子里挑选他认为更出色的段落,不是编辑又是什么呢?霍克思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以一种十分学术化的态度来处理版本问题的”,“我不过是折中处理。我只是要组织一个比较好的故事……这不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做的事情。”③Ibid..优秀的译本不一定是严肃的学者才能做的事情,霍克思也许是认为这样编辑《红楼梦》的底本来进行创造性的翻译,可能不会被学院派严肃认真的学者所认可。但无论如何,“霍克思决心向好友韦理(Arthur Waley, 1889─1966)看齐,为真正的读者而作,为真正爱读小说的读者而译。”④闵福德著,赖慈芸译:《功夫翻译、翻译功夫》,载刘靖之主编:《翻译新焦点》,香港: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96页。他花了很大功夫去校勘各种本子来组织自己的底本,目的也就是要为读者提供一个流畅可读的译本。
二、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⑤陈垣:《校勘学释例》,第130页。
按常理,抄本讹误应该比刻本多,因为手写传抄过程中脱漏增删的可能性更大。但其实刻本也有种种问题,如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版整理者就说:“底本因系活字本,误字、脱字、颠倒、错行的情形很多”。⑥《关于本书的整理情况》,《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版,第2页。而程本对脂本的校改,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因为原有的讹误里面,有些得到了更正,有些继续保留,还有些是原本对的反而改错了。总的说来,脂本原有的讹误大致可以分成三种:一是叙述时间上的前后矛盾;二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前后矛盾;三是情节前后矛盾。
时间是结构一篇小说的相当重要的因素,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但未能完全避免叙述时间上的缺陷。地点也是叙述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曹雪芹声称“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目的是要为其真实性打掩护。脂砚斋早就点明:“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⑦《甲戌本凡例》,见陈庆浩编:《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1页。正如霍克思所说,由于曹雪芹“故意采用隐藏家庭历史的手法—混合辈分,把南京换成北京,等等—这使他在年龄、日期、地点和时间的推移上特别容易出错”。①David Hawkes, Introduction to Vol.1, The Golden Days, p.41.《红楼梦》的细节前后照应之处极多,脂批常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云云。洪秋蕃曾在《红楼梦抉隐》中说:“《红楼》妙处,又莫如用笔之周。他书序事,顾此失彼,或挂一漏万。《红楼》无此弊,虽琐碎极不要紧之事,亦必细针密缕,周匝无遗。”②冯其庸校注:《八家评批红楼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97页。虽然有些夸张,基本上却符合事实,但有时作者却也有疏于照应之处,情节上出现了明显的前后矛盾。
霍克思对这些细微之处的矛盾曾经表示过无可奈何:“至于年龄和日期—几乎是所有关于数字的方面—翻译者真拿雪芹没办法,我怀疑,也许他就是不善数学—那种总是数不清零钱的人。”③David Hawkes, Introduction to Vol.1, The Golden Days, p.42.脂本原有的讹误在霍克思的笔下大都得到了纠正。霍克思是真正从读者的角度出发来翻译的,他的译本在努力创造更合理的叙述氛围。
例1 第十四回:
昭儿道:“二爷打发回来的。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日巳时没的。二爷带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爷灵到苏州,大约赶年底就回来。二爷打发小的来报个信请安,讨老太太示下,还瞧瞧奶奶家里好,叫把大毛衣服带几件去。”
读者单看这段话,没有什么毛病。但与前后文有关的部分一联系起来,就有问题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198页校记[四]注明:“这个日期有讹误。林如海病重、黛玉回南,时在冬底。④原文是“谁知这年冬底,林如海的书信寄来,却为身染重疾,写书特来接黛玉回去。”这也是秦可卿病的‘这年冬底’。秦氏死于次年春。第十三至第十五回写秦氏丧礼,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弄权铁槛寺。贾琏携黛玉回京,以及凤姐为贾琏接风,恰值秦氏丧期刚过,时间当然也是这年的春天或暮春。这里说:‘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日巳时没的’,时间显然不合。至于‘大约赶年底回来’,‘把大毛衣服带几件去’,矛盾也是明显的。因无别本可据,现仍从原本。”
王希廉也看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若林如海于九月初身故,则写书接林黛玉应在七八月间,不应迟至冬底。况贾琏冬底自京起身,大毛衣服应当时带去,何必又遣人来取?再年底才自京起程到扬,又送灵至苏,年底亦岂能赶回?先后所说,似有矛盾。”⑤王希廉:《红楼梦摘误》,见《红楼梦(三家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页。姚燮则说:“暇尝涉览二十四史,其前后相矛盾者,不一而足,况空中结撰,无关典要之书耶!今条著其可疑者如左,非敢毛吹之求,亦以明读者之不可草草了事云尔。……第十二回云如海冬底病重,而十三回昭儿自苏回云如海九月初三巳时没,不甚斗笋。”⑥姚燮:《读红楼梦纲领·纠疑》,见冯其庸校注:《八家评批红楼梦》,第18页。
那么,霍克思怎么处理呢?他在此处悄悄把九月抹去了,贾、林二人回来的时间也做了改动,变成了:
‘The master sent me, ma’am.Mr.Lin died on the third at ten in the morning and the Master and Miss Lin are taking him to Soochow to be buried.They expect to be home by the end of the spring.The Master told me to bring back the news and to give everyone his regards,and he said I was to ask Her Old Ladyship for instructions.He also told me to see if you were getting on all right, ma’am; and he said would I take some fur-lined gowns back with me for winter wear.’ (I, 280)⑦I, 280表示企鹅版霍克思译本第1卷,第280页。下同。
这样,译者不点明林如海死于几月,模糊了原文的叙述时间,同时把年底改成了春末,纠正了原文在时间上的讹误带来的叙事上的不合情理。⑧有意思的是,吴轩丞在1924年上海《小说世界》第5卷第1期上发表《红楼梦之误字》,声称他购得一部抄本《红楼梦》,其中“冬底”的“冬”字,作“八月”二字,于是“不觉恍然大悟”。他感叹说“毫厘千里,不知费读者几许冥想也。”这倒是解释了小说中的矛盾,聊备一说,附记于此。可惜不论霍克思还是杨宪益似乎都没有见过这篇短文,否则他们的译文又多了一种可能。见吕启祥等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
例2 第七十五回:
果然贾珍煮了一口猪,烧了一腔羊,备了一桌菜蔬果品,在汇芳园丛绿堂中,带领妻子姬妾,先吃过晚饭,然后摆上酒,开怀作乐赏月。
“汇芳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作“会芳园”。①也许是程乙本整理者(高鹗?)注意到了这里与前文的矛盾,把“会芳园”改成了“汇芳园”。但会芳园原本是宁府中的花园,因建省亲别墅,第十六回中贾蓉曾回贾琏说:“老爷们已经议定了,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地大,可以盖造省亲别院了。”之后“先令匠人拆宁府会芳园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可见会芳园已经成了后来赐名大观园的省亲别墅的一部分。如何此处又出现会芳园的旧名?戴不凡、李希凡等人都曾提出过这里存在的问题,李希凡说:“如此种种,大观园研究者还可挑剔出不少错讹的描写,假定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大观园,有些路向肯定是难以走通的,这无需替曹雪芹辩护。……然而,大观园又终究是‘空中楼阁,纸上园林’,尽管作者‘胸中大有丘壑’,甚至也可能有过详细的草图,它毕竟是个艺术的境界,不能也不该成为实地考证的对象。”②顾平旦编:《大观园》,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54页。这种观点很正确,但这些矛盾在翻译过程中却无法回避。杨宪益译本十六回、七十五回均译作 Garden of Concentrated Fragrance, 但霍克思却在文中做了说明,添译成:
…he conducted her and the little concubines and Jia Rong and Jia Rong’s wife to the Bosky Verdure Pavilion where it was all laid out.This was in the All-Scents Garden, as they continued to call the little remnant still left them after the main part was incorporated in Prospect Garden.(III, 497)
霍克思补充说明宁府会芳园大部分并入大观园之后,贾珍等仍按旧名称呼其剩余部分。如此一来在此处出现会芳园便仍然合情合理。
例3 第四十五回:
周瑞家的磕头起来,又要与赖嬷嬷磕头,赖大家的拉着方罢。然后他三人去了,李纨等也就回园中来。
杨宪益的译文未作任何改动。但此处作者显然忘记了本回中描写赖嬷嬷唠叨了半日之后,还有一句:“正说着,只见赖大家的来了,接着周瑞家的张材家的都进来回事情。”因此熙凤屋里当时的客人除了李纨和姐妹们外,应当是四个人。霍克思戏称曹雪芹为“我们健忘的作者”③霍克思:《〈红楼梦〉英译笔记》,香港:岭南大学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2000年,第161页。,因此他把这句翻成了:
She wanted to kotowed to Mrs Lai as well, but the old woman reached forward and prevented her.The four woman then left, and Li Wan and the girls went back into the Garden.(II,394)
这样就与前文吻合起来了。
三、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④陈垣:《校勘学释例》,第131页。
其实《红楼梦》的翻译底本,需要运用到他校法的时候多半是作者自己引错,或者是传抄过程中因为抄者粗心而出现错别字,甚或是作者本人故意虚写。有些地方我们现在也无从查证霍克思究竟参考了其他什么书籍或资料,但他根据他书校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版这一底本,则是确凿无疑的。
例1 第五回,秦氏房中陈设的描写:
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宝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版此处无校记,但1982版92页校记[四]:“寿昌公主,各本同。惟舒序本作‘寿长公主’。按,含章殿下卧榻,系寿阳公主(刘宋武帝女)梅花妆事。此处究竟是笔误、抄讹,还是有意虚写,无从断定,故仍其旧。”霍克思的译文直接改成了“寿阳”,译作:
At the far end of the room stood the priceless bed on which Princess Shou-yang was sleeping out of doors under the eaves of the Han-zhang Palace when the plum-flower lighted on her forehead and set a new fashion for coloured patches.(I, 127)
例2 第十八回,宝钗的话:
唐朝韩翊咏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蜡干”都忘了么?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版211页校记[六]:“‘韩翊’,诸本同。按韩翊一作韩翃,各书歧出。‘冷烛无烟绿蜡干’系钱珝诗,非韩翊。今姑存原文。”庚辰本作钱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260页校记[二〇]:“‘钱翊’为‘钱珝’之误。‘冷烛无烟绿蜡干’乃钱珝《未展芭蕉》诗首句。……各抄本均误作‘钱翊’,今改。”这样看来这首诗的作者应该是钱珝才对。因此霍克思的译本采纳了这个意见,直接译成了Qian Xu (I, 368)。
例3 第十四回:
现今北静王世荣年未弱冠,生得美秀异常,性情谦和。
北静王这个人物的名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版写作“世荣”,但庚辰本、戚序本、俞校本均作“水溶”。他叫“世荣”或“水溶”似乎关系并不大,霍克思的译文是Shui Rong,为什么又改成“水溶”呢?因为他觉得“最好叫北静王‘水[溶]’而不是‘世[荣]’(从抄本而非人民[文学]),因为已经有太多Shih了。”①霍克思:《〈红楼梦〉英译笔记》,第12页。
例4 第五十三回:
贾蓝之母娄氏带了贾蓝来。
庚辰本、戚序本、俞平伯校本“贾蓝”作“贾菌”。此处到底是贾蓝还是贾菌,根本就不影响故事情节。考虑到贾蓝和贾兰的英译都是Jia Lan,而贾兰又是李纨的儿子,在小说里也多次出现,所以霍克思此处径直改成了Jia Jun,还特意说明是 Bao-yu’s former classmate (II, 581),来与第九回的内容呼应。
由此可见,人名虽是小事,作家笔误或者有意虚写,也不见得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霍克思考虑的却是对英语读者来说,如何减轻他们的负担:“如果这类修改超出了一个纯粹的翻译者的范畴,我只能说我是出于对西方读者的关照。且不提这部未完成而且编辑也不够完善的小说中的诸种矛盾之处,单是要记住这几百个发音极其困难的人物名字对他们来说就已经负担很重了。”②David Hawkes, Preface to Vol.2, The Crab-Flower Club.London: Penguin Books, 1977, p.20.
最后一个例子也许会有争议,不过也可以看见霍克思的用心:
例5 第十七回:
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若亦用‘泻’字,则觉不妥。
霍克思译文作:But on second thoughts it seems to me that though it may have been all right for Ou-yang Xiu to use the word “gushing” in describing the source of the river Rang, it doesn’t really suit the water round this pavilion.(I, 329-330)
此处到底是酿泉,还是让泉?欧阳修《醉翁亭记》曰:“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让泉也。”因后文又有“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所以泉名又写作“酿泉”。 但其实这二者的繁体写法十分接近:讓泉—釀泉,极有可能是形近而误。霍克思显然是查证了一番,最后决定用“让泉”的。③今天在互联网上搜索到的图片,赫然就是“让泉”。见滁州市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chuzhou.gov.cn/art/2010/9/12/art_285_1626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0月22日。据说因为位于滁州醉翁亭畔的两峰之间,有两峰让出之意,故名“让泉”。而现存《醉翁亭记》的早期版本和碑帖均作“让泉”。霍克思当年可没有互联网,恐怕也没法亲自去滁州核实,只能说明他确实核对过了《醉翁亭记》早期版本、碑帖或者其他资料,才做出这一改动的。
四、理校法:“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④陈垣:《校勘学释例》,第133页。
霍克思译本中用到理校法的所在,比较明显的有两处:
例1 第四十八回:
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见香菱笑吟吟的送了书来,又要换杜律。
此处的“一日”,看似最平常不过,但霍克思的译文是“次日”:
Next morning, just as Dai-yu had completed her toilet, a smiling Caltrop walked in, holding out the volume of Wang Wei and asking to exchange it for a volume of Du Fu’s heptasyllabics.(II, 458)
香菱学诗学得再快,也不太可能一个晚上就把王维的五言律全都读完了,而且还领略出下文所说的“三味”来。这里似乎是霍克思弄错了,把“一日”理解成“次日”了。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这其中包含着译者大费周折的思考。根据霍克思的《〈红楼梦〉英译笔记》,他对此处与文本中其他相关之处的观察如下:
所有的文本在10月-12月的日期上都似乎是混乱的
香菱10月14日去黛玉处学诗,整夜读王维
“一日”她回来换书,她写了两首诗,夜里梦中写了第三首
第二天新来了七个人,宝玉说“明儿十六”
一两天后(?)李纨说“昨儿的正日已自过了”
五十回贾母说:“这才是十月里头场雪”
诗社集会前后,作者告诉我们说新年快到了
四十八回中有两处香菱在户外作诗,好像也没有比她在房里穿更多的衣服。不可能比十月更晚。为什么?
建议
把“一日”改成“次日”
把“明儿十六”改成“今儿十六”
假设“昨儿的正日”是十一月初二
把“这才是十月”改成“这才是十一月”①霍克思:《〈红楼梦〉英译笔记》,第169—170页。译文也就是按照他自己所提供的建议翻译的,这几处译文分别是:
明儿十六,咱们该起社了。By the way, it’s the sixteenth today.It’s the day for our poetry club meeting.(II, 471)
想来昨儿的正日已过了,再等正日又太远。
We’ve already passed the date for our regular meeting, and we don’t want to wait until the next one comes around, because it’s too far ahead.(II, 480)
贾母笑道:“这才是十月里头场雪,往后下雪的日子多着呢,再破费不迟。”
‘We’re only just into the eleventh month,’ said Grandmother Jia.‘There’ll be plenty more snow yet and plenty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aking advantage of your kind offer.’ (II, 505)
对照前面的“一日”,读者不得不承认,霍克思把它译成“Next morning”也有他的道理,他并不是理解错了原文,而是出于对文本前后叙事时间一致的考虑,在尽量弥补原文的漏洞。
例2 七十回中点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共有三处:
(1)如今仲春天气,虽得了工夫,争奈宝玉……
(2)咱们的诗社散了一年,也没有人作兴。如今正是初春时节,万物更新,正该鼓舞另立起来才好。
(3)大家议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为“桃花社”,林黛玉就为社主。
一回之内接连出现三个不同的时间,显然是叙事时间上出了偏差。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版无校记,但1982版1000页校记[二]则说:“上文谓‘如今仲春天气’此处又曰‘正是初春’下文又有‘明日乃三月初二日’语,已是暮春三月了,时序混乱,因无别本可据,仍之。”
按如此顺序发生的故事,认真的读者未免要被搞糊涂了。霍克思的译文做了相应的更改,除了点明时间的“明日乃三月初二日”英译本不方便作任何改动以外,霍克思把其他两句中的仲春、初春的字眼都笼统地用spring 来翻译,这样原文的时序混乱就被遮盖过去了:
(1)Now spring had come and at last there was time for a meeting.(III, 376)
(2)‘It’s more than a year now since our Poetry Club met,’ said one of them, ‘yet in all that time no one seems to have felt the urge to get it going again.Springtime, when everything in nature is renewing itself, seems an appropriate time for reestablishing it.’(III, 378)
(3)After some discussion it was decided unanimously tha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revived Poetry Club should be held the very next day, which as it happened, would be the second of the third month.The club was to be renamed ‘The Peachflower Club’ and Dai-yu was to be its president.(III,380)
胡适总结陈垣先生校勘学的根本方法是:“先求得底本的异同,然后考定其是非”。①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第11页。从上面所引的例子来看,霍克思在翻译《红楼梦》的过程中,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需要校勘各种不同版本,各取所长,来组织成他翻译工作的底本,这显然是一件耗时费力的事。他自己曾说:“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北京的翻译者们翻了一百二十回,但头两卷却一直根据的是以手稿为根据的版本。我也不太明白美国的批评家们的立场是什么,他们的评论以一百二十回本为基础,同时却承认他们不清楚甚至不知道高鹗补充部分的性质。在我看来,二者只能取其一。”②David Hawkes, “The Translator, the Mirror and the Dream,” in Classical, Modern and Humane: Essays in Chinese Literature, p.160.霍克思的意思似乎是说,如果翻译一百二十回本,总应当照顾到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之间的一致,而评论一百二十回本,也应当分清原作与高鹗续作之间的界限,否则讨论起来就不免前后矛盾。他自己的做法就是先求异同,然后考定是非,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译本的故事读起来不至于前后矛盾,留下破绽。
李学勤曾说:“校勘古书,本身也具有研究性质,不仅是机械性的工作。校勘贵有裁断,从而校本的好坏直接体现着校者的才力学识。”③李学勤:《校勘学概论·序》,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页。用这话来评价霍克思在组织他要翻译的中文底本时所做的校勘工作,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从以上的例子不难看出,霍克思注意到了底本原文的讹误,并按照其他本子加以改正,这正暗合我国校勘古书的传统,也深契陈垣所提出的方法论,而我们的分析也证明他的改动都是有道理的。这对一个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英国汉学家来说,无疑十分难能可贵。傅璇琮说过:“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学问,掌握理论当然是不可少的,吸收一些新方法也是需要的,但我们还应立足于我们自己的学术土壤,要有传统的治学方法的训练,这是一种基本功。校勘就是这种基本功之一,而目前恐怕又是很不为人所看重;不但不看重,大有鄙夷不屑一顾的样子。”④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编余随札》,《唐才子传校笺》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11页。其实汇校整理汉英对照双语版《红楼梦》,就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霍克思这样的大家尚且十分注重版本校勘,我们更没有理由忽视版本校勘在研究《红楼梦》英译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