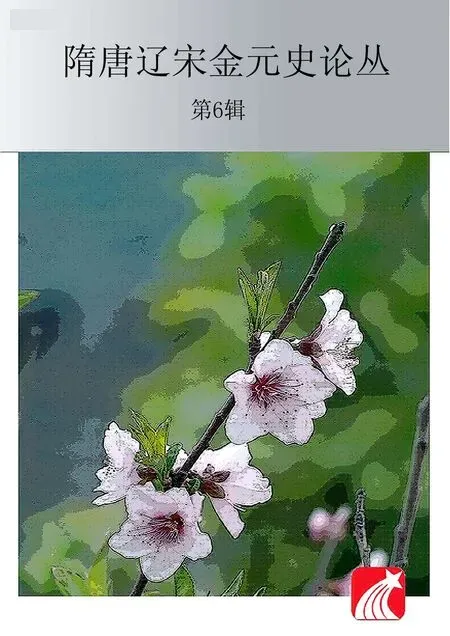五代遼宋金元的“指斥乘輿”罪
王曾瑜
五代遼宋金元的“指斥乘輿”罪
王曾瑜
“指斥乘輿”罪,且不説一般人,就是從事中華古史專業者,只怕也有相當比例者覺得生疏。但如果换一句現代語——“駡皇帝”,大家就都會懂得。明朝高拱解釋説:“乘輿,謂天子也,不敢言天子,故言乘輿也。”*高拱《本語》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49册,861頁。誰要駡皇帝,就算犯了彌天大罪,但也只能稱爲“指斥乘輿”,即指斥了皇帝的座車,避諱用“皇帝”一詞,以示“皇帝”一詞的神聖性。宋朝張浚也解釋説:“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宫闕。是以見君輅馬,必加禮而致恭,蓋不如是,無以肅名分,杜僣亂也。”*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上張浚行狀,《四部叢刊》本。
從古代史籍中搜索,儘管早在秦漢時代已確立了中國特色的帝制,但直到840年後的唐朝,今人方纔在《唐律疏議》中,第一次看到對“指斥乘輿”罪作了法律上的規定。當然,唐律源於隋《開皇律》,但《開皇律》已佚亡。《唐律疏議》卷一《十惡》,確定如今人們常説的“十惡不赦”罪。“六曰大不敬”,其中就包括“指斥乘輿,情理切害”。但疏議又對此作了法律規範和説明:“若使無心怨天”,“不入十惡之條”,“蓋欲原其本情,廣恩慎罰”。同書卷一〇規定,“諸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斬”;“指斥謂言議乘輿,原情及理,俱有切害者斬”;“非切害者徒二年,謂語雖指斥乘輿,而情理非切害者,處徒二年”。同書卷二三又規定:“知指斥乘輿及妖言不告者,各減本罪五等。官司承告,不即掩捕,經半日者,各與不告罪同。”宋理學家程顥對“情理切害”有所解釋,説:“舊言指斥乘輿,言理惡者死。今改曰情理,亦非也。”*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外書》卷一〇,中華書局,1981年,406頁。從上引法律條文看,對“指斥乘輿”罪的處置是極其嚴厲的。
若追溯“大不敬”的刑名由來,《史記》卷九六《申屠嘉列傳》載,他劾奏漢文帝倖臣鄧通:“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同卷《魏相列傳》記載,因“大不敬”罪,“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漢書》卷八九《黄霸傳》説:“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後漢書》卷六〇下《蔡邕傳》載:“下(蔡)邕、(蔡)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經吕强營救,“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髠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漢律源自秦律,故大致可以判斷,在秦漢時,已有“大不敬”、“當死”、“棄市”的刑名,但還没有唐律那樣細緻的規定。
自晉朝以下,歷代都有“大不敬,棄市”的刑名*《晉書》卷五〇《庾旉傳》,中華書局,1974年,1403頁;同書卷六一《周嵩傳》,1660頁。《梁書》一六《王亮傳》,中華書局,1973年,268頁;同書卷五三《伏暅傳》,776頁。《魏書》卷七七《辛雄傳》,中華書局,1974年,1691頁。《北齊書》卷四七《宋遊道傳》,中華書局,1972年,654頁。《北史》卷四二《劉逖傳》,中華書局,1974年,1551頁。,在此不必贅述。《隋書》卷二五《刑法志》記載,北齊河清三年(564),定“齊律”,“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内亂。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北周保定三年(563),定“大律”,“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内亂之罪。凡惡逆,肆之三日”。隋律則“又置十惡之條,多採後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内亂。犯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這就是前述唐律“十惡”之所本。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法律無非是在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之一,“經濟關係反映爲法原則”,“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84頁。。“在歷史進程中,掠奪者都認爲需要通過他們自己硬性規定的法律,來賦予他們憑暴力得到的原始權利以某種社會穩定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451頁。。法律必須維護階級社會的階級統治秩序,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當然,由於國家的公權力是從原始社會的公共事務管理轉化而來,部分法律也有管理公共事務規則的功能。這與前者是互相融合和滲透的,一般並不互相排斥。
就“指斥乘輿”罪的制訂而論,它無非是服務於進一步强化皇權,並將此種功能推進到了極致,其階級性和專制性極爲鮮明。故“指斥乘輿”的罪名也必然被後代所繼承。宋人因避宋太祖祖父趙敬名諱,在《宋刑統》卷一中,將“大不敬”罪改成“大不恭”罪。《元史》卷一〇二《刑法志》照抄《唐律疏議》,其“十惡”之六“大不敬”中,就有“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同書卷一〇四《刑法志·大惡》規定:“諸指斥乘輿者,非特恩,必坐之。諸妄撰詞曲,誣人以犯上惡言者,處死。諸職官輒指斥詔旨亂言者,雖會赦,仍除名不敍。”在中國古代史料中,有時也略去“乘輿”兩字,簡稱爲“指斥”罪;“指斥”罪的範圍較寬,不一定全是“指斥乘輿”。
五代是武夫橫行的時代,皇帝的權威下降。軍閥安重榮上表晉高祖石敬瑭,“其表數千言,大抵指斥高祖稱臣奉表,罄中國珍異,貢獻契丹,凌虐漢人,竟無厭足”。但晉高祖無法給他治罪,“憂其變也,遂幸鄴都,以詔諭之,凡有十焉”*《舊五代史》卷九八《安重榮傳》,中華書局,2015年,1524頁。。後周時,得南唐“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爲言”,周世宗大怒,責備南唐使者孫晟,説:“晟來使我,言(李)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將孫晟“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新五代史》卷三三《孫晟傳》,中華書局,2015年,414頁。。後周時,趙守微“本村民,因獻策,擢拾遺,有妻復娶,又言涉指斥,坐決杖配流”,但没有處死,而御史中丞邊歸讜對周世宗説:“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微!”*《宋史》卷二六二《邊歸讜傳》,中華書局,1977年,9070頁。但處事頗能決斷的周世宗仍未採納,大約趙守微雖是“言涉指斥”,而没有確實的“情理切害”證據。
遼朝法律的制訂,當然參照唐律。遼太宗天顯七年(932),“林牙迪離畢指斥乘輿,囚之”*《遼史》卷三《太宗紀》,中華書局,1974年,33頁。。遼聖宗統和十二年(994),遼聖宗“詔契丹人犯十惡者,依漢律”*《遼史》卷一三《聖宗紀》,145頁;卷六一《刑法志》,939頁。。太平八年(1028),“樞密使、魏王耶律斜軫孫婦阿聒指斥乘輿,其孫骨欲爲之隠,事覺,乃並坐之,仍籍其家”*《遼史》卷一七《聖宗紀》,202頁。。可知遼朝確是沿用唐律之“十惡”和“指斥乘輿”罪。遼朝末年,在金朝的攻擊下,燕王耶律淳自立爲帝,他死後,遼天祚帝下詔,歷數耶律淳罪狀,其中有“僣稱帝號,私授天官,指斥乘輿,僞造符寶,輕發文字,肆赦改元”等罪*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以後簡稱《會編》)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9頁。。
宋太祖時,丁德裕在西川,“奏轉運使、禮部郎中李鉉嘗醉酒,言涉指斥。上怒,驛召鉉下御史,案之。鉉言德裕在蜀日,屢以事請求,多拒之,皆有狀。御史以聞,太祖悟,止坐鉉酒失,責授左贊善大夫”*《宋史》卷二七四《丁德裕傳》,9354頁;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一〇開寶二年十二月己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92頁。。開寶二年(969),丁德裕奏張延通“嘗對衆言涉指斥,且多不法事”,又指張嶼爲同黨。“太祖怒,即收延通、張嶼及王班下御史臺,鞫之,延通等引伏。太祖始欲捨之,及引問,延通抗對不遜,遂斬之。嶼、班并内臣王仁吉並杖脊,嶼配流沙門島,班許州,仁吉西窰務”*《宋史》卷二七四《張延通傳》,9355頁;《長編》卷一〇開寶二年十月癸卯,91頁。。
宋太宗發動政變,篡位成功,於太平興國七年(982),舉辦親弟秦王趙廷美獄案。其中有閻密“恣橫不法,言多指斥”,予以處斬*《宋史》卷二四四《趙廷美傳》,8667頁;《長編》卷二三太平興國七年四月丁丑,196頁。。此案又牽連宰相盧多遜,宋太宗親自下詔説他“包藏姦宄,窺伺君親,指斥乘輿,交結藩邸,大逆不道,非所宜言”,但並不處死,而是“配流崖州”*《宋史》卷二六四《盧多遜傳》,9119頁。。太平興國八年(983),宋太宗“斬孟州進士張兩。兩試吏部,不合格,縱酒大駡於街衢中,言涉指斥,游徼吏捕以聞。上怒,故抵於法,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州長吏罰一季俸”*《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三月乙酉,205頁。。此次獄案甚至株連同保的舉人,罰他們“永不得赴舉”,連孟州知州也“罰一季俸”,足見宋太宗的盛怒,完全是法外加罰。他又下制書,説其寵臣弭德超“詬駡同列,指斥朕躬,爲臣若斯,於法何逭”,“配瓊州,禁錮”*《宋會要輯稿(以下簡稱《宋會要》)·職官》七八之二至三,中華書局,1957年。,但没有處死。宋太宗寵信侯莫陳利用,後“京西轉運副使宋沆籍利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怒,令中使臠殺之,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出濘换馬,比追及之,已爲前使誅矣”*《宋史》卷四七〇《侯莫陳利用傳》,13679頁;《長編》卷二九端拱元年三月乙亥,250頁。。宋太宗實行特務政治,柴禹錫和趙鎔“嘗遣吏卒變服,散之京城察事。卒乘醉,與賣書人韓玉鬥毆,不勝,因誣玉言涉指斥。禹錫等遽以聞,玉坐抵法。太宗尋知其寃”*《宋史》卷二六八《趙鎔傳》,9225頁。。在此件冤案中,韓玉顯然被處死。至道時,鄭元輔“詣檢上書,告(趙)自化漏泄禁中語,及指斥非所宜言等事。太宗初甚駭,命(宦官)王繼恩就御史府鞫之,皆無狀,斬元輔於都市”*《宋史》卷四六一《趙自化傳》,13508頁。。
宋仁宗時,劉敞“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鬥,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鞫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爭之,詔以其章下府,著爲令”*《宋史》卷三一九《劉敞傳》,10384頁;《長編》卷一九〇嘉祐四年七月庚申,1749頁;劉攽《彭城集》卷三五《故朝散大夫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權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劉公行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96册,347頁。。
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皇城使、開州團練使沈惟恭除名,瓊州安置,進士孫棐處死。惟恭,貴妃沈氏之弟,故宰相倫之孫。棐,開封人,惟恭門下客也。惟恭以干請恩澤不得志,觖望,嘗爲棐言:‘皇子生,必不久。’語涉咒詛,又假他人指斥乘輿之言以語棐。棐希惟恭意,毎見,輒詆時事,亦嘗指斥乘輿。後又詐爲司馬光陳五事章疏,以示惟恭,詞極不遜。惟恭轉以示人。四方館歸司官張澤得之,以示閤門使李評,評奏之,故敗。棐既伏誅,餘傳寫人皆釋罪”*《長編》卷二一一熙寧三年五月庚戌,1965頁;《宋會要·職官》六五之三二。。此處所謂“進士”,其實只是文士。熙寧八年(1075),“沂州民朱唐告前餘姚主簿李逢謀反,提點刑獄王庭筠言其無迹,但謗讟,語涉指斥及妄説休咎,請編配”。宋神宗特别派遣官員按治,“庭筠懼,自縊死。逢辭連宗室、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等,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詔捕繫(御史)臺獄”。“獄具,賜世居死,李逢、劉育及徐革並凌遲處死,將作監主簿張靖、武進士郝士宣皆腰斬,司天監學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並湖南編管。餘連逮者追官落職,世居子孫貸死,除名,削屬籍。舊勘鞫官吏並劾罪”。此案還“腰斬進士(文士)李侗”等。李逢謀反案是當時一件大案,也並非僅是“指斥乘輿”罪,而株連頗衆*《宋史》卷二〇〇《刑法志》,4998頁;《長編》卷二五九熙寧八年正月庚戌,2432頁,卷二六一熙寧八年三月甲午,2445頁,卷二六三熙寧八年閏四月壬子,2481頁,卷二六四熙寧八年五月甲子,丁卯,丁丑,2484、2485、2490頁。。
元豐四年(1081),宋神宗“詔前追官勒停人、越州山陰縣主簿、太原府教授余行之陵遲處死”。“行之以廢黜怨望,妄造符讖,指斥乘輿,言極切害”。“行之既伏誅,因赦其妻、子”*《長編》卷三一二元豐四年四月壬申,2921頁。。元豐六年(1083),宋神宗“詔涇原路京東第八將梁用、副將趙潛各罰銅二十斤,坐部卒常斌指斥乘輿,語切害,不可録奏,經略司以聞故也”*《長編》卷三三五元豐六年五月乙未,3118頁;《宋會要·職官》六六之二二。。梁用和趙潛僅屬不上報,也受處分,而常斌大約處死。
宋哲宗元祐時,圍繞着前任宰相蔡確的車蓋亭詩案,其實是純屬捕風捉影的冤案,但諫官們,特别是劉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宋史》卷三四五《劉安世傳》,10952頁。,而御史臺官員等主張從輕,最後高太后將蔡確流放廣南新州。王巖叟所寫蔡確責詞,也詬責他“曾不反思,尚兹歸怨,形於指斥,播在歌謡,託深意以厚誣,包禍心而莫測”*《長編》卷四二七元祐四年五月辛巳,4023頁。。
紹聖四年(1097),“田嗣宗坐指斥,抵死”*陳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四,中華書局,2006年,597頁。。此人爲中書侍郎李清臣“姑之子”,李清臣也因此罷政*徐自明著,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一〇,中華書局,1986年,631頁;王稱《東都事略》卷九六《李清臣傳》,《宋史資料萃編》第一輯,文海出版社,1967年,1483頁。。元符二年(1099),“熙河帥种朴敗死”,宋哲宗“爲之震駭,遂復棄鄯州。關中由此大困,開封民有因醉狂語者”,宰相章惇“請論如指斥乘輿法,上特貸死。惇再取旨不已,自是妄言者莫不誅死,然雖多殺不禁也”*《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六建中靖國元年二月,648頁。。章惇的秉性還是相當殘忍,這是他掌政後期,“取旨不已”,以“指斥乘輿”罪濫殺無辜。
宋徽宗即位之初,其弟宋神宗十三子趙似,“以王府史語言指斥,送大理寺驗治,似上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上諫奏,結果鄧鐸因曾自寫 “隨龍人、三班借職鄧鐸”,“伏誅,蔡邸不掛吏議”。但宋徽宗仍“頗以獄詞平反太過,蓋法官(按: 指吴師禮)不肯以指斥切害之罪罪之也”*《宋史》卷二四六《趙似傳》,卷三四六《江公望傳》,卷三四七《吴師禮傳》,8723、10987、10999頁;《東都事略》卷一〇〇《江公望傳》,1547—1548頁;《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六建中靖國元年七月,653頁。。宋制,皇帝登基後,“凡東宫僚吏一概超遷,謂之隨龍”*司馬光《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三八《言郭昭選劄子》,《萬有文庫》本,商務印書館,1937年,502頁。。鄧鐸自稱“隨龍人”,表明他有意參加宋哲宗死後的帝位爭奪,但也確實説不上是什麽“指斥乘輿,情理切害”。
崇寧元年(1102),宋徽宗重新鎮壓反變法派,爲箝制輿論,下令“禁羇置人入京,及諸色人妄議宗廟,指斥乘輿,並許人告,賞錢三千貫,白身與三班借職,有官人轉兩官”*《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六崇寧元年五月,661頁。。
政和元年(1111)到三年(1113),“以泰州李彪作殿試策題及答,語言指斥乘輿及嘲訕大臣等罪”,宰相張商英“以事在赦前,令開封府一面斷放”,張商英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後,又進一步貶責爲汝州團練副使*《宋會要·職官》六八之二九;《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一二,761頁。。北宋晚期,執政安惇之子安郊“坐指斥誅”,因他有“有不欲立上之語,後爲族人所告”*《宋史》卷四七一《安惇傳》,13718頁;《會編》卷二,15頁;洪邁《夷堅支景》卷六《富陵朱真人》,中華書局,1981年,924頁。。
宣和六年(1124)和七年(1125),開封出了兩件奇案。宋徽宗“御樓觀燈”,“從六宫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深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執於觀下,帝怒甚,令中使傳旨治之,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其誰何,略不一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籍。帝大不悦,爲罷一夕之歡,竟不得其何人,付獄盡之”。另一次“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檐向門戟手,出悖駡語,且曰:‘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爲者,乃於獄中盡之”。所謂“悖罵語”,乃是“汝壞吾社稷矣”!*《宋史》卷六五《五行志》,1419—1420頁;《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二九宣和六年正月,752頁。以上兩案其實都是反映民衆對時政的憎惡。
宋欽宗在位的短暫時間内,教坊樂人司文政以“伏闕上書,無理狂悖”,“其言指斥”,“聖旨處斬”,“號令榜於市”*《會編》卷六六,499頁。。
宋高宗登基之初,追究僞楚張邦昌的罪責,説有宫女華國靖恭夫人李氏以養女侍奉張邦昌,並對他“有語指斥乘輿”。宋高宗將張邦昌處死,另“有旨,李氏杖脊,降配〔車〕營務下〔名〕爲妻”*李綱《梁谿全集》卷一七六《建炎進退志總敍》,卷一八〇《建炎時政記》,《李綱全集》,岳麓書社,2004年,1634、1672頁。。
陳東是北宋末年的太學生,曾領導數萬人伏闕上書的愛國群衆運動,因聽到李綱罷相的消息,立即上書,“論李綱不可罷,黄潛善、汪伯彦不可用,乞親征,邀請二帝”,又指責宋高宗“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歸來,不知何以處”*王明清《揮麈後録》卷九,《全宋筆記》第六編第一册,大象出版社,2013年,197—198頁;《會編》卷一一三,825頁;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以後简稱《要録》)卷八建炎元年八月壬午,中華書局,2013年,234頁。。另有士人歐陽澈也上書,“極詆用事者”,並且“語侵宫掖”,指責宋高宗“宫禁寵樂”*歐陽澈《歐陽修撰集》卷七許翰《哀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36—421頁;陳東《宋陳少陽先生集》卷八許翰《哀詞》,《宋集珍本叢刊》第39册,綫裝書局,2004年,175頁;《要録》卷八建炎元年八月壬午,234頁;《宋史》卷四七三《黄潛善傳》,13744頁。,無非是批評皇帝沉湎女色,寵信宦官之類。宋高宗惱羞成怒,遂將兩人處死,其罪名也無非是“指斥”*《梁谿全集》卷一一二《懷澤與吴元中别幅》説,“潁川(陳東)極論二人(黄潛善、汪伯彦),以謂必誤中興,遂置極法”,“潁川之書,〔甚〕明白激切,初無指斥之語。但論此二人,中其要害,故下毒手,以絶來者”。按李綱只怕未必看到陳東上書原文,但反映陳東和歐陽澈的罪名確是“指斥”,見1061頁。。
建炎時,向大猷“受金人僞命,知青州,其出榜文,多指斥,有反狀明白”,無非是譏斥宋高宗的無道,皇帝下詔,“前知濱州向大猷爲臣不忠,屢爲叛逆,移文指斥,罪狀深重,可令越州領赴市曹處斬”*《會編》卷一三一,951頁;《要録》卷二九建炎三年十一月乙丑,674頁。。大將曲端曾題詩説:“不向關中興事業,卻來江上泛漁舟。”後被張浚誣以“指斥乘輿”罪而處死*《宋史》卷三六九《曲端傳》,11493頁;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五《曲壯閔本末》作“不向關中圖事業,卻來江上汎扁舟”,有“圖”、“扁”兩字不同。中華書局,1983年,269頁。,當然是一件冤案。紹興八年(1138),宋高宗“詔内侍羅亶竄海島,永不放還。亶爲景靈宫幹辦官,有營卒章青告其語言指斥”,“刑寺擬私罪徒,勒停”,可知指斥之語肯定不屬“情理切害”。宋高宗卻説:“亶素凶悖不逞,無可恕者,當竄海島。”*《要録》卷一一九紹興八年五月戊戌,2221頁。於法外加刑。
在南宋偉大愛國民族英雄岳飛的冤獄中,據傳言,紹興十一年(1141),岳飛得知張俊、韓世忠等軍在淮西戰敗後,悲憤的心情再也難以克制,自上一年他被迫班師後,一句鬱結半年有餘的心聲奪口而出:“國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又岳飛曾説:“我三十二歲上建節,自古少有。”此語被引伸和篡改爲“自言與太祖俱以三十歲爲節度使”。這兩句話都被定爲“指斥乘輿”的彌天大罪*岳珂《鄂國金佗稡編》卷二四《張憲辨》,《鄂國金佗稡編、續編校注》本,中華書局,1989年,1075—1076頁;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二《岳少保誣證斷案》,中華書局,2000年,701頁;王明清《揮麈録餘話》卷二,《全宋筆記》第六編第二册,鄭州: 大象出版社,2013年,57頁。,爲其“莫須有”的罪名之一。
在紹興和議後的黑暗年代,“指斥乘輿”罪風靡一時,成爲發生此罪案例相當密集的時期,這主要是對宋高宗屈辱和議的詬病和非議。太學生張伯麟在壁上題寫:“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用春秋時代的典故,譏斥宋高宗向殺父之仇屈膝,被判“杖脊,刺配吉陽軍(治今海南崖城)”。與他同案的宦官白鍔也“出言指斥”,被“特刺面,配萬安軍(治今海南萬寧)”*《要録》卷一五一紹興十四年六月丙申,2862頁;《宋史》卷四七三《秦檜傳》,13759頁。。紹興二十一年(1151)十一月,“斬有蔭人惠俊,以指斥乘輿,法寺鞫實,故有是命”*《要録》卷一六二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庚戌,3084頁。。無品武官“進義副尉劉允中棄市,以上書希求恩賞,指斥乘輿,及謗訕朝廷,法〔寺〕鞫實,故抵於法”*《要録》卷一六二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丁巳,3085頁。。“臨安府徑山能仁禪院僧陸清言決脊杖二十,刺面,配廣南遠惡州軍牢城,以清言撰造偈頌,蠱惑士庶,至有指斥語言,於法應絞,特貸之”*《宋會要·刑法》六之三二;《要録》卷一六二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子,3086頁。。這還算是皇恩寬貸者。紹興二十三年(1153),宦官“入内東頭供奉官裴詠除名,瓊州編管,永不放還。詠往盱眙,撫諭北使,私市北貨,尋被拘收。心懷怨望,有指斥語,法當絞,特貸之”*《要録》卷一六四紹興二十三年六月丙戌,3128頁;《宋史》卷四七三《秦檜傳》,13762頁。。這又是皇恩寬貸的一例。福州長溪縣文士黄友龍在臨安府餘杭縣“聽讀”期間,“醉酒作鬧,語言指斥”,也是犯了駡皇帝的大罪,被“杖脊,刺配廣南遠惡州牢城收管”,服廂軍的苦役*《要録》卷一六五紹興二十三年閏十二月癸巳,3146頁;《宋史》卷四七三《秦檜傳》,13762頁。。紹興二十五年(1155),小武官王世雄“作詩有指斥語”,被判“追毀出身以來告敕文字,除名,勒停,決脊杖二十,不刺面,配邕州牢城收管”,服廂軍的苦役*《要録》卷一六八紹興二十五年六月戊戌,3197頁;《宋會要·刑法》六之三三。。以上只是最簡單的記録,而他們“指斥語”的具體内容,則爲官史所掩覆。當時秦檜“矯誣”,“無罪可狀,不過曰謗訕,曰指斥,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宋史》卷四七三《秦檜傳》,13764頁。。如對付參知政事李光,秦檜“令臣僚誣言其指斥之罪,遂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又再三貶責*《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一五,1050頁。。
不僅是皇帝,秦檜依靠金人撐腰,當上了宋高宗無法罷免的宰相,權勢幾乎等同於皇帝。有官員吴元美作《夏二子傳》,言“夏二子,謂蠅、蚊也”,居然被定爲“指斥國家及譏毀大臣,以快私忿,法當死”,雖純屬捕風捉影的影射文章,宋高宗算是特予寬貸,改爲“除名,容州編管”*《要録》卷一六一紹興二十年九月甲申,3058頁。。一時之間,“譏毀大臣”也成了可怕的刑名。
金朝法律的制訂,“兼採隋、唐之制,參遼、宋之法”*《金史》卷四五《刑志》,中華書局,1975年,1015頁。,也繼承了“大不敬”中的“指斥乘輿”罪。金朝統治階級内爭激烈而殘忍,屢次出現“指斥乘輿”罪的案例。金熙宗“屢殺大臣,(完顔)宗敏憂之,謂海陵(完顔亮)曰:‘主上喜殘殺,而國家事重,柰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此爲指斥,構害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金史》卷六九《宗敏傳》,1609頁。。金海陵王時,金太祖長女完顔兀魯的丈夫徒單斜也,有妾名忽撻,她上告“兀魯語涉怨望,且指斥”,金海陵王“使蕭裕鞫之,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而杖斜也,免其官”*《金史》卷七七《亨傳》、卷一二〇《徒單恭傳》,1757、2616頁。。參與金海陵王篡位活動的完顔秉德,後來被告“謀反有狀”,“秉德妻嘗指斥主上,語皆不順。及秉德與(完顔)宗本相别時,指斥尤甚”等,金海陵王“殺秉德”*《金史》卷一三二《秉德傳》,《烏帶傳》,2818、2819、2821頁。。金世宗即位之初,完顔按荅海和完顔燕京兄弟據廣寧府,“拒弗受”,完顔燕京“亦登譙樓,與使者語,指斥不遜”。後金世宗“釋按荅海,乃誅燕京”*《金史》卷七三《按荅海傳》,1683頁。。金朝季年,在金宣宗興定時,“御史臺奏(蒲察)移剌都在軍中,買沙覆道,盜用官銀,矯制收禁書,指斥鑾輿”等,“坐是誅”*《金史》卷一〇四《蒲察移剌都傳》,2303頁。。金哀宗亡國前夕,丞相完顔賽不之子完顔按春投降蒙古,“從攻京師(開封),曹王(完顔訛可)出質,朝臣及近衛有從出者,按春極口大駡,以至指斥”,後完顔按春逃歸金朝,被“擒捕,斬之獄中”*《金史》卷一一三《完顔賽不傳》,2483、2484頁。。
元朝的《元典章》卷四一《諸惡》中有“大不敬”條目,但無“指斥乘輿”罪的實例。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宋“合州安撫使王立以城降”,但“東川行院遂言,立久抗王師,嘗指斥憲宗(蒙哥),宜殺之”,“降臣李諒亦訟立前殺其妻、子,有其財物。遂詔殺立,籍其家貲償諒”。但因“安西王具立降附本末來上”,元世祖又“即召立入覲,命爲潼川路安撫使、知合州事”*《元史》卷一〇《世祖紀》,中華書局,1976年,208頁。。就此案的處理而言,元世祖並未將王立“指斥憲宗”看得很重。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八月,“四川囊加台以指斥乘輿,坐大不道,棄市”*《元史》卷三三《文宗紀》,737頁。。元順帝時,徹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爲那壁,那壁者,猶謂之彼也”,連同其他罪名,“詔貶徹里帖木兒於南安,人皆快之,久之,卒於貶所”*《元史》卷一四二《徹里帖木兒傳》,3406頁。。由此可見,元朝雖沿用“指斥乘輿”罪,但量刑並不十分嚴格。
縱觀五代遼宋金元官史中所載的“指斥乘輿”罪,顯然有三個特點: 第一,史書一般不記録“指斥乘輿”的具體内容和語言。上引岳飛“國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的話,官史同樣並無記録,而是岳飛孫岳珂從獄案中摘録出來的。官史所以不記録,無非是爲掩蓋皇帝的穢行、劣迹和罪惡。第二,“指斥乘輿”罪的量刑輕重,並不一律。除了是否真有“情理切害”之外,主要還是在古代人治條件下,“皇帝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最大特權者”*郭東旭《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5頁。,“皇帝的最高司法權,不受法律約束”*王雲海等《宋代司法制度》,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18頁。,皇帝願意怎麽判刑,就怎麽判刑。不論判刑結果如何,“指斥乘輿”罪量刑之殘酷,則没有任何疑義。第三,官史上對“指斥乘輿”罪顯然有明顯的疏漏,如前引宋哲宗時,章惇“再取旨不已”,對開封百姓以“指斥乘輿”罪判處死刑者,又不知有多少人,卻並未留下統計數。後引宋真宗的事例也同樣説明。無辜百姓因没有文化,不懂法律,而觸犯“指斥乘輿”罪者,就不可勝數了。
然而即使在專制主義意識籠罩一切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下,宋代還有少量懷抱良知的士大夫,他們反對草菅人命的“指斥乘輿”罪,其理論武器則是先王之道。
北宋人王回説:“指斥乘輿,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斬,而旁知不告者,猶得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於海内,使雖遐逖幽陋之俗,猶無敢竊言訕侮者。然《書》稱商、周之盛,王聞小人怨詈,乃皇自恭德,不以風俗既美,而臣民儼然戴上,不待刑也。則此律所禁,蓋出於秦漢之苛耳。”*吕祖謙《皇朝文鑑》卷一二九王回書判,《四部叢刊》本。他對“指斥乘輿”罪持批判態度,認爲不過是“秦漢之苛”,不合《尚書》中强調的先王之道。宋徽宗即位之初,龔夬上奏説,章惇在宋哲宗親政後,“編類臣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與夫陳亂世以諷今者,謂之訕上,謂之指斥。臣觀《書》,見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紂。丹朱,堯不肖子;紂,商之無道君。禹以堯不肖子戒舜,周公以商無道君戒成王,亦可謂之訕上乎?亦可謂之指斥乎?”*黄淮、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〇龔夬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2365頁。《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一四元符三年七月壬申載豐稷和陳師錫也有類似議論,《宋史資料萃編》第二輯,文海出版社,1969年,867頁。
南宋愛國儒學家胡寅在《尚書·無逸》“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一段話的傳注中,更明確説:“蔡京繼之,專以朋黨一言,禁錮忠臣義士,或謂之詆誣宗廟,或謂之怨讟父兄,或謂之指斥乘輿,或謂之謗訕朝政。行之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則已,仕則必習爲導諛,相師佞媚,歌功頌德,如恐不及。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胡寅《斐然集》卷二二《無逸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37—605、606頁。他特别引用了周厲王“監謗”,而“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古訓,指出設立“指斥乘輿”罪的後果,無非是營造“習爲導諛,相師佞媚,歌功頌德”的惡劣政治環境。

綜合以上議論,大致有三條: 第一,按儒家仁義思想,反對以“指斥乘輿”罪草菅人命,濫殺無辜,認爲“指斥乘輿”罪只是秦漢苛法,不合先王之道。第二,認爲君主受“謗”是正常情況,不足大驚小怪。如果百姓怨王詈王,君主不但不應給百姓加罪,還須反躬自責,省愆念咎。第三,舜“立謗木”,“使人謗己”,而周厲王“監謗”,卻“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爲後世樹立了正反兩種借鑒和教訓。這其實又是如何對待輿論批評的重大問題。彭龜年特别强調:“言路通塞,天下治亂繫焉。言路通,則雖亂易治也;言路塞,則雖治易亂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六彭龜年奏,2713頁。他將“言路通塞”的問題和效應説得非常透徹。筆者曾將彭龜年此言向若干史界同行轉述,他們都認爲這個八百年前的古人的見解相當高明,應當作爲警誡後世的名言。


宋真宗時,“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爲桀、紂者”。宋真宗“令宫中録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説:“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它,若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斥乘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理學家楊時爲此評論説:“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楊時《楊龜山先生集》卷一三《語録·餘杭所聞》,《宋集珍本叢刊》第29册,綫裝書局,2004年,390頁。南宋人俞德鄰也對此事評論説:“《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真廟有焉。”*俞德鄰《佩韋齋集》卷一七《輯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89册,134頁。又天禧時,官員陳靖上奏中有“必是不經聖覽”之語,大理寺“以爲指斥乘輿”。宋真宗下詔,説陳靖“受誣於吏議”,“非汝瑕疵,宜從洗滌”*《宋會要·刑法》三之一六。。宋真宗雖然算不上好皇帝,當時也根本説不上“天下安得而不治”,但處理此類事,還是表現了一定的肚量。
宋仁宗時,官員王益柔“作《傲歌》,語涉指斥,欲下御史按罪”。宰相杜衍“謂羅織獄今起都下矣,執不可”*《東都事略》卷五六《杜衍傳》,835頁。。據説他的詩中有“‘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等語”,可能還有其他近乎“指斥”的語言,一些臣僚認爲“罪當誅”,“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宋宰輔編年録校補》卷五,260頁;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二九首句作“欹倒太極遣帝扶”,中華書局,1986年,3089頁。,但在杜衍、韓琦等力辯後,最終還是没有加刑。
宋神宗時,吕希道“爲開封府推官,民有相詈,激語近訕上,無悖慢情,尹及同僚皆欲以指斥抵法”。吕希道“力爭,請上聞,神宗果笑曰:‘小人無知,灼非本情。’釋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二《左中散大夫守少府監吕公墓誌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00册,461頁。。
宋寧宗慶元初,中書舍人鄧馹上奏追述紹熙時事:“布衣余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誠不爲過,太上皇帝(宋光宗)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寛典。”*《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四慶元元年四月庚申,中華書局,1986年,62頁。
拙作從論證“指斥乘輿”罪的方面,做了一點正本清源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