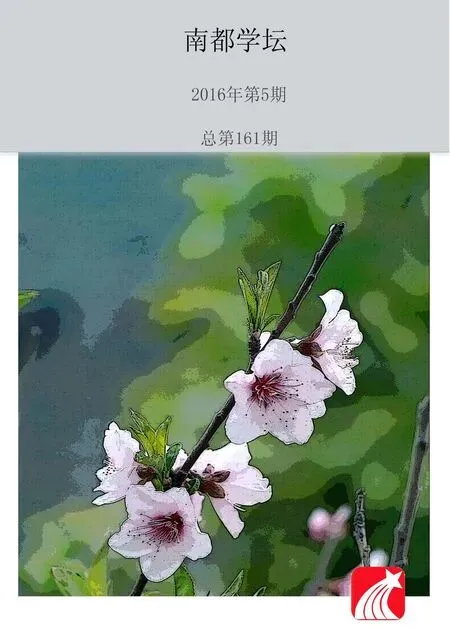战争与环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个案研究
李 文 涛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历史与文博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运城学院 河东文化研究中心, 山西 运城 044000)
战争与环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个案研究
李 文 涛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历史与文博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运城学院 河东文化研究中心, 山西 运城 044000)
战争对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三国时期,魏吴两国因为军事需要在淮河中下游屯田,部分地区人口密度高,土地过度开垦,水土流失严重,导致西晋初年淮河中下游水质比较浑浊,人口在短时期内对环境产生了较大压力。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得屯田人口大为减少,南北朝时期,战争导致淮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减少,土地荒芜,淮河中下游水质又变得非常清澈,生态环境恢复。长江流域中上游也发生类似变化,西晋末年,战乱导致人口向山区迁徙,加之獠人农业快速发展,蜀地山区土壤垦殖率增高,水土流失严重;随着社会安定,迁往山区的汉人回到平原地区,獠人也大量外迁,蜀地山区森林植被恢复,江水又比较清澈。十六国时期,为满足扩张和屯兵的需要,统万城地区遭到过度开发,再加上战争频仍,致使原来河流纵横的草原地区逐渐沦为流沙满目的荒凉沙地。由此可见,传统时代的战争对环境的影响深远。在长期的军事对峙中,由于在某一区域集中了大量的军队,从而使自然资源负荷过重,而恶化了当地的环境。而且为躲避战争,使得人口向丘陵地区聚集。这些地区虽然得到了开发,但破坏了人与自然缓冲的丘陵地带,从长远来看,往往得不偿失。
战争;屯田; 丘陵; 农业;植被;水质;沙漠化
战争对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军事史与环境史的结合而形成的战争环境史是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1]。传统社会中,有关战争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2]。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战争对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个案研究,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对环境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战争局势与淮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
《太平御览》卷五九《地部·水下》引《博物志》记载:“水有浊有清,河淮浊,江济清。南阳有清泠之水,丹水,泉水,汝南有黄水,华山南有黑水,天下之水皆类五色,今载其名也。泞水不流。”*四库本则是:“水有五色,有浊有清。汝南有黄水,华山有黑水、泞水。”现在的标点本则是在四库本的基础上补充《太平御览》中的相关内容。[3]3可知在西晋时期,淮水比较浑浊。但直到明代中期,淮河都是比较清澈的,潘季驯就说过:“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即桂芳所开草湾,亦可不复修治。”[4]卷二二三《潘季驯传》,5871
淮河在西晋时期比较浑浊,是历史事实还是错误记载呢?史书记载:“(张)华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华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5]卷三六《张华传》,1074从史书对《博物志》的作者张华的评价来看,张华记载的西晋时期淮河水比较浑浊是可信的。
西晋淮河中下游水质比较浑浊,应该与魏晋淮河流域人口聚集、植被受到破坏,导致水土流失有关。考察这一时期淮河流域的经济情况可知,魏晋时期,淮河流域的确在一段时期内人口大量聚集,大量土地被开垦,人口在短时期内对环境产生了较大压力。
具体屯田情况,史书记载:“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余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6]卷二八《魏书·邓艾传》,776此外,《晋书·食货志》记载:“宣帝善之,皆如艾计施行。遂北临淮水,自钟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商君书·算地》中提出了一个比较理想的人口与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模式:“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 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7]61这种模式要求人口密度在100/km2以下,这一地区环境压力并不大,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西晋时期,一尺约合现今24.2 cm,六步一尺[8]236,按照二百八十步一里计算,西晋一里约合现在400 m。“以五里一营,营六十人”,即是在半径为2.5里的地区设有60人屯田。2.5里约合现在1000 m,半径为2.5里的地区约合现今1 km2。这1 km2虽然只有60名军人屯田,但加上其家属,人口至少有300人*这里仅按一家五口计算。实际上三国时期,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户均人口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曹魏景元四年(263年),曹魏统治区户均人口达到6.68口。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当时全国户均人口为6.57口。详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1页。[9]20-21。人口密度超过了环境可承载力,加上建筑用材以及燃料,还有牲畜喂养的需要,该地区出现了水土流失的现象。
与此同时,在淮河流域的其他地区,地方官员也比较重视招募人口,发展农业,比较典型的以芍陂为中心的地区。“(刘)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怀绪等,皆安集之,贡献相继。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6]卷一五《魏书·刘馥传》,6463西晋时期,刘颂“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5]卷四六《刘颂传》,1294。合肥地区在短时期内聚集了如此多的人口,对环境的压力也比较大。
到了西晋时期,淮河流域的环境压力已经出现,杜预上疏提到:“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非但五稼不收,居业并损,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硗塉,此即百姓困穷方在来年……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为便。非不尔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莱,与百姓居相绝离者耳。往者东南草创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顷户口日增,而陂堨岁决,良田变生蒲苇,人居沮泽之际,水陆失宜,放牧绝种,树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则土薄水浅,潦不下润。故每有水雨,辄复横流,延及陆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陆种。臣计汉之户口,以验今之陂处,皆陆业也。其或有旧陂旧堨,则坚完修固,非今所谓当为人害者也……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余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5](卷二六《食货志》,789杜预认为西晋时期东南地区水土流失的原因是陂塘过多,而真正的原因是人口压力过大,导致过度开垦,最终导致水土流失。
不过,西晋末年之后,淮河流域人口对环境的压力减少。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屯田士兵很大程度上参与其中,史书记载,淮南王司马允被赵王司马伦杀害后,“淮南国人自相率领,众过万人,人怀慷忾,愍国统灭绝,发言流涕”。这里的国人,大部分应该是屯田士卒[5]卷六四《武王十三子传》,1722。
十六国时期,淮河流域人口已经大为减少,“且江、淮南北户口未几,公私戎马不过数百,守备之事盖亦微矣。若以步骑一万,建雷霆之举,卷甲长驱,指临江、会,必望旗草偃,壶浆属路。跨地数千,众逾十万,可以西并强秦,北抗大魏”[5]卷一二七《慕容德载纪》,3171。姚兴统治时期,也有人建议:“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当从肥口济淮,直趣寿春,举大众以屯城,纵轻骑以掠野,使淮南萧条,兵粟俱了,足令吴儿俯仰回惶,神爽飞越。”[5]卷一一八《姚兴载记》,2996
地板辐射制冷两联供系统也顺应了当前共享经济的潮流,共享经济的本质就是闲置资源的再利用。现在大多数的两联供系统还是夏天用风盘,冬天用地暖,因为设计方案不合理,夏天地暖闲置了,冬天风盘闲置了。而该系统使这种闲置得到了利用,且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
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成为南北方争夺的重点,连年的战争,使得淮河流域农业受到破坏,人口大为减少。芍陂也多年荒芜,年久失修。“高祖将伐羌,先遣修之复芍陂,起田数千顷。及至彭城,又使营立府舍,转相国右司马,将军如故。”[10]卷四六《毛修之传》,1429元嘉时期,“江淮左右,土瘠民疏,顷年以来,荐饥相袭,百城雕弊,于今为甚……芍陂良田万余顷,堤堨久坏,秋夏常苦旱。义欣遣咨议参军殷肃循行修理。有旧沟引渒水入陂,不治积久,树木榛塞。肃伐木开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10]卷五一《宗室·长沙景王道怜附刘义欣传》,1465。南齐时期,“敕崇祖修治芍陂田”[11]卷二五《垣崇祖传》,463。芍陂多次被兴修,是这一地区人口减少、农业荒废的表现。
此外,在淮河流域其他地区也出现荒芜的景象。刘宋元嘉年间,北魏对淮河流域的入侵,对这一地区破坏极大。“既而虏纵归师,歼累邦邑,剪我淮州,俘我江县,喋喋黔首,跼高天,蹐厚地,而无所控告。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时岁唯暮春,桑麦始茂,故老遗氓,还号旧落,桓山之响,未足称哀。六州荡然,无复余蔓残构,至于乳燕赴时,衔泥靡托,一枝之间,连窠十数,春雨裁至,增巢已倾。虽事舛吴宫,而歼亡匪异,甚矣哉,覆败之至于此也。”[10]卷九五《索虏传》,2359而《资治通鉴》则记载:“魏掠居民、焚庐舍而去……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掠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12]卷一二六《宋纪八》,3966除了在淮河流域杀戮之外,还把这一地区人口迁往平城等地,“三月己亥,车驾至自南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赐留台文武所获军资生口各有差”[13]卷四《世祖太武帝纪》,105。这一次战争使得淮河流域更加荒芜。
南齐时期,徐孝嗣上书说:“臣比访之故老及经彼宰守,淮南旧田,触处极目,陂遏不修,咸成茂草。平原陆地,弥望尤多。今边备既严,戍卒增众,远资馈运,近废良畴,士多饥色,可为嗟叹。……时帝已寝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11]卷四四《徐孝嗣传》,774此外,《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记载:“义熙二年,刘毅复镇姑熟,上表曰:‘忝任此州,地不为旷,西界荒余,密迩寇虏,北垂萧条,土气强犷,民不识义,唯战是习。逋逃不逞,不谋日会。比年以来,无月不战,实非空乏所能独抚。请辅国将军张畅领淮南、安丰、梁国三郡。’时豫州边荒,至乃如此。十二年,刘义庆镇寿春,后常为州治。抚接遐荒,扞御疆场。”
淮河流域的荒芜,使得植被有所恢复。南朝时期,淮河流域出现了较大规模象群。承圣元年,“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14]卷八《元帝纪》,240。据《魏书》卷一一二《灵征志》记载:“天平四年八月,有巨象至于南兖州,砀郡民陈天爱以告,送京师,大赦改年。”野象的出现,而且规模较大,正是这一地区植被良好的表现。
南朝时期,淮河流域人口减少,对环境压力减轻,植被恢复较好,淮河流域水质非常清澈。梁武帝修筑浮山堰时,“其水清洁,俯视居人坟墓,了然皆在其下”[15]卷一八《康绚传》,292。这正是淮河流域水质较好,导致能见度较高的缘故。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的战争局势与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变化
《太平御览》卷五九引《博物志》说:“江、济清。”可知在西晋时期,长江和济水仍然清澈。东晋时期,长江干流浑浊的记载开始出现。《水经注·夷水》引袁山松《宜都记》记载:“(夷水东入)大江,清浊分明,其水十丈见底,视鱼游如乘空,浅处多五色石。”这里描述的就是当时宜都附近的夷水入江时和浑浊的长江干流水形成鲜明对比的情景。此外,在长江中游的湘江段附近,也出现这种情况。《水经注·湘水》记载:“水色青异,东北入于大江,有清浊之别。”
长江流经的区域,与黄河不同,原始土壤并不疏松。其浑浊变化,显然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长江中上游直到东汉时期才完成了平原地区的开发,三国后,人口减少,刚起步的丘陵开发又停止。西晋统一之后,国家稳定的局面不长,很快就发生了八王之乱,开启了人口大迁徙的序幕。不过对于长江中上游地区来说,情况比较复杂。以巴蜀地区为例,西晋末年,秦雍流人定居在成汉地区,估计人口在10万以上。李特占据巴蜀后,本地逃亡外地的流民大致有30万[16]309-319。
因此,在巴蜀地区,移出人口比移入人口更多,人口有减少的趋势。但为何在这一时期长江中游干流出现浑浊的情况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有大量人口为了逃避战乱,逃离平原,进入山区,在山区丘陵地带从事农业活动。《晋书·李特载记》记载:“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尚参军涪陵徐轝求为汶山太守,欲要结长生等,与尚掎角讨流。尚不许,轝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说长生等使资给流军粮。长生从之,故流军复振。”我们可以看到,范长生率领千余家,约万余人逃避战乱,躲入青城山,这万余人的口粮,应该主要是在青城山区耕种所得。而且开垦面积较大,有较多的剩余粮食。《宜都记》记载:“限山县东六十里有山,名下鱼城,四面绝崖,唯两道可上,皆险绝。山上周回可二十里,有林木池水,入田种于山上。昔永嘉乱,土人登此避贼,守之经年,食尽,取池鱼掷下与贼,以示不穷,贼遂退散,因此名为下鱼城。”此外,当时不少大族为躲避战乱,也逃亡山区,“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薮……寻而范贲、萧敬相继作乱,秀避难宕渠,乡里宗族依凭之者以百数”[5]卷九四《隐逸传·谯秀传》,2444。可见由于战乱,当时一些高山和丘陵得到了开发。《华阳国志》记载了东晋时期已有丘陵地区被开发的记载,比如涪陵地区,“有山原田,本稻田”;武都郡,“土地险阻,有麻田”;“江原县……有青城山,称江祠。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小亭有好稻田”;在巴地丘陵地区,“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可见东晋时期已有比较大规模的丘陵开发。丘陵的开发,无疑会加重水土流失。
考古表明,在东汉后期的长江三峡大宁河流域,大宁河泛滥,导致该区文化层发生中断,人民被迫迁往高处。东汉之后,本区人地关系出现了恶化,人类过度采伐森林和垦殖,导致森林植被大量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山洪灾害频繁,因此该区自汉代之后再无连续的文化层堆积,而由于山洪暴发导致了坡积物在此大量堆积。由于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导致土壤垦殖率增高,而当时人类的生态意识薄弱,于是该区水土流失比较严重,据统计,历史上水土流失面积达总土地面积的30%[17]。
东晋之后,随着桓温灭成汉,巴蜀地区又出现稳定的局势。移民还在源源不断流入。刘宋时期,“时秦雍流户悉南入梁州”[17]卷三《武帝纪下》,59。南朝时期,蜀地进一步被开发,江水依然浑浊。江水含沙量比较大,成都附近的江边有沙洲生成,《南齐书·州郡志下》记载:“泰始中,成都市桥忽生小洲,始康人邵硕有术数,见之曰:‘洲生近市,当有贵王临境。’永明二年,而始兴王镇为刺史。”这里的泰始年号,应该为刘宋时期的年号,为公元465—471年间。此外,枝江在公元424年左右和536、539年有新的沙洲形成的记载,《南史·梁本纪下》记载:“又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满百,当出天子。’桓玄之为荆州刺史,内怀篡逆之心,乃遣凿破一洲,以应百数。随而崩散,竟无所成。宋文帝为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篡统。后遇元凶之祸,此洲还没。太清末,枝江杨之阁浦复生一洲,群公上疏称庆,明年而帝即位。承圣末,其洲与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可知当时江水中含沙量已经比较大,沙洲逐渐与河岸相连。隋初的《图经》说:“(清江),一名夷水。蜀中江水皆浊,唯此独清,故名。”[18]卷六○《施州·清江》,1051《水经注》卷三四《江水二》记载三峡地区:“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柽柏,悬泉瀑布,飞潄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这说明长江三峡江水在冬春时节是清澈碧绿的,但在夏秋时节就不那么清澈了。
汉族人口迁入到丘陵地区,一方面挤压了獠人的生存空间,引起了獠人的反击。另一方面在与汉人接触之中,獠人也发展农业,过着定居生活。成汉时期,“初,蜀土无獠,至此,始从山而出,北至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5]卷一二一《李势载记》,3040。《魏书·獠传》也记载:“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建国中,李势在蜀,诸獠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獠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獠人的生计模式,已经由渔猎逐渐过渡到农耕。
也有一部分汉人逃到山区与獠人杂居,獠人的农业水平大为提高。《宋书·蛮夷传》也记载:“荆、雍州蛮,盘瓠之后也。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结党连群,动有数百千人。”《周书·獠传》也记载:“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在所皆有之……自江左及中州递有巴、蜀,多恃险不宾。太祖平梁、益之后,令所在抚慰。其与华民杂居者,亦颇从赋役。”
《宋书·沈庆之传》记载了当时獠人的经济模式:“雍州蛮又为寇,庆之以将军、太守复与随王诞入沔……故蛮得据山为阻,于矢石有用,以是屡无功。庆之乃会诸军于茹丘山下,谓众曰:‘今若缘山列旆以攻之,则士马必损。去岁蛮田大稔,积谷重岩,未有饥弊,卒难禽剪。今令诸军各率所领以营于山上,出其不意,诸蛮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战而获也。’于是诸军并斩山开道,不与蛮战,鼓噪上山,冲其腹心,先据险要,诸蛮震扰,因其惧而围之,莫不奔溃。自冬至春,因粮蛮谷……庆之引军自茹丘山出检城,大破诸山,斩首三千级,虏生蛮二万八千余口,降蛮二万五千口,牛马七百余头,米粟九万余斛。”可见獠人的生计模式中农业已经占据重要地位。
由于獠人时常叛乱,遭到历朝镇压与强制迁徙,使得在山谷从事农业的獠人减少,部分丘陵地区荒废,水土流失减少。到了南北朝末期,长江干流又变得清澈。《隋书·五行志》记载:“陈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荆州。祯明中,江水赤,自方州东至海。”“江水赤”,正好反映出平时江水比较清澈,人们很容易观察到江水颜色的变化。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势与统万城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万城周边地区的环境,史书有较多的记载,赫连勃勃北游契吴山时曾盛赞那里的生态环境,说:“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19]卷四《夏州朔方县》引《十六国春秋》《水经注》卷三“河水”条记载:“(奢延)水西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奢延水又东北,与温泉合。源西北出沙溪,而东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东,黑水入焉,水出奢延县黑涧,东南历沙陵,注奢延水。”奢延水就是今天的无定河,《水经注》提到位于无定河畔的统万城(即汉代奢延县)西方有“赤沙阜”,西北方有“沙溪”,东北方有“沙陵”。有些学者又由此认定,《水经注》中这些关于“沙”的记载,加上北魏时期称灵、夏州一线为“沙塞”的说法,反映了统万城建城初期的生态环境就比较差,早已经有流沙分布了。比如,王尚义认为地层探测与史籍资料均表明,在统万城建城时,本地区已有“沙阜”“沙丘”“沙陵”,但自然景观并未形成沙的环境,“沙阜”与“绿洲”相间并存,在河床谷地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而主要的还是能承载数百万牲畜的天然牧场[20]。
不过邓辉等认为,赫连昌时期,统万城内至少有4万人。统万城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类过度使用当地的土地资源而产生的结果。统万城地区的开发虽然可以上溯到西汉年间,但从十六国时期开始,人们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影响越来越大。从5世纪初统万城建成,到10世纪末被放弃,在这大约500多年的时间里,当地人口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当地土地资源由于长期受到过度耕垦、过度牧放,终于使得原来一个河流纵横的草原地区,逐渐沦为流沙满目的荒凉沙地[21]。师海军指出赫连夏时人口数量爆炸式的增长,成为统万城的主导因素。保守估计,外迁统万城的人口至少45万,加之周边地区的人口,至少有60万。人口的爆炸式,对土地过分开垦,加之气候和战争因素,统万城地区沙化越来越严重[22]。
从统万城建立到《水经注》,时间过去一百多年。至于《水经注》中记载的“赤沙阜”“沙溪”“沙陵”在统万城建立时就已存在,还是统万城建立后一百多年出现的,还要进一步考证。统万城建立在生态脆弱地带,加之地表土壤下存在古沙,破坏地表土壤,容易形成就地起沙。然而,统万城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植被环境与表土环境。
公元413年,赫连勃勃“乃赦其境内,改元为凤翔,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23]卷一一六《晋纪三十八》。统万城极其坚固,“初,夏世祖性豪侈,筑统万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高五仞,其坚可以厉刀斧”[23] 卷一二○《宋纪二》。现在调查表明,统万城分为外城郭、东城和西城。东城周长2566 m,西城周长2470 m,西城基厚约16 m,东城基厚约10 m。城的四隅都有高出城外的平面方形墩台,高达31.62 m。统万城蒸土筑城,就是用生石灰,沙和黏土组成的三合土作城[24]。仅以宽3 m计算,东城基须耗沙土约77000 m3,西城基须耗沙土约118000 m3。以城高30 m计算,东城墙要耗沙土约23000 m3,西城墙要耗沙土约220000 m3,仅东西城墙加上城基,要耗沙土约645000 m3。如果取土深度1 m,则这些土方相当于一个长3 km,宽21 km区域的土方。实际上,取土1 m深,早就到达了古沙层。加之其他建筑用土,实际所取土的面积更大。
此外,统万城修筑过程中,又“乃蒸土筑城”,加之城内建筑“台榭壮大,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穷极文采”。此外,还有其他建筑用木,据调查,统万城残坑内的支柱主要是松、柏、侧柏、杉、柠条、沙大王、沙蒿、沙柳等[24]。如果说,台榭等木材取自其他区域,那“乃蒸土筑城”所需的燃料以及其他建筑所需的材料,则取自于本区域,由于土方极大,这无疑需消耗本地很多木材资源。
此外,这十万建筑工人,加之监军,一年所消耗的食物和燃料也极多,如果以肉食为主要食物原料,牛羊等也破坏周围的环境。公元424年,统万城建立之后,“勃勃还统万,以宫殿大成,于是赦其境内,又改元曰真兴……名其南门曰朝宋门,东门曰招魏门,西门曰服凉门,北门曰平朔门”[5]卷一三○《赫连勃勃载纪》。定都统万之后,统万城有多少人,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不过,可以推断,统万城的军队至少有10万,公元417年,赫连勃勃“以子璝都督前锋诸军事,领抚军大将军,率骑二万南伐长安”,攻下长安后,收编了部分军队,“璝率众三万追击义真,王师败绩,义真单马而遁”[5]卷一三○《赫连勃勃载纪》。赫连勃勃回统万,其率领军队大致有三四万。公元424年,“夏主将废太子璝而立少子酒泉公伦。璝闻之,将兵七万北伐伦。伦将骑三万拒之,战于高平,伦败死。伦兄太原公昌将骑一万袭璝,杀之,并其众八万五千,归于统万”[23]卷一二○《宋纪二》。这八万五千人加上赫连勃勃所能控制的军队,统万城内有军人不下10万。此外,修城的10万工匠,一半能活下来,也有近5万人。公元426年,北魏拓跋焘进攻统万,在“杀获数万,得牛马十余万”后,还“徙其民万余家而还”。以五口一家计算,估计有五万人被迁徙。第二年,拓跋焘又一次进攻统万,这一次“杀夏主之弟河南公满及兄子蒙逊,死者万余人……魏主入城,获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23]卷一二○《宋纪二》。不过,《魏书·世祖纪上》记载,“虏昌君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擒昌尚书王买、薛超等及司马德宗将毛修之、秦雍人士数千人,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这次俘虏人口,有宫人上万,加之几千秦雍人士。这些人加上军队以及工匠还有上一年被迁徙之人,统万城内大致上有25万人。除了人口之外,统万城内“还有马匹三十余万,以及牛羊数千万”。人口的大量移入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牛羊数千万,也会导致草场负担过重,出现退化。由于取土的消耗以及人口与牲畜的压力,统万城周边地区在当时就已经有部分地区沙化,随风起沙情况比较严重,也是在拓跋焘攻克统万城的战斗之中,“夏兵为两翼,鼓噪追之,行五六里,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晦冥”。其扬沙的沙源,在统万城附近,而且已经比较严重。此后,统万城为北魏的重要军镇,长期派大员镇守,农业也得到一定发展。《魏书·刁雍传》记载:“雍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此外,还在这一带设置牧场,《魏书·食货志》记载:“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牲畜数量已越来越多,远远超过赫连夏盘踞时代,草场压力进一步增加[25]。加之此后气候变冷,不利于植被的生长,风沙现象越来越严重。
四、结语
传统时代的战争,对环境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长期的军事对峙中,由于一方或者双发在某一区域集中了大量的军事人员,农业的开发与薪柴的需求,加之观察战场需要而砍树,恶化了当地的环境。西汉在西北驻兵屯田,三国时期吴魏在淮河流域的对峙,北朝时期东西魏在汾河流域的对峙,宋夏之间的对峙,乃至明朝时期在北方设置的军事重镇,都对周边环境产生了复杂的影响[26]。这些流域,有些影响是暂时的;而在北方地区的军事活动,其影响是长期的。
其次,战争使得人口向丘陵地区聚集。毛汉光指出:战争使得人口向四方流浪,最有可能的方向是南方地带或者附近的丘陵、山谷间崎零地,或较干旱、远离水系之地,相较于已开发的平原可灌溉之地,其生产力较差,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才能得到一些收获。待战争告一段落,因为经过数代开发变成可用之耕地,人们也定居下来,而原来的家园,因战乱破坏生产体系,人口反而减少[27]234。
侯旭东也指出,战争对普通的生活影响并不大[28]。究其原因,是老百姓远离可能发生战场的城镇,在丘陵地区生活。战争过后,朝廷要求老百姓返回老家,但老百姓已经安居,回家动力不足。因此,丘陵地区虽然得到了开发,养活了大量人口,为社会日后发展提供了动力,但破坏了人与自然缓冲的丘陵地带,从长远来看,往往得不偿失。
[1]包茂红.从第一次世界环境史大会看国际环境史研究的新动向[J].南开学报,2010(3).
[2]金勇强.宋夏战争与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关系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来霞霞.隋唐时期青海草原战争与生态环境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李金玉.论东周时期战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J].中州学刊,2010(3);关亚新.明末清初战争对辽西生态环境的破坏及影响[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3(3).
[3]张华.博物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高亨.商君书注译[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9]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0]沈约.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3]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5]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6]葛剑雄.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17]张芸,等.长江三峡大宁河流域3000年来的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J].地理科学,2001(3).
[18]祝穆.方舆胜揽[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9]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王尚义,等.统万城兴废与毛乌素沙漠的变迁[J].地理研究,2001(3).
[21]邓辉,等.从统万城兴废看人类活动对生态脆弱地区的影响[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2).
[22]师海军.夏州(统万城)地区沙化蠡测[J].江汉论坛,2009(8).
[2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4]陕西省文管会.统万城城址勘测记[J].考古,1981(3).
[25]赵淑芳,等.北魏时期黄河下游水患问题的再讨论[J].人民黄河,1999(4).
[26]景爱.沙漠考古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环境[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27]毛汉光.中国人权史(生存权篇))[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8]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责任编辑:岳岭]
Cas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r and Environment During the Wei, Jin,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LI Wen-tao
(Faculty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Hainan Tropical Ocean University, Sanya Hainan 572022,China;Hedong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Yuncheng University, Yuncheng Shanxi 044000, China)
War imposes great influence on environment.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Wei and Wu opened up the wasteland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Huaihe River because of the military need. The higher density of population in some parts caused the land overcultivated and soil erosion, which resulted in the turbid water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Huaihe River during the early Western Jin Dynasty. However, during the late Western Jin Dynasty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war led to the decrease of population and the land deserted, as a result of which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Huaihe River became crystal-clean. It is same to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late Western Jin Dynasty, the people moved to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because of war, which led to the opening up of the mountainous regions in Sichuan along with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Liao minority. Consequently, the soil erosion became serious. With the society stability, the people returned to the plains. As a result, the river became limpid again because of the vegetation recovery.
war; opening up the wasteland; hills; agriculture; vegetation; water quality; desertification
2016-07-15
李文涛(1974—),湖北省天门市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史、环境史研究。
K235
A
1002-6320(2016)05-002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