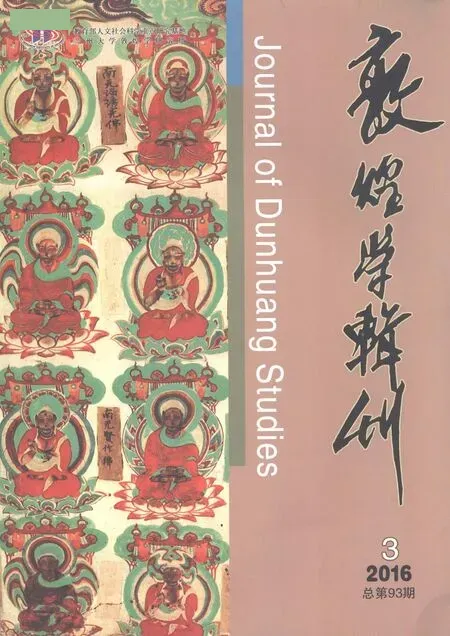近代欧洲法显研究之起源
——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西译开笔200周年纪念
王冀青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佛教于汉代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赴印度的巡礼、求法活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常态,到隋唐时期达到高潮,至北宋以后才逐渐衰落。在这千余年间,求法僧们在中、印间的陆、海“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确切人数难以统计。其中有许多求法僧留下了他们的西行游记或其他相关记录,早已成为研究古代印度历史以及西域史、南海史、中外关系史、佛教史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向来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及其游记中,东晋沙门法显(342—423)撰《佛国记》(又称《法显传》)最早受到欧洲中国学、印度学的关注,也是最早被翻译成西方文字的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
1816年,旅居法国的德国汉学家朱里乌斯·亨利希·冯·克拉普洛特(Julius Heinrich von Klaproth,1783—1835)在巴黎开始法译《佛国记》。1830年,法国汉学家让-皮埃尔·阿贝尔·雷慕沙(Jean-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也在巴黎开始法译《佛国记》。雷慕沙于1832年去世后,克拉普洛特得到雷慕沙的《佛国记》法译本手稿,以此为基础继续法译《佛国记》。但克拉普洛特于1835年去世时,他的《佛国记》法译本手稿尚未完成。1835年,法国汉学家厄恩斯特-奥古斯丁-沙维尔·克拉克·德·兰德瑞瑟(Ernest-Augustin-Xavier Clerc de Landresse,1800—1862)接手雷慕沙和克拉普洛特的《佛国记》未完成法译本译稿,经过一年的补充翻译和考释,于1836年在巴黎出版了《佛国记》的第一个西文译本,书名直译为“佛国记:关于佛教王国的记录,释法显于4世纪末在鞑靼、阿富汗和印度进行的旅行之游记,由阿·雷慕沙译自汉文并加以注释”。[注]J.-P.A.Rémusat,Foe koue ki,ou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voyage dans la Tartarie,dans l’Afghanistan et dans l’Inde,execute,a la fin du IVe siecle, par Chy Fa Hian, traduit du chinois et commente par A.Rémusat,Paris,1836.由兰德瑞瑟总其成的这个《佛国记》法译本,实系克拉普洛特、雷慕沙、兰德瑞瑟等人历经20年的翻译、考释成果。
今年(2016年)恰逢克拉普洛特于1816年开笔法译法显《佛国记》的200周年纪念,也是克拉普洛特、雷慕沙、兰德瑞瑟的《佛国记》法译本于1836年初版的180周年纪念。值此之际,笔者不揣浅陋,草成此文,以法显《佛国记》的早期西译过程为主要线索,略表纪念之意。文中不妥之处,万望方家教正!
一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与之相适应的“东方学”体系应运而生。东方学的两大分支,即以梵学为主的印度学(Indology)和以汉学为主的中国学(Sinology),到18世纪下半叶已初奠基础。1783年12月,英国“东方学之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来到英属印度孟加拉殖民地首府加尔各答,担任东印度公司高等法院的推事法官。1784年1月15日,琼斯和英属印度的一批业余学术爱好者在加尔各答聚会,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东方学研究组织“亚细亚学会”(Asiatick Society,后称“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其宗旨是“探究亚洲的历史(包括文明历史和自然历史)、文物、艺术、科学和文学”,[注]Sir William Jones, ‘A Discourse on the Institution of a Society, for Inquiring into the History, Civil and Natural, the Antiquities, Arts, Sciences and Literature of Asia’,Asiatick Researches, or Transactions of the Society (AR),Vol. 1, 1788, p. 2.琼斯被推举为首任会长。亚细亚学会的成立,是近代欧洲东方学正式诞生的标志性事件。
琼斯到达印度之初,便私下跟随一些婆罗门学会了梵语,逐渐发现梵语与欧洲诸语言之间存在着亲缘关系。1786年2月2日,琼斯在亚细亚学会第3届年会上发表的演讲《论印度教徒》中,宣布了他的研究成果,即梵语与欧洲语言同源。琼斯的原话是:
梵语,无论它的年代多么古老,都可谓具有奇妙的结构。它比希腊语更完善,比拉丁语词汇更丰富,而且比上述两种语言更精美、优雅。在动词词根和语法格式上,它与上述两种语言都有着更紧密的亲缘关系。这种密切的程度,绝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现象。它们之间的亲缘关联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没有一个语言学家在仔细研究过所有这三种语言之后,而不相信它们是出自某一共同来源的,虽然这个共同的根源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注]Sir William Jones, ‘On Hindus’,AR,Vol. 1, 1788, p. 127.
琼斯这段话在国际东方学史和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欧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标志着印欧语系的确定,也标志着欧洲学者已有了探究佛教语言梵语的意愿。
但是,在当时的欧洲,关于梵语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关于佛教的起源和历史,学术界知之甚少。琼斯在同一篇讲演稿《论印度教徒》中,竟这样描述佛教:
塞西安人(Scythian)和北极人(Hyperborean)的教义与神话,在这些东方地区的每一个部分,也都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我们也不会怀疑,沃德(Wod)或奥登(Oden),与佛陀(Buddh)就是一回事。正如北方的历史学家们所承认的那样,他的宗教是被一个外来种族引入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半岛的。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佛陀的礼拜仪式大概也传入了印度。不过,到很晚以后,中国人也接受了佛陀的礼拜仪式,他们将佛陀的名号软化为“佛”(Fo)。[注]Sir William Jones, ‘On Hindus’,AR,Vol. 1, 1788, p. 129.
由此可见,琼斯对于佛教起源于印度、流传至中国等基本脉络一无所知,更不了解佛教曾以梵语作为宗教语言这一事实。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整个欧洲的印度学界都不具备有关佛教的基本知识。
琼斯去世后,亚细亚学会的会员们不断将梵语研究和佛教研究推向前进。亚细亚学会第五任会长亨利·托玛斯·考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1765—1837)于1807年在学会学报《亚细亚研究》第9卷上发表《关于耆拉教派的观察结果》一文,认为耆拉教和佛教都源于印度教,第一次推论佛教源于印度。[注]Henry Thomas Colebrooke, ‘Observations on the Sect of Jains’,AR,Vol. 9, 1807, pp. 287-322.考尔布鲁克关于佛教起源于印度的研究结论传回欧洲后,首先鼓励了欧洲的中国学家们,激发他们从汉文史料中寻找有关印度佛教的记录。原以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印度学(梵学)和中国学(汉学),第一次有望实现学科的交叉。而两者的交汇点,便是佛教文献学和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的研究。因19世纪初欧洲的中国学研究中心是法国巴黎,这项工作首先在法国巴黎展开。
法国的耶稣会从17世纪初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他们陆续从中国带回不少汉文书籍,分藏于法国各地的公私图书馆中,为法国的中国学研究奠定了最初的资料基础。通过其他途径流入法国的汉文书籍也不在少数,如17世纪末清朝康熙皇帝(1654—1722)和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就曾互赠礼品书籍。到18世纪末,法国巴黎各机构收藏的汉文书籍,已成为整个欧洲大陆中国学研究的资料库。到19世纪初,德国汉学家克拉普洛特也被吸引到巴黎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克拉普洛特出生于德国柏林一个化学家家庭,少年时对自然科学最感兴趣,但自1797年起开始迷恋汉文、汉语,自学并掌握了汉语。1800年,还在柏林上中学的克拉普洛特已对汉文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发表过关于朝鲜东海岸的文章。[注]Hartmut Walravens,Julius Klaproth(1783-1835): Briefe und Dokumente,Wiesbaden, 1999, pp. 16-19.克拉普洛特高中毕业后,进入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其间,克拉普洛特热衷于研究有关中亚地理的汉文书籍,并将相关部分翻译成法文。1802年,19岁的克拉普洛特来到德国文化艺术中心魏玛,创办了第一份德语、法语双语东方学杂志《亚细亚杂志》(德语名AsiatischesMagazin,法语名Magasinasiatique)。在1802年出版的《亚细亚杂志》第1卷上,克拉普洛特发表了他自己翻译的一些汉文文献,其中包括一篇题为《博洛尔》的译文,[注]Heinrich Julius von Klaproth, ‘Bolor’,Magasin asiatique,Tome 1, p. 96.译自清乾隆年间成书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涉及位于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博洛尔等西域地方。
1804年,克拉普洛特应邀来到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参加由俄国外交官玉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格洛夫金(Ю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ловкин,1762—1846)率领的出使中国使团,担任汉语翻译。这次使团只走到蒙古库伦,便因清朝的阻止而半途折返。克拉普洛特在恰克图附近考察一段时间后,于1807年返回圣彼得堡。不久,俄国政府任命克拉普洛特为俄罗斯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兼亚洲语言教授,为圣彼得堡藏汉文、满文书籍编目。1810年,克拉普洛特返回德国柏林,后又于1815年定居法国巴黎。
二
克拉普洛特定居巴黎期间,从1816年开始研究、翻译法显的《佛国记》。但克拉普洛特研究领域广泛,又喜欢四处漫游,所以对《佛国记》的翻译工作断断续续。1820年,克拉普洛特在巴黎出版了一部德文著作《论回鹘人的语言和文字》,[注]Heinrich Julius von Klaproth,Abhandlung ü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Paris, 1820.成为国际突厥学研究的先驱。1820—1821年,克拉普洛特再随一支俄国使团出使北京,担任翻译。克拉普洛特在巴黎缓慢翻译《佛国记》期间,结识了同样自学成才、同样热衷于中国古代西域史地的法国汉学领袖雷慕沙。
雷慕沙少年时因偶然看到一部中国草药书,开始对汉文感兴趣,此后自学汉语、汉文。1811年,23岁的雷慕沙出版《论中国语言和文学》一书,[注]Jean-Pierre Abel Rémusat,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erature chinoises,Paris, 1811.奠定了他在法国中国学界的地位,很快被法国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的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推选为院士。1814年,法兰西学院(Collége de France)设立“汉语和鞑靼语语言文学教授”(Professeur de Langue et Litterature Chinoises et Tartares)职位,任命雷慕沙为第一任教授。雷慕沙担任法兰西学院汉语教授期间,开始关注中国西域历史,并与有同好的克拉普洛特关系密切。
清朝于1726年(雍正四年)刊印的大型类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流传到巴黎后,雷慕沙研究了其中的“方舆汇编·边裔典”第55卷“于阗部汇考一、汇考二、纪事、杂录”等部分辑录的中国古代各类典籍中关于于阗国的史料,将第55卷的内容全部翻译成了法文,于1820年在巴黎出版,书名为《和阗城的历史》,副标题是“中国正史资料的辑录单行本,从汉文翻译而成,根据对一种被中国人命名为‘玉石’的矿物的研究以及对古代碧玉的研究而成”。[注]M. Abel Rémusat,Histoire de la ville de Khotan, tirée des annales de la Chine et traduite du chinois; suivie de recherches sur la substance minérale appelée par les Chinois Pierre de Iu, et sur le Jaspe des anciens,Paris, 1820.《和阗城的历史》是欧洲第一部关于于阗史的著作,也使雷慕沙成为欧洲第一位专题研究于阗史的学者。雷慕沙在翻译这部书的过程中,参考资料以中国正史中的西域传等资料为基础,也涉及法显等人游记中的史料。
随着法国东方学研究的不断推进,法国学术界借鉴英国人创办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的模式,于1822年4月1日在巴黎创建了欧洲境内的第一个亚洲研究机构“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出版机关杂志《亚洲学报》(JournalAsiatique)。雷慕沙和克拉普洛特都是巴黎亚洲学会的创始会员,也是《亚洲学报》的第一批编委,并从其第1期开始发表汉学文章。面对法国人的挑衅,前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长考尔布鲁克于1823年3月15日在伦敦召集英国一批东方学家,成立“皇家亚细亚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雷慕沙出版《和阗城的历史》一书后,从1830年开始全力法译《佛国记》。1830年年底,雷慕沙首先撰写了一篇专门研究《佛国记》地理问题的专题论文,在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宣读。他在文章中还汇报了对《佛国记》的检查结果,宣布他从《佛国记》中得出的8点主要事实,或者说是《佛国记》的8点价值。[注]W. H. Sykes, ‘Notes on the Religious, Mor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India before the Mahomedan Invasion, Chiefly Founded on the Travels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Priest Fa Hian in India, A. D. 399, and on the Commentaries of Messrs. Remusat, Klaproth, Burnouf, and Landresse’,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RAS), Vol. 6, No.2, 1841, pp. 256-258.但雷慕沙翻译《佛国记》的工作尚未完工,便于1832年去世。
雷慕沙去世后,克拉普洛特得到了雷慕沙的译稿,也加快了自己研究、翻译《佛国记》的进度。但直到克拉普洛特于1835年去世,他翻译《佛国记》的工作也大功未成。克拉普洛特死后,他和雷慕沙的未完成译稿都落入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助理管理员兰德瑞瑟的手中。兰德瑞瑟于1821年进入法国政府于当年为培养皇家图书馆、皇家档案馆的管理人员而专门创设的巴黎皇家文献学院(École royale des Chartes),属于老校(Ancienne École)1821级第1届(Première promotion)第1班(Première section)学生,即皇家图书馆班(section de la Bibliothèque royale)的学生。[注]‘Liste des élèves pensionnaires de l’École royale des Chartes, publiée d’après les tableaux d’admission’,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tome 1, 1840, p. 43.兰德瑞瑟于1824年从皇家文献学院毕业后,进入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工作,长期担任研究院助理图书管理员(sous-bibliothécaire de l’Institut)。[注]‘Liste des élèves pensionnaires de l’École royale des Chartes, publiée d’après les tableaux d’admission’,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tome 1, 1840, p. 43.兰德瑞瑟在校期间并没有专修过汉语或东方语言,但他通过自学掌握了汉语和日语。兰德瑞瑟到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任职后,利用职务之便,得到雷慕沙和克拉普洛特的《佛国记》未竟译稿,并在前人的基础上,从1835年开始继续研究、翻译《佛国记》。
汉学家在翻译《佛国记》这种包含有大量梵语词汇音译的古代西行游记时,所遇最大困难是如何复原、转写书中的梵语地名、人名,也就是梵语名词的汉字音译还原问题。这是汉学家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必须依赖梵学家的帮助。兰德瑞瑟在翻译《佛国记》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了梵语名词的还原问题。在这方面,他有幸得到了老同学、法国印度学家欧仁·布尔诺夫(Eugène Burnouf,1801—1852)的帮助。布尔诺夫出生于巴黎,早年四处拜师学习梵语,掌握了梵语基础知识。1821年,布尔诺夫进入巴黎文献学院,属于老校1821级第1届第2班(Deuxième section)学生,即皇家档案馆班(section des Archives du royaume)的学生,[注]‘Liste des élèves pensionnaires de l’École royale des Chartes, publiée d’après les tableaux d’admission’,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tome 1, 1840, p. 44.与兰德瑞瑟同级不同班。布尔诺夫于1824年毕业后,并没有从事档案馆管理工作,而是开始四处教授梵语,渐成名家。1829年,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特设普通和比较语法讲座教授职位,聘布尔诺夫为第一任教授。1832年,31岁的布尔诺夫被选为碑铭学与美文学科学院院士。随后,布尔诺夫转任法兰西学院梵语讲座教授,成为法国梵语研究的头号权威。兰德瑞瑟和布尔诺夫因有同学之谊,在19世纪30年代关系甚为密切。因此,布尔诺夫经常到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帮助兰德瑞瑟考释《佛国记》的相关部分。[注]Bruno Neveu, ‘Les membr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d’après les Souvenirs (1834-1890) d’Alfred Maury’,Journal des savants,No.1,2005,p.137.布尔诺夫对于《佛国记》的考释,主要局限于梵语名词的还原,还涉及印度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在布尔诺夫的协助下,兰德瑞瑟于1836年最终完成了《佛国记》的法译本,并在巴黎出版。
由克拉普洛特、雷慕沙、兰德瑞瑟、布尔诺夫合作法译的《佛国记》,不仅是《佛国记》的第一个西文译本,也是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的第一个西文译本。布尔诺夫参与《佛国记》的注释,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即在中国古代西行高僧游记的研究、翻译方面,中国学家和印度学家第一次找到了共同语言,第一次联手合作。在以后翻译、考释、研究其他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的过程中,不乏中国学家和印度学家联手的范例。
三
兰德瑞瑟终生效力于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有掌握资料之便利。他在为该《佛国记》法译本撰写导论时,不仅局限于法显和《佛国记》,而是将视野扩展到其他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的活动和著作。兰德瑞瑟根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典”西方诸国各部的内容,对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的活动进行了一番梳理,除了法显之外,还有北魏宋云(活跃于6世纪初)、唐僧玄奘(602—664)等人的西天取经活动。兰德瑞瑟为《佛国记》法译本写的导论中,详细介绍了汉唐之际中国西行求法高僧们的活动,重点介绍了法显、宋云、玄奘的西游活动,最后提到:
法显(Fa hian)、宋云(Soung yun)和玄奘(Hiuan thsang),他们各自相隔一个世纪,每人都穿越了同一些地区。他们的游记,为截然不同、但又非常明确的各个时代提供了大量细节。这些细节,往往是相似的,但有时也不相同。如果对它们进行一番比较和讨论,便可以为宗教史编年确定一些非常重要的节点,也可以为5世纪、6世纪和7世纪的印度斯坦历史和地理提供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但是,法显时代的佛教状况,以及当时全亚洲的状况,都使得他的游记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因此,雷慕沙先生也更加看重法显的游记,将它放在其他两部游记之上,这并不是完全因为法显游记在时间顺序上排在最前面。[注]W.H.Sykes,‘Notes on the Religious,Moral,and Political State of India before the Mahomedan Invasion’,JRAS,Vol.6,No.2,1841,p.254.
兰德瑞瑟这段话预示,法国人在首选《佛国记》翻译的同时,也将下一步关注的目标指向了宋云和玄奘的游记,尤其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法国的中国学家们前仆后继翻译《佛国记》的工作,很快得到英国印度学家们的重视。第一个将《佛国记》法译本介绍到英国的人,是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理事长霍拉斯·海曼·威尔逊(Horace Hayman Wilson,1786—1860)。威尔逊于1808年赴英属印度担任东印度公司助理医师,此后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梵语,长期担任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干事(1811—1833年在任)。1832年,威尔逊竞聘牛津大学伯登梵语教授(Boden Professorship of Sanskrit)成功。他于1833年就任该职,并从1836年起兼任东印度公司图书馆馆长,从1837年起兼任皇家亚细亚学会理事长。
威尔逊担任皇家亚细亚学会理事长前不久,看到了雷慕沙等人的《佛国记》法译本。作为英国最重要的印度学家和梵语学家,威尔逊立即意识到《佛国记》对于印度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于是,他将《佛国记》认真研读一遍,撰写了一篇题为《雷慕沙先生从汉文翻译的〈佛国记〉或〈法显传〉概述》的长文。1838年3月17日和4月7日,威尔逊分两次在皇家亚细亚学会宣读了这篇长文,后发表于1839年出版的《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第5卷第1期上,[注]H.H.Wilson,‘Account of the Foe Kúe Ki,or Travels of Fa Hian in India,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M.Rémusat’,JRAS,Vol.5,No.1,1839,pp.108-140.长达33页,还附了两幅地图,一幅是不太准确的《法显旅行线路图》,另一幅是《法显在印度旅行地图》。威尔逊该文开宗明义第一段话如下:
对于那些关心早期印度情况的所有的人来说,对于那些渴望看到笼罩在伊斯兰教入侵前印度历史各个时期周围的模糊迷雾被驱散的所有的人来说(不管驱散迷雾的程度是多么有限),在最近欧洲大陆出版的一部书中,为他们呈现了几束最受欢迎的光亮。这部书来自于中国文献,它之所以已能被欧洲读者们利用,应归功于一批学者中最杰出的几位学者的天赋和勤劳,这批学者已经让巴黎变得辉煌卓越,因为那里成了一所培育中国语言和文学的学校。[注]H.H.Wilson,‘Account of the Foe Kúe Ki’,JRAS,Vol.5,No.1,1839,p.108.
随后,威尔逊根据《佛国记》法译本,将《佛国记》的内容概述了一遍。威尔逊在该文中还呼吁:
法显绝不是在基督教纪元最初几个世纪里访问印度的惟一中国旅行家,在他朝圣之前和之后,都有中国旅行家访问过印度。其中一位是玄奘(Hwan Thsang),他在7世纪上半叶旅行到印度并在印度漫游。兰德瑞瑟先生已经从一部关于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总集汇编《边裔典》(Pian-i-tian)中,辑录出并编纂、翻译了玄奘的旅行行程。而玄奘的原著是一部名为《西域记》(Si-iu-ki,orDescriptiondesContréesde1’Occident)的书,在巴黎是无法获得的。这篇玄奘行程的一些部分,对法显游记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说明材料,将在本文中不时地提及。看不到玄奘的原著,这让人感到非常遗憾,因为其中包含了在全印度更为广泛的游历记录,比法显游记还要广泛。但是,根据目前这种形式的玄奘行程,不容易确定有多少来自于玄奘本人的观察结果,又有多少是从其他来源搜集到的资料。本皇家亚细亚学会值得确定一个目标,就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从中国搞到这本书的原著,然后致力于对它的翻译。[注]H.H.Wilson,‘Account of the Foe Kúe Ki’,JRAS,Vol.5, No.1,1839,p.109.
威尔逊这段话不仅预示,《佛国记》法译本问世之后,欧洲学术界将把目光转向更为重要的玄奘《大唐西域记》,而且还暗示,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要在对中国西行求法高僧游记的研究和翻译方面,与法国人一试高下。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埃里加·考尔曼·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在华主编的《中国丛报》,这时也开始关注中国西北地区。在1840年7月出版的《中国丛报》第9卷第3期上,全文转载了威尔逊的《雷慕沙先生从汉文翻译的〈佛国记〉或〈法显传〉概述》一文,[注]H.H.Wilson,‘Account of the Foe Kúe Ki,or Travels of Fa Hian in India,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M.Rémusat’,Chinese Repository,Vol.9,No.3,July 1840,pp.334-366.只是错误地标明该文“选自《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1838年8月第9期”。
与此同时,雷慕沙等人的《佛国记》法译本也引起了英国军官出身的印度学家威廉·亨利·塞克斯(William Henry Sykes,1790—1872)的注意。塞克斯于1803年被东印度公司录取为军校学员,于1804年5月来到印度服役,于1831年返回英国,于1840年被选为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成员。在1841年出版的《皇家亚细亚学会会刊》第6卷第2期上,塞克斯发表了一篇长达237页的文章,标题同样很长,直译为《主要依据公元399年中国佛僧法显在印度的游记以及雷慕沙先生、克拉普洛特先生、布尔诺夫先生和兰德瑞瑟先生的注释而写成的关于伊斯兰教入侵前印度宗教、道德和政治状况的札记》。[注]Lieut.-Colonel W.H.Sykes,‘Notes on the Religious,Moral,and Political State of India before the Mahomedan Invasion,Chiefly Founded on the Travels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Priest Fa Hian in India,A.D.399,and on the Commentaries of Messrs.Remusat,Klaproth,Burnouf and Landresse’,JRAS,Vol. 6, No. 2, 1841, pp. 248-484.这篇长文实际上是一部书的分量,主要根据雷慕沙等人的法译本,对《佛国记》的内容进行了综合研究。
1848年,在加尔各答出版了一部《佛国记》的英译本,由英国印度学家约翰·瓦特森·莱德利(John Watson Laidlay,1808—1884)翻译。莱德利少年时学习实用化学,于1825年来到印度,主要经营一家靛蓝加工厂和一家丝绸加工厂,业余时间从事学术研究。1844年,莱德利突然放弃企业家身份,定居加尔各答,全力投入学术研究。1848年,莱德利在加尔各答出版了《佛国记》的英译本,书名直译为“法显的朝圣巡礼:根据雷慕沙、克拉普洛特和兰德瑞瑟的《佛国记》法译本转译,带有更多的注释和插图”。[注]J.W.Laidlay,The Pilgrimage of Fa Hian; from the French Edition of the‘Foe Koue Ki’of Rémusat,Klaproth and Landresse,with additional notes and illustrations,Calcutta,1848.泛泛而论,该译本勉强算是《佛国记》的第二个西文译本,或是第一个英译本。但由于莱德利不懂汉文,他的《佛国记》英译本并非根据汉文原文翻译而成,只不过是依据1836年法译本转译成英语的本子。严格意义上讲,莱德利的英译本不能算是真正的《佛国记》西文译本。不过,莱德利从印度学的角度出发,在书中增加了大量的注释和插图,也算对法显及其《佛国记》研究有所贡献。
自雷慕沙等人的《佛国记》法译本于1836年问世以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仅《佛国记》的其他西文译本层出不穷,而且玄奘《大唐西域记》等一系列西行求法高僧游记和相关著作也陆续被翻译成西方文字出版。中国古代西行求法高僧游记的各种西译本,在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学科领域,值得当下的国际中国学史、印度学史研究者加以研究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