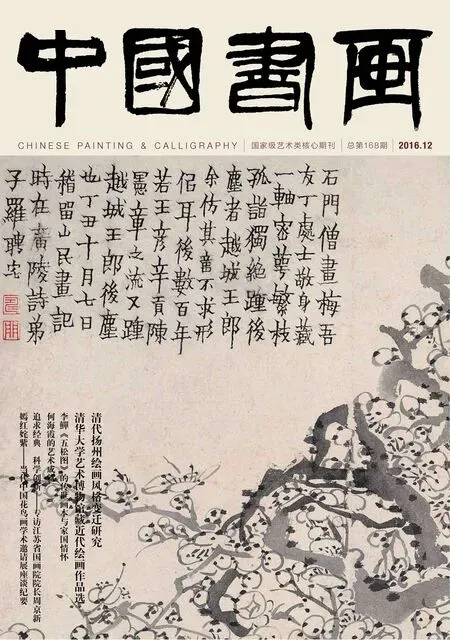《书林藻鉴》《书林纪事》的书学史意义
——马宗霍及其书学著作的学术史考察(下)
◇ 陈硕
《书林藻鉴》《书林纪事》的书学史意义
——马宗霍及其书学著作的学术史考察(下)
◇ 陈硕
作为至今仍旧被许多学者作为征引取资对象的《藻鉴》与《纪事》(尤以前者为甚),其究竟在20世纪书学史中占有何等地位这一问题,依然是需要被深入讨论与界定的。鉴于不少学人在著作中都将主于收录文献的二著视为寻常的资料汇编,因而如何看待其体例,又如何界定其在彼时书学境遇中的若干“长处”与“不足”,不独是我们研究马氏其人其著的重要问题,亦可作为梳理清末民初以降书学著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一、既有的相关评论
以《藻鉴》《纪事》为代表的马氏著作付梓后,除了祝嘉在《书学史》的《序》中有一些涉及体例方面的简短评骘,真正站在书学史的立场对其进行评述、定位,则尤以近二十年来为多。在一些概述民国书法史的专著中,二著往往因其在收录文献的丰富性而被归为资料汇编类型的通史著作,若孙洵《民国书法史》即将其列入“史传类”〔1〕。而对民国书法与书学著作有着专门研究目的的著作中,对其逐渐形成了两种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意见。前一种可以陈振濂为代表:
《书林藻鉴》本来是以辑录古代书家传统的资料汇编,每人列条,自三代以至清末,广收各家评论。对于了解古代书家的情况以及当时或后人对他的评价,有极重要的价值。但是除了在剔抉收罗之功外,马宗霍还在每一朝代前冠有一篇序论。洋洋洒洒数千言,对朝代与书法流变有着第一流的整理与提示,表现出他有惊人的史识。把这些序列按年代前后作单独串联,就是一部书法史—而且是带有个人看法、非同一般辗转抄袭的书法史;仅就这一点,马宗霍在民国书论史上就有特殊的地位。〔2〕
在上述分析之后,陈氏还谓之为“通史研究的一位先知”〔3〕。总结这段话,陈氏对《藻鉴》的褒扬其实主要针对两点:第一是资料的丰富性,第二是诸卷首《序》中体现的史识。与陈氏观点相近者还可参见姜寿田《民国书法思想史论》〔4〕、丁正《从传统到现代:近百年书学略论》〔5〕等文。而随着近年来书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具有新的眼光与学术评判标准的著作脱颖而出,若祝帅则从另一角度针对陈氏所言,予马氏二著以评论:
应该说,把马宗霍的《书林藻鉴》看做一种书法通史的研究,并且把马宗霍称为“通史研究的一位先知”,由于有王岑伯的著作在先,祝嘉影响更大的著作在后,使得这种说法似乎有些牵强。〔6〕
祝氏所持的标准,乃是着眼于在“现代意义”上对相关书法史著作“从知识生成到学科构建”以梳理。因而质疑陈氏的说法“牵强”,恐亦是认为马氏二著并不具备这种“现代意义”的范式。
综上而言,以陈、祝为代表的两种说法之所以参商有别,是因为其立论的角度不同。而不论是立足于资料性和史识,抑或是考察书法史研究序列中“现代意义”的生成,都是对同一问题不同面向的解读,自然也就无法以“是”“非”之类的语词分别加以评定了。但这不意味着对马氏二著的评论只能停留在上述诸说之间参酌进行,恰恰相反,对此问题的研究仍要回溯二著的文本本身—从总结其中表露出的相关特点(包括某些“不足”与“长处”)出发,进而放置在彼时的学术环境与20世纪书学研究的发展脉络中,以求对二著乃至书学学术史以有意义的反思。
二、二著的相关特点
祝帅的相关研究为我们评论马氏二著提供了新的思考,因而对其中相关特点的提要则不妨以当下“后见之明”审视下的若干“滞后性”特点入手。当然,所云“后见之明”即指出:我们无法判定以下陈列的若干“滞后性”特点即是一般意义上的“不足”“缺点”,将其视为有着鲜明时代烙印与个人做法但又多不为今人所身体力行的独特之处似乎更为妥帖。执其大端,笔者总结为以下三点。
其一,“游于艺”的态度。如上文所言,马氏作为章太炎门生,其基本定位是古典学术的专门学者。虽其在《藻鉴》的《序》中言及《流沙坠简》《书道大全》等外邦成果形式而带来了相应的紧迫感〔7〕,但其“固所不遑虑”(实际上表明了其多少还是考虑、顾及了)的正是“识小之讥”〔8〕,纵然其有写著书法“通史”的关怀在。而正是儒家古训的谆谆之教,使其在书学领域上的种种行为如撰写二著,只以一种花絮、偶然的现象出现在其学术生涯中。相较于后来的许多学者,成为一个书学领域的专门作家并倾注大量心力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书学研究,既非其用力所在,亦恐非其意愿所在。
其二,著作体例。《藻鉴》主于辑录文献,《纪事》主于搜罗异闻,且在人物的排列次序(若帝王、公卿、方外、闺阁)上都沿袭了成例,这恰恰是许多专门书学学者着力最多、突破最大的地方,毕竟就从古代文献中钩沉材料这一行为本身而言,古今并没有本质意义的差别。因而如何将大量的零散文献缀合,并以契合历史本来面目的方式加以叙述,是20世纪作者不断努力尝试的。执此观二著的相关体例,后来学人会进行反思:在历经大幅的删润与调整后,仅以既有的次序排列与叙述方式,诸《序》之外的大量文献条目能在何种程度上反映历史的真实?此外,马氏专门写著的《学书三要》与《笔谈》,涉及到对书写与审美本体的叙述方式,亦往往与许多明清书论若刘熙载《艺概·书概》等近似。换言之,马氏本人应不会将当下讨论的体例问题视为其落实“通史”关怀的障碍。

[东晋]王羲之 丧乱二谢得示三帖(摹本) 28.7cm×58.4cm 纸本 日本皇室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其三,个别观点。笔者在上节已经总结了其观点中的若干可商之处,这些观点虽多不能在框架意义上影响二著立场,但从若乡邦情节〔9〕等问题出发,仍可看出其对于全书的写作态度大抵是有一定弹性的。而出于自身的学术立场与交游倾向,其对彼时许多重要学术成果并不跟从,这似乎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若干“现代意义”的生成。
相较于需要见仁见智的“滞后性”,对二著所具有的许多优点则易于形成比较趋近的意见。笔者亦归纳为三点〔10〕。
其一,资料充实。这应是最无争议的优点,马氏《藻鉴》在《佩文斋书画谱》《国朝书人辑略》的积累上增补了大量文献〔11〕,虽然不足三千人的选录作者在数量上远较《佩文斋书画谱》等为少,但在适当删减只存于文献中且实际影响有限的作者之后,全书呈现出的信息反较原有者为清晰。特别是卷十二(清代部分)中的许多文献(尤其是曾熙、李瑞清、谭泽闿、向燊等人论书语)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因而无怪乎当下作者从中取资援引的亦不在少数〔12〕,毕竟在马氏裁剪之后的二著所具有的文献价值与学术意义,远非寻常抄撮旧籍者可比。
其二,叙述多元。据诸卷《序》中相关讨论便可知,马氏对于碑、帖与南、北之类的聚讼大抵持调和态度,在此纲领之下,诸卷中的大量引文亦随着相当数目的金石学乃至碑学文献的辑入变得愈发多元、立体,因而在同一作者名下的文献具有不同的时间、类型甚至褒贬倾向,这种不同以往的格局显然是有意营造的结果。以此考察马氏对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碑学作者相关理论的种种商榷甚至否定,并不妨碍其以十分开放的态度把各类铭刻以至彼时新出的各类材料纳入到其著作的系统中。相比于后来祝嘉在《书学史》中流露出的强烈的碑学本位主义,至少在特定作者及其名下文献这一层面上,马氏《藻鉴》的叙述系统更加开放,亦更加有吸纳包容的能力。
其三,见识卓越。马氏以古典学者的身份进行书学研究,自有其“非专业性”在,但这恰恰时期能够以旁观者的眼光跳出彼时书学的班班聚讼,将各类学术洞见转化为书学研究的基础,并进行大量精彩的论说。许多学者对《藻鉴》诸卷《序》有相当高的评骘,这是符合实际的。除了上文所述诸方面外,即使在并无马氏文字存在的许多文本中,其对于书法的相应见识仍通过其引文多寡及所涉内容的方面得到相当的反映。在这种较为严格控制下的文本与其专门的见解一道,成为整个书学见识的组成部分。
三、对二著书学史意义的评述
概论上述的特点,可以据以试讨论如何认识马氏二著在书学史上的意义。
以当下的学术眼光与标准去在此二著乃至马氏的其他著作中发现“现代意义”的生成,确实可以得出近于祝帅的结论。但二著近于“史料长编”的面目是否一定意味着其在当时的书学环境中没有“进步”之处,则可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若前文已及,二著的“滞后性”恐是马氏以“非专业”身份、心态写著使然。考察马氏写作为鲁迅所批评的《国学摭谭》〔13〕时只有26岁,而此文的学术倾向已十分清晰地反映了其“保守”的一面。而其后来的治学领域与做法即使与同出章门的朱希祖等人相比,亦稍显“保守”〔14〕。则在此人生与学术格局的影响下,其选择以“传统”的著述形式略舒己见诚不足怪。只是在“游于艺”的大纛下,“藻鉴”“笔谈”等一系列语辞的使用加深了这种观感。

[清]何绍基 行书论画语轴 94cm×57cm 纸本
至于其“史料长编”的面目,亦有几点需要申述。彼时诸类书法史著作的密集出现及相关边缘、出土材料的大量引入,亦是整个学术界的风气所尚,若罗志田谓:
由于史学为中国所固有,较易学习和从事,结果各新学术门类无意中仍走入史学一途。……进入民国后,“六经皆史”的观念更进一步发展到把过去的文字记录全部看作历史材料。章学诚已提到“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观点,胡适则对其进行“现代解释”,以为“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史”与“史料”的差别当然很大,但时人恰特别强调这一点。〔15〕
祝帅关于在著作范式、体例上的指陈确是考察“现代意义”生成的一个重要面向。但如果从史料扩充的角度加以审视,马氏二著对于各类新出材料若甲骨卜辞、简牍等以及在传统名家法书之外的铭刻材料、碑学文献的广泛推重与纳入,其实亦具有相应的“现代意义”,而这种多元的材料格局亦是其仍旧被今人较多取资的重要原因。诚然,马氏之于这类材料的认知恐怕不会与胡适的“整理国故”、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等相同〔16〕,甚至未必全盘信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但作为彼时风潮中的一个个体,马氏很可能在自身学术路径所能接纳的范畴内适度地在二著中注入了这个层面的“时尚”与“现代意义”〔17〕。
除此之外,以人为单位、以人名序列的资料纂集为书法通史的作法确实具有相当的局限性,恰如葛兆光所言:
这种写法还有一个也许并不自觉的假设,即我们看到的精英与经典的资料就是当时完整而真实的情景,历史没有进行淘汰与筛选,即使有,那也是准确而公平的,人们应当承认现存的历史记载和历史陈述的合理性。〔18〕
以马氏的学术路径(特别是在经学领域著作体现出的)而言,其在进行许多古典研究(包括二著)时很可能具有如葛氏所云的“假设”。唯其稍稍有别者,由于《藻鉴》的主体乃是据《佩文斋书画谱》《国朝书人辑略》等删润而来,相较于既有著作中数量惊人的诸代作者,马氏只选取了其中一部分加以调整,因而马氏对二著的判断可能未必是“完整”意义上的书法史。而参照彼时的大部分书法史著作,如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与祝嘉《书学史》等,其实都有这种以人为目做法的孑遗。不过这似乎不能用作臧否彼时人物的理由,而应归为《史记》《汉书》以降中国传统正史“纪传”体例的强大影响。
最后需要谈及的是马氏的见解问题。除了上引祝帅文外,尚有不少学者将稍晚的祝嘉《书学史》与《藻鉴》加以比较〔19〕。毕竟二者成书时间趋近,体例亦有相似处。从著作的叙述框架上看,祝嘉所著更为完整,有明显现代意义通史著作的色彩,文本条目亦能综合论之。但若从具体文献上考察,祝氏在《自序》中对《藻鉴》“重在品评”的指陈实际上并没有在己著中得到了彻底的改善:马氏逐条标目陈列,祝氏在多数情况下只选择其中数则连缀成文〔20〕。因而祝著的文本形态反与陈思的《书小史》等为近〔21〕。至于在马、祝著作《序》中体现的书学观点,笔者仍持马高于祝的看法。仅就立场而言,祝氏的书学认知仍有着极其强烈的碑学本位立场,诸卷之《序》每为碑学作家若康有为所论张本〔22〕。以下选录几则祝氏的代表文字:
石刻以北朝为至多,书体亦以北朝为至备,真书至此,尽善尽美,无以复加。〔23〕
书至于唐,雄厚之气已失,江河日下,非天才学力所能挽回。……以愚见唐代楷书诚不足道,行、草尚有可观。〔24〕
史虽称其(按:赵孟頫)于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然纤弱妩媚,乃斗草拈花之技耳,未足以语大也。……赵宗晋者也,取“二王”之糟粕,沿枣木之讹体,虽劳无功,多亦奚为?〔25〕
是代(按:明代)书学,真可谓江河日下,不足观者矣。……书学之废,未有甚于此时者也。〔26〕
自碑学勃兴,一扫帖学纤弱衰颓之势,大家辈出,追攀高古,小而造像、墓志,大而丰碑、摩崖,无体不备,无妙不臻。……清代享祚既久,碑学勃兴,书学之隆、书家之众,几欲度越唐代。〔27〕
将上述文字与上节所引马氏论书史者相比:孰持明显的碑派立场?孰主调和、客观的态度?孰以北碑为预设标准而臧否诸代书学?孰更多地从历史本来状态出发陈述源流?观者可以自行比较,此处不复赘言。
概而言之,二著中的许多优点与某种程度上的“滞后性”都需要我们更立体、客观地看待,而瑕终究不能掩瑜,仍无妨于《藻鉴》《纪事》作为迄今不失其用的民国时期重要书学著作的历史定位。
四、关于书学史著作评价标准的几点讨论
从宏观上讲,针对任何特定著作的评定,都应放置在其所处时代的大环境中进行。因而讨论一部民国时期的书学史著作(若马氏二著),只将其与前后的同类型著作进行比较,再以线性叙事阐释其自前而后的变化,恐怕难敷于用。这一方面,若曹军、薛龙春、严晖所纂《近现代中国书法史文献目录》〔28〕堪称同类成果中的优者,正是由于此《目录》将小学、金石、谱牒著录、字典、题跋、传记、目录索引等著作皆视为广义上的“书法史文献”,体现了编者较高的文献能力与历史眼光。加之祝帅对各类民国时期书学文献的钩沉,我们愈发可以看出一个“长阶段”的生成,其对于当下研究的意义确近于葛兆光所云:
依然试图描写历史变化的轨迹,只不过,它所依据的时间标尺不再是过去的王朝变动与政治变动,而是缓慢却又深刻地镶嵌于历史中的生活样式的变化。〔29〕
在此“长阶段”的环境映衬下,可以发现作为古典学术专门学者的马氏及其二著在彼时的“书学”氛围中,是以自身的眼光与做法运作了相关著述的写作。在体例与立场上与时而进、争得“预流”之果固然是相当一部分作者的选择,但即使在史学其他研究方向中亦非全部如此,何况书学的“现代化”在其中远不是最为激进、突出者。

[清]康有为致伍宪子书札(局部)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即是:许多在当下被视为锐意探索的作者,其对既有传统中的种种成果与做法可能并非持一味批判、贬抑的态度。若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之首即如是云:
书学是中国最早设科的一种艺术,六艺中不就有一门是“书”吗?它的历史固然很悠久,关于它的书籍也很不少,我们只要翻开《佩文斋书画谱》卷首所开的纂辑书籍一瞧,就令人有望洋之叹。本篇所以不说整个的书学史,单说那近代一小部分,只因为古代的书学,你也有论文,我也有点批判,已近够详备—不但详备,而且很复叠的了,所以索性撇开不说,单从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说起。〔30〕
在这一被顾颉刚着重称扬〔31〕的著作中,沙氏并未对以《佩文斋书画谱》为代表的相关古代艺术文献大肆臧否,虽然其不否认“详备”之余的“复叠”。据此可以窥见彼时的作者如沙氏,对何为现代意义上的书学史著作的撰写方式仍在相当谨慎地摸索之中。而另一方面,其仍视层层堆积下的庞大史料为通向书法史研究的重要门径,以至对以往的历史“撇开不说”,而设定《佩文斋书画谱》等未涉猎的晚明迄清代以降作为研究区间。这亦很显然并非持体例标准而言。因而在彼时新旧交集、潮流涌动的时代环境中,相关作者的探索、回应实难免于一定程度上的“各行其是”,有意以现代学术(在彼时或未明晰)的方式与书学本位的立场摸索现代意义上的书法史著述者,毕竟只是少数人。
最后,如何建立较为客观且具有相当历史眼光的评价系统,又如何判定孰为民国以降书学史中的著作“典范”。对于这类问题,若余英时在《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中针对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的关系有如下总结:
在任何一个学术中建立新“典范”的人都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具体研究方面他的空前的成就对以后的学者起示范作用;一是他在该学术的领域之内留下无数的工作让后人接着做下去,这样便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传统。〔32〕
其执此评价民国时期胡适的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
《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实是部深具开创性、革命性的论著。它的意义在于超越乾嘉各家个别的考证成就,把经史研究贯连成有组织的系统,运用的是西方哲学史研究方法。甚至本书最后还进行明显地评判(critical review)部分—即以实验主义观点来批判古人的学说。尽管这一部分尤其受到批评,可是不能掩其开创性的意义,所以我曾称此书是建立“典范”(paradigm)的著作。后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当然超越胡著,可是毕竟要晚了十几年后才刊行,而且在同时期讨论先秦诸子思想的学者事实上也增加了许多,但冯著并未突破胡著的典范。〔33〕
在忽视学科特点与研究气候的条件下,直以沙、马、祝的相关著作类比胡、冯关于哲学史的著作,恐难免于失当,因而无法笃定余氏所云即完全契合于本文所涉的领域。但至于其对学术评价标准中“典范”的归纳,则不啻为我们研究书学史提供了十分折中且宏观的参照,即考察一部书学著作是否是书学历史上的“典范”,既要观其自身的学术成就与示范价值,亦要观此后诸代学者是否对其中的相应问题、线索以回应与延伸,以至成为一个开放而又多元的系统。以此衡量为学界熟稔的民国时期诸类书学著作,未(完整)成文、未公开发表、未有实质意义传播者,自然不应被过分地左袒推重以至于何等崇高的境地。沙孟海及其若干研究〔34〕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此相符契的,但不论是因于右任撰《序》而享有一定时誉的祝氏《书学史》,抑或是迄今仍不失其用的马氏《藻鉴》与《纪事》,恐怕都不能以余氏所云的“典范”视之〔35〕。
综上所述,马氏的《藻鉴》与《纪事》出于其人、成于其时。对其中诸类优点,学界有较为趋近的意见;而对其相关“滞后性”,今人在查阅、取资之余,应抱以“了解之同情”。笔者无意以“典范”赘赞于此,但这毫不妨碍其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书学著作的历史定位,并继续在资料等层面上对当下的书学研究以十分有益的作用。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欧阳逸川

[近代]曾熙 行书论书画轴 145cm×47cm 纸本 1924年
注释:
〔1〕孙洵《民国书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140页。
〔2〕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河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
〔3〕同上。
〔4〕沙孟海书学院、《书法之友》编辑部编《近现代书法研究》,安徽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302页。
〔5〕同上,第328页。
〔6〕祝帅《从“知识生成”到“学科建构”—“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学术谱系》,见氏著《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第84页。
〔7〕前揭《〈书林藻鉴〉〈书林纪事〉》,第1页。
〔8〕同上。
〔9〕若马氏在《藻鉴》卷十二中连续列入了数十位湘籍作者,并在《笔谈》中对历史(主要是清代)上的湘籍作者频施赞誉。
〔10〕主要针对《藻鉴》。
〔11〕参见拙文《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纪事〉研究》,第20—29页。
〔12〕若当下最为学界重视的书法通史类著作—江苏教育出版社七卷本《中国书法史》中,丛文俊《先秦、秦代卷》、刘涛《魏晋南北朝卷》、朱关田《隋唐五代卷》、黄惇《元明卷》与刘恒《清代卷》等皆在注释与参考书目里注明参考、引用了此著。
〔13〕马氏《国学摭谭》连载于《学衡》第1、2、3、6、10 期。1922 年,鲁迅在阅读《学衡》(应是第1期)刊载诸文后,旋写下《估〈学衡〉》一文加以批判,径谓此刊“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并批评马文:“《国学摭谭》中说,‘虽三皇寥廓而无极。五帝搢绅先生难言之’。人能‘寥廓’,已属奇闻,而第二句尤为费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搢绅先生皆难言之,抑是五帝之事,搢绅先生也难言之呢?推度情理,当从后说,然而太史公所谓‘搢绅先生难言之’者,乃指‘百家言黄帝’而并不指五帝,所以翻开《史记》,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纪》,又何尝‘难言之’。难道太史公在汉朝竟应该算是下等社会中人么?”见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 册《热风》,第398 页。
〔14〕若马氏一生几不曾以白话文写著。
〔15〕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见氏著《近代中国史学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据此则愈可澄清一点:马氏并非因信奉碑学理论才收录各类金石学与碑学文献中的材料,这诚为彼时大的学术氛围中的合理行为。
〔16〕按:综合学术路径、师承及政治好恶等多方面原因,作为章门弟子的马氏极有可能对胡、傅等人的学术主张不予认同。若同门的朱希祖在《日记》中的评论可作为评估马氏相关看法的参照:“非若胡适之等政客式学者,既讲哲学,著《中国哲学史》半部,既未完全,又要讲文学、讲考据、讲史学、讲外交,而到底成一官僚而后已也,傅斯年辈尤而效之,学风扫地矣。”见《朱希祖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42页。
〔17〕同样,若将余绍宋著《书画书录解题》,邓实、黄宾虹编纂《美术丛书》等一系列事件统合考察,则彼时许多作者无疑都在自己认知结构、价值判断的框架内,以各自的方式进行着某种保存国粹、赓续文化的著述活动。在此风气中,其人其著便很难用“进步”或“保守”等语词一概而论,而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恐怕是其人对彼时国家境遇、文化脉络的深沉思绪。
〔1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19〕若邱世鸿《再论祝嘉〈书学史〉的现实意义—兼与马宗霍先生〈书林藻鉴〉相比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96页。
〔20〕从对马氏成书方式的研究推而论之,笔者亦不认为《书学史》为祝嘉以从无到有的过程所独立完成。
〔21〕但《书学史》与《书小史》在体例上不同的一点是:前者将很多具名的书学文献系于其作者名下。
〔22〕按:祝氏后来专门撰有《书法源流》一文,首列“商朝以前的书法”,此后大致依照朝代顺序排列。其文辞所涉范围大抵与《书学史》诸卷首的《序》接近。考察其对相关问题的叙述,比《书学史》稍缓和,但其本于碑学立场的种种褒贬并无根本改易。见氏著《书学论集》,金陵书画社1982年版,第1页。
〔23〕祝嘉《书学史》,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9页。
〔24〕同上,第115—116页。
〔25〕同上,第213—214页。
〔26〕同上,第232—233页。
〔27〕同上,第270—271页。
〔28〕前揭《近现代书法研究》,第459页。
〔2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第16页。
〔30〕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见氏著《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31〕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32〕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增订本)》外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45页。
〔33〕余英时《学术思想史的创建与流变》,见氏著《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16—417页。
〔34〕按:此处指沙孟海撰写《近三百年的书学》之后在书学史方面的各类研究。
〔35〕按:如前文所及,马氏著作在后世被较广泛地征引、取资,主要是以其资料性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