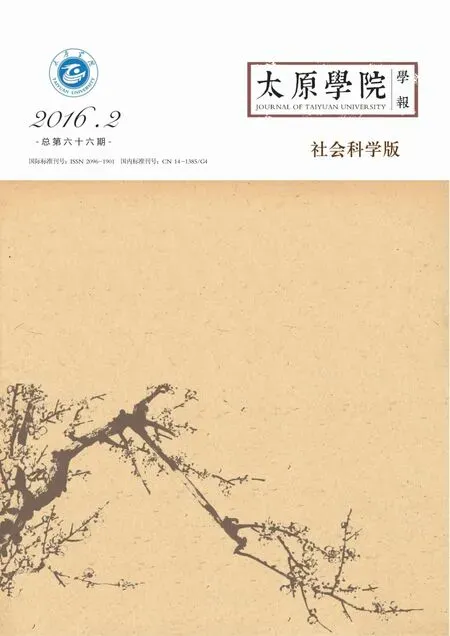错案追究制理论根基的反思
柳 一 舟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错案追究制理论根基的反思
柳 一 舟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第35条一定程度回应了一直以来学界关于错案追究制的热烈讨论,但如何落实该条意见需正确认识到错案追究制的理论根基——法律的确定性理论。对法律确定性理论进行必要的思想史梳理,并尽量展示其全部面貌,会发现该理论大概经历了从确定到否定再到纠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司法程序确定性的重要性不断被凸显,通过司法程序的确定有利于达到司法判决的确定性。反思我国错案追究制,其与所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亦不符合法律确定性理论的发展要求。恢复司法理性,并进一步构建其他科学合理的具体法律制度以实现错案追究制所追求的目标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错案追究制;法律的确定性;唯一正解;法官责任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35条规定完善司法廉政监督机制,其中表明将实现纪检监察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的有序衔接,建立法院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该意见一定程度是对一直以来学界关于错案追究制热烈讨论的回应,乐观而言,学界主张的全国统一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取代分散的错案追究组织将会成为现实。但为防止陷入“钱穆制度陷阱”,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单项的监督制度不可能真正有效发挥其实效,还需一个制度体系,且制度的设计需以坚实的理论作为支撑。不管是错案追究制也好,还是法官惩戒委员会也罢,在中国语境下,人们习惯从判决结果的好坏出发来评定主审法官的功过是非,这其中蕴含了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一个案件只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判决,否则就是错误的判决,就是“错案”。唯一正确的判决是由法律确定性的理论决定,因而,当我们在讨论错案追究制时,法律确定性理论会一直相伴随。法律的确定性符合法的价值追求,有利于人们增强对自身行为的后果以及他人对自身行为的反应的可预期性。但法律的确定性并不当然意味着法律就是确定的,利益法学、批判法学、现实主义法学以及社会法学等都对法律的确定性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和质疑。因而,反观《意见》第35条,我们不应将其作为讨论的终结点,而应进一步梳理清错案追究制背后的理论,并展示其全貌,继而检省各式各样的法官责任追究制,以期为《意见》第35条的真正有效落实在理论层面献上绵薄之力。
一、错案追究制以法律的确定性为理论根基
法律的确定性折射出理性主义的光辉,其可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理解,前者主要有三种用法:其一指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即某一法律在制定或确定之后,其内容在一段时期里要保持相对不变的特性;其二指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即法作为一种制度性社会存在,人们能在遇到法律纠纷时明确知道该适用什么法律;其三指表达上的明确性,与道德等规范相对而言,大部分的法律是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形式出现的,它用社会上通用的词语对人们的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因而它能使人们一目了然,清楚地了解法律的意图,在理解上较少发生歧义。[1]而从司法角度看,法律的确定性是主要指法律结果的可预测性与判决的唯一性。以作者观之,法律的确定性不外乎这三点:法律内容的确定、法律推理的确定以及两者之结合达到的判决的可确定。但不容忽视且十分重要的还有法律程序的确定,正因此,法律内容和司法判决才能有机联系,法律推理的逻辑性和客观性也才能得以保持,进而人们才信服司法审判活动不是主观臆断和权力任性,故又可谓合理的法律程序是法律适用结论稳妥性的前提。
错案追究制正是以法律的确定性理论为根基,虽周永坤教授认为:“法律的确定性程度是不断提高的,而错案追究制却是从有到无,可见法律的确定性与错案追究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或错案追究制不以确定性为依据。”[2]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错案追究制隐含着一个被大众自觉或不自觉接受的理论,即一个案件只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判决,否则就是错误的判决。[3]人们怀着朴素的法感情和是非观,以及对司法公正的期许,认为所谓的依法裁判是查清了事实,理解了法律条文,就自然能得出唯一正确的裁判结果。
法律的确定性散发出理性主义的光辉,早在古希腊就进行了理论尝试,亚里士多德认为与个人的统治相比,法律的统治是一个较好的选择。而作为个人,即使是最完美之人,都会受到各方面的情绪影响,法律却不然。他亦从对希腊各城邦的历史考察得出各种统治都是不确定的,惟有法治国家才值得推崇。由此,他主张法治,而反对人治。亚里士多德敏锐地捕捉到法律的确定性对社会的意义,可以说,但凡后世之种种与之相关的言论都绕不过这座“喜马拉雅山”。如果说古希腊为法律的确定性打下了哲学上的基础,则古罗马在法律确定性上就进行了实践尝试。这其中,西塞罗居功至伟,在他的思想影响下,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法典》的颁布更是将法律确定性向实践层面推进了一大步。当然,在这个时候关于法律的确定性更多地只是停留在对法律内容是否确定的讨论上,还没有体现到司法判决结果的确定性。而关于司法判决结果的确定性,要等到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该时期的启蒙学者极力推崇形式理性,反对立法任性和司法的专横。到19世纪,这种理性法律主义思潮对西方国家的法治化起到了强大的推动力。始自1804年法国《拿破仑法典》的颁布,近代西欧法典化运动使法律内容更进一步趋向了确定,一个世纪后的《德国民法典》更是将法律的确定性奉为圭臬,这些法典都在形式上具备如下要素:(1)法律规则的形式性;(2)法律规则含义的明确性;(3)法律效力的普遍性;(4)法律规则适用的一致性;(5)法律规范体系的自洽性;(6)规则运用程序的稳定性。因此,完备的法典被视为“自动售货机”,只要投入法条和事实,就能得出正确的结果。在这些时期法律的确定性被视为经典理论,法律的确定性背后的哲学基础也即理性主义,人们相信凭借理性可以出创造出一部逻辑缜密、涵括万千社会的法典,尤为重要的是能带来法治的可预见性和法律秩序的稳定。
而错案追究制也正是基于理性主义法律观而构建,人们相信凭借法律文本形式的合理性而当然得到判决的确定,明确性的法律规范能在民众心中建立起相对固定的“行为——法律后果”之间的预期,从而使法律规范对于它所指向的人具有拘束力,正是法律规范的“明确性”保障着法律功能的充分发挥,并逻辑地娩育出法律规范之稳定性特征。[4]因而,错案追究制一定程度而言,符合法治国家的要求,能体现出法治的可预见性和法律秩序的稳定性。此外,同法律确定性理论般,还体现出对司法权的制约和对司法腐败的遏制,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法律公正的追求。但与这个时期对法律确定性的迷信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同,而后法律的确定性遭到了诸多法律流派的批判与诘难,这必然也动摇了错案追究制的理论根基。
二、错案追究制理论根基的动摇
如果说错案追究制是以法律确定性理论为根基相支撑的话,那该理论根基是不牢靠的,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古典自然主义法学派后的几个世纪里,许多法学派都对其进行猛烈的批判和百般诘难。在中国语境下,暂且不论这些批判理论正确与否,其亦存在诸多“中国特色”问题。
(一)对法律确定性理论的诘难
为避免教科书式地简单罗列各学派反对法律确定性理论之观点,本文只从中简单采撷一二以作必要论证。最早对法的客观性提出不同意见的是目的法学派代表人物耶林,在他看来“概念天国”的衍生品成文法典根本不可能解决丰富多彩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而目的才是法律的创造者,无目的的法律规则是不存在的。而在耶林思想引导下的利益法学派更是认为不应该用法律的推理来虚幻性地掩饰法律一定程度存在缺陷和空白,因而,要在现有法律规则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论得出令人满意的决定不总是可能的。这就需要法官发现法律规则的目的,通过创造性的、合理性的诠释去平衡互相冲突的利益。[5]在英美法中,由于法官造法的存在,所以对法确定性的批判也更为猛烈。霍姆斯说法不过是对法院实际上将做什么的预测而已。弗兰克更是批判到了极致,他认为法律永远是不确定的,法律的确定性观点基本上是一种法律神话,而产生这种神话的原因是儿童的“重新发现父亲”的“恋父情结”。而法律实证主义者哈特有关“空缺结构”论更是对法律确定性的有力否定,他基于以下理由认为法律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个语义上、逻辑上封闭的体系:其一,立法者知识的有限性;其二,用以表达规则的一般语言所具有的空缺结构;其三,现代立法技术都重视在法律中预留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留待精明的官员在未来社会出现纠纷时作出选择。[6]法社会学派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质疑和看法,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提出著名的“活法”思想,他认为,社会的变化、语义的变迁,已有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命题必然也随之变化。而美国社会学法学家庞德继续予以发挥,他认为法律有“书本中的法”与“行动中的法”之分,因而,他反对概念主义法学,竭力主张法官应该抛弃原先那种从既定概念之中推导出具体判决的司法理论。
综上,认为法律不具有确定性的学派大抵有如下几点原因:(1)法律内容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法律并不能预知未来,对未来的规划不可能在法律完全控制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文字的表面含义与它所要阐明的目的之间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且任何成文法都是以文字作为依托,文字的局限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带到了成文法中来。(2)法律使用的不确定性。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司法人员的个性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的思维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倾向,在判断作出之前,法官很少先从大前提出发,严格按照三段论推出结论。相反,他们多会先形成一个模糊不确定的结论,再由此出发,寻找能够证明这个结论成立的前提。(3)事实认定的不确定性。囿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和诉讼活动独特的运作规程,真正作为判决基础的事实并非案件的客观事实,而仅仅是法律事实,客观事实能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审判程序本身具有或然性。(4)法律解释的不确定性。对客观的文本解释所引发的主客观之间的对立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文本内容确定性是支撑形式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正是这样,法律的确定性才有可能。但语言哲学的发展使这个条件预设岌岌可危,哈特所提出的“空缺结构”理论即为有力证明。
(二)中国语境下错案追究制可能产生的弊端
法律确定性理论的动摇在中国语境下造成的直接后果,即自错案追究制实施以来,相关法律法规很难对“错案”进行清晰界定,其定义以及追责的范围、程序和方法等一直以来也都未能明确予以规定,甚者,错案追究制中的“错案”一词还易与冤假错案中“错案”一词相混淆。此外,我国司法不独立,行政干预司法,政策先行,某种程度上使得法律的不确定性在我国成为“显学”,法官很难冒着职业危险严格依法裁判,特别是在“疑难案件”的处理上。此时,法官通常会选择正常途径以外的方法来转嫁和规避风险,诸如以下的几种主要方法:
1. 裁判前的沟通
在当前基层法官办案数量激增的背景下,相比严格按照司法程序审理案件,然后做出一份精彩绝伦的判决书相比,法官为保证办案的效率和质量一般会心照不宣地在裁判前积极与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沟通。沟通虽能积极有效掌握案件事实,但更为主要的是美其名曰之下的“沟通”实际上是双方互探底线、利益分配以及与当事人之间多轮且充分的“讨价还价”的过程,案件事实的严格查明更多地被“做工作”式的“和稀泥”手段代替。因此,这要求法官拥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个人魅力以及其他不可言状的“能力”,借此设法说服双方,使双方都能接受不再那么重要的判决。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蔑视程序,强化调解、听从民意、案结了事以及社会效果等司法政治口号会大量充斥在法官的“内部管理措施”中。这导致的后果将是法律的虚无主义,法律程序的荡然无存,且还与错案追究制的初衷背道而驰,不利于法官专业素质的提升,而锻炼更多地则是法官的政治素质。近些年来,与该做法相类似的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调解,诸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以及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些做法所产生的弊端也亦然,不再赘述。
2. 个案请示或汇报制度
该做法之弊端显而易见,其让现存的审级制度被悬置,名义上的两审终审制变为一审终审,当事人欲以二审上诉来实现权力救济之目的亦将难以实现。此外,还违背了司法审判的公开性原则和亲历性原则,这不但不利于法官的独立审判,还与现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之方向相左。甚者,也严重违背程序正义,程序正义要求原被告双方的质证和辩论并不仅是说给对方听,或简单地一味情绪宣泄,而很大程度上是有针对性地向裁判者诉说,希冀裁判者能最大限度上听取并采纳自己的意见。个案请示或汇报制度,使得原被告双方在庭审过程的质证和辩论变得毫无意义,双方的对抗也就只是无意义的“空气振动”,双方程序权利的行使也就徒具形式。[7]未实际审理案件的法官并不能有效地掌握案件事实和原被告双方的意见,而亲历了审判过程的法官却要以非“决定者”的身份承担错案责任,这显然又不利于错案追究制的落实。
3. “疑难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按理说,“疑难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无可或非,但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如同个案请示制度般违背了审判活动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制度,诸如直接审理原则、审判公开原则和回避制度。且在中国语境中,因为“疑难案件”判断标准本身的模糊不清,因人而异,因而我们很难知道究竟哪些案件有可能或实际进入了审判委员会的讨论范围,其疑难复杂性又表现在哪。这也可能最起码造成如下三种不良影响:一是主审法官出于职业安全都会选择将拿捏不稳的案件移交审判委员会来转嫁和规避风险,不利于法官职业素质的锻炼;二是审判委员会不公开的案件讨论方法不利于社会监督,容易滋生司法腐败;三是审判委员会某种程度上就是法院内部结构集权的象征,且在当前审理的案件一般涉及到重大民生问题,因而需紧密配合行政机关以实现社会效果和整体利益,因而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司法的不独立。
三、错案追究制理论根基的纠偏
面对滑向不确定性的法律,人们开始对司法判决究竟有没有确定性产生疑问,遑论疑难案件的判决结论?于是,法学家们纷纷找寻理论上的破解之道,其中尤以德沃金的“唯一正解”理论最为引人注目,之后哈贝马斯在对其理论批评的基础上提出并阐释了“程序确定性”理论,此两者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法律确定性理论的纠偏。
(一)德沃金的“唯一正解”理论
德沃金既不同意现实论无视法律自身内部确定性的观点,也不同意实证论无视法律之外的原则、背景、情境的观点。他认为法官在判决的过程中存在先入为主的前见,但这一前见并不等于法律现实论和诠释学的“前理解”,在德沃金看来这些“前理解”法官可通过“权利理论”为中介,运用实践理性对其所包含的各要素进行合理重构,继而确定谁享有哪些权利,而这些权利又必须能够满足法律自身的确定性要求(事实性)和正当性要求(有效性)。[8]此外,法官为实现事实性和有效性在判决过程中的具体有机联系,德沃金还提出了“建设性解释”,这一解释是整体性法律的实现方法,该方法预设的理论前提认为法律是一个完美的体系,之所以完美,是因为法律内含了任何案件,包括疑难案件的最佳解决方案。[9]这一解决方案主要借助于德沃金所提出的法律的构成要素中“原则”和“政策”二要素来实现,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即使无明确“规则”可依,尚有“原则”和“政策”,它隐藏在浩瀚的判例之中,而要找到它,则可通览整个沿袭中的司法实践来实现,在最终意义上,法律的整体将供应法官足以解决一切案件的法律依据。[10]
但德沃金的“唯一正解”理论也遭到了各种诘难,其中最为有力和激烈的为“不可公度”论,该理论认为在原则和原则之间的选择上,法官很难找到一个客观和具有说服力的标准或尺度。此外,德沃金对法律确定性的拯救还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现实中的法官很难拥有十分完备的的知识和智慧,且难以超越出他所在的社会、传统、历史来客观地俯瞰案件,而这样一位“赫拉克勒斯型法官”是德沃金合理重构理论的依托者。
(二)哈贝马斯的“程序确定性”理论
如果我们说德沃金的“唯一正解”理论所追求的是判决结果的确定性,那哈贝马斯的“程序确定性”理论则基于对法律确定性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理解,追求程序权利的确定性。他认为,德沃金的理论并没有真正解决法律确定性的问题,因为他并没有看到法律不确定性产生的真正原因是内在于法律语言之中的事实有效性和规范有效性之间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哈贝马斯大致的理论推理如下:首先,否定德沃金“赫拉克勒斯型法官”那种独白式、孤立式的审判视角,而基于交往行动理论将审判转变为主体间性的交往视角,是对话式的。在哈贝马斯看来,“赫拉克勒斯型法官”存在缺陷,判决结果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需从主体间的交往理性中得到论证,“道德论辩应完成的任务,不能以垄断方式完成,必须要有一种合作的努力。道德论辩的目的在于重建一个被破坏的合意,因为在规范引导的交互作用范围内的冲突,直接发源于一个被破坏了的规范的同意”[11]。其次,以商谈程序将道德商谈转入到法律商谈,道德商谈有可能是判决直接绕过法律原则而付诸道德原则的论证,不利于法律判决的确定性,而商谈程序能凭借其复杂性和技术性来避免此种不良后果。最后,商谈程序是保证判决自洽性和正确性的关键,它需要有一个“理想的言谈情景”:参与主体必须是理性的;参与双方需保持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的要求;目的是达成共识。而法庭程序某种程度上是理想的论辩条件和现实中种种限制条件的一种折衷、妥协,法庭程序是一个能使得公正审判得以可能的制度平台,离开这个平台,所有妄图直接获得审判的公正性的努力都是不可能的,哪怕由一个全能的法官来审理也不行。
但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指出哈贝马斯的理论不完美之处,“论辩规则空洞无物,丝毫没有谈及方式和内容,例如根本没有涉及我们应该做什么。并且,合意并不确保真理。”[11]哈贝马斯的“程序确定性”理论关心的不在于主张的内容,而在乎主张的产生方式;不在于主张的内容是否合理,而更多是关心其是否具有合法性,最终的目的是希冀创造一个理想的交谈环境,所有参与者都能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地发言。但世上本无完美理论,哈贝马斯一以贯之所追求的程序论很多程度上实现了对法律确定性理论必要的纠偏,他重点想说明和解决的是法律确定性理论不能不顾及法官的专业技术特征,法官为确保法律判决的正确性和有效性需运用程序原则,且须在参与者和公众面前说明和论证其判决,并积极保障参与者可在审判过程中自由交换理由和自由论辩。[12]58
因而,德沃金和哈贝马斯的理论对错案追究制理论根基进行了很大程度上的纠偏,虽各自理论或多或少存在一点瑕疵,但瑕不掩瑜。从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即若想实现错案追究制所追求的目标,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为法官自身的专业素质提高;其二为司法活动应是一种商谈的平台,而司法程序的确定性确保了这一商谈得以理性正常进行,最后双方能达成共识。
四、总结
本文大概对错案追究的理论根基做了一简单的思想史理论梳理,现可做以下几点简单观点陈述:(1)错案追究制以法律确定性为理论根据,两者都散发出理性主义法律观;(2)法律确定性是相对的,法律不确定性也是相对的。尽管法律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制度,但由于法律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因此就可能给解决某些个案带来困难。(3)错案追究制的理论根基一定程度上被动摇,但绝非达到了被否定之地步,理论自身具有纠偏功能,法律确定性不应因个别的、特殊的疑难案件而完全被否定,它仍是人们孜孜追求的梦想。法律从确定到不确定,这是对社会生活的反应,同样之道理,从不确定到确定亦然。
反观我国现阶段的司法实践,“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理念和无法可依的状况已成过去式,法官队伍也并不像以前整体素质偏低、职业道德较差,如何坚持现行法律独立审判才是当务之急,确保司法判决的确定性仍是法官孜孜追求的目标。虽然该制度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意义,诸如提高法官职业素质、遏制司法腐败以及保证司法公平之实现,但其更多是政治思维权宜之计的产物,甚者,其理论根基更值得探讨,因而错案追究制绝不能成为悬挂在法官头上的“利剑”。法律的确定性经历了从确立到否定继而纠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程序的重要性逐渐被凸显出来,确保程序性的确定更能保证案件结果的确定。因而,以司法程序为重要切入点,恢复司法的理性,实实在在多点科学合理的举措更显重要。宏观而言,追求司法程序的确定性,让每个参与者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站在各自的立场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作出充分的解释和说明,与此同时,也应尽可能吸收公民参与进司法审判的过程中,推动司法公开。此外,法律职业共同体内也应形成一种辩论、商谈的氛围,就疑难案件的标准以及解决方法展开讨论,且对现行法律制度提出必要的批判和改进意见,以期对法官的审判提供智力支持。微观而言,《意见》第35条规定给我们提供了启示,即完善司法廉政监督机制,将纪检监察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的有序衔接,建立法院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限于文章篇幅,如何在基于法律确定性理论的清晰梳理上,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反思错案追究制,以及进一步构建具体法律制度以落实《意见》第35条之规定,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何勤华,严存生.西方法理学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221.
[2]周永坤.错案追究制与法治国家建设——一个法社会学的思考[J].法学,1997(9):7-11.
[3]王晨光.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与“错案追究制”的误区[J].法学,1997(3):5-11.
[4]杨剑波.刑法明确性原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25.
[5]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10.
[6]严存生.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66-367.
[7]朱孝清.司法的亲历性[J].中外法学,2015(4):919-937.
[8]陈伟.司法确定性的寻求——析哈贝马斯的“程序确定性理论”[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1):42-46.
[9]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力[M].信春鹰,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02-106.
[10]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66-67.
[11]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M].米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7.
[12]陆玉胜.商谈、法律和社会公正——哈贝马司法哲学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196-200.
[责任编辑:岳林海]
Reflection on Theory Foundation of “Misjudged-case-investigating Mechanism”
LIU Yi-zhou
(Wang Jian Law School,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China)
Abstract:The Article 35 of《Supreme People’s Court on Opinions of Deepening Reform》responds to the lively discussion about the Misjudged-case-investigating Mechanism, But how to implement this opinion needs us to correctly recognize the theory foundation of misjudged-case-investigating mechanism——the theory of legal certainty. Carefully sort deterministic theory of law is necessary, and try to show all of its features, you will find this theory probably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from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orrection to the negative and then to the rectifying. In this process, the importance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continue to be highlighted uncertainty, through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judicial process is helpful to achieve judicial decisions reached certainty. Reflection of the Misjudged-case-investigating Mechanism runs counter to the objectives pursued, nor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legal certainty theory. Restore the judicial rationality, and further build other specific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legal syste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roblem is a priority goal.
Key words:misjudged-case-investigating mechanism; legal certainty; only positive solution; judge responsibility system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901(2016)02-0024-06
作者简介:柳一舟(1990-),男,湖北监利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收稿日期:2016-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