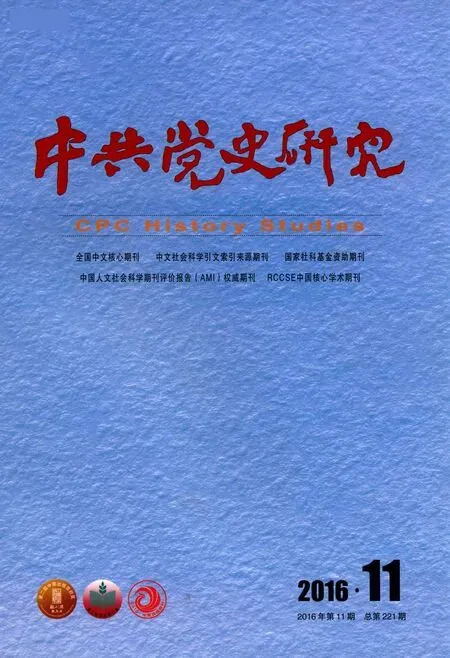文学旗手的调整与延安文艺新方向的确立
郭 国 昌
·专题研究·
文学旗手的调整与延安文艺新方向的确立
郭 国 昌
设立文学旗手是延安文艺体制建构的基本方式之一。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分界线,解放区文学旗手的建构经历了前后两个明显阶段,解放区前期文学旗手的建构以鲁迅和高尔基为中心,解放区后期文学旗手的建构以赵树理为中心。解放区前后期文学旗手的调整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文艺理论”为主体的延安文艺政策的形成,也表明以工农兵为核心的延安文艺体制的确立,解放区文学的发展由此走向了以“大众化”为方向的体制化。
文学旗手;鲁迅;高尔基;赵树理;纪念大会;文艺体制;工农兵;大众化
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选择自己倾心的文学大师作为个人从事文学活动的偶像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然而,在解放区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文学偶像的选择并不纯粹是作家的一种个人行为,而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机构以确立文学旗手的方式进行的。从鲁迅、高尔基到赵树理,文学偶像的选择被纳入解放区文学的生产体系当中,成为延安文艺体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分界线,解放区文学旗手的建构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鲁迅和高尔基是解放区前期由中共确立的文学旗手,赵树理曾一度成为解放区后期文学旗手的最佳选择。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毛泽东作为文艺权威之地位的确立,赵树理则逐步转变为以“毛泽东文艺理论”*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54页。为主导的中共文艺政策的实践者。因此,解放区后期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旗手。从鲁迅、高尔基到赵树理,文学旗手的调整过程既是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作家的规范过程,也是知识分子作家融入延安文艺体制的过程。
一、鲁迅:解放区前期文学旗手建构的革命性面相
解放区前期中共选择鲁迅作为文学旗手表明了延安文艺体制构成的革命性面相。“五四”新文学革命发生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革命文学迅速兴起,到20世纪30年代鲁迅被尊奉为左翼文学运动的“导师”。因此,对鲁迅的推崇意味着解放区文学继承了左翼文学的“血统”,取得了新文学革命以来的革命性传统。
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的建构是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由中共主导下在解放区全面展开的,形成了以中共为中心的政治意识形态规范下的鲁迅形象。中共从革命的政治立场和实际要求出发,将鲁迅形象的塑造纳入自身的文化体制建设当中,其最终目标是要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让鲁迅形象成为解放区文化运动中的文学旗手,让鲁迅所走的道路成为“中华民族一切最优秀、最有骨头的、最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所必然要走的道路”*洛甫:《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中国文化》1940年第2卷第2期。。因此,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是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载体,是经过充分政治化了的产物。
在解放区的文学活动中,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的建构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作为解放区政治权威的毛泽东的观点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1937年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公开发表了《论鲁迅》的演讲,提出了“鲁迅精神”的三个方面的内涵,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认为鲁迅“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0页。。这是鲁迅逝世后中共领导人对鲁迅的首次公开评价,意味着以中共为中心的政治化的鲁迅形象建构的正式开始。毛泽东虽然把鲁迅与“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进行对比,称颂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但毛泽东对鲁迅“空前绝后”的评价并不是从文学层面进行的解读,而是从政治立场作出的肯定性认识。这种评价是在抗战的现实环境下作出的,与中共正在努力“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的任务相适应。因而,鲁迅理所当然地被塑造为“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至于鲁迅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创者的身份和地位,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背景下很自然地就被遮蔽了起来。
如果说毛泽东在1937年的讲话中对鲁迅的评价是与抗战的现实环境密切相关的话,那么在1940年的讲话中对鲁迅的评价则是与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目标直接联系着。随着中共在民族革命战争中政治地位的提升,由中共主导的文化建设也随之逐渐展开。作为解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之一,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0年1月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报告,提出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著名论断。毛泽东从“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政治高度出发,提出了“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的要求,而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在“五四”以后由“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鲁迅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毫无疑问,较之1937年的“圣人论”,1940年的“旗手论”对鲁迅形象的政治性概括更为全面。可以说,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由此得以确立。然而,必须看到,毛泽东对鲁迅形象建构的政治立场更为直接,意识形态目的更为明确。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和新经济服务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4页。。也就是说,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必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必须要选择一个能够代表“新文化”的人物作为一面旗帜,而从“左联”时期就被尊为“革命文学”盟主的鲁迅自然就变成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显然,毛泽东看到了“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是,毛泽东对建立“新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并不是从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角度获得的,而是从政治和文化的主从关系角度提出的。在“新政治”与“新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新文化”是从属于“新政治”的,是为“新政治”服务的,“新文化”并没有获得自身的独立性。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虽然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建构起来了,但是,在“新政治”规范下的鲁迅形象必然是从属于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要求的。鲁迅虽然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旗手,但是他必须是在“新政治”的规范下为“新政治”服务的文学旗手,在“新政治”与“新文化”关系中建构起来的鲁迅形象必然带有一定的政治现实性。因此,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蕴涵着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
当毛泽东以解放区政治权威的身份为鲁迅形象的建构确立了最基本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内涵以后,解放区出版的一些重要报刊也先后发表了大量对鲁迅形象的文学旗手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行全面阐释的文章。由于这些报刊大多是由中共主办的,因而,这些报刊上发表的相关论述就不但具有了政党的集体性特征,而且这个传播过程也就自然隐含了政党的权威性力量。正是凭借报刊作为现代媒体的传播功能,毛泽东将鲁迅形象提升为文学旗手的有关论述迅速传向整个解放区。因此,解放区的报刊承担了传播毛泽东将鲁迅确立为文学旗手的任务,在整个解放区的鲁迅形象建构中发挥着特殊功能,成为从文化传播层面建构鲁迅形象的重要推动力。
解放区的报刊作为鲁迅形象的建构力量主要是通过发表论述鲁迅形象的文章实现的。在延安文艺整风以前,解放区报刊上发表的纪念鲁迅的文章虽然都是个人所写的,但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又常常是在中共党内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因而,这些文章大多自觉地回应了毛泽东的“讲话”或“报告”,自然地发挥了将鲁迅形象建构为文学旗手的功能。在1938年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解放区的报刊上陆续出现了一系列阐释“鲁迅精神”的文章。当时担任延安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的艾思奇将“鲁迅精神”概括为“鲁迅主义”,就是“为民族求解放的极热的赤诚,和对工作的细致而认真的努力”。学习“鲁迅主义”不在于“做文章”,不在于“要成为一个文学作家”,而是要“在政治、军事以及一般抗战建国的工作当中”能够贯注着鲁迅的“切实耐心”和“英勇牺牲”的精神*艾思奇:《学习鲁迅主义》,《文艺突击》1938年第1卷第1期。。担任陕北公学校长的成仿吾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界最前进的一个”,“达到了这一时代的政治认识的最高水平”,要“拿起鲁迅的精神反对汉奸亲日派与托派汉奸”,“创造出新的形式来适应今天民族自卫战争的需要”*成仿吾:《纪念鲁迅》,《解放》1938年第55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的陈伯达提出要学习鲁迅“爱国救国的气魄及其伟大的节义”和“永远战斗的精神”*陈伯达:《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解放》1938年第55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的周扬认为鲁迅的一生是“和中华民族解放分不开的”,“彻底的民主主义,严峻的现实主义,加上对于人民的深挚的爱,使他走向了无产阶级”,鲁迅留下来的遗产就是“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精神”和“战斗性的坚韧”*周扬:《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者的路——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周扬文集》第1卷,第280页。。尽管他们都承认鲁迅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文豪”,但是从来没有人从文学的角度来纪念鲁迅。他们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出发,从政治立场上强调鲁迅虽然“不曾加入共产党,但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伟大的领袖毛泽东赞扬他,讲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是布尔什维克的”*柯仲平:《是鲁迅主义之发展的鲁迅艺术学院》,《新中华报》1938年4月20日。,人们也因此必须接受这样的“鲁迅精神”。如同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所报道的那样,在延安“研究鲁迅,学习鲁迅,继承鲁迅的事业前进,成为努力于中华民族新文化工作者底一个基本的任务”,鲁迅的品格“是每一个革命青年尤其是文化工作者的修养的模范”*惊秋:《陕甘宁边区新文化运动的现状》,《新华日报》1941年1月7—8日。。
按照毛泽东的“报告”与“讲话”提出的标准建构鲁迅形象的意图在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变得更加直接和更为急迫。当毛泽东在大会所作的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报告于《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后,张闻天为《中国文化》撰写的社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也于当年10月发表。在引用毛泽东关于鲁迅形象的基本规范之后,张闻天重点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为大多数人而战斗的方向,他创造的新文化就是为大多数人战斗的文化。鲁迅向什么人战斗?向民族的压迫者战斗,向社会的压迫者战斗,向吃人的旧制度战斗和吃人的旧礼教战斗”,正是“不断的战斗和不断的进步”,使鲁迅“从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成了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鲁迅所走的道路正是“中华民族一切最优秀的、最有骨头的、最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所必然要走的道路。鲁迅虽然死了,中国革命事业仍是艰巨的,而文化界需要第二个鲁迅、第三个鲁迅,以至无数个鲁迅,要他们起来负担鲁迅生时未完成的事业”*洛甫:《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中国文化》1940年第2卷第2期。。经过对毛泽东报告的提纲挈领式的阐释,将鲁迅所走的道路总结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必然要走的道路”,鲁迅形象的文学旗手意义就变得更为明确了。更为重要的是,张闻天对毛泽东报告的阐释是以《中国文化》社论的形式发表的,这意味着其中的观点并不只是代表撰写者个人对鲁迅形象的看法,而是从政党层面表明了中共对毛泽东所建构的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的肯定。“鲁迅的道路”被确定为一种知识分子作家都应当效仿的模式,解放区的所有作家都要以此为对照,修正自己的文学行为,调整自己的人生道路,以便与中共提炼出来的“鲁迅的道路”相一致。由此看来,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完全变成了一种规范解放区知识分子作家的文学机制。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被完全纳入解放区的文学生产体系当中。
(1)车辆条件。配送中心目前使用的主要车辆有三种车型,车型I 6辆,荷载2吨,车型II 3辆,荷载4吨,车型III 1辆,荷载10吨。
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的形成也与解放区举办的各种鲁迅纪念活动联系在一起,正是依靠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群体性参与的鲁迅纪念活动,才使以政治性作为文学旗手之基本内涵的鲁迅形象成为知识分子作家的集体记忆。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举办的鲁迅纪念活动形式多样,数量众多,既有诞辰纪念会,也有作品报告会,还有逝世纪念会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共举行过四次大规模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尽管每次纪念活动的主办机构有所不同,但采用的纪念形式则基本一致。会场外张贴着写有鲁迅名言的标语,会场内悬挂着大幅的鲁迅画像。会议开始后先由不同级别的领导人讲话,接着由大会负责人报告鲁迅的生平,最后由不同的作家发表对鲁迅的感想,形成了固定的程式。在程式化了的会议进程中,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逐渐变成了一种神圣的政治“仪式”*潘磊:《“鲁迅”在延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1页。。正是这种仪式化了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将毛泽东建构起来的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嵌入了知识分子作家的精神结构中,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知识分子作家关于鲁迅形象的基本认识。
在解放区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阐释毛泽东建构起来的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的独特内涵成为周年纪念大会的基本内容之一。然而,由于毛泽东在解放区作为政治权威的影响力,所有的阐释内容都没有超出毛泽东的“讲话”与“报告”之范畴。周扬在1938年的周年纪念大会上说,鲁迅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决定了他的“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主义思想”,他为了“爱祖国爱人民而从事艺术,把艺术当作救祖国救同胞的工具”,在艰苦的抗战现实中要学习他“不屈不挠和持久战斗的精神”*敏英:《延安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3日。。萧三在1939年鲁迅逝世纪念日发表的文章中说,鲁迅的一生“充满了奋斗,挣扎,永远不屈不挠,一点不妥协不调和的精神”,他是“随着时代永远进步的”,是“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是“唯物主义思想家,是批评家,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是社会活动家,革命者,战士”*萧三:《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新中华报》1939年10月20日。。吴玉章在1940年的周年纪念大会上说,鲁迅的伟大事业包括三个方面:“(一)建树了文化上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二)建立了真正为劳苦大众服务的革命大众文学,(三)热心赞助新文字运动,使中国文化能真正深入到大众中间去。”*郁文:《鲁迅先生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志》,《新中华报》1940年11月7日。虽然人们纪念的是“中国最伟大的文豪”*萧三:《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新中华报》1939年10月20日。,但参与纪念者都是从鲁迅的政治人格层面进行评价的,与毛泽东论述的“鲁迅精神”相一致,没有人愿意深入到鲁迅作为“大文豪”的具体文学创作和复杂的精神世界中。
二、高尔基:解放区前期文学旗手建构的世界性面相
解放区前期中共选择高尔基作为文学旗手体现了延安文艺体制构成的世界性面相。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受到国民党的全面封锁,与外界的文学交流也大受限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苏俄文学,成为解放区前期中共开展文学活动的世界性面相的首要选择。
高尔基为中国作家所熟知,主要是在“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在20年代中期左翼文学运动兴起以前,中国现代作家都是将高尔基作为从社会底层自然成长起来的作家来看待的。在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看来,除了个人生活道路的艰辛和对底层民众生活的熟悉以外,高尔基与欧洲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并没有根本性差异。然而,当中共领导下的“左联”成立以后,高尔基却迅速转变为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家。对于中国正在开展的左翼文学运动来说,高尔基的文化身份开始融入革命化和政治化的内涵。在经历了“左联”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立场对高尔基形象的政治化塑造后,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在解放区主要从文学与政党关系的角度入手,努力将高尔基形象建构成解放区的文学旗手。中共之所以能够成功领导中国革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重视和依靠文学的力量,能够将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转化为特殊的文化权力,而真正拥有和能够发挥这种权力的是已经创作出文学“正典”的经典作家。中共作为具有世界性视野的无产阶级政党,将高尔基确立为解放区文学运动的“文学旗手”,正是抓住了经典作家的特殊号召力。高尔基之所以能够成为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文学旗手”,一方面根源于高尔基在苏俄文学运动中的“经典”地位,另一方面也根源于延安文艺体制建构的世界主义追求。高尔基一旦成为解放区前期的“文学旗手”,其所代表的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政治身份将得到中共的确认,并迅速由一种世界性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以在解放区展开行动的文化权力。
在解放区前期的文学运动中,作为“文学旗手”的高尔基形象基本是通过逝世周年纪念大会的方式完成的,政治意识形态成为高尔基形象建构的中心。当高尔基的创作道路、政治倾向和经典作品成为解放区作家遵从和模仿的对象时,作为“文学旗手”的高尔基形象自然就变成延安文艺体制的一部分。1937年6月18日,中国文艺协会在延安隆重举行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这是中共在解放区第一次为一位外国作家举办的纪念活动,拉开了解放区前期高尔基形象建构的帷幕。
在解放区前期的文学旗手建构中,高尔基形象远远处于鲁迅形象之下。高尔基虽然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家,但在解放区的政治现实下,高尔基只能以一个“外来者”的形象而存在。以中共为主体的解放区政权在进行“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过程中,不可能将一个“苏联大文豪”树立为解放区知识分子作家模仿的主要对象。正是由于鲁迅与中共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中共在确立解放区的“文学旗手”时首先选择了鲁迅,鲁迅最后变成了解放区“文学旗手”的核心。虽然高尔基在解放区前期“文学旗手”的建构过程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但高尔基形象的建构又使解放区前期的文学活动与以苏联为主体的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解放区的文学运动成为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增强了延安文艺体制的世界性内涵。
解放区前期的高尔基形象建构完全是在以中共为中心的政治意识形态规范下进行的,其目的是要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背景下,将高尔基塑造成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从事文学活动的“文学旗手”。在作为文学旗手的高尔基形象的建构过程中,同样是毛泽东的观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奠定了解放区知识分子作家理解高尔基形象的基础。在1937年由中国文艺协会主持的高尔基逝世纪念日活动中,毛泽东在应邀发表的演讲中高度赞扬高尔基的“实际斗争精神”和“远大的政治眼光”,认为高尔基“不但是个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个很好的政治家”*记者:《苏区文艺协会召开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新中华报》1937年6月23日。。毛泽东虽然对高尔基了解甚少,但是他以解放区的政治权威之身份,从解放区的政治现实出发对高尔基作了高度评价,指出了高尔基作为一位文学家所具有的斗争性和政治性特点。显然,毛泽东是在解放区的抗战现实背景下,从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高尔基进行评价的。在解放区的对外文化交往受到国民党严格控制的情况下,毛泽东专门针对高尔基发表的唯一一次讲话就成为解放区知识分子作家建构高尔基形象的基本准则。对于解放区知识分子作家来说,斗争性和政治性不但是作为文学家的高尔基的本质,而且也是解放区所有知识分子作家从事文学活动时都应当主动追求的。
高尔基形象建构的目标决定了建构方式的选择。与鲁迅形象建构的复杂性相比,解放区前期的高尔基形象在建构方式上相对要单一得多。解放区将高尔基逝世的日子确定为高尔基逝世纪念日,在逝世纪念日前后举行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大会是建构以“文学旗手”为目标的高尔基形象的最基本方式。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大会的规模比较庞大,参加会议的人数每次少则五六百人,多则超过千人,陕甘宁解放区文化界和文学界的著名人物都会参与其中。但是,每次纪念大会的形式基本相同,先是由主持人报告召开会议的意义和高尔基的生平,接着由不同团体的代表发言表达对高尔基的敬意,最后由熟悉高尔基的作家演说高尔基的精神内涵及其现实作用。显然,这种模式化的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只是为了表达一种意识形态意图,并不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实质影响。也就是说,解放区的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已经变成一种政治仪式。作为“属于特定社会、特定人群的特别事务和活动”,仪式往往会“持续不断地出现同一个主题”,“这种带有无可争议的、强制性的、权威性的宣言指导人们引导到一种类似于疯狂般崇拜程度”,其最后的结果,“一方面,它成为社会控制的有效力量;另一方面,仪式的形式本身也转化成为一种权力”*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66、73页。。所以,《新中华报》的编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吁,“我们今天纪念高尔基,要学习高尔基,研究高尔基”,“空洞的纪念形式,对死人或活人都是毫无意义的”*《编后记》,《新中华报》1940年6月8日。,重要的是要有所行动,对抗战有所贡献。
毛泽东确定了作为“文学旗手”的高尔基形象的基本内涵后,解放区作家在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也作出了基本一致的理解。在1938年高尔基逝世两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解放》周刊编辑的吴亮平提出了高尔基的三个伟大之处:“第一,高尔基击破了今天一切反动的黑暗的东西;第二,他把文学和无产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了;第三,他有一定的政治方向。”而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周扬则不仅要求青年学习高尔基的“反抗的精神”、“伟大的现实主义”、“把艺术家和革命家统一起来的精神”和“反市侩主义”,而且要求青年将高尔基精神“用在我们神圣的抗战上去,别的一切纪念都是无价值的”*柳青:《高尔基被害二周年纪念在延安》,《新华日报》1938年6月30日。。在1939年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日期间,何其芳发表文章指出,高尔基“是一个新的阶级的代表”,“他带着粗率的强壮的姿势走进当时的绅士作家之群,是那样地不和谐,那样地震惊了旧俄罗斯。他的胜利预言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因为他代表了新的阶级,正在生长,壮大的阶级,希望和未来都属于它的阶级”*何其芳:《高尔基——由这个名字引起的一些感想》,《新中华报》1940年6月18日。。在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看来,高尔基是“伟大的文豪,坚韧的战士”*萧三:《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新中华报》1939年6月20日。,是“中国人民及文化界先进的最亲切的挚友”,高尔基“忠实于革命,忠实于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精神“更是在抗战中的中国文学家的一个最应该学习的模范”*若茗:《纪念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高尔基》,《新中华报》1940年6月18日。。在他们的发言或文章中,运用得最多的是“政治方向”“文学家与革命家的统一”“无产阶级的代表”“文学与阶级斗争的结合”“对革命的忠诚”等,这些大致一样的表述其实都是对毛泽东论述的高尔基精神的复述。诚如《新中华报》的编者所说:“就中国来说,为高尔基而写的纪念文字,在数量上的确是相当可观了,然而在质量上,似乎还很菲薄,这位巨人本身以及其作品,简直似一座丰富宝藏,需要我们更努力地掘发,整理,并全部地,有系统地,正确地介绍出来,很多的中国人对他似乎还停留在只知其名不知其人的‘偶像崇拜’的程度,真正理解他的实在很少。”*《编后记》,《新中华报》1940年6月8日。
事实上,在解放区举办的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活动中,作为个人和作家的高尔基已经被消解了。对于解放区作家来说,高尔基因出身社会底层而艰辛奋斗的人生道路,以及对社会底层民众无奈的精神世界的独特表现等已经变得不再重要,解放区作家更关心的是高尔基作为“一个新的阶级的代表”*何其芳:《高尔基——由这个名字引起的一些感想》,《新中华报》1940年6月18日。的政治倾向性。因为,在解放区作家看来,一旦参与了高尔基逝世纪念活动,自己似乎就获得了一种创作的“魔力”,能够按照固定的程序开展文学创作。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完全变成了一种政治仪式。在这种“特定的社会化仪式活动中,会产生精神或人格上的特权和权威”,高尔基已经“被赋予特殊的精神或神圣的力量”,与解放区以文艺社团为代表的“社会机构相辅相成,构成了社会机制的一部分”*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第72—73页。。一方面,中共通过纪念活动成功地将政治意识形态要求楔入了高尔基形象之中;另一方面,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通过对高尔基形象的表态式认同间接接受了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规范。
三、赵树理:解放区后期文学旗手建构的大众化面相
解放区后期中共确定赵树理作为文学旗手显示了延安文艺体制构成的大众化面相。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延安文艺政策开始在解放区广泛执行,解放区后期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艺“大众化”的方向已经明确,赵树理作为解放区后期文艺运动中的文学旗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验证文艺发展的工农兵方向的合理性。
赵树理成为继鲁迅和高尔基之后解放区文学运动中的又一位文学旗手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与赵树理自己的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上的成功密切联系在一起。赵树理从自己对农村文化生活状况的了解和对农民宣传工作的经验出发,认为文化宣传要重视普及工作,文学创作要照顾农民的“大众化的迫切需要”*《四二年晋冀豫区文化人座谈会纪要》,《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上),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87页。,要专门为农民创作和出版他们能够接受的通俗化作品。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赵树理得到了小二黑结婚的故事材料,并完成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随着《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等作品的出版,赵树理成为晋冀鲁豫解放区颇有影响的作家。从“五四”新文学的追随者到“通俗故事”的创作者,赵树理走出了一条以农民为创作对象的文学大众化路子,从而为其被中共确立为解放区后期的文学旗手准备了条件。
赵树理成为解放区后期的文学旗手也是中共根据解放区的政治现实和文化需要不断建构的必然结果。在解放区后期的文学旗手建构过程中,由于鲁迅与高尔基是自革命文学运动开始以来左翼作家“公认”的“大文豪”,再加上毛泽东对两人的高度赞誉,因而,鲁迅与高尔基被确立为解放区文学运动的旗手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质疑。而且,随着解放区现实环境的变化,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与高尔基形象变得越来越完美,作为具体作家的个人缺陷就被完全遮蔽了。这种从现实需要出发的文学旗手建构一直持续到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当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不再需要这种完美得抽象化了的文学旗手时,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和高尔基形象开始逐步淡化。然而,赵树理的乡村知识分子的地位以及他的文学创作的有限性,决定了将赵树理塑造成解放区作家共同模仿的文学旗手要比鲁迅形象和高尔基形象的建构艰难得多。
既然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创作能够代表一种新的文学潮流,即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众化方向。那么,为了使赵树理尽快成为解放区作家的模仿对象,由中共主导下的文学批评必然会参与到对作为“文艺新方向”的赵树理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有鉴于《小二黑结婚》出版前后遭受到文学批评界的“冷遇”,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出版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在《华北文化》上发表了推荐文章《介绍〈李有才板话〉》,从中共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及其普通读者介绍《李有才板话》。他认为,《李有才板话》是比《小二黑结婚》“更有收获的作品”,“更有向读者介绍的价值”,其理由有三点:一是“写作目的的明确和正确”,“能够在作品中处处显示出对读者对象的尊重,考虑到他们的习惯和品味,理解水平,接受能力,通过通俗浅近的文艺形式来进行思想教育”,也就是说,赵树理是为以农民为主体的普通民众创作的;二是“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小说中的人物“都各以本阶级的本来面目出现,甚至观点,情感,生活习惯,语言等,也都大体合于人物自己的身份”;三是赵树理基本掌握了“两种功夫:一是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二是对社会的调查研究”*李大章:《介绍〈李有才板话〉》,《华北文化》(革新版)1943年第2卷第6期。。李大章在文章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联系到此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发布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且李大章提出是否愿意为农民写作“通俗浅近”的文艺作品,不仅是“态度”的问题,而且是“为谁服务”的问题,“也就是立场问题”,这些观点显然来自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可以断定《介绍〈李有才板话〉》是最早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来评价赵树理小说的文章。李大章在文章中不仅提出了此后赵树理评价中“衡量赵树理小说的基本原则”*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7页。,既包括鲜明的“立场”、明确的“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和“容易接近群众”等优点,也包括“新型的青年农民,在书中只是‘跑龙套’似的出现,而缺乏深刻突出的描写”等缺陷,而且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所有作家提出了“改造”要求,希望他们“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正确文艺方针的指导下,为工农兵的新文艺,为新中国的文艺”而努力*李大章:《介绍〈李有才板话〉》,《华北文化》(革新版)1943年第2卷第6期。。
李大章介绍《李有才板话》的文章最初并没有抱着要将赵树理确立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方向”的目的,他的初衷主要是要通过对《李有才板话》的介绍,消除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对赵树理的偏见。因为,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把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乡村知识分子作家“写给农民看的东西当作‘庸俗的工作’,或者是‘第二流的工作’”,以致一部分从事通俗化创作的乡村知识分子作家自己“也有意无意的抱着‘第二等的’写作态度来从事它”*李大章:《介绍〈李有才板话〉》,《华北文化》(革新版)1943年第2卷第6期。。尽管李大章的推荐文章对矫正晋冀鲁豫解放区文学界对以赵树理为代表的乡村知识分子作家的通俗化创作的偏见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赵树理在此后进入了长达两年时间的蛰伏期,并没有创作出可以进一步提升其文学地位的作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6年1月《李家庄的变迁》的出版才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在1946年的一年时间里,赵树理不仅出版和发表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短篇小说《地板》《催粮差》《福贵》等,而且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先后在《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解放区的重要报刊上转载,并且被介绍到上海、香港等国统区大都市出版的文学报刊上。尤其重要的是,随着赵树理作品的广泛传播,1946年甚至变成了赵树理文学创作的“评论年”,来自解放区的周扬、陈荒煤、冯牧和来自国统区的郭沫若、茅盾等著名作家先后发表评论文章,对赵树理的小说给予了高度赞誉,从而形成了赵树理创作的评论潮流。由于这些文章都是以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基本规范的,因而对赵树理创作的介绍和评价就不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批评,而是承担了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
在评论赵树理创作的众多文章中,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最为重要,因为它不仅为晋冀鲁豫解放区确立“赵树理方向”提供了基本依据,而且奠定了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基本地位。自从《小二黑结婚》出版以来,赵树理的通俗化创作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一直存在着争议,许多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将其看作是“第二等的写作”,人们并没有发现赵树理作品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内涵。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周扬的推荐文章一经发表就被解放区的重要报刊广泛转载,完全消除了人们对赵树理创作的质疑。《论赵树理的创作》最初发表于1946年7月出版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张家口分会的机关刊物《长城》上,《解放日报》于同年8月26日转载后才在解放区产生了广泛影响。周扬认为,赵树理小说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在主题上“写农民与豪绅地主之间的斗争”,反映了“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最大最深刻的变化,一种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化”;二是在人物创造上“总是将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斗争的环境中,放在这斗争中的一定地位上,这样来展开人物的性格和发展”,“总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作者总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明确地表示了作者自己和他的人物的一定的关系”;三是在语言上“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但是“他创造出来的决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周扬对赵树理小说特征的分析并没有太多的独创性观点,因为周扬文章中的基本观点在此前已经发表的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冯牧的《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推荐〈李有才板话〉》等文章中都有了或多或少的论述。
然而,周扬毕竟有着敏锐的政治眼光,他不是像其他文章一样一般性地论述赵树理创作的特点,而是从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要求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规范之高度来看待赵树理创作的意义。因此,他这样说:
我与其说是在批评甚么,不如说是在拥护甚么。“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各部门都达到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欢呼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
虽然1942年5月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了为工农兵的“文艺新方向”,但是一直没有出现能够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代表性艺术作品。因此,在周扬看来,赵树理无疑是在文学创作上实践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工农兵文艺”方向的“一个典范”*支克坚:《周扬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4页。。针对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对赵树理的通俗化创作的偏见,周扬更是从“普及”与“提高”关系的角度进行了积极肯定,认为这是“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虽然赵树理一再在自己的小说出版时标明“通俗小说”或“通俗故事”,但是周扬认为这些作品“决不是普通的通俗故事,而是真正的艺术品,它们把艺术性和大众性相当高度地结合起来了”*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也就是说,赵树理作为实践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方向”的典范,并不只是一个“普及”的典范,而是一个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52页。的典范。既然周扬要将赵树理确立为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方向”的典范,就必然要在肯定其普及意义的同时强调其艺术的价值,只有在发现了赵树理创作所具有的“真正的艺术品”价值以后,才有可能在将其树立为整个解放区新的文学旗手时得到其他作家在艺术上的认可。同时,针对人们对赵树理的身份问题有可能提出的质疑,周扬进行了这样的解释:“若有人怀疑,赵树理岂不只是一个农民作家吗?他的创作和思想的水平不是降低到了‘农民意识’吗?回答当然不是。它不但歌颂了农民的积极的前进的方面,而且批判了农民的消极的落后的方面。他写了好的工作干部,这是农村中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骨干,没有这骨干,农民的翻身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批判了坏的工作干部。这好与坏的一个主要区别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替他们解决问题。”周扬要努力证明赵树理不是“农民作家”的目的就是要强调赵树理的“无产阶级作家”的阶级身份的纯粹性,更进一步确认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作为“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普遍性,从而保证“他所树立的典范的无产阶级性质”。*支克坚:《周扬论》,第84页。
正如赵树理的朋友史纪言所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小说虽然“经过彭副总司令和李大章同志的介绍”,但是“几年以来并未引起解放区应有的重视”,直到1946年7月,“先经过周扬同志的推荐,后经过郭沫若先生的评价,大家的观感似乎为之一变”,史纪言由此感叹“文艺批评”在赵树理走向整个解放区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史纪言:《文艺随笔》,《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上),第410页。。正是由于周扬、郭沫若、茅盾等人评论赵树理创作的文章的发表,赵树理的影响迅速从晋冀鲁豫解放区扩大到整个解放区。当文学批评发挥了自己的独特建构功能而使赵树理的影响在整个解放区开始广泛兴盛起来的时候,文学会议就取代了文学批评而开始了“赵树理方向”的确立。于是,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的指示下,于1947年7月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议程之一就是“讨论赵树理的创作”,与会者“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记者:《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一九四七年文艺工作座谈会记事》,《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为此,与会的文艺工作者“都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在这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陈荒煤作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报告,认为必须从三个方面“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是赵树理的创作有很强的“政治性”,“他的笔都尖锐地掘发着农村现实中的基本矛盾”,“从各个角度反映了解放区农村伟大的改变过程之一部”;二是赵树理的创作“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在“创作方法上也贯彻着群众观点”;三是赵树理“从事文学创作,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具有高度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和长期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陈荒煤的论文基本上复述的是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的内容,其目的主要是以赵树理的创作为例子,证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正确性。所以,陈荒煤得出的结论是:赵树理的创作“是最朴素,最具体地实践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因此他获得如此光辉的成就!”*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至此,赵树理正式成为解放区作家模仿的一面“旗帜”,作为解放区新的文学旗手的“赵树理”正式诞生了。尽管“赵树理方向”被作为解放区作家共同遵循的创作道路被确定下来,但陈荒煤提出的“赵树理方向”的三个方面在具体创作中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赵树理方向”的核心仍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基本主张,也就是“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作家和新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71、81页。。因而,陈荒煤又说,赵树理虽然“创造了一种新形式”,但是“单纯的从形式来模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文艺工作者今天的根本问题仍是与工、农、兵思想情感相结合,也惟有如此,才能最后的真正的解决了形式问题”*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其中包含着明确的政治现实目的。这就意味着,“赵树理方向”的确立完全是在中共的意识形态规范下进行的,“毛泽东文艺理论”才是解放区作家从事创作的规范。事实上,“赵树理方向”从来就没有产生过像“鲁迅方向”那样巨大的反响,作为文学旗手的“赵树理”也没有像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和高尔基那样受到解放区作家的普遍模仿。因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成为文学运动的核心问题时,在解放区的大多数作家看来,作为解放区文艺权威的毛泽东提出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新的文艺”才是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真正方向,赵树理只能是这一方向的实践者而已,不可能成为解放区文艺理论的权威,也就不可能成为解放区文艺运动中的文学旗手。
四、结语:文学旗手建构与延安文艺的体制化
作为文艺体制的基本组成部分,解放区前后期文学旗手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延安文艺体制的生成。如果从文学制度层面来看,解放区前后期文学旗手的变更标志着解放区文学逐渐走向了体制化。无论是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建构,还是作为文学旗手的高尔基形象建构,其目的都是要创造一种在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规范下的文学创作范式,使之成为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的模仿对象,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知识分子作家的政治教育,以便使作家全身心投入到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文学活动中。然而,由于鲁迅和高尔基的“外来者”身份的复杂性与解放区的政治现实规范下文化语境的单一性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解放区前期的文学旗手建构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思想冲突。最后,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解放区文学旗手的建构转向了对能够全面体现工农兵大众自身审美需求的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经典”作家的寻找和确认上。
在解放区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随着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意识的逐渐自觉,中共感到确实有必要确立在文学上卓有建树的人物,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的引导者,以此来凝聚文学及文化领域的力量为民族战争和阶级解放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旗手的选择既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要求。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创建后的一年时间里,高尔基与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在解放区相继召开,毛泽东亲自参加纪念大会并通过演讲的方式提出了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和高尔基形象建构的基本准则。中共将鲁迅和高尔基确立为解放区的文学旗手,既表明了中共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革命性内涵,也体现了中共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世界性视野。既然中共选择了将鲁迅和高尔基作为解放区的文学旗手,那么,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和高尔基形象就必然要符合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规范。因此,强调文学家与政治家、革命家的完美统一就成为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和高尔基形象建构的准则。
然而,作为个人化的文学偶像与作为政治化的文学旗手之间总是相互冲突的,解放区文学旗手的建构目的就是要消弭文学偶像的个人化内涵而凸现文学旗手的政治化规范,从而使解放区的文学旗手在内涵上符合“中华民族新文化”引导者的标准。对于解放区知识分子作家来说,当他们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以后,都面临着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人生道路转换问题。因而,如何叙述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和高尔基的人生道路就显得至关重要。高尔基“出自民间,也终身和人民在一起,从幼年时代起他便受了人民性格之好、光明的一面底熏陶”,“在童年时代他已经看到沙皇制度下人民所受的痛苦,黑暗,悲惨,而且知道这些之所由来,因而痛恨压迫者”*萧三:《伟大的爱,神圣的恨——为纪念高尔基去世五周年而作》,《解放日报》1941年6月18、19日。,作为解放区的文学旗手是符合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要求的。鲁迅虽然出生于一个与普通民众完全不一样的家庭,有着更加复杂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矛盾,但鲁迅始终将目光对准下层社会,后来成为“中国工农劳苦大众和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这样的人生历程对解放区知识分子作家的人生道路转换反而更具说服力。因此,对于中共来说,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引导者的鲁迅经历了一个“由个人的反抗,自由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一直到稳稳地站在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到拥护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萧三:《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新中华报》1939年10月20日。的发展,完成了从“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向“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洛甫:《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中国文化》1940年第2卷第2期。的转化,他的人生道路“像一条红线那样明显,描画着革命的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的结合”*魏东明:《鲁迅的创作道路》,《鲁迅研究丛刊》1941年第1辑。。中共按照政治意识形态需要开创的鲁迅人生道路的政治化叙述最符合解放区的现实状况,理所当然成为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的模仿榜样。至于鲁迅自己所说的对于“‘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做的“绝望的抗战”*《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页。,则被完全过滤掉了。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取得了解放区的政治权威地位以后,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要求出发,也迫切需要成为解放区的文艺权威来指导解放区的文学运动。然而,由于鲁迅与高尔基在解放区知识分子作家眼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从抗战的政治现实出发,因势利导地将鲁迅与高尔基确定为解放区的文学旗手。所以,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和高尔基具备了成为文学权威的可能性。在解放区的文学活动中,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与鲁迅和高尔基相关的纪念活动,既表达了自己对一代文学伟人的尊崇,也向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表明了自己作为解放区的政治权威对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和高尔基形象的独特理解。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参与活动也显示了毛泽东对解放区的文艺权威的自我建构意向。也就是说,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和高尔基形象的建构过程,其实也就是作为文艺权威的毛泽东形象的自我建构过程,这两个方面是同时进行的。简言之,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和高尔基有可能成为解放区的文艺权威,作为政治权威的毛泽东更有可能成为解放区的文艺权威。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报告,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观点,并且进一步将鲁迅确立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709页。。在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陕甘宁边区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虽然重申了鲁迅在解放区文学旗手建构中的核心地位,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以此向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表明了自己对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独立思考,初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的文化理论体系,从而也奠定了毛泽东作为解放区文艺权威的基础地位。
文学家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世界往往是复杂而多样的,正是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为后来者的多元解读提供了基本依据。尽管中共已经确立了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和高尔基形象的政治意识形态方向,但伴随着1941年鲁迅和高尔基逝世五周年纪念日的到来,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依然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开始了对作为文学旗手的鲁迅形象和高尔基形象的个人化解读。尤为重要的是,这种个人化的解读往往与解放区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要么在对鲁迅的文学家形象的张扬中强化文学的“暴露黑暗”*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的功能,要么在对高尔基的政治家形象的赞誉中脱离了解放区的政治现实环境*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毛泽东文艺论集》,第97页。,因而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关注。也就是说,以鲁迅和高尔基作为文学偶像形成的个人化的文学潮流远离了解放区的政治现实规范,沿着“不正确”的方向前进,由中共主导的文学旗手建构并没有朝着预定目标发展。因此,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就成为势所必然。如同毛泽东所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48页。。从这一根本目的出发,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战争环境下文艺工作者的立场与态度、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文学的目标与任务、文学的批评标准等问题,要求“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真正完成文学与工农兵大众的结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第52页。。毛泽东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文艺的基本理论,确立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在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面前,毛泽东从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要求出发,按照文艺服务于政治的基本原则,以自己对文艺的明晰而独特的理解,确立了自己在解放区的文艺权威地位。此后,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关于文艺问题的任何理解都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准则。因此,在解放区文学旗手的建构过程中,延安文艺座谈会无疑是一个分水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尽管人们对鲁迅形象和高尔基形象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他们仍然承担了文学旗手的引导功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鲁迅形象和高尔基形象逐渐失去了作为文学旗手的功能,新的文学旗手必然会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全面贯彻而被创造出来。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彻底终结了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按照个人意愿建构文学旗手的幻想,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规范下,“大众化”不仅成为解放区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而且成为新的文学旗手建构的基本标准。一方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就已经模式化了的鲁迅形象和高尔基形象的建构方式迅速走向消解。作为一种“政治仪式”的鲁迅和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大会,虽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曾经激动过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的心灵,但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便停止了一切纪念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才重新举办类似纪念活动。另一方面,解放区后期新的文学规范开始创建,知识分子作家全面走向工农兵的生活天地,与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改造自己的精神和灵魂。1943年3月,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知识分子作家大会,以“深入群众,改造自己”为目标的知识分子作家的“下乡运动”随之开始,知识分子作家从此离开借以从事文学活动的文学社团,成为具有实际工作单位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 毛泽东同志曾指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解放日报》1943年3月13日。,由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变成有具体工作岗位的文艺工作者,作家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认为“工作”重于“创作”。陈学昭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应由政治来领导。我在国外住得太久了,我希望和祖国广大人民在一起生活。作家投身到群众的大海,向群众学习,这是划时代的大事。”*《延安作家纷纷下乡 实行党的文艺政策》,《解放日报》1943年3月15日。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政治决定文艺的根本价值,群众决定作家的创作走向,这是文学大众化的基本要求。紧接着,在1943年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这一天,《解放日报》以公开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式取代了以往的大规模群众性纪念活动,“纪念仪式”的变革更是显示出建构“文艺运动的新方向”的紧迫性,已经参与到解放区文学大众化运动中的文艺工作者对过去“自己口头上讲‘人民大众’,但是看不见人民大众”的错误行为表示了深深的忏悔,认为“不粉碎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就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刘白羽:《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6日。。文艺工作者要想写出工农兵大众能够接受的文学作品,“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改造自己”*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而“改造自己”的途径只有一条,就是“到实际工作中去,住到群众中间去,脱胎换骨,‘成为群众一分子’”*立波:《后悔与前瞻》,《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定为中共“在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要求文艺工作者“研究和执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地发展”*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如果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更多的是从政治层面确立了毛泽东在解放区知识分子作家心目中的文艺权威形象的话,那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则从文学制度层面规定了毛泽东在解放区文学运动中的文艺权威地位。至此,延安文艺座谈会完成了从“会议”的准时召开、“讲话”的公开发表到文艺政策的全面确立等三个阶段,由中共主导下的解放区文学旗手的建构最后以文艺权威的形式固定下来。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以后,从情感态度、思想意识和组织形式上都接受了毛泽东在“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中的文艺权威地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指导知识分子作家从事文学活
动的基本方针,解放区文学由此走向体制化。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并不适合直接作为解放区后期文学运动的旗手。因此,中共必须找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能够体现解放区文学创作风貌的作家成为新的文学旗手,并且以此来印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新方向”的正确性。故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形成的以“大众化”为创作方向的新文化语境规范下,赵树理逐渐进入了解放区后期重新建构文学旗手的文学潮流中。“赵树理方向”的提出以及赵树理被确定为文学旗手意味着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艺“大众化”方向的确立,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作为中共的文艺政策开始在解放区广泛实践,并极大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共和国文学,解放区文学也以体制化的方式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
(本文作者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兰州 730070)
(责任编辑 吴志军)
Adjusting the Standard-bearer of Literature and Establishing the New Direction of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Guo Guochang
During the course of Yan’an constructing its literature and art system, establishing the standard-bearer of literature was the basic approach. In the Liberated Areas, it underwent two obvious stages with the Yan’an Forum on Literature and Art being held in 1942 as a boundary. Lu Xun and Gorky were highlighted before 1942, but after that, Zhao Shuli became the new center. Adjusting the standard-bearer of literature not only impli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ready formulated its literature and art policies which was largely based on Mao Zedong’s “theories on literature and art”, but indicates the Yan’an literature and art system focusing on workers, peasants and soldiers fell into a pattern.
I209;K26
A
1003-3815(2016)-11-002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