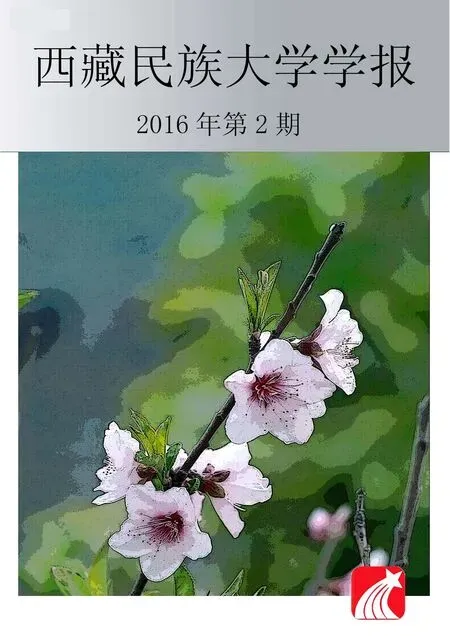与之共存和为治先
——基于唐金城公主入藏史实的考量
喜饶尼玛,韩敬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与之共存和为治先
——基于唐金城公主入藏史实的考量
喜饶尼玛,韩敬山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金城公主入藏的价值和对汉藏关系的意义一直为史家大书特写,也影响了此后历代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她居吐蕃30年,以宗教文化为依托,“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为唐朝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新鲜经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唐蕃矛盾,减少了战争频次,对促进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和团结,推动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与之共存,和为治先”,对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无启示作用。
关键词:唐蕃和亲;金城公主;汉藏关系
韩敬山(1974-),男,满族,辽宁大连人,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藏族历史和近现代边疆地区社会管理。
文成公主入藏的价值和对汉藏友谊的意义一直为史家大书特写,其以和亲为载体,在唐廷和吐蕃间走出了一条非同寻常的甥舅亲情,铺垫了汉藏民族关系发展的新基石。70年后,金城公主沿着“唐蕃古道”上文成公主的足迹再次入藏,她在吐蕃30年,始终牢记柔远之图,始终践行和亲之义,始终力促兵战之息,为唐蕃双方的和平书写了最生动、最具体的范式。她以宗教文化为依托,以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具体实践,为唐代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新鲜经验。甥舅一家策略的再实施成为汉藏民族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同时,亦应看到金城公主面对与唐朝截然不同的吐蕃社会,甚至身处逆境、边战叠起之时,懂团结、会团结原则下的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成为她身夹其间的圭臬。从金城公主入藏的历史作用与现实价值出发,在历史审慎思维中关注其可行性策略,对今天思考如何构建西藏开放型新格局,如何自觉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如何实现跨文化交流、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都有着具体而清晰的现实启示。
一、落实“安边之略”的艰难:政治考量下如何“走出去”
文成公主入藏70年后,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这70年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唐始设控制西域的安西四镇(648年),玄奘《大唐西域记》(664年)撰写完成,“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唐罢安西四镇”(670年),[1]武则天称帝,改国号“周”(690年),再复置安西四镇(692年),吐蕃最有权势的大臣论钦陵攻打到离长安不远之地(696年),统辖天山北路的北庭都护府设置(702年),李显复位并复国号唐(705年)……这些眼花缭乱的政治事件中有两个人值得注意:一位是论钦陵,吐蕃实际权力掌控者;一位是武则天,唐廷最高权力掌控者。面对吐蕃在双方边境区域展开的不断骚扰,称帝后的武则天经过研判,将反击吐蕃的关键点缩小到论钦陵身上,并迅速展开一个具体而成功的三步走战略:一是拒绝吐蕃的和亲请求,因为她“感觉到了吐蕃内部的骚乱,拒绝了和亲请求,这是放任吐蕃国内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的策略”;[2](P257)二是以此引诱论钦陵征战在外,降低其在吐蕃王朝的影响力,即“扼阻了吐蕃势如破竹的侵轶,迫使论钦陵……必需经常领兵在外,威势不再”;[3](P232)三是在确切得知“论族在吐蕃人中日益不得人心,于是她顺应时势,派使者前往就和亲和交换领土进行谈判,而使者的真正目的是挑拨离间”,[4](P284)以此实现“有意制造吐蕃君臣矛盾……给予吐蕃赞普蓄势挣脱噶尔氏家族垄断政权的机会”。[3](P232)分析上述有计划的路径,可以看出,唐廷在吐蕃问题上所采用的政治手腕——即在成功剪除吐蕃掌权大臣后赞普权力回归时迅速以和亲方式实现双方可能出现的和平。这种掌握主动的和亲是因为“吐蕃历经如此多内部纷乱,在与唐朝接壤的边境上显然安静了许多”,[5](P47)唐的策略走向了成功。这种实践的背后依靠,是其正在分阶段将西部广大地区的政治版图、军事建置纳入自己的管辖之下。这场双方协商的结果是吐蕃将占据22年的陇右“安西四镇”归还给唐,吐蕃随即遣使来到长安,按照双方的约定对唐提出和亲。
这是唐朝安远柔边策略中最生动、最具体的范式。唐中宗显然吸纳了文成公主入藏的一些经验。遗憾的是,虽然吐蕃迎婚使名悉腊“颇晓书记……皆称其才辩”,[6]但并没有打消唐朝君臣内心深处的疑虑。即使“吐蕃迎亲使来唐,兼学汉语”[7],双方沟通显然障碍,但关键时刻依然没有让双方实现互信,相反朝廷上下对“吐蕃无礼”、[5](P69)言而无信产生反感抑或恐惧。这种心理扩散效应以致造成“官员出使吐蕃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8](P278)唐中宗为了实现金城公主入藏和亲,前后数次任命婚使以送公主赴蕃,结果却屡遭被任命为婚使的大臣用各种理由予以推辞。直到710年正月,距离吐蕃提亲已过四年,人选依然没有,以至于唐中宗召见处讷时称其“有安边之略,可为朕充此使也”,[9](P9)而处讷却以“不练边事固辞”。[9](P10)婚使大臣的一次次难产,是金城公主婚事屡屡拖延依然无法动身的最重要原因。
但事情迅速有了转机,唐中宗在较短时间内突然决定让杨矩这位骁卫大将军充任护送金城公主的使臣,并专门为金城公主入藏之事发出正式文告,这是史无前例的做法。文告的措辞显然经过朝廷众臣的深思熟虑:计划——“启柔远之图”;[7]战略——“建和亲之义”;[7]目标——“兵役休息”;[7]展望——“克致和平”。[7]
唐中宗为金城公主入蕃举行盛大仪式,他在众人瞩目下作为父辈“悲泣歔欷久之”[7]后直言:“割爱,全为敦睦唐蕃关系”[10]并即下达实行两道和亲事件中前无古人的重大举措——一是“改始平为金城”;[7]二是“始平县大赦,免去该县百姓徭役一年”。[10]这种罕有的做法,可见唐中宗对金城公主此次入藏所承担的重大使命与期许。与此相呼应的是,民间诗歌对金城公主入藏显然受到了正式文告的导引:“青海和亲日……汉国旧家慈”;[11](P397)“广化三边静,通烟四海安”;[12](P399)“筑馆许戎和,俗化乌孙垒”。[13](P400)这些企盼金城公主入藏开创新和平的呼声显然是社会当时的主流情绪,用交流化解矛盾,用交往化解分歧,用交融实现和平,最终促进双方的友好往来,实现双方经济社会的新发展。
二、再现“安边实践”的成果:值得关注的六件大事
金城公主的远嫁是当时唐蕃关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双方友好的最高象征,藏族民间传诵至今的诗句“汉家女子远嫁到此地,生下举世无双的王子”[14](P48)中,这位“汉家女子”就是金城公主,唐中宗李显的侄女,与皇帝有血缘关系,而她生下的王子则是后来的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在五世达赖喇嘛的著作中明确记述母亲金城公主与儿子赤松“小王站立”[5](P34)时的对话:“我系汉地所来女,而生小王无伦比”,[15](P35)“赤松我乃汉家甥”。[15](P34)这短短的一句话可知唐代和亲政策出现了最为重要的成果——血脉一家,亦由此肇源,这在唐蕃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今天,无论是在拉萨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亦或冬宫布达拉宫,还是班禅驻锡地扎什伦布寺,都有《赤松德赞宴前认母图》和《金城公主与儿子赤松德赞》的壁画,用生动的载体呈现汉藏甥舅一家的血缘关系。
不负众望的金城公主不遗余力地利用自身带来的各种资源弥合唐蕃政治罅隙,促进文化沟通,竭力交流交融,取得了传诵后世的六件大事,为今天正在施行的“一带一路”愿景,借鉴金城公主入藏本身所具有的经济硬实力及文化软实力的有效配合有着很强的启示。
(一)“调解纷争”即以己之力积极调处唐蕃间的边疆冲突。
客观地讲,在唐蕃矛盾交织的大环境下,双方交战并没有因为金城公主的和亲而消失。由于赞普刚刚长成,权力和影响尚嫌不够,金城公主上书皇帝“今乃骚动,实将不安和”,[16](P38)告知皇帝边将好大喜功,屡次起衅,致使战火不断,“前任赞普做不了其将军们的主”。[17](P23)这个理由成了双方都可不必承担并杯释前嫌的说辞,这种被人为定性的战争性质顺理成章地被认定不是唐蕃关系的失信。由于汉藏甥舅联姻的源流,金城公主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坚信人的力量在心上,尽力在双方间斡旋,顺理成章地“在两位执政君主之间作了调解以重修友好关系”。[17](P23)在金城公主的超然努力下,攻心则反侧自消,唐蕃在这一时期的矛盾没有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总的来说是和平多于战争。
(二)“七期荐亡”的丧葬仪式与中原自此开始合流。
金城公主入藏后,目睹吐蕃“佛法尚未发展”,[18](P112)对“往昔大臣死”[18](P112)没有“当应怜悯”[18](P112)的事实,提出要为亡人建立“好的善事习规”,[18](P112)希望依据“中原佛法兴旺,人死后四十九天以内逢七就要做法事,超度亡灵”[14](P47)的建议被吐蕃采纳,自此“就有了七期荐亡之俗”。[14](P47)这是金城公主入藏取得的重要成果,并与之建立共信。
(三)“觅释迦佛”为佛教兴盛创设舆论上的基础。
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还是纯粹宗教上的考量,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结论显然是后者。事实上,金城公主到藏之后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接续文成公主的具体做法并加以符合西藏实际的创新发展。随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佛像,仅仅是安置在寺院内,吐蕃当时并没有举行各种仪式的习俗。金城公主入藏后寻找到文成公主即“姑母之释迦佛”,[18](P112)“从此始建谒佛之供”。[18](P112)这种由金城公主亲自践行的佛教仪式为日后佛教参与吐蕃朝政奠定了舆论上的基础,是促使佛教走向兴盛的重要举措。
(四)“文化入藏”——在深化两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文化成为深层次的媒介。
唐中宗赐予金城公主“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19],如此丰厚的嫁妆显然是比照吐蕃查遗补缺后精心准备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唐朝采用的策略,即用嫁妆传递价值,延续文成公主的做法继续文化入藏。随着许多汉僧随金城公主入藏,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再次命人“迎请出家沙门”[15](P33)并派人“自唐都京师翻译《金光明经》、《毗奈耶分品疏及少部分医药典籍》”[15](P33)等书,僧人们顺理成章地作了吐蕃和唐朝的文化播迁介质。需要指出的是,与金城公主一同进藏的官员在辅佐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以及金城公主之子赞普赤松德赞和传播佛教方面所起的作用更是值得一提。最著名的就是唐朝大臣巴德武及其子桑希。此外西藏现存最早的藏医著作《月王药诊》就是金城公主专门组织藏汉学者翻译并带到藏区的医书。这部著作比宇妥·云丹贡布的藏医经典《居悉》要早近一个世纪。
(五)“佛教入朝”使赤松德赞成为吐蕃政治史上重大成就者。
赤松德赞成为吐蕃第41代赞普,在位43年,由于其母坚定的信仰,带动其日益尊崇佛教,最终演化成“赤松德赞之伟大可与松赞干布相媲美”,[20](P5)成为“圣文殊菩萨的化身,他为弘扬佛法所建立的功业不可计数”。[21](P96)在琼结桥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到大家颂扬其“内政与外教的业绩”。[20](P5)1984年西藏自治区古碑保护委员会的专业人员对赤松德赞墓碑发掘结果显示,墓志铭的“最后12行明显包含有佛教语汇和术语”,[20](P148)这是赤松德赞深受其母崇佛影响的历史证据。他承袭母亲的做法派人“往汉地迎请汉僧”,[22](P73)但显然没有就此停留,而是在此基础上邀请印度高僧入蕃,并在其支持下,莲花生使用密宗法术战胜苯教,并“涌现了不少翻译家将许多佛语和论著译成吐蕃文字”,[23](P375)为佛教登上吐蕃政治舞台扫清障碍。这场变革“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发起,但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则涉及了社会的各个方面。”[24](P130)显然可以明证佛教已经在政治上发端并顺理成章地首次出现在吐蕃藏王墓碑中。不仅如此,推行佛法同样对“以后封建农奴制时期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4](P130)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对吐蕃产生的影响,有观点称“这对自古就具有好强进取、英勇善战、决不屈服于任何强暴的民族,灌输了一种向虚幻世界寻求解脱和来世幸福的精神,从根本上削弱了这个民族英勇好强、奋发进取的锐气。”[25](P110)这种说法未免偏颇,但是吐蕃尊崇佛教、传扬佛教的氛围由此形成,延续至今。P·戴密微就认为“西藏皈依佛教并非像当地传说的那样,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结婚时,也不是在八世纪上半叶……而是在赤松德赞和他的继承者时代”。[26](P259)
(六)“盟誓誓文”受其影响,刻于石碑,永存于世。
赤松德赞统治时期,大量誓文开始出现,“盟誓文书刻刀石碑上立于神殿之前的这种做法,首先开始于赞普赤松德赞时期。”[27](P52)为了防止佛教被权贵阶层破坏和阻止,他要求君臣起誓,不得毁坏佛教,并据此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时机。藏文史书《贤者喜宴》就记录了大臣毁坏佛教的诸多案例。
金城公主入藏是对和亲政策的肯定和延承,其中包含历史的选择因素以及在民族问题处理上的经验借鉴。她的入藏是在唐蕃处于对峙的局面下进行的主动选择,这是与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威慑的迥异之处。历史证明了这种政策在当时当地的合理性及其对于巩固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三、思及“言而有信”之规矩:立互信而坚共信
唐廷正式决定金城公主远嫁吐蕃的时间是707年,这一年恰好是唐蕃会盟,这种友善的氛围其实是个梦幻,并没有给唐朝带来放心的和平环境。在金城公主入藏到逝世的这30年间,唐蕃于714年和733年相继进行了两次会盟,最终还是因战争使盟誓成了一纸空文。[28](P139)唐朝的边防政策似乎也没有因为金城公主的出嫁而出现丝毫的松懈与麻痹,此时全国设置的九大藩镇有三个与防范吐蕃有关,可见,吐蕃对唐朝边界施加巨大压力的军事考量。这一点可以从与吐蕃接壤的三大边境藩镇设置的战略目标一窥究竟:在河西凉州,防御吐蕃对河西走廊的侵袭(711年);在陇右鄯州,防御吐蕃对关中西部的侵袭(714年);在剑南成都,防御吐蕃对四川边境的侵袭(717或719年),由此可见吐蕃断续袭扰唐朝的弧形军事路线图。
吐蕃如此袭扰,原因何在?反思其时唐朝的政治现状:“武周末年因贪污和行政普遍废弛而号召的彻底改革干脆没有进行。相反,这几年出现的只是在日益恶化的财政和行政局势下展开的激烈的权力斗争。”[2](P290)在斗争的最后阶段,唐中宗在710年被“他妻子或女儿在他喜爱的糕点中下的毒所害”,[29](P295)这发生在金城公主正式前往吐蕃的路上,两件大事巧合般地发生在同一年。事实上从707年至710年这四年间,双方的“长期和谈,在睿宗即位前不久以和亲结束。吐蕃人能够从唐朝廷取得非常有利的条款”,[2](P330)不管唐朝目的如何,金城公主前往拉萨试图缓和与吐蕃的关系,减轻军事压力,以便集中精力处理中央王朝的内部事务已成为可能。此后吐蕃抓住机会“借金城公主与唐谋和,以作为其将势力伸入帕米尔高原,并试图侵夺李唐所控制西域地区的烟幕而已”。[30](P228)仅从这一点上看,和亲的背后双方都有着特殊的政治考量。
金城公主前往拉萨之后不到三年,和平的成果开始显现,唐蕃关系和缓并签订了一份和约,无疑这有着金城公主的努力。遗憾的是和约签订不久,吐蕃开始攻击兰州但遭到了彻底失败。值得一提的是,在金城公主入藏的30年间,唐蕃关系中不断的战争和结盟穿插进行,除了737年的战争之外,多由吐蕃引起。这使唐玄宗产生并滋长了不信任,多年不愿再作任何和平安排。①在这种背景下,717年,面对吐蕃君臣百姓均不愿与唐朝为敌的形势下,金城公主不失时机,再次毅然上书唐皇,代奏吐蕃思求和平之意,发出《乞许赞普请和表》,说“赞普甚欲得和好,亦宜亲署誓文”,[31](P38)但是“皇帝兄不许”,[31](P38)希望“怜奴奴远在他国,皇帝兄亲署誓文,亦非常事,即得两国久长安稳”,[31](P38-39)言辞之恳切,就是希望能对吐蕃的各种错误不计较、要宽容。唯此,金城公主启动的亲情牌又一次获得成功。
739年,金城公主逝世。唐玄宗拒绝了吐蕃希望“在长安为她举行葬礼的机会缔结新的合约”,[2](P392)吐蕃于是迅速控制青海湖区,进而攻入今天甘肃区域。“安史之乱”使吐蕃进一步看清唐朝军力的羸弱,于是毫不犹豫地于763年攻打到唐都长安,并立金城公主之侄李承宏为皇帝。吐蕃何以立李承宏为帝,从姻亲关系上分析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文成公主入藏的640年到金城公主逝世的739年,前后近一个世纪,两人在藏时间总共超过70年,唐蕃皇室在两次重大的联姻事件中艰难建立起来互信,为唐蕃建立政治策略上的亲密关系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外在的表征就是吐蕃贵族子弟不断被送往唐朝学习,唐朝的书籍和工匠被带到拉萨。
事实上,金城公主在长安时期,“佛教已长期从国家和贵族那里得到无与伦比的庇护”,[2](P372)由于金城公主是虔诚的佛教徒,她的入藏不可避免地带动佛教的大发展,入藏之前生活在长安的金城公主不可能不知道“吐蕃与大食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使者往来关系”,[32](P264)大食的宗教迥异于佛教。但伊斯兰教和同唐廷崇奉的道教并没有在吐蕃迅速发展,而佛教却渐成一家独大。在《于阗悬记》北京版中有这样的词句:“金城公主入藏后,中国在宫廷采用道士之法”,[33](P46)道士之术对金城公主来讲是完全陌生的,加之路途遥远,道教的核心内容在轻车熟路的佛教面前从感情上和接近性来讲自然不被金城公主重视,哪怕“敦煌文献内有玄宗御制道德真经”[33](P46)也毫不影响金城公主及其前往吐蕃的团队信仰佛教的信心,因为改宗立派需要大量舆论准备,内在动力本身不足,外在推力更难聚集,佛教的发展在这种境况下发展起来。
金城公主入藏20年后,意识到建立信任的基本价值需要普及,意识到这对双边交往的重要。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战略传播,有很强的现实寓意。她在入藏二十多年里奠定了双方文化共识的基础,趁势而上又做了一项功德无量的大事,即731年正式通过吐蕃使节给唐朝发去一份书单要求将《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送到吐蕃,这种正式的要求显而易见不是金城公主个人的意愿,争论却由此展开。中原文化是否应该普及,是否具有普适性,不同的人出发点不同,结果当然迥异。《资治通鉴》详细记述了金城公主这封信件引起的轩然大波,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以意识形态斗争论为考量的休烈希望朝廷不要答应吐蕃的要求,这些中原典籍传入吐蕃会使他们“知用兵权略,越生变诈”;[34]以意识形态普世论为考量的裴光庭等人则真切希望吐蕃实现核心要义——“忠、信、节、义,皆从书出也。”[34]裴光庭上书皇帝称这些典籍缘何传递是因为吐蕃“不识礼经,心昧得义,频负盟约,孤背国恩”,[35](P124)在同意其求和的前提下,将“所请书随事给与,庶使渐陶声教,混一车书”,[35](P125)最终在吐蕃实现“文轨大同”。[35](P125)今天来看,事物的正反面均需要权衡利弊,通盘考虑,不能仅仅看到其某一层面的影响,最终双方斗争的结果当然实现了金城公主的想法。果不其然,这些典籍对吐蕃的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吐蕃的许多习俗逐渐吸收这些经典,并翻译成藏文传播,“这说明当时吐蕃朝野上下,学习汉文化的风气十分浓郁,效果也相当显著。”[36](P30)
此后,吐蕃宫廷逐步建立了修史制度,出现第一批官修史书。敦煌的古代吐蕃历史文书和南疆的吐蕃文书,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吐蕃最早用纸笔记录的历史文献。由于有了这些历史文书,我们对古代西藏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和民族关系等有了深入的了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金城公主注重文化交流以及这种交流在西藏的深远影响。
诚然,文成公主入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相处仅三年,此后孤身在藏,“其间道路、人事之阻隔竟达六年之久,盖亦难矣”。[37](P253)金城公主与文成公主相较,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和众多制度的有效建立。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金城公主入藏之后,在藏生活30年,更因为赞普的大力推行,佛教成为青藏高原统治者的宗教。在金城公主逝世82年后,双方几经和战恩怨,最终以会盟的形式促双方走向互信共信的道路。金城公主的功业再次在唐蕃会盟碑中呈现,因为会盟碑的主题是甥舅亲好,我们今天看到这通庄严的碑文西侧用藏文写下“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或有猜阻”。[20](P51)会盟碑显然不能狭义地仅仅理解为甥舅,因为碑的开头第一句就写明“大唐文武孝德皇帝与大蕃圣神赞普甥舅二主商议社稷”[20](P51)。会盟碑的正式书写,使唐蕃双方以刻碑传世千秋的方式,在互信的基础之上正式进入了共信时代。
在今天看来,这通会盟碑的重大意义之一在于直面了当时双方反复交战的敏感议题。在东面的碑文中明确记录了唐蕃关系恶化为战争的缘由,使这种甥舅亲好关系因为边境的冲突而被扰乱。这就牵扯到边境的冲突是偶发的事件还是朝廷正式军令,无论是《旧唐书》中称“那时汉藏边境发生战事,通常归咎于边关将士”,[20](P69)还是《新唐书》中称“正如唐蕃会盟碑文所载,唐蕃双方统治者也是这样宣称的”,[20](P69)显然双方互给台阶,将责任归咎于守边将领的“相互侵袭,发生了数次抢占土地的矛盾斗争”,[38](P132)以此淡化领土之争而使用土地的字样,不再纠缠过去的是非,而是着眼于未来的和平,这应是值得称道的。
这一政策缓和了唐蕃矛盾,减少了战争频次,对促进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和团结,推动了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金城公主入藏是“与之共存,和为治先”的民族政策的具体实践,更是在历史审慎思维中可行性策略的一次大验证。唐朝在边疆民族问题上的言与行,对此后历代中央王朝的民族政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面对全球当下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面对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呈现出的文明冲突,在“与之共存,和为治先”基础上共信互信的秩序重建,坚定目标之后“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对搞好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显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关于与吐蕃的关系,见伯希和《古代西藏史》(巴黎,1961年),书中把《旧唐书》卷196上和下及《新唐书》卷216上和下译成法文。最佳的批判性研究载于佐藤长的《古代西藏研究》(两卷,京都,1960-1961年),此书把中文材料与J.巴科、F.W.托马斯和Ch.图森编译的《敦煌文献中有关西藏史的材料》(巴黎,1940年)中的藏文编年史互相印证,转引自(英)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330页。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历史年表(修订珍藏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加拿大)奥斯卡·J·雅克布斯著,邓小咏,王启龙译.追忆通往青海之路——公元600-900年汉藏关系汉文史料[A].王尧,王启龙编著.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八辑)[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
[3]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
[4](英)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5](美)白桂思著,付建河译.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
[6]《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
[7]《册府元龟》卷979,《外臣部·和亲二》.
[8]陈小强.试析吐蕃王朝社会结构[A].藏学研究论丛(第七辑)[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9]苏晋仁:唐蕃使者之研究[A].藏学研究论丛(第三辑)[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
[10]《旧唐书》[Z].《郭元振传》.
[11](唐)张说.奉和圣制送金城公主適西蕃应制,卷87页942[A].范学宗,王纯洁编.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12](唐)武平一.送金城公主適西蕃(卷102页1084)[A].范学宗,王纯洁编.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13](唐)赵彦昭.奉和送金城公主適西蕃应制(卷103页1088)[A].范学宗,王纯洁编.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14]李学勤,鄢玉兰整理.西藏民间故事(第七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
[15]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
[16]范学宗,王纯洁编.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17](法)J·巴科著,耿昇译.吐蕃王朝政治史[M].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二辑)[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18]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19]《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20]李方桂,柯蔚南著,王启龙译.古代西藏碑文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2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22]次旦扎西主编.西藏地方古代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
[23]恰白·次旦平措著,陶长松译.藏族文化史上的偏见辨析[A].藏学研究论丛(第二辑)[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
[24]周毓华.吐蕃时期的宗教与政治关系研究[A].藏族历史与文化论文集[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
[25]得荣·泽仁邓珠.藏族通史·吉祥宝瓶[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
[26]戴密微.拉萨僧诤记[A].巴黎,1952,第188-189页,转引自(法)麦克唐纳夫人著,汪萍译.松赞干布时代的西藏宗教:作为历史的神话[A].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三辑)[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27]陈庆英.陈庆英藏学论文集(上)[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28]李大龙.唐蕃关系发展动因解读[A].藏族历史与文化论文集[C].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9.
[29]《资治通鉴》卷209,第6641-6642页;《旧唐书》卷51,第2174页,转引自(英)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0]林冠群.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31]范学宗,王纯洁编.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32]张云.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33]许明银.西藏佛教史(改订增补版)[M].台北:佛哲书舍,2006.
[34]《资治通鉴》卷213,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正月辛未(二十二)条.
[35](唐)裴光庭.金城公主请赐书籍议(卷299页7上)[A].范学宗,王纯洁编.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36]王尧编著.王尧藏学文集(五)——藏汉文化双向交流·藏传佛教研究[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
[37]王尧编著.王尧藏学文集(一)——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吐蕃制度文化研究[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
[38]恰白·次旦平措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上)[M].拉萨: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顾祖成]
[校对梁成秀]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16)02-0017-07
收稿日期:2015-11-29
作者简介:喜饶尼玛(1955-),男,藏族,四川炉霍人,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民族教育研究》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历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