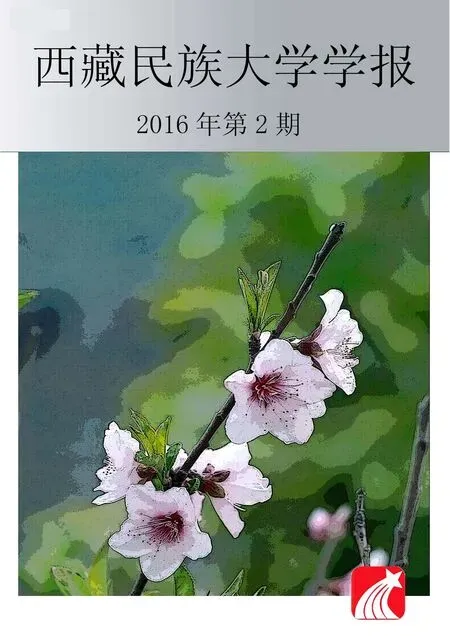宗教在华锐藏区的传播及其特点分析
华锐·东智(甘肃省藏学研究所甘肃甘南747100)
宗教在华锐藏区的传播及其特点分析
华锐·东智
(甘肃省藏学研究所甘肃甘南747100)
摘要:历史上,坐落在古代“丝绸之路”河西走廊门户之上的华锐藏区,藏传佛教文化高度发达,也曾对这里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等产生过深刻影响。在河西地区藏传佛教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华锐藏区又起了桥梁和纽带作用。文章以历史的角度,从华锐藏区的形成、佛苯文化的传播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宗教在华锐藏区传播的历史以及发展的特点。
关键词:华锐藏区;历史沿革;宗教文化;发展特点
“华锐”系藏语,是英雄的部落或地区之意。从现代意义上讲,华锐藏区主要指今天祝藏族自治县,本文所谈内容主要限于现代意义上的华锐藏区。华锐藏区是古“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之一,为河西走廊之门户,属安多藏区。据历史记载、民间传说、风俗习惯、语言等方面综合分析,该地区是公元633年吐蕃王朝时期,松赞干布建立强盛的吐蕃王朝后向其境内派驻边防军队,就此形成并世居华锐的一支藏族部落。因此,史书称华锐藏区为“噶玛洛”,意为“没有赞普之命不得返回”。华锐藏区的藏传佛教文化高度发达,高僧学者层出不穷,曾为河西地区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一、华锐藏区的形成
华锐藏区是河西走廊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新石器时代,境内已有人类活动。据《天祝县志》记载:商、周时期,为戎羌驻牧地。秦时,月氏迁入与土著人一同生活。秦末汉初,匈奴大规模南下,冒顿势力进入河西走廊,月氏被迫西迁,少数留居者进入祁连山和羌族共同牧畜生活,史称“小月氏”。西汉时,华锐藏区岭北分属姑臧、张掖、仓松县,属武威郡。东汉时,岭北属姑臧、张掖、仓松县,属武威郡。三国时,为凉州武威郡姑臧、仓松县和金城郡令居县管辖,为曹魏地。西晋时,岭北为姑臧、仓松县,属凉州武威郡。东晋十六国前凉时,岭北属凉州武威郡姑臧、仓松县。南北朝时,岭北为昌松、莫口、林中(姑臧)。岭南为广武县,属凉州(今武威)。隋朝,岭北为武威郡姑臧、昌松县(初改为永世,后复)。岭南为允吾县。唐时,岭南为姑臧、昌松县,属凉州武威郡。广德元年(公元763年)陷吐蕃。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沙州人张议潮率民起义,收复沙、瓜等十一州,华锐岭南地区复归于唐,由起义军管辖。五代,由吐蕃折逋氏家族控制。北宋时为西凉府,初由凉州六谷部潘罗支政权管辖,后于公元1036年为西夏所有,仍称凉州。元时,岭北初为西凉府。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降为西凉州,属永昌路。明时,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岭北置凉州卫,属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清时,岭北初为凉州卫,雍正二年改为武威县。同年置凉州府,治武威县,改古浪千户守御所为古浪县。岭南为庄浪卫,康熙时降为所,雍正二年为平番县。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设庄浪茶马同知,管理今华锐岭南藏区事务。民国初,为平番县管辖,属甘凉道。
关于“华锐”这个名称有三种说法:一说这里最早有“蕃人”俩兄弟,哥哥称阿秀,弟弟称华秀,阿秀生活在现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境内,他所管辖的领地叫“阿热”,而弟弟华秀生活在华锐地区,他所管辖的这一地区就称“华锐”;二是说因华锐地区山势陡峭、挺拔雄伟,就像是一位英勇的武士披甲戴盔、守卫家园,所以藏语中称“华日”,汉意为英雄的山峰;三是说在藏王松赞干布时代,从卫藏派遣军团守卫与汉、蒙相接的边界地区,这些边防军团长期守住这里繁衍生息,其后人就是英雄之师之后裔,故称“华吉”(意为英雄的后裔)、“华威戴”或称“华锐”(意为英雄的部落)。[1](P3-4)在历史学家中持第三种说法的较多,有一定的可信性。从“华锐”这一语义的文化内涵可以推断,无论是史料记载松赞干布之边防守军,还是传说中英勇善战的华秀部落,在古代,这里曾是一个群雄争霸的地区,有可能处在“英雄时代”的某一部落在战争中称雄而得“华锐”,即“英雄部落或地区”之名。
据华锐地方史记载,“实际上最早进入今华锐藏区的吐蕃人应该是在唐圣历二年(公元699年),降唐的吐蕃大相伦钦之弟赞婆,其率部千余人及钦陵之子莽布支(即伦弓仁)本部及吐谷浑七千帐归唐,他们先后安置在凉州昌松洪源谷(即今古浪峡,属天祝、古浪)。”“唐至德元年(公元753年)至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吐蕃驻青海积石山的下勇武部先后占领青、甘部分地区(包括今华热),在这一时期,即公元755年至797年,吐蕃本土的札、珠、党三大种姓迁入今华热。勇武部落的迁入为形成华热奠定了基础。”[2](P47)北宋初,今华锐藏区建立了吐蕃地方政权——凉州六谷蕃部,“六谷部”(阳妃谷、洪源谷、浩门河谷、庄浪河谷、东大河谷和西大河谷)是形成今华锐藏区的基础。“关于华热藏族的渊源很明确,即由西藏本土吐蕃军旅之一部,东迁之部分部落、‘嗢末’起义的奴隶,同本地的羌、小月氏、吐谷浑及一部分汉族,在长期的交往及历史演变融合而成,这个新兴的民族组合体即是华热藏族的雏形。”[2](P3)六谷部首领皆受宋王朝的册封。宋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党项羌李元昊自称皇帝(即西夏),当时,西夏和吐蕃交往频繁,接受吐蕃的传统文化,信仰佛教,修建佛寺。
公元1226年,蒙古汗国军攻克凉州,次年西夏被蒙古汗国所统一。自此,华锐藏区皆属蒙古汗国统治。元代华锐藏区归凉州所辖。明、清两朝统治华锐藏区共达543年,期间,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华锐藏区发展迅速。以上史料可看出,形成华锐藏族的主体是吐蕃,即吐蕃军队的定居和部分吐蕃本土部落的迁入构成了华锐藏区的主体。从笔者掌握的一些史料看,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包括华锐在内的凉州武威郡管辖六县,藏族22462户,人口120281人。五代、宋时期,“凉州六谷部”人口15万,25393户(汉族只有300户)。公元1815年华锐藏区人口有10万,1867年人口突然减之千人左右,1949年藏族人口只有14012人。[3]
二、苯教文化的传播
苯教在藏语中称“温宝”,有些学者将其称为“本波教”,是植根于原始时期的一种宗教。据传,苯教的创始人是辛绕米沃且(意为最高巫师)。从内容上看,它是一种古老的原始宗教,所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冰雹、山川,甚至还有土石、草木、禽兽等万物在内,是故,研究者称苯教是一种“万物有灵”的宗教。王辅仁教授在《西藏佛教史略》中记:“这种宗教在学科上称作灵气萨满教。它本是流行在西伯利亚和亚洲腹心地带(包括我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一种原始宗教,因为这种宗教的巫师叫做萨满,所以称作萨满教,后来逐渐成了全世界公认的一个学科名词,……,苯教可以说是灵气萨满教在西藏的地方形式。”[4](P15-16)苯教的来源、发祥地是象雄及其以西的现巴基斯坦、伊朗一带。卡尔梅在研究苯教时说:苯教教义从大食(现伊朗)的俄茂林传到印度、象雄、汉地,再从这三个地方传到西藏。又说:教主死后,经文将在南方出现,然后在东方,最后在北方,北方是指西藏。又记:教主来到西藏后,传授了召神法、拔魔法、驱鬼法,从此,西藏的诸神和恶魔都能听从命令,执行委托他们去做的任何任务。[5](P281)
苯教注重祭祀,祭祀方法名目繁多,各有特点。苯教崇拜的原始神灵主要有赞神、念神、鲁神、地神等,另外,还有家神、灶神、帐篷神、阳神、战神等等。苯教自己的神灵有塞喀五神即贝塞恩巴、拉都托巴、卓却卡迥、格措和金刚撅,这五位神属苯教的护法神,心性残暴。另外还有苯教最重要的一组神,俗称“最初四尊”,即:萨智艾桑(苯教最早的神、万物最早的母亲、众神之母,居首位),辛拉俄格尔、桑波奔赤、辛绕米沃且(苯教创始人)。
苯教在吐蕃早期社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一些史料中可以看出,从藏王聂赤赞普执政时期到第二十六代赞普期间,他们都认识到了苯教实力对吐蕃社会的极大影响,充分利用了苯教徒在藏族社会中的威望,让他们来参与行政事务,用“仲”、“德乌”和“苯”三种宗教来辅助赞普、护持国政。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所著《西藏王臣记》中记载,吐蕃宫廷中有一个名叫“敦那钝”职位,由一人充任,其职责是在赞普身边占卜凶吉。“敦那钝”在赞普左右享有崇高地位,并参与部分政治事务。苯教这种参与吐蕃社会政治决策和宗教统治的双重作用,一直延续到公元8世纪中叶。可见,当时苯教在青藏高原具有很强势力,教义传播极广,在人们心目中印象极深。
公元633年,松赞干布建立了强盛的吐蕃王朝后,于663年向东发展,灭吐谷浑后随之将世居甘、青一带的诸羌部落统辖其下。唐朝中期,吐蕃进占河陇后,开始向今甘肃境内派驻军队,并按照“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原则,派遣一些吐蕃本土的部落定居其内。吐蕃统治甘、青地区后,按其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宗教、文化等制度治理地方。当时,为鼓励将士在前线奋勇杀敌、保卫领地、吐蕃统治者在军队中又特派苯教巫师随军助战。“每千户有一个大的苯教巫师,称之为‘拉布波’;每一个战斗小组有一个小巫师,称‘拉巴’”。[6](P92)出征时由这些苯教巫师念咒经,以求战争胜利。此时松赞干布虽迎佛抑苯,佛教在统治阶级上层中发挥着作用,但广大劳动人民则仍然虔信苯教,所以,这些士兵和巫师后来(因诸多因素未能返回)长期定居华锐藏区,并连同“拉布波”、“拉巴”一起不断传播苯教教义,吐蕃时期这种向东两百多年的武力拓展,其结果使吐蕃本部与华锐藏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均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和交融。洲塔教授在其著作《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中说:“藏巴第悉噶玛丹迥旺布时期制定的《十六法典》中就明确规定,在军队中有4种人不可缺少:一是救治伤病员的医生,二是预示凶吉的卦师,三是卜测天象物候的星象师,四是祈祷战神的巫师。”[7](P467)这一记述更加证实了苯教巫师在传播苯教教义时发挥的特殊作用。
据华锐地方史载:“在吉勒(今华锐天堂乡境——引者)十三神山的《祭辞》中写道:‘往昔阳章苯教供奉时,降魔除害消灾保平安’。称作扎贡曲吉多杰的成就师,被吉勒沿岸的藏族部落迎请,表示崇敬,这事引起一些苯教徒主要人物的妒忌,说要比试本领。扎贡心想,如果对这个苯教徒不使点神通手段,佛教密宗无法立足。决定要在天地河水形成三角形的地方收拾他。不久苯教师被湮死在吉勒里”。[1](P19-20)在《安多政教史》中对此人也有记载,传说是扎贡曲吉多杰首先征服了吉勒河里的毒龙。这些资料表明,早在元朝以前,华锐藏区苯教就已流行。“在第十六绕迥土狗年之前,在藏族家里还有念多纳经的,赛马会上群众和苯教士聚集在一起念诵‘琼’。至今在一些古老风俗尚未完全消失的藏族地方,娶新娘时还有一个叫‘苯’的巫师做‘伍吹’(洗浴新娘)、说婚礼献词等古代习俗。”[1](P19)这些史料都充分说明了苯教在华锐藏区发展、延续的历史脉络。
华锐天堂寺,藏语称“却典堂扎西达吉琅”,汉意为“宝塔滩吉祥兴旺洲”,其前身是唐宪宗(公元806至822年)时所建的苯教寺院,当时称“雍仲”寺。五百年后,即公元1360年,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第四代黑帽系活佛噶玛若贝多吉(公元1340-1383年)进京路过此地,接受当地群众的请求,遂取名“却典堂”,意为宝塔滩。自噶玛大师建塔后,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便在此兴盛,古老的苯教寺院遂变为噶举派寺院。
另外,从本地区民间传说中也可以搜寻到苯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和遗存情况。从华锐石门沟上至三岔,沿药水沟而进,行至20里,便到达马牙雪山脚下的药水神泉。据说,这里原有108眼药泉,泉泉都有治疗各种疾病的功能。明、清时有高僧活佛曾多次为药泉开光,并分类用藏文雕刻立碑,一时病人、游客络绎不绝,并医治了许多病人。这一事件引起了苯教徒的嫉恨,他们将石碑置乱,甚至摧毁。从此,各泉分类混乱,来人不敢乱用,数年间无人问津,苯教徒得意洋洋,认为摧垮了佛教。约至清代,一位高僧大德来此泉旁广做法事七七四十九天,重新进行开光,使泉水变得更加清净,所有的泉都恢复了治百病、消百灾、健身体的功效。从此,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喝药泉水的信民络绎不绝。有人说,这里曾出现过一只雄猛异常的雪狮,也有人说,有一头雄性白牦牛和一只白臂鹿清晨在此喝水。以上阐述大致勾勒出苯教在华锐藏区传播和遗存的简略历史。
三、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
佛教在华锐藏区传播的路线有两条。东汉至唐,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主要是河西走廊,也就是丝绸之路,包括甘肃河西道和南之青海道。华锐地处这两条路中间,影响较大。北魏时期,在华锐和周边建立了诸多佛教寺院,如木塔寺、马蹄石窟寺、大佛寺、天梯山石窟寺、大云寺、清应寺、鸠摩罗什寺、亥母洞寺等。藏传佛教传入华锐的路线一般是西藏→青海→甘肃→华锐;或西藏→四川→青海→华锐→凉州→甘州→内蒙古、宁夏。
地处交通要道的华锐藏区,其两侧(祁连山东端南北麓)皆为佛教传入的主要路线和地区。佛教传入华锐的时间始自吐蕃进占河湟、河西之后。唐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吐蕃进占敦煌,佛教事业日益兴旺,掘凿石窟,塑绘佛像,广建寺庙,翻译经卷,并由此向东传播。根据武威天梯山石窟发现唐时的藏文文书、经卷、宗教用品、佛像绘画等分析,当时凉州的佛教非常兴盛。这时的佛教,主要是宁玛派(古旧派)。这里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是宁玛派与吐蕃的民间原始信仰已经开始结合;二是吐蕃军旅和东迁之部落也带来苯教文化和当地的民间信仰结为一体,而且有广泛的传播。
公元838年,吐蕃最后一位赞普达玛继位,开始打压佛教势力。佛教在西藏受到严重限制后,今西藏曲水县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藏·饶塞、约·格迥和玛尔·释迦牟尼等三位僧人携带经卷逃到西宁一带弘扬佛法。在他们的门徒中有一名为格萨瓦(喇钦·贡巴饶赛)者佛学造诣精深,他晚年出游至今青海互助县(与天祝毗邻)、祁连一带弘法,这对包括天祝在内的华锐藏区有很大影响。吐蕃王朝崩溃后,在华锐兴起了以潘罗支为首的“凉州六谷部”(包括今甘肃天祝、肃南东南部、青海互助、门源一带),由宋朝资助大量财物作为修建喇嘛寺院的费用。西夏建国后(公元1032至1227年)统治凉州六谷部地区,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佛教广为流传,与吐蕃联系日广。尤其在天盛十一年(公元1159年),夏仁宗遣使邀请噶举派始祖都松钦巴到西夏弘法,都松钦巴未能前来,派大弟子藏·琐布携带经卷、佛像至西夏,被仁宗奉为上师,并组织人力大规模翻译经卷,广建寺庙,这对华锐藏区有一定影响。
依众多史料来综合分析,宋、元年间藏传佛教在该地区还有未牢固的社会基础,严格意义上讲,只是一个重要的传播阶段。此时噶举派(意为口授传承)已经在华锐藏区和凉州一带传播,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二世教主噶玛拨希(原名曲杰)在青海及甘肃甘州、凉州及蒙古一带弘扬佛法,后有第三世噶玛热迥多吉、四世若贝多吉、五世德银多吉先后来甘、青建寺弘法,对华锐天堂寺、百灵寺等影响颇大。这一时期,萨迦派也开始在华锐传播。
公元1238年,阔端邀请当时西藏最负盛名的萨迦派第四代领袖萨班·贡噶坚赞来凉州和谈,萨班于公元1246年同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到达凉州。途经华锐停留尕哒寺,发现此地有福德瑞祥之兆,在他的亲自主持下,扩建寺庙,并改尊为萨迦派,赐名为“乔尕琅”。萨班在凉州广设经场,弘扬佛法,其间又在华锐多次弘扬佛法,给僧俗民众摩顶赐福,并创建了极乐寺。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途经康区,噶举派领袖噶玛拔希亲见忽必烈,他不肯留忽必烈左右,而自行北上到凉州一带弘法,在华锐藏区有极高的威望,深受藏、蒙民族的崇信。其后又有噶举派三世让迥多杰先后两次赴京为皇帝灌顶说法时途经华锐弘法、讲经,并修建了许多噶玛噶举派道场和寺院。元朝对华锐藏区的施政,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册封了一些佛教上层主要人物。公元14世纪中叶,被朝廷封为“大宝法王”的噶玛若贝多杰在进京途中经过华锐藏区,根据吉勒河地方广大僧俗的请求,降伏了吉勒河里的毒龙。为显示降伏毒龙之征兆,建镇龙塔108座,并在此弘法。把“斗曲巴龙齐哇”(毒水沸腾)改称“德子”(甘露),把原称“扎西堂”改为“桥天堂”(宝塔滩),随建成噶举派寺院。
明朝中期,宗喀巴创建的格鲁派传入甘、青藏区,经与其他教派的激烈斗争,取代了诸派,占据宗教上的统治地位。此后,有许多格鲁派僧人到华锐弘法,创建寺院,原来其他教派寺院全改尊为格鲁派。格鲁派势力在华锐的迅速发展,使华锐藏区的藏传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为藏传佛教在华锐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1644年,清顺治继位后,普遍敕封了一批格鲁派著名活佛为呼图克图。当时在华锐藏区敕封的有章嘉、土观、松巴、东科尔、达隆等等。这些活佛大多被召往朝廷供职,由国家发给年俸成为驻京呼图克图。清代为格鲁派极盛时期,五世达赖赴京途中曾到华锐弘法,据传说,后来六世达赖被蒙古和硕特首领拉藏汗废黜,在押往北京途中脱身后避居华锐,其间他重建石门寺,并担任石门寺、东大寺、先明寺等十余座寺院的法台。格鲁派在华锐藏区盛行之时,安多及其他地区来华锐弘法的高僧逐渐增多,他们不但传播教义,而且扩建寺院,制订寺院清规,发放布施。华锐许多寺院的执事者和各头人、土司带头发放布施,承担来华锐弘法高僧的生活费用。到清中期,藏传佛教在该地区达到了鼎盛状态,高僧学者层出不穷。
华锐藏区的寺院,大多为明末清初所建,均为格鲁派寺院。从明末至清,藏传佛教在华锐藏区十分兴盛。同时,寺院不仅成为该地的宗教中心,而且成为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天祝藏族自治县成立之初,有“三十六族,十四寺院”之称谓。藏传佛教对华锐藏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在人们生活中无处不在、无处不显。华锐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深受其思想体系的影响,同时也充分展示在华锐人的现实生活当中。1943年,永登县(此时华锐藏区属永登县所辖)县长章金泷在给甘肃省政府的呈文中说:“番族无论男女,概信仰佛教,并有奉祀山神之神者,各族均建有寺院,如华藏、石门、达隆……天堂等十四寺,……,寺院建筑,无不壮丽辉煌,喇嘛权威,高于一切,虽各族头目亦俯首听从。”[1](P167)
四、宗教在华锐藏区发展的特点
今华锐藏区准确的位置处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祁连山东端南北麓,西与阿柔(祁连)相连,南与觉仓(乐都、民和南山)接壤,东与永登毗邻,北靠古浪、武威、永昌等县。其主要聚居地在甘肃边界两侧,即大通河湟水、庄浪河流域之间。华锐藏区是古“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之一,为河西走廊之门户。吐蕃时期,华锐属“三围四茹六岗”之中的叶摩岗或东方安多宗喀神变区。自古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重要战略地位。在藏传佛教向河西地区传播过程中,华锐藏区又起了桥梁纽带作用,对生活在河西的各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藏传佛教的包容性使得苯教文化在华锐藏区得以持续发展
藏传佛教在华锐藏区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对本土宗教即苯教采取了包容的态度,包容的结果是吸收了许多苯教文化。藏传佛教吸收了苯教的一些神祇和仪式,与其有共同的神山、圣湖,比如苯教最尊崇的冈仁波钦神山,也同样成为华锐藏区信仰者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山。这种“包容性”后来逐步演变为藏传佛教的一大特点即就是“兼容性”,这方面尤其是格鲁派最具有代表性。也就是说,为了取信于民,也为了统战当地的苯教信仰者,它在传播自己文化体系的同时,针对苯教在广大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也在吸收和传播着苯教文化。
(二)藏传佛教以华锐藏区为中心向河西地区辐射发展
华锐藏区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也是“河西走廊”之门户,地理位置的特殊使得藏传佛教各派都特别重视首先在本地的传播。如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二世教主噶玛拨希(原名曲杰)、萨迦派领袖人物萨迦班智达·贡噶坚参以及萨班之得意门徒八思巴等先后来华锐藏区传播萨迦派之教法。格鲁派兴起后,也迅速在华锐地区传播格鲁派教义,如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六世班禅华丹益希等宗教领袖人物在华锐藏区建立寺院,在各寺院讲经说法,影响颇大。藏传佛教在华锐藏区的广泛传播,为河西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三)“政教合一”制度对华锐藏区的影响深远
自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到华锐藏区至清康熙年间就基本上实行了“政教合一”的制度,这一制度对华锐藏区各民族的政治生活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格鲁派的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使得华锐藏区境内的寺院一时多达18座,僧人近万,这一时期,寺院不仅成为该地区的宗教中心,而且成为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除藏族外,藏传佛教对本地区的蒙古族、土族、裕固族也影响很大,藏传佛教文化同样成为这些民族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主心骨,各部落大小头目都要接受寺院活佛的册封。
(四)藏传佛教在华锐藏区的传播中改宗频繁
明朝中期,宗喀巴创建的格鲁派传入包括华锐在内的甘、青藏区,经与其他教派的激烈斗争,取代了诸派,占据宗教上的统治地位,原来其他教派寺院都改尊为格鲁派。明朝对各教派的封赐不像元朝那样唯萨迦派独尊,是故,藏传佛教在华锐发展迅速,但萨迦、宁玛、噶举派的寺院在修学方而尚无严密的学科分类和规模性的研习体系,所以影响不大,鉴此,改宗频繁是宗教在本地区传播过程中的一大特点,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华锐藏区的天堂寺。天堂寺历史悠久,是唐朝时期吐蕃所建的苯教寺院,1360年噶举派高僧噶玛·若贝多吉将其改为噶举派寺院,明代后期天堂寺又改宗为格鲁派寺院。
[参考文献]
[1]东永寿,苏得华编译.华锐历史文献选编[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
[2]乔高才让等.华热藏族史略[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
[3]华锐·东智.清朝后期天祝藏族人口锐减之原因探析[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汉),1996(1).
[4]王辅仁编著.西藏佛教史略[M].兰州:青海民族出版社,1991.
[5]《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辑[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6]华锐·东智.拉卜楞民俗文化[M].兰州:青海民族出版社,2004.
[7]洲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索南才让]
[校对陈鹏辉]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16)02-0033-06
收稿日期:2016-01-16
作者简介:华锐·东智(1967-),男,甘肃天祝人,现为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安多研究》(汉)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