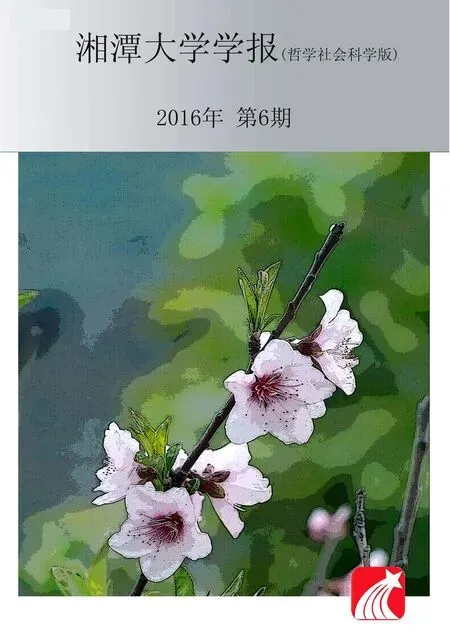毛泽东与长津湖战役研究中的相关争议问题辨析*
张海燕,梅世昌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005)
毛泽东与长津湖战役研究中的相关争议问题辨析*
张海燕,梅世昌
(湘潭大学 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005)
长津湖战役是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东线部分。此次战役交战双方褒贬不一,也引发了一些研究者对战役本身及毛泽东与战役相关评价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毛泽东为何考虑让第9兵团投入东线长津湖战役,为何力主要在东线发动攻势,是否直接指挥长津湖战役,对长津湖战役结局的评价是否客观等问题。辨析这些争议性问题对于还原历史的真相,正确认识长津湖战役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长津湖战役;第9兵团;战略任务
长津湖战役是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东线部分,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于1950年11月27日发起,目标是与东线“联合国军”作战,保障西线志愿军侧翼安全,并在运动战中寻机围歼美第10军主力部队(陆战一师以及步兵七师)。经过20多天战斗,志愿军共歼敌13916人,成功收复朝鲜东北部地区,东线“联合国军”被迫由海上撤至三八线以南的釜山地区。毛泽东对此次战役的评价是“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1]241有意思的是,美方也高度赞誉此次战役。
此次战役作战中美双方褒贬不一,也引发了一些研究者对战役本身及毛泽东与战役相关评价的争议。本文将根据现有公开的档案、资料以及出版的文献,对毛泽东为何考虑让第9兵团投入东线长津湖战役,为何力主要在东线发动攻势,是否直接指挥长津湖战役,对长津湖战役结局的评价是否客观等主要争议性问题展开辨析,以求还原历史的真相。
一、毛泽东为何考虑让第9兵团投入东线长津湖战役
(一)从作战经验来看
第9兵团隶属于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下辖20、26、27三个军。20军前身为坚持三年闽东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在9兵团部队中资历最老,后改编为华野一纵,善于纵深穿插;26军前身是抗战时期鲁中军区部队整编而成,解放战争时期改编为华野八纵,以防守著称;27军前身为抗战时期胶东军区部队编成,后扩编为华野九纵,擅长攻坚战。
1947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一、四、八、九纵将国民党整编第74师包围在孟良崮并彻底歼灭,这一次战役“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3]81孟良崮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劣势装备与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部队第一次交手,这一场战役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是毛泽东运动战思想、围点打援战术的一次成功实践。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解放军武器装备的同时,也给后来参加长津湖战役的20、26、27军积累了极其重要的作战经验,尤其是取得如何以劣势装备迎战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第9兵团作战经验在解放军中极其丰富,除了在孟良崮战役中围歼第74师外,还在淮海战役中围追堵截,使蒋介石嫡系部队杜聿明集团成为瓮中之鳖。解放上海后,成为被国人传颂的“霓虹灯下的哨兵”。[2]6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第9兵团装备精良,战斗经验丰富,纪律严明,是解放军的精锐之师。
东线战场,志愿军面对的主要敌人是陆战一师,陆战一师在美军当中一直被视作“尖刀部队”,[4]5其作战经验相当丰富,各兵种之间协同默契,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师级作战单位。以驻扎在东北军区,适应寒带作战部队的战斗力、作战经验而言,很难与美陆战一师抗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第13兵团被调往西线战场之后,国内只有第9兵团和第19兵团相对来说能与陆战一师一战,但是第19兵团的人数、装备及其作战经验和各级官兵战斗素质与第9兵团相比较弱,难与陆战一师抗衡,因此,从作战经验上看,第9兵团是较好的选择。
(二)从各级将领素质来看
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湖南醴陵人,入黄埔军校学习过,参加了红军长征,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屡立战功,多次受表彰,是解放军中一名出色的“儒将”。第9兵团副司令员陶勇,在历次指挥作战中,身先士卒,所向无敌,曾被誉为“拼命三郎”,与叶飞、粟裕、王必成并称第三野战军四员“虎将”。1949年4月,在“紫石英”号事件中指挥炮击英舰的正是陶勇,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率部第一次在战场上与西方列强交手。20军军长张翼翔,虽然没有经历过长征,但是在南方随陈毅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军事素质过硬;26军军长张仁初,参加过鄂豫皖苏区一、二、三次反“围剿”,后在长征途中参加了腊子口战斗,资历老,作战经验极其丰富;27军军长彭德清,1926年便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坚持过三年游击战争。在第9兵团中,彭德清率领的27军最先入朝,并且27军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中还担任过后方的警戒任务。
我国贯彻依法治国的方针,在发展过程中,要有法律的约束,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发展过程的安全性、明确性以及清晰性。所以在林业保护与天然林保护中,相关的政府部门一方面要加大对生态保护的投入力度,为生态保护工作提供充实的后备力量,引进品质优良的树种,扩大种植的面积,优化种植地土壤,提高土地营养成分的含量,从而进一步提高森林的质量,为生态保护工作作出贡献[1]。另一方面,相关的政府部门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约束人们的行为习惯,让人们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活动,从而有效改善生态环境。
考虑到要对付东线“联合国军”当中的精锐部队,毛泽东认为“必须使用宋时轮主力于该方面有把握”。[1]179可以说,历经战火洗礼、作风顽强、敢打胜仗、战功赫赫,加上各级将领素质过硬、资历老、信仰坚定,这些优点无疑是毛泽东看好第9兵团的原因。
二、毛泽东为何力主要在东线发动攻势
2012年,学者光亭认为长津湖战役“表面上看是为了应付联合国军在东线的迅速发展,保障西线侧翼安全。而实际上朝鲜北部由于狼林山脉所隔,形成天然的东西两部分(交通阻绝,大兵团更难以逾越),险恶的地形是双方都无法利用的,根本不存在东线威胁西线侧翼的情况(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双方都从未有过大兵团穿越狼林山脉的事例),”但是“毛泽东10月31日致宋时轮、陶勇电报中就明确赋予九兵团‘以寻机各个歼灭南朝鲜首都师、第3师、美军第7师及陆战1师等四个师为目标’”,“逐个歼灭东线联合国军四个师,这么宏大的战役决心很显然还是建立在解放战争中大歼灭战的经验上(第一次战役特定的遭遇战性质也使志愿军对美军战斗力产生了错误而又致命的低估)。这样的决策,从战略上讲是毫无必要,因为东线只是次要方向,只要集中力量击退西线美第8集团军,那么东线美第10军就必然后撤”。*http://www.hljnews.cn/fou_wh/2013-05/06/content_1969023.htm.此外,部分国内战史学家也认为“东线战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和气候环境,交战双方没必要在此大打出手”,[2]2如能将第9兵团投入到西线,则会获得更大的战果。这些都是争议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简而言之,他们都认为东线长津湖战役没有必要进行。而实际上,毛泽东力主在东线发动攻势是有其必要性的。
(一)从敌军的战略部署上看
1950年10月,“联合国军”在元山、咸兴一带登陆后,毛泽东就开始预料到朝鲜东部战线的韩国首都师、三师、美军第七师共三个师的部队由“咸兴向北进攻的可能性极大”。[1]179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迅速制定出来的“圣诞节”攻势就是从东西两线同时进攻,其中东线美军第10军(辖陆战一师、步兵七师、步兵三师)计划由长津湖地区兵分两路向西推进,一路准备与掩护西线“联合国军”右路进攻的南朝鲜部队在武坪里(长津湖以西的一个小镇)汇合,而后向北推进,另一路则由东向西北方向进攻,准备攻占领朝鲜临时首都江界,包抄西线志愿军后路,“在第10军‘抢占一个实施包围的战略要点,将敌占区北部分割成两段’后,第8集团军准备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压缩包围’,并‘合上老虎钳’”,[5]66与西线“联合国军”包围并彻底消灭中朝联军,一举结束战争。也就是说,东线“联合国军”必将翻越狼林山,合围中朝联军,如此一来,西线志愿军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可见,毛泽东关于敌方战略部署的预判是完全准确的。
(二)从双方战略态势上看
“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1]201因为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中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在西线鏖战,所以造成了东线部分只有42军2个师的兵力负责警戒、防御工作,而“联合国军”起初有3个师的兵力部署在东线,加上后来登陆的美军第10军(辖王牌部队陆战一师以及步兵七师),总兵力超过了10万人,到1950年11月24日,“联合国军”已经将东部战线推进到了下碣隅里(长津湖南端地区)——惠山(位于中朝边境)——清津(位于朝鲜东北部沿海地区)一线,西线推进到了新安州(位于朝鲜西海岸)——德川(位于朝鲜中部),并且在东线的陆战一师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了距离熙川不到100公里的柳潭里(长津湖以西地区),战略态势上已经从东西两线将中朝联军压缩到了朝鲜西北部地区。西线志愿军虽然已经站稳,但是东线志愿军兵力不足(仅42军所辖两个师的兵力,约3万人),根本无法阻挡联合国军从东线的迅速西进,因此,毛泽东决定让第9兵团加速入朝,尽快到达预定位置,趁敌立足未稳,“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1]201在朝鲜东北部打开战线。
(三)从政治方面来看
毛泽东对于歼灭陆战一师是十分重视的,因为“美军陆战第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1]200“如果陆战一师发生崩溃,不光是朝鲜战争,对美国的世界战略都会带来无法预知的打击”。[6]346另外,美陆战一师与中国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烧杀抢掠,在这其中就有陆战一师的前身部队,而后在“沈崇事件”中,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也是陆战一师的士兵皮尔逊等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如志愿军能在东线将其歼灭,在对美军的士气产生重大的打击,并且动摇美军继续将朝鲜战争进行下去的决心的同时,也能从很大程度上鼓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斗志,重新树立起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尊严。可见,毛泽东对于在东线发动长津湖战役有着极其深远的政治考量。
综合起来,无论是从敌方战略意图,还是双方战略态势、战役的政治价值上看,毛泽东力主在东线发动长津湖战役都是有着十分慎重的考虑,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东线长津湖战役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胜利的基础。
三、毛泽东是否直接指挥长津湖战役
从目前公开的文献资料来看,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关于长津湖战役的相关电文较少,在《彭德怀自述》关于第二次战役的内容中也没有涉及东线战场,而毛泽东关于长津湖战役的相关电文较多,其中大部分涉及到第9兵团的作战任务。据此有研究者撰文《毛泽东怎样指挥第9兵团长津湖作战》,认为:“根据公开资料可以推断长津湖作战期间第9兵团由毛泽东直接指挥”,并且认为毛泽东的指挥与实际战斗脱节,干预了前线作战,*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51102130179_all.html.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从战役之前的电文来看
战役之前,尽管早在1950年10月23日,毛泽东就致电陈毅、张震,要求“宋兵团须从速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并准备先开一个军去东北”,[1]149不过这只是毛泽东从整个战略全局的角度出发,未雨绸缪,先让第9兵团做好入朝准备。此后,毛泽东所发出的有关第9兵团事项的电文大都经彭德怀转告,并由彭德怀做最后的决断。10月27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九兵团定十一月一日起车运梅河口地区整训,前线如有战略上急需可以调用,如无此种急需则不轻易调用”,[1]169也就是说第9兵团的调动需要彭德怀根据朝鲜战局的战略形势判断,决定权在彭德怀手中。11月5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回复的电文中特意提到“各电均悉,部署甚好。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九兵团之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1]197此电文中“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已明确第9兵团归志愿军司令部指挥。而后彭德怀发出的电文也应证了这一点。11月6日,彭德怀指示宋时轮、陶勇“东线战场(小白山以东)归宋兵团担任,应采取诱敌深入至旧津里、长津线,首先达到消灭美陆战一师两个团之目的”。[7]34311月8日,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将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发电报给毛泽东:“敌为牵制我主力,有沿清川江北进,配合其东线迂回江界的企图。我为以逸待劳,便于后方运输,拟仍以诱敌深入,各个歼击方针。西线部署为:以三十八军一个师沿清川江东岸节节抗击,引敌至妙香山地区,坚决扼守之;主力荫蔽集结于下杏洞、球场以东,德川以北之山地。四十二军主力掩护任务,待宋时轮兵团到后,靠一二五师集结德川东北、德岘、杏川洞、校馆里地区;待宋兵团打响后,协同三十八军主力由东北向西南出击,但不放松消灭伪军之一切机会。三十九军、四十军、六十六军主力位温井、云山、泰川、龟城地区,休息七天,搜索散兵,补充粮弹,修路。如敌不进,待宋兵团打响后调动敌人时,拟集中三个军出德川及其以南寻机歼敌,把战场推向前些,以利持久作战。现正准备修熙川经杏川洞至宁远的公路”,[1]199此电文表明彭德怀对第9兵团如何部署已有明确的安排。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美军陆战第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四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为预备队,九兵团的二十六军应靠近前线,战役指挥必须是精心组织的,请不断指导宋、陶完成任务”,[1]219这封电文毛泽东直接发给了彭德怀、邓华、朴一禹而没有直接发给第9兵团宋时轮,如果是毛泽东直接指挥第9兵团,那么他必然会直接致电宋时轮,何必又要经彭德怀等人再去“指导”呢?不能因为毛泽东在电文中使用了“指导”这样的措辞就推判彭德怀没有指挥而毛泽东直接指挥第9兵团作战。
(二)从战役期间的电文来看
战役期间,毛泽东多次致电彭德怀、宋时轮等人,对战役给予了一定的指导,而非直接指挥。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宋时轮等:“请不要提出过冬休息的口号,只在两个战役之间作必要的休息整训。此种整训只要情况许可,在一个大战役之后,可以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情况许可则延长,不许可则缩短。部队整训宜在前线适当地点实施,打残破了的部队,可以在较安全的地点,但在鸭绿江以南朝鲜境内各军军部直接掌握和监督为有利。以上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1]200此电报带有商量性质,只是指导性的意见,是否采纳还需宋时轮等自行决断。12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宋时轮等:“美七师主力及伪三师一个团由惠山西犯,企图切断我厚昌、长津间补给线,请宋覃令在厚昌之一个师向东迎阻该敌,务使敌不能西进”,[1]221此处电文毛泽东用了一个“请”字,而非强制性命令,意在提醒宋时轮注意敌军向西推进。12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宋时轮等:“我九兵团除应加紧歼灭被围之敌外,并应准备与必然增援之两个李承晚师和美三师一部作战”,[1]225实际上这封电报并不是指挥宋时轮打援,而是提醒宋时轮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敌军可能有解围部队出现在第9兵团的外围。12月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宋时轮等:“(一)请宋覃考虑,将二十六军迅速南调,执行打援任务。(二)对柳潭里地区之敌,除歼灭其一部外,暂时保留一大部,围而不歼,让其日夜呼援,这样便可吸引援敌一定到来,使我有援可打。如果柳潭里地区之敌被我过早歼灭则援敌一定不来了,他们将集中咸兴一带,阻我南进,对我下一次作战不利,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宋覃就当面情况统筹决定为盼”,[1]231也就是说毛泽东只是提出一些战术性的建议和指导,而有关长津湖战役的具体行动,则需要宋时轮依据战场实际情况自行决断。12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宋时轮等:“伪首伪三两师因火车甚少其主力由步行撤退,何时到咸兴尚难定。敌已下令由下碣隅里以飞机撤走被围之美军五七两团,望宋陶覃迅速控制下碣隅里飞机场不使敌军撤走,并对五七两团之南退部队予以歼灭,只留下其在柳潭里地区之固守部队围而不歼,以利钓鱼”,[1]223此处毛泽东是希望宋时轮能够达成预期的目标。同日,宋时轮回电志愿军司令部并报中央军委:“二十六军现正接替二十军,担任攻击下碣隅里之任务。拟明晚发起战斗。二十军将下碣隅里攻击任务交代后,其五十八、六十师主力即进入黄草岭及以南地带,准备打北援之敌。八十九师主力即进到隐峰里、上下通地带(五老里西北)。五十九师今晚仍参加对柳潭里南逃敌之作战。二十七军大部今晚正与柳潭里逃敌作战中”,[1]238毛泽东12月5日回电:“宋陶覃十二月四日二十二时五分电部署意见很好,望即执行”。[1]237由战役期间的电文来看,毛泽东在战役期间只是根据彭德怀、宋时轮等反馈回来的信息,给予宋时轮一定的指导,而具体军事行动的部署是由宋时轮依据战场形势而制定和修订。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于长津湖战役是间接性的指导,而不是直接指挥,这也就不存在干预前线作战,更不存在毛泽东“瞎指挥”的问题了。
四、毛泽东对长津湖战役结局的评价是否客观
部分学者这样评价长津湖战役的结局:“志愿军九兵团在态势、地形、人数均为优势的情况下,付出了巨大代价仍未能全歼甚至未能给予陆战1师重创,怎么也不能说成是一次胜利。虽然挫败了美军的进攻,但毕竟让捏在手中的陆战1师逃出了重围。因此长津湖之战,比较客观来说,双方应当是打成平手”。*http://news.163.com/10/0616/15/69AG3MKT00011232.html.这样的评价与毛泽东对于长津湖战役结局的评价“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有一定的出入。这些学者单纯从战术角度出发,客观上认为长津湖战役中美双方打成了平手,而毛泽东是站在第9兵团完成的巨大战略任务的角度来评价长津湖战役,这其中包含达成的军事战略任务和政治战略任务两部分。
(一)从军事战略任务的达成来看
1.长津湖战役是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第9兵团在东线长津湖地区的作战配合了西线志愿军在清川江一线的反攻,将整个战线由朝鲜北部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扭转了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东北部战线不利的局势。第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将美第10军击退,从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西线志愿军部队后方补给线的安全,并且“联合国军”在日后再也没有踏入过朝鲜东北部地区,从一定程度上说,长津湖战役将朝鲜东北部的“联合国军”彻底逐出,打开了东北部战线,永久性地消除了“联合国军”对朝鲜临时首都江界的威胁。与此同时,长津湖战役还挫败了麦克阿瑟从东线合围志愿军以及朝鲜人民军的企图,保障了西线志愿军后方的安全,并且配合西线志愿军粉碎了麦克阿瑟的 “圣诞节”攻势,从而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初步胜利的基础。对此,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特别提到:“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把侵略军从鸭绿江和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一举收复了朝鲜北部广大土地,奠定了这场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基础。”*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0/25/c_12700037.htm.the Penguin Group in New York.以此可见长津湖战役在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2.长津湖战役也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够战胜装备优良的美国军队,为下一步作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第9兵团在极寒条件下,全歼美步兵7师第31团级战斗群(“北极熊团”),并缴获该团团旗,进一步积累了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重要经验,这也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成建制歼灭美军团级以上作战单位的战例。而从另一方面说,第9兵团虽然一次性包围陆战一师大部及步兵七师一部,但因敌军火力强大而未能将陆战一师围歼,这一事实让毛泽东从一定程度上逐步认识到美军火力极其强大,“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1]282志愿军一次性包围美军一个整师、甚至一个团都难以歼灭,因此在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分析历次战役的胜负得失,指示彭德怀 “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1]282
(二)从政治战略任务的达成来看
1.沉痛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嚣张的气焰,鼓舞了中朝联军的斗志,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新闻周刊》曾评价这次战役是“美国自珍珠港事件以来遭受到的最大的挫折”,[4]433并且长津湖战役结束后,美陆战一师受挫,被迫撤离,直至从兴南港死里逃生的消息传到杜鲁门耳边后,杜鲁门才说:“这是我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好的圣诞礼物”,[4]436这句话颇有讽刺意味,一方面陆战一师的撤离行动令杜鲁门感到欣慰,而另一方面,“联合国军”在第二次战役东西两线的败退让他感到不安,尤其是东线长津湖战役中陆战一师的败退。因此,长津湖战役在很大程度上打出了中国军人的气势,在震慑敌人的同时,也打出了中国在世界的大国地位,赢得了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尊重,也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彻底明白,“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1]355
2、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考虑停火谈判。西线战役与东线长津湖战役所组成的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联合国军”,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局势,并且 “确定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8]260美国总统杜鲁门早在长津湖战役期间就开始考虑:“停火是可以接受的,但条件必须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南朝鲜或台湾,或使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席位”,[9]109尽管杜鲁门的态度依旧强硬,但是面对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当中东西两线的猛烈攻势,杜鲁门还是不得不考虑停火谈判的问题。而长津湖战役中,陆战一师在志愿军层层包围下逃离长津湖地区,这一举动“鼓舞”了美国军方,尽管军方一再表示能够在朝鲜坚持下去,但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当中的部分外交官则表示“将通过谈判来争取和平”。[9]122不难看出,长津湖战役作为第二次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基本实现了其政治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令美国高层对于朝鲜战争是否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产生了分歧。
毛泽东是站在战略全局的角度,综合了政治、军事双重考量,对长津湖战役做出评价,因此,毛泽东对长津湖战役结局的评价是中肯而且客观的。
五、结语
有学者认为第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使用的是“人海战术”,非但没有“淹没”陆战一师,反而自身伤亡巨大,15万大军已完全瘫痪。[2]279关于第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的伤亡情况,据统计,第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战斗30日,战伤14062人,冻伤30732人,阵亡7304人,减员总数为52098人[10]327(这其中,第27军、26军的伤亡数字是依据20军的伤亡数字推算出来,20军在长津湖战役中负责穿插、迂回,其作战强度远远高于攻坚的27军和作为预备队的26军,因而伤亡数字自然比26军以及27军要大很多,所以,长津湖战役当中实际减员人数应不足5万人,故毛泽东所认为的“减员达四万人之多”[1]241较符合实际),其中战斗伤亡为21366人,并非美军战后所宣称造成志愿军37500人[4]433的伤亡总数,总减员数也并非国内部分学者所认为的“减员超过70000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9兵团非战斗减员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并非永久性减员,因此,第9兵团被陆战一师打残之类的说法基本不成立,只是需要一定时间来恢复战斗力。
以长津湖战役当中的中美双方伤亡数字作为依据来判断战争的胜负是不可取的。评价长津湖战役乃至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胜负必须要立足于当时的政治、战略的背景,剖析战役对全局的推动作用,分析战役主次目的的达成情况,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长津湖战役是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一个关键性的战役,主要目的均达成。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2] 陆宏宇,凤鸣,何楚舞.最寒冷的冬天III:血战长津湖[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4.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
[4] Martin Russ, Break out——The Chosin Reservoir Campaign [M].New York: Penguin Group, 1999.
[5] [美]李奇微.北纬三十八度线[M].王宇欣,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6] [日]儿岛襄.最寒冷的冬天IV:日本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下)[M].周晓音,宫彬彬,张敬,译.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5.
[7] 彭德怀军事文选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8]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1.
[9] [美]约瑟夫·古尔登.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下)[M].于滨,谈锋,蒋伟明,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卫生勤务[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熊先兰
On the Discriminate Related Issues about the Study of Mao Zedong and the Battle of Chosin Reservoir
ZHANG Hai-yan, MEI Shi-chang
(CenterforStudiesofMaoZedongThought,XiangtanUniversity,Xiangtan,Hunan411105,China)
The Battle of Chosin Reservoir is the eastern line in the second battle of the Korean War.The comments on the two belligerent parties of this battle are mixed.And it also arose arguments on the related comments about some researchers on the battle itself as well as Mao Zedong and the battle.Those arguments mainly focused on why Mao Zedong considered the 9th Corps going into the eastern line in the Battle of Chosin Reservoir, why he was urged to launch the attack on the eastern front, whether he directly commanded the Battle of Chosin Reservoir, whether the evaluations on the Battle of Chosin Reservoir are objective or not, so like this.Analysis on those disputed issues present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restore the historical truth and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Battle of Chosin Reservoir.
Mao Zedong; the Battle of Chosin Reservoir; CCF 9th Corps;strategic task
2016-08-25
张海燕(1975—),男,湖南邵阳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梅世昌(1990—),男,湖南常德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毛泽东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评析”(编号:14ADJ001)阶段性成果。
A84
A
1001-5981(2016)06-0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