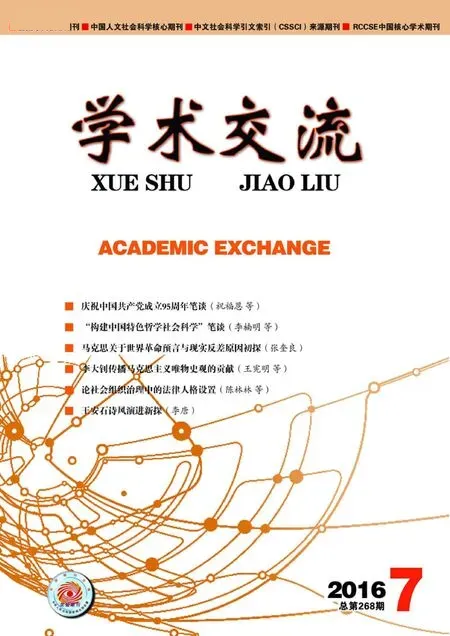王安石诗风演进新探
李 唐
(哈尔滨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哈尔滨 150080)
王安石诗风演进新探
李唐
(哈尔滨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对王安石诗歌创作历程的认识,宋人以“优劣”为论的“两期说”与今人着眼于诗风变化的“两期说”都不够恰切。把王安石在政治激流中的人生轨迹与其诗歌创作历程结合起来,考察其诗歌阶段性的风貌特征,才能够对王安石诗歌创作历程有全面准确的认识。王安石诗歌创作历程应分为四个阶段,即入仕后任地方官时期、入京为官和丁忧时期、入朝执政变法时期、罢相隐居时期。各个阶段呈现出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风貌特征。
[关键词]直切时弊;思理深长;造语工致;沉郁凝重;深婉简淡
对王安石诗歌创作历程的认识,宋人多主“两期说”。《漫叟诗话》谓:“荆公定林后诗,精深华妙,非少作之比。”[1]卷33,222把王诗分为“少作”和“定林后诗”两个阶段。《后山诗话》亦云:“鲁直谓荆公之诗,暮年方妙。”[1]卷33,222也把王安石诗歌分为暮年和暮年前两个时期。今人论王诗创作历程也以隐居前后“两期说”为主流。不过,宋人“两期”说的划分标准是他们所认为的“妙”与不“妙”,实即以“优劣”为论。事实上,王诗在晚年之前亦不乏精妙作品,晚年作品亦非尽属精妙。今人的“两期”说,不再以“优劣”为论,而是着眼于诗风变化。如果从重点说明罢相后诗风的角度,比较整个罢相前的诗歌创作,大体而言,自无不可,但具体考察他从入仕到罢相隐居之前三十余年的诗歌,在其间的不同时期也明显呈现出阶段性不同的风貌特征。因此,无论是宋人“两期”说,还是今人“两期”说,都未免笼统,不够恰切。
作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王安石,其人生经历中各阶段不同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审美情趣等都会作用于该阶段的诗歌创作,随着创作经验不断丰富,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也自然会带有相对不同的阶段性特征。笔者认为,把王安石的人生轨迹与其诗歌创作历程结合起来考察,其诗歌创作历程可分四个阶段,即入仕后任地方官时期、入京为官和丁忧时期、入朝执政变法时期、罢相隐居时期。当然,不同阶段的时限划分只能是大体上倾向性的,它不可能像诗人生平经历的时限划分那样,这是需说明的。
一、任地方官时期的诗“门户已立”,并形成具有倾向性的风貌特征
王安石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进入仕途,此后做地方官十二年,到至和二年(1055)入京为官。这是王安石政治生涯的第一个时期,也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一个时期。此时的王安石不仅是政治舞台上的地方官员,也成为诗坛上初露锋芒的诗人。梁启超所谓“自其少年而门户已立矣”[2]204,主要当指这一时期的诗。在此期间,王安石长期担任地方官职,更加直观、深切地体察到北宋王朝日益激烈的土地兼并和各种弊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及给王朝本身造成的危机。同时他深受范仲淹改革思想影响,对社会现实敏于洞察、深于思考,积极探索改革之路。这种社会生活经历、思想情感取向以及年富气足、性格梗直等精神气质特点,都成为激发并综合作用于他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使他在诗歌中的抒情言志,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直”“朴”“劲”。
(一)“直”——直发时弊,一吐为快
关注政治现实的精神,在王安石诗歌中是一贯的。在这个时期,突出表现为直发时弊,放言为诗。确如蔡上翔所言,他在地方官任上“所见闾阎之疾苦,官吏之追呼,无不具托于诗篇”[3]卷4,75。其表达方式则以正面直抒,一吐为快,凌厉奋发为主要特点。叶梦得《石林诗话》就说:“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为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皆直道其胸中事”[1]卷34,75写于这个时期的《省兵》《收盐》《发廪》《感事》《兼并》《寓言十五首》(婚丧孰不供)(父母子所养)等诗,都成为此时期的代表作品。这类作品,都紧紧针对政治现实中的要害问题,直发其弊,直辨是非,不稍假借,不作婉转,凌厉奋发,一泻而下。如《收盐》一诗把孟子“一民之生重天下”的古训,与现实中“君子”们盘剥盐民秋毫到骨对比而言,直接质问统治者,以喷发式的力度,揭发出“盐政”的残民本质,诗人痛切、愤慨的情感也一发无遗。
(二)“朴”——表达自然,用笔质朴
王安石刚入仕途时,就特别称赞“明而不华”(《张刑部诗序》)的诗歌作品,这也是他自己诗歌创作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追求在这一时期尤显突出。发露型的一吐为快的抒情方式,其艺术效果当然就是“明”。“不华”则是指这种“明”乃不假雕饰,自然质朴之“明”。此阶段诗中的这一特征,一般是由思想情感的表达自然而切实,语言的运用质朴而富于表现力,意象的营造平常而具有特征性等艺术层面合力构成。《收盐》等政治诗、《杜甫画像》等抒怀诗,即均具此风貌特征。这个时期,王安石以写古体诗为主,代表他这个时期诗歌成就和风貌特征的也是古体诗。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云:“古体劲而质,近体婉而妍,诗之常也。”[4]古体诗不受格律束缚,便于张扬个性的特点和“劲而质”的诗体气格,正适于这个时期的王安石“以意气自许”,直切时弊,“勿复涵蓄”,一吐为快,放言为诗的诗歌风格。即使在近体诗中,往往也用“劲而质”来改造“婉而妍”,以自然质朴出之。如《慎县修路者》一诗:
畚筑今三岁,康庄始一修。何言野人意,能助令君忧。戮力非无补,论心岂有求?十年空志食,因汝起予羞。
诗中抒写了对筑路民工辛苦劳动的体察之情和对他们筑路贡献的赞颂之意,同时也通过自己作为地方官的感受,讽刺了那些“耻问耕稼”,漠视百姓疾苦的官僚。按格律,这本是一首五言律诗。但此诗并无一般律诗讲究辞采优美、情景圆融、意脉婉转、各联之间起承转合的章法等特点,对仗也不觉其为对仗,从抒情方式到语言风格都很像一首“劲而质”的古体诗。
(三)“劲”——气度劲拔,格调雄健
“荆公少时以意气自许”,梁启超更认为在他的个性里有一种“逋峭雄直之气”[2]208。上述他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自然质朴特征也与一般的自然质朴诗风不同。一般的自然质朴诗风,往往与平淡从容相联系,而他的自然质朴却含有一种劲拔雄健之气。清人方东树亦云:“荆公健拔奇气胜六一,而深韵不及,两人分得韩一体也。荆公才较健爽,而情韵幽深不逮欧公。”语中把欧诗、王诗学韩做了对比,其中所指出的“荆公健拔奇气”“才较健爽”,在王诗的这个时期确实是最为明显的。
前面提到王诗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那些政治诗,就都在直发时弊,一吐为快,表达自然,用笔质朴的同时,具有感慨痛切,叙议锋利,用语决断,气势凌厉的特色,往往形成一种劲拔雄健的气势。这个时期,有些近体诗,也都明显具有劲拔雄健的风貌特征。如《舒州七月十一日雨》一诗:
行看野气来方勇,卧听秋声落竟悭。淅沥未生罗豆水,苍茫空失皖公山。火耕又见无遗种,肉食何妨有厚颜。巫祝万端曾不救,只疑天赐雨工闲。
蔡上翔解此诗云:“纪雨,伤旱也;火耕无遗种,悯农也;肉食有厚颜,刺时也。”[6]卷4,68
诗中伤旱,用云“来方勇”与雨“落竟悭”的对比,再用虽闻“淅沥”而水少,虽见“苍茫”而雨稀的进层,写出从急盼雨来到雨却极少,满怀希望到极度失望的巨大情感落差,造成强烈的情感震憾力;悯农,用“又见”二字表明农民年年刀耕火种却年年“无遗种”,今“又”遭“雨工闲”,生活悲惨,激切而沉痛的忧民之心直出言表;刺时,则径指“肉食”者,以“肉食”与“火耕”,“有厚颜”与“无遗种”相对,不仅把“肉食”者不劳而获,无恥享乐的生活与农民辛苦悲惨的生活做了鲜明对比,更形成了对“肉食”者麻木不仁,漠视民命的尖锐指责: “何妨”二字又使尖锐的指责带上了辛辣的讽刺。全诗深刻犀利,劲健有力。
二、入京为官和丁忧居家时期的诗则另有倾向性特征,可自成阶段
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至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为王安石诗歌创作的第二个时期。至和二年王安石始入京为官,至嘉祐八年(1063)因母丧离京丁忧。这个时期其政治改革已进入了具体的设计和准备阶段。写成长达万言的政治改革纲领,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是其变法的基本蓝图。考察其诗歌风貌倾向,突出的特征则是:
(一)思理深长
思理深长是王安石这一时期诗歌风貌新的重要特征之一。以议论入诗几乎是王诗的一贯特点。前一时期许多直切时弊、一吐为快的政治诗就以议论取胜。不过,诗中所议还大都是就事论事。《省兵》即言国家未经政治、经济改革,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裁减军队,必然有损国防之理。《发廪》《兼并》都直言土地兼并害民害国之理等等。但到了这个时期,以议论入诗就往往超越了就事论事,此事此理的层次,赋予诗中所言之理以更高的概括形式和哲理品格,提升为深长的思理意蕴,表现出对政治见解、人生体验、历史感悟的更深刻、更成熟的思索。他的名作《明妃曲二首》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篇章。这两首诗问世之后,立即轰动诗坛。一时间,诗界名流欧阳修、梅尧臣、刘敞、司马光等均有赓和,后来黄庭坚甚至称:“荆公作此篇,可与李翰林、王右丞并驱争先矣。”[6]卷6,66而二诗的最精采处或者说“诗眼”,都是各自特定语境中的议论。前一首使感慨和议论从昭君出塞事生发出来,又超越昭君出塞事,指向一种更普遍、更深刻的人生体验——“人生失意无南北”,既新颖独到,又意蕴深长,耐人寻味。后一首,主要通过昭君出塞弹琴寄情的描叙,写她离汉入胡的无助与哀怨,但同样借安慰之辞,引出“汉恩自浅胡自深”的感慨,进而生发出“人生乐在相知心”的思理,也同样超越了昭君无助与哀怨的具体事理,使议论更具哲理品格。但因为它是从昭君无助与哀怨的情景中生发出来,所以又带上了厚重的情韵。
这个时期,他写了许多咏史、怀古诗,都以勇于翻案,见解新颖而著称,表现出高超的史识和一个政治家敏锐犀利的眼光。此类诗中,往往就史实找出异于通常认知的切入点,展开议论,形成超乎一般认知的更深刻、更新颖、更富于规律性的历史感悟及其现实观照,集中体现出他这一时期诗歌思理深长的特点。如《范增》(其一)、《开元行》、《赐也》、《乌江亭》、《读唐书》、《读史》、《读后汉书》、《诸葛武侯》(恸哭杨颙为一言)等大约写于这个时期的咏史、怀古诗,大都具有这种思理深长的特点。所以宋人说他的《范增》等咏史诗“有如此议论,他人所不及”[7]。 此时期其他题材的诗歌,往往也以深长的思理构成作品风貌的重要特征。方东树评《送程公辟之豫章》一诗曾说王安石“所以为作家,跳出寻常庸人应酬套,此非深思有学人,不能作,不同俗手,分别在此”[5]288。“深思”的特点,正是在这个时期突出显现出来的。
(二)韵味沉厚
王安石入京为官后,曾写有《虎图》一诗。诗中有句云:“神闲意定始一扫,功与造化论锱铢。”称赞《虎图》画家作画时的精神状态。他认为只有“神闲意定”才能有作品的“造化”之功。这也应是他自己到这个时期思想性格逐渐成熟,人生感受更加丰富所带来的新的审美体验与追求。在诗歌创作中,许多作品就是以“神闲意定”的沉稳和意味深长,改变了前一时期以直质发露、一吐为快为主的风貌形态,形成诗中沉厚的韵味。叶梦得《石林诗话》载,王安石“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1]卷34,229。可见王安石在这个时期曾精读唐诗,而唐诗最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正是追求“文外之旨”“味外之味”,注重韵味,即叶氏所说的“深婉不迫之趣”。从“尽”字可以看出,叶氏是强调王在“晚年”这种诗风已达到极致。实际上,在入京为官和丁忧居家时期,许多作品就以注重韵味而区别于前一时期的诗歌,成为新的诗歌风貌倾向。比如前边谈到的这一时期的那些咏史诗,从表面上看,把道理说得斩钉截铁,但并没有意随言尽,而是蕴涵着可以让人深长思之的世事或人生哲理,留下可以体悟的广阔空间,这已是一层意味;而诗意的哲理化,又自然涵盖现实事物,具有观照现实的“终极”意义,在特定的现实语境中,诗人特别写出来,就会带着不言而喻的指向性,由诗歌文本延伸出对现实事物的深刻思索和回味,这又构成一层意味。如《诸葛武侯》一诗:
恸哭杨颙为一言,余风今日更谁传?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
本诗咏诸葛亮在杨颙死后痛哭三日一事。杨为诸葛亮主簿,曾建议诸葛亮不可事无巨细必自躬亲,避免“为此碎务,形疲神困”。一般情况下此事更能说明诸葛亮忠于蜀汉,鞠躬尽瘁,“志决身歼军务劳”(杜甫《咏怀古迹五首》),而王安石此诗却从诸葛亮为曾有“一言”的杨颙之死而痛哭的角度,把感慨引向对诸葛亮“虚心”“得贤”的议论,形成一种历史经验的感悟。其中自然含蕴着为政治国必须重贤从谏的政治哲理,特别是通过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感慨,以“不是”“岂得”的反诘语气表达,尤显意味深长。更有言外之意的是诗中同样以有力的反诘语气,感叹诸葛亮这样的“余风”,“今日”已没有谁能够承传了。它自然会使人们把深刻的政治哲理与政治现实联系起来,体味王安石自己改革政治的“一言”不被宋仁宗采纳的心情。
(三)造语工致
造语工致也逐渐成为王诗此时期风貌特征中一个新倾向。在这一时期,随着思想性格走向成熟,写诗讲究“神闲气定”,向唐诗学习,所以更加注意诗歌艺术,古体、近体双峰并峙。近体诗的诗体格律和气格,关于对仗、押韵、用典、下字等要求,也更便于他施展造语工致的诗才。据龚颐正《芥隐笔记》载,嘉祐元年,“荆公在欧公坐,分韵送裴如晦知吴江,以‘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分韵,时客与公八人”,其中王安石得“而”字作二诗“最为工”[6]卷10,153。以“而”字这样的险韵,在欧阳修等诗人当中,把诗写得“最为工”,亦可见当时王安石诗歌创作造语工致的艺术功力。七言律诗《思王逢原三首》即较有代表性:
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入酒卮。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此诗为悼念好友王令所写。第一联写故友虽已去世一年,而自己仍然难以忘情。他不仅通过想象中墓地凄凉景象的描写,抒发对王令已长眠地下的悲哀,而且下一“想”字,蕴涵自己无法忘怀故友以及不但与故友泉壤永隔,连坟墓也不能一见的更为悲哀的心情。“想”字极为普通,但用于此语境中,却赋予了丰富的内涵,极具表现力。以自然出工巧,是王安石造语工致的一个重要特点。第二联可看出用典的造语工致,此联是感叹王令生前孤高不为世人所理解,只有自己才深知王令。“妙质”用《庄子·徐无鬼》运斤成风故事。这里是说世间没有王令可以相投契、为知己的对象,实际是抒发对王令孤高特立,不偶流俗人格的崇敬和缅怀。“微言”则用《汉书·艺文志》“仲尼没而微言绝”的文意,是说王令那些深刻的思想和言论,只有我才理解,实际是表达自己与王令相知相契的深厚友情。这两个典故不仅用得熨贴精确,启人联想,意蕴丰富,而且词意畅达,属对工整,把容易板滞的议论化为自然生动的抒情。第三联的对仗,造语更为工致。此联是回忆当年与王令一起读书饮酒时的豪情逸兴。句中把读书与饮酒的描写形成工整的对仗。经过对仗句式,使“庐山南堕”与“湓水东来”交织起来,已经在具有动感的阔大客观景象中渗透出主观的雄阔气势,又用“当”“入”两个动词,分别将自然景象与代指人事活动的“书案”“酒卮”各自绾成一体,均以大入小,以小笼大,不仅意象生新,而且上下相对,豪迈情怀更见充分。对往日二人豪情逸兴的深情回忆正是今日对故友的痛切思念,在往日豪情逸兴的对照下,更显今日友人已故的悲怆凄凉,于是自然引出第四联无尽的今昔之感。诗中造语工致的艺术效果十分明显。
三、入朝执政变法时期,沉郁凝重、工琢老练风貌渐成突出倾向
这个时期是从治平四年(1067)至熙宁九年(1076),在王诗艺术风貌演进的链条中亦有着较为明显的自成阶段的特征。
(一) 沉郁凝重
这个时期王安石已进入权力集团的核心,其执政后,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进行政治改革。他在这一时期倾注全副精力于变法革新的政治斗争中,诗歌创作与前一时期及后一时期相比不算活跃,而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则多与变法斗争密切关联。在激烈尖锐的政治斗争中抒情言志,一方面不时表现出前两个时期质朴劲拔,思理深刻等特点,并且更为老练;另一方面,巨大的精神压力,沉重的心情,又使他这一时期的诗歌较普遍地带上沉郁凝重的风貌特征。如《孟子》一诗便很有代表性:
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王安石刚执政变法,反变法的保守势力就攻击他“但知经术,不晓世务”。诗中就是抒发在这种“举世嫌迂阔”的严峻境遇中,以孟子的执着进取精神,坚持变法事业的心情。然而诗中感叹自己心仪的孟子早已离开人世,只能凭他的“遗编”想象他崇高的精神风范,已经渗透出一种深长的千秋怅望之感;继而感叹自己同孟子一样处于“举世嫌迂阔”的境遇,孟子正可以作为自己在孤独之中持守政治节操的精神支柱,就更体现出诗人虽坚持斗争,无奈众口烁金,虽固守气节,但处境“寂寥”的悲剧性的“孤高”情结。从情感到用语,更加低回而沉郁。
(二)工琢老练
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歌,又能在前一时期思理深长、韵味沉厚、造语工致的基础上,表现出更为透辟警策、工琢老练的风貌特征。据《石林诗话》载:
熙宁初,荆公以翰林学士被召,前此屡召不起,至是始受命,(王)介以诗寄云:“草庐三顾动春蛰,蕙帐一空生晓寒。”盖有所讽。荆公得之大笑。它日作诗,有“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自不知”之句。盖为介发也。”[1]卷34,230
这则记载,就是称道这个时期王安石作诗透辟警策、工琢老练。王介用诸葛亮起南阳和《北山移文》的典故讽喻王安石从“屡召不起”到应召为翰林学士,而王安石同样以王介所用的两个典故作答,而且以“丈夫”指自己,以“猿鹤”喻王介,颇有反唇相讥的味道,既切中要害,一语破的,又深中情理,且要言不繁,属对工稳,工琢透辟的效果自生其中。如著名的《商鞅》一诗就诗意看,应推测为写于诗人的执政变法时期。诗中针对当时保守势力攻击他“尚法令则称商鞅,言才利则背孟轲”的舆论,明确地赞扬了商鞅变法,但又并未泛泛叙议商鞅变法的功业,而是意外地以为政必须信诚这一历史的“定律”为前提,指出商鞅正是以“一言为重”,取信于民,而使变法得以推行。既强调了商鞅不仅制定利民利国的法令,而且坚决推行,实现予民之承诺,又暗中反讽了那些“今人”只能空谈孔孟仁义、“先王之法”而于民于国无补,不能望商鞅项背,更表现出王安石自己推行新法的坚决态度和果决厉行的精神,语短意长,言浅思深,格外工琢老练。
四、罢相离朝隐居金陵时期的诗,还具“简淡”“深婉”特点
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到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是王安石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时期,论者通常称为“晚期”。这个时期,王安石已无政事缠身。栖身山水,寄情诗酒,读书会友,酬唱往来成了他主要的生活方式。而无论是在山光鸟性,参禅悟道中的舒散体验,还是忧患国事,关注政局但又无所作为的苦闷心情,正都可以在诗歌中得到宣泄。他有原来诗歌艺术经验的积累,又有时间、条件做更充分的涵养体味和艺术加工,所以这个时期的诗歌既多且精,出现了一个新的创作高潮。在他的全部1600余首诗中,写于这个时期的作品约占三分之一。其中最多的又是更便于表现艺术加工的近体诗。仅绝句即有300首左右。这些作品,历来被称为“精绝”“精深”“精严”“精妙”。后人所谓“王荆公体”,即主要指这时期绝句的风格,它成为王安石诗歌艺术的代表。关于王安石这一时期诗风的变化,有论者往往把它放在与整个罢相前诗风相反的方位上进行比较,将二者截然分开。其实,这一时期新的风貌特征,也主要由以前各时期风貌特征在诗人新的主、客观创作条件下,发展演进而成,也是其整体风貌特征的一种新的体现形态,把它笼统地表述为对以前诗风的割断、抛弃甚至对立,似乎不妥。
(一) 简淡
简淡是这一时期王诗给人印象最深的风貌特征。这当然与诗人追求在隐居情趣中超脱现实的矛盾、苦闷心境而写下的许多富于恬淡闲适的写景或咏物小诗有关。集中体现于这些小诗的简淡风貌,其基础要素则是自然。离开自然的语言、自然的意象、自然的情感,则简淡亦无从谈起,而自然又几乎贯穿在王诗各个时期的风貌特征之中。第一个时期的质朴劲健,本来就是以自然为重要因素,第二个时期成为倾向性特征的思理、韵味,第三个时期的沉郁凝重也都往往以自然的语言、自然的意象出之,乃至工巧的用典、琢炼的下字往往也能化精工为自然,成为“眼前景物,口头话”。这个时期,诗人把时常要抒发的隐居情趣、恬淡心境,熔铸在最适于表达它的自然笔调之中,使“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1]卷36,241,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倾向性的简易冲淡的风貌特征。比如以下两首小诗:
桃李白城坞,饷田三月时。柴荆常自闲,花发少人知。(《杂咏四首》其四)
爱此江边好,留连至日斜。眠分黄犊草,坐占白鸥沙。(《题舫子》)
司空图《诗品》以“素处以默,妙机其微”表述“冲淡”风格,清人黄子云《野鸿诗稿》亦谓:“理明句顺,气敛神藏,是谓平淡。”[8]850这两首小诗即均无过深地使气用意、过重地涂饰展藻,而是以疏朗、浅淡的景物,平常、浅近的语言,舒缓、轻灵的节奏,形成寂静、空灵、明秀的大自然与超脱、淡泊的心灵感悟融而为一的意境。值得注意的是,王诗这个时期的简淡风貌,绝非简单粗浅,正如清人薛雪《一瓢诗话》所言:“古人作诗到平淡处,令人吟绎不尽,是陶熔气质,消尽渣滓,纯是清真蕴藉,造峰极顶事也。”[8]687以上两首诗就可看出,其内蕴都没有止于与简淡风貌相应的淡泊、超脱的情趣层面,而是“清真蕴藉”、曲径通幽,沿着淡泊、超脱的情趣,可探测到深层不得已而隐居的孤独、寂寞和冷落的心灵阴霾。
(二)深婉
深婉的抒情方式构成了这一时期王诗的另一主要风貌特征,亦即我们前面提到的《石林诗话》所说的“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实际上,深婉风貌亦非本期突然而生。早在王诗的第二个时期,许多作品与议论的含蓄化、哲理的意蕴化相适应,就已经很注意韵味,以至于成为该时期的风貌特征之一。在“言外之意”这一点上,韵味沉厚与深婉不迫是相通的,只不过那一时期作品的韵味,一般是与作品表征信息方向一致,又向表征信息之外的意义延伸或深入,造成深广的体悟空间,而这一时期的深婉,则往往是与作品表征信息方向相异甚至相背,但又在表征信息笼罩下,意义曲折隐约的内藏和深蕴,造成丰富复杂的诗意内涵。可看如下两首诗: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谢公墩二首》其一)
春残叶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盏疏。斜倚屏风搔首坐,满簪华发一床书。(《晚春》)
前者表征信息是与谢安“争墩”,在诙谐当中表达自己与谢安一样的隐居情趣。但深长的感慨也曲折隐约地深蕴其中:谢安的处与出,名声与事业,早已风流云散,现在“公去我来墩属我”。自己的处与出、名声与事业也会与谢安一样风流云散,将来这墩又属于谁?当年谢安隐居而“东山再起”,自己又会如何呢?这些感慨与表征层面的隐居情趣一诙谐,一严肃,一轻松,一沉郁恰好相反,显得格外深婉。后者的表征信息是抒发闲散淡泊的心境,但韶光易逝,在无所事事中老去的悲凉与无奈却曲折隐约地在深层展开,也以表征信息与内藏意蕴的方向相异而成深婉的艺术效果。
罢相退隐后的诗,是王诗诗风演进的最后一个时期。其间,王诗既多且精,诗风也进入了简淡而深婉,自然而精巧的新境界,形成一个新的创作高潮,被称为“荆公体”。对此,前人及时贤之述备矣,兹不赘言,于此只想强调的是,王诗此时期的诗风,乃前几个时期诗风的发展变化,仍然含蕴着前几个时期诗风的元素,如简淡之于自然,深婉之于思理,精巧之于工致等,不能视为不同诗风的断裂,更不能解读为不同诗风的对立。
[参考文献]
[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二七,第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郭绍虞.清诗话读编(第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6]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321.
[8]王夫之.清诗话(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850.
〔责任编辑:曹金钟〕
[收稿日期]2016-05-10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王安石诗学思想与宋诗美学”(12542117)
[作者简介]李唐(196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7-0176-06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