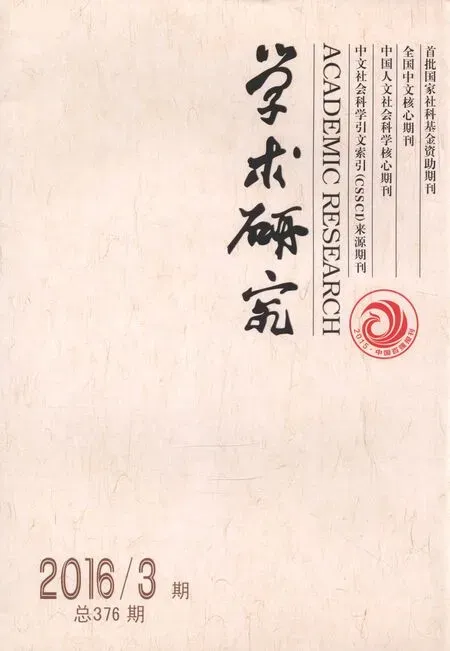少儿教育内容的正当性基础初探*
翟振明 颜志豪
少儿教育内容的正当性基础初探*
翟振明颜志豪
[摘要]经典有两类,一类是诗歌文学类,不由直接的义理判断为内容;还有一类,基本由义理判断为内容,试图告诉我们是非对错。针对第一类,让少儿背诵一些诗文,无可非议;但对于第二类,成人根据自己的偏好选编章节让无理解能力的少儿去背诵,这非但不能培养他们的德性,反而可能使他们养成盲从的习惯,从而不能长成独立的道德主体人格,这相当于对下一代的摧残。
[关键词]少儿读经道德教育修身养性
*本文系中山大学社科资助项目“2012年度新兴交叉学科项目”(12wkjc11)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子
少儿教育问题,像一般的教育问题一样,既涉及教育的方法,也涉及教育的内容,还涉及其他因素。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期间,知识界对教育问题的讨论相对集中在内容的取舍问题上。相比之下,如今的讨论,在一般读者容易接触到的文字媒介上,关于教育方法方面的比较常见,而关于教育内容取舍方面的,却相对较少。
在这种态势下,对少儿教育的功能与目标有不同理解的人,就极力在内容上直接进入操作性的竞争。目前,以标榜“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为主的、以“国学”中的儒学为压倒性内容的“诵经”派,似乎得到了不小的社会响应。不过,他们由之推动少儿读经的价值原则并没有经过认真负责的讨论,他们面对质疑时的辩护,也没有展现其有说服力的理由。但是,这种事关我们下一代心智健康成长的极其关键的问题,在缺乏坚实的理念基础的情况下直接在社会运作的层面诉诸非理性的话语权和行动力的角逐,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必须在这种角逐进一步白热化之前,明确提出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少儿教育内容的正当性,应该源于何处?
二、被作为少儿读经根据的道德堕落论
某些儒家学者宣称,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不断受到侵蚀,最近几十年来更是遭遇极大破坏。他们觉得,国人认为中国传统理论已无法拯救中华,而中国人在丢失传统道德之后,仍然没有找到可替代的理论资源。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教育思潮之东渐,中国的古代传统教育——读经教育——也被抛弃,而作为所谓当时“最先进”并以“养成君子”作为目标的教育模式也因此无法阻止中国社会的道德堕落。[1]他们由此认为,现代中国社会已被道德虚无主义全面扫荡,而驱散这股歪风邪气的有力手段则是复兴古典教育,实现礼乐“理想”社会,恢复“文明”之邦。
然而,事实上,每个发生社会变化的时代,都有很多年长一些的人对年轻一代的行为给予一般性的负面评价,都在感叹“世风日下”,在他们眼里,年轻人好像都在堕落。这种感叹恰恰是站在道德立场上对其所认为的现象进行评判,谴责年轻人不屑于遵守公序良俗。但是,假如他们的看法都是对的,那么人类就在一代一代堕落,累积起来,人类社会早就因此变成类似于人间炼狱的地方了。按照这种逻辑,当下的社会就必然是有史以来最差的社会,而这个炼狱在未来只会更坏,社会进步也因此无从谈起。但是,果真如此吗?这种“世风日下”的说法,里边隐藏着非常重大的理论内涵,与我们对历史与道德的一般看法很不相符。并且,这些倡导读经之学者并非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正是通过媒介、家庭、学校等不断施加影响,试图介入年轻人的道德教育。他们试图改变自古以来人们道德一代代堕落的趋势,或者,他们认为以往历代人们“世风日下”的评判都是毫无根据的情绪发泄,而他们这一代人却真的碰上了道德堕落的大劫难,需要他们出来力挽狂澜?这种判断,听起来似乎很有家国情怀和历史正义感,但是,历史的劫难很多时候恰好就是在错置的正义感中酿成的。有鉴于此,在对这种或明或暗的判断的正确性进行分析探讨之前,我们与其一下子就盲目跟随或热情拥抱,为何不暂且以保守的态度对待之,先对其进行系统的质疑和反思,看看其是否经得起理性的推敲?
首先,这些以道德教育者面目出现的长者,常常将对貌似流行的或历史上曾被人们坚持过的道德观念的描述,混同于道德规范的有效性诉求,从而误把自己跟从或认可的习俗当做普遍有效的道德规范,站在自以为正确的道德立场上对后代肆意谴责。其实,以描述的方式使用“道德”一词,指的是某些人或群体实际上持有的道德观念,亦即他们偶得的行为上的“规矩”,而不管这些规矩是否合理。一个人不按这些规矩行事,并不一定就是做了错事或坏事。[2]如果有人将不合风俗习惯的现象加以拒斥,理由仅仅是违背“公序良俗”,但又对“良俗”与“恶俗”之区分不提供有效的衡量标准,那么,这种拒斥就是不讲理的专横。换言之,在有争议的情况下,风俗是不能当做道德评判的根据的,相反,对过往的风俗习惯的理性取舍,正是任何一个时代道德进步的前提。正因为如此,伦理学家才经常需要对所处时代的风俗习惯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试图区分“良俗”与“恶俗”,而在为对公序良俗进行辩护之前,这些所谓的道德规范实质上都是描述性道德。
历史上,很多被当时主流社会看做“世风日下”的现象,恰好就是道德上的进步。我们知道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一开始就被谴责为最大的“伤风败俗”。但理性告诉我们,如果“社会进步”的说法不是全无意义的话,妇女解放就会是这种进步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类成员的一半与另一半之间的尊严关系问题,是妇女是否在道义论和功利论意义上被伤害的问题。用不伤害原则衡量一下,我们就会知道,“伤风败俗”所指的现象,一般地,就其被认为“伤风败俗”的方面讲,与对人的伤害没有任何逻辑的或因果的必然联系。然而,我们不能以排斥新事物的人心理上的不快而认定其为“受害者”,因为在这里,不合理的道德观念本身是导致这种“不快”的所谓“伤害”的原因。这类似于有人因为被蛇咬过从而一见到井绳就害怕,在心理上受到伤害,我们只能怪他自己心理有毛病,而不能怪碰巧把井绳暴露在他面前的无心人。考虑到“伤风败俗”的指责还会给被指责的人带来伤害,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无根据的道德观念本身反而有可能是不道德的,而被这种观念评判为“不道德”的行为或现象倒不见得是不道德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里并不需要预设社会进步论,因为这些反对者们自己的“堕落”概念,已经预设了进步概念的正当性。
根据蒋庆的说法,“经”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的汇集,适应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它本身就是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经”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中来体现永恒普遍的真理的。[3]在他看来,不符合他所认定的经典的生活方式,就是道德上的退步。亦即,所谓“读经”就是让小孩认识已经确立的真理,其中主要为道德真理。这些真理在各个不同的文化形态表现各有不同,而在中国就是流传下来的经典书籍。诚然,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无疑不能仅仅包括科学真理,而弃道德教育不顾。但是,我们如何甄别道德真理与道德谬误呢?
我们认为,道德判断和价值判断中当然有类似于真理的东西,它们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基本判断。这些具有普遍性的判断可以区分两种:道德判断和前道德的价值判断。既然存在道德真理,只要我们经过理性的考察确定了,当然可以教给儿童。但是,根据蒋庆的说法,我们对他所认定的经典中的道德判断是无法判断其真假对错的。他认为,写作这些经典的圣人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平凡人的理性与圣人的理性是有天壤之别的。于是,如果我们能理解则理解,不理解则背诵即可,对少儿的读经教育也因此要遵守这一法则。如此一来,中国人似乎确实是因为背弃圣人智慧而变得道德沦丧,因此,当下我们应该重新复兴儒家文化,恢复往昔的所谓道德“黄金时代”。
假如我们取信了蒋庆的说法,认定平常人没有能力审查经典,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确定哪些是经典?而中国古代被称作“圣人”的人也不少,究竟要听从哪家“圣人”,孔子还是老子抑或其他?且不说各家之间相互矛盾,即使儒家内部也存在意见不一致,难道现代中国人应该不加分析予以接受吗?既然他说过“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4]但他自己又在这里审查起圣人及其经典的“适”与“不适”来,他岂不是直接宣布,自己是当代圣人且高于以往所有的圣人?各种迹象都表明,这种说法,谬误多于洞见。对于这种说法,我们也不应感到怪异,因为自古以来谬误的传播,经常都以“真理”的面目出现,我们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甄别。
事实上,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大凡都包含某种合理因素,我们可以认为,这些东西方“圣人”之所以闻名于世,很可能恰恰在于他们的著述包含真理因素。只是,西方人也读经典,他们的阅读方式却是必须理解经典中的主要判断的根据,并在此基础上领会其意义。而他们都假设,这些古代思想家也都会犯错误,从而是可以被超越、正在被超越或将要被超越的。西方的“圣人”和经典不比中国的少,但有谁会认为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知识不可超越,并把他们的著作拿来叫儿童去背诵以进行“道德教育”呢?他们对待经典的态度,本来是所有理性的经典继承者的必要前提,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
因此,我们对待这一部分涉及义理的经典时,应该慎之又慎,这些涉及是非对错的义理言说,不能让孩童盲目背诵。退一步讲,即使背诵的经典都是绝对真理,毫无理解力的儿童就能通过背诵而享受这些真理的价值吗?而不管是真理还是谬误,要让我们天真无邪的儿童像鹦鹉学舌那样去背诵,岂不就是对这些儿童的潜在人格尊严的否定吗?单单背诵这些所谓的“道德”经典就可能导致儿童成年后的盲从心态,从而使他们道德人格形成的根基遭到不可逆转的毁坏,而没有独立的人格,道德责任便无处落实。
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为何我们可以让小孩背诵数学真理(如乘法表)而没有侵犯到儿童的尊严,背诵经典中的道德真理就损害了儿童的尊严了呢?在这里,我们先不必论述道德命题正当性与数学命题的真确性之差别的问题,而仅仅考虑那些需要我们背诵的数学真理,我们会发现需要背诵的也仅仅是那些基础性的公理,而这些公理性的真理,即使是成年人也都得靠背诵,对于不同人来说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其他衍生定理以及推论也同样需要靠对论证的理解才能被掌握。而道德真理也类似,往往也需要得到理性的辩护才有理由接受。从这一点上看,两者都是需要经过论证推理才值得我们接受,我们才因此有理由相信那是正确的。而那些基础性的“道德公理”是否无需理性基础呢?其实,任何稍微对道德学有些许涉猎的人都知道,像康德这样的思想者,在其相关著作中恰恰就是为道义论基本道德原则做出辩护,以那些论证为基础宣示他们各自理论的可接受性的。而没有经过理性审视的所谓“道德”训诫,很有可能正是谬误。将没有经过理性审视的所谓“道德”灌输给尚未成年的下一代,无异于对下一代的奴役。
三、文化复兴与个人权利
我们暂且悬置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之争论,把儒家当正统来看。不少人认为,儒家经典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遭遇了一系列打击,先是科举废除,继而蔡元培废止小学读经,而后是“文革”破四旧,儒学也因此式微。他们认为,亡儒家文化意味着中国人实际上就沦为“禽兽夷狄”。这种想法,看似合理,实则荒谬。这是因为,按照这种思路,儒家文化圈外的人都属于“蛮夷”。而这种夜郎自大式的论调,毫无理性基础,反映的只是一帮人的文化认同焦虑。
持有亡文化论调的儒家学者也可能会将儒学作为儒教来阐释,[5]这种儒家宗教论,常常与当下中国流行的观点相合:人们常常感叹,没有信仰的人必然道德堕落。某些国人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牺牲他人性命以及健康,而不少人由此感慨,中国人因为没有宗教信仰也就没有道德底线。于是,儒教宗教论者宣称,作为中国人,只有“复兴”儒家文化,才能重建中国人的道德。其实,假如道德堕落的说法成立,必定是某些普适的道德原则不被人们遵从,而这些普适的道德原则,并不是因为特定的文化归属而成为普适,而是因为其符合普遍理性的要求。因此,道德真理的普遍有效性决定了它并不属于何种传统,更不能说是“儒家真理”。某些时候信教可以防止某些道德败坏,但有时候信教却是败坏道德的直接原因,而稍微了解基督教历史的人都知道,以上帝之名而行残暴之事比比皆是。因此,我们也不能说宗教信仰是保卫道德的必要条件。
于是,我们可以说,信仰问题并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个人生活方式或群体认同问题,其中涉及的信念不以理性为基础,因而不具有普适性。在某些儒家学者看来,传统文化具有某种特殊价值以及意义,这种价值以及意义要求我们尊重并善待自身的传统文化。而现代性问题存在于东西方社会之中,欧洲的价值迷失以神性丧失的方式呈现,而中国人则不再相信儒家传统文化所提供的理想。在这种背景下,儒家文化鼓吹者有可能采取比亡文化论稍弱的方式为之辩护,他们以为虽然亡儒家文化未必沦为夷狄禽兽,但儒家传统对中国人的价值与意义极其深远。少儿读经运动,意在复活中华儒家传统的意义与价值,并使得它们成为现代生活的思想资源,为现代国人提供身心安顿之精神家园。
这里存在一种可疑的辩护,大意是:儒家传统作为中华之根本,丢弃儒家亦即丧失身份,国人如同无根之游魂。而少儿读经只不过意图恢复传统教育,维护这一民族传统,恢复国族之根本,以求保国存种。然而,倘若我们对世界历史有所涉猎便知,传统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新教运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当时被当成背弃传统,而在现代却成了基督教传统的一部分。而孔子所推崇之周礼,因袭于商礼,商又沿袭夏礼,这一过程因时代变迁而不断有所损益,而这些损益之所以有必要,往往在于旧礼法之老旧而不合理,从而需要革旧立新。因此,我们对待传统就不能单纯机械地全盘接受,更不能将之推及少儿强行背诵;相反,恰当的做法是需要审慎对待传统经典,批判地去接受它。况且,中国文化中诸子百家观点各异,虽然时有统治者独尊儒术,但将此一家之言当做中华文化之传统似乎牵强。即使儒家作为中华民族之主流形态,儒家学者要将儒家文化当成国人之身份辨识也不合理。鲁迅熟读古书,但却以批判为目的,难道他由此竟非中国人?而若有洋人熟读儒家经典,就属于中华民族一分子了吗?更重要的是,按照他们的说法,现代国人已经不再阅读儒家经典,那么大多数国人已经不再属于中华民族,那儒家学者们又有何理由要求他们重新阅读儒家,甚至要求少儿强制背诵读经,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或许,支持儒家的人还可以寻求另一种辩护方式,少数族群权利诉求。有人认为,我们若要平等对待弱势族群(包含文化的以及宗教的团体)的权利,单单依靠宽容原则是无法支持这一诉求的。国家仅仅保护个体人权,而对各种文化族群保持中立,对比强势的文化,少数族裔文化难以持存,进而很难维持不同族群群体间的公正。比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应该加入本地语言的教学课程,不然因为语言能力差别最终难免使得少数族裔出于劣势地位而有失公正。若基于文化多元主义,我们却可以很好地回应全球化世界少数族群的生存问题,因为根据文化多元论,他们不仅承认个体权利,而且还认为存在着少数族裔权利。[6]少数族群权利可以算作“集体权利”,可被看做一种人权,其补充了个体权利上的不足。[7]而根据该权利,族群内部对后代的教育问题具有决定权,加拿大的少数族群的教育权归属问题,就曾引起争论。加拿大印第安人子女之教育权一度被联邦政府收回,而其民族内部一再抵抗最终逼迫加拿大政府将印第安后代的教育权下放,而这教育权,实际上保存了印第安人对后代独特的教育方式,其中一个项目的就是培养印第安人后代对其族群的认同感。于是,倡导读经运动的儒家学者们似乎可以依靠文化多元主义的论证,类似地对少儿读经运动进行辩护。根据少数族群权利的看法,国家对下一代的教育普及,应当尊重并且偏向少数族群之传统这一特殊情况。在中国的情况,即使儒家得不到国家的支持推广,国家也不应该干涉民间自发以及儒家内部的积极推崇。因为根据儒家少数派这一群体之权利,儒家学者与少儿家长们所认同的儒家群体对少儿读经的诉求是合理的诉求。
首先,在笔者看来,当代儒家学者对于儒学传承状况似乎过于担忧,虽然近代中国对儒家传统的破坏严重,但其生命力却仍旧极其顽强。各地孔子学院遍地开花,许多海外华人更是坚持让子女学中文、阅读中国传统经典,而海外的新儒家研究也蔚然成风。其次,即使儒家是一种弱势文化,但将儒家当前之状况类同于加拿大印第安人族群曾经的文化困境,我们仍旧要质疑儒家经典中要求少儿死记硬背的内容的合理性。儿童之教育权力归属问题可能是有所争议的,然而无论行使教育权主体是谁,我们仍然可以基于教育内容提出独立的批评。因为从本质上来讲,教育权力归属以及教育内容的施与两者是不同的问题,将少儿读经运动之争论引向教育权归属,实际上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差别。我们反对的不是儒家社群来执行对小孩的教育权,而是反对教育者对少儿不加批判地灌输所谓的儒家道德观念。再者,即使我们承认少数族裔权利,而这权利得以支持这一儒家传统之保持,这也不意味着少儿之个人自主权利可以忽略。儒家长者对其文化前途怀有忡忡之忧心,要求保存传统文化,这种情怀我们可以给予同情的理解,但这并不能支持儒家社群权利无条件优先于个人权利的说法。特别是在人文理性的框架内,个体尊严才是最终的诉求。
四、两类经典的区别
经典分两类。一类涉及的是情感的陶冶、解读世界的一种视角转换或感受力的增强,包括文学、诗词、戏剧、音乐、书法、绘画等。这类经典一般不直接涉及判断是非对错的问题。比如唐诗,读起来朗朗上口,里边基本不含是非价值的判断,没有明显的对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人该怎么样活这些问题进行一个判断。这样的经典,或许可以让小孩拿来背诵,继承起来,也可能正面的东西比较多,就是提高我们的语言能力,还有增强我们对世界上各种花花鸟鸟、人情世事、小桥流水等的感受力。音乐经典,不从小培养的话,除非你是天才,不然就没有这些所谓“音乐细胞”了。培养了以后,就可能有较强的感受力。对前人的感受有所理解,也帮助自己提高。这是一类经典,以文学艺术类为主。
还有一类,我们一般讲经典就是儒家经典,《论语》之类的,像蒋庆列的那些经典目录。那里边是对世界人生有直接判断,以及有关于是非对错的直接训诫的。小孩子的“蒙书”,包括《弟子规》、《三字经》等都属于此种,虽然不是大学里研究的经典,是小孩读的,它也教你这样好,那样不好,这样做,不要那样做,诸如此类,这些东西就要注意了。第一,小孩缺乏判断力,把他们不懂的东西灌输给他们,是对他们人格的不尊重。第二,把背书当成一种最正规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不管内容是什么,拿起来就背,如果变成一种心理习惯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第三,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内容像“三纲五常”之类的不一定是对的东西,如果连带加上“二十四孝”等有严重问题的内容,我们都让小孩原封不动地背下来,当成理所当然的规矩,那就是极其严重的问题了。
在没有进行辨别之前把所谓的“经典”整套拿来让小孩子背,还说从小趁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记忆力强的时候把它背下来,以后自然而然就会按照所背的东西去做了,此所谓“道德教育从小抓起”。但是,如果记下来的内容是非颠倒,不是变成反道德教育了吗?这样背诵,小孩在成长过程中也许就自然而然地吸收了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形成了自己的三观,这样一定不是好现象。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说的就是“未经考究过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他说得不一定全对,但是我们如果觉得他还有一些道理的话,也就不应该置若罔闻。起码,苏格拉底一定会反对人家背这种东西的。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这种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三观都凝结在里面的东西,小时候就背下来,以后就自动按照那个去做的话,就是把小孩日后的生活变成“不值得过的”。
很多人都说,小时候人要学会遵守各种规矩,坚守各种道德观念。“三观”对一个人的人生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基本上决定了你一生会做什么选择,你会追求什么生活目标。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人生的初始阶段,你就要好好地选择、思考,慎重地挑选,而不是从小由父母督促,或者是学校教育,或者是社会刚好流行什么,我就背了那个,以后一辈子就随它主宰自己的命运了。太过分的话,以后没有批判反思能力苟且一生,就是出卖了自己的一生。作为父母,刚好碰到现在流行“国学”背《弟子规》,不仅照单全收,还要硬塞给孩子。以后人家不流行这个,不知道流行啥了,你又听任偶然的社会风气摆布的话,又会如何选择呢?无论如何,让偶得的东西驻扎在小孩心里,让他一辈子跟着走,这是负责任的父母应该做的事情吗?
五、结语
学经典,该如何学?学哪些?该不该用背诵的方式学?如果只针对小孩来谈,当然小孩开始读经典肯定是要背诵的,他不可能有多少理解,跟大人不一样,小孩背诵经典用不着理解力。这样让小孩背经典,是福还是祸?
回过来看,我们成年人掌握着话语权和决定权,于是就趁小孩记忆力好,还是白板一块、白纸一张的时候,赶快给他装进去很多内容,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这样做,似乎小孩就会如愿长大了,就会成熟了,在“起跑线”上比人先走了一步了。也许是在“起跑线”上先走了一步,但是在起跑后,跑往何方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啊。这点是需要我们严肃判断的,绝对不能无意中残害了自己的小孩。起跑了没两步,就碰到悬崖,收不住脚,那就是灭顶之灾。所以,方向的东西要定了才跑。根据什么定方向呢?这就需要人文理性,而不是文人情怀。
[参考文献]
[1]姚中秋、李强、从日云等:《通识教育与文明复兴》,《学海》2013年第4期。
[2]翟振明、陈纯:《自由概念与道德相对主义》,《哲学研究》2014年第1期。
[3][4]蒋庆:《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蒋庆先生谈儿童读经面临的问题》,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us/ jqxstetdjmldwt.htm。
[5]蒋庆:《再论政治儒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7-268、341-342页。
[6] Sarah Song,“Multiculturalism”,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pring 2014 Edition),Edward N.Zalta (ed.),URL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14/entries/multiculturalism/〉.
[7] [加拿大]威尔·金里卡:《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65-88页。
责任编辑:罗苹
作者简介翟振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颜志豪,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广东广州,510275)。
〔中图分类号〕B82-02;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3-0026-06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