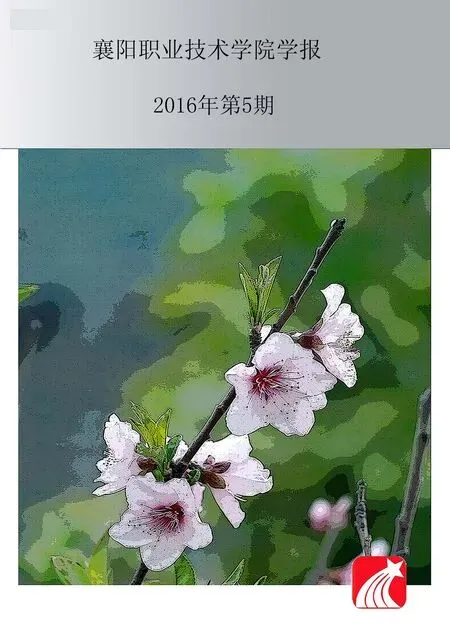浅析新《行政诉讼法》之受案范围的修改
周 泽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公共管理系, 南宁 530000)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核心问题,主要反映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范围和公民行使诉权的大小。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是依托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概括性规定了“凡是行政机关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所有外部具体行政行为,均属于受案范围之内”。随着法治社会的发展,受案范围的狭隘已经无法涵盖日益增长的新型行政争议,于是1991年最高院颁布《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于受案范围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司法解释;2000年《关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1条规定对受案范围作出了进一步解释,将“具体行政行为”界定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出台各项司法解释的过程可以看出,受案范围呈现出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行政诉讼法》在实施过程当中遇到了新的情况和困难,已经难以解决司法实践当中出现的各种新型问题。因此修改《行政诉讼法》可谓是大势所趋,不负众望,特别是扩宽受案范围更有利于保障公民的诉权,真正诠释了“民告官”的理念,为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概述
在中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指的是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主管范围,或者说,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是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提起行政诉讼的范围和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裁判争议范围的统一。[1]这一范围决定了行政权受司法权监督的广度,即司法机关应对行政机关的哪些行政行为可以进行合理合法性审查,也决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在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所享有诉权的范围,决定着行政终局裁决权的范围。
为了能够更好地防止行政权恶意异化,减少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侵害,真正做到把行政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必须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制度。然而旧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狭窄,界定也不明朗,导致很多行政案件无法及时立案,造成公民“信访不信法”的现象频发,给建立理想的行政诉讼制度带来不利影响。因此2014年11月1日对《行政诉讼法》的首次大修改中最大的特色就是扩大了受案范围,进一步强化通过行政诉讼手段解决行政纠纷的作用,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二、新旧《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对比
(一)旧《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规定
旧《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采取的是总体概括和正反面列举的方式。主要表现在旧法的第2条和和第11条规定:一是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二是若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的,公民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其次又通过旧法的第11条正面列举的八项行政行为和第12条否定列举的四项行政行为以及《若干解释》规定的几类行政行为分别做列举的规定。针对这种“概括+正面列举+反面列举”的方式规定受案范围会显得彼此之间互相矛盾,是不可能去穷尽目前日益增长的新型行政争议,必然会造成法律法规无法涵盖的真空地带,导致公民权利救济的空白。
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行政行为类型过于单一。旧法第11条采用肯定列举方式规定了典型的几类行政行为,比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以及行政机关不作为行为、违反要求履行义务行为和不依法发放抚恤金行为这三种非类型行政行为。这几种行为主要是从具体行政行为标准和权利类型标准来划分,此类划分方式不合理,标准不统一,类型重叠,容易产生受案范围边界模糊不清。
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保护范围过窄,第11条第1款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除此以外的其他权益是无法得到有效救济,可见旧法对公民的权利保护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二)新《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规定
新《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这是对受案范围的概括性规定。跟旧法比较,新法将“行政行为”代替了旧法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法律还规定此类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可见“行政行为”一词的概念更富有弹性,解释空间大,能够把更多的违法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范围之内,为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给予更大的裁量权提供了基础,解决了“立案难”的尴尬局面。另一层面上也体现了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的扩大,即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这一行政主体。这无疑是扩大了民众司法救济途径,充分保障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和诉权,弥补了从前对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而无法诉讼的缺陷。笔者认为此改变为今后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受案范围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和实现性。
新《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行政行为种类增加。新法将旧法肯定列举的八类行政行为种类增加到十二类行政行为。特别增加了以下几类行政行为:作出对自然资源确权决定的行为、征收征用行为、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行为、行政协议相关行为。特别修改了以下几类行政行为:①新法在原法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不依法发放抚恤金行为”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社会保险待遇和最低生活保障待遇”。②新法在原先规定的“侵犯经营自主权”的基础上增加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村土地经营权。③新法在原先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行为”的基础上增加了“行政强制执行行为”。④新法在原先规定的只针对“申请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以及行政机关不予答复、拒绝颁发的行为”基础上扩大到“所有申请行政许可以及行政机关作出的所有有关行政许可的决定”。⑤新法在原先规定的“拘留、没收财物”修改为“行政拘留、没收非法财物”,大大提高了受案范围的确定性。新《行政诉讼法》将这些行政行为进行明确列举,使受案范围的规定更加清晰,有助于法官及时有效审理行政案件,进一步加强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新《行政诉讼法》扩宽了公民的权利保护范围。新法第12条第1款第12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增加了“等合法权益”这一表述,意味着可以涵盖很多除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外的权益。姜明安教授认为,应将保护的范围扩充至各类合法权益,而不应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那么对“合法权益”应做广义的解释,就应该包括宪法规定的“劳动权”、“受教育权”、“选举权”、“文化权”等。
三、新《行政诉讼法》的缺陷及完善对策
新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在受案范围方面做了大量修改,在原有的受案类型上加以扩充,去除了“具体行政行为”标准的限制,增加了很多新型合法权益,充分表明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范围也在扩大,但是新法对受案范围的规定也存在一定的瑕疵:比如立法模式仍旧采取概括+肯定列举+否定列举,对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审查还是采取“附带审查”方式,排除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等行政行为于受案范围之外。此次修改之举还不够创新,仍显保守。就这些缺陷来有以下几点完善对策。
(一)建立科学合理的立法模式
新《行政诉讼法》依然沿用概括+列举方式确立受案范围。新法第2条采用概括方式囊括所有行政行为纳入到受案范围,第12条采用肯定列举方式,第13条又采用否定列举方式。
这种又肯定又排除的列举方式是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行政争议,二者之间必然会出现法律无法涵盖的真空地带。结合当前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笔者建议在实行可以审查的假定原则的基础上可用“肯定概括+否定列举”的模式来规定受案范围。即可以考虑保留新法第2条肯定概括规定和第13条排除性规定,删除新法第12条肯定列举的规定,而是可以考虑把第12条规定的内容纳入到司法解释来指导行政诉讼立案实践。因为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只针对法律明确列举可以受理的案件才进行立案,而那些没有被纳入到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却由法官个人的自由裁量权而决定是否受理,无疑是限制了受案范围,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大量的违法行政行为不能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建立这样的模式可以避免难以穷尽所有行为且标准不统一的缺陷,更加明确受案范围。
(二)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范围
新《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行政相对人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起诉时,可以请求法院对规章以外的国务院部门和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一并进行审查,即法院可对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进行“附带审查”。对于新增“附带审”内容,姜明安教授认为,从形式上看,该“附带审”似乎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实质上并没有对原《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有任何真正意义的扩大,甚至还有可能有所退缩。[2]实际上还是排除了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笔者认为应当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受案范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新型纠纷类型的日益增加,多数都是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违法现象。虽然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不特定的人和事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但是具有持续性、普遍性,一旦违法,会给行政相对人带来更大的伤害和损失。由于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许多行政机关为了规避司法审查扩大行政权力往往会把本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事项以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制定出来。而且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大部分都是依据抽象行政行为的规定,司法机关若无权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此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受案范围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
(三)内部行政行为纳入到受案范围
新《行政诉讼法》依旧规定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不属于受案范围,将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外,主要是受到国外的特别权力关系影响。特别权力关系是指国家或公共团体等行政主体,由于特别法之法律原因,对行政相对人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概括性的命令强制之权力,而另一方面行政相对人却有服从义务。[3]目前我国公务员管理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司法审判经验也很丰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该有所突破,为了保障公务员的基本权利,笔者认为应当有选择性地把内部行政行为也纳入到受案范围,特别是涉及到公务员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的行为。因为公务员具有双重身份,首先应该把其看做是公民,应当也享有公民应有的行政诉讼救济的权利。比如,涉及到对公务员实施的开除、辞退、解聘、录用、降级等处分行为,直接影响到公务员的职业前途、工资福利等重要基本权利,故应纳入到受案范围,给予公务员提供相应的诉讼救济途径。
总之,新《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的修订扩大,有利于保障公民人权,减少社会矛盾纠纷,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防止行政权的异化和滥用。笔者希望今后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当逐渐把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行政公益诉讼等纳入其中,以便真正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充分保障民众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法治社会。
参考文献:
[1]马怀德.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王振.关于行政诉讼修正案受案范围评析[J].法制博览,2015(9):18-21.
[3]翁岳生.论特别权力关系之新趋势[J].行政法与现代法治国家,1990(3):13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