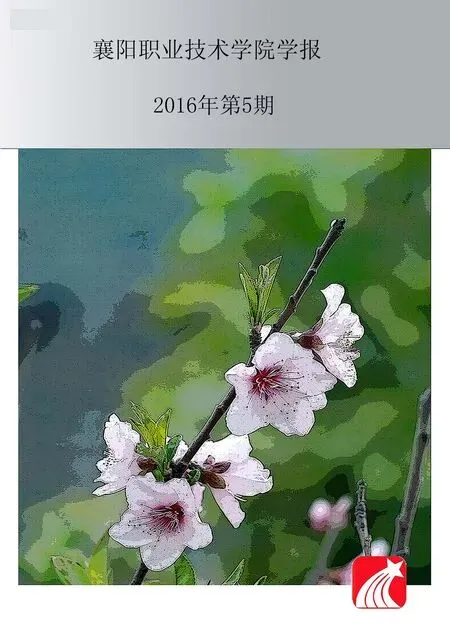疯癫:文学形象的异端呈现
秦 闻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法国着名作家米歇尔·福柯所著《疯癫与文明》是一部历史性与哲学性相结合的著作,在震惊哲学界的同时也震惊文学界。罗兰·巴尔特说:“这部著作是对知识的清洗和质疑。”[1]福柯以哲学思维解释“古典时代”的疯癫,“把我们当做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1]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力图表明疯癫是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知觉对象,它是在历史过程中由多方面建构而成的,是由多种社会实践,而不是由一种集体感觉所捕捉到的。疯癫是理性与非理性冲突的结果。在理性话语权力的控制下,疯癫成了异端。马尔库塞说:“社会的不合理性愈明显,艺术领域的合理性就愈大。”[2]当疯癫进入文学视野成为一种知觉对象,从文艺的对象的角度进行审美的审视,能更好地对现代社会与人性的疯癫本质做恰如其分的揭示。
一
对中西方疯癫现象的研究很容易发现疯癫形态下产生三类人:第一类是对社会没有危害的傻子。他们中大部分人构成了波德莱尔眼中游荡于巴黎都市街头的各种“游手好闲者”。他们靠拾捡垃圾为生,以桥洞、公园躺椅、残垣的建筑为安身立命之所。既不妨碍社会治安也不会危害自己,偶尔成为常人嘲笑的噱头和供人围观、调戏的对象。社会对其采取自生自灭、放任自流的态度。第二类是对社会产生一定危害的疯癫暴力狂。他们的疯癫表现出的谵妄状态,常常引起人们的恐惧,幻觉会导致他们无法控制自己,不是伤害自己就是伤害他人。他们的行为是社会伦理道德、法制所不能容忍的,需要社会采取强制性的医疗措施对其进行禁闭。第三类是思想精神上的疯癫。由于他们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离经叛道的行为,会给社会秩序带来一定潜在的威胁,甚至有时候这种危害力大大超过单纯的暴力性的疯癫。社会对后两种疯癫者的控制就更为严格。
“艺术不是对实在的摹仿,而是对实在的发现。”[3]从文化视角转向文学视角,会发现,从虚拟的古老的亚尔古英雄传奇中的愚人船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阿来的《尘埃落定》……疯癫形象牵引出了大量值得反思的疯癫故事。疯癫者独有的非理性状态通常深深表现在疯癫话语之中。对文学作品中这些疯癫形象、话语的分析,透视疯癫之下的理性内涵,可以看出作者在面对疯癫世界对于生命现象的倾情关注与深刻体悟。文学极力寻找本真,救赎失落的灵魂,探索应对疯癫现实的良方。按照疯癫形象的三种分类,与之对应的是文学作品中呈现的三种类型的疯癫形象。第一类代表就是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少爷——“我”。这位川西藏族最后一位土司麦其家族中的小儿子是一个生来就令人同情而又鄙视的傻子。他拥有无尚的地位和权威,管理着整个麦其家族。但正是这个连“我是谁”都搞不清楚的傻子,以与正常人不同的思维方式,获得了那些“文明人”、“聪明人”所不具有的人格品质——同时拥有疯癫与童心,即使是信口开河却也能语出惊人。他总是随心所欲,但人性的光辉却光芒四射,他看似呆滞愚钝却智力超群。正如福柯所言:“(傻子)他的傻言傻语,一点也没有理性的外貌,却说出了理性的语言。”[1]“哥哥因为我傻而爱我,我因为是傻子而爱他。”“我”的疯疯癫癫是对文明理性的消解,对聪明人世界人与人的冷酷关系的嘲讽。“要做一个统治者,做一个王,要么是一个天下最聪明的家伙,要么,就干脆是个傻子。”[4]愚蠢的傻子一次次地化解危机,而聪明的哥哥费尽心机却只有失败,戏剧化地嘲讽了聪明人常犯的错误:“小看一个傻子”。在这里,聪明与愚蠢、理性与非理性早已被“文明世界”做了颠覆性的解释。然而,虽然智力超群,但傻子“我”最终倒在麦其家族的敌人匕首之下,完成了一个傻子孤独的旅程。“我”也明白要像父亲一样懂得“规矩”、“秩序”和“权力”的辩证关系——失去“规矩”,就失去“权力”。阿来通过傻子“我”的独语告白形式将故事娓娓道来,透过人道主义的眼光审视疯癫与文明,嘲讽了“权力”、“秩序”、“规矩”等代表“文明”社会对人的束缚和毁灭,诉说着疯人的灵魂并不疯,而世界永远是一个疯狂的世界。第二类代表人物一种是如福柯所述患有狂躁症或者歇斯底里症的患者,他们通常具有暴力性,如悔改之前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病态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另一种是常人眼中的疯癫暴力者——最经典的形象要数鲁迅笔下的狂人。在没有大禁闭时代的中国,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塑造了禁闭。面对“被吃”的恐惧,狂人行为疯癫,言语疯癫。正常人的理性认知对狂人精神状态的判断成为狂人被囚禁的标准。大哥对狂人采取禁闭,不让其外出,并把狂人视为异端,隔绝于“正常人”。大哥作为封建家长制度的代表,行使着对被管理者的禁闭权力。而赋予其强制性权力的是大哥身后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社会统治者拥有的话语权。传统理性表现出冷漠固执,即便是大哥这样的亲人也露出凶狠的眼光和铁青的面孔。被“理性”光晕笼罩下的“家”,这时候成了狂人最恐惧的禁闭所。强大的疯癫世界使狂人无力摆脱和抗拒。狂人不可避免地被他眼中的疯癫所吞噬。第三类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预言家”——查拉图斯特拉。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人只有成为具有强力意志的超人,人的一生才有意义。”“人类是应当被超越的。”[5]他对一切的怀疑终致喊出了让人类震惊的呼声:“上帝死了!”预言家不断地上山下山,寻找可以接受自己超人理论和强力意志的人。他蔑视一切的善,认为善是懦弱之人的代名词,行善就是作恶。当狂人还在用善意的心去劝说周遭的众人时,查拉图斯特拉已经在寻找能够在思想上与他一致的徒弟、朋友。当他明白最后的真理是“生命的永恒反复”中唯有“强力意志”才能从困苦、荒诞的现实中摆脱出来,实现人类的超越,查拉图斯特拉从对民众、门徒的教育走向了自我的教育。查拉图斯特拉抽身于人类社会之外,睥睨众生,在对疯癫世界的嘲笑的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孤独的超人意味着对抗一切的文明与疯癫,理性与非理性。这种自我教育与清醒虽然孤独但不至于使自己灭亡。
不管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超人”语言还是狂人口中的“吃人”理论,抑或是土司少爷“我”的傻言傻语,都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疯癫话语。从叙事的角度来看,作者苦心经营的作品一方面表达着作者对疯癫世界的深刻看法与对生命状态的高度关注,一方面也透示出作者内在精神视域的局限性和意欲打破疯癫世界牢笼的迫切渴望。
二
萨德认为:“人类疯癫的产物不是属于自然本性的表露,便是属于自然本性的恢复。”[1]救赎被疯癫禁锢的肉体与被疯癫吞噬的内在心灵,赎回真正的自由,成为自始至终的一个难题。禁闭并不能解决疯癫。福柯在讨论治疗精神病患者时,介绍图克的救治方法是博爱行动,即解放病人,废除强制,创造一种人道的环境。上帝创造的彼岸世界是否可以给予疯癫者莫大的安慰,福柯的答案是怀疑的。当“理性”与“非理性”冲突、疯癫企图拯救文明时,疯癫者也在拯救他们眼中的疯癫。狂人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救赎疯癫的众人。狂人用独语式的自白劝谏大哥:“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6]肉体的禁闭与独语式的规劝发自于相对立的自以为理性的双方,在相互的指认中指向他(他们)所以为的疯癫者。这种善意的规劝企图让大众受到启蒙,从而为反对疯狂的社会团结起来:“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6]但是,被压制的疯癫者内心的呐喊依然只是微弱的喘息。由于时代的局限,拯救国民的启蒙教育落在知识分子头上。面对时代的疯癫,鲁迅希望通过自己的呐喊,唤醒嘲笑疯癫却已成疯癫的冷眼看客。这种救赎仍然是站在善的立场,站在人道的立场,拯救愚民脱离愚昧。狂人的善只能是被吃的下场。在包办婚姻面前,善使鲁迅畏葸不前,成不了“敢于直面淋漓鲜血”的摩罗诗人。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使他着眼于拯救蒙昧的大众,却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真正令疯癫者失语的是疯癫的制度本身。
尼采指出现在的世界已经陷入了癫狂状态:内在的紧张和外在的匆忙。尼采指出:“猥琐、敏感、不安、匆忙、聚众起哄的景况愈演愈烈——纷乱状况的现代化所谓‘文明’,愈来愈轻,个人面对这巨大机构灰心丧气,只好屈服。”[7]缺乏信仰导致的现代式的匆忙带来的空虚加剧了无信仰状态。现代人表露出的是个性的丧失和灵魂的平庸。尼采的救赎策略是抛出“超人”的哲学,蔑视一切善,追求强大的“力”,并且不断地寻找可以领导大众的至高无上的“超人”。当权力与利益结合,他不愿对疯癫的世界俯首称臣,而是以高贵的姿态颠覆文明世界的一切文明,宣告上帝死了,而强力就是上帝。超人所做的不是同情和帮助贱民,而是诅咒并促使他们灭亡。在超人眼里疯癫世界毁灭是必然的,只有超人才能拯救世界。面对疯癫的世界,宗教之树已被连根拔起,科学的力量也不足以挽救世界。尼采意欲要求的是恰当地看待人类生活中的手段作用,切不能把手段当做目的,迷失了方向。这也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尤其在最高价值崩溃、信仰沦丧的时代,当务之急是创造新价值,建立新信仰。科学虽然繁荣了物质生活,但却不能完成这一任务。艺术也迎合商业利益和虚无者的需要,成为需求刺激和麻醉的商品。[7]尼采认为,唯有强力意志是生命的最高价值和战胜虚无主义的利器。由此着眼,艺术、文学再一次被置于镁光灯下,暴露自我,反省自身,能否坚守立场,揭露疯癫的真面目,重塑日渐消解的价值观念,从而发挥其必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下意义,成为解开斯芬克斯之谜的关键。
三
尼采假借预言家查拉如斯特拉之口诉说着忧虑:“我看见一个巨大的悲伤正降临到人类头上。最好的人都已经厌倦了他们的工作。”[5]绘画中,画家借荷马的云像遮盖住想要摄走的身体,不是使对象成为不可以眼见的,而是使主体变成了瞎子。疯癫与禁闭的怪圈以强劲的势头淹没现代社会,我们为着既定的利益行色匆匆,不再关心永恒。我们之所以无所察觉,是因为面对疯癫的社会,人们已然完全顺应,成为睁着眼睛的瞎子,自主性和理解力都在衰退。单向度的思维方式使麻木、茫然的现代人已然被疯癫裹挟,具有漠然的“对社会罪行持肯定态度的幸福意识”。[2]这是良心的丧失,其根源在于一个不自由社会所赋予的使人感到满足的特权。荒诞的社会日渐吞噬文学艺术的否定性力量,文学艺术对美的追求也只停留在粉饰虚假幻象的表面,流于俗化和大众化。正如伊格尔顿所言:“人文科学或‘文化’,是敏感地显示现代性整体危机的所在。文化涉及礼仪、社群、想象力的创造、精神价值、道德品质以及生活经验的肌理,所有这些都陷入了冷漠无情的工业资本主义重围之中。”[8]《疯癫与文明》以哲学的思维审视分析了现代社会的荒诞本质,依次进入了人类的心灵和精神地带。疯癫与文明、禁闭与开放,文学文本在时光中穿行,透过历史的眼光,寻找救赎之路。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在面对多元化、无中心、碎片化、欲望化的文化环境,某些被文化研究忽略的“大问题”诸如真、德行、客观性、道德等需要我们关注。[9]日渐被忽视的文学与文学性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德性的生活”[8]不失为一种途径:在寻求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同时促成我们互相的自我实现。这种互惠精神对于欲望私利化的社会不啻有着强烈的抗拒意识,亦是引导我们从非工具主义的角度对现代历史进行深度思考。当下,重塑坚定的信仰、正确的价值观念已迫在眉睫。警醒人们找回失落的自由和创造力,成为总体的而非单向度的人,不至于无奈地留下“救救孩子”的呼声。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75.
[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214.
[3](德)恩特斯·卡希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225.
[4]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94.
[5](德)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杨恒达,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7:4.
[6]鲁迅.狂人日记[C]//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5-432.
[7]周国平.尼采与形而上学[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2:26.
[8](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1.
[9]姚文放.从文学理论到理论——晚近文学理论变局的深层机理探究[J].文学评论,2009(2):6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