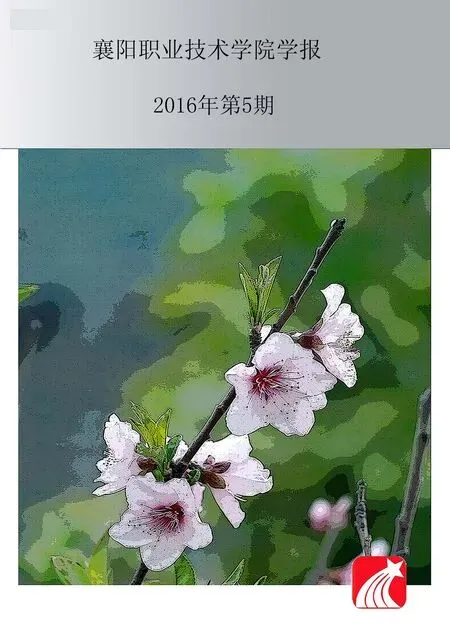从中国古代小说看黑格尔的悲剧论
——从《水浒传》的悲剧说开
李晓文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是西方古代悲剧理论史上的集大成。黑格尔认为悲剧的本质是矛盾冲突,造成冲突的根源不是罪行或偶然性的灾祸,而是具有一定片面性的道德力量或伦理力量。按他的理解,悲剧之所以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不在于它表现了人们的悲惨命运,强化了恶人当道、好人受苦的情景,而在于悲剧并不是正义与邪恶、好人与坏人那样清楚明白的矛盾对立,是矛盾的双方都没有错,都有各自的道理,只不过由于两者的道理是相互冲突的,从而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水浒传》便具有浓厚史诗意蕴的忠义伦理悲剧。其悲剧成因、悲剧人物的形成及其悲剧效果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德伦理的矛盾冲突,从中国古典悲剧精神的角度体现了黑格尔的悲剧冲突说。
一、黑格尔的悲剧冲突理论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美学的顶峰人物。程孟辉在《西方悲剧学说史》曾经这样评价过黑格尔对悲剧美学的卓越贡献:“他第一个把矛盾冲突的学说真正运用于悲剧学说,第一次自觉地把悲剧看成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1]黑格尔特别重视悲剧,因为黑格尔认为“充满冲突的情境特别适宜于用作剧艺的对象”,“悲剧是一切艺术中最适合于表现辩证法规律的艺术”。[1]
黑格尔认为悲剧所表现的是两种对立的理想或“普遍力量”的冲突与调解,使代表片面理想的人物遭受痛苦或毁灭。就悲剧主角个人而言,或许他的牺牲是无辜的,但就整个世界的秩序而言,他个人的死遭到毁灭,然而他所代表的理想却没有毁灭。这或许就是悲剧带给我们读者的真正的力量,它不是让我们读了之后觉得悲恸、怜悯,而是使读者振奋乃至一种精神的愉悦。这种愉悦不是对于悲剧人物的命运而言的,而是对于悲剧本身所表现的效果。悲剧的本质即矛盾冲突,造成冲突的根源是具有一定片面性的道德力量或伦理力量。而黑格尔所谓的冲突,便是指人物性格在某种具体情境中所遭受到的两种“普遍力量”(人生理想)的分裂和对立。悲剧人物在某种情境中所表现的两种人生理想的矛盾冲突,不是他个人造成的,而是他所生存的那个社会必然也存在着某种道德和社会力量的冲突。这种矛盾冲突是社会的产物,是不可逆转的。而处在当时社会的人物就必然会在个人和社会、个人人生理想的矛盾冲突中走向悲剧结局。悲剧便由两种对立统一的理想的冲突而产生。
黑格尔把悲剧冲突的情境分为三种,一是由物理的或自然的情形所产生的冲突,这种冲突一般是由于疾病、自然灾害、自然规律对先前的和谐生活的破坏。这种导火索本身不具备任何意义,但自然灾害可以发展出心灵性的分裂,作为它的结果。所以古希腊作品往往以纯粹物理的或自然的情况引起冲突。
二是由自然的血缘关系、等级地位等引起的。这种冲突比自然的肉体疾病、痛苦所引起的冲突更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其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为由自然血缘关系相关的亲属关系和继承权产生的冲突。“与自然密切联系的权利,如亲属关系,继承权之类,正因为这种权利是与自然 (或出身情况)相联系的,它就可以有众多的自然定性,但是权利这种主要的东西,却只是单一的”。[2]第二种情况为由于个人出身的高低贵贱的无法跨越而引起的冲突。黑格尔认为:“按照事物的概念来说,阶级的分别当然是有理由可以辩护的,但是个人凭自由意志去决定自己属于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权利也不应被剥夺去,只有资禀、才能,适应能力和教育才应有资格在这方面作出决定。”[2]所以,如果个人要超越他卑微的出身等级的界限的权利被社会的法律规定等硬性规定所剥夺,那么造成的冲突是“一种悲惨的不幸的冲突,因此它来自一种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不是真正自由的艺术所应敬重的”。第三种情况为“天生性情所造成的主体情欲。最显著的例子是奥赛罗的妒忌”。[2]这些情欲本身不造成冲突,只有在人们因为这些情欲而违反社会伦理道德原则的情况下,才引发悲剧冲突。
三是人物的行动导致心灵和精神的分裂而引起,这个冲突是导致悲剧的最深刻的根源,“一方面须有一种由人的某种现实行动所引起的困难、障碍和破坏,另一方面须有本身合理的旨趣和力量所受到的伤害”。[2]这三类冲突存在着层次递进的关系,在导致悲剧的三类冲突中,由心灵本身的分裂和矛盾引发的冲突是导致悲剧最深刻的根源。
黑格尔自觉地运用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来解释悲剧冲突,揭示了悲剧的本质,体现了他在悲剧理论方面的独创性,他的悲剧冲突说又向下开启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理论。
二、《水浒传》蕴含的悲剧精神
《水浒传》历史地表现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压迫是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社会根源。同时,小说歌颂了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农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这次农民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展现了其演变为悲剧的内在历史原因。
悲剧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意味。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3]悲剧给读者心灵的震撼、感情的升华、主题的深化方面,更加沁人心脾,留下无数的回味。
《水浒传》第一百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写的是卢俊义、宋江、李逵被害,吴用、花荣在宋江墓前自缢,五人同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的事情。关于这一回,郑振铎先生曾评论:“最后的一回‘神聚蓼儿洼’更极凄凉悲壮之至,令人不忍卒读。有了这一回,全书便更显伟大了。全书本是一部英雄传奇,有了这一回,却无意中成为一部大悲剧了。”[4]这便体现了《水浒传》不仅仅反映农民起义的英雄豪气,而且也是“令人不忍卒读”的生命悲剧。
《水浒传》是一部人物命运的悲剧,无论是中下层官吏还是平民均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首先是一些小人物的悲剧。小人物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在阴暗的社会角落里苦苦挣扎,即使他们各有各的营生,但却找不到自己的人生坐标。像武大郎、郓哥,他们都是社会黑暗的牺牲者。小人物的命运始终与社会和大人物唇齿相依,他们是社会的受害者,却承担了社会黑暗带来的灾难。其次,那些有着社会地位却得不到重用的中下层官员的悲剧。林冲便是其典型。其实林冲的愿望很简单,无非就是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但是,偏偏事与愿违,在高衙内等逼迫下,不得不落草为寇。林冲的悲剧可以说让人们真真切切认清了整个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处于如此阴暗社会的人的困苦和无助。
此外,《水浒传》还描写了梁山泊起义事业的悲剧。上梁山之人或是不满阴暗的社会,主动投奔梁山,或是被逼无奈,落草梁山。这些人尽管目的不同,身份各异,但是却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下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是,在招安之后,一切所谓的辉煌都化为乌有,伴随着招安的是水浒英雄们的悲剧命运。
《水浒传》可谓是“农民起义史诗”。通过一部《水浒传》,人们能透视出乱世民众挣扎求活的悲惨生存状态,谛听到作品本身所传达出的悠长历史喟叹,感受到浸润于作品之中的深广悲悯情怀。
三、在《水浒传》的悲剧中所体现的黑格尔的悲剧冲突
一直以来我们中华民族都会莫名地有所谓的英雄情结,我们渴望破阵杀敌,希望济弱扶倾,期冀匡扶正义。所以,《水浒传》中的众多英雄好汉便成为我们所尊崇的楷模,在我们心中他们是可爱的草莽英雄。于是,当一个个英雄好汉在招安之后走向了不可更改的宿命,《水浒传》所展现给我们的已不再是“侠义如酒浓于酒,男儿放饮情烈烈”轰轰烈烈,而是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悲歌。
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5]但是,在《水浒传》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所谓的大团圆,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希望它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可是,这样一来,《水浒传》的悲剧意蕴便消失殆尽了。所以说不管后世对宋江招安有多少诟病,他对于整个小说的悲剧意蕴所做的铺垫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文学里所呈现的多是“静态的悲剧”,为此,从《水浒传》的悲剧中便可寻得黑格尔悲剧冲突的踪影。
《水浒传》在第一回中,讲述了北宋皇帝在位四十二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6]可谓是“三登之世”。但是,“谁道乐极生悲,嘉佑三年春间,天下瘟疫盛行”、“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6]只有在这种民不聊生的情景中,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才会引发动荡,这就暗示着即将到来的北宋王朝的悲剧命运。皇帝派洪太尉去迎接张天师来祈禳瘟疫,可是洪太尉却误打误撞地将“伏魔殿”里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放走。这便为后来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齐聚梁山泊做了铺垫。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悲剧冲突的第一种情境是由物理的或自然的情形所产生的冲突,这种冲突一般是由于疾病、自然灾害、自然规律对先前的和谐生活的破坏。《水浒传》在开篇便描绘了北宋天灾瘟疫的盛行,这便是由瘟疫产生的冲突,瘟疫对以前五谷丰登的和谐产生了破坏,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奸臣当道及其国家和人民的悲剧命运。
《水浒传》一百零八好汉,基本上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悲情故事,都贴上了悲剧的标签,在对现有体制社会的不满下,在被冷漠无情社会排挤和抛弃下,林冲也好,武松也好,都是命运悲剧下的一个注脚。当他们出征方腊无数英雄战死的时候,读者读到的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悲哀与无奈,也许这正是作者所想达到的文学效果,它让这种悲情美在文学中得到了展示。
《水浒传》中最悲壮的、最令人不忍卒读的应该是林冲的人物悲剧。鲍鹏山教授曾形象地说过:“《水浒传》里的英雄有三种类型:一个是惹事的,一个是遇到事的,第三种是最糟糕的,是事找人。”[7]林冲是典型的“事找人”的悲剧英雄。中国有句古话“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林冲本来是一个不想惹事的人,他有一个在他看来很完满的一个生活,有一个非常美丽、贤惠的妻子,有一份适合他的工作,八十万禁军的教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为国立功,然后封赏,封侯,博一个封妻荫子。他希望一生就这样走下来,每一步都清清楚楚,每一步都明明白白。但是,在那样一个时代,林冲的命运早已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朝廷。于是,林冲成了一个官场势力迫害的牺牲品。从被骗买刀,到误入白虎堂,再到野猪林,最后的草料场,和林冲过不去的都称得上是他的领导或同僚。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林冲不得不反,成为第一个上梁山的天罡星。然而,被逼上梁山后的林冲却受排挤,直到晁盖上梁山之后林冲才坐稳了自己的位置。其实,林冲最后中风而死,也是对其英雄末路的一种慨叹。林冲的悲剧人生便体现了黑格尔悲剧冲突中的第二种情境由自然的血缘关系、等级地位等引起的。这种冲突更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更值得让人悲叹。可以说,林冲是整个一百零八将中最值得人悲悯的英雄人物,其最后的结局,虽然没有让他战死沙场,中风而亡,其实对于林冲来说,后者更为狼狈,对于读者,或许更是多了些许的怜悯之情吧。
然而,《水浒传》最具深厚的悲剧意蕴,不是瘟疫盛行,国家动荡,不是一百零八位英雄的悲剧性格所引发的悲剧人生,而是那种忠与义的矛盾冲突。忠义矛盾冲突可以说是导致水浒英雄最终走向不归宿命的根本原因。《水浒传》最重要的闪光点是宣扬忠义思想。在《水浒传》中,所谓忠就是忠于大宋皇帝,这是其一贯标榜的忠君思想。因此,《水浒传》又名叫《忠义水浒传》,梁山的聚义厅也在大聚义之后被宋江改为“忠义堂”,同时宋江还口口声声说:“今皇上至圣主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错位。”以至于宋江在临死之际,仍然要表白忠心,“宁可朝廷负我,我不可负朝廷”。这种忠君思想或许正是封建正统思想,但它却给起义事业带来莫大的伤害,最终使得艰难缔造的义军接受招安,从而导致了最终的悲剧结局。《水浒传》的义,既有仗义疏财、济危扶困的侠义之情,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是义,武松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是义,又有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之间兄弟的情义,如宋江给晁盖通风报信是义,梁山众兄弟江州劫法场是义。正是这种义才使得梁山能齐聚一心,肝胆相照。然而也正是这所谓的义,在《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往往从属于忠。梁山好汉百战之后为朝廷除去祸患,但终究未能躲过贪官的毒手,李逵为了义,最终陪宋江饮下毒酒,从而使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落得个如此凄惨的结局。《水浒传》的中心思想是儒家思想范畴的伦理道德观念,以人物形象诠释着忠义的价值观。于是,《水浒传》演绎了忠义的颂歌与悲歌,体现了水浒好汉崇高的忠义道德理念。从黑格尔的悲剧冲突论的第三种情境看,《水浒传》中所揭露的是忠于君主和兄弟情义两种理想之间的冲突,这两种理想在我们看来都是神圣的,正义的,不可否认的。但是处在当时那种冲突的情境里,却都是具有片面性,不可调和。其最终的结局必须是摒弃一方来成就另一方,而宋江的选择便是弃义求忠。最终,一百零八位好汉或在战场上伤亡,或在朝中被奸臣所害,落了个悲惨的结局。
《水浒传》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在书中看到了宋江等好汉的英雄气概,从梁山旗帜倒下的那一刻读懂历史的无奈,而这一切都在其悲剧结局中升华,造就了一部伟大的旷世著作。同时,黑格尔悲剧论说也正是因为这种个人与社会道德伦理的矛盾冲突而在中外美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中国古典名著无不体现着忠与义、爱与恨的交织与冲突,而这一切又与黑格尔的悲剧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可以在学习研究黑格尔悲剧的基础上去体味中国古典小说的悲剧意蕴,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内在涵义。
参考文献:
[1]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6-17.
[2](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66,367,369.
[3]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C]//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C]//郑振铎.郑振铎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123-124.
[5]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曲改良[J].新青年,1918(4).
[6]金圣叹.金圣叹评本《水浒传》[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1:35-38.
[7]鲍鹏山.鲍鹏山新说《水浒》[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4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