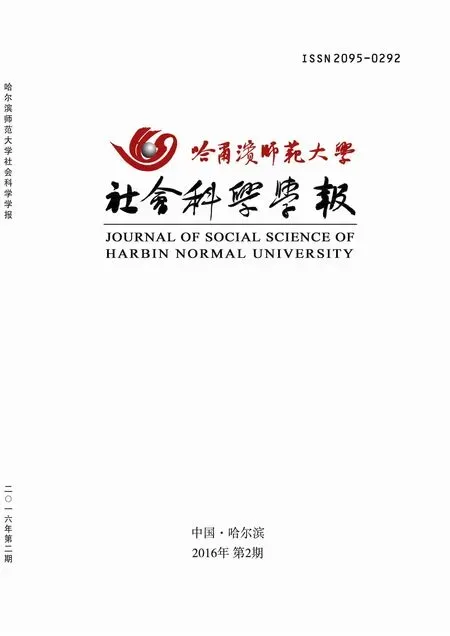从《聊斋志异》爱情故事里的男性形象看蒲松龄的两性观
丁祥倩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从《聊斋志异》爱情故事里的男性形象看蒲松龄的两性观
丁祥倩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摘要]《聊斋志异》作为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由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独立创作,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别具一格的佳作。文章以《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为参照,对其中的男性形象进行分析,根据其在与女主人公相遇相知相爱以及面对不测时的反应,从人物最终的结局,将其进行分类,在找寻共同点的同时,也探讨其个性的一面,探寻作者蒲松龄创作时的思想基础,进而透视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两性观。
[关键词]《聊斋志异》;爱情;男性形象
作为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在我国古典小说群中具有其独特地位,全书共491卷,由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独立创作,流传至今,显现其非凡的吸引力和艺术魅力。小说刻画了极其丰富的人物艺术形象,其中以女性形象尤为突出,虽然男性角色大多为引线或配角,但其性格样貌具有时代的典型特征,值得回味与探究。从宏观上看,爱情中的男子无非两种:钟情或负心。但蒲松龄笔下的男性却在此基础上有着相似又不同的人格特质,钟情男子往往专情刚直,但也不免有懦弱的一面,因此,在忠贞的爱情面前,不一定抓得住圆满的结局;而负心汉们却常因其本性中的贪婪与无耻,换来凄凉悲哀的后果。应当说,蒲松龄对男性形象的架构,实际上传达了他对身处爱情中的男子的心理和欲望的看法,正如他在《聊斋志异·自志》中所写的那样:“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他想通过叙述人与鬼怪间的感情故事,一窥人性丑恶,将心中所想尽数倾吐。
本文将以《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为蓝本,对其中的男性形象进行分析,根据其在与女子相遇、恋爱和婚后的表现,以及面对不测时的反应和人物最后的结局进行分类,从共同点和个性两方面探寻蒲松龄创作时的特定心态,进而透视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两性观,深入把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作者自身的密切关系。
一、重情重义、为爱痴狂的钟情男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之所以让人过目难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其情节的跌宕起伏与事件矛盾的普适性,为特定历史年代下的爱情增添几层波澜,使我们看到出现在爱情中的各种诱惑,从而产生的不同的宿命。情痴,便是那些对爱情忠贞、执着、甚至有些痴傻的人。这些在爱情里沉沦的情痴男子,为了心中所爱之人可以义无反顾地付出自己,以致生死不渝的爱情多次感动了地府里的冥王,使相爱之人最终死而复生,可谓“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而在如此钟情至爱的男子共性形象里,亦呈现出不同类别极具魅力的典型人物特征。
(一)独爱一生者
1.不惜生死之情痴
自古英雄爱美人,而《聊斋志异》里的这群书生,为了心中所爱,同样具有勇士般不畏世俗眼光的魄力。比较典型的如《阿宝》中的孙子楚,天生就有六根手指,为人憨厚真诚,但也就是他的木讷不懂人情为他的爱情带来好运。朋友玩笑似的戏弄他,使他向阿宝提亲,而后阿宝两次难为他,孙子楚用斧头自断手指,结果血流不断,卧床三天三夜,万念顿消。又见阿宝时,痴性变成痴情,归家后终日不起,应了那句玩笑话“魂随阿宝去耶”,阿宝终于决心下嫁,结成良缘。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孙子楚其诚其心,天地可鉴,而能和其断指丢魂相媲美的,可以说或许只有乔生的割肉相救。乔生为了心爱的女子连城,毅然决然地将自己胸前的肉用白刀割下,事后却并不收取任何钱财,只求救女子性命,只为报还知己,用情之深,实在感慨。
2.不唯美是图之情子
在蒲松龄的爱情故事里,女子往往生有俊俏而惹人怜爱的脸庞,但美与丑的转换,往往可以验证爱情的真伪,而《瑞云》中的贺生在这种考验下一定是众人之中的佼佼者。当瑞云美若天仙时,贺生自言“穷踧之士,惟有痴情可献知己”,而当瑞云变成丑女被挖苦后,他花光积蓄将瑞云赎出。瑞云觉得自己的容貌已毁,便希望贺生再娶,但贺生坚决回绝,认为自己绝不会因为她面庞的衰老变丑而遗弃她。当面对别人的侧目时,他不仅没有嫌弃她,反而对瑞云产生更深切的情感,最终,上天恢复瑞云的美貌,这是不忘初心的人应得的结果。
3.相思成病之情种
因一见钟情而生病的情种很多,而在《聊斋志异》莫过于《阿绣》中执着追寻、明辨真假爱人的刘子固。女子迁居,他“神志乖丧……忽忽逐减眠食”,而难能可贵的是,有狐女两次假扮阿绣,他人模糊不明时,刘子固却可一眼分辨。另有《阿纤》中深切思念、思慕爱恋的三郎;《婴宁》中节食无语、一心追求的王子服;《白秋练》中始终不渝、为爱觅生的慕生均是此等情意深重之人。
4.狂放刚毅之情郎
《聊斋志异》中除了柔情温厚的男子,还有面对忠贞爱情刚毅不群的大丈夫。如《伍秋月》中为了救出爱人将冥吏杀死的王鼎,《章阿瑞》中终生坚持与亡妻相守,对阿瑞关切有加的戚生等。《鲁公女》中的张于旦,当鲁公女突然去世后,张生对其灵施礼焚香祭祀,日夜思念,最终使女子感动,其后形影不离。为使女子顺利投生,张生曾为鲁公女诵经5048遍,并彼此约定十五年期限,终成眷属。
(二)爱情双美者
在《聊斋》中不乏这样的爱情:三人的痴心,双美的爱情,抱得娥皇女英。这样的男子,在蒲松龄的笔下,并非对感情不专,而是可以做到平等对待每一位爱人,对每个人都怀揣着一颗真心,如《陈云栖》《巧娘》等。《小谢》里双拥阮小谢、乔秋容的陶望三,“有婢夜奔,生坚拒不乱”。后陶望三境遇困顿,二人鼎力相助,从此他对二女不离不弃。这里,陶望三先是叱责二女为鬼物,后又表白:“相对丽质,岂独无情?”鲜明地刻画了其多情而又情笃的个性特点。
(三)有爱无果者
有爱而终不得果,再美好的爱情也不过沧海桑田,然而在为其惋惜的同时,《聊斋志异》中这类故事的男主人公,也都有其性格中致命的弱点。他们纵然真心爱慕,却因本性懦弱或爱之不坚,终致多疑嫉恨,难得圆满,正如蒲松龄所说,“人不能贞,亦其情之不笃耳”。如《爱奴》中的徐生和爱奴,若想二人相守,仅需满足一个条件,即切忌强饮强食,否则爱奴将魂飞魄散,但却因徐生的无知,一年后强行灌酒,魂去楼空,徐生再悔恨也无济于事。
二、忘恩负义、贪财好色的负心男
由于历史局限性的束缚,蒲松龄笔下的负心汉与当代社会的定义差异显著:可以妻妾成群,可以性爱不专,但决不可剥夺贤妻名分。在《聊斋志异》中,分为以下几类负心男,尽管类型有别,但却掩盖不住背信弃义、以怨报德的共性。
(一)朝秦暮楚之负义者
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可谓自古以来是爱情不专的代名词,《聊斋志异》中比较典型的是《阿霞》和《武孝廉》。《阿霞》中的景星有了新欢后,便将与其结婚十年的妻子阿霞驱逐出门,最终,景星被剥夺名禄,娶回一个相貌丑陋、性格剽悍的缙绅家婢,正如作者所云:“人之无良,舍其旧而新是谋,卒指巢覆而鸟亦飞,天之所报亦惨矣!”而在《武孝廉》中,石举人遽然离世或许也是命中该有的报应,功成名就后的他将妻子定性为“终非良偶”,妻子多次上门找他,他却置之不理,甚至想杀人灭口。看清他真实本性的妻子终于清醒,并收回当年救他的药,石举人旧疾复发,半年便卒。如此不仁不义者,虽处盛年,死有余辜。
(二)见金忘情之负心者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在《聊斋志异》中,却有这样一类见金忘情的男子,如《丑狐》和《云翠仙》中的穆生和梁有才,二人在金钱上的经历殊途同归——暴富或失财,二人的绝情也如出一辙——欲杀妻或欲卖妻,最终的结局都很凄凉——几代家贫或客死牢房。如《云翠仙》中的梁有才,一开始其秉性就被定格在寡福无行、心地轻薄的程度,之后嗜酒成性,最终因赌博而变卖妻子的首饰嫁妆,甚至有逼妻为娼的念头,可谓梁有才早已成为衣冠禽兽,当云翠仙认清了梁有才真实的丑恶面目后,愤然离去,而梁有才则病死狱中,以儆效尤。
(三)有始无终之负信者
小说中不乏玩弄女性情感的有始无终之徒,如《窦氏》中的南三复,出身晋阳世家,属于纨绔子弟,利用女子的情窦初开,在窦氏拒绝他的“捉臂狎之”时,他指天发誓,永生不渝。然而,当窦氏有了身孕,他却置之不理,仗势多金使他摆脱了法律制裁,但最终的惨死也是天意,爱情中若是掺杂欺骗与不道德,必然不值得怜悯。在蒲松龄眼里,这样的男子不仅在爱情里背叛了爱人,同样,在做人方面也违背了道德标准,理应受到惩罚。
(四)因孝逐妻之负情者
自古中国以孝为善首,但盲目为孝,却不见得是正确的选择。《珊瑚》中的安大成,面对其妻陈氏与悍谬不仁的婆婆之间的矛盾,非但不从中调解,反而鞭打憎恨她,将珊瑚逐出家门,最终娶了丑陋的恶媳妇,独自承受痛苦。然而这样盲孝休妻的安大成,在作者看来却是正义的,他认为“人以为孝友之报云”。事实上,是安大成欺善怕恶的本质,使其在家庭关系中不分是非,这不仅是不爱,事实上更是不孝。
三、 蒲松龄笔下的男性形象与其两性观
尽管《聊斋志异》爱情故事中的男子有着不同的经历和命运,但却基本有着共同的发展框架——书生在穷苦潦倒之时巧遇善良动人的狐女,二人你情我愿地陷入爱情之中,最终,狐女用自己的灵力帮助书生从举步维艰的境况中走出来。这正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蒲松龄的坎坷穷困个人生活,他对自身及士人阶层的理想构思,恰恰通过笔下的故事和人物逐一勾勒出来。古语有云,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因此可以说,这更是蒲松龄作为士人阶层的一员内心的渴求。
一方面,从科举考试的角度上看,《聊斋志异》的爱情故事里,许多书生的身份便是名落孙山之辈。如《青凤》中的耿生、《连琐》中的杨于畏等。他们绝大多数均未中过举,境遇穷愁潦倒,不少人流落他乡。同样,在很多故事的结尾中,那些正直真诚的书生往往会金榜题名。这与蒲松龄自身科举考试中的屡次失败不无关系,为官生涯的青云直上可谓他的毕生梦想,也因此,他笔下的正面书生形象都最终仕途圆满,如宁采臣进士及第和冯相如受领乡荐,可以说,蒲松龄将自己的未圆之梦在笔下人物的命运中得以实现,进而在幻想中肯定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其小说中的人物多少会带有蒲松龄自己的个性和意愿。在蒲松龄眼中,男子步入仕途,考取功名利禄才是真正的毕生所求,在他的很多故事里,女子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影射了他的希望,即在自己处于困境之时,能有贵人出手相助,以帮他平步青云。在这一点上,蒲松龄是秉承了传统两性观的,士人要通过科举实现自身价值,而女性似乎充当着辅佐的角色,无论在物质抑或精神方面。
另一方面,从爱情婚姻的角度上看,蒲松龄笔下投入爱情的男子不乏用情专一者,如《连城》中的乔生可以割肉相救和《鲁公女》里的张于旦,这些男子对爱人的不离不弃,使其终获良缘,是蒲松龄对爱情专一笃定的肯定,这从他赋予笔下在爱情中始乱终弃之男子或一败涂地,或门楣衰颓甚至患疾而卒的结局便可见一斑,这是他不忘初心爱情观的体现。除此之外,《聊斋志异》中共有38篇双拥故事,即男子同时拥有两位或更多妻妾一同生活。由此可见,蒲松龄是赞成一夫多妻制的,他的婚姻观仍受特定历史传统的束缚,毕竟很少有人能够跳出自身所处的人类发展阶段而超越历史。另外,也应看到,作为士阶层,在封建社会日益衰落的当时,蒲松龄同大多数士人一样,过着清贫不达的生活,空有一身才华和抱负,却无处施展。同时,自身的物质条件与其精神追求差距明显,当经济基础不能满足其精神需求时,以蒲松龄为代表的士阶层便开始在虚幻的世界中寻求宽慰,通过笔下幻想出的善良美丽的狐女等,来弥补现实中无力实现的一夫多妻生活。因此,在《聊斋志异》中,人与狐凄美的爱情故事在士阶层中才能够引起共鸣。
而蒲松龄看似矛盾的爱情观与婚姻观,事实上与其自身经历息息相关。每一位作者的创作,都难免有自己过去或现在的影子,同时,也会寄托自身的理想或信念。《蒲松龄集》里记载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位女子,其中,结发妻子刘氏与他相伴一世,患难之交陈淑卿与红颜知己顾青霞让他难忘惦念却不得相守,成为他心头永久的“两颗朱砂痣”。而蒲松龄执着笃定的爱情观,正是他对三人情感的外现,不会抛弃妻子,但对每一位都钟情可鉴。同时,婚姻中不能实现的一夫多妻是蒲松龄永远的心结,他渴望却又无能为力,因此,将这种婚姻的理想架构进笔下的爱情故事中,聊以慰藉心中遗憾。多妻的婚姻、忠贞的爱情似乎是蒲松龄真正希望拥有的两性生活,但封建士人阶层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或许也只有通过《聊斋志异》来偶尔逃避或放松,在这一点上,蒲松龄在封建士人中所引起的共鸣,可以说是其所处的阶层两性观作用下的结果。
四、结语
马克思曾写道,“有人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超人的存在,而他找到的,却只是他自己本身的反映”。这与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内心出发点与归宿点似乎不谋而合,通过他虚幻的人与狐等的爱情故事,将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寄托笔下,倾诉衷肠。而通过分析其爱情故事中的男性形象,可以观照到蒲松龄对士人阶层的同情与期冀,对科举制度的又爱又恨,以及对爱情和婚姻看似矛盾又不能摆脱自身局限的无奈与希望。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聊斋志异[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李厚基,韩海明.人鬼狐妖的艺术世界——《聊斋志异》[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李占鹏.论《聊斋志异》男性人物形象[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4]徐峰.《聊斋志异》中的“痴男”形象解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2).
[5]陈建萍.论《聊斋志异》中男性形象折射出的蒲松龄内心世界[J].蒲松龄研究,2009(4).
[责任编辑孙葳]
[收稿日期]2015-12-27
[作者简介]丁祥倩,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6)02-00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