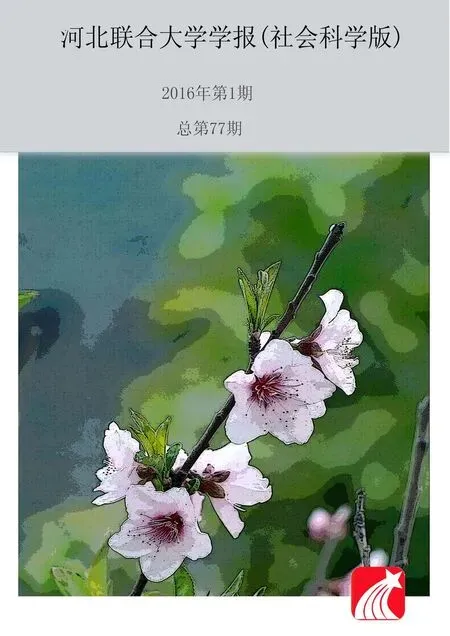莫里森《慈悲》中的圣经原型
苏娜
(长治学院 外语系,山西 长治 046011)
莫里森《慈悲》中的圣经原型
苏娜
(长治学院 外语系,山西 长治 046011)
关键词:原型;《慈悲》;自救
摘要:莫里森《慈悲》中的圣经原型数不胜数,它们丰富了作品内涵,人物形象。她用圣经故事的大气磅礴展示其笔下的小人物,突出小人物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中也可以成为英雄。同时她赞扬了黑人女奴在蓄奴制下的成长历程,精神面貌及自我救赎。证明黑人女性摆脱奴隶制阴影的方法就是自救,确定并保持自我黑人身份。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里森继《爱》出版五年后又推出新作《慈悲》,坚持其一贯风格,以圣经式的标题命名,以悬念的结局开头,篇幅短小,笔触细腻。评论家纷纷表示,说“莫里森更为明确地回归到蓄奴制撒下的痛苦之网,这一主题在《宠儿》中曾表现得如此令人难忘。”(“A Mercy”, 42)“神奇、神秘、难忘,莫里森围绕隐秘的和外显的慈悲,讲述了一则痛楚的寓言故事”(Carrigan 58);《华盛顿邮报》称该书是《宠儿》的“令人着迷的姊妹篇”(Charles BW 03);作家厄普代克称赞莫里森:“在这个处于原生状态、充满纷争的殖民地世界发现了诗意,”小说人物塑造方面“白人比黑人更加栩栩如生”(Updike 113)《人民》称该书“充满近似《圣经》的力量和优雅”(Leshko 49)。《慈悲》被《纽约时报书评》选为“2008年度十大最佳图书”之一。(“Best Book”)。王守仁教授从“超越种族”的角度解析这部作品中的“奴役”性,挖掘出莫里森在描写各色黑人悲惨生活背后的精神枷锁及其解脱之道。尚必武教授从创伤叙事角度探索黑人在身体与精神双重创伤下的生存之道。也有学者从身份构建角度分析等,笔者发现每个人物都离不开圣经原型的影子,所以尝试从圣经原型视角探析《慈悲》中人物的成长与自救。
一、麦瑟琳娜的征服:出埃及记
莉娜即麦瑟琳娜的缩写,表示一丝希望。在瑞典考古学家艾伦和塞西莉亚·科里尼(Cecilia Klynne)编撰的《古代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中记录了古罗马国王克劳狄乌斯的第三任妻子瓦莱利亚·麦瑟琳娜向罗马一个最炙手可热的妓女发起挑战:看谁能一口气应付的男人最多,最终麦瑟琳娜以坚持“25轮”的佳绩摘得“桂冠”,从此麦瑟琳娜便以女色情狂的形象闻名于世。莫里森借用这一名字取其“征服”内涵。
琳娜所在部族由于一场天花瘟疫几乎灭绝,使琳娜完全陷入“魔怪的形象”世界中,她想到上帝对她们的惩罚时,借用《圣经 新约》中启示录去描述这次灾难,是上帝把七个碗中的一个倒在地上对族人懒惰的惩罚。长老会救了琳娜,却将她投入另一邪恶世界中,他们充当了琳娜邪恶世界中一个极端的独裁领袖:“不能望着狂野为母亲或玩伴哭泣,烧掉了她的鹿皮裙,撤掉双臂上的珠镯,劈掉几英寸头发,不允许她出席宗教活动”。(Morrison 52)根据弗莱原型意义理论魔怪的形象,琳娜内心“表现被人类欲望彻底鄙弃的世界:是噩梦,劫难,奴役,痛苦,迷惘的世界”(Frye 208)主宰她命运的成为一帮“恣意逞性,排斥世人,干涉人间事务主要为维护自身特权”的人。这导致琳娜精神世界的崩溃,使她变得悲观,疏远又束手无策,最终做出麦瑟琳娜般的叛逆行为,被长老会变卖。老爷雅各布看到贴有“吃苦耐劳的女性,能做一切家务”时将她买来,生活在比较自由的环境中,琳娜开始找回自我,寻找一种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时她进入了“神谕的形象”世界中。她结合自己民族的习俗、医术、经文、口头传说寻找失去一切后的立足感、存在感,就像在伊甸园中的夏娃,将工作的场所神圣化,与自然界的飞禽走兽交流、唱歌以释放内心的孤独感。时光流逝,脑海中的“火”净化了她内心地狱魔怪形象,她能将生活打理地井井有条,帮老爷管理农场。靠自己的坚强毅力,克服创伤的记忆,重拾能力,重塑全新自我。
老爷婚后,她和太太成了好朋友,相互学习。丽贝卡太太认为她非常冷静,甚至料事如神:她一开始就看出老爷的悲剧结尾,弗洛伦斯的爱情悲剧,看出在老爷盖新房后愚蠢的一面,预感到铁匠到来的破坏作用,及老爷死后女奴们被迫离开过更惨生活的状况等。她能在下雪天帮受困即将被饿死的太太和孩子从冰层下捞出足够多的鲑鱼供她们食用。太太甚至称赞琳娜是“上帝”般的人。琳娜变化很大,因为她一直处于自我警醒状态,努力跳出创伤记忆得到精神自由。她是乐观智慧的人。正如出埃及记中的摩西,作为精神领袖能带领众人走出埃及、荒漠、冰川迈向流有蜜与奶的耶路撒冷。琳娜在家中充当了智者角色,走出自我困境,也帮助太太,弗洛伦斯、悲哀走出困境,收获精神自由。正如其名,不受男人奴役,不受悲伤记忆奴役,主宰生命,主宰自由。
二、丽贝卡受试炼:约伯记
小说设定时间在1680年前后,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清教徒受到严重迫害,教派纷争不断,宗教改革轰轰烈烈,对年纪尚小的丽贝卡产生了模糊却又清晰的悖论影响。模糊的是因其父母对宗教改革的狂热引起的争吵带给她许多困惑,她认为宗教是“由某种奇妙的憎恶点燃并维持的一团火焰”( Morrison81)似乎父母对陌生人的“点滴宽容都威胁着要浇灭”他们对宗教事务的狂热追捧。父母对宗教的偏执使丽贝卡心存偏见,在她看来“他(上帝)不过是个更大的王而已”“肤浅的教徒只需要一个肤浅的神,胆怯的教徒更喜欢怒气冲冲到处复仇的神”(Morrison81)清晰的是,王朝复辟与革命带来对清教徒的残忍迫害使她一生受到折磨与惊吓,诸如绞刑、分尸之刑,浸水之刑等,“成堆的扔在活蹦乱跳的脏腑被置于罪犯本人眼前,然后扔进框里,抛进泰晤士河;散落的手指抖动着寻找丢失的躯干;一个犯重伤罪的女人的头发在火焰中熠熠发光。”(Morrison 83)这些酷刑极刑使丽贝卡失去对宗教信仰的能力,并产生质疑。在亲情与信仰的背叛下,丽贝卡急切逃脱,希望找到救赎机会。
与雅各布结婚,成为她的唯一机会,融入到宗教信徒中,试图再次信任上帝时,他们“拒绝为她的第一个孩子洗礼时,丽贝卡转变了态度”(Morrison 86)她认为:“尽管她的宗教信仰很淡漠,但他们没有理由不保护一个婴儿使她免下永恒的地域啊”。(Morrison 86)为此,她痛苦、困惑、绝望。在第二次埋葬帕特里仙(第一个孩子)时,她守在坟前一整夜,谁都拉不走她,因为牧师和宗教信徒“剥夺了她孩子们获得救赎的权利。”(Morrison 87)只有异教的小玩意比祷告词更能安慰她的心,她甚至“说些亵渎神灵的话”。(Morrison 88)“我认为上帝并不知道我们是谁。要是他知道,我觉得他会喜欢我们的,不过,就我看,他并不了解我们。”(Morrison 88)她甚至怀疑她生的四个健康宝宝的四也与她对“上帝的关照并不那么感恩戴德”有关。她一再质疑上帝,宗教,决定不再去教堂。
失去孩子、丈夫让她反省,正像约伯记中的约伯受试炼,她忽然想到自己像个女约伯在受神的试炼,她的人生像约伯:一天之内失去了产业,儿女,一切,而且自己从头到脚都长了毒疮。在等待弗洛伦斯与自我冥想中,她忽然顿悟:“不是为了证明主的存在,也不是为了证明主的权能。他只是想引起主的注意。不在于被认为是高尚或可鄙,而是要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被制造和毁弃生命的那个主注意到。不是要达成某种协议,而仅仅是为了看到一线神迹的光亮。”(Morrison 101)她承认自己犯了罪,并为此受到惩罚,逐渐意识到,她整个生命就是“一条通往启示的道路上的一些驿站。”(Morrison 111)丽贝卡对宗教信仰经历了由提出质疑,到分析反省,回答得出结论的过程,渴望得到上帝关注,成为入选者这一过程。她主动积极回归信仰,但又将她投入另一极端。
病好后,她变得更加严峻,忧郁,把时间都耗在阅读《圣经》上。她又走入了类似父母般的极端:对上帝的狂热追捧。从欧洲到新大陆,宗教信仰一直是丽贝卡的精神牵绊与枷锁。表面看,丽贝卡的信仰失调是由于亲人的背叛与死亡造成的;深层次看,她是宗教狂热,迫害,王朝复辟残余影响的牺牲品。莫里森结合历史事件,及其给白人一代人的影响,从反面窥探黑人生活及精神现状。
丽贝卡在虔诚信教的背后“有某种冰冷或残忍”,她的变态地对待农场奴隶:不让任何人进入丈夫盖的豪宅,杂务变多,威拉德被卖,琳娜住在牛棚里等。“惩罚自己,惩罚每个人”。(Morrison 168)莫里森用微妙的笔触将殖民地社会变革带给被殖民地白人的精神枷锁间接产生对黑人生活的影响通过丽贝卡对宗教信仰的变化展示出来,对白人小人物的描绘入木三分,更从白人遭受精神痛苦来反衬黑人奴隶遭受白人精神痛苦与白人奴役的双重压迫,强化社会变革给黑人奴隶带来的强烈身心影响。莫里森以微观著、细腻、含蓄、聪颖地阐释白人精神世界的细微变化直接影响黑人奴隶的命运,牵一发而动全身。她将白人、黑人的琐碎生活细节相互结合,从丽贝卡白人视角叙述自身的苦楚,渗透黑人奴隶生活的无奈。白人尤如此,黑人何以堪。
三、弗洛伦斯的成长:天路历程
弗洛伦斯是整部小说的讲述者,小说第一、三、五、七、九、十、十一章都在写她的成长经历。她是老爷雅各布讨债时交换回来的,她的妈妈放弃她而留下弟弟在自己身边,把她给了老爷。因为母亲悯哈妹经历过非人折磨,亲眼目睹其他黑人女性奴隶的遭遇,所以她想保护自己的女儿免受其害。而她认为雅各布厌恶蓄奴制并不像其他主人一样邪恶,所以当雅各布要求悯哈妹做交换时她请求带走弗洛伦斯,这样自己的女儿或许还可以获得些许慈悲,不受白人奴隶主的非人践踏。
而这种行为对弗洛伦斯来说是一种抛弃,母亲选择了弟弟舍弃了她。这一取舍场景经常出现在她梦中、幻想与想象、甚至爱情中,无法摆脱阴影留给她的恐惧感,使她一直处于缺爱、缺乏安全感的不安紧张状态中。“在那些梦里,她总是要告诉我些什么。她从来都只把手伸给她的小男孩”。(Morrison 113)因此生活中的弗洛伦斯一直渴望得到爱,却不知如何去爱。铁匠的出现完全攻破了她爱的防线,她被铁匠完全吸引,她亲切地用心理距离较短的“你”称呼他,他就是她的“保护者”,“只有和你在一起,我才是活着的。”“你一走,我就枯萎了。”(Morrison 117)她心中母爱的缺失带给她的创伤让她这次要牢牢抓住她爱的人,但事与愿违。她不顾铁匠的感受,只顾自己一味追求,献身铁匠,“任凭自然生理的引力做主。”她成为爱情与铁匠的奴隶。当她去寻找铁匠的路途中,铁匠成为她的精神支柱,让她忘却路途艰辛,恐惧,勇敢走向铁匠,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而她一度膨胀夸大爱情的力量并在其中迷失自我。
所以当她看到铁匠收养的一个弃儿时,她立刻重归被抛弃的境地,敏感,容易妄想:“总是看到悯哈妹牵着她的小男孩的手斜倚在门边。”小男孩的出现给她造城威胁,精神危机,因此她与小男孩大打出手,失手将男孩胳膊脱臼。铁匠回来后朝她大嚷,打了她,赶走了她,并狠狠地侮辱了她:“是你自己变成了奴隶。你的脑瓜空空,举止粗野。你也是这爱情的奴隶。除了举止粗野,你一无所有。没有自制力。没有头脑。只要活着,只要呼吸,就自愿当个奴隶。”(Morrison156)铁匠是个自由的黑人,“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特别注重个体的独立自主。”在寓言中,“铁匠的职业要求他去锻造、塑造、修补他人的灵魂,充当一个挑明真相的人提醒被奴役者人性的觉醒。”(王守仁 吴新云 43)心灵备受创伤的弗洛伦斯沦为爱情与亲情的奴隶,被铁匠鄙视。因此,铁匠以语言、行为暴力给她以警告、提醒,希望她能从梦中清醒,面对现实,他认为奴隶也可以比自由人更自由。
铁匠充当了她的引路人,而弗洛伦斯当局者迷,不能体会铁匠的好意,用锤子打伤他。铁匠以某种方式延续了母亲的引导作用:母亲把孩子交给雅各布目的是为了让她摆脱作为一名黑人女奴的悲惨命运,希望她以某种方式自救,“有一天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Morrison180)而铁匠看到弗洛伦斯的执迷不悟,以爱的力量给予她教训,希望她清醒,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救赎者,只有精神自由身体才可获得自由。铁匠和母亲分别用爱情与亲情的力量保护弗洛伦斯,但这种保护太过复杂,含蓄,隐晦,使弗洛伦斯用血的代价才逐渐意识到。但这一切都是奴隶制下的产物,一个单纯的小女孩无法享受应有的亲情与爱情,悲哀至极。
在两位引路人的指引下,弗洛伦斯开始意识到:“失去你之后,我的路清晰了,我对你而言什么都不是。”(Morrison174)她脱下老爷的皮靴,赤脚走回家,她的脚由莉娜说的“没用的太娇嫩”的脚变成了“和柏树一样坚硬”的脚了。她意识到“奴隶。自由。我延续着。”(Morrison177)脚象征走路,之前弗洛伦斯急于穿“高跟鞋且很野”的鞋,太太扔掉的高跟鞋“一只高跟断了,另一只则磨破了”,所以她穿着走路蹒跚,踉踉跄跄,需要人搀扶,象征她没有独立思想。母亲的抛弃使她永远都无法穿上母亲亲手为她做得鞋,受困于过去带来的缺失,无法正常生活。更加剧她心理的自卑与胆怯,但当她勇敢地用不穿鞋的脚走回家,一路的成长与反思使她顿悟,思考铁匠的话,母亲的舍弃,并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学会独立思考,理解,忏悔。归乡途中,她好似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遇到坎坷,但坚强,自信,虔诚。
四、“悲哀”的重生:耶稣复活
“悲哀”座得船遇难,但由于脖子上的疖子被带到手术室,用鸦片止痛,醒来后船上的人几乎都遇难了。她关于家的唯一记忆就是那艘船。被救后,又遭人凌辱强暴。痛苦的记忆使她精神失常,失忆,总是四处游荡。被老爷带回家后,她被太太、莉娜孤立,排斥,孤独寂寞使她产生幻觉妄想,另一个自己“双胞”成了她的好朋友,倾听,给予安慰。她的第一个孩子溺死后,痛苦不堪,她“永远都忘不了她的宝宝没日没夜地呛着水。”表面看,悲哀痛苦,艰辛,孤独,深层次看,她渴望找人倾诉,有人帮助。面对一切恐惧,悲哀只能将其内化给另一个自我,双胞成了她内心世界的独白,她用自我独白的方式排解创伤。外界对她来说太可恨,太可怕,所以她将自我紧紧包裹,封闭内心世界,不肯交朋友:“每个女人都禁锢着自己,各自织着思绪的网,不向别的任何人吐露。”(Morrison148)直到她再次陷入无助状态,面对临盆,她“一筹莫展”,双胞不在,她缺席一切重要且需帮助的场合,“奇怪地沉默或不友善。”(Morrison146)因此第二次生产成为她释放自我的重要契机。她“抱着一丝微弱的希望,想到威尔和斯卡利,并及时向他们求助,顺利生产。她独立完成救助并生产这一过程,看似虽小却救了自己和孩子的性命,使她重获自信:“她独自完成了一件事,一件重要的事”。(Morrison147)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改变了“悲哀”的思想,从“悲哀”到“完整”就是重生的过程。此后,“双胞”走了,“悲哀”也停止了游荡,她能正常面对生活中的琐事,给自己重新命名为“完整”。悲哀如同死而复生的耶稣,重获生命的同时也重新获得精神自由。
五、结语
《慈悲》可谓就是一部改编版《圣经》,除去以上的四个原型之外,还有悯哈妹的忏悔:启示录;雅各布的毁灭:失乐园等。莫里森能工巧匠般的将二者紧密相连,细腻、含蓄、大胆地展现奴隶制下黑人女奴的悲惨命运及其精神痛苦。用圣经故事展示黑人抗争的大气磅礴,但其笔下却是生活中的小人物,莫里森重在用圣经故事中的英雄人物类比她笔下的小人物,突出小人物在自己生活的世界中也可以有大作为,她们生活中的一丝顿悟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她赞扬了黑人女奴在蓄奴制下的精神面貌,成长历程及自我救赎过程。并以此告诉所有黑人女性:唯一可以摆脱奴隶制阴影的方法就是自救,只有自救黑人民族才有未来,才能确定自我身份,立足美国社会。
参考文献:
[1]“A Mercy” Publishers Weekly 255. 37 (15 September 2008).
[2]Carrigan, Henry L “A Mercy” Library Journal 133 17 (15 October 2008).
[3]Charles Ron “Souls in Chains” Washington Post (9 November 2008).
[4]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5]Leshko, Adriana. “Exploring Slavery’s Tangled Root” People 70 20 (17 November 2008).
[6]Morrison,Toni. A Mercy.New York:Alfred A.Knopt, 2008.
[7]Updike, John. “Dreamy Wilderness. Unmastered Women in Colonial 8.Virginia” New Yorker84.35(3 November 2008):112-113.
[8]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1994.
[9]王守仁,吴新云.超越种族: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奴役”解析.当代外国文学, 2009(2).
Abstract:There are enormous biblical archetypes in A Mercy, which had enriched implication of the work and individualization of characters. Morrison borrowed epic-like biblical heroes to exhibit the nobodies in her work, and embodied that even nobody could become hero in their own world. Besides, she eulogized the experience progression, spirit performance and self-salvation of the black women under the mercy of slavery. She indicated that their only way to ensure identification is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black identity.
Biblical-Archetype Exploration of A Mercy by Toni Morrison
SU Na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of Changzhi University, Changzhi Shanxi 046011,China)
Key words:archetype, A Mercy, self-salvation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708(2016)01-01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