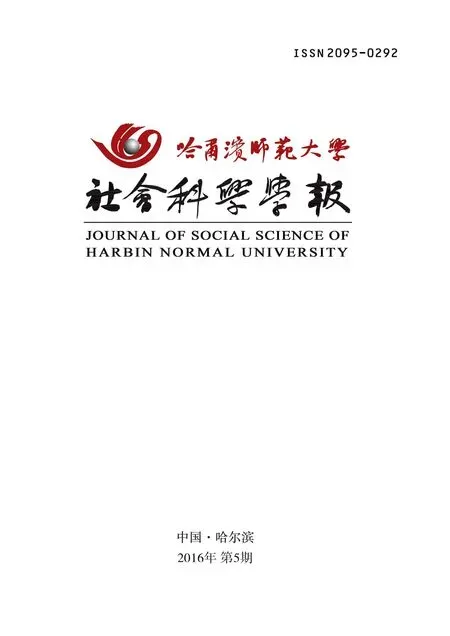诗论·诗心·诗学——也评林庚的《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
刘海英
(1.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世界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871;2.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外语系,北京 100083)
诗论·诗心·诗学
——也评林庚的《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
刘海英1,2
(1.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世界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871;2.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外语系,北京 100083)
林庚是学者型诗人和诗人型学者,他以写作新诗为起点,踏入中国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他在《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一书中所提出的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等理论观点,既与他的新诗创作实践经历密切相关,也是他凭诗心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细致研究而得来的创见,是一项重要的中国诗学研究成果。
林庚;《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新诗格律;新诗创作
林庚(1910-2006年)历任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出版过多部中国文学论著。出版于2000年的诗论集《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体现了他六十多年来关于新诗形式和语言问题的基本理论构想。国内学者对林庚的新诗理论多持高度肯定态度:郭小聪认为,林庚通过对几千年诗歌发展史的宏观考察和微观透视,得出“诗歌从散文化走向新的诗化乃是新诗发展必由之路”的重要结论[1](P338);钱志熙认为林庚的诗学是真正的诗学,他的文学研究以文学的创作活动的存在为基础[1](P340-341);钟元凯写道,林庚关注的焦点是诗歌语言的解放之途,他提出“诗歌语言两度解放”的命题,该命题的重要性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1](P96)。但是,林庚所倡导的九言诗和十言诗等形式在中国现代新诗创作史上并未得到普遍应用。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林庚新诗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他的观点有何理论渊源;他的新诗理论在中国诗学史上重要性如何,有无可供商榷之处。
一、诗论:林庚新诗理论的主要观点
林庚新诗理论的第一个要点是诗歌本体论。他认为,诗歌要“凭借语言来突破概念,表达出高于生活语言的一种境界……但是,诗歌语言不能脱离生活语言,诗人的思想感情是建筑在生活之上的”[2](P169)。好诗就是“新鲜”的诗,“要新鲜得像刚生长出来的果子那样有一种新生命的力量,透着朝气才好。文学艺术要的就是这个,比的乃是谁更为鲜气扑人”[2](P171),而那些“不能使人精神奋发”[2](P174)的诗,便不是好诗。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自由诗,自由诗便是成功的诗歌体式,它能“通过诗歌语言跨度上的自由,解放了诗人的冥想力与思维敏感的触角,因而又重新获得诗歌语言的飞跃性、交织性、萌发性,这些诗的艺术特殊功能,其功是不可没的”[2](P170)。
关于诗歌的语言形式,林庚认为,既然诗歌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新鲜感觉,新诗则有存在的理由,但是新诗的语言必须防止走向散文化。他提出,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根本区别,在于散文是“有着更多的逻辑语言……诗歌语言乃是更灵活更富于飞跃性的语言”[2](P67),只有当诗人使新诗的语言具有这种特征时,才能在对事物抱有新感觉之时,不但能够及时捕捉住这种新感觉,而且能用诗的语言将自己的感觉表达出来,让读者也有同感,这样的诗才是成功的新诗。自由诗必然走向新的格律诗,因为自由诗对于传统的文言诗坛而言也如同是一场革命,新诗要想“走出困境,就需要面对散文规范性的压力建立起自己的语言规范化来,这也就是格律,也就是诗歌的阵地”[2](P目录前19)。只有这样,诗歌才能“自由地运用散文所不能有的语言跨度”[2](P目录前19)。因此,自由诗“不是天生与格律诗成为对头的,格律诗所想保证的正是自由诗所要取得的语言上的自由,而自由诗所唤醒的久经沉睡的语言上的艺术魅力也正是为格律诗的建设新诗坛准备下丰富的灵感”[2](P目录前20)。
林庚由此提出以“五四体九言诗”为核心概念的新诗形式理论。九言诗的“五四体”是指一种九言诗行,在一行之中它的节奏分为上“五”下“四”,“五”与“四”各代表着白话与口语的一般性,这便都统一在口语的发展上[2](P47-52)。他关于这种新诗体的意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要寻求掌握生活语言发展中含有的新音组。在今天为适应口语中句式变长的情况,新诗应以四字、五字等音组来取代原先五言、七言中的三字组,正如历史上三字音组曾经取代了四言诗中的二字音组一样。第二,要服从于中国民族语言在诗歌形式上普遍遵循的“半逗律”,也就是将诗行划分为相对平衡的上下两个半段,从而在半行上形成一个类似“逗”的节奏点,每个诗行的后半截,林庚名之为“底部”,底部如何配置,意义重大。第三,要力求让这个节奏点保持在稳定的典型位置上。如果它或上或下、或高或低,那么这种诗行的典型性就还不够鲜明,这个典型位置必须保持稳定[2](P5)。以现代汉语为基础,致力于语言的诗化,以建设新诗的格律,这就是林庚新诗理论的核心观点。
汉语诗格律的基本要素是停顿,中国古代的五言诗、七言诗字数不同是形态上的区别,更深一层是因为汉语有不同的停顿方式,能形成反复轮替的节奏感。格律诗的关键是要建立典型诗行,即普遍的、有节奏的、具有跳跃能力的、有助于跳跃的诗行。这种诗行能使人产生期待感,有一种后浪推前浪的效果,这种诗歌形式“不是对于内容的束缚,而是有助于内容的涌现”[2](P目录前26)。诗歌形式是基于一种有规律的节奏感而产生的,韵脚是隔着一定距离而一次一次出现的,这就要求诗行有一定的长短,因为诗行的长短正是韵脚与韵脚的距离;这距离愈均匀,韵就愈自然,愈有魅力。建立这样的诗行,就是诗歌形式的中心环节。诗歌节奏的形成有赖于诸多因素的协调,比如,押韵、平仄、停顿、轻重音、不同长度的音节的使用等,但是,只有找到典型的诗行,其他相关因素才能有所附丽。钱志熙将林庚关于典型诗行的观点概括为两个要点:一是每句相对固定的字数,其中,九言体被唤作“林庚体”;二是诗行中固定的音组与逗律的确定,即“五字音组”和“半逗律”[1](P342),这是有道理的。
二、诗心:林庚新诗理论的思想来源
林庚的新诗理论研究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的新诗创作实践,二是他的古诗研究工作。
林庚的新诗创作实践是他进行新诗理论研究工作的起点。他从没有将写诗与研究诗歌当作两件事情来做,他始终将二者结合为一体。他在《问路集·自序》中写道:“我写新诗是从自由诗开始的,自由诗使我从旧诗词中得到一种全新的解放,它至今仍留给我仿佛那童年时代的难忘的岁月。当我第一次写出《夜》那首诗来时,我的兴奋是无法比拟的,我觉得我是在用最原始的语言捕捉了生活中最直接的感受。”[2](P3)这等于是说,他对诗歌的本质的看法,来自自己的诗歌写作实践,正是因为他自己在写诗的过程中亲身体验到一种新鲜的感受,他才在新诗理论中将这种“新鲜”的感觉,作为评判诗歌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林庚的新诗理论是建构在他的实践写作经验基础上的。他于1935年尝试写新格律诗,“对于新诗格律方面还真没什么很具体的方案,只是通过创作实践来不断地摸索而已”[2](P15-16)。当他提及典型诗行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典型诗行乃是建立诗行的理想目标,它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两三个或者更多些,过去我曾经推荐过九言诗行,并且我相信十言(五五)、十一言(六五)也都很有希望;现在我愿意推荐一种走向典型诗行的过渡形式,正像“楚辞”一样,只遵循“半逗律”先取得基本节奏,建立起一般的节奏诗行来,我们无妨称这个为“节奏自由诗”。例如:
春天的蓝水奔流下山,(五四)
河的两岸生出了青草;(四五)
再没有人记起也没有人知道(六六)
冬天的风那里去了(四四)
这里仿佛还是自由诗,实际上却是具有了“半逗律”的节奏诗行,这种节奏感将会有助于从自由诗发展而成为格律诗。实践比空论更为有益,我们如果能及早进入写作的实践,再从实践中取得进展,也许会比只一味在理论上争辩要来得更好些。[2](P75-76)
此即,林庚的新诗理论并非空穴来风,他将写诗实践的重要性置于理论创新上,他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诗歌的最佳形式。或者说,他的新诗理论也指导了他的诗歌写作实践,他的有些诗就是为了进行九言体的试验而写的。林庚在《我的楚辞研究》中曾经写道:“我这人是兼差的,一方面搞文学创作,一方面讲中国文学史。我在写文学史的时候总想着新文学的发展,总想为新文学找一些可以参考的经验。”[3](P21-22)林庚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始终执着于新诗的发展方向,执着于探讨新诗的形式问题,所以在新诗形式方面能够不断提出新的理论见解。
另一方面,林庚擅长从古代文学(主要指古诗)中寻求新诗的出路。他于1994年6月5日作《悼念组缃兄》一文中写道:“六十年漫长的岁月过去了,我们走的是一条道路,都以教学为业而心在创作。”[4](P17)林庚付出毕生的精力,要为中国新诗找一条路,创造新的诗歌形式,他的文学史研究正是通过寻求中国古人的经验与教训,来寻找新诗的发展道路。他认为,新诗可以从古诗中寻求到最佳形式,而且新诗可以借鉴古诗的艺术性,如它的飞跃性、交织性,即各种形象互相的交织等[1](P384)。他写作《中国文学简史》时有两个考虑:一是为了沟通新旧文学的愿望而写;二是为了探寻文学的主潮,参照过去文学主潮的消长兴亡来寻找我们今后的主潮。《中国文学简史》是以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史,以文学的创造性为中心,哪个时代创造性最强,他就关注哪个时代。林庚的心在创作,他关心文学创作的奥秘,主要是新诗创作的奥秘,搞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创造性。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终极目标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学。
林庚由写新诗到研究中国文学史,目的是为了将新旧文学沟通起来;他从写旧诗到写新诗,由写自由体新诗到写新格律诗,都是为了沟通古今文学,而沟通正是创造的前提,是创造的第一步,学古诗不是为了模仿,而是揣摩其内在的规律,学其精髓,以便发展新时代的新鲜诗作。
三、诗学:林庚新诗理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
林庚既从古诗中吸取营养,又充分借鉴外国文艺理论,他从创作新诗的目的出发研究古诗,在探寻古今诗歌创作规律的同时,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新局面,他的新诗理论推动了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林庚作为诗人学者,能够充分运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他考证楚辞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对句、词的考订从不脱离对作品贯通的理解以及对诗人思想的准确把握。同时,他在言说自己的新诗理论时,也能将古诗实例信手拈来,用以论证自己的观点。比如,在《关于新诗形式的问题和建议》一文中,他为了说明过时的诗歌形式仍会偶然出现于优秀的作品中,举曹操的《短歌行》和陶渊明的《时运》为例,来说明中国诗歌史上四言诗虽然在建安时期已经过时,但仍存在四言佳作[2](P63-64)。类似的写法在林庚的文章中多次出现,足以说明他对中国古代诗文的娴熟程度,而且他始终将古文研究成果,用于阐述他的新诗理论。
他不但精熟于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等三种方法,而且较早地借鉴外国文艺理论来研究古代诗歌,因而能在诗学的宏观思辨方面站在同行的前列,以其新颖而富有生气的创见引导和启发着一代学人。厦门大学版《中国文学史》全书分为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夜时代等四编。林庚在《中国文学简史》(上卷)的后记中写道:“《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是参照苏联《十一世纪至十七世纪俄罗斯古代文学教学大纲》拟定的,当然结合着中国古代文学不同的内容……《苏联教学大纲》中所贯彻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的自豪感,历史主义的论述与民主成分的发扬,以及民族形式与文艺风格的具体分析,正是本书努力的方向。”[5](P385)
林庚对于西方文艺思想并未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比如在探讨诗歌建行问题时,他仔细辨析了西洋诗歌音步不适用于中国诗歌的具体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我们民族形式的诗歌建行规律,即“半逗律”[2](P72-73),认为既然诗歌是最单纯的语言艺术,这语言的土壤就特别重要,新诗要发展,自然要首先根植于自己的土壤上[2](P2)。近代中国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潮流中,林庚早年所处的清华大学,也是这股潮流中有力的弄潮者,具备推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有利条件。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激进派排斥中国传统文化,视西方自由诗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林庚却坚持认为“全盘西化”在新诗创作中行不通,认为用中文写诗就必须遵从汉语的特点。他依据对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精到研究所提出的新诗理论,是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
中国的新诗还处于发展阶段,林庚的九言体诗及相关理论目前并不能成为现代诗歌的普遍形式,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林庚运用中国古诗的发展历程来论证和建立新诗理论的努力,也并非没有不妥之处,毕竟文学艺术不可能按照一条逻辑线索构筑它的发展历史,古诗的格律特征未必就能用来说明新诗格律的必要性。他从古诗中得来的“半逗律”诗论,虽然解决音顿的问题,它作为诗歌语言形式的一种理论,却不能不建立在诗歌语言意义的基础上。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是诗歌创作实践的基本要求,但对于新诗理论,则无异于真正的“镣铐”,不能达成林庚提出的使诗歌得以自由、脱离束缚的理想。若使新诗既具有诗化的语言,又能自由地表达诗人的新鲜情感,九言诗行或十言诗行不得不越来越趋向于口语化,成为一种新式民歌,其原因不但在于今天的生活语言与唐代的生活语言有着诸多明显的差异,而且因为古代社会在今人眼中,本身就具有素朴的诗意,这种由距离而产生的美感,是无论何种韵律或节奏都无法弥补的。
林庚的诗论根植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他并不视诗歌理论为第一要义,他的理论篇章同时具有诗歌作品的感情充沛、立意新颖等特征,却仍难免在立论和论证方面存在不足。林庚与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对于诗歌形式建构的主张一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放现代格律诗思路的作用,但中国诗论者和诗歌创作者们对于新诗格律的思考与构建工作,还在进行中。
四、结语
林庚身兼诗人与文学史家两种身份,长期坚持一边创作新诗一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为诗人所具有的敏锐的感受力、想象力和活跃的灵感,与作为文学史家所具有的理性逻辑思维能力、概括和分析能力,在林庚那里,得到恰当的统一。林庚是一名学者型诗人和诗人型学者,他的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等理论观点,既是他的诗歌创作经验的升华,也是他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细致研究而形成的创见,是中国古典文论现代化转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林庚探索诗艺的孜孜以求精神,将永远鼓舞着一代学人,他以学者的睿智和诗人的情怀来关注诗歌原始意义的努力,必将为我们唤起生命觉醒的力量。
[1]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诗歌中心. 化雨集 [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林庚. 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 [M] .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3]黄中模,王雍刚. 楚辞研究成功之路——海内外楚辞专家自述[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4]《吴组缃先生纪念集》编辑小组. 吴组缃先生纪念集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林庚. 中国文学简史:上卷[M]. 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责任编辑 孙 葳]
2016-06-20
刘海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诗歌、西方诗学与比较诗学。
I207
A
2095-0292(2016)05-014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