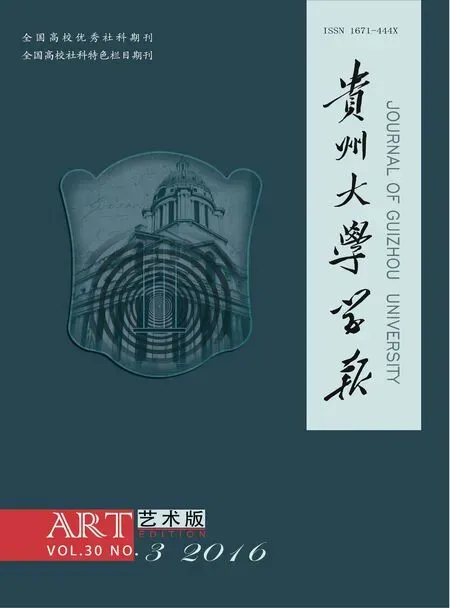曹禺:“中国的易卜生”之路
洪忠煌(浙江传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曹禺:“中国的易卜生”之路
洪忠煌
(浙江传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曹禺是“中国的易卜生”,堪称“中国现代戏剧之父”。文本分析支持这一结论。个性化人物的自我内心剖析、基于“理想与现实”悖论的人物关系格局、复式戏剧结构、戏剧性口语、诗的意象诸剧作元素之综合所表现的现代性,是曹禺受益于易卜生而具有迥然不同于其话剧前辈的开创性之所在。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青年戏剧大师经典,“曹禺三部曲”构成了浓缩版的“易卜生之路”。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素,“中国的易卜生”之路的迷茫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反思与教训。
曹禺;易卜生;现代性
DOI:10.15958/j.cnki.gdxbysb.2016.03.011
曹禺话剧创作所受的西方剧作家的诸多影响中,易卜生的影响无疑是最显著的。曹禺曾自述其西方戏剧宗师,易卜生居于首位,其次才按顺序为莎士比亚、高尔斯华绥、奥尼尔、契诃夫。这当然不是唯一的根据,在本文将要展开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本分析支持如下的结论:曹禺主要是受益于易卜生而在中国话剧中取得了类似易卜生在世界戏剧中所占的地位。众所周知,易卜生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
与其说曹禺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不如说曹禺是“中国的易卜生”更为贴切。一个最突出显眼的比较是,曹禺戏剧结构显然师法从古希腊悲剧到易卜生的“锁闭式”、“回溯式”的西方近现代“写实剧”的结构模式,而非莎士比亚那种巴洛克“开放式”的广阔多变的叙事体史诗戏剧结构。再者,以戏剧艺术中其重要性仅次于结构的戏剧语言这一要素进行比较,也可看出,曹禺剧本所用的戏剧语言也显然是接近易卜生、奥尼尔那种简短有力、富于潜台词和“弦外音”的活生生的现代人的口语,现代人的对话,而非莎士比亚式的华丽夸张、词句复杂的诗剧语言——肖伯纳以其透辟论调一语道破称之为“已经死去的语言”(见于《莎士比亚与电影》一书),——除了根本不能算是成功的《王昭君》这一例外(曹禺在这一“应周总理遗愿”而写的遵命之作中似乎在有意识地尝试运用莎士比亚式的诗剧语言)。
不错,曹禺在20世纪40年代曾应张骏祥提议翻译了莎翁名剧《柔密欧与幽丽叶》。但翻译是一回事,作家自己的创作道路则是另一回事,尤其是戏剧创作——正如我在一文中指出的那样,中国话剧主流并未接受莎士比亚影响,或者主要不是在莎士比亚影响下发展的,曹禺亦不例外;何况其时(译莎剧时)曹禺在自己创作生涯中已越过了 1930年代的创作高峰期。
曹禺的早年学养中最突出的耀眼处,也是易卜生剧作对他的滋养:“南开之花”(作为新剧团演员)万家宝不但粉墨登场扮演易卜生剧中女主角娜拉,而且熟读了其导师、戏剧引路人张彭春赠予的《易卜生全集》。这些事实对曹禺成才和他走上戏剧创作道路所起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从曹禺早年的习作中,例如他最早发表的小说《今宵酒醒何处》中,所透露的近现代文学倾向也昭示出:这位未来的青年剧作家主要是被19世纪下半叶以降的西方文学思潮激发灵感的,他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着力描绘纸酔金迷中的墮落女性,——这自然使我们联想起后来曹禺塑造的剧中人物陈白露(竹筠),——从中盈溢出感伤气息和诗意。显然,曹禺最初的创作冲动和文学憧憬,不是指向文艺复兴时代的莎翁,而是指向现代社会生活、指向易卜生和莫泊桑等现代作家的。
文革以后,中国学者注意到国外曾有报道曹禺在文革中的遭遇,西方媒体指称这位“中国的莎士比亚”在被指派看传达室云云。于是近年来学界就大张旗鼓地顺势赞誉曹禺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其实,媒体所谓“莎士比亚”可能只是泛指杰出戏剧家的一般喻义代词而已,犹如称某影星为“中国的嘉宝”、某某滑稽戏演员为“中国的卓别林”之类,并非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角度的指认;若以这种泛指意义上的称谓来代替严肃的学术研究,长此以往,也无助于准确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实足以对年轻人起误导作用。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相对确切的指认应该是:曹禺是“中国的易卜生”,曹禺堪称“中国现代戏剧之父”。至于易卜生与莎士比亚,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具有各自代表性的西方伟大戏剧诗人,则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将曹禺比喻为“中国的易卜生”,比之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丝毫没有贬低的意味,——难道你以为“与易卜生相比”对一位戏剧家而言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吗?这就看你是否明白易卜生的份量了!——恰恰相反,这才准确地凸显出曹禺在中国话剧中的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及其所具有的导向意义。
一、从剧作诸元素看现代性
在《雷雨》问世(1934年剧本发表、1935年首演)之前,中国话剧舞台上尚未出现独具个性魅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这里是指由新文化运动所催生的、在20世纪20年代渐趋活跃的“白话剧”,即已摆脱“旧剧”(戏曲)束缚的有别于文明戏的“现代话剧”,当然更遑论文明戏了;在曹禺之前创作了第一批产生较大影响的话剧的田汉、熊佛西等人(即被公认为“现代话剧奠基人”的),所能提供给观众的,或是沉湎于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和感伤情调中的不幸男女(《湖上的悲剧》)和遭恶势力迫害的艺人(《名优之死》),或是有变态心理的刽子手(《王三》),多以其事感人,却没有一个是有丰富复杂的独特性格、足以如同活人那样揪住观众心灵的“个性化人物”。事实上,《雷雨》之前的话剧人物,基本上都只是一个剪影、一个侧面造像、或是剧作家意念的形象化而已。这种状况直至《雷雨》公演才彻底改观,竟然有女观众给青年剧作家曹禺写信倾诉自己感受剧中蘩漪那样的苦闷心情,——这位署名“竹筠”的女士显然是把蘩漪当作实有其人的同病相怜者(活人)来看待的!
这种能唤起观众想见其一举一动、体认其实际处境而感同身受的剧中人物,就是这里所指的“个性化人物”。这是曹禺使中国话剧别开生面的显著贡献,我们有理由把他这种在话剧舞台上创造“活人”形象的功力,联系到易卜生对他的决定性影响。
让我们就从这一点切入,考察曹禺怎样“师承”易卜生而赋予话剧(中国现代戏剧)以“现代性”。下文从戏剧创作的五项元素来逐项展开,以追踪曹禺的创作思维,从中发现他师承易卜生的若干轨迹。
(一)个性化人物的自我内心剖析:潜意识表现与理性批判的结合,理想与现实的悖论
在《雷雨》中,观众叹为观止的是这样一些“瞬间”(场面):戏刚开场不久,鲁贵“说鬼”,他对女儿描述自己于深夜窥探到的这家在传统道德笼罩下的公馆秘密,男女二鬼紧挨着偷情,却被一声咳嗽惊得倏然分开,从此那位精明的太太就对这个老仆人有所忌惮了。还是在第一幕,老爷好意劝太太喝药,按照传统道德规矩责令两个儿子依礼节尽孝心,却在老爷无意中一步一步逼到继母面对长子向她下跪的尴尬,终致蘩漪忍无可忍而感情爆发。上述这两个场面,都是极其精湛地刻画出女主人公的不受理性控制的潜意识冲动:幽会中害怕秘密暴露而意外受惊,私密亲昵关系却被拘囿于旧礼教的令人难堪的规矩中!这里,剧作家对外在社会环境的彻底的理性批判,是通过人物内心的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来呈现的。这就使得处于外在社会环境中的人物自我的个性被激活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充满欲望和情感的受压抑女性的活生生的形象呼之欲出!
不仅如此,剧作家还让人物看似矛盾的失控举止在舞台上展露得淋漓尽致:蘩漪深夜冒雨跟踪周萍到鲁家,对他与四凤的幽会施展毒招,从屋外把窗户关紧以给鲁大海入内将他“打死”提供机会;这个疯狂报复的阴鸷女性却又在绝望中表现出极端软弱、“委屈求全”的一面,她跪求大少爷在带走丫头时也带上她,她愿“和四凤住在一起!”这里不仅是潜意识表现,而且是自我的人格分裂,是一种可以称之为“理想与现实的悖论”的内心状态在极端情况下的披露。
这种体现“悖论”(自我分裂)的极端表现在其它人物、乃至在“曹禺三部曲”的其它两部(《日出》和《原野》)中也有,只不过有着发展程度和力度的差异,而蘩漪这个人物是曹禺最大也最成功的创造。其它的可以略举数例:周冲是那样倾心四凤,可是一旦面对哥哥要把她带走,却又恍然若有所悟地觉得自己仿佛并不真爱四凤。而这立即遭致蘩漪大骂“你不是我的儿子!”可是转眼间站在亲子被雷电烧焦的尸骸旁边,她又转而痛责自己并数落亲子“你有了这样的母亲,你该死!”这种体现“悖论”(自我分裂)的潜意识表现,是那种拘囿于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的直线式创作思维所无法理解的。
应该说,潜意识表现早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乃至其他“前现代”的伟大作家作品中已有了,“个性化人物”也是如此;但是体现理想与现实的悖论的自我分裂、内心剖析,到了易卜生戏剧中得到集中运用,则是易卜生在世界戏剧中开创现代戏剧的划时代的艺术创造,是“现代性”的最突出标志。如果说莎士比亚戏剧中描绘人物个性的潜意识表现,主要是通过大开大阖、大起大落的情节线,造成惊心动魄的内心冲突场面(例如麦克白夫人“梦游洗手”、奥瑟罗拉伊阿古“同跪起誓”),那么易卜生开创了那种以凝炼的细节、以仿佛不经意间发生的几乎不易觉察的细微动作所表现的内心潜意识活动,发挥了同样甚至更巨大的震撼人心的效果:只要想一想《群鬼》剧终阿尔文夫人面对儿子欧士华突然失明的瞬间台词“太阳。太阳”,想一想《海达-高布乐》女主人公将曾经的情人与情敌合作写成的书稿(遗失落入她手)慢慢地投入火炉,喃喃自语:“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烧你们的孩子。”就可以体验到向观众披露自我内心隐秘冲动的特殊人物个性,那种惊人的震撼效果!
正是这种于细微处产生震撼效果的细节创造,使曹禺剧中的个性化人物栩栩如生;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位青年剧作家受益于易卜生,抓住了现代人的脉搏和自我内心的潜意识冲动,——这种自我剖析折射出了现代人的焦虑、现代社会的理想与现实的“两难”选择。
(二)人物关系的设置:悲剧性悖论(冲突)的祭坛格局,其中除了体现“理想与现实”悖论的自我分裂的系列人物之外,还少不了充当献祭品的无辜牺牲者
与上述个性化人物紧相联系的是,“曹禺三部曲”中引人注意的人物关系格局,恰好形成了“理想与现实”悖论,即悲剧性冲突的祭坛。《雷雨》女主人公蘩漪及其亲子周冲是剧中最炫目的理想的亮点,这种形象符合曹禺自述的蘩漪具有“最雷雨”的性格,而周冲在某种程度上堪称剧作家的自我投影,——这两个人物据曹禺自述是他创作构思中最先出现的人物,事实上也是整个“雷雨”的总体戏剧意象的核心。围绕着蘩漪的自我分裂、内心冲突,引申出移情别恋却又自称“我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的大少爷周萍,以及他爱过的继母的情敌四凤,这一对青年男女也同样在“理想与现实”悖论中煎熬。作为这对恋人遭致毁灭的道德现实(由传统道德积淀而成的宿命力量)的体现,又引申出上一代的同样经受过悲剧性悖论煎熬的“少爷与女仆”——如今的老爷周朴园与鲁妈。这样就形成了以蘩漪为中心枢纽的、代表过去与现在两个悖论的双三角人物关系,如同一个悲剧命运的祭坛,成为支撑起《雷雨》全剧的框架。(至于周冲在戏剧结构中所占的几乎与其母亲同等重要的核心地位,我们留在第三项剧作元素中展开论述。)
在《日出》与《原野》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人物关系格局。《日出》中最先出场而又最后“淡出”的、仿佛与剧情进展无甚联系的人物方达生,在剧作家构思中决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正是他(以及未出场的早已死去的“诗人”)与女主人公陈白露(竹筠)构成了剧中“理想”的亮点,与陈白露遥相对应的还有第三幕下等妓院内“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的善良妓女翠喜。陈白露在此剧构思中就是被置于这一“系列人物”与他们的对立面、高等豪华旅馆内的形形色色“大鱼吃小鱼”系列人物之间,展开“理想与现实”悖论的内心搏斗,终于在“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的诗句忆诵中离开人间。只有从体现这一悲剧性悖论的自我分裂、内心冲突着眼,我们才能理解陈白露之死,正如曹禺所述,最后她不是活不下去,而是不想活了。——须知陈白露不是为苟且偷生而活着的!《日出》是个悲剧性悖论的祭坛,《原野》也是。仇虎带着花金子逃进原始森林,这一对传奇式恋人终于在复仇后奔向那“黄金铺地的”理想国;他俩除了面对那个恶毒的瞎婆子,还要挣脱各种“阴间”系列人物的无休止纠缠,这就是此剧的悖论祭坛式的人物关系格局。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青年曹禺熟悉的易卜生戏剧。这里只是略举数例,我们就可以看到易卜生首创的在“理想与现实”悖论中煎熬、挣扎的悲剧命运祭坛,看到在这祭坛上的人物关系设置。《群鬼》中的阿尔文夫人坚持一生尽到“责任”,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欧士华(成长为画家)身上,儿子成才回家后却给她呈现死去的丈夫生前那“快乐”的一幕(与女仆调情),而现今与儿子相恋的年轻女仆却正是丈夫留下来的“同根之苗”,丈夫的另一“遗产”则是在儿子脑中发病最终致盲的梅毒。“上一代人造孽而由下一代人还债”的人物关系格局,显然给青年曹禺带来了灵感!《野鸭》中本已安于现状的照相馆老板雅尔马,因其好友格瑞格斯“认死理”执意要把“真相”揭露出来让其面对,结果使他全家陷入乱局,无异于这一家人(夫妻和女儿)一起进入了“理想与现实”悖论的难堪的煎熬中。《罗斯莫庄》的志趣相投的男女主人公在舆论压力下,经受了真挚爱情与道德良心的悲剧性悖论的拷问,双双走向自我毁灭,剧中人物关系(包括他俩周围的亲友)也是围绕着这一悖论的建构来设置的。《海上夫人》的男女主人公(以及作为女主人公内心理想外化的“陌生人”),将这一悖论从濒临悲剧命运转向和谐结局。《海达-高布乐》则是女主人公“理想”的极端发展,她在这一悖论中选择了孤注一掷,偏执女性“理想”(本能的欲望冲动)而不顾一切的态势——与“海上夫人”艾梨达兼顾“自由与责任”正相反——,以致最终走向毁灭对方也自毁;此剧的人物关系就围绕着这一点来设置,海达-高布乐拖住她的新婚丈夫以及过去的情人和现在成为情敌的女友,四人同上悲剧性悖论的祭坛。这种几乎覆盖易卜生全部剧作的“微妙而复杂”的人物关系设置,青年曹禺肯定是注意到并记取了。无可置疑,“微妙而复杂”的人物关系设置正是曹禺剧作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而其基础则是“理想与现实”的悲剧性悖论的祭坛格局。
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还在于,在易卜生剧中人物关系所围绕的悲剧性悖论祭坛上,往往有一个因其完全无辜并且善良可爱而特别令人惋惜的人物,几乎称得上是理想的化身,却在“悖论”(冲突)的漩涡中涉足不深,他(她)在人物关系格局中纯粹是作为祭坛上的“献祭品”而存在的。这种人物在《野鸭》中是14岁的纯洁女孩海特维格,在《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中是主人公之妹艾勒,在《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中是曾给艺术家鲁贝克教授当模特而在剧中意外重逢的爱吕尼。这种人物身上洒满理想的光辉,是剧作家自我的感情投射。我们在“曹禺三部曲”中也看到了这种作为“献祭品”的理想化的悲剧人物,这在《雷雨》中是周冲,——蘩漪之子本不应该承担“上一代人造孽而由下一代人还债”的宿命责任;——在《日出》中是小东西,在《原野》中则是焦大星及其幼儿黑子。这就是为什么按照庸俗社会学来看难以理解剧作家怎么会去“美化”焦阎王的后代,于是只能用一顶现成的帽子扣在《原野》作者头上,叫做“调和阶级矛盾”,其实这种伪批评正表明评论者对真正艺术创作的无知:从易卜生到曹禺这些戏剧大师这样设置人物关系和创造悲剧人物形象,正有其深意在!正是从“献祭品”的形象中彰显了悲剧性冲突的历史深度,突出了理想与现实的“两难”选择的历史困境(包括中国农民暴动的历史局限性在内的社会现象也已在剧作家的视野之内)!
(三)复式戏剧结构:情节层面与象征层面的结合
如上所述,《雷雨》构思中蘩漪及其亲子周冲同为核心人物,居于“理想与现实”悖论的中心枢纽位置;但在某种意义上,这母子二人本身又构成了“理想与现实”对比、即灵肉对照的双重关系,从而分别主导了全剧的双层结构。作为母亲的蘩漪以其倾向肉体(现实)爱欲争夺的冲动不断引爆“雷雨”,主导着剧中情节层面;作为亲子的周冲以其纯洁少年的诗意激情“旁观”了两个家庭内发生的冲突,他还没有跨进现实生活的门槛,没有涉及悲剧性悖论这条情节主线的行动,但他却从灵魂的高度上凌驾着全剧的沉闷的雷雨氛围,主导着剧中象征层面,并在最后作为“献祭品”被端上祭坛时如同一道闪电插入雷雨的夜空,照亮了所有人物(包括他母亲)的内心使他们看到了各自的罪错,——蘩漪就在此时痛责自己未尽母亲的责任。如同易卜生的《野鸭》剧中海特维格只在寥寥几个场面中现身,周冲也在很少几个场面中作出插曲式的亮相,但他的每次出场都把“理想与现实”悖论激化并提升到诗意的象征高度。例如他对四凤表达诗样的情意;他闯入鲁家表示要和大海握手;他在周萍要带走四凤时刻目睹了母亲与哥哥“情战”,并表白了他自己天真的“爱慕”心迹。由于周冲作为“灵的存在”仿佛拨动全剧情节主线的“灵肉二重奏”,剧中就形成了提升情节涵义的象征层面,加强了“三角恋”和“乱伦”故事的悲剧意味与崇高感。
《日出》的结构比较特别,处于人物关系格局核心位置的陈白露与其男友方达生,其实在情节主线中涉入不深,两个人都仿佛以超脱的姿态俯视着旅馆内(社会现实缩影)的芸芸众生;方达生不用说,是整个游离于情节层面的“局外人”,而陈白露至少从表面上看也只是通过她与潘月亭经理的依附供养关系,加入了那一伙人的鬼混,她在剧中的唯一积极行动是偶遇小东西,为了保护后者而拉上潘经理顶撞了(未出场的)金八爷的黑恶势力。但陈白露在戏剧结构中起着双重作用,她一人连接了情节层面与象征层面,她与方达生作为见证人的存在和亲历过程,构成了诅咒黑暗现实、期盼“日出”理想的象征。正是由于以陈白露为枢纽连接点的双层结构,把第三幕下等妓院的“黑地狱”与其他三幕(豪华旅馆)统一起来,使表面上缺乏情节连贯性的两个板块合成一个戏剧结构的有机整体。
《原野》在结构上又有其独特之处,这就是所有人物都处于情节层面上,围绕着仇虎复仇和带花金子两人结伴逃跑这条单纯的主线展开,三幕戏有一气呵成之感;同样是情节主线上的这批人物,以仇虎与花金子这对情侣为悲剧性悖论的中心,每一个又都是象征性角色:例如象征黑暗蒙昧势力的白傻子、常五爷(死神“无常”)、瞎婆子(讨命鬼)、焦大星与黑子(前述的“献祭品”)等等,他们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使命区别只在于,前两幕以情节的延续贯串为主,到了第三幕(原始森林)的五景中则以象征(理想与现实的对照和搏斗)为主。从全剧的场面发展来看,象征成份越来越重,情节成份则逐渐退居次位,以焦大星在睡梦中被仇虎所杀和黑子被其奶奶瞎婆子误击致死为转折点,进入第三幕的“象征戏”。此剧在结构上这种前重情节而后转象征的双重性特点,从表面上看(后半部戏、即第三幕)学奥尼尔《琼斯皇》之处颇多,但从结构深层的人物关系格局上看——如上所述的有焦大星父子俩作为“献祭品”,——更可理解为曹禺在此剧中主要还是接受了易卜生影响!至于奥尼尔《琼斯皇》在戏剧结构上的影响,我们宁可相信曹禺本人的解释,他说过他写此剧前并未读过或看过《琼斯皇》(只是从张彭春导演所述中闻知有《琼斯皇》这样的戏剧结构并有黑暗森林中鼓声的运用),而且第三幕五景中出现的多个场面和细节均显示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例如阎王殿上的牛头马面、深夜传来的做“道场”的磬、钹声响等等,绝非对奥尼尔剧作的简单模仿,而是植根于传统记忆的艺术创造。
我们依次审视过“曹禺三部曲”的结构创新,再看易卜生戏剧创作历程中贯串着的象征性,对曹禺从易卜生那里吸收的滋养就更可理解了。在易卜生的范围广阔、门类多样的剧作中,象征始终与叙事平行,只是越发展到后期,以细节与虚象为特征的象征层面越益上升到超越、笼罩叙事线和情节层面的显著位置。早在《皇帝与加利利人》这部规模宏大、气势磅礡的“世界历史剧”中,与丰富而紧张的情节主线平行或交叉着展现了古罗马皇帝朱利安与神秘学家马克西莫斯的密商对话,阐发了扣人心弦而又深奥的哲理——关于将古希腊多神教与基督教合二为一的“第三帝国”的构想及其悲剧性破灭。在《玩偶之家》和《群鬼》中,象征也渗透了剧情氛围。到了《野鸭》,久别重逢的一对老朋友之间围绕着“理想与现实”悖论展开博弈,关于那只“受伤的野鸭”的意象时隐时现地不断穿插其间,随着剧情发展和女孩海特维格成为这场博弈的牺牲品,引发了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探讨。
在戏剧结构问题上,展开曹禺与易卜生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可以提供无穷兴味的亟待深入的课题。现代戏剧中哲理性加强,这与戏剧结构中出现象征层面及其份量逐渐加重有关。
(四)戏剧性口语:散文化对话与舞台感
剧中人物写活,与活的口语分不开。“曹禺三部曲”与易卜生开创现代戏剧一样都是“用日常生活中直白的、朴实的口语写作散文剧。”[1]225-226例如,《雷雨》中周萍与蘩漪摊牌的一段对话:“......我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哦,你是你父亲的儿子。(笑)父亲的儿子?(狂笑)父亲的儿子!”又如,四凤埋怨周萍:“......你又不是真......”由个性化人物在特定情境中说出的这样的语句(甚至只有半截子话),只有当事人或身临其境的人(真正现代戏剧的观众)才听得明白,其含义都远远不限于字面上的意思,其情感意涵(即戏剧艺术中所谓“潜台词”)胜过书面语言的千言万语!
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就是曹禺话剧、特别是“曹禺三部曲”对于培养中国话剧演员的作用。解放以前,民国时期(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旅行剧团演出“曹禺三部曲”(以唐槐秋导演的《雷雨》为主),历来缺乏研究和总结,诚属历史的遗憾!1950年代后期,新中国话剧舞台上在中断几年以后,以夏淳导演在北京人艺恢复上演《雷雨》为开端(随后在中央戏剧学院也上演此剧),以严格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排演这部曹禺经典话剧,对于建立中国现代剧场艺术和话剧表演艺术,其意义我认为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希望今后加强研究总结!
曹禺的确做到了如同易卜生对自己的要求那样:“所有只适合在书上阅读的对话与音调必须小心地在戏剧中避开,尤其是在我的戏剧中不能出现这类对话;因为我的戏剧力求制造这样的效果:读者或观众在阅读剧本或欣赏演出的过程中,感到他是在真实地体验一段真实的生命历程。”[1]218自从《雷雨》问世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观众与读者,确实从曹禺笔下的字里行间感到自己是真实地体验过蘩漪、陈白露、花金子与仇虎等等话剧舞台上的活人各自的“一段真实的生命历程”,他们的爱、恨、情、仇!
与戏剧语言相关的,还有剧作家的舞台感或戏剧想象力。易卜生曾自述他有这种对戏剧时空的想象能力:“由于我对一切关涉戏剧性的事情具有很强的想象力,因此我能够看到一切真正自然的、真实可信的事情真真切切地在我眼前发生。对我来说,看一个剧本可以产生跟看一场演出同样的效果。”[1]282曹禺也发展了这种舞台感,这与易卜生影响和他自己早年在南开新剧团的演剧活动都有关。
(五)诗的意象:戏剧的文学性与剧场性的统一,强调“潜在的诗情”
近些年来,浮躁的中国演艺圈似乎忘记了戏剧按照古典的(即经典的)美学来看属于诗(即文学)的范畴,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这里不涉及什么学院派或非学院派的问题,而是关乎对艺术本身的认知。
与易卜生戏剧一样,曹禺话剧(首先是其“三部曲”)也是既可供剧场演出,也可作为文学经典(剧本)供案头阅读的,甚至像诗一样来朗诵其台词。易卜生戏剧的每一部都是先出版剧本,而后演出;曹禺三部曲也是如此,先在刊物上发表而后上演。这正表明现代戏剧格外重视文学性的一种特质,而不是像现在国内有人胡诌的那样什么现代戏剧是一切由导演(甚至演出经纪人或投资人)说了算。上述事实表明,现代戏剧按其开创者的要求是应首先作为文学作品站得住脚(有读者即其证明之一),然后上演才有意义。易卜生甚至认为,“让一部戏剧作品首先以舞台演出的形式与公众接触是有害的”,因为“一般说来,老百姓对表演和演员总是比戏剧本身更感兴趣。”[1]171易卜生所说的“戏剧本身”,显然是指剧作家所写的剧本;而且他总强调他的剧本是诗,——尽管从《青年同盟》(1869)起他就从诗体剧本转向写“散文剧”(即他创建现代戏剧最终确定的体例而开风气之先),他对诗有自己广义的理解(留待下文详述)。曹禺也是这样,强调他写《雷雨》剧本是在写一首诗。事实上易卜生戏剧与“曹禺三部曲”的确都具有诗的特质,是由诗的意象孕育而成的,剧作通篇含蕴着“潜在的诗情”。看来正是(首先是)易卜生培育了青年曹禺的审美感知能力和对戏剧诗的精辟判断力。
易卜生提到“潜在的诗情”是在他对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丹麦)的一段评语中:“我一次又一次地读着你优美的、深情的、高尚的诗歌,渐渐明白了你现在为什么不再写诗了。你已经把你写诗的天才倾注到关于莎士比亚的长篇大论中,倾注到关于迪斯雷利和拉萨尔的创造性著作中,以及其他著述中。那些材料看上去尽管是历史性的,但渗透着潜在的诗情——带着你年轻时写作青春诗歌时特有的诗情。”[1]350如同他所理解的勃兰兑斯一样,一生致力于剧作并开创了现代戏剧的易卜生本人就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不仅就他也有不少诗作而言,更重要的是缘于他的全部剧作是作为“一个持续发展的、前后连贯的整体”的戏剧诗。在易卜生影响下于20世纪30年代开创了中国现代戏剧的曹禺,以其至今无人超越的《雷雨》、《日出》和《原野》也已位列戏剧诗人的崇高行列。
从易卜生到曹禺,这些戏剧诗人在现代戏剧的开创中有着一致的美学追求:一方面使剧本适应现代观众的剧场要求,运用散文化、口语化的戏剧语言把人物写活;另一方面以自己“潜在的诗情”渗透人物的台词和行动,使全剧成为诗的意象的有机整体、一个总体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易卜生的戏剧创作道路所经历的三阶段,是从富于传奇色彩的、强有力的一系列浪漫诗剧起步,中间开始转向现实主义的“散文剧”并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剧”,最后又“回归”并开创了一系列富于诗情哲理的象征主义戏剧;简言之,是从“重象征”起,到“重写实”,而后走了一条曲线又回到“重象征”。再看我们的“曹禺三部曲”,则是从一部强有力的、含蕴着古典命运悲剧意味的《雷雨》起步,到接近现实主义“写实剧”的《日出》,而后也走了一条曲线回归到“重象征”的含有表现主义意味的《原野》。曹禺以其“三部曲”在1930年代他作为青年剧作家的短短几年内走完了浓缩版的“易卜生之路”。两者相同的是,都以戏剧诗人的美学追求,在各自的民族文化土壤上开创了兼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现代戏剧。当然,就易卜生戏剧影响范围之广(遍及世界戏剧)、其作品规模之巨大多样以及艺术成就之高而言,当时中国的青年剧作家曹禺无法与伟大戏剧诗人易卜生比肩而立,乃是不言而喻的。
二、从与各自戏剧前辈比较中看易卜生、曹禺的现代性与开创性
“曹禺三部曲”中与易卜生戏剧遥相呼应的上述五项剧作元素,综合在一起就确切无疑地构成了戏剧中的“现代性”。这就是为什么《雷雨》刚公演就使当时中国整个戏剧界对曹禺刮目相看,所有与话剧相关的有识之士都感觉到不同凡响的杰作已出现在话剧领域,揭开了中国话剧的崭新一页;尤其是通过“中旅”携“曹禺三部曲”长年大力巡演推广,全国大中城市的观众与读者都意识到中国从此有了这种叫做“话剧”的现代戏剧!
事实上,构成戏剧“现代性”的这五项剧作元素互相联系,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可悲的是,当今有些自炫“新潮”之士还在徒然质疑“话剧”名称,意在取消民族语言(母语、口语)在戏剧艺术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取消文学性(诗的意象)在现代戏剧中的地位与作用。当然,此类企图动摇曹禺为中国现代戏剧奠定的基石、乃至动摇易卜生为世界现代戏剧奠定的基石之举,是徒劳的,也是很可笑的。试想,如果取消话语而让人(在生活中或在舞台上)都变成哑巴,那还谈得上什么剧中人物的交流、乃至人类全体的沟通呢?!进而言之,如果取消或贬斥文学性(诗的意象),那种所谓“现代戏剧”就成为没有灵魂的舞台把戏,也就不成其为任何戏剧艺术了。
比较一下曹禺与其话剧前辈的剧本语言,很容易发现戏剧“现代性”之有无的区别。长期成为中国话剧(以左翼为主导)的领军人物的田汉,以至在新中国文艺界被尊称为“郭老”(沫若)诸人的剧本中,“只适合在书上阅读的对话与音调”比比皆是,而田汉等“现代话剧奠基人”——现在实事求是地看来他们应被视为相对于曹禺的“中国现代戏剧先驱者”——的剧中人物有时甚至口出洋文,或以含有罗曼蒂克情调的西方文艺用语来进行对话,这实在显示了曹禺前辈们的“食洋不化”(相对于“食古不化”而言)。与“曹禺三部曲”一比,《雷雨》之前的那些话剧语言显然缺乏真正的戏剧“现代性”。至于人物的比较,已如上述;剧本兼含情节与象征层面的“复式戏剧结构”,也是随着曹禺才出现的,之前有的基本上都只是沿袭戏曲的单线情节结构。这就很清楚了,正是曹禺赋予中国话剧以现代性,把中国话剧推进到真正的现代戏剧的境界。
易卜生意识到诗体剧本已不适合现代观众与现代剧场,“如果我让所有人都用同样的韵律来讲话,那么,我刻意放进这部戏(按指《皇帝与加利利人》)里的许多普通的小角色就会变得模糊不清,难以区分。”他随即断然认定,“我们已不再生活在莎士比亚的时代了。”前述肖伯纳指莎剧语言是一种“已经死去的语言”,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易卜生宣称,“我试图刻画的是人类,因此我不会让他们用‘天神的语言’来说话。”[1]147-148他还从戏剧应有的客观性效果出发,主张以现代人的口语来写对话,以便给读者与观众“仿佛身临其境、亲历其事”之感,“这样能最有效地防止读者产生剧中对话体现了作者个人意见的印象。”他强调指出,自己的剧本“没有宣传任何东西。”[1]205
易卜生的许多剧本是在德国首演,或因在德国成功演出而扩大影响到全欧洲的。早于易卜生半个多世纪的德国剧坛,曾有席勒的激情澎湃的“倾向戏剧”——意指此类剧作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风靡一时;而易卜生戏剧显然与其异趣,相比之下他所开创的现代戏剧较为内敛,比较接近古希腊悲剧那样以内在爆发力见长,也更具客观性。——易卜生曾以古希腊雕塑为例谈及自己的审美价值取向:“那脸上无可名状的崇高而又平静的喜悦之情,那戴着月桂花冠的头上所表现出的某种超自然的旺盛精力和纵情之态,那双眺望着无尽的远方、显得若有所思又穿透未来的眼睛,所有这些正是希腊悲剧的精髓所在。”[1]27在看重客观性这一点上,易卜生倒是正如他的同时代人(稍早)马克思、恩格斯所希望的那样,使自己的剧作“莎士比亚化”而不是“席勒化”。易卜生所引领的现代戏剧发展方向,是与“莎士比亚化”一致的。虽然在戏剧语言和结构上,特别在对现代人的自我分裂的内心剖析上,他与莎士比亚相距甚远,这表明他是在适应时代剧变而在戏剧创作中抓住了现代性。易卜生有一段话描述了他所理解的和他表现于戏剧中的“人性内在的冲突”:“不同的精神功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不是均衡地、齐头并进地发展的。人的欲望,特别是贪欲,总是不断延伸,永无满足之日。而另一方面,人的道德意识——就是我们所谓的良心——往往是非常保守的。它的根通常深植于传统和过去之中。因此就有了个人内部的矛盾冲突。”[1]276-277与易卜生所开创的现代戏剧对人性越益深入的表现相呼应,他的另一个同时代人尼采则在西方(历来强调理性的)哲学领域里打开了非理性之门,——而易卜生略早于尼采已在自己的剧作中将人的非理性行为纳入视野,——比他们稍晚的弗洛伊德则以精神分析的医学实验在探索一向是黑暗的潜意识活动。这些思想巨人所共同致力的事业,就是易卜生经常提到的“精神自由”或“精神解放”。
我们理应珍惜从易卜生到曹禺开创现代戏剧的艰难历程,理解现代戏剧从创新中诞生的必然性和这些开创者的宝贵的创作经验。无论当今那些以“后现代”或“后后现代”自诩的“后后后”们怎样鼓吹“新潮”理论,易卜生、曹禺的现代戏剧经典的文本和形象总是靠得住的,而“后后后”们的论调和赝品则未必靠得住。
三、曹禺是易卜生的中国知音
在发表于1930年的为自己翻译的高尔斯华绥剧本《争强》所写序言中,年方二十的青年曹禺表达了其与四年后发表《雷雨》剧本序言所述相同的观点。他在《争强》序中指出,艺术不是宣传,作家是不必为剧中涉及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负责的。与此一脉相承,他在《雷雨》序中坦率地表明自己并非是在剧中“匡正”或“攻击”一些什么,自己创作《雷雨》剧本是在写一首诗。
将曹禺表明这些观点放在20世纪30年代初至上半叶这一时代大背景上看,确有值得注意之处。其时正值中国左翼文艺思潮与组织活动在老上海方兴未艾并且迅猛进军,中国社会日趋激进化和政治化的发展态势明显起来。在这一大背景上,青年剧作家曹禺的文艺观点显然是与左翼文艺相悖的。(至于后来鲁迅按自己对革命文学的广义理解而将曹禺也作为“左翼”戏剧家向外国友人推介,则是另一回事。)毋庸讳言,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于1930年制订的《最近行动纲领》明确地而且最大限度地拉近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将文艺的功能与使命直接等同于政治的。
上文通过文本分析已可看出曹禺主要是在易卜生影响下走上戏剧创作道路的,再看他的文艺观点是如何与易卜生相一致的。易卜生坦承,“我一直把描写人类的性格与命运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而从不有意识地去寻求什么政治方向。”[1]308他把艺术与宣传作了适当的区分:“我在作品中无论写什么,都不会有意识地做某种宣传。与人们通常以为的不同,我主要是个诗人,而并非社会哲学家。”[1]385他从诗人、艺术家的特殊劳动和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出发解释“诗人之路”:“事实是,参加社团不合我的性情。在一定意义上,社团组织是最不适合作家的;因为作家必须以他们自己的野性的方式走自己的路——是的,如果他们想要完成其生活的使命的话,就必须像其想要的那样桀骜不驯。”[1]381易卜生坚持“独立地写作,追求我自己的事业,对我来说是绝对必需的生活条件。”因而合乎逻辑的是,易卜生认定“我过去不属于,将来也不会属于任何政党。”[1]308曹禺未必读到过易卜生在书信和演讲中的这些话,但易卜生的全部剧作已足够使他领悟诗人思维和艺术创造的不同于政治宣传的客观性、独立性与特殊性了。
易卜生自白:“我一生从未投身政治,而只关注社会问题!”[1]280曹禺从 30年代初起——其时与发表《争强》序平行的是孕育《雷雨》——,他完成“三部曲”的全过程中也与易卜生一致地超越政治宣传而关注社会问题,他这三部经典剧作可以视为从深层给30年代的中国社会造出镜像。不仅如此,正如易卜生关注的是“他所属的时代和社会中那些让人感到激动的暂时的和永恒的问题,”[1]368曹禺也不以仅仅反映“暂时的”社会问题为己任,而是更关注“永恒的问题”,他像易卜生那样深入表现人性,“把描写人类的性格与命运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因而他在1930年代所走的“易卜生之路”上既超越了政治宣传,也超越了在左翼文艺思潮中被简单化了的所谓“社会问题剧”,他的“三部曲”没有一部可以被直白粗率的“社会问题剧”模式框住。正因为这样,他写下的是表现人类的性格与命运、表现终极的人文关怀的中国现代戏剧经典。
易卜生在20世纪中国的文坛与剧坛上——自从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后——曾受到过热烈追捧,但长期被庸俗社会学片面评介为似乎只有《玩偶之家》等四部所谓“社会问题剧”,而“社会问题”四字更被曲解为图解某时某地的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只是关涉某项政策的具体问题。这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就为图解政策张目开路了。实际上,易卜生比他在中国被长期曲解的所谓“社会问题剧”作家远为伟大得多!改革开放以来,首先需要感谢徐晓钟院长早在1980年代就在“中戏”舞台上呈现浪漫诗剧《培尔-金特》,为人们打开了对易卜生的新视域。——在中国也只有徐晓钟导演才有此眼界与功力将此剧与《俄狄浦斯王》和《浮士德》先后搬上舞台,在此我谨向他表示敬意和谢意!——加之二十年来《易卜生文集》和《易卜生书信演讲集》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这位伟大的现代戏剧之父的原貌才在我们面前变得清晰起来。现在有机会对曹禺与易卜生作比较研究,更显示出曹禺是易卜生在中国的最大知音!简言之,除了上述两个“超越”(政治宣传与“社会问题剧”),曹禺还像易卜生那样超越一般的剧场技巧而将戏剧升华到诗境,并超越借鉴模仿而实现了植根于民族文化的艺术创新。我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青年剧作家曹禺,以其《雷雨》等“三部曲”成为中国现代戏剧之父,其时他已是名至实归的戏剧大师了。
四、“中国的易卜生”之路的艰辛与迷茫
在“曹禺三部曲”被国内剧坛广泛接受之后的较长时期内,他到南京的国立剧专任教,并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校迁往“大后方”的四川江安和重庆等地。抗战期间,进入1940年代的曹禺剧作主要有《北京人》、《家》和《蜕变》等。它们虽然各有思想艺术上的成就,但显然不能与1930年代的“三部曲”相提并论。其中《北京人》在评价上可能有争议,历来的主流评论咸认其为曹禺的“现实主义高峰”——这是基于将曹禺归结为中国版的“现实主义”剧作家的一种提法,即认为《北京人》是曹禺最高成就(例如中戏的晏学教授);的确它在试图吸取契诃夫风格神韵并将其与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上,是有开拓意义和示范价值的;但在效法《樱桃园》构建“现代喜剧”氛围上,《北京人》却似乎欠缺契诃夫剧中那种内在的支撑力度,——后者的人物关系格局与诗意潜流更有力地支持“告别过去”的乐观的喜剧氛围,——除了人类学家袁任敢及其女儿的象征性的外加形象成份之外,“旧家族”人物关系格局中的女主人公愫芳的性格描写与形象塑造似已欠缺“曹禺三部曲”中那种女性形象的内在魔力与完整统一性。对《北京人》及其后的曹禺剧作,我的研究很不够,不便多谈、妄加评价。近年来已有年轻学者如李杨教授的专著中批评《北京人》,我翻阅相关章节后颇有同感,虽然还未及仔细拜读。有一点可以确认:进入1940年代的《北京人》形成一个拐点,显示曹禺的“中国的易卜生”之路已不再持续,他在逐渐向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和“社会问题剧”靠近,甚至最后与绝大多数中国剧作家一样也滑向了宣传剧模式。在这一点上,他是违背了自己在1930年《争强》序及其后的《雷雨》序中表达的见解的,可以说未能“忠实于自己”。《家》作为超越“改编”的一部具有独立的思想艺术价值的力作,——人物关系格局的重心显然从巴金原著的三弟觉慧转为悲剧人物瑞珏及其丈夫觉新,——但此剧与《北京人》同样难以列入“曹禺三部曲”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戏剧经典范畴则是显然的。至于稍后的《蜕变》,更明显是在努力效法“社会问题剧”以至“倾向戏剧”(恩格斯语)了,作者与宋之的合作的《黑字二十八》则标志着曹禺从此已迈上宣传剧之途了。当然,从肯定性评价的角度着眼,此时已处于左翼强大影响下的曹禺有得有失,他已投入“抗战剧运”的洪流之中,而“抗战戏剧”在总体上自有其政治上的价值,需要用艺术之外的另一把尺度来衡量,这在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开展民族解放战争的国家也实属必然。从艺术上看,“抗战戏剧”不外乎宣传剧与情节剧之结合的模式。这在曹禺此后的长期戏剧生涯中不可避免,新中国建立后他处于政治上较为显赫的地位(1956年他是党中央按统战政策所需“从知名人士中”直接发展的一批中共党员之一,行政职务则从中戏副院长兼北京人艺院长到文革后的全国剧协主席),——除了文革中被贬为人艺看传达室人员之外,——使他在客观上更有理由需要服从组织安排。如此看来,“中国的易卜生”之路最终进入迷茫状态,即使对于曹禺这样的艺术天才来说,也是身不由己、无可选择的。
“独立不倚的人(按这一词语过去的中译为“孤立的人”,此处从戴丹妮译文)才是最强大的人。”[1]122易卜生此言见于致勃兰兑斯的信,也在《人民公敌》剧中作为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的台词广为流传。这在曹禺内心深处(特别是进入晚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不时荡漾。易卜生还指出:“归根结底,大多数吹毛求疵的评论行为只要有可能,最后都变成了指责作家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感受、观察和创作,而没有按照批评家认取的方式去观察和创作。重要的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东西,使之不受外界毫无关系的事物的影响。此外,还要格外小心区分您所观察到的和您所体验到的事情,因为只有后者才是创作的基础。”[1]91他还在不止一处指出,作家“要忠实于自己。”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素,“中国的易卜生”在其青年时代之后的大半生中未能做到易卜生本人实践了一生的信条,诚属可惜可叹!
所幸的是,曹禺晚年有了反思,即使这些反思未能导致结出创作硕果。但他的反思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这就是我在自己创作的话剧《诗魂惊雷》(剧本及导演阐述文本均发表于《曹禺研究》第六、七辑)中意图表达的主题以及创作动机。读者当能从此剧本中看出与我在这篇论文中的阐述相一致的艺术表现,如果此剧有读者的话。
在现当代中国的左翼文艺和红色文化的大环境中“转向”的一流剧作家,绝非曹禺一人;早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原先醉心浪漫派的激进剧作家田汉,以发表《我们的自己批判》一文为标志,接受了“普罗列塔利亚”(来自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话语系统)并入中共,对自己此前持“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文艺创作大彻大悟表示弃绝;1950年代初,老舍自美回国,也在写出艺术上具过渡性质(从观念到结构均呈内在矛盾)的《龙须沟》、《方珍珠》二剧以后,转向一系列描写生产建设过程和政治运动的宣传剧创作。
上文提到中国剧作家们“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素”,客观因素具有压倒一切之势,这是谁都明瞭的;如果说主观因素也确有作用,那就不得不考察到理性能力的相对软弱,恐系其中之一。易卜生曾指出:“对于一个现代作家来说,具备广博的历史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要是没有的话,他就不能判断他所处的时代、他的同时代人以及他们的动机与行为,即便能判断也只能得出非常片面和肤浅的看法。”[1]184曾被英国作家肖伯纳和“五-四”时期的中国学者胡适都大力提及的所谓“易卜生主义”,以易卜生自己的话来表述则“主要是一种彻底的、真正的自我主义”,其根据在于“你如果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1]113他又指出,“我们每个人唯一能做和做得最好的事情是在精神和真理上实现自我。”[1]240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假设了一种极端的情况:“在我看来,在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中,的确有一些时刻像是海上撞沉了船,此时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救出自己。”[1]113当然,这种描述性的文字不应被误解为我们惯常所说的“自私自利”,而是意指通过反思和自我剖析达到自我完善、“实现自我”的绝对重要性。易卜生的一生就是如此立身处世的,易卜生戏剧所要达到的社会效果也是如此,这就是自我理性的坚强,也是剧作家希望世人实现的理性坚强。
田汉、老舍都先后“转向”了。所幸的是,这两个人到了晚年通过反思实现自我,精神上“救出自己”了。(当然此处只是援引易卜生的一个譬喻而已,由于种种力量避免沉舟并能继续扬帆远航,则是另当别论的一回事。)他俩都给世人留下了一生精神自由结成的硕果,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这是为数寥寥的堪与“曹禺三部曲”并列的中国现代戏剧经典。(当然他俩都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两个人都在文革中罹难。)
可以看出易卜生“理性坚强”的一个事例是:当《玩偶之家》在德国上演时,译者和剧院人士改动结尾,引起易卜生的强烈反应,“在一封给译者的信中,我自己曾把这种改变称作是对于这个剧本的‘野蛮的暴行’。”在易卜生看来,“戏剧范畴......必须符合戏剧文学的事实——而不是相反。”[1]186-187意即演剧艺术诸环节均应服从剧作。易卜生敢于直言,敢于坚持。
事实上,理性相对软弱确会导致作家错失某些历史机遇。据传闻,曹禺多次容忍了若干导演对他的剧作的改动,不但在新中国的“前十七年”以至1930年代老上海的左翼剧团中如此,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也如此;他这种态度还被传为美谈,且被解释为剧作家理应如此的“宽容”美德。其实,若将这一点与其他诸端相联系,显见我们的中国剧作家与易卜生之对照。
从本质上看,易卜生所主张并在戏剧中作了艺术表现的自我剖析、反思和自我实现,不正是与我们所熟知的概念——鲁迅的“批判/改造国民性”相一致的吗?!此处作为宾语的“国民性”,也应包含每个人、包括作为创作主体的剧作家的“自我”在内,即“批判/改造国民性”归根结底意味着“自我剖析”——展开自我内心里的“跟魔鬼搏斗”[1]81。这样才能提高自我,把自我“铸造成器”,亦即提高全民族每个人的“人的素质”,达致“人的解放”。易卜生认为,“越是进步的地方,人们越是看重‘人的解放’而不是机构的解放。”[1]215
曹禺作为“中国的易卜生”所走过的戏剧创作道路,真的可以给我们提供太多太多的启示和经验教训。我们应该深深感谢并永远缅怀这位我们自己民族的天才戏剧诗人!
为2014年“曹禺文化周”而作
[1] [挪]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M].汪余礼,戴丹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bsen of China”CAO Yu’s Path
HONG Zhong-huang
(School of Television Arts,Zhejiang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and Media,Hangzhou,Zhejiang 310018)
This paper elaborates why CAO Yu is viewed as“Ibsen of China”and“Father of modern Chinese drama”.What CAO Yu adopted while differentiated from Ibsen lies in the modernity that can be embodied in characters’self-analysis,relationships based on the paradox of“the ideal and the reality”,polyphonic structure,colloquialism and poetic images.As the classics of the young drama master in 1930s,CAO Yu’s trilogy is the condensed version of “Ibsen’path”.Due to various constraints,the bewilderment in CAO Yu’s path has made people reflect profoundly.
CAO Yu;Ibsen;modernity
J805
A
1671-444X(2016)03-0060-12
2015-01-16
洪忠煌(1941—),男,浙江余姚人,浙江传媒学院影视艺术学院教授,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终身荣誉院士兼客座教授,中国文艺家联合会副主席,浙江省莎士比亚学会会长,研究方向:戏剧电影史论。
——评葛斯著《易卜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