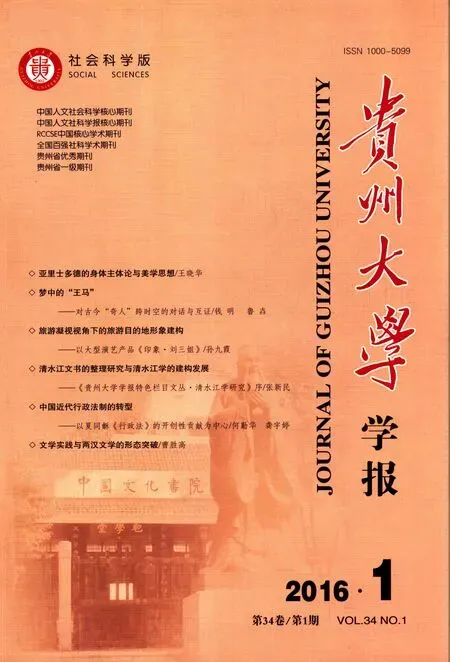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与清水江学的建构发展*
张新民
(贵州大学 清水江学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25)
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与清水江学的建构发展*
张新民
(贵州大学 清水江学研究中心,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清水江学是继敦煌学、徽学之后,又一获得学界普遍认同的地域性专门学问,其得益于大量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而其发展必须将资料整理的范围由文书延伸扩大至典籍文献、口述史料、田野实录,同时兼采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论优长,拓展研究视野,深化研究内容,真正做到以中国解释中国而非以西方附会中国,以全面反映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和发展变化。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清水江学;研究;建构
清水江学是继敦煌学、徽学(又称“徽州学”)之后,又一获得学界普遍认同的地域性专门学问。徽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学问,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离开了徽州文书,就不可能出现徽学;徽学研究却广涉地方民众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构成了整体而全程的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内容①。与微学一样,清水江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新的学问, 亦在于大量清水江文书的发现,离开了清水江文书,就不可能出现清水江学,但清水江学研究同样广涉地方民众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当然也构成了整体而全程的中国历史必须大书特书的重要研究内容。二者的产生一先一后是相互衔接的关系,代表了学术发展的新动向,不能不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或重视。
清水江文书的庋藏地主要分布在清水江两岸及其支流地区的各自然村落,由当地乡民世世代代长期守护和珍藏,是一种活态的民间文化记忆遗产,已列入国家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从形式上看,当地文书既有制式化的单张散件,也有名目繁多的成册抄本;从内容上讲,严格意义上的契约文书——特别是士地、山林买卖契约——固然最多,但书信、婚约、日记、账册、课蒙读物、日用类书、诉讼案卷、宗教科仪书一类的文本也不少,其中不乏诸如鱼鳞图册一类的关键性史料,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有关土地制度、地权分配方面的历史信息②详见《《同治十二年重钞本春花鱼鳞册》(利1至64)CT-GCH-003/CT-028-007)、《民国十六年一月订东清冲、是要冲、冲玩等六处循下三甲春花鱼鳞册》(贞1至73)(CT-GCH-055/CT-027-056),张新民主编:《天柱文书》卷五十、卷五十二“高酿镇春花村文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册18册/第30-93页,第18册第66-138页。参阅黄敬斌、 张海英《春花鱼鳞册初探》,载《贵州大学学报》2015年2期。,反映了与地方复杂社会对应的多样性内容特征。其数量之多,完全可与徽州文书比肩媲美,堪称大规模的原始资料富矿,形成了难得的地方知识结构谱系。而论其涉及时段之长,则主要保存了自13世纪至20世纪近七百年的社会历史记忆,足以反映自明以迄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生活,多为地方族群的“自表述”或“自书写”,乃是研究明清或民国历史不可或缺的民间史料大宗[1]。至于其所涵盖之地域范围,则固然以清水江流域如黎平、天柱、锦屏、三穗、剑河、台江等县各为主,涉及湘、黔、桂毗连的广大地带,乃是与内地文化差异颇大的所谓“蛮夷”之地,或可称为研究工作必须关注的第一空间。但由于清水江作为重要的“苗疆文化走廊”[2],乃是旁通横贯贵州全境的“滇楚大道”的重要航行水道*滇楚大道又称“滇楚通道”,见道光《贵阳府志》卷二十九《疆里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上册,第6660页),除横贯贵州东西全境的驿路外,显然也包括连结湘黔两省的清水江水道。由于清水江乃沅江上游,氵舞阳河乃沅江支流,故广义的清水江亦可泛指清水江-沅江,当然也包括在湖南境内注入沅江的舞阳河。,至迟明代以来便已成为西南交通的大动脉,乃是明清两代国家经略开发的重要区域,仅其向东陆路一线即直接连结了黄平、镇远、都匀、贵定、龙里、贵阳等重要城镇,故研究清水江文书不可不兼顾整个西南地缘区位,或可称为研究者必须重视的第二空间。又由于当地木材贸易活动极为活跃,大量木材均由清水江—沅江远销长江南北,遂与湖南、江西、安徽等地产生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关系,其中湖南的例木采运即与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运输直接相关,徽商、临商则已深入清水江腹地进行贸易活动,清水江文书亦时见“三帮客商”即徽帮、临帮、陕帮的记载*道光八年《清浪碑》:“三帮协同主家公议,此处界牌以上,永为山贩湾泊木植,下河买客不得停。”文中两见之“三帮客商”,即指徽帮、临帮、陕帮商人,或又称为“水客”,主要与当地“山客”进行木材交易,可证其已深入清水江腹地。,足证表面一地之文书其实尚涉及广大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妨视为研究者理当旁及的第三空间。三个空间互有交叉或重叠,但却连结了广袤的汉文化区与非汉文化区,不仅是国家与地方长期复杂互动的战略要地,同时也是地方与地方、族群与族群频繁交往的文化要冲。当地文书研究的范围固然应以清水江流域为主要对象,但也广涉整个西南乃至南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与之相应的学术成果则应做到宏观与微观兼顾,个案分析与大视野讨论并重,从“小地方”见“大历史”,从“大历史”看“小地方”。足证利用清水江文书本来具有的系统性、连续性、真实性等多方面的特点,深入开展地方社会历史实况的研究工作,推动清水江学的健康发展,不仅能够改变西南史地研究长期滞后的局面,积累地方秩序重构再造的经验,而且可以深化我们对传统乡土社会的认知,摸清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发展变化的规律,不能不是一项值得严肃认真地对待的重要学术事业。
当然,清水江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重要的新学科,固然主要得力于大量清水江文书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但具有综合性质的清水江学并非就完全等同于单一性的清水江文书学,前者显然以当地复杂的族群及其所创造的灿烂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必然涉及民间契约文本及文本之外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内容,较诸后者更多地局限于狭义的民间契约文本本身,不能不受到文书学自身即单一性的学科与学科之间内涵外延的排他性的规约,故无论时间空间涵盖的范围都要显得广阔得多。易言之,二者尽管有着大量的重叠和交叉,甚至彼此都是对方的“增上缘”,但前者完全可以涵盖后者,后者则绝难取代前者。只有将资料整理范围从契约文书延伸扩大至典籍文献、文物遗存、口述史料,才真正足以支撑综合性的清水江学学科今后能够欣欣向荣地向前发展。因此,清水江学的建构发展除最具突出史料价值和独立研究意义的契约文书外,尚必须广搜家谱、碑刻、摩崖、古歌及各种乡规民约等小传统文本,同时更要认真查阅比对正史、实录、会典、方志及各种公私文集等大传统文献,必要时尚应该深入田野展开多种方式的调查,获取历史语境现场化的切身经验实感,了解乡民社会活态的历史记忆和生存劳作方式,摸清乡土文化局内人自身的视野特征与理解方法,形成历史认知必须依赖的最佳“史料环境”。而在已有长足发展的文书学的基础上,也有必要建立涵盖面更加广大的乡土文献学,即以扎实可靠的乡士文献资料为基础,同时兼采历史学与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论优长,以求全面了解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获取更多的扎实可靠的一流学术研究成果。
乡士文献学固然以民间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又不能仅限于民间文献,一味夸大民间史料的价值,乃至轻视或遗忘官方文献的重要。其实无论官修或私撰,典籍或文物,成文文本或口传历史,大传统或小传统,举凡涉及地方文化史迹,牵联乡民社会生活的文献,均可纳入乡士文献的范畴,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估和研究。记载乡土社会生活的文献,无论其自觉或不自觉,亦无论其形式内容当如何归类,历代积累的数量颇多,未必都可称为“民间文献”,却完全能够归入“乡土文献”。清水江学得以建构的优势,即在于契约文书提供的研究便利,但仍有必要扩大资料搜考的范围,将不同途径或方式形成的各种公私文献,都纳入学科建构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基础范围,同时借鉴己有长期发展的大传统文献学的成熟研究方法,兼采晚近以来形成的甲骨文、简牍、敦煌文献、明清档案等相关资料的整理经验,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寻找乡土文献的分类整理方法,为乡土中国社会的研究建立可靠的资料利用基础。史学并非就能等同于史料,但却离不开史料,只有凭借科学合理的史料整理方法,一方面还原文献固有的真实形态,不可人为地任意切割拆散,一方面又予以恰当合理的分类,尽可能地保存其系统性与完整性,才能更好地实现有效利用一切资料的目的。传统乡土社会的研究涉及的题域极为广泛,缺少了乡土文献学的支撑便难以有大的作为,无论清水江学或其他地域学,都必须以大量的资料积累为学科建设的前提。但资料不按学科方法归类整理,便只能是杂乱无章的一团乱麻,既无从找到研究方法上的入手路径,也难以发现地方社会变迁发展的根本线索,可见我们固然希望清水江学能像徽学一样成为地方性的显学,但依根本的预设仍是有大批学者甘愿做“劳己逸人”的基础性资料整理工作。
贵州大学历史系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便开始注意乡土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今尚见存于历史系资料室的部分清水江木业碑文及档案卷宗,即是当年(1961)学校师生关注当地社会经济史料的实物见证。而既重视大传统变迁发展的历史性走向,注意上层经典载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也留心小传统的自我生存调适机制,关注下层地方文献的访求、入藏和分析,也始终是我们长期坚持的学术发展方向,代表了多数同仁的学术关怀与事业抱负*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曾创办《阳明学刊》与《人文世界》两大学术刊物,一侧重大传统,尤其是包括阳明学在内的儒学史的研究,一偏向小传统,特别是西南史地文化及乡民社会,虽质量不尽如人意,仍体现了办刊者的学术旨趣与文化关怀,不失为文化边缘化缝隙中生长出来的两棵学术幼苗,值得后来者继续精心呵护,俾其成为足可乘凉的参天大树。。这自然是学术传承内在理路不断延伸的必然结果,也与更广大的外缘环境的实存生命感受密不可分。学术事业的发展无论赓续或中断,后来者均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仅就清水江学的研究而言,长期以来我们均一再强调资料搜集整理与公布出版的重要,煌煌22巨册精装本《天柱文书》2014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出版,便是我们长期沉潜耕耘的初步成果。资料的搜集整理不仅奠定了的必要的清水江学文献基础,而且也方便了海内外学人的研究利用,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正如卜宪群先生所说:“明清史料丰富,可以选择的课题也远较其他时期广阔,但以各种公私文书构成的新材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依然是新世纪明清史研究最活跃的前沿和学科生长点。”而在各种公私文书构成的新材料中,清水江文书显然占有重要的地位,相关的发掘、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则当视为“近年来明清契约文书研究的一件大事……成为徽州文书以外中国第二大民间契约文书宝库”*以上均见卜宪群:《新出资料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委会编《中国历史学年鉴》(2002-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4年版,第50-51页。,“研究苗、侗地区民族、经济、文化方面最真实的第一手实物史料”[3],明清以迄民国地方文书档案的一重要典型代表。不仅能推动了民族史、经济史、法律史等学科的发展,即“对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社会习俗、文化心理、家族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等等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或者换一种说法,《天柱文书》的整理乃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只有具备扎实的功底才能为学术界贡献一流的精品”[5],它的出版已成为“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最新成果”[6],为“更长期的历史研究和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某些领域和课题上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大大增强站在世界学术研究前沿的可能性”[7]。倘能进一步扩大规模,则“无疑是中国出版史上令人瞻目的巨大工程,而一门国际性显学——清水江学也将随之诞生”[4]
从全国范围看,“近十余年来是明清以及民国文书整理与研究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也决定了今后若干年明清以及民国史研究的方向”*卜宪群:《新出资料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编委会编《中国历史学年鉴》(2002-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4年版,第55页。关于全国各地文书遗存情况及整理出版进度,尚可参阅栾成显《明清地方文书档案遗存述略》(增补稿),载《人文世界》2012年第5辑。。除徽州文书和清水江文书外,黑水城文献、石仓文书的整理研究成果也颇令学林瞩目,新近发现的太行山文书的整理工作则正在开始有序进行,从而形成了“东有石仓文书,西有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南有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北有太行山文书的研究格局”*鲁书月、刘广瑞:《“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学术研讨会”简述》,载《光明日报》2014年6月25日。按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的相关整理研究成果,己为世人所稔熟。黑水城文书和石仓文书的整理成果,举其要者则有《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至2000年先后出齐)、《石仓契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大量新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编纂出版,不仅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激活了新的问题意识,而且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具体内容,构成了史学发展的一大重要动因。
但是,就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而言,尤其是与蕴藏在民间的约50万件文书相较,现有的学术成果却十分单薄,有待开拓的空间依然十分广大,如何进一步扩大文献搜考整理的范围,在已有的文书学整理研究的成果基础上,继续扩大文书编纂出版的规模,尽可能地做到全面、系统、完整和准确,同时建立与之相应的乡土文献学,将搜考的范围扩大到一切公私文献,显然也为学者应该继续思考的一大重要学术论题。至于学术研究成果,则一方面应尽可能地扩大资料取用的范围,以翔实的资料占有为基本前提,本着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精神, 不断提升或拓展国人应有的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水平和范围,一方面则要勇于建立新的研究范式,形成有自身学科特色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真正做到以中国解释中国而非以西方附会中国,不断深化或展现国人应有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睿智与洞见。正是怀抱宏大的学术抱负与强烈的学术愿望,我们在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并出版了大型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之后,又以“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为主题,成功发起和举办了“首届国际清水江学高峰论坛”*参阅张新民:《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创获》,《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2期;《开拓契约文书与地方社会研究的新空间: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人文世界》2015年第6辑。。这次会议的一大收获,就是高度评价了清水江文书整理工作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丰富了苗疆研究的学术成果,深化了清水江学与徽学的交往和互动。而《明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研究:以清水江为中心、历史地理的视角》、《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的研究》、《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凸洞三村:清至民民国一个侗族山乡的经济与社会(清水江天柱文书研究)》等一系论著的出版,则多为文书整理与研究的后续学术成果,既反映了文书学研究的新进展,也体了清水江学研究的再开拓。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清水江文书研究论文的逐年增多,以及题域范围的日趋扩大,《贵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自2012年以来,遂有意开设了一个颇有学术新意的特色栏目——“清水江学研究”,搭建了一个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平台,刊载了一批有份量的研究论文。栏目自开设以来,便受到政、学两界的广泛好评。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不妨试举两例以作佐证。一是《贵州报刊审读与管理》曾以《〈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清水江学”专栏有特色》为题,高度评价清水江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本土性”,专栏的创办则“突出了地方特色,彰显了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对提升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地位和西南学的国际地位,都有积极意义,应予肯定”[8]。再即清水江学专家林芊,亦撰有《一份期刊专栏与一门新学术的诞生:读〈贵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清水江学研究”》,热情赞扬该专栏“是《贵州大学学报》五十多年来的一次大变革,也是对贵州学术文化、中国学术文化做出的贡献”,“为贵州历史文化研究奉献出一个走向全国的学术论坛平台,实际上是将清水江学推向全国和世界”。他甚至以影响世界的法国年鉴学派来比况清水江学的末来发展,认为先后有四代传承并产生了不少史学巨匠的年鉴学派,“不就是从一份期刊的专栏,演变成一份有共同学术宗旨与话题的期刊,从而造就了一个影响世界至深的学派吗?”[9]。这无疑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价值期盼,但却反映了办刊者推动学术发展的真实心理想法,描绘了与国际学术接轨的愿景,预设了建构自身理论体系及相关学派的目的。
统计全国范围涉及刊登清水江学的相关刊物者总计已达三十家,清水江学论文数量或竟可以千计,当已成为明清以迄民国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若论其数量之集中,题域之广泛,特色之鲜明,则当以《贵州大学学报》之“清水江学研究”专栏最为突出。而作者则来自四海,遍布大学及科研机构,既不乏大家作手,亦时见后起新秀,俨然已成一大学术群体。内容则下至经济生活、风规习俗,上至伦理价值、宗教教信仰,无不灿然具备,多得益于文书资料之整理公布,不失为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之佳作。而随着未来研究视域的不断扩大,不仅有关清水江文书丰富内涵的认知将会进一步深化,即涉及传统乡土社会复杂结构的了解也会更加全面,单一方法的研究必然转向多学科交叉的探索。前人较少论及的民间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尤其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日常交往运作方式,也将日趋清晰地呈现出生动具体的面相,极大地丰富明清以迄民国的历史学叙事内容。主编杨军昌教授有鉴于此,遂将历年发表之论文,分类合编为一帙,拟交出版社合刊重梓,嘱我撰写一序,以说明前后原委。我受命惶怵,以为兹事体大,非才浅者能为;然又颇感惊喜,以为文书整理工作虽艰辛,然“一人劳而千人逸”实已为莫大补尝。前人所谓“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10],信不诬也。而合多方面之力共同开展整理与研究工作,亦为今日学术界一大刻不容缓的务。乃不揣翦陋,略陈管见;千虑一得,或可供同好!商榷发明焉。
参考文献:
[1]张新民.走进清水江文书与清水江文明的世界[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2]张新民.叩开清水江文化走廊的大门:以清水江流域天柱契约文书为中心的调查[J].人文世界,2012(5).
[3]吴铭能.四川大学建构“中国西南文献研究中”的意义与理想[J].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11(3).
[4]府建明.在乡土中国发现历史:<天柱文书>出版的意义与启示[J].中华读书报,2014-12-17.
[5]谢开键.民间文书整理与研究的重大学术果[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6]卜宪群.新出资料与中国古代史研究[M]//.〈中国历史学年鉴〉编委会:中国历史学年鉴(2002—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4.52
[7]朱荫贵.民间文书宝库的又一重大进展:清水江文书天柱卷首发式暨第一届国际清水江学高峰论坛会召开[M]//张新民.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2014:1010.
[8]〈贵州报刊读与管理〉编委会.〈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清水江学”专栏有特色[J].贵州报刊审读与管理,2012(5).
[9]林芊.一份期刊专栏与一门新学术的诞生:读〈贵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清水江学研究”[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4(3).
[10]王国维.最近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M]//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第五册〈静庵文集继编〉.台湾:大通书局,1976:1987.
(责任编辑杨军昌)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6)01-0098-05
作者简介:张新民,贵州大学清水江学研究中心主任,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儒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长期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区域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收稿日期:2015-10-21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1.014
*该文为作者为《贵州大学学报特色栏目文丛·清水江学研究》所作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