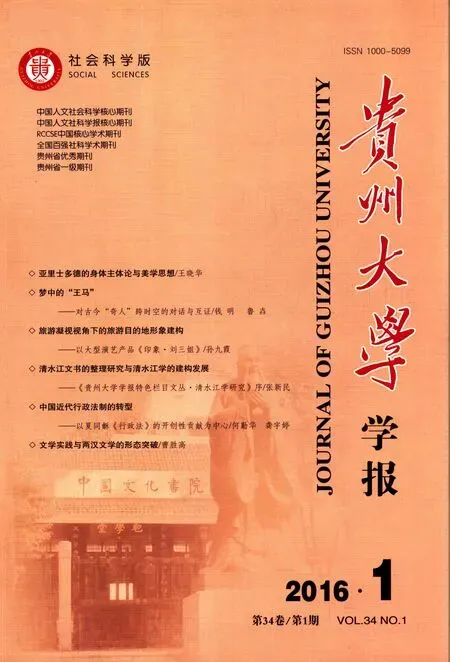文学实践与两汉文学的形态突破
曹胜高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文学实践与两汉文学的形态突破
曹胜高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00)
摘要:中国文学得以自觉,在于东汉的文学认知与文学实践所进行的量变积累。两汉间对文学表意功能的探讨,使得文章撰述更加重视技法,与经学重义理的倾向有了分野;东汉不断强化作家的属文、著述技能,并主动要求以文传世,促成了作家的个体自觉;在民间文人创作风气的影响下,汉灵帝设置鸿都门学,献帝提倡著述,三曹雅好文学,使得文学特征日益明显,为两汉朝野共同崇尚。
关键词:文学实践;文学表意;文学著述
我们要探讨文学认知如何自觉,主要指标应该是衡量作者或者文论家如何看待文学的表意功能①理论界对文学表意进行了诸多阐释,参见陈学广《“语言说我”与“我说语言”:文学如何以言表意》,《江海学刊》,2004年第6期。汪正龙《论文学的指称:超越分析哲学视野的文学表意路径考察》,《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等。。文学表意是指用文学的技法表达创作主体内在的观察、思考或感受。这里所谓的文学技法主要指带有描述性(如赋、比)、想象性(如兴、象)、审美性(如崇高、优美)等表达技巧。从历时的进程来看,文学表意实际是对文学特征的自觉体认,这一体认的自觉程度,决定了这个时期文学自觉的实现程度。我们讨论两汉时期文学的概念形成时,可以将两汉间人对文学表意功能的讨论,视为衡量文学形态演进的一个参照。
一、两汉对文学表意功能的探讨
周秦学者对于文学表意功能的理解,有两个基本的视角:一是孔子所言的“文质彬彬”,二是诸子所讨论的“名实”问题。孔子眼中的“文质彬彬”,更多指向于礼的文饰与人的质实之间的关系。尽管可以将之视为孔子的文论观点,但平心而论,孔子的指向不是今天所谓的文学意谓,而是讨论个人与礼文的关系。诸子所讨论的名实,主要集中在命名问题上,用现在的话来讲,便是事物的“名”与其本质之“实”的关联性,也不着力于文学本身。
作为论辩的基础,先秦诸子所讨论的所指与所谓之间的差异,不仅是诸子著述自身逻辑确立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诸子无法在同一个层面进行辩论的原因。老子的“道可道”“名可名”之谓,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之论,便是出于同名而异实造成的表述困境所产生的命题。《墨子·经》对名实进行规范,可以看成先秦试图解决名实问题的一种尝试;诸子辩论时常常采用随文自注的方式,以确定名所代表的实义,如《韩非子·五蠹》中所言的“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之类的解释,便是通过自我界定来明确字词的含义,而不至于被读者误读,被辩论者抓住把柄。
秦汉对名实问题的解决,是以《尔雅》《释名》等字书的出现来实现的。尽管四库馆臣认为《尔雅》“释五经者不及十之三四”,但班固认为其“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1]1707其规范了经书所引之字词的名与实,用以“释六艺文言”,从而使得经学的解释更加统一。《释名》的立意,更是要辨析名与所称之实的关系:“夫名之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2]1936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日常生活中所用字词的基本含义。此外,扬雄《方言》对各地区异名、异实的汇总,《白虎通》对国家制度所设名物的词义汇通,以及《风俗通义》对民间称谓的解释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确立了常用字词的名与实的关系。这样一来,秦汉间对字词意谓的不断规定、界定,使得名实逐渐统一,不再困扰学者交流与辩论。
如果说名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词义的解读,那么文质问题的关键在于表达的方式。词义的界定可以采用约定俗成的方式实现,即若干本为大家公认的字书、词书编定之后,作为后世交流的规范,足以解决名实之辨。但文质问题所涉及的如何表达,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墨子反对文饰,认为修饰之辞害于意思的表达;韩非子承认修饰是表达的需要,但不主张使用。而《荀子·正名》中将文饰称为“丽”,认为这是表达的产物:“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荀子既认为命名本身就是文饰,必然带有“丽”的属性,可以实用文饰;又认为文章所表达的意思,应该避免以丽名惑实:“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啧然而不类,誻誻然而沸,彼诱其名,眩其辞,而无深于其志义者也。”荀子能够理解文饰的功用,但明确反对无用于是的文辞雕饰和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
两汉学者对于文学表意的理解,正是站立在文质彬彬的经学立场上,仍以言意相称的标准衡量文学。但问题是,周秦语境下的文学,儒家基本指的是礼学,而诸子所言的基本是论辩。二者虽然涉及到夸饰、象征、比喻等文学技法,但因其所涉及的内容多在于明理,文学性的特征尚不明显,因而这些讨论的要点在于何者为重、何者为轻。至于汉代,随着辞赋创作的繁荣,作品中作为“文”的形式要素如夸饰的修辞、虚构的手法和华美的语言,与作为“质”的教化、讽谏、明理等实际功能出现了较大的分野,文学如何表达,便成为这一时期学者们的困惑。
一个时代的困惑必然要成为这个时代讨论的焦点,虽然并不能够得到解决,但讨论注定很热闹。扬雄意识到文与质的问题不可回避时,便试图将二者分开讨论。他在评价“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时,采用了“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进行分类处理。[3]49其所谓的“诗人之赋”,显然是基于经学立场而进行创作的赋,是以《诗经》中的赋法作为标准,讲求雅正规则之美。基于文学立场而进行的赋作,则可以奢侈相胜,靡丽相越,不必归于正。*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辨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杨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严可均辑:《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19页)扬雄早年创作辞赋的经验和后来的经学立场,使得他固守“质胜于文”的古文经学视角,[4]对“文丽用寡”的辞赋进行了批评,认为“雾縠之组丽”为“女工之蠹”,提出“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主张以经学标准衡量文字的表达:“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3]164他反对不合经义、经法的文字,要求经言合乎经学原“道”的要求。[5]
但扬雄无法回避的是,他自己所创作出大量“丽以淫”的辞赋,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潮流,无可回避,也无法阻止。扬雄只能从理论上表明自己的立场,是要求辞、事相符合:“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3]60认为文章将事功、辞美相辅相成,才合乎经典之道。但他不得不承认文质彬彬的要求,已经无法实现:“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鞶帨,恶在老不老也?”[3]222认为当时的风气,不仅在辞赋创作上华美过甚,而且在经学解释上也虚辞过滥。这种虚浮的学风,班固言之为“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1]1723范晔言之为“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6]2588正是对两汉之际虚浮学风影响下的文风之批评。扬雄对这种学风和文风提出的解决办法,便是要求作者自我约束,学风上要“约而解科”,即简约而有条理;文风上要“言必有中”,即中正而不淫丽。
由此观察王充《论衡》中的观点,就会发现其所面临的困惑与扬雄一样,那就是以经学立场要求文学。经学用意在于经世,即建立一个能够超越朝代而形成的群体共识和价值认知,其寻求的是众人认知的一致性。而文学的用意在于抒写情志,即表达个人的一己之情,是个人情感、认知和思考的独特表达,其指向于表达的个性化。这样一来,经学的理论既解释不了文学发展出现的新命题,也使得经解者对经典中的表述也充满了困惑。如王充在《艺增》《儒增》《语增》中对前代经典中“文过其实”的描述进行的责难,正是对文学表意功能的一种抵触。[7]他反对“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因此对前代典籍中的修饰性描述、技巧性表述都予以驳难。这显然是因为固守经学立场,而对文学表意存在较深的误解,让王充在看似有理的讨论中不断兜着圈子批评指责文学的修饰。
我们还可以用《论衡》文本的记述来透视东汉中期的文学风尚。《论衡·艺增》言:“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盖伤失本,悲离其实也。”王充认为言过其实、辞过其事的夸饰修饰, 是时人好奇所致。可以看出,王充时代文学修饰已经形成,而且成为写作的潮流。《自纪》又言:“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悦虚妄之文。何则?事实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既然大家都这么俗,那自己就固守经学立场,以保守者的心态来做中流砥柱,对流俗进行大无畏的批评和抵抗。王充由此确定自己著述的用意在于“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8]1179立志于此,与流俗抗争。在这抗争中,王充有来自于经学的理据,不仅自信,而且坚强。例如,他继承了“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道德判断,认为“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8]1149将繁丽之文视为俗人、小人所为,鼓励君子抱道不屈,固守经训,赞扬述而不作的世儒,反对“为华淫之说,于世无补”的文儒。
与扬雄一样,王充不得不承认,东汉的儒生已经不再固守家法师法,抱残守缺,他们已经开始将著述作为事业。王充用“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进行分类,承认著述不仅是文人所尚,而且是鸿儒所为。也就是说,王充尽管对文学手段排斥,反对虚辞滥说,但并不反对著述本身,他甚至赞扬文人、鸿儒“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论说古今,万不耐一”,认为他们“衍传书之意,出膏腴之辞,非俶傥之才,不能任也”。[8]606他又言“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笔能著文,则心能谋论,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观见其文,奇伟俶傥,可谓得论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杰也”。[8]609由此来看,王充意识到著述的表意,是无法回避“膏腴之辞”,能为繁文,已经成为东汉以来的创作倾向:“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8]1174这种倾向与此前所谓的好奇、好俗遥相呼应——王充既然要批判好俗好奇的学风文风,就必须对桓谭、班固、傅毅之人的创作一并否定,由此上溯,对五经中的修饰之辞大量篇幅一并否定。
王充《论衡》的逻辑困境正在于此,那便是东汉经学和文学已经开始分化。若以经学的教义立场审视文学的形式,不仅无助于解释文学的表达,而且也会扭曲经学自身的表达。王充著《论衡》的目的,是反对华伪的文风,期望“实虚之分定,而后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8]1180他以经学正则传统纠正东汉学风之虚浮、夸伪,在经学史上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在思想史上也具有相当的地位。但其恰处在文学表达技巧被强化、文学修辞日渐形成的历史阶段,以经学立场审视文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将文学纳入到经学的轨道进行臧否。而经学立意于经世,文学立意于审美,二者旨趣不同,因而其呈现形式也存在差异:经学为世人示范,故而以文风讲求正则,格调注重中和;而文学重抒情达意,故而文风要求奇伟,情调重乎多姿。
以经学眼光审视文学,其优点在于强化文为世用的目的,可以形成文学的教化观;其缺点也在于这种强化要求文学以干预社会生活为目的,会削弱文学的个性化表达。如班固所言的“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1]1756他在承认辞藻之美的同时,要求文学能够担负起经学的使命。从文学的功能来看,这一要求并不过分,因为文学要承担着“兴、观、群、怨”的责任。但从文学的特质上来看,在文学技法尚未形成、文学特质尚未明确、文学表意功能尚在讨论的过程中,过于强化文学的现实功用,并以之作为衡量文学得失的尺度,会不可避免地损害文学的自我成长。两汉之际文学观念的徘徊不前,正在于学界以经学的眼光审视文学,忽略了文学特有的因唯美而夸饰、因蓄情而象征的表意手段,在理论上强化质实、正则的要求,使得文学认知难以跳出经学的路径,在两汉间步履蹒跚。
二、著述实践与文学创作的自觉
扬雄、王充对文学表意特征的不解,在于其固守传统的经学立场,将“踵事增华”之类的文学技巧视为虚浮。他们也无法回避,两汉不断增加的辞赋创作和日渐丰富的著述,使得文学不仅成为新的表达方式,也成为一种创作的潮流。文学对经学立场的突破,不是理论性的逢山开路,而是实践中的水滴石穿。
西汉士人的文学才能,班固《汉书》多以能“属文”括之。如《汉书·楚元王传》言刘辟强“亦好读诗,能属文”;《贾谊传》言贾谊“能读诗、书,属文”;《桓宽传》言“宽为人温良,有廉知自将,善属文,然懦于武,口弗能发明也”等,不胜枚举。而被班固描述为“属文”之士者,非以经学取长,常以文章为长,如终军,“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军为谒者给事中。”从《汉书·终军传》所载来看,终军的属文之才,主要是能言事立论,自为新辞,而非专守经说。
从西汉学者的视角来看,“属文”之才更多是对撰文著述才能的肯定。贾捐之等人荐杨兴的上奏中,对杨兴的才能进行了如下描述:
……观其下笔属文,则董仲舒;进谈动辞,则东方生;置之争臣,则汲直;用之介胄,则冠军侯;施之治民,则赵广汉;抱公绝私,则尹翁归。兴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坚固,执义不回,临大节而不可夺,国之良臣也,可试守京兆尹。[6]2837
用董仲舒的策略、著述之业形容杨兴的文学才能,并以汉之名臣为喻,形容杨兴的文学、言辞、品行、能力、德望等。这些类比,显然是文学的夸饰,体现出贾捐之“言辞动天下”的功夫。后来因为石显作梗,贾捐之被处死、杨兴髡钳为城旦而结束,从中可以看出武帝时期对“属文”之士的界定,主要指以文辞之美进行著作。
在两汉间人看来,著述多由善属文者完成。比如,班固言《盐铁论》的撰成,便出于善属文的桓宽的手笔:“汝南桓宽次公,……博通善属文,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6]2903高诱也认为,正因为淮南王刘安的“善属文”,才使得他有兴致、有能力组织《淮南子》的编纂:“后淮南、衡山卒反,如贾谊言。初,安为辩达,善属文。……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自旦受诏,日早食已。上爱而秘之。……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9]2善属文,便是有着高人一等的文学表达能力。后人托名伶玄而作《飞燕外传》,也是其属文才能的自然流露:“学无不通,知音善属文,简率尚真朴,无所矜式,扬雄独知之。……有才色,知书,慕司马迁《史记》,颇能言赵飞燕姊弟故事。”[10]578由此可见,两汉所谓的“属文”,不仅限于撰写政论散文,或者编纂史书,而是指能著书立说、撰写带有虚构性质的文学作品。
范晔《后汉书》首立“文苑传”,既可以看成他的创造,也可以视为其对东汉“善属文”者大量涌现事实的无可回避。如果说西汉对属文之士的记述,大多数是对其文章撰写能力的肯定,那么东汉文人的“属文”,则是对他们层出不穷的文学才华进行概括。如北海敬王刘睦,“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6]557能为经注、赋、颂、史书。东观史臣言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11]在时人看来,属文之才并不局限于经著、政论,而是无所不在、无处不用。范晔言边让“少辩博,能属文。作《章华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6]2588擅长辞赋。司马彪史言蔡邕“通达有隽才,博学善属文,伎艺术数,无不精综”,[12]471在辞赋、碑铭等诸多方面体现出高人一等的文学才华。范晔眼中东汉文人的文学才华,不是出于西汉世儒、文儒那样的照本宣科,而是带有鲜明的文学创作属性。他曾言赵峻“志性聪敏,又能如属文,所制才藻,落纸如飞,下笔即成,都不寻覆也”。[12]728其所谓的才藻,便是指其既具有文学才华,又能为藻饰之文,很类似于扬雄所谓的“丽以淫”,也接近于曹丕提倡的“诗赋欲丽”,蕴含着更多的褒义。
东汉文学著述的实践,并非西汉儒生经注那样出于利禄与功名,而是出于一种立言的自觉。有些作家甚至主动拒绝政府的征辟,而宁愿隐遁起来著书立说,将著述作为一项事业。如班固在《答宾戏》中说:“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喻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尽管后来班固也曾出任窦宪幕僚并陷于党争,但其在永平年间确实将著《汉书》作为其事业追求。王充言自己著《论衡》,也是出于著述的自觉:
充任数不耦,而徒著书自纪。或亏曰:“所贵鸿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说纳,事得功立,故为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数黜斥,材未练于事,力未尽于职,故徒幽思属文,著记美言,何补于身?众多欲以何趍乎?”答曰:“……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禄泊,非才能之过,未足以为累也。士愿与宪共庐,不慕与赐同衡;乐与夷俱旅,不贪与蹠比迹。高士所贵,不与俗均,故其名称不与世同。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杨雄为双,吾荣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细,于彼为荣,于我为累。偶合容说,身尊体佚,百载之后,与物俱殁,名不流于一嗣,文不遗于一札,官虽倾仓,文德不丰,非吾所臧。……富材羡知,贵行尊志,体列于一世,名传于千载,乃吾所谓异也。”[8]1204-1205
王充这段话中,当然有怀才不遇的牢骚,但其面对他人的嘲弄,能够意识到立德、立言的重要性,远比位高有意义,并以此自勉,以此自信。这一表述,可以视为两汉学者已经在功名利禄之外,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新方式。其中的“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一段,代表着东汉学者对于著述之业的理性认知,也是对立言不朽的高度认同。以此观察曹丕所谓的“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13]720正得此泽被。
我们以王充这段话的立意来观察东汉士人对待著述的态度,可以看出东汉的文学实践,是建立在著书立说自觉追求之上的。如崔骃“常以典籍为业,未遑仕进之事”[6]1708,张衡更是如此:
……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载。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
……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捡遗文,毕力补缀。[6]1940
范晔描述了张衡的才华之高、性情之美:“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认为张衡才高而淡泊,多次拒绝政府征召,甚至直接婉拒大将军的招募,在于强调其文学创作,不是出于现实需求,而是出于立言的自觉。张衡后来在不得已而入仕后,曾在《表求合正三史》的上表中说:“愿得专于东观,毕力于纪记,竭思于补阙,俾有汉休烈,比久长于天地,并光明于日月,炤示万嗣,永永不朽。”从中最能看出张衡愿以“立言”为志业,毕生从事著述。
这种自觉著述的风气,不仅促成了王符“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6]1630;也促成了应劭撰述《风俗通义》:“今王室大坏,九州幅裂,乱靡有定,生民无几。私惧后进益以迷昧,聊以不才,举尔所知,方以类聚,凡三十一卷,谓之《风俗通义》。”[14]他见制度败坏、士风不振,遂愿以一己之力纂辑旧事,作为东汉改良风俗之用。此外,蔡邕在贬官之后,也曾上书灵帝,言自己“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6]3084,一度试图以著述终生。
桓灵时,这种自愿隐遁而以著述为业,成为士人的自觉风尚。仲长统“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常以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6]1644如果说王符的潜隐带有欲出不得而最终彻底放弃的成分,仲长统的不就则是明显的拒绝。拒绝的原因便是,仲长统清醒意识到游走于帝王周围所获得的所谓名分,不过是朝廷赏赐的暂时声名罢了,朝政日非背景下获得的声名,赢不得士林的敬重,只不过是狼藉的图腾而已,莫不如安心著述,自娱自乐。与此同时,侯瑾“徙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于世,故作《应宾难》以自寄。又案《汉记》撰中兴以后行事,为《皇德传》三十篇,行于世。……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称为侯君云”[6]2649;荀爽“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十余年,以著述为事,遂称为硕儒”[6]2056。如果说侯瑾、荀爽隐遁著述是个人选择的话,那么世人对他们的敬重而褒扬,则意味着汉末世人对立德、立言者的推崇。
敬重什么人,褒扬什么人,最能看出一个时代的风尚。东汉学者以立德为尚,以著述为业,拒绝征召,自行隐遁,不仅没有为朝廷所责难,反而为世人所赞颂,既意味着东汉士林一改西汉学者多汲汲仕进的功利之心,以清流自居,赓续了“太上立德”的传统;也表明东汉学界意识到“立言”是“名传于千载”的事业,自觉以著述为业,而不再将“立功”视为毕生之追求。由此开端,汉魏之际将文章著述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独立和繁荣。
三、东汉文学新风尚及其理论认知
东汉对文学的认知,一在于重视文章著述,二在于逐渐接受了文学重视修辞的新风尚。由创作实践的积累,到认知的清晰,文学重视修辞、虚构与夸饰的特征越来越被强化,文学也从经学的附庸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独立特征的艺术形式。
西汉时期所谓的文学,基本是指经学。如本始元年(前73)夏四月,汉宣帝因地震“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其所谓的“文学”,依然是指经学。元康元年(前65)秋八月,诏曰:“朕不明六艺,郁于大道,是以阴阳风雨未时。其博举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先王之术,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1]255所谓的通文学,实际是精通经学。元康三年(前63)又曰:“及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修文学经术,恩惠卓异,厥功茂焉。”[1]257其所言之事,便是即位前“师受《诗》、《论语》、《孝经》”等事。[1]238即便新莽始建国三年(11)诏“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石举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者各一人,诣王路四门”[1]4125后录取的文学,依然侧重于经学。
而至东汉,文学则更多具有“文章之学”的含义,多被用来形容著述等后世意义上的文学活动。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6]2613此文学之士的主要职能,不再穷究经学,而是以校书为业。班固也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1]4225其中,傅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6]2613文学之士更引人瞩目的作用,在于撰写文章。
章帝初即位,曾赐东平宪王刘苍书中言:“先帝每有著述典议之事,未尝不延问王,以定厥中。”[11]165相对于西汉通经学,东汉更重视著述。虽然此时的著述,尚多集中于经学章句学,如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又撰《礼内外记》,号曰《礼略》。又抄风角杂书,列其占验,作《兴》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余万言,数上书陈救灾变之术”[6]2572,其文学才能的重点已经转移到著述、编纂和撰写。东汉对文学之才的描述,更多指向于诗赋创作,如范晔言李胜“亦有文才,为东观郎,著赋、诔、颂、论数十篇”,[6]2616郦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论给捷,多服其能理。……有志气,作诗二篇曰……”,[6]2647张超“有文才。……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6]2652,并直言王粲、刘桢等皆“以文才知名”[6]1826,2640。
与朝廷提倡文章著述的风气相表里,民间的文学活动则更多体现为对文学技法的自觉追求,虚构性的文字开始大量出现,并且逐渐得到文士的喜爱。在盐铁辩论中,御史大夫们依然认为:“文学结发学语,服膺不舍,辞若循环,转若陶钧。文繁如春华,无效如抱风。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从之,则县官用废,虚言不可实而行之;不从,文学以为非也,众口嚣嚣,不可胜听。”[15]291-292他们将文学的修饰视为虚言,认为此类文字惑乱正道,不合雅驯。刘向在《条灾异封事》中也说:“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这段文字当然表明了刘向对浮泛文辞的抵触,但却可以看出文学表达已经在经学之外兴起,且成为一种时尚。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更是说:“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从中也能看出西汉后期朝廷官员对于玄奇文字的爱好。哀帝在《罢乐府诏》中明确说:“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文巧则趋末背本者众;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可以看出,朝廷对民间追逐文巧之风已经不甚满意,试图以罢免乐府来恢复雅乐传统。
东汉立国之后,一度反对虚言浮词,如光武帝《赐隗嚣书》中自己“厌浮语虚辞”,汉明帝也说:“先帝诏书,禁人上市言圣,而间者章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蚩也。”[6]109汉明帝主张文学要以质实为用,并批评“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13]682,显示出东汉初年朝廷仍坚守重质的文学观。但从这些诏书的口气中,已经透出东汉朝野对文学修饰功能的日渐喜爱。
王充在《论衡》中多次言及世俗之好虚妄:“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这里所谓的奇,一是故事之奇,如刘歆所言朝士多好《山海经》;二是文字之奇,即用全新的表达形式,不再如经典般古奥。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蜚流之言,百传之语,出小人之口,驰闾巷之间,其犹是也。诸子之文,笔墨之疏,人贤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实,犹或增之。”[8]381修饰、夸张之法不断增多,文学的表达技能愈加出奇。在王充看来,这类文字常常“言事粗丑,文不美润,不指所谓,文辞淫滑”[8]617,但这类文字的作者,却常常得到朝廷的重用。王充还认为,受文学风气的影响,东汉的经学也“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8]1123经说的无凭之增,使得东汉学风由质实转而玄虚,著述成为东汉学者施展才能的新领地:“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8]1179王充站在经学的立场审视东汉文学的新风尚,对“言奸辞简,指趋妙远;语甘文峭,务意浅小”的新文风极度排斥[8]1200。
王符也曾描述章帝、安帝、顺帝时期文学风气的变动:“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恩,而长不诚之言也。”[16]19认为注重辞藻、多用夸饰、讲求技巧已成为东汉解经、作赋的基本风气。
从刘向、刘歆、哀帝、光武帝、明帝以及王充、王符对虚言浮词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注重修饰、强调技法越来越成为东汉文学的新风尚,不仅体现在经学著述中,而且体现在辞赋创作中。尽管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甚至打压,但文学风尚一旦形成,会逐渐成为一种创作潮流,不断销蚀保守的文学认知。从崔瑗对张衡的评价中,我们可以读出较为中和的文学观:“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与神合契。”[10]456崔瑗对张衡文章的辞采之美进行了高度肯定,可以视为东汉文士对文学新风尚的中肯之辞。
与之相应的是,东汉后期对屈原辞赋的评价,不再如班固那样以经学本位衡量屈原的讽谏之法,转而以文学本位审视其辞藻之美。王逸在《楚辞章句叙》中说:“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17]49王逸肯定了屈原华藻之辞美,他在《离骚经》中说:“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17]3对屈原辞才及人品双重肯定。玉逸又认为,《远游》“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17]163指出屈原的辞藻之美,为后世学者钦羡效法。而且他还认为王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溷浊,莫之能识,追而愍之”,而作《九怀》。[17]269王逸从人品、辞藻、文笔、文风上着眼,尤其注重屈原辞赋体现出来的文学特质,不再局限于经学雅驯的立场。
新的文学风尚获得官方承认,在于汉灵帝时期设立鸿都门学,并以辞赋之士选用官吏。由于固守经学取士的传统,汉灵帝采用直接敕封的方式任命文学之士为官,不仅扰乱了东汉的选官制度,而且成为时人诟病文学才能的一个理由。蔡邕便直言鸿都门下“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6]1996要反对文学取士,就必须反对文学的功能,蔡邕尽管创作了大量的辞赋,但仍将矛头对准当时流行的通俗而浅白的辞赋创作,认为这些赋作本无多少价值,赋家更无才能,汉灵帝居然待以不次之位,是对汉代取士制度的彻底扰乱。
关于鸿都文学,后世有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鸿都门学的文学价值不足道,刘勰曾言:“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18]673刘勰不屑于鸿都之赋及其作者,延续了蔡邕的见解,但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即由于灵帝的提倡,东汉后期形成了一个短暂的文学创作热潮。刘永济便说:“灵帝以后,学贵墨守,文亦散缓,其时作者,类多浅陋,比之俳优;文章风气,由盛而衰,此五变也。”[19]151认为鸿都门学的浅陋之辞,是文学衰败风气的开始。站在经学的立场观察,可以认为鸿都文学并不能成为一个文学集团,不能拔高其文学史意义;[20]二是认为建安文学重视作品辞藻、讲求文学技巧的风气,恰导源于此。何焯曾言:“建安词人,后魄兆于此矣。”[21]1686范文澜亦说:“按东汉辞质,建安文华,鸿都门下诸生其转易风气之关键欤?”[18]681认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在于对东汉形成的重视辞藻之美的文学风尚得以延续,其中辞赋的大量出现,不仅促使了文学技巧的发展,而且通过赋法为诗,促进了诗歌题材与样式的出新。这里所说的“大量”,不仅是指东汉著名作家作品的不断增多,而且指在民间出现了众多的辞赋作家,即蔡邕所谓的“作者鼎沸”。尽管诸多赋家水平有限,但却对创作乐此不疲,这是文学繁荣的一个表征,也是文学大家得以出现的基础。因为,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更需要大量作者参与创作,才能推动辞赋创作技法的不断完善,并为大作家的出现提供创作经验积累,为文学繁荣提供创作人才的储备。由此观察,王充所谓的“言奸辞简,指趋妙远;语甘文峭,务意浅小”的文学风尚,与蔡邕所言的“连偶俗语,有类俳优”,皆体现了民间辞赋创作重视排偶、浅俗、抒情之风,而这不仅体现了东汉文学的下行,而且也契合了汉魏辞赋发展的总态势,可以视为建安文风新变的先兆。*毕庶春《鸿都门赋考论》,《文史哲》2012年第3期。参见张朝富《“鸿都门学”的建立与汉末“文人群落”重组》,《青海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钱志熙《“鸿都门学”事件考论:从文学与儒学关系、选举及汉末政治等方面着眼》,《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我们认为:文学作品评价可以以成败论英雄,但文学思潮的讨论和文学史线索的描述,不能以简单的成就论成败。鸿都文学的创作虽不能与此前明章时期、此后的建安时期相提并论,但其恰恰是二者转换的关键时期:一是从文学认知上,汉灵帝以文学之士取代经学之士出任州郡官员,扰乱了东汉的选官制度;但成长于民间的他能如此褒扬和鼓励文学新风尚,可以看作汉王室对文学脱离经学趋势的一种回应,而这一趋势,不仅代表了两汉文学发展的走势,也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走向。*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8曰:“呜呼!世愈移而士趋日异,亦恶知其所归哉!灵帝好文学之士,能为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乐松等以显,而蔡邕露章谓其‘游意篇章,聊代博弈’。甚贱之也。自隋炀帝以迄于宋,千年而以此取士,贵重崇高,若天下之贤者,无逾于文赋之一途。汉所贱而隋、唐、宋所贵,士不得不贵焉;世之趋而日下,亦至此乎!”参见《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2页。二是从文学思潮上来看,灵帝时期出现了以文学之才创作辞赋的热潮,蔡邕批驳的是以文学取士,但他本人不仅曾入鸿都门,而且大量创作远超过鸿都文学水平的俗赋,更重视文学辞藻和骈偶句法,代表了包括鸿都文学在内的辞赋创作的新倾向。而“鸿都”也由于重视文才被视为文笔之工、辞藻之美的象征*庾信《为杞公让宗师表》曰:“臣幼无学植,长阙裁成。鸿都之门,不能定其章句;鸡鹿之塞,无以名其碑碣。……臣有何德,能兼此荣。”(《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46页)欧阳修《又上李学士启》曰:“仰惟俊望,允彼佥谐,入聚石渠之书,坐擅鸿都之笔。”(《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479页)。
汉魏之际的著述,不仅延续了东汉重视著述的传统,而且更加注重辞藻;文学的特征不仅得以凸显,而且更为清晰地得以表述。受灵帝影响,“献帝颇好文学,(荀)悦与彧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6]2058。此事发生在建安元年至三年间,当时荀悦任秘书监侍中,荀彧以侍中守尚书令,孔融任将作大匠,三人长于史笔、政论和经学。如荀悦“能说《春秋》。……尤好著述。……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6]2058是为政论。献帝又“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荀悦于建安三年完成呈上[22]631,是为史笔。荀彧长于策略,居中持重,曹操“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23]311,荀彧长于谋议,其能言者,多为政论。而孔融长于经说,其任职时,“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绵隶名而已”[6]2264,成为建安经学名家。汉献帝所好的文学,兼采史论、策论、经说,且多以著述出之,遂开魏晋著述之风。由此观之,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繁荣,正是对东汉文学风尚的继承和发扬。陈寿言曹丕“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以魏王太子之重,组织文士著述。从汉臣的角度来看,是对建安文学风尚的响应;从此后魏文帝的身份来看,其“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23]88,则是对文学创作的引导、示范和鼓励。他的这种创作自觉,正是基于文学观念的自觉,其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论,便是对属文、著述的文化意义的高度概括。以此为开端,中国文学以其辞采之美、结构之巧、技法之工,成为独立的艺术样式。
参考文献:
[1]〔汉〕班固,颜师古.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汉〕刘熙.释名[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汪荣宝.法言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孙少华.扬雄的文学追求与文学观念之迁变[J].清华大学学报,2012(1):101-118.
[5]束景南,郝永.论扬雄文学思想之“文质相副”说[J].文艺理论研究,2007(4):83-87.
[6]〔南朝宋〕范晔,〔唐〕李贤.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时永乐,智延娜.清人不重视校注<论衡>之原因[J].河北大学学报,2011(6):79-82.
[8]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9]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清〕严可均.全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1]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2]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3]〔南朝梁〕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4]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5]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6]彭铎.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宋〕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9]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0]张新科.文学视角中的“鸿都门学”:兼论汉末文风的转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1):103-108.
[21]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2]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3]〔西晋〕陈寿,〔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4.
(责任编辑钟昭会)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6)01-0149-10
作者简介:曹胜高(1973—),男,河南洛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与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国家建构与中国文学格局之初成”(12BZW059);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国家建构与两汉文学格局的形成”(12YJC751005)。
收稿日期:2015-11-12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