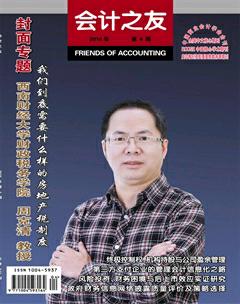行为审计处理处罚配置:理论框架和经验数据分析
郑石桥 张翔



【摘 要】 行为审计处理处罚配置是处理处罚的制度框架,涉及理论基础、宏观配置和微观配置三个层面。处理处罚配置的理论基础包括配置目的和如何配置两个理论问题,配置目的是惩处功能和预防功能的统一;如何配置是违规惩处相应,认为违规行为对经管责任的危害是衡量处理处罚的真正标尺。处理处罚宏观配置搭建处理处罚的主体框架,主要包括:处理处罚主体、处理处罚对象、处理处罚立法模式、处理处罚类型和位阶。处理处罚微观配置主要涉及各类处理处罚在各类违规行为上的配置,主要包括:处理处罚配置模式、处理处罚自由裁量权、针对各类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规定。
【关键词】 行为审计; 审计处理处罚配置; 审计处理处罚类型; 审计处理处罚位阶; 审计自由裁量权
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4-0117-08
一、引言
一般来说,行为审计对于发现的违规行为要予以处理处罚。审计处理处罚涉及诸多问题,本文关注其中的审计处理处罚配置问题。审计处理处罚配置是指审计处理处罚种类、总量的分配和布置,以及审计处理处罚在各类违规行为上的分配和布置。显然,它是如何处理处罚的制度框架设计,是审计处理处罚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直接影响审计处理处罚的效率效果。同时,不同的审计处理处罚配置还会产生不同的实施成本。因此,审计处理处罚配置是审计处理处罚的一个重要且基础性的问题。
现有文献涉及到审计处理处罚权配置、审计处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等,然而,大多数的审计处理处罚配置问题都鲜有文献涉及。本文借鉴刑罚配置理论,构建审计处理处罚配置理论框架,并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配置。随后的内容安排如下:首先是一个简要的文献综述,梳理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借鉴刑罚配置理论,以违规行为为背景,提出审计处理处罚配置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配置经验数据,以一定程度上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
根据本文的主题,相关文献包括两类,一是审计领域中对审计处理处罚配置相关问题的研究,二是刑罚配置理论。
审计处理处罚有不少的研究文献,涉及审计处理处罚配置的研究主要有审计处理处罚权配置、审计处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两方面。关于审计处理处罚权配置,一些文献从理论上分析审计处理处罚权的属性及其配置(刘强,1996;胡智强,2009;魏昌东,2010;胡贵安,2012),但是,关注的焦点是执法主体中没有明确标明审计机关的违规问题,审计部门是否有处理处罚权?针对这个问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凡是法律法规的执法主体中没有明确标明有审计机关的,审计机关就没有处理处罚权;另一种观点认为审计机关作为综合经济监督部门,可以依据不同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处罚,不管法律法规中规定的执法主体是谁,审计机关都可以进行处理处罚(张宗乾,2002;郝婷,2010;程度平,2011)。关于审计处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研究,主要涉及自由裁量权在审计处罚中的主要表现、审计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要求、存在问题及对策(陈妙松,2010;谢开盛,2013;王广庆,2013)。
刑罚配置有许多研究文献,主要涉及刑罚配置的理论基础、法定刑配置模式、刑罚配置原则、刑罚配置目的、刑罚配置实现路径、刑罚配置合理性(周光权,1998;周光权,2000;邓文莉,2009;蔡一军,2009;蔡一军,2011;魏柏峰,2012)。此外,还有不少文献研究各种具体犯罪的刑罚配置(欧锦雄,1998;邓文莉,2008;万国海,2008;刘宪权,2011)。
上述文献综述显示,总体来说,关于审计处理处罚配置并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许多问题鲜有文献涉及,而刑罚配置理论的相关研究对审计处理处罚配置有较大的启发性。本文借鉴刑罚配置理论,构建审计处理处罚配置理论框架。
三、行为审计处理处罚配置:理论框架
审计处理处罚配置是如何处理处罚的制度框架设计,涉及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层面来说,是指审计处理处罚种类、总量的分配和布置,主要涉及审计处理处罚种类的选择和配置以及处理处罚体系的建构;从微观层面来说,是指审计处理处罚在各类违规行为上的分配和布置,主要涉及各类审计处理处罚在各类违规行为上的配置(董淑君,2004)。在此之前,无论是宏观配置还是微观配置,都有一个理论基础问题。因此,本文提出的行为审计处理处罚配置理论框架包括三个问题:理论基础、宏观配置、微观配置。
(一)审计处理处罚配置的理论基础
行为审计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具有准司法性质,所以,需要借鉴刑罚配置的理论基础来构建审计处理处罚的理论基础。
法学中的刑罚配置理论基础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刑罚;二是如何刑罚。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一般来说,“为什么要刑罚”会影响“如何刑罚”。
关于“为什么要刑罚”,基本上可分为报应刑论、目的刑论和合并论三类,报应刑论认为,刑罚的本质是报应,是要对犯罪这种恶因给予恶报而存在的;目的刑论也称功利刑论,这种观点认为,刑罚并非是对犯罪的报应,而是预防将来犯罪,保护社会利益的手段;合并论一方面承认刑罚是对犯罪的报应,同时主张刑罚具有预防目的(马克昌,1995;邱兴隆,1998;刘军,2014)。
关于“如何刑罚”,历史上出现过三种刑罚配置理论:同态相应的刑罚配置理论、罪责相应的刑罚配置理论和刑罚个别化的刑罚配置理论(蔡一军,2009)。同态相应的刑罚配置理论是以犯罪的具体形态为考察基点来配置刑罚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刑罚配置应当与犯罪绝对对应,也就是严格针对犯罪的形态和严重程度来对犯罪人配置绝对相同的刑罚。同态相应论折射了朴素的“公平”刑罚观,但是,这是复仇式的刑罚配置,带有野蛮性。罪责相应的刑罚配置理论是指要求以抽象化后的犯罪严重性为考察基点配置刑罚的理论,也就是应对犯罪的结果或行为以及主观过错的严重性进行抽象性的认识和评价,并以稳定的刑罚种类与其相联系。许多学者主张这种理论。黑格尔(1961)认为,犯罪是触犯法律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责罚,国家根据法律的规定,对犯罪人予以惩罚,以维护社会的正义。贝卡里亚(1993)认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刑罚个别化的刑罚配置理论以犯罪人之个别情况为配置基点,认为刑罚的轻重应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来配置,它以刑罚的矫正与预防为目的,认为犯罪本质应从犯罪人的反社会性格去探究,而不能从客观行为及结果来判定。
一般来说,刑罚目的会影响刑罚配置理论。报应刑论主张刑罚配置的绝对理论,认为刑罚配置的唯一基点在于犯罪的严重性。因此,报应刑论可能主张罪责相应的刑罚配置理论,也不会否定同态相应的刑罚配置理论。功利刑论主张刑罚配置的相对理论,认为犯罪的严重性只是刑罚配置的基点之一而已,最终决定刑罚配置结果是如何实现预防犯罪的功能,因而理想的刑罚配置基点应当包括两方面:首先,刑罚应与犯罪对应,大致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其次,刑罚应与预防犯罪的目的相对应,尽可能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显然,功利刑论会主张刑罚个别化的刑罚配置理论,也一定程度上会接受罪责相应的刑罚配置理论。
就行为审计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来说,其目的或功能应该是惩处功能与预防功能之统一①,所以,需要选择这两种目的都能接受的配置理论,这就是罪责相应的刑罚配置理论。事实上,上述三种刑罚配置理论,同态相应的刑罚配置在文明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基础;刑罚个别化的刑罚配置理论强调了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而罪责相应的刑罚配置一方面体现了刑罚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则兼顾了刑罚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功能。因此,罪责相应的刑罚配置理论较好地兼顾了报应刑论和功利刑论。
借鉴罪责相应的刑罚配置理论,不妨称行为审计处理处罚配置理论为违规惩处相应理论,也就是说,违规行为对经管责任的危害程度是衡量处理处罚的真正标尺,要以抽象化后的违规严重性为考察基点来配置审计处理处罚,需要对违规行为的结果以及主观故意的严重性进行抽象性的认识和评价,并以稳定的审计处理处罚种类与其相联系。
(二)行为审计处理处罚的宏观配置
审计处理处罚的宏观配置搭建审计处理处罚的主体框架,主要涉及如下问题:审计处理处罚的主体、审计处理处罚的对象、审计处理处罚的立法模式、审计处理处罚的类型和位阶。
1.行为审计处理处罚之主体
行为审计处理处罚主体是指行为审计发现违规问题之后,针对该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决定由谁来作出。这里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审计机构是否就是审计处理处罚机构;第二,如果审计机构是处理处罚机构,专门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标明审计机构能处理处罚的违规问题,审计机构是否有处理处罚权?
行为审计发现违规行为之后,是由审计机构来处理还是由其他机构来处理,这是审计处理处罚主体配置的基本问题。实践中有多种模式,总体来说,有两种情形,一是由审计机构来处理处罚,例如,政府审计是属于司法系列或隶属于行政部门时,就属于这种情形,许多内部审计机构也有处理处罚权;二是由其他机构来处理处罚,例如,政府审计体制属于立法机构或不隶属于任何机构时,就属于这种情形,许多内部审计机构没有处理处罚权,民间审计机构基本上也没有处理处罚权。现实生活中的多种模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总体来说,审计只是委托人、代理人共同构造的治理机制的组成要素之一,审计权配置到什么程度,需要从治理机制的整体构造来考虑,而不能就审计论审计。审计处理处罚权配置给什么机构,核心的问题是处理处罚的效率效果,何种机构持有这种处理处罚权的效率效果好,这个权力就应该配置给该机构(为简化起见,后续内容中称其为审计处理处罚机构)。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专门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审计处理处罚机构能对该法律法规约束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理处罚时,审计处理处罚机构能否对该类违规行为进行处理处罚呢?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审计处理处罚机构无权进行处理处罚,理由是,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主管部门是处理处罚主体,只能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处罚,审计处理处罚机构没有处理处罚主体资格(刘强,1996;张宗乾,1998;张宗乾,2002)。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审计处理处罚机构有权进行处理处罚,理由是,审计相关的法律超常规赋予审计处理处罚机构具有有关法律法规的处理处罚主体资格,审计处理处罚机构据此完全有权进行处理处罚,不是越权行为(陕西省审计厅课题组,2008;郝婷,2010;程度平,2011)。
笔者赞同审计处理处罚机构有权进行处理处罚的观点。专门的法律法规的制裁规则中可能没有明确法院有对违反该法律法规的犯罪行为具有司法权,这并不影响法院对这些犯罪行为具有司法权,因为法律赋予了法院对所有犯罪行为的司法权。许多的法律法规都有其主管部门,在这些法律法规的制裁规则中,明确规定了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权,可能没有明确规定审计处理处罚机构具有处理处罚权,而审计相关法律法规赋予了审计处理处罚机构这种权力,所以,如同法院对所有犯罪行为具有司法权一样,审计处理处罚机构对所有属于审计管辖范围的违规行为都具有处理处罚权。
2.行为审计处理处罚之对象
行为审计当然是以违规行为作为处理处罚之基础,但是,违规行为是有行为主体的,所以,行为审计要处理处罚的客体应该是违规行为之主体。借鉴单位犯罪理论,本文认为,根据违规责任自负原则,违规行为的类型决定审计处理处罚对象之选择。如果是为了单位利益而实施的违规行为,则责任人意志和单位意志达到对立统一,此时的审计处理处罚对象应该是责任人和责任单位,采用双罚制;如果责任人完全为了自己的利益,违规行为只是体现责任人自己的意志,此时的审计处理处罚对象应该是责任人,不包括责任单位②。
3.行为审计处理处罚的立法模式
行为审计处理处罚的立法模式是指行为审计中对违规行为处理处罚规则的建立模式,类似于刑法中的经济刑罚立法模式。综观世界各国,经济刑罚的立法模式有三种:普通经济刑法模式、单行经济刑法模式、附属经济刑法模式(孙建伟,1987;李建华,2001)。普通经济刑法模式指把经济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内容集中规定于刑法典之中;单行经济刑法模式指专门制定经济刑法典,用以规定经济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和刑罚;附属经济刑法模式指把经济刑罚引入民事、商事、经济、行政等法律法规中,并在其中规定经济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和刑罚内容。我国的经济刑罚立法采用普通经济刑法模式和附属经济刑法模式的混合式立法模式,把经济犯罪的内容同时规定在刑法典和单行法规中(李汉军,2010;韩小莲,2013)。
从行为审计处理处罚规则的建立来说,笔者主张比经济刑罚更加宽泛的混合模式,要建立三个层级的违规行为处理处罚规则,第一个层级是通用的违规行为处理处罚规则,适用于所有违规行为,例如,建立适用于党的纪律检查、行政监察、审计的违规行为处理处罚规则,这个层级的处理处罚规则可以做到各类处理处罚之间的平衡;第二层级是审计机构专用的违规行为处理处罚规则,由于审计关注的行为一般是与经管责任的履行相关,这个层级的处理处罚规则专注于经管责任履行中的违规行为;第三层级是各种专门的经济、行政等法律法规中设置专门的章节来规定对于违背本法律法规的行为之处理处罚规定。
上述三个层级的处理处罚规则中,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都属于从横向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之规定,二者只是规范的违规行为范围不同;第三层级属于从纵向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之规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显示,混合模式下,各层级的处理处罚规则都是针对违规行为,所以,事实上是具有多重覆盖,也就是说,同一个具体的违规行为,在不同层级的处理处罚规则中都有规定。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协调,从规则的阶位来说,专门法律法规最高,通用的处理处罚规则次之,审计专用的处理处罚规则最低。所以,审计专用的处理处罚规则应该包容或补充通用的处理处罚规则,而二者应该包容或补充专门法律法规。
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了避免专门法律法规的处理处罚规则与另外两个层级处理处罚规则的不协调,在专门法律法规中干脆不设置处理处罚规则。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在专门法律法规中设置处理处罚规则,是保证专门法律法规的科学性、完整性和实际效力的需要。任何一个法律法规都必须具有假定、处理、制裁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否则就不是完整的法律法规,而三要素中的制裁部分,是保证这一法律法规实际生效的关键部分,如果缺了它,专门法律法规就形同虚设(王金滨,1984)。
4.行为审计处理处罚的类型及位阶
行为审计处理处罚措施的构建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处理处罚类型,主要是指具体的处理处罚方式或手段;二是处理处罚的位阶,主要是指审计处理处罚因其严厉性程度不同而呈现的序列性层次。处理处罚类型和位阶是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有不同的处理处罚类型,才会呈现位阶;也正是需要有位阶,才会出现不同类型的处理处罚措施。
审计处理处罚配置中的位阶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了处理处罚位阶,处理处罚可达到区别不同危害程度的违规行为之目的,针对越严重的违规行为,施予越严厉的处理处罚。因此,处理处罚对违规行为的抑制力将随其危害程度而上升,处理处罚发挥惩处和预防违规的功能也在此过程中得以实现。如果对于不同危害程度的违规行为施予同样严厉程度的处理处罚,则不仅会破坏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的公正情感,影响审计权威性,更会因其处置的不公正性而抑制处理处罚的惩处和预防违规行为的效果。因此,处理处罚位阶的有效配置是保障处理处罚功能的制度设计前提(蔡一军,2009)。
前已叙及,行为审计处理处罚对象包括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而处理处罚措施基本上可以分为行政处理处罚和经济处理处罚,上述两个维度结合起来,审计处理处罚类型总体情况如表1所示。
然而,基于处理处罚位阶的考虑,对行政处理处罚和经济处理处罚还需要设置不同类型,确定不同位阶。综合《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200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06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2010年修订)关于处理处罚的规定,针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处罚类型及位阶如表2所示,针对责任人的处理处罚类型及位阶如表3所示③,表中的位阶是笔者经过对各种处理处罚措施的严厉性考量之后确定的,原来的法律法规中并没有明确它们的位阶,经济处理处罚类型和行政处理处罚类型的位阶之间无对等关系。
当然,针对责任人或责任单位的罚款,本身也存在配置问题,也有多种模式可供选择(欧锦雄,1998;徐向华、郭清梅,2006;邓文莉,2008),限于本文篇幅,这里不展开讨论。
(三)行为审计处理处罚的微观配置
刑罚配置的核心是解决犯罪与刑罚的量度对应关系问题,在范围上包括对特定犯罪的法定刑的确立和判定刑的裁量(Sebba,1978)。行为审计处理处罚的微观配置主要涉及各类审计处理处罚在各类违规行为上的配置,也就是将各类型、各位阶的处理处罚落实到各种类型的违规行为。一般来说,主要包括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行为审计处理处罚的配置模式,二是行为审计处理处罚的自由裁量权,三是针对各类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规定。事实上,前两个问题是微观配置中较为原则性的问题,最终要体现到各类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规定。第三个问题过于细致和庞大,限于本文篇幅,不能展开讨论,这里只阐述前两个问题。
1.行为审计处理处罚的配置模式
行为审计处理处罚的配置模式是指如何将各类审计处理处罚配置到各类型的违规行为。在法学领域,如何将各类刑罚配置到各种类型的犯罪称为法定刑配置模式,主要有三种模式:绝对确定模式、绝对不确定模式、相对确定模式(周光权,1998)。绝对确定模式主张刑法条文对某一犯罪只规定一个没有量刑幅度的刑种。绝对确定模式使刑罚明确化,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以收刑罚公正之功。但是,由于人类有限理性,无法以列举的方式穷尽地建立不同危害与不同刑罚的对应关系,所以,绝对确定模式显然缺乏针对性,无法根据每一种犯罪的具体情节判处轻重适当的刑罚。绝对不确定模式主张在法律条文中只抽象地规定对某种犯罪判处的刑罚,但并未具体规定刑种和刑度的情形。这种模式认为,设置法定刑的目的是威慑和改造犯人、预防其重新犯罪,而改变人的行为方式的种种因素也是复杂的,所以,立法者很难预设出一个使犯人改恶从善的时间和惩罚严厉程度,因此,法定刑只能是不确定的。事实证明,绝对不确定模式不利于实现罪刑均衡。相对确定模式主张刑法条文对某一犯罪明文规定刑种和量刑幅度,并针对犯罪的情节,规定最高刑和最低刑。这种相对确定模式既有明确的限度,又在此限度内赋予法官一定的灵活性,有利于实现罪刑均衡。但是,相对确定模式存在自由裁量权问题。
就行为审计处理处罚的配置模式来说,笔者倾向于相对确定模式。现实世界是复杂的,违规行为的产生原因也很多,具体情节更是多种多样,无法事先设想到违规的具体状况,所以绝对确定模式不能采用。相反,如果不具体规定各类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类型及幅度,审计处理处罚机构可以无限制地自由裁量,可能影响审计处理处罚的公正性。因此,绝对不确定模式不能采用。相对确定模式对某一违规行为明文规定处理处罚的类型和幅度,并根据违规行为的具体状况,规定最高幅度和最低幅度。这种模式下,既有明确的限度,又在此限度内赋予审计处理处罚机构一定的灵活性,有利于实现违规与惩处的均衡。当然,这种模式下,可能存在审计处理处罚机构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
2.行为审计处理处罚的自由裁量权
法学领域中有大量关于自由裁量权的研究(司久贵,1998;江必新,2006;董玉庭、董进宇,2007;辛建华,2009)。这些研究对于审计处理处罚自由裁量权配置有较大的启发价值。至于审计领域,本文在文献综述中已经指出,审计处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研究主要涉及自由裁量权在审计处罚中的主要表现、审计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要求、存在问题及对策(陈妙松,2010;谢开盛,2013;王广庆,2013)。
借鉴法学领域自由裁量权理论,从审计处理处罚配置视角来说,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是否需要审计处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第二,如果审计处理处罚需要自由裁量权,如何控制滥用这种权力。关于是否需要审计处理处罚自由裁量权,在绝对确定模式、绝对不确定模式、相对确定模式中,审计处理处罚需要选择相对确定模式,当选择相对确定模式之后,审计处理处罚自由裁量权已经成为其核心内容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控制滥用审计处理处罚自由裁量权?先来看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自由裁量权是行政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共有四种控制模式:通过规则的命令控制模式,通过原则的指导控制模式,通过程序的竞争控制模式,通过监督的审查控制模式(王锡锌,2009)。通过规则的命令控制模式认为,自由裁量是法律规则供给不足的产物,因此,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制定明确的规则,明确地表达某种命令和指令,执法者必须依照这一指令进行处理,失去了判断、选择和斟酌余地,裁量余地很小。在目前的行政实践中,各种裁量基准就是通过规则的命令控制模式的典型例证(余凌云,2008)。通过原则的指导控制模式认为,法律规则总是显得滞后,而基本原则可以为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现实提供基本调控框架,所以,原则的控制提供了原则与弹性,在承认自由裁量存在的现实及其合理性基础上,通过基本原则的指导性功能,一方面为自由裁量权行使划定基本框架,另一方面又使执法者保留一定的判断、斟酌和选择空间。通过程序的竞争控制模式从程序上对行政主体行使裁量权的行为进行控制,这种控制技术的要旨是,在自由裁量过程中的所有行动者在程序规则导引下进行知识交流和理性讨论,构成一种竞争和制约机制,从而防止行政裁量权非理性的行使。这种控制所强调的核心技术是当事人的有效参与,通过设定行动者的相互关系结构来使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和结果符合理性化的要求。通过监督的审查控制模式是通过权威主体依据预先的标准对权力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审核和判断,它是一种事后监控和校正机制。
上述各种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模式,在审计处理处罚中都已经有所应用,不少审计机构制定了审计自由裁量基准,并且还确定了审计自由裁量的一些原则,这是应用通过规则的命令控制模式和通过原则的指导控制模式;一些审计机构实行内部机构的审计权分离,甚至是审计听证,这是应用通过程序的竞争控制模式④;所有审计机构都建立了质量控制机制,这是应用通过监督的审查控制模式。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各种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模式之间不是相互独立和排斥的,由于审计自由裁量权存在原因的多元性、情形的复杂性,意味着单一的控制模式无法完成对审计自由裁量权的良性控制,理想的情形应当是将不同的控制模式进行整合,形成立体的审计自由裁量权控制体系。
四、行为审计处理处罚配置: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经验数据分析
以上提出行为审计处理处罚配置的理论框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能用上述理论框架来全面分析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配置。但是,本文用经验数据来描述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效果,以此为出发点,从若干审计处理处罚配置因素的视角来分析其原因。
(一)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效果
本文采用“每个审计项目平均违规金额”的变动情况来刻画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效果,每个审计项目平均违规金额=违规金额/审计单位数。根据最近10年《中国审计年鉴》“全国审计机关分行业审计(调查)情况表”,不同类型审计项目的每个审计项目平均违规金额计算如表4所示。
表4中的数据显示,“每个审计项目平均违规金额”并不是呈现下降趋势,而是上升趋势⑤。总体来说,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并未能实现其预期效果。
(二)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配置存在的若干问题
从审计处理处罚配置视角来分析我国审计处理处罚并未能实现预期效果的原因,涉及宏观配置和微观配置的许多因素。由于篇幅所限,再加上公开数据方面的限制,本文仅分析审计处理处罚主体和对象两个因素对审计处理处罚效果的影响。
1.行为审计处理处罚主体配置对审计处理处罚效果的影响
我国的审计处理处罚主体有多种情形,一是审计机关自行处理处罚;二是移送司法机关惩处;三是移送纪检监察部门处理处罚;四是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处罚。多个审计处理处罚主体存在协同问题,表现为移送处理处罚最终落实情况。根据近10年《中国审计年鉴》“全国审计机关分行业审计(调查)情况表”,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如表5至表7所示。
表5至表7数据显示,审计移送案例或事项的落实情况并不好,其原因是审计处理处罚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存在问题。
2.审计处理处罚对象选择对审计处理处罚效果的影响
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审计处理处罚对象包括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但是,现实审计生活中,对责任人的处理处罚很少。据近10年《中国审计年鉴》“全国审计机关分行业审计(调查)情况表”,对责任人的处理处罚情况计算如表8所示。
责任人处理处罚度=(移送司法机关涉案人数+移送纪检监察部门涉及人数+移送有关部门涉及人数)/审计(调查)单位数
表8的数据显示,对责任人的处理处罚力度很小。
五、结论和启示
审计处理处罚配置作为审计处理处罚的一个重要且基础性的问题,本文尝试从理论基础、宏观配置、微观配置这三个方面来构建其理论框架。理论基础包括配置目的和如何配置两个理论问题,本文认为,配置目的是惩处功能和预防功能的统一;如何配置是违规惩处相应,认为违规行为对经管责任的危害是衡量处理处罚的真正标尺。宏观配置层面,本文讨论了处理处罚主体、处理处罚对象、处理处罚立法模式、处理处罚类型和位阶等问题。处理处罚微观配置主要涉及各类处理处罚在各类违规行为上的配置,包括处理处罚配置模式、处理处罚自由裁量权、针对各类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规定等。
通过对审计年鉴数据的分析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审计处理处罚的效果并不理想。从审计处理处罚配置视角来分析,这一现状的背后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审计处理处罚各主体的协同不善导致处理处罚效率低下,审计处理处罚忽视了对责任人这一对象的处罚等。希望本文构建的配置框架能够为审计处理处罚的进一步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带来启发。
【参考文献】
[1] 刘强.论审计处理权的界定[J].中州审计,1996(1):17-18.
[2] 胡智强.论我国国家审计权的配置[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9(1):56-62.
[3] 魏昌东.中国国家审计权属性与重构[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2):32-37.
[4] 胡贵安.国家审计权法律配置的模式选择[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2.
[5] 张宗乾.关于审计处理处罚依据的探讨[J].北京:中国审计信息与方法,2002(3):42-43.
[6] 郝婷.准确把握执法主体资格依法行使审计处理处罚权[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2010-03-11.
[7] 程度平.审计机关何种情况下具备执法主体资格[EB/OL].中国审计网,2011-11-17.
[8] 陈妙松.浅谈自由裁量权在审计问题定性处理中的合理运用[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2010-12-28.
[9] 谢开盛.论自由裁量权在审计定性和审计处罚中的合理运用[J].审计与理财,2013(2):28-29.
[10] 王广庆.国家审计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及规制[J].审计月刊,2013(11):16-17.
[11] 周光权.法定刑配置的合理性探讨——刑罚攀比及其抗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98(4):43-48.
[12] 周光权.法定刑研究——罪刑均衡的建构与实现[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13] 邓文莉.刑罚配置论纲[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14] 蔡一军.刑罚配置论纲[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15] 蔡一军.刑罚配置的基础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16] 魏柏峰.论刑罚配置的实现路径[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30-32.
[17] 欧锦雄.论经济犯罪数额的立法模式[J].政治与法律,1998(5):50-53.
[18] 邓文莉.罚金刑配置模式之研究[J].法学评论,2008(4):154-160.
[19] 万国海.论我国经济犯罪刑罚配置的完善[J].政治与法律,2008(9):36-41.
[20] 刘宪权.论我国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J].政治与法律,2011(1):10-18.
[21] 董淑君.刑罚的要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03.
[23] 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8.
[24] 张宗乾.审计处理处罚的三个误区[J].理财,1998(9):11.
[25] 陕西省审计厅课题组.审计机关处理处罚权主体资格问题研究[J].现代审计与经济,2008(1):12-13.
[26] 马克昌.论刑罚的功能[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4):46-52.
[27] 邱兴隆.撩开刑罚的面纱——刑罚功能论[J].法学研究,1998(6):56-75.
[28] 刘军.该当与危险:新型刑罚目的对量刑的影响[J].中国法学,2014(2):222-234.
[29] 孙建伟.国外经济刑法简介[J].法学,1987(3):44-46.
[30] 李建华.关于制定经济刑法典的思考[J].东疆学刊,2001(6):62-64.
[31] 李汉军.中国经济刑法的立法模式与思路[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0(6):76-79.
[32] 韩小莲.经济犯罪刑罚配置研究[D].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33] 王金滨.经济法规中可以规定刑罚[J].政治与法律,1984(12):46-47.
[34] 徐向华,郭清梅.行政处罚中罚款数额的设定方式——以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为例[J].法学研究.2006(6):89-101.
[35] SEBBA L.Some explorations in the scaling of penalties[J].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1978,15(2): 247-262.
[36] 司久贵.行政自由裁量权若干问题探讨[J].行政法学研究,1998(2):27-33.
[37] 江必新.论司法自由裁量权[J].法律适用,2006(11):17-22.
[38] 董玉庭,董进宇.刑事自由裁量权基本问题[J].北方法学,2007(2):49-57.
[39] 辛建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规制[J].法学研究,2009(5):56-57.
[40] 王锡锌.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的四个模型——兼论中国行政自由裁量权控制模式的选择[J].北大法律评论,2009(2):311-328.
[41] 余凌云.游走在规范与僵化之间——对金华行政裁量基准实践的思考[J].清华法学,2008(3):5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