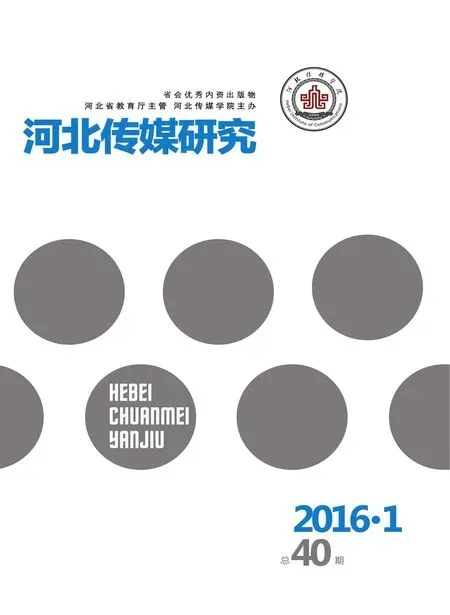论正定隆兴寺惠演碑的刊刻时间*
程宇静
(河北传媒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71)
论正定隆兴寺惠演碑的刊刻时间*
程宇静
(河北传媒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71)
正定隆兴寺内惠演碑文的落款时间为“乾德元年”,早于正文所涉年月约6至8年。这一落款时间有误,惠演碑刊刻时间在景祐年间。这一错误导致古今学者误认为龙兴寺大悲菩萨像铸于北宋“乾德元年”。据田锡碑,该像铸于“乾德中”,这个时间虽模糊却比较可靠。
正定;隆兴寺;惠演碑;刊刻时间
河北省正定隆兴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以来,它的建筑艺术、历史文化甚至植物生态不断得到学界的关注,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①惠演碑是隆兴寺内的一方宋碑,碑文由北宋龙兴寺(清代改称“隆兴寺”)僧惠演所作,本文为叙述方便简称惠演碑。此碑是研究隆兴寺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的由来、隆兴寺历史的重要石刻文献。笔者发现,该碑文落款年月为“乾德元年”,早于正文内容所涉年月约6至8年,显然不合情理,因此惠演碑的落款年月即刊刻时间堪疑。而此前学者多凭借惠演碑的落款时间认定大悲菩萨像铸于“乾德元年”,未见有学者就这一疑点发表见解,因此有必要将其拈出并认真讨论,以期厘清事实,更科学准确地梳理隆兴寺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的历史。
一、刊刻时间考述
惠演碑碑文标题全称《真定府龙兴寺铸金铜像菩萨并盖大悲宝阁序》,序文记述了隆兴寺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的由来,详尽生动,颇多细节。但细读碑文内容,不难发现,碑文涉及的年月前后矛盾,完全不合情理。现摘录4条相关内容如下:
1.太祖皇帝至开宝二年(969)岁次己巳三月,驾亲征晋地,领二十万之军至于太原城下安营下寨。水浸攻城,前后六十余日,并未获圣捷。至闰五月内,大驾巡境按边至真定府歇驾……五月内驾却归帝阙,并无消息。
2.后至开宝四年(971)六月内,天降云雨于五台山北冲。
3.至开宝四年(971)七月二十日,下手修铸大悲菩萨。
4.讲经论僧惠演知虽不慜,聊序修铸之因,显示后人,用贯通于耳目,大宋乾德元年(963)岁次五月八日记。[1]
由上述所摘录碑文可见,最后一条即碑末落款时间“乾德元年(963)”,明显早于正文中事件发生的时间“开宝二年”或“开宝四年”,早了约6至8年。也就是说,如果“乾德元年”属实的话,那么碑文记述了8年之后发生的事件,这显然极其不合常识、不合情理。上述碑文引录于清嘉庆十年(1805)王昶编撰的《金石萃编》。“乾德元年”会不会是王昶在拓印、抄写或刻录过程中出现的错误?那就再看一看其他历史文献对惠演碑的记载与《金石萃编》是否一致。
据笔者考察,关于惠演碑的信息,在宋、金、元、明代的史志、方志及文人别集等文献中极为罕见,而诸多信息皆涌现于清代。乾隆二十四年(1759)翰林侍读学士朱珪过正定憩隆兴寺。他细览了此碑,并写诗作序以志其所见,《隆兴寺大佛歌并记》云:“十七日过正定,憩大佛寺。铜像高七丈三尺。寺有宋碑,僧惠演记,略云:‘镇州城西旧有大铜佛,唐时所铸,五代时铄于契丹,周显德间,毁天下佛像以铸钱。至太祖开宝二年三月亲征晋,闰五月巡边驻跸是州,问像之兴废。僧可俦对曰:“像间有字‘遇显而毁,遇宋而兴。’”乃命修之。掘菜地得铜,五台山漂大木至以为梁柱,于龙兴寺建铸,凡七铸而成,四十二臂具焉,曰大悲观音像。时开宝四年也。乾通元年记。’”[2]考宋代年号,并无“乾通”,“乾德”与“乾通”形近,故应是朱珪误书,或刊刻者误刻。②无独有偶,乾嘉学者钱大昕乾隆年间过隆兴寺,题咏诗《登隆兴寺大悲阁,周览隋、宋、元碑刻,晚宿雨花堂对月得诗七首》其一末注云:“《隆兴寺铸金菩萨像并盖大悲阁序》,乾德元年僧惠演撰。”[3]上述两位清代学者乾隆年间在隆兴寺所见的惠演碑均题为”乾德元年”。此后这篇碑文被完整记载于前揭清嘉庆十年王昶编纂的《金石萃编》上。同时,惠演碑的碑题及作者、时间几项主要信息又见载于清孙星衍《京畿金石考》“宋龙兴寺铸象修阁记碑,僧惠演撰,正书,乾德元年立”[4],与孙星衍《寰宇访碑録》“龙兴寺铸象修阁记,僧惠演撰,正书,乾徳元年五月,直隶正定”[5],皆作“乾德元年”。上述朱珪、钱大昕所见与王昶、孙星衍所录应是同一碑刻,皆为“乾德元年”。以上历史记载说明“乾德元年”的文字记录无误。那么碑文落款与内容时间上的矛盾又该如何解释?
寺僧惠演,何时人也,生平如何,这也是判断碑文刊刻时间的一个重要线索。但笔者就中国基本古籍库等电子古籍数据库检索,没有关于龙兴寺僧惠演生平的记载。王昶在惠演碑跋文中称惠演文字“鄙俗不足论”[1]716,可能惠演只是一个普通寺僧,名不见经传也是可以理解的。至此,可以确定,其一,此碑一定不是乾德元年(969)所记,作者不可能穿越到6年之后。其二,也不应是开宝四年(971)所作,如是,惠演作为开宝四年当时人,应不致于粗疏到以8年前的年号作为落款时间。因此,笔者认为,此文应是后代补记;补记时因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历史常识或受某个文献资料影响而误书时间。那么此碑是何时补记,所补内容有何依据?
除了惠演碑,今隆兴寺还有两方相关宋碑,即田锡碑和葛蘩碑。田锡碑,碑文标题全称《大宋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并序》,由北宋初期著名古文家、“朝奉郎、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柱国、赐绯鱼袋、田锡”奉敕撰写,简称“田锡碑”。序文记述了五代至北宋前期镇州(治今河北省正定县)大悲菩萨像的废兴历史,赞颂了北宋皇帝德超三古,以致国运昌隆,使佛亦为之瞻依,故兴修佛事,以“彰皇宋其昌”[1]761。将田锡碑与惠演碑对比阅读,以下两个事实特别值得注意:其一,田锡碑立石于“端拱二年(989)”,比惠演碑中的开宝四年(971)晚约18年。但碑文丝毫未提及开宝二年宋太祖驻跸镇州、开宝四年敕令兴铸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以及惠演撰写序文诸事。惠演碑所述事件是大悲菩萨像及大悲阁修筑史上的大事,且与田锡碑撰写时间相距不到20年,田锡奉敕撰文不大可能不知晓、不了解,寺僧也不大可能不粗陈梗概使之了解。而且,田锡碑文中明确指出此文旨在叙大悲菩萨像“修铸废兴之事”[1]759,从周显德毁佛说到乾德重修,直到太平兴国七年再修,如果他看到或了解到惠演碑及其所录之事,不至于只字未提。其二,田锡碑中有一段文字与惠演碑基本相同,这是关于后周柴氏毁佛的一段记述,如下所录:
显德中,世宗纳近臣之议,以为奄有封畧,不过千里;所调租庸,不丰边备,校贯屡空于军实,算□莫济于时须。于是诏天下毁铜像鼓③铸以为钱货,利用以资帑财。金人其萎,梁本其坏。化④身从革,通有无于市征;国府流形,岂执着于我相。而惟镇之邦,惟镇之民,⑤万人聚,千人计,惜成功□见毁,冀上意以中辍,虽卜式出财以有助,而□皇执议以不回。⑥洎像坏之际,于莲叶之中有字曰“遇显即毁”,无乃前定之数乎?物不可以终隳,必授之以兴复;时不可以终⑦否,必授之以隆⑧昌。我国家应乎天,顺乎人,革有周之正朔,造皇宋⑨之基业。[1]759
另有一小节田锡碑与惠演碑文字亦相近,这是关于大悲菩萨像形象的一节描述。田锡碑云:“七十三□,宝相穹隆。仰之弥□,瞻之益恭。”惠演碑作:“七十三尺,四十二,宝相穹隆,瞻之弥高,叩之益躬⑩。”那么由这两点是否可以说明田锡碑晚于惠演碑,文字上参考了、甚至抄录了惠演碑呢?笔者认为这一见解是经不起讨论的。田锡,北宋太宗朝著名文人士大夫,太平兴国三年进士榜眼及第,宋代文学的奠基人。据《宋史·田锡传》载,他在政坛上以直言敢谏著称[6],范仲淹为其撰墓志铭亦赞曰:“呜呼田公!天下正人也。”[7]撰此碑文时田锡任尚书兵部员外郎。像这样一位文坛、政坛闻人,品行以“正直”见称,应不会抄录惠演文,即便参考也会提及作者,况且惠演文“鄙俗不足论”,大段抄录其文,岂不有失文人操守和体面?再者,上述一段文字,在田锡碑文中前后圆通、文脉流畅,而在惠演文中语意却时有漏洞,如某些措辞与人物身份、语境不符。在惠演碑中,这段文字是宋太祖的自述,他说“朕忆得先皇显德年中”云云,既然是自述,应通俗口语化,可这段文字全是四六骈文应制之体,毫不通俗,且文最后自夸“我国家应乎天,顺乎人,革有周之正朔,造皇帝之基业”,这样的自我标榜也不大符合宋太祖的身份。而且此段之后,紧接“今为菩□□于□外,与大德移菩萨在郭内得也”,语意跳跃性过大,不像是自家写就虽粗陋却圆通之话,倒像是拼合攒凑之文。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田锡碑不大可能参考甚至抄录惠演碑文字,惠演碑刊刻时间不在田锡碑之前,而在田锡碑之后。进一步讲,就二碑大段相似文字而言,惠演碑应是参考并抄录了部分田锡碑的内容文字,且抄录得十分拙劣。除田锡碑外,惠演碑所依据的内容应该还有《宋高僧传》、宋初历史和传说。
据《宋高僧传·唐镇州大悲寺自觉传》载,镇州大悲寺有大悲菩萨,“高四十九尺,梵相端严,眼臂全具”,至周显德初被毁,“时州人相率出钱赎此像,不允”,后“匠氏暴卒”,“自此罢工,迨宋太祖神德皇帝追铸”[8],但传记中并未明确是宋太祖哪一年“追铸”。又据《宋史·太祖本纪》,开宝二年宋太祖亲征太原,讨伐北汉,回京途中曾经过镇州(治今河北省正定县),史载:闰月(五月)“戊辰”“驻跸于镇州。六月丙子朔发镇州”[9],在镇州停留约9天。上面所引惠演碑第一条内容即记录了这一过程。不过“五月内驾却归帝阙”与史实相左。当然,史书也未记载宋太祖在镇州驾临城西大悲寺,召众僧询问大悲菩萨像一事。除历史外,在北宋中期还有“太祖征太原还,至真定,幸龙兴观,道士苏澄隐迎銮驾”[10]的说法,但宋太祖只是询问苏澄隐“养生之要”,并未提及大悲菩萨像之事。笔者认为,惠演碑文正是根据以上《唐镇州大悲寺自觉传》、宋太祖开宝二年驻跸镇州的历史与传说、田锡碑的内容,编撰了开宝二年至开宝四年,宋太祖敕令建大悲菩萨像,菜园得铜,水漂大木,继而修建之事。那么惠演碑碑文编撰并刊刻于何时呢?
隆兴寺内的另一块宋碑“葛蘩碑”提到了一个时间:“景祐中(1034-1037)”。文称“景祐中,寺僧惠演录其兴建之迹甚详”。葛蘩碑碑文由北宋绍圣四年(1097)“朝奉郎、管句真定府路都总管、安抚司机宜文字、骁骑尉、赐绯鱼袋、葛蘩记”[11],碑文标题全称《真定府龙兴寺大悲阁记》[11]490。此碑文称“大帅宝文吴公”见惠演碑“言不雅训”,即语言不典雅,无法度,于是请葛蘩在惠演碑的基础上润色修饰撰成新文,“今大帅宝文吴公以道存心,以德惠民,观宝相雄壮,圆悟不思议之旨,灼见太祖皇帝道莅天下之意,欲以发挥圣人难名之勋业,传之无穷,于是使蘩因旧文而为之记。”[11]491该记文将惠演文精炼提纯,言简意赅地记述了隆兴寺大悲菩萨像与大悲阁的历史。葛蘩看到了惠演碑,为什么不说乾德元年或开宝年间寺僧,而是说景祐中寺僧呢?可能根据他在当地的了解,惠演确实为景祐中人。他为什么不在记文中指出乾德元年之误呢?可能是葛蘩认为惠演碑言辞粗鄙,不值得纠错。葛蘩记撰成之后,刻石立碑,刻在碑阳,同时将惠演文刻在了碑阴,于是就有了后世所见到了一块石碑碑阳碑阴两篇记(序)文,惠演碑在碑阴[11]492。朱珪《隆兴寺大佛歌并记》亦云“其(惠演碑)背有绍圣年间葛蘩记一篇”[2]。由于惠演文在碑阴,所以按碑刻惯例不大可能先刻惠演文,也就是说惠演文有葛蘩之前没有刻碑上石。
笔者认为葛蘩碑记比较可靠。北宋实有葛蘩其人。他自号鹤林居士,丹徒人,良嗣的长子。崇宁间官临颍主簿,累迁镇江守[12]。其人向佛,曾为人撰写多篇佛寺记文,如《净业院给业记》[13]《天台教院记》[14]之类。因此,葛蘩记文中所说“景祐中寺僧惠演”的说法应该是可靠的。
二、结语
前揭 《宋高僧传·唐镇州大悲寺自觉传》末云:“迨宋太祖神德皇帝追铸”[8],只说宋太祖重铸,并未说具体时间。对于这一点,田锡碑与惠演碑的说法是矛盾的。田锡碑说“乾德中(963-967)乃重铸大悲之像”[1]759,像成,七十三尺,四十二臂,宝相穹隆,又“构以摩云之阁”[1]759。惠演碑说此前龙兴寺并无大悲菩萨像,开宝二年宋太祖下令,于“龙兴寺内最处宽大,别铸金铜像,盖大悲阁于后”“开宝四年七月二十日下手修铸大悲菩萨”[1]713-715。正像本文前面所论,田锡碑较为可靠,“乾德中乃重铸大悲之像”的说法虽未明确哪一年,但模糊恰恰是相对可靠的。
勾勒隆兴寺大悲阁在北宋的历史主要依靠四部文献:《宋高僧传》、田锡碑、惠演碑、葛蘩碑。下面将四部文献撰写次序及后世情况简要梳理如下。
《宋高僧传》于端拱元年(988)十月上交朝廷。端拱元年七月至端拱二年 (989)正月田锡奉敕撰碑,作为朝官,他结合《宋高僧传》及其他史料撰成田锡碑。景祐年间,龙兴寺僧惠演根据田锡碑与其他史料撰成序文一篇。绍圣年间,吴公即吴安持帅真定⑾,见到惠演文,恶其鄙俗,遂请葛蘩在惠演碑基础上更作一记,以发挥圣人之旨,并将两篇记文同时刻石立碑。元代延祐三年(1316)《赵孟頫胆巴碑》回顾大悲阁历史时提及“僧可传(笔者按:应为”俦“)言,寺有复兴之谶……”“僧惠演为之记”[15]。这是惠演碑中的内容,葛蘩碑中无。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中提及“龙兴寺乃乾徳元年(963)建”[16],应该也是借鉴了惠演碑落款的说法。清初顺治十年《重修东耳阁记》提及“详在景祐寺僧惠演之记与绍圣大帅宝文复请葛蘩为序矣”[17],所说即惠演碑文和葛蘩碑文。惠演碑和葛蘩碑一石两面,乾隆年间,朱珪与钱大昕都有见到。清嘉庆年间,三碑被一齐载入《京畿金石考》等金石著作中。
由于文献资料有限,本文有诸多假设,但有些事实还是十分明了。综上所述,田锡碑与葛蘩碑比较可靠。惠演为北宋景祐年间龙兴寺僧,惠演碑撰于景祐年间,落款“乾德元年”应是受田锡碑“乾德中乃重铸大悲之像”说法的影响,与碑文中的事件发生时间矛盾,故“乾德元年”的落款有误。惠演碑刊刻时间应为绍圣四年。其碑文内容中菜园掘铜、河漂巨木,五台山文殊菩萨送予建像与阁之说,渲染了龙兴寺大悲菩萨与大悲阁由来的神秘性,应当是有其当时的撰写背景和需求,但其说荒诞无稽,视为传说则更为允当,正如清代学者朱彝尊所言“流传宋太祖曾幸其地,寺重建于乾德元年,龙兴之额所由更也”[18]。
注释:
①研究成果有:梁思成 《正定调查纪略》(《梁思成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该著作涉及隆兴寺部分对隆兴寺建筑的艺术与历史文化价值有许多重要而独特的见解,如认为隆兴寺转轮藏为宋代遗迹,与宋代《营造法式》完全吻合,全国保存只此一寺,兼具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此外还有张秀生《正定隆兴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王京瑞 《隆兴寺故事传说》,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等多本著作。刘友恒 《正定隆兴寺千手观音手臂问题辨误》,《文物春秋》1994年第1期;李秀婷、杜平《隆兴寺与封建皇室资料汇编》,《文物春秋》2006年第1期等20多篇学术论文。
②清代陶梁《国朝畿辅诗传》卷三七、董诰《皇清文颖续编》卷七七皆转录了此诗,并作“乾通元年记”,沿袭了原诗错误。
③惠演碑中无“鼓”字。“鼓铸”指鼓风扇火,冶炼金属、铸造钱币或器物。“鼓铸以为钱货,利用以资帑财”,田锡碑语意完整,上下句对仗工整,形式整饬。惠演碑无“鼓”字,一字之差,文之高下立显。
④惠演碑无“化”字,一字之漏导致语意不通,形式不整。
⑤“而惟镇之邦,惟镇之民”这九个字惠演碑无,导致语意欠通。
⑥以上四句惠演碑作三句,且有异文,曰“见成功不毁,虽卜议以出财,皇帝执议以不回”。“卜式”指西汉人,以牧羊致富。武帝时,匈奴屡犯边,他上书朝廷,愿以家财之半捐公助边。又以二十万钱救济家乡贫民。惠演文为“卜议”,语意不明,也失去了原文的整饬。
⑦“终隳”“终否”,二“终”惠演碑皆作“修”,“终隳”“终否”指一直崩毁,一直坏恶。“修”语意不通。
⑧“隆”惠演碑作“降”,前后语意不通,误。
⑨“宋”字惠演碑作“帝”。“有周”对“皇宋”则工整,对“皇帝”则不考究。
⑩惠演碑之“躬”字语意不通。
⑾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五载:“吴安持以绍圣三年十月帅真定,”清秦缃业《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三亦载:“(绍圣三年十月)是月,吴安持为真定等路经略使。”
[1]王昶.金石萃编[M]//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研究分会.历代碑志丛书:第6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713-715.
[2]朱珪.知足斋集[M].清嘉庆刻增修本:卷三.
[3]钱大昕.潜研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019. [4]孙星衍.京畿金石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下.
[5]孙星衍.寰宇访碑録[M]//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研究分会.历代碑志丛书:第23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358. [6]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9792.
[7]范仲淹.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M]//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四部丛刊:卷一二.
[8]赞宁.宋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658.
[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29.
[10]文莹.玉壶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4:7.
[11]沈涛.常山贞石志[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90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491.
[12]昌彼得,王德毅.宋人传记资料索引[M].台北:鼎文书局,1977:3264.
[13]嵆曾筠.《(雍正)浙江通志[M]//景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二五六.
[14]潜说友.(咸淳)临安志[M]//景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八五.
[15]赵孟頫《胆巴碑》[M]//历代碑帖丛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6.
[16]顾炎武.金石文字记[M]//景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二.
[17]敕建隆兴寺志[M]//罗氏雪堂藏书遗珍:第8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616.
[18]朱彝尊.曝书亭集[M].四部丛刊景清康熙本:卷四八.
(责任编辑:杭长钊)
2016-01-23
*本文为河北传媒学院第七届科研立项课题“河北正定佛寺文化遗迹与文学研究”(序号:201526)阶段性研究成果。
程宇静,河北传媒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教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