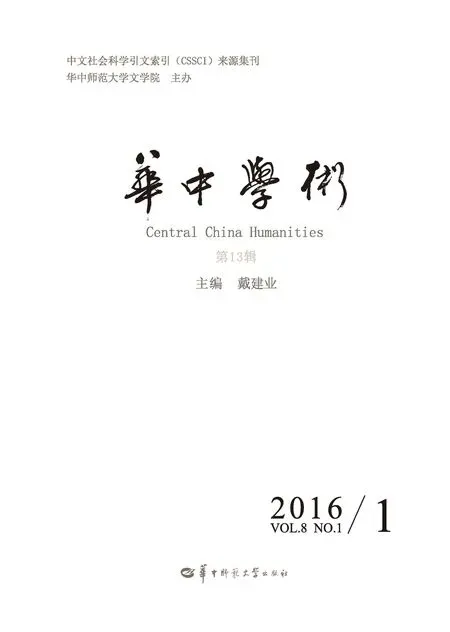《驿站长》:一出伦理悲剧的隐喻文本
王树福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驿站长》:一出伦理悲剧的隐喻文本
王树福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内容摘要:在普希金的名作《驿站长》中,杜尼娅为了追求个人幸福,与骠骑兵大尉明斯基不辞而别,抛弃了父亲维林;维林于京城寻女不遂,受到女儿和女婿的不公平对待,备受打击,陷入因情感真空和生活无序而形成的伦理困境,并最终悲惨死去。由此,杜尼娅个人主义行为严重违背了普遍认同的集体主义家庭伦理原则,破坏了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民族伦理秩序。小人物维林的悲惨命运和潦倒至死,主要原因在于女儿的伦理越位而导致的伦理困境。作为一个隐喻文本,《驿站长》本质上是一出现代化变革之初社会背景下的家庭伦理悲剧,其叙述重心不在于批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级压迫,而在于表达对因现代化变革而引发的民族伦理失范之忧思和警醒,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小人物的深切同情和人道关怀。
关键词:《驿站长》;隐喻文本;小人物;伦理悲剧;民族伦理
伦理问题的由来
作为普希金《别尔金小说集》(Повести Белкина,1831)中的点睛之作,《驿站长》(Станционный смотитель)是俄国小说史上无可替代的经典之作:“《别尔金小说集》为后来俄国文学的主要体裁——小说树立了典范,特别是其中的《驿站长》,上承卡拉姆辛《苦命的丽莎》的余绪,下开40年代 ‘自然派’的先河,对俄国现实主义民主文学的确立起过较大影响。”[1]对驿站长之死,学术界普遍认为,萨姆松·维林之悲剧在于社会压迫和等级对立,反映的是小人物备受欺凌的悲惨命运。“《驿站长》是全部小说的重心。小说通过驿站长的女儿被人拐走、寻女被驱、最后潦倒至死的故事,第一次在文学中表现了 ‘小人物’的不幸命运,将贵族社会与平民阶层对立起来,进行艺术表现,具有强烈的效果”[2];“《驿站长》以简洁生动的文笔描写了乡间驿站的十四等文官维林的不幸遭遇。小说饱含人道主义的情感,是俄国文学史中第一个成功地描写小人物的作品”[3];“在这篇小说中,普希金描写了一个备受打击、无力反抗的小人物形象……当然普希金并非仅仅诉说老人的悲惨故事。他揭示了等级世界的不公平,这个世界不允许小人物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爱的权利”[4]。
集中关注父亲维林和女儿杜尼娅、骠骑兵大尉明斯基之间的伦理关系,不难产生一种情感之惑与伦理之思:何以杜尼娅争取个人幸福,对父亲维林而言却是致命的悲剧?按照人之常理和生活逻辑,女儿生活优越,备受疼爱,夫婿英俊,家庭和睦,维林应感到高兴;再者,维林的生活虽清苦寂寞却自得其乐,并非一贫如洗。将维林的悲惨命运归结为社会等级压迫,在逻辑上似乎值得商榷。作为一种“包容性很强、准百科全书性的形式”和民族精神的“想象的共同体”,《驿站长》以虚拟的艺术镜像反映着19世纪上半期建立在帝俄专制“社会结构和它的权威和权力之上的一整套社会参照体系”[5]。其中,大尉来访、女儿离去、京城寻女与落魄归乡等情节所传达的伦理关系,不仅推动着小说故事的展开,决定着人物命运的结局,而且也反映着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文化规训。
大尉来访与伦理危机
驿站长虽是“十四级文官,驿站的主宰”(37)[6],但要承受来自各方的冷眼、呵斥、指责、辱骂,其地位之低下,其官职之卑微,其内心之压抑,让人一掬同情之泪:“驿站长是何许人?就是一个十四级的真正受难者,他的官职仅仅能使他免遭殴打,而且还不保证他永远不挨打。”(37—38)尽管生活如此清贫艰苦,但维林苦中作乐,视女儿为生命的唯一和生活的支撑,与如花似玉的女儿相依为命,生活过得温馨而甜蜜。在维林的眼中,十四岁左右的杜尼娅“脑子好使,手脚麻利,活像她死去的母亲”(39);在叙述者——职位低微的九品小官吏А.Г.Н.的眼中,“她的美貌令我吃惊”(39),有着一种让人着迷的魅力风情,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小妖精”(кокетка),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只两眼便已察觉出”“我”的心思,“回答我的问题时没有任何的胆怯,像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姑娘”(40),和父亲陪着客人随意喝酒聊天,“就像是老熟人似的”(40)。
行文至此,小说展示了一个外貌漂亮、善解人意、了解风情的成熟女性形象。叙述者话语中的кокетка,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杜尼娅的道德形象,即一个精通人情明白世事的庸常少女;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叙述者内心的道德水准和道德期待,即一个道德素养泯于众人的庸俗男性。按黑龙江大学辞书研究所编著的《大俄汉辞典》解释,кокетка意即卖俏的女子[7];按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著的《现代俄语辞典》,кокетка意即让男人心生爱意,靠外在装饰和行为举止吸引男性的女人[8],可译为“小妖精,骚妞儿,卖弄风情的女人”。对杜尼娅的谙熟世故和女性魅力,维林也是心知肚明,且引以为豪:“打这儿过的人,人人都夸她,没有一个人说她不好。太太们常送东西给她,有时是头巾,有时是耳环。过路的老爷们故意留下了,说是为了吃顿午饭或是晚饭,其实只是为了多看她几眼。那时,不论多么生气的老爷,一见到她就安静下来,对我说话也就客气了。”(41)
对杜尼娅性情和心理的侧面描写,为她钟情贵族明斯基,和明斯基驾车不辞而别,埋下一个秘而不宣的情节伏笔。有了女儿的存在和宽慰,五十岁上下的维林虽然备受上级斥责和打骂,但却“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情”(39),“脸色很好,精神矍铄”(40)。然而,世事难料,人生变幻,造化弄人:三年前一个冬天傍晚,“一位身材匀称、蓄着黑色唇须的年轻的骠骑兵”来到驿站,刚要高声发怒,见到貌美惊人的杜尼娅,“怒气消失了;他同意等马回来,并为自己要了一份晚餐”(42)。年轻人对杜尼娅心中顿生爱意,于是装病在驿站住了下来。
年轻人生病期间,杜尼娅与骠骑兵形影不离,将他照顾得无微不至。短短数天之内,两个年轻人情愫暗生,感情迅速升温,唯有维林尚蒙在鼓里,一无所知。“驿站长在场时,病人哼哼着,一句话也不说,但是却喝了两杯咖啡,并且还哼哼着说要吃午餐。杜尼娅寸步不离地守着他。他不时地要喝水,杜尼娅便给他端来她调制的柠檬茶。”(42)“病好”之后,开朗活泼的明斯基和维林父女熟络起来,说说甜言,开开玩笑,登记马匹,一派平等开心、其乐融融之象,并无所谓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等级差异。如此一来,“善良的驿站长着实喜欢上了他,在第三天的早上,他已舍不得和他的这位可爱的客人分手了”(43)。分别之日恰逢礼拜天,杜尼娅准备去做日祷;明斯基付过食宿费,与维林道别后,提议顺路捎杜尼娅去村边的教堂。对此,维林和杜尼娅的回应可谓相去甚远,截然不同,耐人寻味:一个踌躇不前,“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一个干脆利落,劝女儿顺路去祈祷,“你怕什么?……你就坐他的车去教堂吧”(43)。杜尼娅之所以犹豫不决,主要出于两难的伦理情感:愿意与心上人过幸福生活,却又不想伤害父亲的情感;维林之所以马上同意,并不因为明斯基的甜言蜜语,而是出于待客礼仪。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杜尼娅并非被军官武力胁迫拐走,而多半是心甘情愿,心向往之:据送骠骑兵离去的车夫所言,“杜尼娅和骠骑兵在一起,离开下一站又往前走了”(43);“杜尼娅一路上都在哭,虽说她好像是自愿跟他走的”(44)。通过车夫传达的信息,至少可以得出两个判断:其一,杜尼娅与明斯基两情相悦,彼此相爱,并非暴力胁迫;其二,杜尼娅离开父亲,抛弃父亲,虽心中有愧,但并无后悔。
简言之,在骠骑兵大尉到来之前,维林和杜尼娅相依为命,互相关心,虽然清贫卑微,但却其乐融融,体现出浓厚的传统家庭伦理氛围;骠骑兵大尉到来之后,他与杜尼娅的不辞而别,让维林的情感发生了强烈的伦理危机,面临着家庭生活的伦理失范问题。
女儿离去与伦理失范
随着女儿的不辞而别,维林的生活境况遭遇到强烈的家庭伦理危机,精神状态发生了彻底的伦理变化。维林前后变化之巨,超乎叙述者之想象;杜尼娅离别的结果之严重,让叙述者错愕不已;维林寻女未果之遭遇,更令读者深思探寻。
三四年之后,叙述者再次光临驿站,满怀欢欣重逢之情,看到的却是悲伤凄凉的景况:虽然“桌子和床铺摆在老地方;但是窗台上已没有了花,屋里的一切都让人觉得陈旧、凌乱”(40)。维林头发花白,羸弱驼背,神情恍惚,在叙述者眼中已然“老得多厉害啊!”(40)一幅家庭伦理失范之图油然而生:“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满是胡须的脸上那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和他佝偻的背——我不能不惊讶,三四年的时光竟能将一个精神抖擞的男人变成这样一个瘦弱的老头。”(40)女儿在时,维林的一切都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充满温馨和快乐。路过的太太和老爷们对杜尼娅疼爱怜惜,慷赠礼物;对维林轻声细语,礼貌有加。
显而易见,随着杜尼娅的离去和杳无音讯,维林的个人生活重点完全转移,家庭伦理关系彻底改变。维林先是心情抑郁难受,“一种不安的心情笼罩了他”(43);接着去教堂寻女未果之后,心情备受打击,得了严重热病,“经受不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他躺倒在那个年轻的骗子昨天晚上躺过的床上”(43)。维林开始反思何以杜尼娅抛弃自己,不辞而别:“我这个老傻瓜,对她也是看不够、喜欢不够啊;难道是我不爱我的杜尼娅?难道是我不关心我的孩子?难道是她的日子过得不好吗?”(41—42)从维林的角度而言,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那么杜尼娅何以不辞而别,音讯全无?于是,带着这个疑问,病刚有好转,维林就不顾身体疲惫不堪,向邮政支局长请假两月,步行去京城寻女,希望能将“这只迷了路的羔羊领回家来”(44),借此重构和谐美好、相亲相爱的家庭伦理关系。由此,作者塑造出一个充满浓浓慈父爱心的父亲形象,一个备受俄国宗法制传统文化熏陶的父亲形象,一个虔诚的笃信东正教的父亲形象。从父亲的伦理身份出发,维林的反思并无不当之处,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是问题在于,彼得大帝西化改革百年之后,随着欧风细雨的浸润,旧有的家庭父爱与女儿的个人生活之间,传统的集体主义伦理与西欧的自由主义伦理之间,已然发生了强烈的思想碰撞和显在的伦理冲突。
作为一个外源性后发现代性国家,俄国在西方工业文明成为中心话语背景下推行现代化,追求的是西方技术、军事成就和物质力量,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式的西化。这种改革在促进俄国社会进步、追求强国富民和面向世界的同时,也导致了两种可怕的后果:俄国斯拉夫民族特色逐渐丧失,民族伦理混乱、社会道德堕落;俄国上下层社会、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发生严重分裂。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大力推进,俄国在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问题上急功近利,判断失误,陷入误区:“不是整体性、均衡化地对精神资源、制度资源、物质资源做出理性的制度安排,而是精神资源弃之不顾、制度资源高度垄断、物质资源权力化配置。”[9]于是,伴随经济腾飞、国家富强等物质快速增长,出现了社会两极的分化、伦理的失范、道德的沦落等问题。普希金登上文坛时,这些背离民族精神和国家利益的改革状况还在继续恶化。在变革动荡中成长起来的作家,必然深切感受到了现代化和民族化、西欧主义和斯拉夫主义、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等矛盾冲突。这种新旧伦理秩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恰恰是维林与杜尼娅之间发生错位和矛盾的深层根源。
简言之,为了追求个人幸福,杜尼娅与骠骑兵大尉一起不辞而别,对维林而言是非常致命的,难以言喻的。“杜尼娅身上并不缺少自私自利和感情冷漠,她感觉自己在父亲面前有罪,但却为了新生活而牺牲了他。”[10]这种抛弃父亲的伦理越位行为,不仅使维林的生活秩序混乱不堪,使他的精神世界暗淡无光,丧失了活下去的价值与意义,失去了仅有的支撑与兴趣;更使他陷入前所未有的伦理困境之中,感受到一种伦理失范和道德沦落所带来的困惑和悖谬。
京城寻女与伦理重构
面对由于杜尼娅不辞而别而导致的家庭伦理失范,维林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以慈父爱意和宗教情怀,远赴圣彼得堡寻女。在一个退伍士官的帮助下,维林很快打听到明斯基住在德蒙特饭店。然而,借京城寻女重构家庭伦理的梦想,在贵族的上层生活面前不堪一击;珍视家庭和亲情关系的传统集体主义理念,在追求个人幸福生活的自由主义现实面前落荒而逃。
在勤务兵的通报之下,维林在约定的时候再次来到德蒙特饭店。想到女儿可能遇人不淑,遭到抛弃,维林就心跳加速,泪水盈面,声音颤抖,恳求明斯基将女儿还给他:“求您至少把我可怜的杜尼娅还给我。您已经玩够了她;您就别再把她给白白地坏了吧!”(44)面对此情此景,明斯基并没有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而是心中惭愧:“明斯基飞快地看了他一眼,脸一下子红了;他抓住老人的手,把他带进办公室,又随手关上门。”(44)作为骠骑兵大尉,明斯基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与杜尼娅一起不辞而别感到心虚脸红,为自己的莽撞行为感到不知所措。因此,他从心底请求获得维林的谅解,请求维林允许他和杜尼娅在一起,并且承诺给予杜尼娅以最大的关爱和最多的幸福。从当时的人伦关系和社会现实来看,始于两情相悦而能彼此厮守善始善终,在俄国贵族阶层可谓难能可贵。小说接着描写道:
“生米煮成熟饭,谁也无法挽回了。”极其狼狈的年轻人说道,“在你面前我有罪,我也乐意请求你的原谅;但是你别指望我会离开杜尼娅,我向你保证,她会很幸福的。你要她干什么?她爱我;她已经不习惯她从前的生活了。不论是你,还是她,你们都忘不了过去的事。”然后,在往驿站长的袖口里塞了点什么之后,他打开了门,连驿站长自己也不明白,怎么就来到了大街上。(44)
明斯基以为维林风尘仆仆来京城造访,多半为了兴师问罪,怕他将杜尼娅带走,不想让维林破坏自己的幸福生活和家庭关系。不难断定,明斯基对当时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伦理比较熟悉,并且认真切实遵循这些伦理规范。19世纪上半期,“城市开始对乡村地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进城打工的现象迅速增多,与此相关,在城市的生活也拓宽了往昔农民的眼界”[11]。从历史角度而言,这是一个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符合历史潮流的现象:“居民离开农业……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12]离家三四年之后,杜尼娅虽然“忘不了过去的事”,感到有愧于父亲,但却已然习惯了安逸温暖的生活。首次寻女未果,维林骗过车夫,再到明斯基家中,“从未看到他的女儿如此美丽”:“在这间装饰得很漂亮的房间里,明斯基坐在那里想事。穿着时髦、豪华的杜尼娅,则坐在他那张椅子的扶手上,就像一个坐在英国马鞍上的女骑手。她温情地看着明斯基,用自己戴满戒指的手指抚弄着他黑色的卷发。”(46)此时此刻的她,已然无法适应清贫艰苦的日子。抬头见到久别的父亲,杜尼娅并非欣喜万分地迎上去,亦非心中愧疚地请求宽恕,而是“尖叫着倒在了地毯上”(46)。这一举动着实耐人寻味,在杜尼娅的心中,对明斯基的爱超过并战胜了对父亲的爱,女儿已不再需要父亲;渴望爱情的自由意志战胜了怜惜父亲的理性意志,这种自由意志对杜尼娅意味着个人幸福,对父亲却意味着伦理危机:“她沉湎于新的感情,沉湎于自己的爱情之中,把他忘得一干二净。这就是普希金在父女两人命运的最后交汇点上,在这决定性时刻所揭示的女人禀性的实质。”[13]
简言之,伴随欧化改革的持续与深入,自由主义学说、思潮和运动在俄国贵族社会广为传播,强调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个性解放、道德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展而产生相当影响。就杜尼娅的去留问题,维林与明斯基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一个要以父女之伦理身份,带迷途女儿回归和谐家庭;一个要以恋人之伦理身份,用金钱解决家庭纷争。两种做法凸显的乃是两种不同伦理秩序的分歧,即基于农业文明的传统集体伦理秩序与基于商业文明的自由主义伦理秩序之间的分歧。
落魄归乡与伦理死结
维林京城寻女未果,受到明斯基极不礼貌、极不客气的对待,怀着郁闷的心情,放弃上诉,落魄回到家中。由此,维林的伦理处境完全陷入一片荒芜之中,成为一个难解的伦理死结。对骠骑兵大尉诱拐杜尼娅一事,维林之所以放弃控告明斯基,并不在于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因为问题不在于对明斯基进行追究。问题毋宁说是在于对女儿有所不满。可是你向谁去控告她?……最最不幸的是,杜尼娅还剥夺了他可怜她的机会”[14]。在痛失爱女的伦理困境中,维林身心备受打击,对女儿念念不忘:“她是死是活,只有天知道。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被过路的花花公子拐骗的姑娘,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把姑娘养上一阵,就扔掉了。”(46)怜惜女儿的伦理之情,溢于言表;想念女儿的亲情之态,跃然纸上;复杂丰富的父亲心理,丝丝入扣。
面对女儿不公平对待父亲,维林如何解决这一伦理困境,排遣内心的苦闷呢?先是借酒消愁,难以承受生命之重,维林“用衣袖缓缓地擦着眼泪”,“那些泪水,有一部分是由果酒引起的,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他喝下了五杯酒”(47);接着身体困顿,内心极度苦闷不堪:不过数月,维林形神消瘦,形貌大变,精神困顿,萎靡不振,“我有时想到,我的杜尼娅或许已经堕落了,我就恨不得做一次孽,咒她早死……”(46—47);最后带着无言的愤懑,悲惨死去:维林最终以悄无声息地悲惨死去,葬在“一块光秃秃的土地,没有围栏,立了许多木头十字架,但是一棵树也没有”(48)。在内外伦理交困之中,维林结束了正直善良、朴素坦诚的,充满道德信念和伦理意识的一生。由此,《驿站长》中强烈震撼人心的“那出人类在家庭关系上的共同悲剧”[15],在某种程度上,与被女儿抛弃的李尔王的内心痛苦性质相似。
横跨欧亚的地理环境、东西兼顾的民族气质和独有的村社制度等因素,共同生成出俄国独有的斯拉夫主义社会伦理观念,即强调个人依附共同体的集体主义、以斯拉夫为中心的本土主义、排斥个人智慧的非个人主义、带有感性色彩的非理性主义[16]。随着18世纪以来追求社会物质进步的现代化进程的加剧,这种由依恋斯拉夫共同体的特性逐渐被提升为祖国、家园、民族和公民意识,斯拉夫主义理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弗·索洛维约夫以及弗洛连斯基等主流文化作家,都试图维护这种非个人主义的民族伦理传统[17]。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觉意识的作家,普希金的创作历程即是脱离西方中心主义而趋于民族化的过程;其创作道路的变化即是他以民族化的文学形式表达并反思现代化进程及其效应的过程,从而为俄国和东欧等斯拉夫民族知识分子共同接受[18]。正因如此,“普希金在俄罗斯民族意识中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与其说是他作为诗人的伟大,毋宁说是普希金神话处于俄罗斯民族认同的中心位置,而认同在俄罗斯皇权的威严形象与俄罗斯过去的萧瑟、现在的不确定性的冲突中得到详细说明。这种情状可视为跨越复杂的自卑和高傲的界限。俄罗斯(民族)性是在普希金所引发的分裂中觉醒起来的”[19]。
简言之,受西欧浪漫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影响,19世纪早期俄国文学的伦理内涵主要以追求斯拉夫伦理价值观为核心。面对女儿生活幸福,个人家庭和睦的局面,维林悲惨潦倒死去,主要原因不在于贵族压迫平民的社会性主题,而在于女儿不公平对待父亲的家庭性问题,在于女儿违背家庭传统秩序的伦理性问题。
隐喻文本的生成
概而言之,杜尼娅为追求个人幸福而不公平地对待父亲,违背了社会普遍认同的家庭伦理原则,破坏了传统的民族伦理秩序,使维林陷入因情感真空和生活无序而形成的伦理困境,并最终悲惨死去。父亲死后,杜尼娅带着孩子到墓地祭奠父亲,显然不足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小说开头讲述的浪子回头的宗教故事,暗含着作者的伦理之思,即以宗教的博爱、民族的伦理和人道的情怀去对抗西化带来的伦理困境。由此,《驿站长》是一出处在现代化变革之初社会背景下的家庭伦理悲剧。小人物维林的悲惨命运和潦倒之死,本质上不在于社会的不公和等级的压迫,而在于女儿的伦理越位而由此导致的伦理困境。相较批判社会不公和等级对立而言,《驿站长》的叙述重心在于,表达对因现代化变革而引起的民族伦理失范的忧思和警醒,展现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小人物的深切同情和人道关怀。由此,非个人主义的伦理性,集体主义的民族诉求,乃是普希金民族化创作的叙述重点之一,追求斯拉夫价值观构成是普希金创作的整体特征。这种斯拉夫伦理价值,在现代化运动中被提升为抵御西化的重要力量,进而成长为系统化的斯拉夫主义伦理价值观,深刻影响着19世纪以降俄国文学与文化的嬗变,也成为后来斯拉夫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文学流派和文化思潮论证合法性的思想资源之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13&ZD128】和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大培育计划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研究”【CCNU14Z0200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蒋路:《作家与西欧语文、评论家的失误》,《俄国文史采微》,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2]张铁夫,等:《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229页。
[3]《外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外国文学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14页。
[4]任光宣、张建华、余一中:《俄罗斯文学史》俄文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3页。
[5][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96页。
[6]参见А.С,Пушкин,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 й в19 moMax,Т.8(II).М.: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1940,С.639;译文参阅《普希金小说选》,刘文飞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第37页。相关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随文标出具体页码,不再说明。
[7]《大俄汉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811页。
[8]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 голитературно гоязыка,Т.5.М.иЛ.: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1956,C.1130.
[9]王云龙:《现代化的特殊性道路:沙皇俄国最后60年社会转型历程解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9页。
[10]В.И.Коровин,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ХХ века вдвух частях,Ч.1.М.:Просвещение,2001,С.185.
[11][俄]М.Р.泽齐娜、Л.В.科什曼、В.С.舒利金:《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苏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66页。
[12]《列宁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30页。
[13][俄]达·格拉宁:《父女之间》,陆肇明译,《苏联文学》1985年第5期,第117页。
[14][俄]达·格拉宁:《父女之间》,陆肇明译,《苏联文学》1985年第5期,第119页。
[15][俄]达·格拉宁:《父女之间》,陆肇明译,《苏联文学》1985年第5期,第119页。
[16]林精华:《想象俄罗斯:关于俄国民族性问题的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17]Илья Ильинидр,“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идея дляРоссии?Сфилософом Ильей Ильиным беседуют Андрей Цуканов и Людмила Вязмитинова,”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No.39,1999,С.241-253.
[18]林精华:《斯拉夫主义:俄国视野中的普希金》,《俄罗斯文艺》1999年第2期,第67~72页。
[19]Andrew Kahn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ushkin,Cambridge:Cambridge UP,2006,p.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