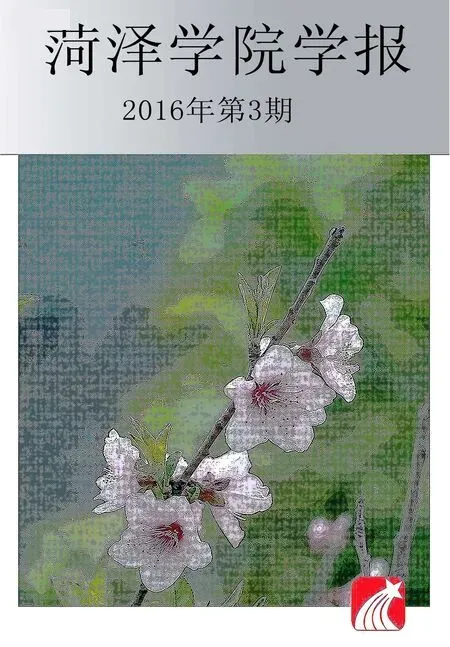《红楼梦》第一回与曹雪芹的小说创作观*
孟 幻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031)
《红楼梦》第一回与曹雪芹的小说创作观*
孟幻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031)
《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总结和开创的意义,其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在开卷第一回中得以充分体现。曹雪芹既注重生活真实,又注重艺术创造的“虚”“实”结合,理解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极真”“极幻”的关系,在古代小说理论中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创作观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曹雪芹的代表作,主要就在于他以自己独特的文学创作方式把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感悟诗化地表达出来,抒写了一部震撼人心的人间悲剧。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红楼梦》在文学史上具有总结和开创的意义,其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在开卷第一回中得以充分体现,小说表现的虚实结合的创作论、文学创作的审美观等,标志着曹雪芹成为新时代最初的一位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本文拟以《红楼梦》第一回为例,探讨曹雪芹小说创作的虚实观。
一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不但是整部书的引线,而且是整部小说的总纲。其主要写整部书的缘起,在全书结构上有其特殊的地位,“交代了自己的写法是将真事隐去,借通灵之说,写一块石头梦醒后返璞归真的故事。”[1]369第一回无疑是读懂《红楼梦》的关键所在,作者用虚幻的笔触点明了贯通全书的主线和刻画的主要人物,阐述了作者自己的一些文学创作观点,使内容和正文有了天衣无缝的镶嵌链接,让正文的面貌更加明了。第一回也是作者匠心独运所在,其构思设计精巧新颖,比如,在第一回中,作者用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借顽石说“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表明了作者自己的现实经历和感受——半生潦倒,将人生感悟寄著于书中,虽叹“无才”实际是作者的激愤之辞,要走一条与封建环境相悖的道路和一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与勇气。
第一回引出全书的关键内容即宝黛爱情悲剧。内容条理清晰,能够生动形象地阐明主旨,让读者读出作者的心声,如作者在第一回中讲的第二个神话故事“绛珠草还泪”,绛珠仙子为报神瑛侍者的辛勤灌溉之恩,也要随之下凡,用一生的眼泪还他。这个令人感动的美丽神话就引出了正文宝黛的爱情悲剧这一条主线,林黛玉的泪眼涟涟、多愁善感和宝黛爱情的凄苦、悲哀通过绛珠仙子用一生眼泪偿还神瑛侍者影射出来,为全书抒写宝黛爱情埋下伏笔。
同时,第一回还引出了另一条以贾家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兴衰成败的重要主线,这两条主线共同奠基了正文的整体结构。第一回中以甄家的繁荣枯竭预示着正文中贾家同样的境况,乡宦甄士隐本是当地望族,谁料,独生女英莲走失,偌大家产毁于一场大火,甄士隐最终得以彻悟,同疯道人而去。其实甄士隐这一人物形象与全书主人公贾宝玉有紧密的联系,他们都有坚定的不愿走进仕途道路的思想情感,但他们也有同样令人唏嘘的结局。
最后的《好了歌》以及第一回中提到的人物名字所隐藏的寓意也直接预示了全书一些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为全书奠定了牢固的悲剧基调。
可见,曹雪芹所创作的《红楼梦》第一回具有丰富深刻的内蕴,承继了传统手法,但又突破了传统的小说写法,不仅吸引了读者的阅读注意力,更将中国古代小说带入一个崭新的创作境界。所以,如果能将《红楼梦》第一回读懂,读透彻,能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红楼梦》,也能让我们抓住曹雪芹文学创作手法的精髓。
二
曹雪芹主张小说创作要以生活真实为依据,艺术性、典型化地反映生活。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开门见山地批评了那些才子佳人小说公式化、概念化、违反现实的创作倾向,阐明了自己所遵循的创作原则,即艺术创新的基础是生活。继承明代世情小说理论,尤其重视小说描写现实。虽然,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融入其中,但他认为“小说创作要以生活真实为依据,但又不能照搬生活,记生活流水账,而是要根据创作需要,对生活材料进行选择,或删或添,或藏或露,以求艺术性、典型化,天然浑成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他主张在生活体验甚至亲历的基础上,取其事体情理,进行艺术虚构或概括。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是一种“极真”与“极幻”的“虚”与“实”的关系,这在小说理论史上是一种发展的形态。
古代小说的重要渊源之一是史传,写实的传统由来已久。六朝创作的原则是“实录其事”;明清小说的理论中,写实也是重要内容。但是,像《红楼梦》这样达到亲闻亲见亲历的程度及在理论中明确的提出来,是以往诸类小说及其理论所不可比拟的。
在《红楼梦》第一回里,曹雪芹说:“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其中,人物是作者“亲睹亲闻”的,情节的曲折起伏,并不敢有一丝的胡牵乱扯。不仅如此,他还说:“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红楼梦》创作的一个目的,是为闺阁立传。作者认为不能因为自己“差劲儿”,护短而放弃小说的创作。很明显,这里的闺阁故事,作者是其中的参与者。不仅亲闻亲见,而且亲历。这是一种极真的生活形态,生活的原生态,生活的生色真香。
《红楼梦》既不借助于任何历史故事,也不以任何民间创作为基础,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滲透作者本人的血泪感情。第一回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它的表层意思:曹雪芹只是《红楼梦》的编辑者,不是作者;作品也是一部荒唐不经之言,不能当真。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曲折之笔。与曹雪芹关系密切的脂砚斋就指出了这一点:“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脂砚斋告诫读者,不要被曹雪芹“狡猾”的话“瞒蔽了去”,要看清作者在这里采用的是“烟云模糊”之法。而且,透过荒唐之言,能够感受到一把辛酸之泪,这是曹雪芹的辛酸之泪,作者就是曹雪芹。脂砚斋说:“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红楼梦》是由曹雪芹的血泪凝聚而成。
曹雪芹在强调生活的真实同时,又反对拘泥于生活和历史,提倡审美的艺术创造,即“艺术真实”。如他强调自己“不敢稍加穿凿”,又提出“将真事隐去”,“借假语村言”的命题。在《红楼梦》第一回里,他说:“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生活是创作的基础,小说创作不能照搬生活。真人真名,时间地点,甚至生活等一些与表现主旨和审美旨趣没有关系或者关系不大的人或事,都可以舍去不用。而留下的是生活的感受、启发,及其基础上的事体情理,使它更好成为承载来源于生活体验的感悟、美感或理想的有效载体。诚如所评,《红楼梦》,“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使作品婉约含蓄,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从而,“写实与诗化的完美融合,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甜美感,既是高度的写实又充满了理想的光彩。”[1]这种“诗意”、“理想的光彩”,即作者所说的“新奇别致”。
《红楼梦》这种极大的艺术魅力,极高的审美品味,可称为“极幻”的形态。 鲁迅先生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2]愈是抛开生硬的理性观念和写作套路来写作,这种反映愈是自然真实,愈是新鲜别致。通过如实的抒写,却收到了传奇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极真”与“极幻”的辩证关系。
比较而言,曹雪芹其前的小说创作,尽管既有极真理论,也有极幻理论,但是鲜有人能将真与幻两种风格特征统一在一部作品中,达到亦真亦幻的境界,理论上也没有明确提出这种观念。就生活真实而言,世情小说没有达到曹雪芹的真实深刻的程度,其艺术性总体上也不如《红楼梦》。主要以文本立论,自然也没有或没有条件把侧重点放在这些方面。世情小说注重表现时俗,作者的生活体验被提高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们用以构成作品的依然主要是通过收集、积累而得到的材料。真实体验和深刻的程度以及提倡的力度还不能与曹雪芹比肩。例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不能承载作者的主要经历。在理论上,诚如张竹坡评论《金瓶梅》说:“读之。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做出来的”[3]。作者赞赏《金瓶梅》中的生活的真实性,好像是作者亲见亲闻一般,体现了张竹坡对小说真实性的真实看法。然对作者亲历的强调,尚不及曹雪芹。
再如才子佳人小说,其与《红楼梦》及其体现的观念也形成明显的差别。程式化的才子佳人小说,既没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又不尽符合“事体情理”的艺术真实。在虚实关系上可取之处并不多。曹雪芹批评说:“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其人物,不过是“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之类,情节是“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创作动机是“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动机不是源自生活的审美灵感,而是缺少生活基础的某种理性的意识或者心理。这样写出来的东西, 一般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大同小异,逐步走向了千篇一律得到公式化的道路,其在艺术水平也大打折扣。
当然,才子佳人小说的评论者主观上也想跳出窠臼,但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而只是致力于材料奇异、构思曲折而已,即烟水散人《珍珠舶序》所谓“嵬罗闾巷异闻,一切可惊可愕可欣可怖之事,罔不曲描细叙,点缀成帙,俾观者娱目,闻者快心。”[4]这样的结果,不但跳不出窠臼,反而会导致出现更多不合事体情理的破绽,显得不合情理,违反生活真实。即便一些论者也提到小说创作须遵守生活的事体情理,但在真实体验和深刻的程度上,与曹雪芹的“极真”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总之,曹雪芹“极真”与“极幻”辩证关系,在古代小说理论中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的。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98.
[3] 朱一玄 编,朱天吉校.明清小说资料选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4] 烟水散人.珍珠舶序[M]//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2006.
The First Chapter ofADreaminRedMansionsand Cao Xueqin’s View on the Creation of Novels
MENG Huan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31, China)
AdreamofRedMansionsha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ummary and creation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its unique literary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was fully reflected in the first chapter. Cao Xueqin paid attention not only to the reality of life but to the virtual and real combination based on the artistic creation. It is creative in 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 theories to understand extreme reality and magic in the life reality and artistic truth
Cao Xueqin; the first chapter ofADreamofRedMansions; the view of creation
1673-2103(2016)03-0056-03
2016-04-20
孟幻(1992-),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
I207.41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