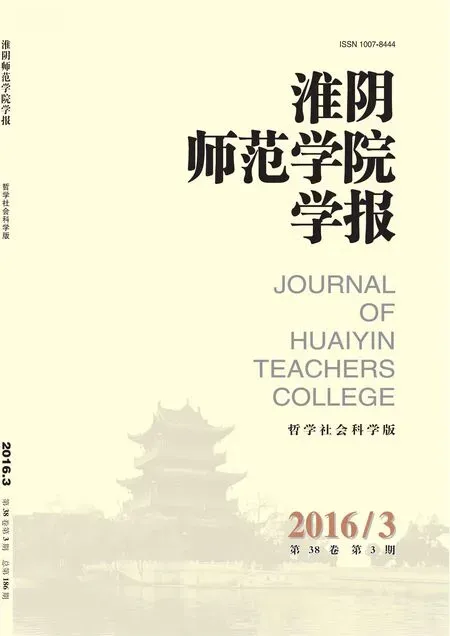钱澄之南明史记载的认识与实践
吴 航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钱澄之南明史记载的认识与实践
吴航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钱澄之亲历明清鼎革之变,积极参与南明抗清斗争。对于记载这段“痛史”,他重视史料来源及口述者的身份,又博取史料,参互考证,强调求真核实的史学认识,形成对于私家南明史记载的一些有价值的看法。他保存南明历史的途径有三:一是“以诗存史”,通过诗篇记载时事,二是撰著、增订“当代史”著作《所知录》,三是试图在地方政府主修的地方志中载入抗清节烈人物的事迹,但因涉及清廷历史禁忌,未被采纳。
关键词:钱澄之;南明历史;记载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钱澄之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尤侧重于其文学、诗学、易学、楚辞学等方面。至钱氏史学,向来比较注意其南明史撰述《所知录》。事实上,翻检《田间文集》前三卷所收史论25篇,是为研究钱氏史学的基本材料。此外,他在康熙初年参与《建宁府志》的修纂工作;晚年流寓苏州时,又与徐秉义商订经史,徐氏撰就《明末忠烈纪实》,与有力焉[1]480-481;又佐徐乾学次子徐炯笺注《五代史》[1]809。然他从中年到晚年,更专注于保存和记载南明历史的学术工作。
一、钱澄之在明末清初的政治活动
钱澄之,原名钱秉镫,字幼光,江南桐城(今安徽枞阳县)人。明末诸生。少时颇有正气,敢于当面倡言诋排阉党官吏。目睹危机四伏,以经济自负,屡上疏言时政得失,不为重视。钱氏与同里方以智交好,并得方父孔炤的垂青。崇祯五年(1632)冬,桐城举中江社[2],钱氏参与其事,得以结识诸多文人学士[3]407。然乡人阉党阮大铖实为中江社幕后主使,钱氏不知其情而入社[4]。值方以智东游归,始知就里,坚辞不赴,遂与之结怨。崇祯十四年(1641),钱氏授经南京。后屡试不售而弃去科举,“益肆志于诗酒山水”,为钱棅(礼部尚书钱士升长子)约为同学,南游吴越之间。时社事鼎盛,复社、几社名流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魏学渠等雅重之,遂结云龙社,以接武东林。
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钱氏在南京得知明亡消息。不久,弘光政权肇立南京,阮大铖得势,大兴“钩党”之狱。钱、阮早年不睦,故名在刊章之列,被迫亡命嘉兴,隐匿于钱士升居所。其妻无依,携子东来。次年三月,左良玉挥兵南下,党祸始解。不久,弘光政权覆亡,南京、杭州相继失守。六月,三吴兵起,钱棅举义抗清,钱氏举家参其军。八月中旬,抗清失败,退至震泽时,钱棅为炮火击中死亡。钱氏妻方氏、次子、幼女皆死,只好带领长子南逃福建[3]564-568。时唐王朱聿键在福州重建明朝政权,以当年为隆武元年。冬,钱氏被授为吉安司理,不得达,改授延平府司理。次年秋,隆武政权又亡,延平被清兵攻破,钱氏与长子相失。纷乱抢攘之际,钱氏只好潜隐于福建山中。至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钱氏得知长子在肇庆,便间道入粤,投奔永历政权[3]570-574。
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十二月二十四日,钱氏参加了永历朝廷举办的科举考试,授翰林院庶吉士官[5]100-101。次年秋,澄之西上桂林。及十月,清兵长驱直入,永历帝奔南宁,钱氏遂与永历行朝相失,被迫剃发易服,法号西顽,潜伏于山中。至永历五年(顺治八年,1651)冬,钱氏披缁与长子返归桐城。顺治十六年(1659)前后,钱氏返俗,改名钱澄之,字饮光,号田间,以遗民身份隐居田园,著述不辍。晚年因长子死于盗贼,迫于生计,不得不频繁出游于南京、武昌、北京、苏州等地,交接故交新贵。
明朝社稷虽被农民军倾覆,但满族统治者以“夷族”乘机入主中原,定鼎北京。随后建立的弘光、鲁监国、隆武、永历诸南明王朝,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逐一土崩瓦解。清廷建立了以满族统治者为核心的联合专政。按照顾炎武的说法:“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6]756-757在汉族士大夫学者眼里,大顺政权倾覆明朝社稷,是“易姓改号”,“亡国”之举;而满族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亡天下”。此一时期,“亡国”与“亡天下”,兼而有之,与中国历史上的宋元之际相似。所以,当时学者往往以“天崩地裂”“天崩地坼”加以形容。对汉族士大夫来说,这种历史记忆是难以抹去的。因此,他们本着“国可亡史不可灭”的学术传统,勇于保存这一段历史。
二、求真核实的史学认识
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之后,明遗民学者对亲身经历的这段“痛史”,自觉担当了记载“当代史”的重任。有人明确提出:“士君子生当乱世,有志纂修,当先纪亡而后纪存,不能以《春秋》纪之,当以《诗》纪之。”[7]这些幸存的遗民人士,或以诗篇记录历史,或以私史保存历史,以秉笔直书或客观再现明清鼎革之变为撰述宗旨。
历史记载首先遇到的是如何求真的实际问题。钱氏慎重史事,推崇韩愈记载史事之范例,说:“韩退之读李翰所为《张巡传》,以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为恨。及闻张籍述于嵩所言,遂据之,因详书巡、远及南霁云事于传后;已,记嵩始末而终以‘张籍曰’,则以言之所自来与传其言者之人皆可信也。昌黎不敢作史,即此见其慎重史事,亦即此可以为后世野史之法矣。”[3]212-214所谓“慎重史事”,根本在于去伪存真,尤其是重视口说史料的来源和口述者的身份。
按照作者(或口述者)与史料的关系,史料可分为所见、所闻、所传闻。钱氏重视口说史料,但对道听途说尤注重辨析。顺治十一年(1654)九月,钱氏访方以智于南京高座寺,听崇祯帝宦官叙述方以智往事,为文记之:
顺治甲午年,方密之以智既为僧,闭关高座寺。余往看之,寓报恩寺,坐卖卜周勿斋肆中,有老僧与同坐,故中官也,问余,知为桐城人,因曰:“桐城有一方以智,尚在乎?昔于内廷供事,烈皇一日御经筵回,天颜不怿,忽叹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如是者再。……上曰:‘……朕闻新进士中,有一方以智。其父方孔照亦以巡抚湖广,与陈某同罪下狱。闻以智怀有血疏,日日于朝门外候百官过,叩头呼号,求为上达。此亦是人子。’言讫,又叹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未几时,释孔照而辟某。孔照之得生由此,外廷岂知之乎?”余闻其语,随到竹关说与以智。以智伏地哭失声,北向九叩头谢恩。甲午秋月事也。[3]494-495
钱氏以口述者老僧原系崇祯帝宦官,所述又是老僧亲见亲闻,故既诉之方氏,又以专文记之。足见他重视亲历者的口说资料及其价值。
钱氏所著南明史撰述,以“所知”为名,更直接地体现他慎重记载历史的史学思想。他在编纂此书时,注意区别亲见与传闻。如记载隆武朝史事,“闽立国仅一年,某以乙酉冬十月始到行在。既补外吏,不悉朝事;又终日奉檄驰驱,无因得阅邸钞。兹编凡福州十月以前事,皆得诸闻者也。至于延平行政、赣州用兵,亦祗记其所亲见者而已”。记载永历朝史事,“粤事自戊子秋九月过岭到肇,忝列班行,略有见闻,随即纪录。兹编凡戊子以前,皆本诸刘客生之《日记》也。于湖南战功多不甚悉,亦因其所记者而已。辛卯春,滞梧州村中,略加编辑。夏四月,始离粤地。去南日远,间有传闻,不敢深以为信,亦不敢记也”[6]11-12。因此,《所知录》颇为并世学者所推重,黄宗羲赞许为“考信不诬”[8],陆元辅亦给予“文直事核”的高度评价。
在重视史料来源之同时,钱氏还注重博取史料,参互考证,归于一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陆元辅自苏州寄书钱氏,希望为其《争光集》作序。钱氏因未睹其书,复信勉以“博访四方亲经丧亡之士”,“参以故老之见闻”,多方征集史料,以成信史。他在信中指出:“甲申以后,国凡数变,死者遍东南,人不能尽知;即有知之者,足下亦未必尽知人所知,有不知,则足下书已成,后将以之为据,其所遗者即终不为世知矣。虽后此有人能补其遗,而于足下阐幽之志终未慊也。”事实上,明清鼎革之际,吏民惨遭荼毒,死者众多,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期死而死者”,“骂贼而预办死者”,二是“不期死而死者”,“仓卒无所逃避而死者”。他以崇祯八年(1635)以后农民军攻打桐城、隆武二年(1646)清军攻破赣州诸死者为例,虽“等死耳,而所以死不等”,主张尤须分辨真赝。因为“死后表章褒恤各有差等”,“大抵子弟门生有气力、能文章者在世,其死也必传,传亦甚烈;不则仅纪其死耳,未知其所以死也;又甚,则死亦未有纪之者矣”。这样一来,“世之期死死者未必传,而不期死死者之请恤建坊者比比,而为之纪载者,复增饰其事,气节凛然可观;至于期死死者,虽或传之,其激烈或反未能及也。……所载者不足信,后将与并载者俱不信矣”。据此,他提出对明清之际死节、死难之“幸而传者,又未可一概论也”,要“核其实”,有所分别。钱氏之所以如此,“欲于死后求其所以死而分别之,非有苛于死者也,惟悲夫烈烈而死与碌碌而死者之死无以异也。松柏摧矣,而与众芳之芜没同嗟,则松柏不足嗟矣。干将亡矣,而与牛刀之缺折并惜,则干将不受惜矣。是故幽光不阐,非徒与草木同腐之为幽也,以烈烈与碌碌者一例,其光犹之幽也。”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深入考实、严肃求真,才能达到名副其实的“阐幽”,表彰抗清人物的忠节行为。在信的结尾处,他希望陆氏“广搜详考,不厌过慎,然后敢为之序言,附以不朽也”[3]83-85。
及陆氏书成,他撰《序》重申道:“丧乱以来,死而不传者多矣,其传者未必尽可信也。以不可信者与可信者一例并载,后有识者,将并可信者疑之;即不之疑,而使烈烈而死与求生不得而死者概称忠义,杂明珠于鱼目,其光犹之幽也。故吾谓,此事必且需之岁时,博访四方亲知灼见之士,其言之足信者,而又审焉,然后载之于书。”[3]214-215可见,注重求真核实,才能保证历史记载接近真实,这是“阐幽发微”,表彰抗节人物的基础。
三、对私家野史的看法
钱氏阅及并世学人所作记载明清鼎革史事的多种私家野史,如刘客生《日记》、邹漪《明季遗闻》、曹溶《明人小传》、汪蛟《滇南日记》、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陆元辅《争光集》,以及方以智《两粤新书》、方其义《乙酉记略》[9]。较之清朝官方记载,他更倾向于野史记载的真实性,曾说:“吾阅历世变既久,尝以为史家之言不足深信,则庶几野史犹有直道存焉。惟是野史者流,其言皆得诸传闻,既无情贿之弊,亦无恩怨之私,徒率其公道,无所忌讳,故其言当可信也。”但野史亦有不足,其作者“大抵草茅孤愤之士,见闻尠浅,又不能深达事体,察其情伪,有闻悉纪,往往至于失实。集数家之言,大有径庭,则野史亦多不足信者”[3]212,故野史亦未必皆可信之书。
顺治十六年(1659),他目睹坊间流传野史《明季遗闻》记载荒谬,不胜愤慨,赋诗写怀。其诗云:
史家称实录,孔子赞阙文。所以信后世,岂不贵其真。不见韩退之,有论不敢伸。天刑与人祸,言之悸心神。斯人愍不畏,谬妄撰《遗闻》。甲申殉国变,烈哉数名臣。此外安足道,表章必有因。又如卖国者,丹书著国门。公论岂能废,曲笔乃为原。皆言此书出,意实由斯人。南渡政多端,纲领略不存。所载诸谠论,当时未一陈。乃知纪失实,总以循交亲。至于闽粤事,有若梦中言。年月既错乱,爵里亦纷纭。是非与功罪,颠倒难具论。闻有华小吏,遭斥怀怒嗔。私意撰伪书,诋诬无不云。俨然编野史,小人语是遵。此事吾亲见,纪录亦未湮。奈何当吾世,亲见是非翻。《遗闻》颇流布,人图耳目新。耳目既以惑,后世何所循?安得有识者,一见辄为焚。慨然作此诗,聊以写烦冤。[10]101*按:诗名《偶见坊间有近刻〈遗闻〉一书,悖谬特甚,不胜愤惋,遂成此诗》,在《田间诗集》卷五;本卷旧题《江上集》,原注“己亥”,即顺治十六年。
按《明季遗闻》,旧题“江左邹漪流绮辑”,卷首《自序》署曰“顺治丁酉孟夏梁溪邹漪流绮题”*按:邹漪《明季遗闻自序》,所引之本不署年月。此参见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50—452页。。丁酉即顺治十四年(1657),与钱氏所称“近刻《遗闻》”相符。诗有“甲申殉国变,烈哉数名臣。此外安足道,表章必有因”之句,盖指襄城伯李国桢降“贼”自缢而“谬称节义”[11]1796-1797。全祖望指出:“邹氏《明季遗闻》秽诬不堪,其为张缙彦、李明睿、王燮,各曲笔增饰,是思以只手掩天下目也。”[11]1819且《明季遗闻》记隆武、永历时事,始乙酉八月,迄庚寅十二月,仅为书一卷,邹漪自称“南渡事多不备,止记耳目所及”[12]。故钱氏讥为“至于闽粤事,有若梦中言”。由于作者的不同动机和阶级属性,野史之作往往失实乱真,混淆视听。钱氏有见及此,秉持谨慎态度,给予实事求是的批评。
与之相对,钱氏尤重视亲历事变之人的南明史撰述,认为这些撰述大多记录亲见亲闻,保存了宝贵的“当代史”资料。如汪蛟《滇南日记》一书,他明确指出:
今日野史,即异时正史所据。惟存心虚公忠厚者,能为此事。不虚则中有成见,而其言不信;不公则意有偏私,而其言不信;不忠则情实不核,而其言不信;不厚则求人过刻,而其言不信。惟足下之盛德,足以具有四者,故弟以为《日记》出自足下之手,必可据也。主上以神宗之嫡孙,称号十有六载,天命虽移,人心犹系,虽僻处天隅,实正统所在也。惮狐聚一日不迁,则正统一日在周;崖门舟一日不覆,则正统一日在宋。足下《日记》正未可以偏方小史视之也。譬之故家遭难,第宅已为他人所有,子孙仅存,寄身籧庐,无知识者以宅内为主人,而有知识者终以籧庐中为主人嫡派之所在也。足下《日记》,不过籧庐中语,异时重之,固有胜于金匮石室之藏者。[13]395
此书具有重要价值,而汪氏“不甚秘惜,容易示人”,钱氏担心“恐笥无别本,一有遗失,后欲追记,未免缺如”,劝他倍加珍重此书。可惜汪氏之书,今不知尚在天壤间否。
至于鉴别野史真赝,钱氏认为要搞清楚史料来源与作者(或口述者)的身份、经历的关系,“夫欲信其书,必先信其言之所自来,与夫传其言者之人。其言之出于道路无心之口,足信也;言之出于亲戚知交有意为表彰者,不足信也。其人生平直谅、无所假借者,其言足信也;轻听好夸,喜以私意是非人者,其言不足信也”[3]213。所谓的鉴别,是基于作者与传主的亲疏关系,以及作者的作史态度。他进而指出,仅仅取材“家传及郡邑志书”而成的私家野史,“至不足据”。这种认识来自于他参修地方志的史学实践。他说:“自丧乱以来,死事者多矣,然而其死甚不等:有慷慨誓死,百折不回而死者;有从容自尽,既贷以不死,而必欲死者;亦有求生无路,不得已而死者。若一以家传、志书为据,岂尽得其实哉?则真能死者,或反泯灭无传;传之,亦不能详且尽。盖由其人素无名位,而知其事者又不能作为文章,足以为之传也。其传之详且善者,类必其子弟有气力,能表扬其亲,而门生宾客多有文笔,复为过情之褒,因而失其实者比比。”最后总结道:“后之史家,但据其所传之文为之纪载,毋怪乎实之不传,而传者之未必实也。吾盖以今之家传志书,而逆知后世之史不足信,因以不信前世之史也。”[3]212-213
基于以上认识,钱氏为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陆元辅《争光集》撰序时,充分肯定二书在“当代史”记载上的纪实、阐幽之功和学术成就,“盖一主于纪实,一主于阐幽,命名不同,其所以为诚一也,二书当并传。后有史家取据于斯二者,亦可以为一代之信史矣”[3]215。他称《明末忠烈纪实》,“于先朝死事者,自崇祯二年以来,广搜纪录,一无避忌,其中有此然而彼不然者,有一事而彼此互异同者,或有仅存其名而年月未详,本末不载,于是,遍询海内亲知灼见之士,识其言之足可深信者,审之又审,然后据实以书。犹恐未核也,乃仿编年之体,书某年因某事某死。其死之情事历历有闻于世者,则为小传以纪之,如列传焉。至有传闻异辞、事涉可疑者,亦不忍竟没,别为存疑,附诸传后,以俟后之人有如于嵩者,更出其说以相订也。其肆力可谓勤,用心可谓厚矣”[3]213-214。称陆氏《争光集》,“广搜博采,多方裒集……皆采辑旧闻,询诸遗老,亦或有得自道路之口者。或一人而数见,或一事而异词,兼收并载,不敢擅易一字,虑失真焉;不敢以己意去取,宁存疑焉。故其书卷帙繁复,盖惟恐有一事之偶遗,一人之失传也”[3]215。充分肯定了他们保存明清鼎革之史的良苦用心。
四、保存南明历史的途径
钱氏保存南明历史的途径,大概有三。其一,“以诗存史”,通过诗文来记载和反映时事*参见许晓燕《钱澄之闽粤桂诗歌研究》,安徽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郗晓莉《钱澄之及其〈藏山阁诗存〉研究》,暨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杨年丰《钱澄之文学研究》,苏州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其《藏山阁诗存》含《生还集》七卷、《行朝集》三卷、《失路吟》一卷,俱是钱氏隆武、永历时期赋咏时事之篇什。
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七月,钱氏刻《生还集》,“断自弘光元年乙酉,迄永历二年戊子冬止,约计四载,共得诗若干篇,为六卷……其间遭遇之刊壈,行役之崎岖,以至山川之胜概,风俗之殊态,天时人事之变移,一览可见。披斯集者,以作予年谱可也。诗史云乎哉!”[13]399-400又说:“仆昔流离闽中,以吟咏纪事,凡所传闻,即为诗志之,有《哀江南》《续哀》《广哀》及《悲赣州》诸杂诗,俱录入《生还集》。已,在岭外,复值乱亡,亲见死事诸君子,皆系以诗,亦散见《两粤集》中。”[3]83钱氏亲历丧乱,颠沛流离之际,将亲见亲闻载诸诗篇,感时伤事,悯惜生民,表彰节烈,是对这段“痛史”的真实记录,具有深刻的“诗史”精神。
其二,试图在清朝地方政府修纂的地方志中载入抗清人物的历史事迹。
康熙五年(1666),钱氏来游福建,为建宁府推官、同乡好友姚文燮推荐,助建宁知府修纂《建宁府志》。至易代之际建宁籍抗清人物,钱氏从“教忠作孝”、维护纲常名教的角度,希望于《节义传》中立传表彰,但因涉清朝忌讳,不被地方官吏认可。他致书姚氏称:
《节义传》,风教所关,而当事于丙戌死事诸君子颇有忌讳,禁勿书。汉世祖与隈嚣书云:“足下与吾相去绝远,本非吾乱臣贼子,当时欲为君所为者甚众,但事定,宜自审去取耳。”夫嚣与世祖同时举事,尚不目以乱贼,岂有本其故物,一姓继起,而谓之伪朝?忠于故主,守死不屈,而比之叛逆?古帝王于天下初附,未尝不录降者之功,而听不降者之死;天下既定之后,则必以死事者为忠臣,降者为失节:所以教忠也。不当国家鼎革之秋,则忠臣义士之节不见。今禁丙戌死事者不得名《节义》,则节义将以何事见,当于何时成乎?当事既讳,各县亦不肯采访以闻,无从记载。[3]74-78
信中重点列举了隆武抗清死节人物黄大鹏、郑为虹、揭重熙、谢宫锦、陈有祚等,希望表彰此等“忠臣义士”。
在当时严厉的历史禁忌下,为如实记载抗清人物的事迹,他甚至选择权宜之计,“此事附诸《节义传》末,双行细字,以为别纪,宁足讳乎!”[3]76但这一提议亦未被认可,钱氏为之扼腕叹息,赋诗抒发心中愤懑。其一云:“死事前朝彦,于今载不妨。自来非改革,胡以别忠良?正朔相承在,残疆未尽亡。如何同逆命,一概没幽光。”其二:“戊子城屠日,铢锄岂记名。即应讳国事,何至匿家声。士隐疑无罪,女贞合共旌。幽芳不许阐,难解此人情。”[10]304他后来亦称:“近丙、丁间再游闽,为建宁当事属修郡志,各县以节义上者寥寥;问之,则当事不欲以丙戌秋死难者入志。仆力争之,仅存数人,犹是仆所熟知数人而已。”[3]84
钱氏所修《建宁府志》50卷,有清康熙五年(1666)刘芳标抄本,藏日本帝室图书寮。是书第35卷《人物志四·忠烈》,于明清之际死节诸人,仅录及黄大鹏一人。在记载上详前略后,至述其南明行迹,仅有“乙酉秋,巡仙霞关,与郑为虹同死于浦城”16字。第43卷《人物志十二·寓贤》末,录金堡、林增志、刘景瑗3人,皆只字不提其南明抗清事迹。[14]
康熙十一年(1672),钱氏北上京师,途经江阴,当地官员欲聘修地方志,因有“忌讳”,不能如实记载抗清人物事迹,只好作罢。他致书陆元辅有云:“壬子冬入都,过江阴,江阴令苦留修志。仆问曰:‘志肯载乙酉秋守城事乎?’曰:‘不可。’仆曰:‘他吾不知,如戚中翰勋,城破之日,一门七命自尽,血书在壁,今屋毁壁立,每阴雨,字血逾鲜。如此忠赤,能使其终于湮没不彰乎?名教攸关,鬼神可畏,仆未敢闻命也。’遂辞去。由是观之,吾人耳目既隘,地方居官者复以此事为忌,人传者益少,则吾人之所得知者盖亦寡矣。”[3]84可见,清朝历史忌讳深重,中央政府既无松动的政治趋向,下级官吏也不敢私自征入地方志书。钱氏试图在地方志中表彰抗节人物的想法难以实现,迫使他继续增订《所知录》。
其三,撰著、增订“当代史”著作《所知录》以保存南明历史。
其中《隆武纪年》一卷,《永历纪年》三卷,以编年体纪唐、桂二王事迹。唐王始末粗具,桂王则尽四年。此书有四卷、六卷两种系统。四卷本为《隆武纪年》一卷、《永历纪年》三卷,缺录大部分诗作,成于顺治八年(1651)春,为初刊本;六卷本则在前四卷基础上,增以《南渡三疑案》《阮大铖本末小纪》两卷,盖作者在康熙二十年(1681)前后据行世野史事略增补,并录入早年大量诗作,成为此书定本。[15]
《所知录》在体例上有所创新,记载南明史事之同时,又系以钱氏历仕隆武、永历二朝时赋咏篇什。钱氏自称:“某平生好吟,每有感触,辄托诸篇章。闽中舟车之暇,亦间为之。粤则闲曹无事,莫可发抒,每有纪事,必系以诗。或无纪而但有诗,或纪不能详而诗转详者,故诗不得不存也。删者甚多,亦存其纪事之大者而已。”[5]11-12对此,有些人不能理解,认为有乖史体。晚清南明史专家傅以礼所作的解说,道出了钱氏难以言喻的苦衷:“至注中分系诗篇,人亦疑其有乖史体,故传本多删削者。不知钱氏本擅词章,所附各什,尤有关系。祗以身丁改步,恐涉嫌讳,未便据事直书,不得已托诸诗歌,藉补纪所未备。观例言所称,‘或无纪但有诗,或纪不能详而诗稿转详’等语,即知其苦心所在。乌得以寻常史例绳之!”[16]此书编年纪事之下,系以当日赋咏诗篇,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俨然有“诗史互证”的特点,堪称此书之一大特色。在具体编排上,“有大书,有分注,注内散附诗文,又有缀后各条,则另行一行以别之”,虽以编年记事,然更似具纲目之形。此等变通更能反映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形势,展现真实的历史环境。“文不能详,诗转详之”,是钱氏南明史撰述的优点之一,是对传统编年纲目史书体例的变通和创新。
参考文献:
[1]李铭皖,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钱撝禄.先公田间府君年谱[M].影印国粹学报.扬州:广陵书社,2006.
[3]钱澄之.田间文集[M].彭君华,校点.合肥:黄山书社,1998:9536.
[4]朱倓.明季桐城中江社考[J].中研院史语所集刊,1930年第一本第二分册.
[5]钱澄之.所知录[M].诸伟奇,辑校.合肥:黄山书社,2006.
[6]顾炎武.日知录[M].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屈大均.翁山文钞[M]//屈大均全集:第3册.王贵忱,等,编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79.
[8]黄宗羲.黄宗羲诗文集[M]//黄宗羲全集:第10册.吴光,等,编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476.
[9]方其义.时术堂遗诗[M]//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4册.影印清康熙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09.
[10]钱澄之.田间诗集[M].诸伟奇,校订.合肥:黄山书社,1998.
[11]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M]//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铸禹,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2]邹漪.明季遗闻[M]//续修四库全书:第442册.影印清顺治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583.
[13]钱澄之.藏山阁文存[M]//藏山阁集.汤华泉,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4.
[14]程应熊,姚文燮.(康熙)建宁府志[M]//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第6—1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15]陈祖武.钱澄之著述考略[J].文献,1984(3).
[16]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08-111.
责任编辑:仇海燕
作者简介:吴航(1978-),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6)03-0350-06
收稿日期:2016-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