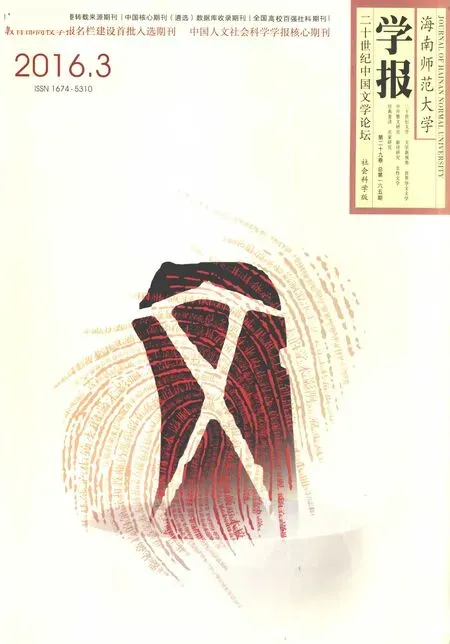“以诗为名”
——谈文学研究会与学衡派间的一桩公案
高晓瑞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以诗为名”
——谈文学研究会与学衡派间的一桩公案
高晓瑞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文学旬刊》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研究会将其作为自己发表新文学观念和打击旧文学的阵地,文学研究会与学衡派之间的论争也主要是在这里进行的。细查《文学旬刊》,发现这场持久的口诛笔伐竟始于当时南京高师学生编辑出版的报纸“诗学研究号”。透过这段历史,可以一睹两派之间的恩怨过节,更可以深入地理解南北学风的差异以及这场论争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文学旬刊》;文学研究会;学衡派;文学论争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在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的倡导下浩浩荡荡地兴起的,他们向旧文学投出匕首的阵地是《新青年》。但1919年前后,新青年同人们的编辑方针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即胡适的“多研究问题”和陈独秀的“干预政治”。这种内部分化使得《新青年》越来越向社会批评与政治批评的方向发展,并且从1920年9月第8卷起,它开始成为提倡社会主义运动的刊物,逐步远离了与新文学紧密相连的初衷。而作为当时国内惟一的大型新文学刊物,《新青年》的分化无疑给当时的文学界造成了一段空窗期,这种留白对于当时以除旧立新为己任的文学青年而言是具有刺激作用的,因为他们渴望对新文学产生一种导向作用。正因为有着独一无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以组成社团的方法来扩大影响力,恰巧促成了文学研究会等新文学社团的成立。所以新文学社团的一个标志便是要“有作为”,“没有一个社团承认自己的办社初衷只是闲情逸致的驱使,也没有一个社团创办之后的一切作为都围绕着闲情逸致。”*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33-34页。因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的文学研究会,在成立初期便自觉地接了此前新青年同人的班,朝旧文学阵营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从社团的角度来讲,文学研究会的完备程度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都是别的社团无法比拟的,它成立时即发表了《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简章》(即章程),还拥有了《小说月报》《文学旬刊》等刊物;在组织程序上,责任分工明确,除了12个发起人以外,还包括“书记干事、会计干事”等,而对于北京以外地区的成员,甚至还订立一些工作计划,如“组织读书会”“设立通信图书馆”*《文学研究会简章》,《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可见为了握住《新青年》传下的接力棒,文学研究会成员们可谓是下足了功夫,而他们在被予以重任的同时,也不忘设计新文学未来的走向。在成立之初,便在宣言里高调地打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的口号,目标对准长久以来把持文坛的鸳鸯蝴蝶派,力图重整新文学界的格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文学研究会的创作、理论、翻译等活动,并不仅仅是为了培养一批独具特色的作家、批评家,更大的目的是为了对新文学潮流和文坛走向进行建构。在《新青年》同人分化后,我们可以理解在那个新文学刚刚起步的时代学界无首的状况,因此在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初期,他们积极向旧文学势力宣战。当然,我们也同样理解了他们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师生间那场关于新诗与古体诗的持久的论争。
一、“一条疯狗”:《文学旬刊》上的口诛笔伐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一项是“反文言”,它宣告了文言文时代的结束和白话文时代的开始,但在文言文传统历时持久的中国,这突然的改变对于部分知识分子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而让白话从一种语言表达到构成文学的基础,再到如何用白话承担起改造社会的任务,这经历了几代知识分子的思考。从胡适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是什么时代,说什么时代的话”*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60页。,到新潮社的傅斯年提出的“欧化的白话文”*傅斯年:《怎样写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这些关于白话文的讨论,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白话被赋予了重大的责任,即傅斯年所说的“借思想改造语言,借语言改造思想”*傅斯年:《怎样写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这是与传统文言文仅为表达自己情怀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众位思想家们知道,虽然有白话未必就能产生出新思想、新文学,但是我们首先得有一个新的媒介——白话,“先要做到文学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集》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2页。所以,白话文在“五四”一代新文学家那里,就成了一项必备的传播新思想、改造旧思想的工具,人们对于经济、文化、道德、人生的观念都改变了,对于一些问题将会有了新的意见和言说,旧皮囊无法装下新鲜的美酒,“新的思想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了”。*周作人:《文学革命运动》,《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
既然白话如此重要,那么当文学研究会的骨干人物郑振铎看到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仍以宣扬古体诗为本时,我们可以想见他当时迫切想纠正这种思想的心情。所以他在1921年11月3日给周作人的信中如此写道,“南高师日刊近出一号‘诗学研究号’,所登的都是旧诗,且也有几个做新诗的人,如吴江冷等,也在里面大做其诗话和七言绝。想不到复古的陈人在现在还有如此之多,而青年之绝无宗旨,时新时旧,尤足令人浩叹,圣陶、雁冰同我几个人正想在《文学旬刊》上大骂他们一顿,以代表东南文明之大学,而思想如此陈旧,不可不大呼以促其反省也。写至此,觉得国内尚遍地皆敌,新文学之前途绝难乐观,不可不加倍奋斗也。”*郑振铎:《郑振铎致周作人信》,《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五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353页。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出刊于1921年10月26日,而遭到文学研究会成员的猛烈批判仅仅就在其出刊后的两个星期。首先站出来的是化名为斯提的叶圣陶,他在1921年11月12日的《文学旬刊》第十九号上点名道姓地指出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为“骸骨之迷恋”,他指出诗的作用是“批评人生表现人生”,如果人生是变动不息的,那么诗歌就该随时代变化,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思想上,而南京高师那群师生依旧“照抄以前的批评人生表现人生的诗学的研究”,过去的诗留下的精神曾给当时的人以启示,如“塚墓里的骸骨曾经一度有生命”*斯提:《骸骨之迷恋》,《文学旬刊》第19号,1921年11月12日。,但对于现在的人却没有了意义。在叶圣陶眼中,他们在“诗学研究号”中居然推崇旧诗,把精力耗费于已成骸骨的事物上,那就相当于犯了十恶不赦的错误了。
这篇犀利的批评一出,立即引起了南京高师师生们的反攻,由此也开创了《文学旬刊》自创刊起最富有战斗性的一段时期。紧接着在《文学旬刊》第20期,立刻在通讯栏里刊出了薛鸿猷在1921年11月13日致西谛先生的一封信,全文无标点,一边挑战似的坚持拟古的特色,一边要求“纠正斯提之谬误”*《通讯:薛鸿猷致西谛》,《文学旬刊》第20号,1921年11月21日。。乍一看这种回复无可厚非,但此信后有一编者附记让大家窥到了玄机:“薛君大稿,题为《一条疯狗!》。全篇皆意气用事之辞。本不便刊登……但新旧诗的问题,现在还在争论之中,迷恋骸骨的人也还不少,我们很想趁此机会很详细的讨论一番。所以决定下期把薛君的大稿刊登出,附以我们的批评。”
就这样,围绕着“一条疯狗”的骂战就开始了。在《文学旬刊》第21号上,首先就刊出了守廷的《对于〈一条疯狗〉的答辩》,在题目上似乎就把薛鸿猷对斯提的谩骂不动声色地还回去,更指出他的这种谩骂根本不值得新文学者的注意,但是现在同薛君一样的“准遗少”并不算少,所以还是有讨论的必要了。守廷首先就指出薛鸿猷对于斯提君的文章的不切实际的理解,指出斯提批评的是《东南大学南高日刊》里“诗学研究号”中的旧诗依旧沿袭古代人的旧形式,并非在骂薛君的“大文”《诗与哲学》。其次,他通读南高日刊,发现里面所刊载的诗文颇像“前清或前明的落魄秀才,三家村学究的作品”,消沉黯淡的气息弥漫其中。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拟古诗磨灭了作者的创作个性,“读者能够知道前一首是谁做的,后一首是谁做的么?这种诗还曾包含作者的人格在里面么?像这种空空泛泛的感怀之作,还会有什么时代精神么?”*守廷:《对于〈一条疯狗〉的答辩》,《文学旬刊》第21号,1921年12月1日。所以“诗学研究号”占用“诗学研究”这个名字,根本就是名不副实的。而薛君的不分青红皂白乱骂一气,不得不让人感叹“薛君休矣!”
紧接着守廷长文之后的是薛鸿猷当时回复斯提的那篇《一条疯狗!》。在文本一开篇就称斯提的批评为“狂吠一阵罢了”,并洋洋洒洒地提出了自己的诗学观,条条都为自己以及南京高师诸师生教学古诗文正名。其中几条为:“(四)我认定我们当在文言诗中,做一番整理的和改革的工夫,在语体诗中,做一番建设的工夫。……决不能因为是前人的作品,就鄙弃之,一笔抹煞,谓之毫无价值,而失学者研究精神。”“(五)我认定一个学府中,对于各家学说,当并容兼蓄,决不能受一种学阀之把持。所以‘诗学研究号’全发表文言诗,改日尚须另刊语体诗,从长讨论。”“(九)我们以前人的文学做食品,我们吃了消化了,很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增长我们的智力。”*薛鸿猷:《一条疯狗!》,《文学旬刊》第21号,1921年12月1日。这些观点首先就确定了文言诗不为“骸骨”,反倒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而且对现代人有巨大的启示。其次,还影射文学研究会为“学阀”,称他们为了自己的主张压制其他学派,而这个词在之后不长的时间中,即将被学衡派诸君引用来批胡适。
在这期短短四版的刊物中,骂战并不止于此。之后连续刊载署名卜向的《诗坛底逆流》,声明若有人迷恋骸骨,我们本不必在意,但“现在这一二人竟想将他们那嗜好发挥光大,叫大家也迷恋骸骨,我们却不敢认为妥当”*卜向:《诗坛底逆流》,《文学旬刊》第21号,1921年12月1日。。署名“东”的《看南京日刊里的“七言诗文”》称读了他们的旧体诗“不觉起了个恶呕”*东:《看南京日刊里的“七言诗文”》,《文学旬刊》第21号,1921年12月1日。。而署名“赤”的《由〈一条疯狗〉而来的感想》更是言辞激烈,声称恭候薛君的“第二条疯狗”*赤:《由〈一条疯狗〉而来的感想》,《文学旬刊》第21号,1921年12月1日。。
关于新旧诗问题的讨论,双方当然不会这么快就偃旗息鼓。所以在第22期的《文学旬刊》上,首先就刊出了缪凤林的《旁观者言》,他站在南京高师的立场上,称“余觉两方俱以日刊少数人之诗牵涉学校”这事失之公正,同时称斯提守廷诸君之论“以偏盖全”*缪凤林:《旁观者言》,《文学旬刊》第22号,1921年12月11日。,所以有必要以“旁观者”的眼光来论证一下此事。说是旁观,其实依旧“意气”,按末尾的编者语来看,其中删除了几段“他不必说而说的话……但原文的真意确是毫无失掉”。本期末尾处还登有守廷和欧阳翥的通信,继续讨论“新”与“旧”能否调和,“诗学研究号”中的旧诗是否含有惋惜帝制之意。客观看来,这一期的争论相对平缓了很多,但却在编者后记中隐藏了玄机,“薛鸿猷先生:来信因篇幅关系,且中多意气之辞,不便登出,乞谅解!”
在之前已经论述过,对文学研究会而言,最重大的任务是要引领新文学走上正轨,同时摒除其发展途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倒流”因素,所以在“破”的过程中更要“立”。于是在《文学旬刊》第23号中,先后登出了刘延陵署名Y.L的《论散文诗》、台静农的《读〈旁观者言〉》、吴文祺的《对于旧体诗的我见》。尤其是吴文祺,在其论文中鲜明地指出:“诗和时代精神相表里的,时代精神既变动不息,那末诗也应当跟着变迁。‘旧壶不能盛新酒’,已死了的文字决不能表微妙的情绪;印板式的诗体,决不能达活泼的想象。”*吴文祺:《对于旧体诗的我见》,《文学旬刊》第23号,1921年12月21日。吴文祺于1917年从南京的金陵大学肄业,对东南一带学风相对了解,而且擅长语言学,所以除《文学旬刊》第23期外,他还在第25期上发表《驳〈旁观者言〉》,反对缪凤林并指出新诗之好坏不在韵律、平仄、格式等问题上,更于1922年2月11日在第28期上撰文《〈又一旁观者言〉的批评》,广征博引,表达自己对于现代无韵白话诗的支持。
时至于此,文学研究会与南京高师诸师生间关于新旧诗的论争,以及由“一条疯狗”引发的口诛笔伐才稍稍平息下来。而平静并不意味着两派的相互承认和妥协,反倒是因为文学研究会把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诗学研究号”这些人背后的更大的一个势力——学衡派,一群受过欧化教育却又极力反对新文学运动的守旧者。
二、南北学风: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的“对立”
从1922年起,这段时间的《文学旬刊》《小说月报》上刊登的对于复古派的清算,也基本上是针对学衡派成员的。细查学衡派成员列表,“初期的成员是早期留学哈佛大学的几位白壁德的学生(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和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师生(老师主要是柳诒徵、胡先骕、王伯沆、王易、刘伯明、汪辟疆此时尚在南昌心远大学任教授、文科主任。学生主要是缪凤林、景昌极、张其昀、王焕镳、徐震堮、束世澂等)以及南京支那内学院的师生”,*沈卫威:《“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而其中缪凤林等人皆是在“诗学研究号”事件中与文学研究会笔战的主力,所以他们基本代表了东南大学整体的学术研究倾向。而从文学研究会这边来看,“主力”茅盾曾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茅盾:《学生时代》,《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00页。,郑振铎虽然就读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却参与了北京大学举办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陈福康:《一代才华——郑振铎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页。,他们的前辈周作人,当然也是文学研究会成员,更是从1917年开始就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就开始宣扬白话文,所以这场针对“诗学研究号”的论争,表面上是文学研究会和南京高师学生之间的对立,某种程度上更可以看成是北大和东南大学这两所学校之间学术风气的对立,而学校学术风气的相悖,更深层次显示的是地缘文化的差异。
一直以来,学界对社团、学派以及它们相对应的刊物的研究都相当充分,研究者们习惯于从每个社团入手,以时间为维度研究他们的思想变迁、对比彼此之间的差异,却鲜少从地域文化空间、地缘文化谱系等方面考虑社团文学风格的殊异性。因而当我们重新来看待文学研究会与学衡派之间论争的这段历史时,不应直接就从两派理论主张入手,更应考虑地域这个无形的大手在背后潜移默化的作用,正如郁达夫所言:“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就不得不受什么地方的感化。”*郁达夫:《夕阳楼日记》,《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1922年8月25日。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这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作家,更有扎根于各个城市的社团。
先看成立于“五四”时期北京的文学研究会,鲁迅先生曾说,“北京是明清的帝都……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鲁迅:《“京派”与“海派”》,《申报·自由谈》1934年2月3日。不仅明清,在中国历史上,做官多是靠的种种考试制度,而要参加考试的前提则是有一定的文化积累,知识分子有实现抱负的雄心,则需要做官;官员若需表达心迹,也总以文学的形式来记录。所以对于北京这样一个帝都,现代文人受到的最深影响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心意识。如《新青年》的真正发展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是在移师北京,并得到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大学的推广之后。《新青年》的推广者以及接收者都与北京大学有巨大的联系,潜藏的原因则是知识分子胸怀天下的中心意识。在《新青年》改组后,一手承担起文学使命的文学研究会则在建社初期就宣布要“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目标是“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和“建立著作工会”,*《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同样也是这种中心姿态的直观表现。所以纵观文学研究会的发展,不管是以“研究”一词作为自己的社团名词,还是打着“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姿态来启蒙大众,更有的是刚成立就以强势的姿态来对鸳鸯蝴蝶派、学衡派等团体进行笔伐,都可以理解为它的目的是在进行着对整个新文学格局的设计,不断强化着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工会”的形象,以此来据守文坛中心地位。这种对社会改革所自觉担负起的责任,不能不说有传统知识分子精神的遗传。其次,与上海的租界不同,当时北京最为流行的是大学,学院派风气的盛行是当时北京的一大特色,尤以北京大学之风最盛。学院风气的一种体现就是打通中外古今的文学,所以文学研究会的宗旨定为“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文学研究会简章》,《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对待别派的态度则取“人生的艺术派”*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北京晨报》1920年1月8日。,显示出四平八稳,包罗万象的气势。即使是在打击旧文学时,也依旧不忘提倡“整理国故”,原因是“完全是为了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并不是向古人去学本领,请古人来收徒弟”*顾颉刚:《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1923年1月10日。。这种倡导与复古的学衡派是不同的,它的目的是让人了解旧文学以更好地为新文学服务。综上所述,从发起人到所处地域都与北京息息相关的文学研究会,不自觉地就染上了帝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也拥有了一种纵横捭阖、指点江山的气势,更拥有了北京大学兼容并包的学术风尚,因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势。
身处南京的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师生和学衡派诸人,却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学术气质。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学术板块便大致分为两大传统,一是以北大为根据地的主张革新的师生,二是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为首的对新文学抱有批判态度的一帮人。他们的地域分别与对待新文学态度的差异,俨然成为近代文学史上“南北”与“新旧”的代名词。细看东南大学的治学之风,首先就是强调文言文、反对白话文;其次是重视古典文学研究、轻视新文学创作;再有推崇固有文化、吸取西方文化来改良传统文化。这不仅是新文学阵营对他们的指责,更是南京诸人对自我的一种肯定。其实相比于“新旧”而言,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之间的差异更在于“激进”与“保守”之间,且不论从20年代到40年代南北学派的几次分和,就我们讨论的学衡派时期的东南大学,也不能完全和甲寅派等纯粹的复古派划上等号。他们的口号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即首先是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成分,同时也强调吸取外来文化,将中外的精髓同时吸取,摒弃新文化运动者那种模仿西人不得法的错误。在破旧立新面前,他们主张的是保守的方法,即“古语有云,利不十,不变法”*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06页。,在没有确定废文言立白话是否完全有利的时候,不应抛弃文言。白话的产生对文学只是多了一种表述的方式,还远远没有达到要取代文言的地位。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对白话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认同的,但这种瞻前顾后的态度对于新文学的倡导者而言是迂腐不堪的,所以两派之间的对立不可避免。若同样从城市的角度来讲,南京与北京一样也曾是国都,但却曾在明代被明成祖朱棣废弃,显示出“而今王气暗销沉”*欧阳翥:《谒南京古物陈列所》,《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日刊·诗学研究号一》,1921年10月26日。的衰颓之气,颇有遗少遗老之风。其次,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虽在北京风起云涌地进行着,但在南京,似乎远远没有受到同等的影响。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南北学者之间的不通“声气”。早在1923年,尚为东南大学历史系学生的陈训慈就敏锐地发现当时学术界的一个问题:“耆学宿儒往往与新进学者各不相谋。又因地域之暌隔,而各地学者常不能共通声气”,这实乃“不幸之现象”*叔谅:《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史地学报》第2卷第3期,1923年3月。。就是这种各自为王的思想和天各一方的地域差异,导致各地学者“不通声气”,也间接促成了他们之间学术的对立。
其实学衡派的保守不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才形成的,早在胡适、梅光迪、胡先骕等在留学美国期间,对立就已经开始了。1915年至1917年间,留学美国的胡适就开始白话诗的实践,而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便开始有了与他截然不同的立场。两人虽然同宗英美文学,却由导师观念不同而各异,“胡适所宗的是科学主义、实验主义的大师杜威,而梅光迪所宗则是人文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古典主义的大师白璧德(学衡派的主将吴宓、张歆海、汤用彤等都是白氏的门生),新文化派的胡适与文化保守派的梅光迪之间的对立,其背后实质上是当时美国两大文化派别的对立。”*潘正文:《“文学地理”与现代社团文风》,《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所以回国后,胡适率先提出了改革的主张,而梅光迪等人则选择了保守落寞的南京城来弘扬保存旧文化。而心系旧文学的吴宓在1919年学成归国后也毅然放弃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抛出的橄榄枝,自觉来到了东南大学。正在新文学风生水起的时候,他来到南京是否也意味着与北京的背离?而之后在他主导下的学衡派也确实是做到了这一点。
三、“谁的胜利?”:论争对新文学运动的影响
文学的发展需要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环境,这种健康对应的是一个多元共生的局面。任何时代的文学若想要健全地成长,就必定需要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环境。就“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发展而言,出现多种多样的文学社团、文人派别,他们之间的论争、制衡都为文学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各派以不同的思想相互碰撞,给后世学人呈现了那个时代绚丽的风采。
文学研究会与学衡派及南京高师师生等人的论争,虽然就历史的观点看起来前者进步,后者保守,两者对新文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多寡也是一目了然的,但其实这场论争不论胜败,都对现代文学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因为他们各自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才形成了不同文学团体之间的相互制衡、优劣互补的局面。若非如此,只有一种单一的声音占领文学的话语权,则会显得思想单一、审美单一、题材单一,缺乏文学应有的思想性和活力,因而各种流派之间的相互制衡才显得如此重要。朱寿桐在其著作中谈到了文学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问题:“一是发展缺乏参照……二是容易造成对一定文化资源的恶性开发。”*朱寿桐:《中国现代社团文学史》,第94页。意思是说,如若一时代的文学只剩下独门独派,那么它发出的声音即使再正确再美妙,缺乏了其他门派的砥砺,它也会逐步走向话语霸权,在自满自得之中逐渐丧失自己的创造力。其次,由于缺乏其他派别的文学倾向作参照,这种单一的话语则只会按照自己的选择对文学题材、体裁等进行筛选,即使是再丰饶的矿藏也经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开发,在这种恶性循环下,不得不生产出让人啼笑皆非的作品,如“文革”时期的工农兵文学以及样板戏。所以我们要承认,文学的健全发展,是离不开多社团、流派彼此之间的论争和制衡的。
既然社团间的论争客观上是对整个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有利的,那么,我们也应该这样看待上世纪20年代发生在文学研究会与学衡派之间的这场论战。在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初期,旧文学虽已经在“五四”运动的冲击下面临巨大的挑战,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占有着相当程度的文化市场,而新文学虽然方兴未艾,但尚未进入文学中心场。不仅如此,它还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境况,一时间似乎无人反对也无人赞同,因而先驱们自导自演了“双簧戏”,借以引起文学界的关注。所以文学研究会的产生,一是要巩固新文学的地位,二则要笼络新文学的同道者。希望克服中国向来有的“文人相轻”风气,“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这种诉求是希望实现各种团体广泛的联合,但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自定义的中心主义,有可能会逐渐消解各个团体的个性色彩。与此同时出现的南京高师和后来的学衡派等人,他们其实并未完全反对新文学运动,“素怀改良文学之志,且与胡适之君之意见多所符合。”*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03页。惟一不同的只是对新文学者们过度偏激的做法采取怀疑的态度。客观上看,他们的保守也并非完全等同于落后,因而他们实为一种制衡的力量而非反动的力量。当我们在重看这段风气云涌的历史论争时,更应采取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客观地看待两个社团,他们之间并不能简单地说谁胜谁负、谁对谁错。若非要说谁从中获利,那就只能是有了健全发展空间的整个新文学运动了。
(责任编辑:毕光明)
A Complicated Legal Case between the 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Xueheng School
GAO Xiao-rui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Wen Xue Xun Kan (Ten-day Literary Review) is not only the official organ of the 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the position where the Association would voice its new literary views and crack down old literature but also the very place at which the Association and Xueheng School debated against each other. By scrutinizing Wen Xue Xun Kan (Ten-day Literary Review), the persistent debate, as is found, arose unexpectedly from a newspaper—“Poetic Study”—edited and published by higher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in Nanjing at that time. By virtue of this phase of history, one can have some idea of the feud between the two literary schools and get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ces in the style of study between the northern part and the southern part in China as well as of the impact of such a deba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Key words:Wen Xue Xun Kan (Ten-day Literary Review);the 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 Xueheng School; debates in literature
中图分类号:I 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3-0015-06
作者简介:高晓瑞(1990-),女,四川自贡人,西南大学文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