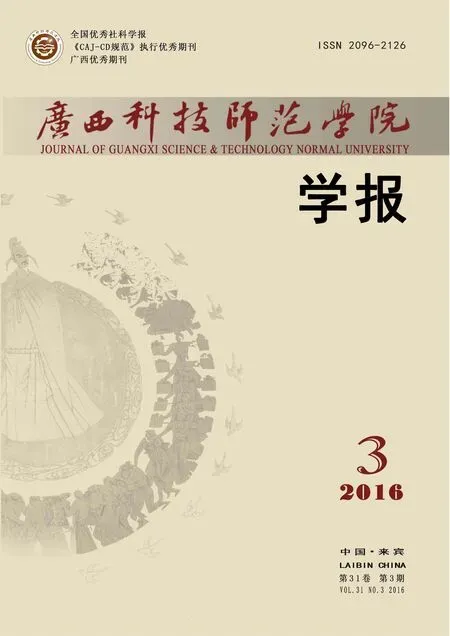西方美学视域中审美经验的“形而上”研究
雷文彪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广西来宾 546199)
西方美学视域中审美经验的“形而上”研究
雷文彪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广西来宾546199)
摘要:审美经验是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西方美学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审美经验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内涵。就审美经验的“形而上”研究发展流变而言,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将审美经验视为审美客体“形式”显现的“和谐”,柏拉图将审美经验视为审美主体对“理式”世界的“迷狂”观照,而康德将审美经验视为主体审美判断的“非功利性”传达,黑格尔则将审美经验看作是理念世界的感性显现。通过对西方美学视域中审美经验的“形而上”研究的历程与流变进行评述,以期明晰西方审美经验研究的发展脉络,从而推进现代审美经验的研究。
关键词:西方美学;审美经验;“形而上”
在美学发展历程中,自从苏格拉底在《大希庇阿斯篇》里追问“美是什么?”开始,关于“美是什么”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外美学家,不同的美学家和美学流派不仅赋予了“美”不同的意蕴,而且建构出了颇有洞见的美学理论体系。伴随着对“美是什么”的追问,“审美经验为何”的述说也成为了西方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和主要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审美经验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意蕴和审美内涵,不同的美学家和美学流派对审美经验进行了不同的理论阐释。波兰美学家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在《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曾对西方审美经验研究的流变历程进行了梳理,他将西方审美经验研究的流变历程分为“早期”、“启蒙时期”、“近百年”三个阶段,但遗憾的是,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只是从审美经验的“心理学性格”的维度考察了西方审美经验的“概念史”[1]318—343,并不能从整体上反映西方审美经验发展的宏大视域及其内在丰富的内涵。从宏观来看,西方美学对审美经验的研究主要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维度,从不同美学流派对审美经验的研究来看,西方心理学美学、接受美学、形象学美学、实用主义美学、阐释学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后现代美学等美学流派都对审美经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阐释,使审美经验不仅承载着“美的历史”的光环与诱惑一路踏歌而行,而且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仍然焕发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正如美学家杜威所言:“审美经验是一个显示,一个文明的生活的记录与赞颂,也是对一个文明质量的最终的评判。”[2]362本文主要对西方美学视域中审美经验的“形而上”研究的历程与流变进行研究,以期明晰西方审美经验研究的发展脉络,从而推进现代审美经验的研究。
一、审美经验:审美客体“形式”显现的“和谐”
在西方美学视域中,“审美经验”是一个既宽泛又含混的美学概念,在不同的美学理论中,“审美经验”常常被“美感”、“美感经验”、“审美趣味”、“审美意识”、“审美态度”、“审美观念”等美学术语所替代。
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研究视域中,审美经验是审美客体的抽象“形式”——“数”所呈现出来的“和谐”。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最基本的元素是“数”,“数的原则”统治着宇宙万物的一切。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以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为主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乃万物之原。在自然诸原理中第一是‘数’理,他们见到许多事物的生成与存在,与其归之于火,或土或水,毋宁归之于‘数’,数值之变可以成‘道义’,可以成‘魂魄’,可以成‘理性,可以成‘机会’——相似地,万物可以以‘数’来说明”[3]。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在宇宙万物的诸多属性中,有一种属性构成了美,这便是和谐,“美”就是“数”所呈现出来的“和谐”。毕达哥拉斯学派将审美对象抽象的形式范畴,如比例、对称、秩序等所呈现出的“和谐”之美视为审美经验的本体,“和谐来自秩序,秩序出乎比例,比例出于度量,度量本子数目。和谐、比例、数目于是成为美之客观的基础”[1]204。
毕达哥拉斯学派不仅将宇宙万物的“和谐”之美视为审美经验的本体,而且将审美经验的产生视为是人与宇宙万物“同声相应”结果。毕达哥拉斯学派将人与世界的关系视为“小宇宙”与“大宇宙”之间的关系,“小宇宙”与“大宇宙”都是由“数的原则”与“和谐”统辖,当“小宇宙”(人)的内在和谐与“大宇宙”(世界)的和谐相契合时,“美感”便油然而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美学乃是以宇宙为中心的,他们认定美乃是宇宙的属性;人类除了在宇宙间发现到美之外,并没有能力去创作它;宇宙之美,是一切人为之美的尺度。”[1]204毕达哥拉斯学派将审美经验抽象为审美对象的客体属性,其审美经验理论充满着抽象神秘主义的色彩。
二、审美经验:审美主体对“理式”世界的“迷狂”观照
在柏拉图的美学视域中,审美经验不属于现实可感的经验世界,而属于“理式”世界,审美经验本质是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不具有真实性。在柏拉图看来,“理式”是宇宙万物来源的“本源”,是事物普遍性存在的“共相”,“理式”并不依存于人的意识,理式世界是个绝对独立的世界,是人类感性经验世界存在的根据和理由;人类感性经验世界只是理式世界派生物,是对理式世界的“摹仿”,是理式世界的“影子”;而艺术创造是对人类感性经验世界的“摹仿”,是对理式世界“摹仿”的“摹仿”,是“影子”的“影子”。为了生动具体的说明理式世界、经验世界和艺术世界三个层面的本质区分及其内在联系,柏拉图用三种样态的“床”来做了具体的阐释,即理式世界的床、木匠制造的床和画家创作的床。“理式”世界的床是“自然中本有”的床,是抽象“理式”的床;木匠制造的床是木匠依据“床之所以为床”的“理式”而制造出来的个别的床,是人类现实世界具体的、实在的床;画家创作的床是画家摹仿个别床而创造的作为艺术品的床。在这三类床中,“理式”的床由于直接体现了“床之所以为床”的“理式”,所以它具有真实性和永恒不变性;木匠制造的床只是对床的“理式”摹仿,这种床由于受到制床材料、环境、时间、空间以及木匠自身的影响,因此它只是个别、一般的床,是床的“理式”的“摹本”,不具有真实性、普遍性和永恒性;画家所画的床只是依照现实中个别、一般床的外形而创造出来的床,是“摹本”的“摹本”,更不具有真实性、普遍性和永恒性。可见,在柏拉图看来,宇宙万物的存在于三种世界中,即理式世界、现实感性世界和艺术世界,理式世界“最真实”,是真理、真知的来源;人类感性经验世界是流动、变化的,只是理式世界“摹仿”的产物;而作为理式“影子”的影子艺术经验则“与真理隔三层”,最不具真实性,只是理式世界的“审美幻象”。因此,柏拉图极力否认人类感性世界中的审美经验和批判艺术创造的审美经验的生成,在他看来,审美经验的生存只有审美主体在对现实世界之美进行欣赏或对艺术世界进行美的创造的过程中,以一种“迷狂”的状态去观照“理式”时才能产生。
柏拉图对现实中的感性审美经验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他否认审美经验的感性存在,甚至认为“快感是最大的骗子”,感性经验的多样性、流动性与变化性是阻碍日常审美经验和艺术审美经验回归理式世界的最大障碍。他所认同审美经验只是生存在抽象的理式世界中的审美经验。在他的审美视域中,只有观照性、内省性的审美经验才有存在的权利。而所谓的观照性、内省性的审美经验就是指审美主体在进行审美创造或审美欣赏时,沉溺于“理式”的反省和作为“理式”捕获的审美经验。
三、审美经验:主体审美判断的“非功利性”传达
康德的美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其理论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的基础之上的。《纯粹理性批判》主要是研究哲学的纯粹“知”性问题,《实践理性批判》主要是研究伦理学复杂的“意志”问题,而《判断力批判》主要是研究美学的“情感”问题。《判断力批判》是联通《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中间桥梁,康德认为:“判断力在知解力与理性之中起桥梁作用,情感(快感与不快感)在认识与实践活动(道德活动)之中起桥梁作用,审美活动在自然界的必然与精神界的自由之间起桥梁作用。”[4]347
康德对审美经验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其美学著作《判断力批判》中,在康德看来,审美经验是联通“知性世界”和“理性世界”的桥梁,它不仅具有“情感性”、“普遍性”的特征,而且也是一种审美判断。如审美经验“这朵花是美的”,“花是美的”是因为“花”具有外在的形式美感,而“花”的形式美感只能通过情感桥梁才能获得。因此,“这朵花是美的”,既不是知性的逻辑推理,也不是伦理意志的判断,而是审美主体审美的情感体验和审美判断。同时,“花是美的”既是人类审美经验的情感表达,也是人类审美经验共通性的“普遍传达”,而审美经验的这种普遍可传达性是建立在人类“审美共通感”的基础之上的。康德说:“比起健全的知性来,鉴赏有更多的权利被称为共通感,而审美的判断力比智性的判断力更多的冠以共同感觉之名……我们甚至可以把鉴赏定义为对于那一种东西的评断能力,它使我们对一个给定的对象的情感不借助与概念而能够普遍传达。”[5]康德指出,与一般经验相比,审美经验有其自身的美感特质,一般经验与“利害”、“欲念”等内容密切关联,而审美经验拒绝“利害”、“欲念”等功利性内容。他认为:“审美判断只要掺杂了丝毫的利害计较,就会是很偏私的,而不是单纯的审美判断。人们必须对于对象的存在持冷淡的态度,才能在审美趣味中做裁判人……(而)审美趣味是一种不凭任何利害计较而单凭快感或不快感来对一个对象或一种形象显现方式进行判断的能力。这样一种快感的对象就是美的。”[4]352—353也就是说,审美判断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目的性”是指审美判断不涉及审美对象的功利、欲望、善等内容,“合目的性”是指审美判断要符合审美主体“先天形式”的目的。康德将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相区分,将审美经验从丰富复杂的日常生活经验中抽离出来,把审美经验的性质与范围限定在“无功利性”的范畴内进行讨论,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经验类型,促进了审美经验的独立化发展。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康德的审美视域中,审美是人类经验认识之外的“欣赏”,审美经验只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一种“形式的直观”和“纯粹的审美判断”,是主体审美判断的“非功利性”传达,将审美经验的主体规定为人的先天形式,割裂了审美经验与现实感性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以抽象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作为“审美批判”的价值皈依和目标旨向,从而否认了审美经验内在丰富的历史积淀性和现实可感性。
四、审美经验:理念世界的感性显现
审美经验是黑格尔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康德割裂审美经验与现实感性世界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同,黑格尔将审美经验融入到现实感性世界中,赋予审美经验以“感性”特质。黑格尔将“美”定义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6]63。“理念就是绝对精神,也就是最高的真实。……艺术、宗教和哲学都是表现绝对精神或‘真实’,三者的不同只在于表现的形式,艺术表现绝对精神的形式是直接的,它用的是感性事物的具体形象;哲学表现绝对精神的形式是间接的,即从感性事物上升到普遍概念,它用的是抽象思维;宗教则介乎于二者之间,它所借以表现绝对精神的是一种象征性的图像思维。”[4]467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将哲学视为“真正的科学”,并将哲学知识的思维逻辑演绎分为“感性的确知”、“意识自身的确知”和“理性的确知”三个环节。黑格尔说:“那最初或者直接是我们的对象的知识不可能是别的,而只可能是其自身就是直接的知识,即关于直接性的知识或者说关于存在者存在的知识。同样,对于这种知识,我们必须如它所呈现出来的那样,不加改变也不含概念地采取直接的、接纳的态度把握它。”[7]在黑格尔看来,“感性确定”是一种最直接、最朴素的意识形式,是意识在经验中发展的最初形式。可见,在黑格尔的美学视域中,理念不仅具有“真”的普遍性,而且具有“美”的可感性,审美经验是理念世界的感性显现。
黑格尔将审美经验将理念世界的感性显现,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是黑格尔对艺术美的褒扬和对自然美的轻视。黑格尔认为艺术美要高于自然美,艺术美才是真正的美,而自然美只是一种不完善、不完全的美。其原因是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产的,他甚至认为“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高多少”[4]475。艺术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产物,也是人类审美经验生成、积淀的产物。黑格尔对艺术美的褒扬和对自然美的轻视,反映出他已经充分认识到艺术与审美经验之间的密切关系和审美经验与“心灵”创造的关联,只不过他将审美经验视为艺术存在过程中“心灵”对“精神理念”的显现。其二是黑格尔认识到了审美实践与审美经验的内在关系。黑格尔把艺术与人对自然的改造同人的劳动实践结合起来,认为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在改造自己,而人在改造自然、改造自己的过程也是审美经验产生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黑格尔举出这样一个事例:一个小孩在河边玩耍时,他将一块石头投入水中,石头落入水中产生一圈一圈波浪水纹,小孩以一种惊讶的神情观看这一圈一圈波浪水纹的不断扩散,顿时觉得这是他创造的一件作品,并在惊讶的神情中和高兴的欢呼声中体验自己的“劳动成果”。小孩的审美经验也正是在小孩“投石”的劳动创造过程中和欣赏水纹的实践过程中显现出来。其三是黑格尔认识到了审美经验的矛盾性与辩证性。黑格尔认为,审美经验的生成过程充满着深刻的矛盾性,特别是艺术美表达心灵“绝对精神”的矛盾冲突。他说:“艺术的要务在于它的伦理的心灵性的表现,以及通过这种表现过程而揭露出来的心情和性格的巨大波动和艺术人物形象矛盾性格的矛盾冲突”[6]275。同时,他指出,审美经验形成的过程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我、这一个我看见那树木,并且肯定这里是一棵树木;但另外一个我看见那所房子,并且肯定这里不是一棵树木;而是一所房子。两条真理都有同样的可靠性,都有亲眼看见的直接性,两者都有从各自的认识得来的确信和确定性;但是一个确定性却消失在另一个确定性中。”[8]从某种意义上说,审美经验生成的矛盾性与辩证性促就审美经验的创造性。
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将理念视为审美经验存在的依据和判断审美经验高低的标准,但并没有像柏拉图那样极力否认和贬低审美经验的感性存在,而是赋予理念以丰富的社会生活的感性内容,认为纯粹的理念必须要通过感性、个别、具体的现实内容呈现出来。然而,他将审美经验作为其“绝对精神”的依附,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绝对理念”的异化形式,把审美经验视为”纯思”的理念活动和“绝对精神”理念的感性显现,否认了人类审美经验的内在丰富性与差异性。
[参考文献]
[1](波)瓦迪斯瓦夫·塔塔尔凯维奇[M].刘文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美)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62.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2.
[4]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37.
[6]黑格尔.美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7]罗伯中.论黑格尔的“感性确知”概念[J].学术研究,2006 (3):41.
[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67.
(责任编辑:刘婧)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126(2016)03-0021-04
[收稿日期]2016-04-21
[基金项目]2015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审美人类学视域下广西大瑶山瑶族的民族记忆与文化表征研究”(15BZW004);2015年度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广西金秀瑶族文化的审美人类学考察与审美认同机制研究”(KY2015YB363)。
[作者简介]雷文彪(1979—),男,湖南蓝山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审美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美学。
The“Metaphysical”Research under the Western Aesthetic Horizon of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
LEI Wenbiao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Guangxi Science&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Laibin,Guangxi,546199 China)
Abstract:Aesthetic experienc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study of aesthetics.In western aesthetics,aesthetic experience carries different 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aesthetic connota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As far as the rheological of“metaphysics”research development on aesthetic experience is concerned,the Greek Pythagoras view aesthetic experience as the aesthetic object of“harmony”revealed by“form”;Plato considers aesthetic experience as aesthetic subject to“manage”the“fan”picture of the world;and Kant’s aesthetic experience regards aesthetic experience as the main body of aesthetic judgment“utilitarianism”and Hegel holds the concept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as the perceptual appearance of the world.This paper reviews the“metaphysical”research process and the rheological under the western aesthetic horizon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in order to clear the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tud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thus,to promote the study of modern aesthetic experience.
Key words:western anthropology;aesthetic experience;“metaphys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