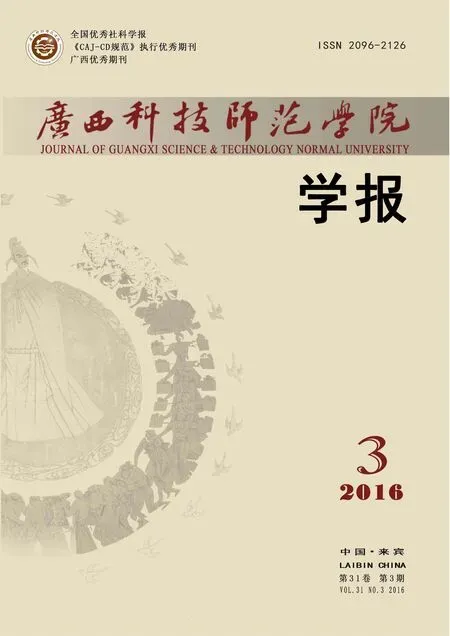日常生活语境下的诗性建构
——论非亚诗集《倒立》
李及婷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1)
日常生活语境下的诗性建构
——论非亚诗集《倒立》
李及婷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1)
摘要:《倒立》是非亚的第二本公开出版的诗集。在这部诗集里,诗人对日常生活有其独特的认识姿态,他以日常具象的书写和独特的形式创新来反思现实生活,形成特定的主题阐释。诗人解构了日常生活“无聊”“无意义”等刻板印象,构建了日常生活的诗性,使诗集《倒立》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关键词:非亚;日常生活;《倒立》;诗性建构
非亚从1986年开始写诗至今已有30年之久,显然,诗歌已成为诗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更是他探析日常生活本质的一种特殊方式。在笔者看来,非亚有三个角色不容忽视:第一个角色和建筑相关,非亚毕业于湖南大学建筑系,现职业为建筑师,建筑师对结构与形象的敏感程度较高,这样的一个职业特征渗透到诗歌创作中,从而影响诗歌的关注点及风格;第二个角色便是诗歌名刊《自行车》的创刊人之一,自身投入到期刊的创办中,给诗人提供了一个及时更新和调整诗歌理论的环境,使非亚对诗歌现象的关照倾向于一种较为全局的角度;第三个角色是诗人,由于受前两个角色的影响,非亚作为诗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创作风格。这三个角色统一于非亚,使非亚个人身份的特殊性得到充分的彰显,形成了“非亚只能是非亚”的创作特色。非亚的诗歌创作之初便呈现了自我身份的独特性,如1987年的《生命的幻觉》中对生命逝去与更新的一种矛盾心理的独到阐释,诗中意象的选择和组织就可见一斑。此后,非亚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诗歌创作理论。1995年之后,他的写作慢慢褪去灼热的追求,回归到客观冷静。“诗歌创作则从抽象转向具象,在保持现代性的同时,诗歌的‘现实感’慢慢成为一种新的追求和可能。”[1]43诗集《倒立》就是在诗人有了较稳定的文艺观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诗人以日常生活为维度,从不同的层面思考生活的本质,让本该沉寂的日常生活迸发出诗性。本文将试图勾勒诗人是如何在日常生活语境下构建诗性,为困在生活“围城”的“城内人”提供一种诗意栖居的可能性。
一、日常具象书写:唤醒日常生活诗意
非亚曾多次提到现实和生活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诗就是对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个具体可感的重要性的维系”[2]172。受其诗歌理论的影响,非亚的诗歌创作基本上依赖于诗歌和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明确表示:“生活,或者我个人的生活,那是我写作的来源、灵感、内容和素材,这一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①非亚.生活,与写作[EB/OL].http://blog.tianya.cn/post-123926-32743381-1.shtml.2011-5-8.非亚所说的个人生活即日常生活,通俗地讲就是我们每天的吃、住、行等事情。不难发现,日常生活具有零散、琐碎、重复等特点,能成功打通日常生活和诗意的通道并非易事。从诗集《倒立》中,我们可以看到非亚将观察的笔触延伸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洗澡、吃饭、睡觉等这些最为日常的内容。他将日常生活纳入诗歌中,而且让其焕发出诗意。笔者认为,这有赖于他对日常具象的书写。
具象,是与抽象相对的概念。用非亚的话来说就是“具体细微的事物”,他认为“具体是事物感受的基础,它构成诗歌所需要的形象,好的诗歌基本都是这样”[3]。诗集《倒立》正是诗人日常具象书写的典型代表和现实实践。诗集按照创作年份整理而成,每两个年份为一部分,共五个部分,时间跨度整整十年。“作为一种生活的证明”[4],该诗集记录了诗人从38岁到48岁黄金阶段的思想变化和成长过程,里面包含了诗人所面对的各种重复细小的具象。具体分为日常小事和具体场所两个方面,通过诗人的书写,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下充满了诗意。
《倒立》的写作对象基本都为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日常小事,这是日常生活书写的最为重要的一部分。非亚的诗是刻意规避“有意”地抒情的,他试图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书写日常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耳目能及的具体事物,在这些看似平淡、朴素的叙事中可以窥见诗人对生活的深刻认识。比如《电灯和我》:“电灯和我/都是两个/很孤独的东西/我们/互相看着/在十月十一日的晚上/在两个粗糙的水平面/天花和地板/之间/电灯橘黄色的光线此刻无声地/落在我的身上。”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坐在电灯下这样一件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重复无数次的小事。可是诗人将这样的具象赋予全新的意义,使平常的事物变得与众不同。诗人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平常的画面,画面里就只有两点(即电灯和“我”)和两面(即天花板和地面)。这样的画面本身就给人一种空寂和孤独之感。最后,光线无声的“落在我的身上”,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电灯和“我”早已融为一体。仿佛庄周梦蝶,到最后却不知谁是蝶了。抓住瞬间感受,将日常生活的具象赋予生活的诗意并从其形象背后窥见生活本质。类似这样的诗,在诗集《倒立》中随处可见。《橙果》是午睡之后,和儿子一起切橙果、吃橙果的温馨画面,平常我们容易忽视的日常具象所存在的诗意在诗歌中得到展现;《衣服》《灰色衣服》则用最平常的生活素材入诗,思考“衣服”本身与“身体”的关系;《阳台上的风景》《桥》《洗澡》《浴室里》等诗都是以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日常细节配合客观陈述来展现日常背后的某些诗意。可见,诗人用最朴素的日常画面勾勒出每个人在生存空间都会感到的虚无感和孤独感。没有刻意地抒情,只是客观地叙事,却分明营造出日常生活的诗意,给人一种在都市生活中诗意栖息的体会。
另外,诗集的写作对象有很多具体场所的出现,是日常具象书写的另一重要部分。诗人主张“诗即万物”,这就必然涉及到“万物所在的场所”[2]171,因此在对日常生活诗意的唤醒中,也少不了对场所的关注。《倒立》中有大量具体的地点地名出现,这些都和诗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通过这些我们就可以窥见作者某些本土文化的诗意所在。比如《流失的》:“在夜晚,一个人沿着华强路走到解放路/再走到江边的民生广场”“几个抽烟的男人,蹲在中医院的门口交谈”。“华强路”“解放路”“民生广场”以及“中医院”都是南宁本地的地名,诗人通过这些具体的地点转换来暗示时间的流逝,用陈述的语气来叙述自己搓洗内裤,去饭馆吃完饭后,一个人游荡在城市夜晚的日常经历。路上的风筝、发廊里的姑娘、看单车的女人、几个抽烟的男人这些陌生人充斥在“我”的世界之外,仿佛我所流逝的一切与“他们”无关,流逝的时间只有自己知道,体现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孤独的离合感。又如《华东路的某个晚上》这个题目本身就带有南宁本土之感,除了题目中的“华东路”,诗中的“瑞康医院”也是南宁本地人所熟悉的地方,具体地名的出现给读者带来了一种亲切和真实的情感体验;《一些日子》《不协调》《生活》等诗里的“林苑宾馆”“华西路”“永和桥”“东葛路”等都是南宁本地具体的地名。“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越是具有地域文化色彩的,其散发的光芒便会长久很多。诗人将本地特色融入诗中,并在特色场所的基础上继续日常具象的书写,使其诗意打上了本地特色的烙印。
诗人非亚对日常具象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书写的笔触基本到达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非亚将日常生活的具体事物融合进独特的思考,在朴素地叙述中展现日常的某些“瞬间”,给人以思考。同时,他还关注场所问题,将本地特色带进诗歌创作中。以非亚式的感受能力,捕捉某些具象,营造出平淡的生活诗意,给久居都市的“他者”提供了某种精神的诗意慰藉和情感认同。
二、形式突破:连接日常生活诗情
值得一提的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的创作为突破口。当时胡适等先驱大胆提出“作诗如作文”、“以文入诗”等观念,倡导彻底打破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创立自由体的白话诗,即“新诗”,在形式上有了很大的突破。至此以后,“新诗”便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口语化写作、个人写作等现象。诗人非亚自然受到了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理论的影响,他认为诗歌的形式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并在文章中明确提出“诗无体”这一概念,在唤醒日常生活的诗意后,成功找到了连接诗情与日常生活的突破口。
具体来说,非亚所说的“诗无体”是指“诗歌不是文学,不是诗体文学,也不是散文体。诗无体。甚至,诗不是诗;‘诗本身’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是人,个人、人们、人类。人就是诗,此外无诗”[2]171。不难看出,“诗无体”中的“无体”是指淡化模糊对诗歌形式的刻意追求,而重视日常生活中作为人所存在的现实意义。那么,为了打通日常生活和诗情的通道,非亚认为开放的结构和形式感便是诗歌探讨的一个方面。只要能够书写现实生活的流变与诗意,诗歌的形式是可以打破其传统概念的束缚的。也只有打破了诗歌本身在形式上带有的禁锢,才能自由地表达日常生活呈现给我们的具象。非亚在形式上的自由与日常生活的随意形成对接,打通了日常生活的诗情。在“诗无体”所提供的自由空间下呈现的一种更为饱满的“形式美”,便是诗集《倒立》形式突破的独特所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诗人非亚打破了诗歌结构中的刻板印象,书写了一种全新的结构,赋予形式更为丰富的内容。比如《下午的某一时刻》:“停车场安静的汽车,阳光灿烂的/下午,紧靠一块空地的/窗户,一张桌子,几本书/一个人,那是/我/树木渴望静止,但风/一直摇晃它们的叶子,高楼围住/幽暗的心,在这一切之上/广阔的蓝色天空,除了一些云/没有任何轰鸣的飞机/我坐在桌前,继续低头/写字,阅读/吃一只苹果。”这首诗带有强烈的电影镜头转换的立体感,使其内容呈现出丰满的动感。诗人仿佛是一个导演,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从停车场的汽车,移动到空地上的桌子,一个长镜头慢慢拉进,镜头里出现一个人,镜头聚焦到点的时候发现是“我”,不免有一种无意被发现的惊讶之感。接着,镜头从导演的手里交付到“我”的眼睛,顺着我的眼睛,看到了被高楼围住的树,接着视角移动到树以上的空间,没有声音的天空便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镜头又回到导演手中,镜头中“我”在桌前,“吃一只苹果”。这本是一幅日常生活中个体被包围在其他客体的无力静止的画面,因为在“诗无体”的自由下,诗人打破了传统的格局,快速转换视觉,远近高低的景物不同层次地出现在画面里,赋予孤独不同形式的动态阐释,结构的打破便给予了“个体孤独”更多内容的可读性。日常的生活在这样结构的转换里,承载了更为饱满的内容。另外,《每天的一些记录》《身外物》等诗同样也是超越传统诗歌的构图模式,以作为建筑师的诗人视角勾勒出与众不同的视觉审美体验。这样形式的突破与建构,化解了日常生活的无聊与平淡,给形式注入更为饱满的内容,成功挖掘出其诗情。
此外,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诗人在断句和分行的自由运用上也体现出其特有的突破与创新,使形式也成为一种内容的表达。比如《最短的诗,给死亡》:“死亡就是一个沙漏/每天/一点/一/点。”非亚这首诗要表达的意思极其简单,即死亡就像沙漏一样不易捕捉且不知不觉地走进我们每个人身边。但是这首诗的形式美所赋予诗歌的另一层内容是其创新之处。我们都知道沙漏的形状是上圆下尖,“沙漏”这个词出现在前面,首先给读者投射出沙漏这个物体,亦即给读者定型死亡的形象,如沙漏一般。接着,诗人打破形式,一句“每天一点一点”被分成四行,从“一点”到“一”再到“点”,顺着往下看,一幅沙漏里的沙在纸上一点一点往下漏的画面便出现在读者眼前,仿佛电影再现一般。诗人独具匠心地借助这样的断句和分行,从形式的创新来赋予死亡抓不住,必然到来等内容,给读者带来了极大的视觉形式美和诗性的审美体验。再如《那个梦》的最后几句:“仿佛是我另一次未曾展开的/生活的/开始”。“生活的开始”被诗人分为两行,“生活的”停顿后,“开始”停留在最后一行,给人一种无限的延伸感,用这样的分行真正传达出“开始”含义,使诗人所要表达的内容更为深刻,日常生活的诗性从而被这样的“新形式”所连接。此外,《香蕉和苹果》《下午的寂静》《雨》等诗同样以断句和分行来打破其形式,日常的画面被打磨出更为多彩的内容,焕发出“非亚式”的诗情之美。
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诗是不能没有“形式”的。诗人打破传统的形式,在“诗无体”的指导下,创作出一种内容更为饱满的形式,传达出不一样的审美体验。同时,诗人在唤醒日常生活的诗意基础上,用对诗歌形式的“反叛”,打破诗情与带有世俗意味的日常生活的禁锢,在全新的视觉形式美的创新下,传达出内容的多义性,成功地展现了日常生活的诗情。日常生活在人们心中固有的概念被诗人一点点击碎,贯彻以全新的观念。
三、主题阐释:构建日常生活诗性
主题即中心思想,是通过对素材、题材的归纳、概括和抽象,以此得出来的高度浓缩的思想结晶。诗人虽然主张“万物即诗”,但同时也说“这个世界的事物之多,这必然涉及事物的选择和选择什么事物的问题”①非亚.现实的通道[EB/OL].http://blog.tianya.cn/post-123926-19587563-1.shtml.2009-10-20.。可见,选择入诗的素材和题材是影响主题阐释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诗人受个人经历、人生态度以及个性偏好的影响,对题材的选择和介入性必然就会有差异,即使是同一题材,所展现的主题也不一定一样。同理,即使是同一诗人,在不同时期,心境发生变化,其主题的阐释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主题的这种主观性就决定了主题是具有动态性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诗集的主题阐释就缺少了探讨的可能性,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诗人发生某些变化之外所保留的“不变”,更能彰显其固定主题的特殊意义,给了我们探讨的必然性。
非亚认为“从生活到诗,不是直接的照搬”②非亚.现实的通道[EB/OL].http://blog.tianya.cn/post-123926-19587563-1.shtml.2009-10-20.,在转化过程中,受个人的发现能力的制约。而笔者认为这个发现能力更多的是表现为对主题的一个发现。比如诗人认为在诗歌的转化中如何体现和反映诗歌的当代性也是诗歌表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问题,同时也是衡量诗歌是否有力量的一个标志。在进一步探讨当代性的问题时,诗人表示:“我觉得当代性的表现,除了涉及到内容(包括题目),也涉及到诗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当代性就不太可能得以展示。”③非亚.现实的通道[EB/OL].http://blog.tianya.cn/post-123926-19587563-1.shtml.2009-10-20.由上可知,在非亚看来,诗人的感知能力、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影响素材选择以及主题阐释的重要因素。受上述因素影响,诗集《倒立》中固定诗歌主题主要为死亡(具体来说有关时间和生命的思考也属于这一范畴)和自我(包括孤独、陌生等)。笔者认为,通过前面对唤醒日常生活诗意和连接日常生活诗情的分析,我们已经了解到诗人非亚对日常生活的独特感悟和塑造,在“唤醒”和“连接”的基础上,诗人通过阐释主题,成功构建了日常生活的诗性。
第一个贯穿诗集的主题便是“死亡”。诗人自身对时间和生命的关照,是这一主题呈现的最为根源性的原因。此外,2001年诗人的父亲病危、死亡,这样一种失去至亲的打击,加深了非亚对死亡的思考。在诗集中有关“死亡”主题的诗歌多达40多首,是我们分析其对日常生活的诗性建构绕不开的话题。从2003年到2012年,诗人对死亡的态度有某些细微的变化。比如写于2004年的《死》:“死就像一杯/喝了很多年的/白开水/在煤气炉上/死就像烧了很久/准备发出鸣叫/在弯曲的/气嘴/喷出白色蒸汽的/铝制/水壶。”诗人将“死”比作“喝了很多年的白开水”,暗示死亡看似平淡却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接着,诗人又将“死”比作“铝制水壶”,而且是“烧了很久”“准备发出鸣叫”的水壶。这两个比喻都暗示“死”无处不在,我们要保持一种警惕的心态,从侧面也透露出诗人对“死”的一种焦虑和些许害怕的心理状态。而写于2008年的《死亡就像一只蝴蝶》则给人一种轻松乐观的心理感受。诗人塑造了一个穿着“花衣”的“死亡”形象,并将“死亡”比作“蝴蝶”。在一首不足90字的诗里两次赞叹“死亡”“真美丽啊”。一种对死亡的豁达开朗的状态跃然纸上。“老头”“青年”“妇女”“儿童”“警察”都跑过大街去看像蝴蝶一样的死亡,将“死亡”平民化,消除了其陌生感和神秘感,给读者传达了诗人对“死亡”一种坦然接受的心态。通过两首诗歌的对比,我们不难看出,随着阅历的增长,非亚对死亡主题的不同阐释,后者比前者更为积极。诗集中还有诸如《给爸爸,也给妈妈》《死亡》《有一天》等诗歌也是对“死亡”的思考。不管是积极的还是略显消极的,死亡主题的一路贯穿都体现了诗人对生命的肯定,以及“认识到生命的局限,重新赋予自己生活的力量、勇气和生活下去的信心”[1]45。比较2008年以后的有关诗歌,也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非亚面对死亡的姿态越来越坦然。此外,《消耗》《我的抽屉》《一块手表》《除夕之夜》等诗都是涉及对时间流逝与追忆的感慨,同样从侧面反映“死亡”主题。
非亚诗集《倒立》探讨的另一主题便是对“自我”的阐释,相关的诗歌达30多首。这一主题凸显了作为个体的主体性,以达到剖析自己认识自己并由此思考我与“他者”关系的目的。诗集的第一篇诗《我喜欢的形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我喜欢的形象是光头/胡须浓密下巴/用须刀剃出山羊胡子/头发要么很长要么中间/极短,两边剃得/精光,打上啫喱水/让它们爆炸/戴耳环,或高挺的鼻子别一枚/晃动的银质金属/穿皮衣,T恤,黑色/圆领衫/手臂文上蝎子/和毒蛇的形象。”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完全叛逆的形象。首先进入读者的“光头”便可看做是“我”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行为主义的反抗,后面对“胡子”“耳环”“皮衣”“手臂”等的具体描写都是诗人的理想形象的一个刻画。这与《离骚》中屈原穿着奇装异服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用这样的一种放荡不羁的外在形象来挑战固有的生活,是一个反叛者的形象,是非亚对内心深处自我的一种释放,亦如梵高的自画像,透过这样的一个形象可以窥见自己内心更为隐秘的东西。再如《交谈者》融入现代科技对人的现实生活的影响,体现了“绝对的交流,绝对的孤独”这一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我意识深处的酒鬼生活》刻画了一个摆脱世俗束缚,去见想见的人,醉了可以放肆地发泄,不用管什么红绿灯,可以“乱喊乱叫”,做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酒鬼”,体现了平常的主体失落只有在非正常状态下才能找回的现代生存困境。此外,《上午的一幕》《简历》《我》《自闭》等诗都不同程度地回归到自我的维度,体现现代人所面临的孤独和异化之感。
诗集《倒立》在其“死亡”与“自我”的主题阐释中,呈现出对现实生活的深刻关照,将焦点透视到个体,揭示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诗人非亚凭借对日常生活的独特观察,在“唤醒”和“连接”的基础上,通过主题阐释,成功构建了日常生活的诗性。
总之,诗人打破日常生活固有的局限,通过唤醒日常生活的诗意,继而连接上日常生活的诗情,成功建构了日常生活语境下的诗性,为现在较流行的“日常主义诗歌”提供了借鉴的可能。但是,在日常生活语境下创作诗歌,其题材所能承受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厚度必然受到限制。诗人非亚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在2013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表示会将笔触延伸到更为广阔的领域,增加诗歌“当下性”和“现实感”结合的力度,我们有理由期待诗人的下一阶段的创作。
[参考文献]
[1]钟世华,非亚.关注人的灵魂与生命状态——广西诗人非亚访谈录[J].河池学院学报,2013,34(4).
[2]罗池,非亚.我们诗歌的基本原理[J].诗探索,2011(2).
[3]非亚.倒立·代序[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1.
[4]非亚.倒立·后记[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332.
(责任编辑:雷文彪)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126(2016)03-0009-05
[收稿日期]2016-04-15
[作者简介]李及婷(1992—),女,四川达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Poetic Construction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Context: on Fei Ya’s Anthology Inverted
LI Jiting
(College of Arts,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Nanning,Guangxi 53000 China)
Abstract:Inverted is the second collection of poems published by Fei Ya.In this collection of poems,the poet has unique understanding attitudes towards daily life.He ueses his daily figurative writing and unique form of innovation to reflect real life,which forms a specif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me.Poet deconstructs the“boring”,“meaningless”and other stereotypes of daily life,constructs the poetic feature of everyday life,which makes the poetry anthology Inverted be a kind of unique artistic appeal.
Key words:Fei Ya;everyday life;Inverted;poetic constr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