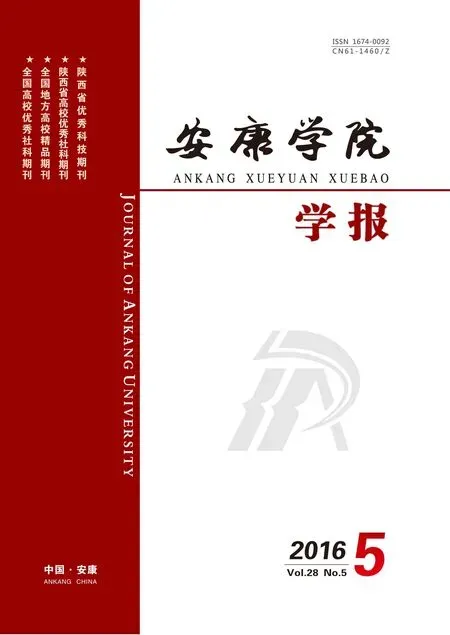《物不迁论》的思维方式探微
张彤磊
(湖南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物不迁论》的思维方式探微
张彤磊
(湖南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物不迁论》以“迁”与“不迁”关系为轴心,以“不迁”否定“迁”立论,旨在否定“迁”的主体自性。本论侧重破现象之自性,通过剖析动静矛盾,重点对治世人迷惑于假象而以诸法万象为动以及执著于动静的二分观念,阐明大乘空宗中观学派诸法不生不灭之义。
僧肇;《物不迁论》;思维方式
《物不迁论》以动静关系为切入点,阐明大乘空宗中观学性空思想,是东晋著名佛教理论家僧肇的一篇经典哲学论文。本论思想晦涩,历来注家对本论的理解歧义颇多。就动静关系而言,或以现象为动,或以本质为静。本文认为,作为“秦人解空第一”人,僧肇应该是准确把握般若空义,即空是毕竟空,只能直观而非能用任何语言思维所描述。如果以“静”来指征、描述空,都面临“静”成为空的一种属性的问题,那么这个能被描述的空就不是空,是有;其次,如果以“静”来指征、描述空,那么空就成为一种肯定式的表述,这也违背了中观学坚决贯彻的彻底否定式表达方式。本文以“迁”与“不迁”的关系为轴心讨论《物不迁论》的主旨,以求方家匡正。
一、“迁”与“不迁”的时空关系
“物不迁”之语源出《庄子·德充符》,“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1]144-145。庄子“不与物迁”之本意在阐明心不为物所扰,任物自迁之德性。所谓“迁”即流转变化,“不迁”即非流转变化。在《物不迁论》中,僧肇讨论的“迁”有两种含义:
第一种含义是指实体在空间上前后位置的转移,如事物由此至彼,在空间位置发生变化的同时,此物与之相依存之物的存在关系发生变化也即参照系的变化,此即为狭义的“迁”——运动,与之相反即静止。此论的前提是物体是有自性的,有自性才能占有空间,如康德所言:“吾人固能思维空间为空无对象,然绝不能想象空间之不存在。故必须视空间为‘所以使现象可能’之条件,而不视之为“依存于现象”之规定”[2]。而且,单纯从空间和位置而言,事物可作往复运动而不变(存在状态),由此及彼再由彼及此。我们通常也以此物在空间和位置上前后序列的变化来度量时间,也就是把时间空间化。但是一旦附着时间观念,时间的不可逆性也就附着于物体在空间上前后位置序列,所以可以由古至于今,但不能由今至古。
第二种含义是指在相对不变的空间位置中事物在时间坐标系内的自身存在状态的无时不刻的变化,无论有机物的新陈代谢还是无机物的组织结构,都处在这种永不停止的瞬时变化中。在这种瞬时变化中,事物相对自身的空间位置发生着瞬时的变化,但通常我们需要在较长时间段内才能观察到此物的变化而以其为不变,如日月穿梭、春秋交替。而且,事物这种在空间位置的瞬时变化让其根本无法在时空坐标系下找到相应的坐标点,我们只能以概念的逻辑规定“不迁”指征这处在时间点上不断的瞬间变化。
在《物不迁论》中,僧肇的“迁”是时空关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广义上看(绝对变化),经验世界之事物同时处在自身不断变化与空间位置变化之中;从狭义上讲(相对静止),并非所有的物体时刻都处在位置的运动中。但是,正如任继愈指出:“古人虽然对事物发展、变化、运动往往有很精辟的见解,但古人讲到变与不变、运动和静止,经常用‘静’和‘动’来表达;至于发展的观点,就更不明确了”[3]。《物不迁论》中的“静”和“动”除了空间位置的运动与静止之外,更侧重第二层含义的“迁”——发展变化,而且和其时空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物不迁论》中的“迁”的这两重含义造成历来注家对《物不迁论》的理解歧义颇多。
二、“迁”与“不迁”关系立意
《物不迁论》开篇即言:“夫生死交谢,寒暑迭迁,有物流动,人之常情。余则谓之不然。”[4]142僧肇在本论中大量描述了常人以常识观察世间万象,无论“生死交谢,寒暑迭迁”“四象风驰、璇玑电卷”“江河竞注、野马飘鼓”,还是“庄生之所以藏山,仲尼之所以临川”“梵志出家,白首而归”[4]142-143,莫不处于流转变迁之中。然而,对于这种事实的经验现象,僧肇却说“余则谓之不然”,认为“物不迁”。佛陀以依缘起法立诸法无常之法印,缘起之物因恒常流转变化而无自性,僧肇何以作出了貌似有违诸法无常的结论?
僧肇对“迁”的否定——“不迁”立意在何?①对于学术界动静关系讨论《物不迁论》的思想,以现象为动,以本质为静的观点,吕澂指出:“僧肇之所谓不迁,并非是主张常来反对无常,而是‘动静未尝异’的意思,决不能片面地去理解”(参阅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3页)。汤用彤认为“全论(指《物不迁论》)在证明动静一如,住即不住。非谓由一不动之本体,而生各色变动之现象。盖本体与万象不可截分……称为《物不迁》者,似乎是专言静。但所谓不迁者,乃言动静一如之本体。绝对之本体,亦可谓超乎言象之动静之上,亦即谓法身不坏”(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不迁”是不是否定缘起之物的流转变化?如果僧肇否定缘起之物的流转变化,那么是否意谓缘起之物的本质是非流转变化的?如果这样,僧肇岂非肯定了缘起之物非流转变化的本质,也就即肯定了缘起之物是有自性?以“秦人解空第一”的僧肇对般若空义的造诣,应该断然不会下如此结论。
那么僧肇“物不迁”的立意是什么?作为罗什门下高足,僧肇是深谙般若空义,精通《中论》论法。罗什译《中论》以“生灭”为核心范畴论证“八不中道”,是通过对“生”的否定来论证“不生”,因为“不生”故“不灭”,以证万法“不生不灭”。如果循此思路,僧肇对“迁”的否定来论证“不迁”,有“迁”就有生灭,“不迁”故无生灭,“不迁”与“不生不灭”同义,故僧肇说:“不灭不来,则不迁之致明矣”[4]141。据此而言,僧肇对“迁”的否定旨在说明缘起之物的本质是无自性,有自性所以才有流转变化,无自性就不存在流转变化。也就是说,一个非实存、相依待、无本质的缘起之物怎么能说它自身是在流转变化的呢?可见,与龙树否定视作实体性的“生”一样,僧肇也是反对经验世界缘起之物的实体性,也即否认缘起之物之自性。
但是常人常识之“迁”的表象是事实存在的,如何面对“迁”与“不迁”的矛盾呢?或者说僧肇揭示“迁”与“不迁”矛盾的目的是什么?僧肇说:
夫谈真则逆俗,顺俗则违真。违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谈而无味。[4]142
谈真有不迁之称,导俗有流动之说。虽复千途异唱,会归同致矣。[4]143
僧肇认为,从真谛言诸法“不迁”,诸法“不生不灭”亦没有变化;从俗谛言“迁”,是为了引导世俗的人理解。虽有真俗二谛之别,实则殊途而同归,真俗二谛不即不离。在《注维摩诘经》中,僧肇进一步指出:
小乘观法生灭为无常义,大乘观法以不生不灭为无常义。[5]354上
僧肇指出,小乘观法是以经验世界中的生灭变化为无常,而大乘观法是以不生不灭为无常。对于“迁”与“不迁”而言,俗谛以“迁”为无常,而真谛是以“不迁”为无常。也就是世俗之人所见经验现象之流转变化即为圣人所见之“不迁”,从这个意义上讲,“迁”即是“不迁”,“无常”即是“常”。此义正如吕澂所言:
《物不迁论》,从题名看,似乎是反对佛家主张“无常”的说法,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之所谓“不迁”,乃是针对小乘执著“无常”的人而说的……依佛家“无常”说,应该讲迁,现在反讲不迁,正是针对声闻缘觉执著无常不懂得真正意义者而言……僧肇之所谓不迁,并非主张常来反对无常,而是“动静未尝异”的意思,绝不能片面地去理解。①参阅吕澂《中国佛教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3页。方立天也认为《物不迁论》是“运用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中观学说反对小乘佛教偏重无常的倾向”(参阅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5页)。
所以,《物不迁论》“不迁”旨在说明缘起之世间万象本质是无自性,故“不生不灭”,亦“不迁”,无常;而世俗之人执著于经验现象之流转变化而以之为常而不见无常。僧肇以中观学派真俗二谛相即义来统一“迁”与“不迁”的矛盾,真俗二谛不即不离,“迁”与“不迁”也不即不离,只是俗谛所表达的是对现象的认识而非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三、认识“物不迁”的方法
虽然僧肇指出否定世间万象之流转变化是为了世间阐明万象不生不灭,本质是空、无自性,但如何透过流转变化的现象来把握世间万象的本质——“物不迁”呢?《物不迁论》说:
《放光》云:法无去来,无动转者,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以于诸动。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故虽静而不离动。然则动静未始异,而惑者不同。[4]142
《放光般若经》说,事物不生不灭,没有变化。但佛经所谓不变,并不是教人离开了变化而寻求不变,而是在变化中认识不变。事物虽然变化但本质无自性,不生不灭。站在事物本质不生不灭的高度来看事物的变与不变,那么变化和不变本来没有区别,惑者才以之有别。僧肇指出世俗之人执着于动静、去留二元两分的认识方法,割裂了动静关系而不见诸法实相。僧肇通过揭示事物变化中的动静辩证关系为核心,运用双遮双遣的方法,认为应该以动静相即来认识诸法本质与现象不即不离。
(一)动而非静,静而非动
《物不迁论》说:
夫人之所谓动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动而非静;我之所谓静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静而非动。动而非静,以其不来;静而非动,以其不去。[4]142
首先,从空间向度看,“昔物不至今”,即过去存在的事物现在不存在了,所以,事物是变化的而非静止的。这就是常识所见“动而非静”。这种变化是我们通过对一事物在空间位置上不可逆的前后序列存在状态的比较而来,同时也隐含着事物变化的过程中我们体验到时间真实流淌的存在,而这不可逆的前后序列存在状态的变化本质上是一事物占据空间和位置的变化。比如一个事物存在,它有它的位置和空间,一个事物消逝,它不再占据它曾经的位置和空间;或一个事物运动或属性如大小的变化也就是它占据位置和空间的变化;或者一事物自身性质在变化而我们感知不到其变化,但这种变化总是要变现出来,仍然在空间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常识是以空间的变化来度量“迁”与“不迁”的。这种事物在空间变化的前提是事物是有自性的,所以能够占据空间和位置。一切有为法皆依赖空间而变现。正如康德所表达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事物的纯粹空间,但绝对不能想象一个不占有空间的事物。
但是,僧肇认为,从时间向度看,“昔物不至今”也可以推出如下结论:
既知往物而不来,而谓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不来,今物何所往?何则?求向物于向,于向未尝无;责向物于今,于今未尝有。于今未尝有,以明物不来;于向未尝无,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4]142
既然“昔物不至今”,那就说明过去存在的事物只是过去存在;在现在不存在过去的事物,所以过去的事物并没有延续到现在;以此类推,现在的事物只存在于现在,不会延续到将来。这样,过去的事物、现在的事物以及将来的事物都是完全独立而又不相关联的个体。换言之,如果事物可以自由穿梭于时间洪流之中,今古就无悬隔,过去的事物可以来到现在,现在的事物可以返回过去,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僧肇说:
是谓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以至今。[4]142
既然事物今昔彼此不能往来,哪里还有运动呢?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是僧肇在时空坐标系上完全剥离了事物的空间性,也就是把时间“空”了,把占据空间的事物的自性空掉了,时间的流动只是一个无任何内容的纯形式的变化,时间流动中不带有任何事物。在每一个时间坐标点下,僧肇把事物存在状态的变化无数分解放在对应的无数个瞬时时间点上,不同的瞬时时间点上对应此事物不同的存在状态,并且每一个瞬时时间点与此时间点前后事物存在状态是没有任何由此及彼的联系。这样,僧肇就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如果把时间比作电影的胶带,胶带快速移动的时候,这些画面依次瞬息生灭。这就是人们所看到的运动变化的假象。而每一张胶带就是一个瞬间,这些瞬间相互之间不能往来移动,就如同古今各住一世一样,这就是静止”[6]。
僧肇所要表达的是,我们从现象中看到事物由此及彼貌似有空间和位置的变化,貌似“迁”;实际上,每个瞬时时间点上的事物是不同地定格在特定的空间里,根本没有空间和位置的变化。换言之,我们看到的事物的“迁”只是一种假象,事物根本没有保持自性在空间和位置上变化,这就是“静而非动”。
(二)即动即静
“静而非动”是通过对常识所见从事物空间位置变化来而作出“动而非静”地批判而得出的结论。但是,“静而非动”仍有问题,那就是定格、静止在特定时间点上的事物仍然占据则空间,仍然有自性。僧肇认为这个“静”非静,每个瞬时时间点事物的存在状态仍然处在永不停息的变化之中:
故仲尼曰:回也见新,交臂之故。[4]142
“回也见新,交臂非固”出自《庄子·田子方》:“丘以是日徂。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与?”[1]535意指事物无时不刻地发生变化。《注维摩诘经》又言:
新新生灭,交臂已谢,岂待白首,然后为变乎?[5]361中
诸法如电,新新不停。一起一灭,不相待也。弹指顷有六十念过,诸法乃无一念顷住,况欲究停。无往则如幻,如幻则不实,不实则为空,空则常净。[5]356中
僧肇是讲,貌似静止的每一时空坐标点上的事物的存在状态随时发生变化,此起彼伏,念念不住,我们根本找不到与这种有而还无,才生即灭的瞬间变化相应的对应物。如“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邻人以为过去的梵志还是那个梵志,僧肇却说现在的梵志已经不是过去的梵志,梵志时时刻刻在变,事物根本不具内在的质的稳定性!事物本质是缘起性空,无自性。正因为事物在刹那之间变幻无常,生即灭,灭即生,亦生亦灭,即生即灭,也就更无法在时空坐标下找到与之相应的对应物。所以僧肇说:
是以言常而不住,称去而不迁。不迁,故虽往而常静;不住,故虽静而常往。虽静而常住,故往而弗迁;虽往而常静,故静而弗留。[4]142
到这里,僧肇的即动即静的观点才真正表达出来:缘起之物的无自性决定了其在时空坐标点下的刹那生灭,既是动又是静,既非动又非静,动静皆无自性。因此,缘起之物在每个瞬时空坐标点上,因不生不灭,时间在此永恒;因不依赖任何事物,属不生不灭的无为法,空间在此无限。
[1]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52.
[3]任继愈.关于《物不迁论》——一篇形而上学的佛学论文[M]//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61.
[4]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G].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僧肇.注维摩诘经·卷3[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8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6]洪修平.论僧肇哲学[M]//中国佛教学术论典:第19册.台北: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
【责任编校龙霞】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ings are not moving on
ZHANG Tonglei
(Institute ofMarxism,Hunan University ofArtsand Science,Changde 415000,Hunan,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move”and“not moving”is the key problem of the Things are not moving on.This paper attempts the phenomenon no subje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ynamic and static conflict,the key to rule the world confused in illusion and to all themethod for the dynamic and clings to the dichotomy ofdynamic and static concept.
Sengzhao;Thingsarenotmoving on;methodoiogy
B948
A
1674-0092(2016)05-0017-04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5.004
2016-02-22
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中国佛教辩证思维研究——以汉译《中论》 《肇论》为中心”(13C640);湖南文理学院博士启动项目“中国佛教辩证思维研究”(15BSQD12);湖南文理学院校级一般项目“中国佛教辩证思维研究”(14YB13);湖南文理学院思政重点项目“宗教传播多元化背景下高校文化安全研究”(SSZD 1103)
张彤磊,男,湖北黄石人,湖南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宗教学博士,主要从事佛教、中国思想史研究。
——从体、相、用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