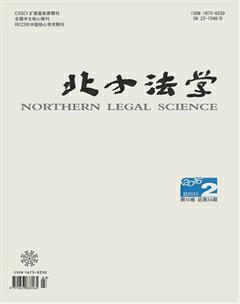“制度性保障”宪法理论的流变及现代价值
那艳华
摘 要:“制度性保障”理论为德国宪法学上的通说,其涵摄的宪法学思想对德国基本法产生深远的影响,经历了从传统制度性保障到“作为制度的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并推动了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产生。制度性保障理论展现了国家宪法学说及宪法实效性的发展为一个渐次的法治进化过程。既为法治后发国家推进宪法实施提供文本规范的解释路径,又为其展现宏观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制度性保障 基本权利 客观价值秩序 国家的保护义务
中图分类号:D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2-0135-10
“制度性保障”理论在德国的系统化与发展,与德国19世纪的制宪史、形式法治国学说、法律实证主义及其影响下的“立法者主权”理论有着深厚的渊源,其流变映射了德国社会政治经济及法学理论的发展与变迁。近年来,“制度性保障”理论在中国的宪法学研究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①但有关研究缺乏针对该理论的系统性梳理与探源,对我国宪法理论及宪法实效性的价值也缺乏深入的考察。本文旨在对该学说的发展演变做系统的梳理分析,阐述其对国家法治发展的意义。
一、魏玛宪法时期:制度性保障理论的起源
德国立宪可溯至19世纪早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立宪目标“不是反立法;而首先是反封建”。 ②“宪法不是‘超越法律之上的规范。无论在法理资格方面还是在程序法方面,它都不拥有特别的优越地位”。 ③在此背景下,形式法治国和法律实证主义理念产生,二者互为促进,将“法律视为纯粹的‘工具,重视的是实证法律所发挥的规范国家生活秩序的功能,不强调法律的‘内容,而是强调法律的‘形式”。 ④在实践中,宪法并非法律的上位概念,不具实效性,对法律不具拘束力。基于此,魏玛宪法时代盛行“立法者主权(Souvernitt Gesetzgebers)”理念,即“立法者是最权威的宪法诠释者,其制定的法律可以更改宪法的规定。立法权原则上是无所限制的,并无所谓立法者的义务存在”。前引④,第196—198页。 即立法者原则上是自由的,其立法内容并不受宪法文本规范的制约。由此,《魏玛宪法》缺乏以宪法和法律相区别为基础的宪法学说理论作为支撑,只是“形式上”的宪法,并不具有效力上的最高性,并非是法律的法律。因此,“宪法破坏在魏玛宪法时期的国家实践中与占主流的宪法学说中都是被允许的”。[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27页。
(一)制度性保障理论的提出
缺少宪法学说理论支撑及实效性的宪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宪法。与《魏玛宪法》受到的诸多捧誉相反,卡尔·施米特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魏玛宪法本身包含自己推翻自己的合宪成分”,刘小枫:《现代人及其敌人:公法学家施米特引论》,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 其实效性大为欠缺,尤以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第二章为显例,基本权利条款面临着被立法者以法律的方式架空,丧失宪法上之意义的风险。原因在于“自从传统的自然法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规定国家的法规体系已经没有‘终极正当性的基础”。[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文本前言第3页。 由此,需要另立“宪法学说”。参见前引⑧,中文本前言第5页。 因为“欧洲国家的历史有订立契约的经验,但绝无民主‘立宪的经验,虽然有了宪法,但还没有宪法‘学”,前引⑦,第20页。 还没有搞清楚何为宪法及其作用与本质。
鉴于国家有宪法,但无法达至其目标的现实,卡尔·施密特1928年出版了《宪法学说》一书并提出“绝对的宪法概念”,卡尔·施米特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西方的政治和法学思想,是20世纪最具学术创造力和思想辐射力的学者之一,也是该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宪法学说》是施米特一生中撰写的最具学术分量、篇幅也最大的论著,以解释魏玛宪法为基调,深入讨论了民主宪法这一现代国家立身之本的各种基本问题,被学界公认为宪法学史上的重要论著。参见前引⑦,第19页;[美]乔治·施瓦布:《例外的挑战——卡尔·施米特的政治思想导论(1921—1936)》,李培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总序第3页。 或曰“实证宪法”参见[加]大卫·戴岑豪斯:《合法性与正当性——魏玛时代的施米特、凯尔森与海勒》,刘毅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0—62页;前引⑦,第246页。 的概念,并试图建立一个体系。施米特认为,“每一部宪法都包含不能被简单多数或特定多数废除的基本核心,他举出神圣不可侵犯的各种制度”。前引B11乔治·施瓦布书,第107页。 被其指涉为应该由宪法予以保障的、不得由法律加以侵犯的制度性保障的实例有:《魏玛宪法》第103条关于职业公务员队伍保障机制的规定;第105条关于禁止设置例外法院的规定;第119条关于婚姻是家庭生活的基础的规定;第127条关于地区自主管理制度的规定;第139条关于星期日为休息日的规定;第142条对科学研究自由的宪法律保障等等。参见前引⑧,第182—184页。 他指出:“应当将制度保障与基本权利区别开来”,“(制度性)保障的结构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法律上都完全不同于基本权利的结构。……它仅仅存在于国家之内,并非建基于原则上不受限制的自由领域的观念之上,而是涉及一种受到法律承认的制度”。“透过宪法法规,可以为某些特定的制度提供一种特殊保护。宪法律的目标就是防止用普通立法来实施一项废止行为”。前引⑧,第182页。 这就是原初意义上的制度性保障。
(二)早期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内涵
鉴于制度性保障在宪法学说史上的地位,有两个层面的内涵需要澄清:一是该理论的提出是否为保障基本权利;二是该理论在宪法学说上的价值。
1.对具体制度内容的保障
制度性保障中的“制度”仅仅涵摄于国家之内,而“非存在于国家之前或国家之上,也并不一定指涉基本权利,虽然有些制度的保障会涉及主体权利,但主体权利与诉讼途径的保留并非制度性保障的本质”。参见前引⑧,第182—184页。 德国学者认为,早期“制度保障所称的‘制度,指的是规范具有制度特征之特定基本权所保障社会生活事实之法规范总和,而制度保障指的是保障这些制度中具典型特点的传统核心原则,免于遭受立法者的侵犯。此时的制度保障所保障的只是一种现状的担保而已,并未课予国家积极创设理想制度的义务”。参见Carl Schmitt, Verfassungsrechtliche Aufs tze aus den Jahren 1924—1954,2.Aufl. 1973,S.140ff.,181ff.转引自许宗力:《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04页注释B16。 此时的制度性保障指涉的是被《魏玛宪法》肯认的诸如婚姻与家庭、财产权与继承权、地方自治及专职公务员制等传统制度,并未要求国家积极创设其他制度,只是“意味着有一些私法上或公法上的制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根据传统,这种制度已经存在很久,有其特殊的存在意义,立法者便不能将此制度完全废止,或对其重要核心内容加以改变”。具体参见许育典:《宪法》,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15、117页;李建良:《“制度性保障理论”探源——寻索卡尔.史密特学说的大义与微言》,载吴公大法官荣退论文集编辑委员会:《公法学与政治理论》,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22页;许育典:《从权利救济宪法保障论公益诉讼制度》,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1年春季卷,第70页注释;许志雄:《制度性保障》,载《月旦法学教室(3)(公法学篇)》,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78页;法治斌、董保城:《宪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428页注16。 即早期的“制度性保障是对制度内容的保障,受益的可能只是制度本身。因为其目的是在保障这些制度本身,并非是在保障这些制度的使用人(个别的自然人)”。前引B18许育典书,第116页。 例如,就公务员制度而言,是公务员“制度”本身得到保障,并非每个公务员的各项权力得到保障,即“只有前者得到保障,后者是得不到保障的。个人只有在他从属于一个具体的秩序时才拥有各项权力”。前引B11乔治·施瓦布书,第108页。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许志雄在《制度性保障》一文中对原初意义上的制度性保障做了全面总结。他认为,消极性制度保障的内涵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制度性保障之目的在于保障特定的法律制度,而非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且该制度为现行宪法制定之前即已存在。2.制度性保障的前提要件是相关法律制度必须有宪法连接点。3.制度性保障的内容是立法者不能对已经纳入宪法范畴的法律制度之典型特征加以侵害,亦即制度性保障的范围仅限于保障既存法律制度的核心、本质部分”。前引B18许志雄书,第78页。 因此,此时的制度性保障并不直接指涉基本权利,由于此等“制度”具有宪法位阶,立法者不得侵犯该制度的核心性原则,客观上起到了对某些基本权利予以保障的效果。
2.以实证宪法为基础实现国家治理的法制化
制度性保障理论的提出以反思“立法主权主义”为背景,对宪法学进行体系性思考,探索何为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并以实证宪法为基础实现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其意旨在于消除对“‘实证主义的一种特定理解,将宪法理论的根本问题排挤出国家法,使之进入普通国家学的疆域”前引⑧,序言第2页。 的影响,防止立法权的无限扩张,借助“法律就是法律”的“实证主义”进行“违宪”但却具有“合法性”的统治,为其“违宪”的侵权行为创造“合法性”、“正当性”依据。宪法与法律应有严格的界分,即“如果要让‘法律的统治与法治国概念保持关系,就有必要给法律的概念注入一些特定的品质,以便将一项法规范与随心所欲的命令或措施区别开来”,前引⑧,第151页。 深意在于宪法要具有实效性,具体通过“制度性”思维路径予以践行。
其一,以传统“制度”存在为基础,认为每种制度本身为一种正当性的秩序,每种秩序在一个强势国家的范围内拥有其自身的合法存在。通过每一具体制度本身所保障秩序的实现,建立国家法律与秩序。参见前引B11乔治·施瓦布书,第107页。 即每一具体的制度都为一种具体的生活秩序,制度蕴涵独立的“法的实质”。国家是诸“制度”的“制度”,其他为数众多的制度都在该制度的秩序中寻得保障及秩序。 这是一种“制度性思维”。参见[德]卡尔·施密特:《论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苏慧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0、100—107页。 比如在婚姻家庭制度上,立法者要接受“‘家庭这个具体制度的具体秩序观,而不是抽象地提列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而如果要接受家庭制度,就必须接受其中所蕴含的‘良善家父的概念,否则就意味着扬弃家庭制度”。前引B25,第20页。
其二,制度性保障理论的提出与施米特指称的制度的“独立性”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他认为在魏玛宪法时期的“国家生活中应该要有多少‘独立性存在,以及为什么要不断将新制度从政党政治之运作和多元体系中抽离出来的原因还没有体系上的清楚而明确的答案”,[德]卡尔·施米特:《宪法的守护者》,李君韬、苏慧婕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08页。 但无疑将一些制度独立出来对国家民主政治生活是极其重要的。比如《魏玛宪法》第142条“讲学自由”——受宪法保障之大学教师的独立性与自由,作为制度性保障之一的文官制度中的专业法官的独立性等等。这些形态各异的“独立性”类型不仅可以免于政治意志形成的侵害,还可以反过来确保其对于政治意志之确定或影响力的独立积极参与。这些“独立性”与政治统一体的整体概念紧密相扣。参见前引B27,第208—214页。 这些制度都是宪法层面的制度,是政治国家的重要制度或者说是可以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统一”的制度,每一制度本身都具有其独立性的特征,都应根据其自身的传统情况做具体的、单一的理解,每种制度都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
其三,制度性保障理论强调的制度核心不可侵犯原则是对国家立法权的有效规制,目的是通过“立法者不得打破现行法秩序——这一特殊的保护机制来防止立法权的滥用,确保权力的区分,维护法治国的法律概念”。参见前引⑧,第191页。 “这一针对魏玛宪法的功能主义所做的斗争,被后来的《德国基本法》所采纳,在该法中明确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组成部分,并限制了议会多数的修宪权”。参见前引B11乔治·施瓦布书,第188页。 《德国基本法》通过第19条“基本权利之实质内容绝不能受侵害”及第79条的规定成功限制了国家立法权,并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
二、基本法时期: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发展
二战后,德国法学界对法律实证主义予以批判,指出“实证法想要在不考虑其正义性与合目的性的情况下具有有效性”。[德]G·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而“正义性”与“合目的性”才是法律之根本,否则就背离了人类制定法律的基本价值诉求。基于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反思,自然法思想回归法学者的视域,认为权利是一种普适的、更高的客观准则,立法权并非绝对,必须服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至此,实质法治国思想生成并居主导地位,“宪法最高性原则”为其核心内涵之一。《德国基本法》由此诞生。
(一)《德国基本法》对于“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吸收
基本法确立了宪法在法秩序中的绝对地位及基本权利的直接效力。原初意义上的制度性保障理论与基本法相结合而进一步发展,“一种从传统制度性保障理论中发展而来的新理论,即所谓的‘作为制度的基本权利理论或称‘制度性自由理论已广泛得到宪法学界及宪法判例的认同”。参见[日]芦部信喜:《宪法》(2),(日本)有斐阁1994年版,第89页。转引自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注释18。
基本法设计了开放的“基本权利”体系,将某些制度纳入基本权利范畴。基本权利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其一,《德国基本法》第一部分(第1至19条)所涵摄的基本权利内容,即作为基本法第93条第1项第4句a之前提而存在的基本权,是作为基本法之基础的基本权利。其二,从实证宪法的角度而言,除第一篇内容之外,基本法另外规定的一些权利,就权利特性而言与那些被明确表述为基本权利的权利并无区别。如第33条第1至3项、第38条第1项、第101条第1项、第103、104条规定的权利都被理解为基本权。第1条第3项与第19条第3项对这些权利同样适用。前引⑥,第223—226页。 其三,将一些制度界定为基本权利的位阶,或是对某些宪法文本规定做基本权利与法律制度的双重理解。即如德国学者康拉德·黑塞所言:“基本权利不仅是个人性的主观权利,它还能够保障某项法律制度或某一生活领域的自由(如基本法第6条第1项、第14条第1项、第5条第3项)。基本权同时也是共同体客观秩序的基本要素。有些并非主要包含个人权利或根本不属于保障个人权利的条款(如基本法第7条第1项,第3项第1、2句,第5项)也被收入了宪法基本权序列。”前引⑥,第226—227页。《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1项规定婚姻与家庭、第14条第1项规定财产与继承权、第5条第3项规定艺术与学术,这分别为婚姻家庭制度、财产与继承制度、大学自治制度的规定。第7条第1项整个教育制度应受国家之监督,第3项第1、2句宗教教育为公立学校课程之一部分,惟无宗教信仰之学校不在此限,第5项关于私立学校设立的规定。
可见,基本法将某些法律制度列为宪法位阶,做包含法律制度和基本权利的双重理解,将该宪法条款既理解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又理解为保障该基本权利实现的法律制度,制度为保障基本权利而存在,具有基本权利的效力。例如在汉堡洪水控制案中,1964年,汉堡州通过了“排水堤防法”,把州内所有被归为堤坝区域内的草地征用为公共财产,并对草地的私人所有者给予经济补偿。几个在堤坝区域内的地产拥有者在宪政法院挑战这项法律,宣称它侵犯《基本法》第14条授予他们的基本权利。 宪政法院第一庭认为:“《德国基本法》第14(1)条把财产同时保障为法律制度和个人所有者的具体权利。财产之所有,乃是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它和个人自由的保护紧密相关。在宪法权利的普遍体系内,财产的职能是保证所有者在经济领域中的自由层面,从而使之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作为法律制度的保护,财产为这项基本权利而服务。这项宪法个人权利的条件基于‘财产的法律机制,制度保障禁止对私法秩序做出任意修正”。张千帆:《宪法经典判例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页。 同样,这些制度也为国家的社会生活秩序原则,法律不得任意侵犯。参见关于“单身条款案”的判决。该案的原告是一位年轻女性,自1954年4月1日起在一家州立疗养院当护士。根据北威州(Nordrhein-Westfalen)社会部1950年3月1日公布的IB1b号规定,女性护士在合同期内不得结婚,如果在职期间结婚,疗养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该女性与疗养院之间的合同也据此订立,约定如该女性在此期间结婚,则疗养院可以解除合同1955年8月25日,该女性结婚。8月31日,疗养院解除其与原告的合同。原告认为,合同期内不能结婚的约定是违法的,于是提起诉讼。联邦劳动法院于1957年5月10日认定:“此项单身条款的无效,是因为其违反了《德国基本法》第6条第1款(婚姻与家庭的保护)、第1条(人格尊严)和第2条(人格自由发展)的规定。《德国基本法》上若干重要的基本权利不仅在于保障个人自由以对抗国家权力,而且也是国民社会生活的秩序原则(Ordnungsgrundstze),对于私法上的交易也具有直接规范性。私法上的法律行为也不能违背这种国家法律秩序的基本结构(Ordnungsgefuge)”。参见BAGE1,185,193f.转引自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基本权利总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8—40页。张千帆教授将这种保障模式描述为“机制保障”。张千帆:《法国与德国宪政》,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32页。
(二)制度性保障理论的现代发展
1.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功能的提出
《德国基本法》确立了宪法秩序。 Basic Law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the Press and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998,pp15—26. 第19条第4款确立基本权利的“主观权利”地位,第1条、第19条第2款、第79条第3款确立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地位,基本权利约束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行为。其中,“‘客观价值是普遍与抽象适用的价值,它独立于任何具体关系,是普遍法律秩序的一部分”。PQ,Free Speech and Private Law in German Constitutional Theory,48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aw Review,247,347,261(1989)转引自前引B38张千帆书,第334页。
在德国,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发展不仅来源于《德国基本法》的规定,更得益于宪政实践的发展,宪法法院的判例阐释与宪法学说理论逐渐达成共识。在吕特案的判决中,宪法法院对基本权利的客观性质进行了如下说明:“这一价值秩序以社会团体中的人类的人性尊严和个性发展为核心,应当被看作是宪法的基本决定而对所有的法领域产生影响。立法、行政和司法都应该从这一价值秩序中获得行为准绳与驱动力”。张翔:《基本权利的规范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宪法法院在实践中发展了“价值客观秩序(Objective Order of Values)”的概念,要求政府去创造并维持有利于实现基本宪法价值的条件与环境,即“基本权作为一种客观价值决定,即使国家没有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基本权仍是客观的宪法价值决定,拘束国家的任何行为,拘束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在宪法上国家负有义务,必须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尽可能地落实基本权的保障”。Vgl.PHberle,Wertepluralismus und Wertewandel heute,München 1982;Jan Schapp,Grundrechte als Wertordnung,JZ 1998,S.913ff;Ralf Dreier,Rech-Staat-Vernunft,1.Aufl.,Frankfurt∕M.1991,S.73ff.转引自许育典:《文化宪法与文化国》,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2页。 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面向强调的是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在立法层面,强调国家的法律制度创设义务,强调国家不可以通过立法行为形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合法侵害,不可以侵害基本权利的核心部分;在行政层面,不仅要依法行政,而且要具有合理性与适当性;司法则要对立法、行政有效的监督。
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实效性,敦促国家基本权利保障义务的实际履行。从表层上看,得益于《德国基本法》的规定和德国宪政实践的发展;从深层上看,其理论根源来自于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合理内核。康拉德·黑塞对此做了深入论述,“基本权客观法的意义得以被提出,是制度性的保障(公法意义上的)以及制度保障(私法意义上的)理论的贡献,这一点已被联邦宪政法院采纳”。参见前引⑥,第226页注释④。
2.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功能的具体内容
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面向在德国的宪政实践中经历了一个渐次发展不断丰富的历程,发展出具体包括基本权利的放射效力(俗称的第三人效力)、基本权利作为组织与程序的保障、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三个方面的功能。同时,每一项内容又都经历了自身的发展。参见张嘉尹:《论价值秩序作为宪法学的基本概念》,载《“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台湾大学法律学系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十卷第五期,第11—15页。
第一,第三人效力的肯认和具体论述是通过著名的吕特案。关于吕特案参见前引B37张翔主编书,第20—47页。 联邦宪法法院关于吕特案的判决,堪称是确定基本权利客观价值面向的典范性判决。宪法法院认为:“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以人格及人性尊严在社会共同体中的自由发展为中心,应有效适用于各法律领域,自然也会影响民事法律;……民事法律的各个方面都必须在基本权利的检验下予以解释适用。”前引B37张翔主编书,第25页。 此即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准确地说应为基本权利的放射效力。前引B44,第12页。
第二,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同样是通过一系列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而确定的,具体由1972年大学招生名额案、1973年大学判决案、1977年招生名额第二案等确定了基本权利保护的国家制定相应组织与程序的义务。参见前引B37张翔主编书,第95—143页。在大学判决案中,宪法法院阐述道:“那些由《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款的价值决定所产生的基本权利主体有权要求国家采取包括组织方式在内的某些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其基本权利保障的自由空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唯此其自由的学术活动才成为可能。”前引B37张翔主编书,第124页。 1972年大学招生案中,宪法法院指出:“由自由选择教育地点(基本法第12条第1项)之基本权利导出各邦整体之补充义务,共同——例如经由缔结国家条约——担负协力实现基本权利保障的共同责任,借此所有入学名额透过一个跨区域性机构在适用统一的选择标准之下被分配。”BVerGE12,205(259ff.);57,295(319ff.);73,118(152ff.);74,297(325);83,238(195);87,181(196ff.);90,60(87ff.).参见[德]Christian Starck:《法学、宪法法院审判权与基本权利》,杨子慧、林三钦、陈爱娥、张娴安、李建良、许宗力等译,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83页。 由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衍生而来的国家保障基本权利的组织与程序职责确定,并成为基本权利实现不可或缺之内容。
第三,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到了8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最受瞩目的基本权利客观法内容。前引B44,第14—15页。 其中,促生该理论发展的具有建设性的案例有1975年第一次堕胎判决案、1993年第二次堕胎判决案等关涉人的生命权的案例。参见前引B37张翔主编书,第144—183页。 随着德国宪政实践的发展,该议题不断丰富。目前,依判例及学说之见解,系指“国家负有保护其国民之法益及宪法上所承认之制度的义务,特别是指国家负有保护国民之生命和健康、自由及财产等之义务。保护义务之表现形态为立法者制定规范、行政权执行保护性法律(包括行使裁量权)、宪法法院审查立法者及行政权之相关作为及不作为,普通法院审理相关案件并做成裁判。”参见前引B50Christian Starck书,第411—412页。 当然,这是持广义理解的视角。
3.制度性保障理论与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功能理论在功能上的契合
在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功能的关系阐述中,目前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制度性保障成为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功能体系的一环”,何勤华、张海斌主编:《西方宪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70—571页。 有学者将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即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保护义务三个层面。参见前引B41,第114—122页。其中,保护义务分为狭义、广义两种,狭义的保护义务仅指国家保护公民免受第三方侵害的义务;广义的保护义务是指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所针对的国家的所有义务,包括制度性保障义务、组织与程序保障义务以及其他各种排除妨碍的义务。当然此处采用的是狭义概念。 即在基本权利功能体系的发展中,制度性保障成为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功能之一。
另一种观点由德国Peter Haeberle 与Ernst-Wlfgang Bckenforde 两位学者的观点延展而来。他们认为,新的“制度性保障功能不仅适用于每一基本权利,同时也课予立法者积极去形成、保护的义务,不再是消极的‘现状的担保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已有若干判决受到这种新的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影响(例如BVerfGE 12,205,259;20,162,175;35,79,114),使得制度性保障与受益权功能、保护义务功能以及程序保障功能产生相当程度的功能重叠。参见前引B17许宗力书,第204页注释16。 因此,随着德国宪政实践的发展,“立法机关必须通过制定法律来建构制度,以进一步明确宪法上基本权利的具体内涵,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基本权利所具备的这种积极要求立法者建立和维护制度,以促进基本权利实现的功能,就是所谓制度性保障(Institutionelle Garantien)的功能,国家对此负有制度性保障的义务”Michael Sachs, Verfassungsrecht∥Grundrechte,Berlin u.a.Springer,2000.S49.ff.转引自前引B41张翔书,第114页。 的观点已成通识。可见,制度性保障的内涵在发展中逐渐丰富,涵摄了客观价值秩序的其他功能或者说与客观价值秩序功能重叠共生。
在基本权利保护的实践运行中,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国家保护公民免受来自第三方的侵害的保障等概念很难做出实质的界分,在某些情况下互相存在很大的交集,并有相混淆的态势。因此,有学者将制度性保障分为广义、狭义两种,“狭义的制度性保障单指组织与程序保障;广义的制度性保障则包含现代意义上国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应履行的组织与程序保障、国家的给付义务、受益权功能等所有义务。如将制度性保障作为组织与程序保障、国家的给付义务、受益权功能的上位概念可能更有利于理论上概念的澄清”。参见前引B17许宗力书,第204页。
从学说发展的层面上讲,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与制度性保障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学说体系,有各自的生成背景和价值涵摄,其内涵都随着宪政实践的发展而渐次丰富。在基本权利保护面向上,二者的功能似乎渐趋一致,但对二者作为宪法学说的独立性并无本质影响。同时,制度性保障理论对《德国基本法》的诞生及其确立的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虽然随着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兴起,制度性保障理论式微,但其在德国宪法学乃至世界宪法学中的理论价值及在宪法学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且被宪法学说发展所证立。
三、制度性保障理论的现代价值
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形成以法律可以架空宪法的“立法主权主义”为背景,卡尔·施米特阐明了《魏玛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不具有宪法实效性的根本原因,阐释了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宪法学内涵并创建了“宪法学说”。作为一种宪法学说,对《德国基本法》宪法秩序的确立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如果说基本法是站在《魏玛宪法》的肩上,不如说是深受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启发。该法所涵摄的宪法与普通法律明确界分、第79条规定的即使是修宪也不可更改的条款、宪法对立法者的约束等宪法秩序原理均得益于卡尔·施米特的思想。二战后,其宪法学说被广为认同。参见前引⑦,第9—10页。
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宪法学学说价值及其对国家具体制度构建的指导意义在于其由近及远、从部分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思索和制度创设。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制度层面,其思考均是严谨而深远的。其着眼点在于对某一具体制度基于其宪法位阶的保障,但其所包含的宏大思想则在于国家与宪法的关系,并且是在后者能够巩固前者的意义上解释后者。参见前引B11乔治·施瓦布书,第10页。 对法治后发国家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宪法文本的实施提供解释的媒介,以区分并强化宪法与法律不同位阶的观念及推动宪法的实证效力,使位于或应然位于宪法位阶的制度得以保护;对不尊重宪法的立法者予以权力限缩。在宪法学说及宪法实施机制成熟的情况下,则在宪法学说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严谨的宪法、法律制度建构,合理地限缩国家立法权,避免法律层面上合法性与适当性的混同,以免国家以合法的方式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合理地限制行政权力,使行政权力的运行不仅具有合法性而且具有适当性;合理地设置司法权力,以实现对立法、行政的有效监督,使司法成为宪法的守护者。国家通过严谨的宪法、法律制度建构,使公民基本权利成为切实的实有权利。
(一)具有 “进化论”法治的典型特征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中指出,人类制度有两种产生方式,一是为实现人的目的而刻意设计出来的,二是社会的有序性并非由发明或设计出来的制度所致,而是进化的过程促成的。参见[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在进化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制度属于“一种源于内部的(endogenously)均衡,为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前引B61,第55页。 依据哈耶克的社会秩序理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发展亦可分为“进化”模式发展和“建构”模式发展两种路径。“‘进化论强调法律的进步依赖社会自身的自发的自治力量实现法律制度演化,认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人民群众的呼唤和参与,是法律演进与发展的真正动力,也是避免法治文明出现逆转的根本保证;‘建构论则更重视通过人为的理性建构实现法律制度的变迁与进步,特别赞赏在法律制度的变革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页。 由于“进化论”法治是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基于其自身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法律制度本身具有某种程度的内生性,社会个体更易于接受和遵守,因此,也更有利于国家法治化进程的进化和发展。从法治发展路径模式划分的角度讲,制度性保障机制与进化论法治发展路径相契合,属于进化论法治发展模式。
(二)以宪法实施为基础
制度性保障是宪法保障,是一种以宪法实施为基础的保障。原初意义上的制度性保障要求国家立法者不得侵犯宪法所肯认的制度的核心性内容。现代意义上的制度性保障以宪法直接实施为基础,通过宪法司法化检验立法、行政是否违宪,以保证国家“合宪性秩序”为基础的基本权利保障方式。在此,基本权利保护的展开以宪法实施为基础,以国家合宪性的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生成与运行为纽带,体现为一种严密的制度设计理念与机制。制度性保障作为一种宪法学说理论,理论价值及实现基础在于其体现为宪法保障,以宪法实施为基础,这是现代宪政民主国家法治文明的基石。
(三)强化国家义务的基本权利保护机制
依据德国学者Christian Starck在《法学、宪法法院审判权与基本权利》一书中的阐述,国家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含义及形态可做如下表述:“基本权利之保护义务,依判例及学说之见解,系指国家负有保护其国民之法益及宪法上所承认之制度的义务,特别是指国家负有保护国民之生命和健康、自由及财产等之义务”。“保护义务之表现形态,乃指立法者有制定规范之任务,行政权负有执行保护性法律之义务,宪法法院以保护义务为标准,审查立法者及行政权之相关作为及不作为,普通法院以保护义务为准则审理案件,并做成裁判”。参见前引B50Christian Starck书,第411—412页。 制度性保障的功能正是要求国家立法者积极立法、型塑制度,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司法机关依法受案、裁判以保障基本权利的实现。而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国家行为无不以宪法所确定的规范条款及价值为判断基准。
(四)为国家立法设置合理边界
从宪法学学说的角度讲,国家依据人民的委托而存在,政府依据人民的选举而产生,权力由权利所赋予。但国家作为一种掌握权力的强大力量,如其建构法律制度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则很容易产生国家以合法的方式侵犯社会个体权利的结果。国家合法侵害权的存在是法治后发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制度性保障学说则为有效防止立法者通过建构法律侵害公民权利提供了思考路径。尤其在我国,“享有立法权的主体极其广泛,行政规章甚至政府的‘红头文件都在实践中发挥着法律规范的作用,司法解释也发挥着重要的补充立法的作用”,前引①任喜荣文,第7页。 在此种情况下,如何约束立法主体的立法行为,促成“良法”的生成,防止“恶法”亦法,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四、结语:对我国宪法实施的启示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立法层面存在或多或少的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合法侵害现象;行政权力的行使虽然具有合法性但存在不具适当性或权力架空法律而无有效约束与规制的问题;司法还远未发挥其宪法守护者的职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才将“依宪治国”作为重要方略予以提出,并逐步落实,足见我国加强宪法实施的决心。但宪法实施是目的、是方针、是价值指引,宪法实效性的切实贯彻是一个逐渐发展夯实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亦不是空洞的宣誓与口号,其落实需要具体的制度设计与媒介,需要宪法学说理论的探讨、求证与支撑。在尊重宪法文本的前提下,宪法解释对推动宪法实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宪法实施的深入,相应的理论跟进、制度设计、观念转变则为应然与必然。在此背景下,制度性保障理论的生发脉络及其蕴含的宪法学说思想即可为我国当下宪法的实施提供解释理路,又可为宪法领域的学说探讨及长远的宪法、法律制度建构提供框架性思考路径。
制度性保障理论的生发源流给我国宪法实施的另一深远启示是,宪法的实证性需要一个过程,其需要宪法学说理论发展的完善,亦需要社会发展的因应。如果借用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点,参见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张逸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 中国宪法的实施同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发展一样,其所经历的波折具有历史必然性、不可逾越性、不可或缺性。从国家法治建设的角度而言,如果将宪法实施类比于国家的“上层”建构,其他法律制度机制——比如司法的建构就好比“下层”,则需要“下层”与“上层”的契合因应,才能切实推动“上层”的发展。如果二者相互割裂,“下层”无法因应“上层”,则“上层”的制度设计是无法正常良性运转的,只能导致差强人意的结果。比如我国刑事司法方面的法律制度不可谓不健全,但在刑事证据的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保护、刑事审判中律师、法官职能的发挥等方面都远没有达到制度设计的初衷,“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处于优势地位,消减了刑事法律制度的实效性。参见陈瑞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 《魏玛宪法》实施的失败及《德国基本法》的成功均证明了这一论点。即宪法文本不会凭空实施,其践行需要成熟的社会土壤、制度土壤和学说支撑。面对中国当下的问题,“既要不断返回问题的源头,重读经典,又要对古典思想发展,以现代的问题意识为归依”,前引⑦,总序第5页。 寻找理论与现实的契合。
我国对宪法实施的探索远可以追溯到清末,至今一直在冥想探求宪政民主的问题,也一直在进行法律、社会的重整再造工作。对于前者的探究仍在进行之中,而后者的逐步推进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亦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回溯历史,我们发现,无论是下层法律制度的发展建设,还是上层宪政民主制度的实施,均是渐进的过程,而且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可能是缓慢的过程。展望未来,以宪法实施为核心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法治终究会实现。这既是一种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与应然结果,亦是宪法学术研究上应采纳的一种“大历史”观点与视野。
Abstract: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is a dominant theory among German constitutional theories where its constitutional thoughts have profound impact on German basic laws. This theory has developed from the traditional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to“ system as a basic right ”, which has generated the objective value order of the basic rights.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theory indic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al theories and co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 is a gradual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rule of law. Thus, this theory has provided a path for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texts and a macro-development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ruling of law.
Key words:institutional guarantee basic rights objective value order national duty of protection